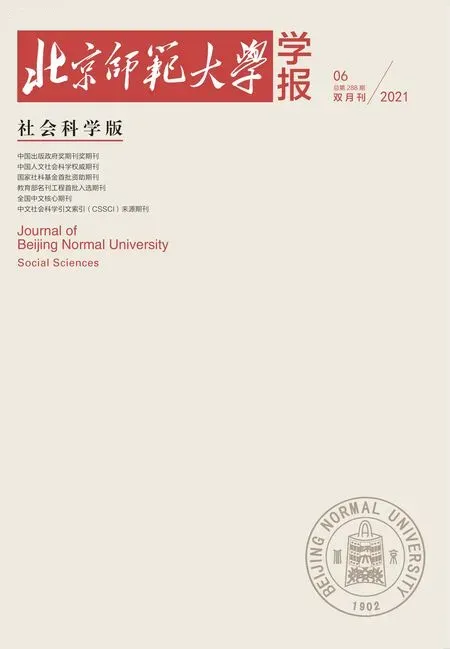《诗经》中的“天”、“下土”与“地”
——早期“天地”观念溯源
翟奎凤
山东大学 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儒学高等研究院,济南 250100
郭沫若认为西周金文中无“地”字,“以天地相对立的这种观念在春秋以前是没有的”(1)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青铜时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1页。。而陈梦家认为“天地上下对立的观念发生很早”,“周人称上下,殷人称下上,都是上天下地之意”,“上下牝牡对立的观念,始于殷契,亦见于周金;天地对立,见于《诗经》。金文没有天地对举,并非无此观念,乃因铭辞上无此需要”(2)陈梦家:《郭沫若〈周易的构成时代〉书后》,《陈梦家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22页。。陈梦家反驳郭沫若的观点最为重要的文本依据是《诗经》。《诗经》中“地”字两见,而且出现“天高地厚”之天地对举的观念;《诗经》中也多次出现“上天”与“下土”相对的诗句,“天”、“土”对举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始源性天地观念。但是《诗经》中出现“地”及“天”、“土”对举的诗篇,其年代需要再斟酌,有可能是作于或修订于春秋时期。
《诗经》成书应当是一个漫长累积的动态过程(3)参见陈一平:《先秦古诗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8页。。陆侃如认为《诗经》各篇的成书时间约从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500年(4)陆侃如:《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74页。具体说来,陆侃如认为“《颂》的年代是自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600年”(第185页)、“《风》和《南》的一部分的年代是自公元前770至公元前510年”(第199页)、“《雅》的一部分的年代是公元前827年(宣王即位)至公元前697年(桓王崩)”(第191页)。,美国汉学家柯马丁(Martin Kern)认为,“传世《诗经》和《尚书》的早期文本层中的古典词汇、用词选择和思想总体上都与西周晚期(不包括早期)和春秋早期的青铜器铭文证据相契合”(5)〔美〕柯马丁(Martin Kern):《从青铜器铭文、〈诗经〉及〈尚书〉看西周祖先祭祀的演变》,陈彦辉、赵雨柔译,《国际汉学》,2019年第1期,第27-28页。。《诗经》文本也经过多次统一润色,这种修订可能一直持续到战国时期(6)参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关于〈诗经〉的征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余冠英:《关于改“诗”问题:讨论〈诗经〉文字曾否经过修改的一封信》,《文学评论》,1963年第1期。。本文持谨慎与弹性的观点来看待《诗经》成书,通过其中的“五天”(“皇天”、“旻天”、“昊天”、“苍天”、“上天”),以及“下土”与“地”这些词语(7)《诗经》中的“天”字共出现169次,按出现的频次来统计的话,昊天26次、天子21次、天命九次(天之命一次)、苍天九次(苍者天三次)、旻天三次、上天三次、天下一次(天之下两次)、皇天两次。《诗经》中还有一些“天”完全是在自然之天意义上(如天空、星空、天气)来说的,有一处是在与“地”相对时出现的。来讨论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天”观念的变化与“天地”观念的形成。
一般来说,上帝为殷人的最高主宰神,而天为周人最高神。“天”在西周时期是人格神,有意志性和主宰性。从《诗经》来看,大概是到了西周晚期或东周早期,天拥有了自然天空义、星空义、天气义乃至哲学义,并逐步形成天地观念。由绝对意义上的最高神之天,到相对意义上的天地观念的形成,是早期中国哲学发展的重大突破,其思想史意义正可谓“开天辟地”。
一、神格义的“皇天”、“天”
在西周金文和《尚书·周书》中,“皇天”一词常见,“旻天”也出现过,但没有“昊天”一词。《诗经》与今文《尚书》和西周金文的情况几乎相反,“昊天”多达26次,而皇天、旻天仅仅各出现两次和三次。“皇天”、“旻天”为西周古老用语,“昊天”一词应当是西周晚期或春秋时期才出现。“皇天”、“旻天”作为人格神,其情感性、意志性很强,相对来说,“昊天”有了一定的自然性。
“皇天”见于《诗经》两次,分别是《周颂·雝》和《大雅·抑》。《雝》“是周王祭祀宗庙后撤去祭品祭器所唱的乐歌”(8)高亨:《诗经今注》,《高亨著作集林》,第三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58页。,其中说“假哉皇考,绥予孝子。宣哲维人,文武维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燕及皇天”的意思是说“文王能事上帝,使之安乐,故能昌大其后嗣也”(9)屈万里:《诗经诠释》,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第427页。。《大雅·抑》据说是春秋早期卫武公在九十多岁做周平王卿士时所作的诗,其内容是劝诫平王,并以此自警(10)参见刘毓庆、李蹊译注:《诗经》,(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55页。《抑》中也同时出现了“昊天”两次,后面会具体论及。。诗中说“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无沦胥以亡”,意思是上天不再保佑,一切就像那泉流逝去,很快就会垮台。可见,“皇天”是主宰之天。
《诗经》中“旻天”出现三次,分别见于《大雅·召旻》、《小雅·小旻》、《小雅·雨无正》。一般认为这三首诗都是讥刺、抨击幽王无道。《召旻》中说“旻天疾威,天笃降丧。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小旻》中说“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谋犹回遹,何日斯沮”。《雨无正》说“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旻天疾威,弗虑弗图。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此中“旻”字,有些本子作“昊”,认为既然开篇说“浩浩昊天”,后面也当作“昊天疾威”(11)参见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十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30页下校勘记。。实际上,《雨无正》与《召旻》、《小旻》一样当作“旻天疾威”。对此,明末张次仲认为,“人穷则呼天,故首章以天发端。《说文》‘元气广大则称昊天,仁覆悯下则称旻天’。昊天则宜骏德,旻天则不宜疾威,今皆反是,诗人所以呼而告之”(12)张次仲:《待轩诗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2册,1986年,第1949页。。传统上多认为“旻天”本义是上天很仁慈,“旻天疾威”是说天隐匿了仁慈,表现得很可怕,而且善恶不分(弗虑弗图)。“疾威”在《诗经》中出现四次,另一次是《大雅·荡》中所说的“疾威上帝,其命多辟”时。前者“疾威”应作统一解释,但是在《诗经正义》中毛传、郑笺并不一致,如解释《荡》“疾威上帝,其命多辟”时,毛传说“疾病人矣,威罪人矣”,郑玄笺云:“疾病人者,重赋敛也。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又多邪辟,不由旧章”(13)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十八,第1154、1264页。;解释《召旻》“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瘨我饥馑,民卒流亡”时,郑笺云:“天,斥王也。疾,犹急也。瘨,病也。病乎幽王之为政也,急行暴虐之法,厚下丧乱之教,谓重赋税也。病中国以饥馑,令民尽流移”(14)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十八,第1154、1264页。;《小旻》“旻天疾威,敷于下土”,郑笺云:“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罚威恐万民,其政教乃布于下土。言天下遍知”(15)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十二,第737页。。这样“疾”就有三义:“疾病”、“急行”、“厌恶”。“疾”当取“急速”、“厉”、“过分”义,“疾威”近于暴虐,但是直接说成“暴虐”又有些重。清初钱澄之注《召旻》“旻天疾威,天笃降丧”时说,“疾,犹急也。谓天以仁闵为德,今急行威怒,天笃降丧,以下皆疾威之”(16)钱澄之:《钱澄之全集之二·田间诗学》,朱一清校点,余国庆、诸伟奇审订,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第852页。。这与张次仲的观点类似,“急行威怒”比较贴近“疾威”的字面意思。当然,这四首诗表面上是说“旻天”、“上帝”,诚如郑玄所说,实际上是批评君王无道。
西周中晚期或春秋早期的毛公鼎(17)参见张世贤:《从毛公鼎的真伪鉴别展望中国古器物学的研究》,(下),《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1995年第1期。中也有“敃天疾畏”一语。一般认为“疾畏”即“疾威”,“敃”与“旻”通(18)顾颉刚则认为“旻”本作“敃”,是打击之义,那就有威猛、威严乃至凶狠的意思,与传统上认为的仁闵之义恰恰相反了,作“威猛”讲也能直接契合《诗经》“旻天疾威”的语意(顾颉刚:《浪口村随笔》卷三《旻天、昊天》,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4页)。但是,《孟子·万章上》、《尚书·大禹谟》“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这里“旻天”还是当作仁闵来讲更为通顺。如果这样的话,“敃天”与“旻天”似乎可以被看作是两个词组,又不宜直接将其等同。。据说西周晚期的师询簋,其铭文也称“今旻天疾畏降丧”(19)参见何景成:《论师询簋的史实和年代》,《南方文物》,2008年第4期。,这与《召旻》“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的说法非常接近。由此看来,“旻天疾威”似是西周后期的常用语(20)参见陈民镇:《清华简〈摄命〉性质小议》,“清华简入藏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会议论文,2018年。。《逸周书·祭公解》中也载穆王说“祖祭公,次予小子虔虔在位!昊天疾威,予多时溥愆。我闻祖不豫有加,予惟敬省。不吊天降疾病,予畏之威。公其告予懿德”(21)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37页。,这里作“昊天疾威”。《清华简·祭公之顾命》与《逸周书·祭公解》是同一文献,但文字表述有些出入。《祭公之顾命》说:“祖祭公,哀余小子,昧其在位,旻天疾威,余多时假惩。我闻祖不豫有迟,余惟时来见,不淑疾甚,余畏天之作威。公其告我懿德”(22)李学勤: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174页。,这里作“旻天疾威”。因此,与“疾威”连用当为“旻天”。
在《诗经》诸“天”中,从历史出现的前后顺序来看,“皇天”当为最早,其次是“旻天”,就后世的一般理解而言,“皇”有大、光的意象,“旻”取其仁慈义。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中说:“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这与《诗经》中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旻天”在义理上是贯通的。“皇天”的神圣性更强,而“旻天”一词则突显了其德性义。
二、兼具神格义与自然义的“昊天”
“昊天”不见于金文,全部今古文《尚书》中,仅《尧典》一处用到“昊天”(“钦若昊天,敬授民时”),而《尧典》在近现代以来的研究中又多被认为其为晚出,文本写定应当在西周以后(23)顾颉刚在1923年作《尧典皋陶谟辨伪》一文(载《古史辨》第一册),举出八个方面的证据,论证《尧典》和《皋陶谟》的晚出,《尧典》等篇的时代问题随即成为当时的热点。对“古史辨”的成果,徐旭生在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6页)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评价:“疑古学派最大的功绩,是把《尚书》头三篇(即《尧典》、《皋陶谟》和《禹贡》)的写定归之于春秋和战国的时候。”参见李山:《〈尧典〉的写制时代》,《文学遗产》,2014年第4期,第28页,注1。按:今文《尚书》之《尧典》、《舜典》、《皋陶谟》,及古文《尚书·大禹谟》皆以“曰若稽古”开篇,意味着此文本为后人追述。。因此,西周时期可能没有“昊天”一词。《诗经·周颂》出现两处“昊天”,其一为《昊天有成命》,这是一篇祭祀成王的乐歌,开篇说“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成命”是既定、明确、坚定的命令(24)日本学者家井真认为,“成命”与盛命同义,类此“成命” 亦与毛公鼎中“大命”同义。参见:〔日〕家井真:《〈诗经〉原意研究》,陆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4页。,当然这种命是一种权命、福命,让文王、武王接管天下政权,成王不敢安于享乐,早晚奉行天命,丝毫不敢懈怠。其二为《时迈》,据说这是首讲武王巡视诸侯国、祭祀山川的乐歌,其中说“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右序”是帮助的意思。实际上,这两处“昊天”若改成“皇天”,意思并无影响,甚至可能更符合周初的用语习惯。
“昊天”在大小《雅》中分别出现13次、11次,这些诗歌多作于西周晚期昏庸无道的厉王、幽王时期,多属于传统上所谓的“怨诗”,主要表达对君王的批判与不满。人们在遭遇自然灾难和社会不公所带来的生存痛苦时,往往对上天也会有某种怀疑甚至埋怨。《大雅·云汉》是叙述周宣王遭遇大旱时向天诉苦、求神祈雨的诗,里面出现三次“昊天上帝”的说法:“昊天上帝,则不我遗”、“昊天上帝,宁俾我遁”、“昊天上帝,则我不虞”,其大概意思是,大旱持续了这么长时间,“昊天上帝”为什么一点不体察、关心世人的煎熬。“昊天上帝”的说法也见于《逸周书·克殷解》、《周礼·春官宗伯》、《左传·成公十三年》。“皇天上帝”的说法则在先秦更为多见,《尚书·召诰》、《礼记·月令》、《大戴礼记·盛德篇》中都有出现。西周金文中多见“皇上帝”、“皇帝”的说法,而目前金文中无“昊天”一词,因此,“皇天上帝”的说法应当在前,“昊天上帝”是后起的。
《小雅·节南山》两次出现“不吊昊天”的说法:“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不吊昊天,乱靡有定”。“不吊”的意思是上天不慈悲且太狠心,表达的是人们对发生不幸之事的惋惜之情或悲痛之情。这种类似表述,也见于今文《尚书·周书》:“弗吊天降割于我家”(《大诰》)、“弗吊旻天,大降丧于殷”(《多士》)、“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君奭》)。《逸周书·祭公解》也说“不吊天降疾病,予畏天威”。《左传·哀公十六年》载孔子去世时,鲁哀公在悼词中说“旻天不吊,不憖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史记·孔子家语》、《汉书·五行志》记述与此同)。《孔子家语·终记解》也有同样的记述,但是作“昊天不吊”。由此,可以推测,“不(弗)吊旻天”的说法更为古老。结合《周书·多士》来看,《节南山》“不吊昊天”写作“不吊旻天”似乎更为合适,这一点与“旻天疾威”的情况类似,“旻”与“昊”在古籍中似很早就出现了混用。
与“不吊昊天”的表述相类似,《节南山》中还有“昊天不佣,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昊天不平,我王不宁”的诗句。《小雅·雨无正》也说“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25)“昊天罔极”,郑玄理解为“我心无极”、朱熹解读为“恩大如天”,王念孙、王引之认为是“昊天不惠”的意思。彭慧发挥王氏父子的观点,认为“昊天罔极”犹言“昊天无常”,是诗人对天发出的怨愤之词。参见彭慧:《〈诗经·小雅·蓼莪〉“昊天罔极” 释义辨补》,《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这种“怨天”思想在《大雅》中也多见,如《云汉》“昊天上帝,则不我遗”、“昊天上帝,宁俾我遁”、“昊天上帝,则我不虞”,《瞻卬》“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桑柔》“倬彼昊天,宁不我矜”。过去多认为这些表达的是一种怨天的思想,即人们遭遇灾难、不幸与巨大痛苦时对天道公平的一种怀疑。但我们并不能说那时人们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天命信仰,与其将其看作是对天的埋怨,不如说是苦难中的人们对天的悲情倾诉与呼喊;人们内心还是希望能感通上天,以扭转厄运与苦难。《小雅·巧言》中说:“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无罪无辜,乱如此怃。昊天已威,予慎无罪。昊天泰怃,予慎无辜”。“已威”与“疾威”类似,意思是上天太可怕,“泰怃”则是指上天太荒唐。这实际上是人们在遭遇不平、处于极度痛苦时内心深处对上天的呼喊。《巧言》以“父母”与“天”比拟,类似的,《鄘风·柏舟》也说“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这里以“母”与“天”相比拟(26)在“母也天只”、“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的观念中,还没有“地”的观念,后来(战国或春秋中晚期)“天父、地母”的观念非常流行,可能导源于此。。古文《尚书·大禹谟》说“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孟子在与学生万章讨论此句时,认为大舜“号泣于旻天”是孝子“怨慕”心态的流露(《孟子·万章上》),所谓“怨慕”即“哀怨不得其亲而啼呼”(27)黄群建:《古代词义例话》,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5年,第145页。。《诗经》中有不少传统上认为的怨天之诗多与“旻天”、“昊天”相关联。一方面,这些诗实际上是批评君王;另一方面,诗人对天的态度与其说是怀疑,不如说是这种“怨慕”的心态,当然这种心情往往是极度痛苦的。
《大雅》中“昊天”常与光明、察照之象密切关联,如《大雅·板》说:“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意思是要敬畏上天,不要懈怠放纵,昊天之明时时刻刻都在察照我们(28)这句话蕴含的修身意识很强。后来儒者如宋代张载、明代湛若水,一直到现代新儒家熊十力,他们谈修身都引述到这句诗。。《大雅·抑》中的“昊天孔昭,我生靡乐”、“取譬不远,昊天不忒”大意是:昊天非常明亮,记着世间的善善恶恶;因无德而倒台的君王很多,应汲取教训,上天的报应和惩罚从不差错。
与“皇天”具有绝对神格性相比,“昊天”既有神格性一面(这点类似皇天),同时也有自然性一面(这是皇天一词所不具备的)。自然意义上的“昊天”,最为典型的就是《大雅·云汉》中所说的“瞻卬昊天,有嘒其星”,这里“昊天”显然就是指高高在上的天空、星空。在一些诗句中,昊天与皇天、旻天互换,似乎语义并无多大影响,甚至可能更为贴切,但是在“瞻卬昊天,有嘒其星”的诗句中,如果用“皇天”或“旻天”,则明显不宜。“昊”有广大、高大义,有空间无限的意象,虽然也有神格义,但同时有了空间性和自然义的一面。
三、苍天、自然之天及“天”、“渊”对举
“苍天”一词在《诗经》中出现的频次仅次于“昊天”,达11次之多,其中《小雅·巷伯》两次,《王风·黍离》三次、《唐风·鸨羽》三次,《秦风·黄鸟》“苍者天”三次。
《小雅·巷伯》说“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毛序》说“《巷伯》,刺幽王也。寺人伤于谗,故作是诗也”(29)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卷十二,第766页。,这是宫中侍御小臣孟子作的怨诗,表达了对进谗者的憎恶,呼告上天去审视那骄横者的罪恶,可怜这忧愁者的苦痛(30)刘毓庆、李蹊译注:《诗经》,(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36页。;“骄人”是指那些进谗言陷害忠良的邪恶之人。这首诗连用两个“苍天”,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希望苍天有眼,主持世间公道。《王风·黍离》“很可能是一个因故出亡的人(或许是贵族)诉说他的忧苦的诗”(31)刘毓庆、李蹊译注:《诗经》,(上),第177页。,诗中三段咏叹均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结尾,表达了作者无处诉说的苦闷、忧愁与伤感。《唐风·鸨羽》三段也是分别以“悠悠苍天,曷其有所”、“悠悠苍天,曷其有极”、“悠悠苍天,曷其有常”结尾。这是一首服役者的悲愤之诗,诗人在艰难的服役中,想到家中父母无人照料,甚至没有吃喝,心中万分焦急,而又无可奈何,他无助地呼喊着茫茫苍天(32)参见刘毓庆、李蹊译注:《诗经》,(上),第297页。,希望没完没了的劳役快些结束,早日回到家乡照顾父母。《左传·文公六年》(公元前621年)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秦穆公去世,竟以三位心爱的大将殉葬,国人对此哀痛无比,这是《秦风·黄鸟》的历史背景。诗中三段结尾皆哀叹曰:“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诗经》中还有“穹苍”一词,《大雅·桑柔》(33)《毛序》说“《桑柔》,芮伯刺厉王也”,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十八,第1177页。中说:“哀恫中国,具赘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苍”,其中,“念”有呼告之义,也含有悲悯苦痛之情;“穹苍”虽然仍有神格意味,但从字面上看已有自然空间义。穹苍与苍天的意思很接近,孔颖达据《尔雅·释天》“穹,苍苍,天也”,认为“穹苍”即“苍天”(34)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十八,第1185页。。
以上五首诗中的“苍天”或“穹苍”都笼罩在忧伤、痛苦、悲伤、悲痛的感情中。《诗经》中“苍天”多与“悠悠”连用,“悠悠”形容了时间的久远和空间的广大,有一种无限绵延性、幽深性,同时也表示一种无尽的思绪、忧愁与悲伤。在先秦两汉,对《诗经》“苍天”和“穹苍”诗句的引用仅见于西汉时期的《韩诗外传》、《说苑》和《新序》,战国典籍没有引述过。《尚书》、《逸周书》、《左传》、《国语》均不见“苍天”一词。《诗经》中的“苍天”、“穹苍”虽字面上有感官空间自然义,但实际上还是指一种有情感意志的人格神,这种用法在战国文献中也极少见。战国后期,作为自然意义的“苍天”时见于多种典籍,这些语境下的苍天神格性弱化,更多是一种自然意义上的天空义了。神格义的苍天当在前,自然义的苍天为后起。就此而言,《诗经》之苍天可能是春秋时用语,也可能是战国早期才出现。
纯自然之天的观念在《大雅》中多有流露,《旱麓》中说“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其中“戾”是至、冲上的意思,雄鹰在天空展翅高翔,鱼儿在水底翻跃嬉戏(35)《中庸》引此诗句说“言其上下察也”,宋明理学常以“鸢飞鱼跃”来形容生动活泼、生机盎然的精神气象。。“戾天”一词在《小雅》中也多次出现,如《采芑》中说“鴥彼飞隼,其飞戾天,亦集爰止”,《小宛》中说“宛彼鸣鸠,翰飞戾天”,《四月》中说“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鳝匪鲔,潜逃于渊”。类似的,《大雅·卷阿》“凤凰于飞,翽翽其羽,亦傅于天”,《小雅·菀柳》“有鸟高飞,亦傅于天”,这里“傅”与“戾”意思相近,都是上达、迫近的意思。《小雅·鹤鸣》也说:“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显然,这些“天”都是自然意义上的天空、高空。随着天的自然化、空间化,潜在地可以说有“天”就有“地”,“地”与“天”、“地”对举的观念相伴而生。从上面来看,大小《雅》中三次出现“天”、“渊”对举的诗句,从宽泛意义上来讲,这也是一种天地观念的相近表述。有意思的是,《易经》爻辞中也有几处自然之天的用法,而且在语句表述上与《诗经》有相似之处。如乾卦九四爻辞“或跃在渊”、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里也是“天”、“渊”对举;中孚卦上九爻辞“翰音登于天”,类似《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大畜卦上九爻辞“何天之衢,亨”,《诗经·商颂·长发》也有“何天之休”一语。因此,《易经》爻辞与《诗经》中诗句的形成时代有接近性。陆侃如认为,卦爻辞到东周中年(约公元前500年)才写定(36)当然,陆侃如也指出,“我们须知,《易卦爻辞》的产生与写定是两件事。这部‘卜筮之书’的起源或在商、周之际,所以研究历史的人尽可依赖它来讲古代社会;迨经过数百年的口耳流传,到东周中年方写定,所以研究文学史的人却不能根据它来讲周初的散文或韵文”(陆侃如:《论〈卦爻辞〉的年代》,《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5页)。,《诗经》主体文本的形成年代可能大致也在同一时期。
《大雅》中自然之天还有多处,如《崧高》中说“崧高维岳,骏极于天”,其中“骏”为高大,“骏极于天”是高耸入云的意思。在《云汉》“倬彼云汉,昭回于天”以及《棫朴》“倬彼云汉,为章于天”中,“倬”有大而明、鲜明、灿烂的意思,云汉指银河,这里的天即天空、星空。类似的,以天为天空、星空,论及银河的还有《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这里的“天毕”指天上的毕星,其象如田猎时的捕兽网。关于这种星空意义上的天,《唐风·绸缪》中也说“绸缪束薪,三星在天”。此外,《诗经》中还有一种自然之天,是从天气、气象上来说的,如《小雅·信南山》中说“上天同云,雨雪雰雰”,其中“同云”是阴云密布的意思(37)《小雅·信南山》“上天同云,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疆场翼翼,黍稷彧彧。曾孙之穑,以为酒食。畀我尸宾,寿考万年”。《易传》需卦大象辞“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可能受到此诗句的影响,两者在意象和用语上非常相似。。《豳风·鸱鸮》中也说“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这些自然意义上的天的观念也应该是在春秋时期衍化出的。《诗经》中已出现雨雪、云雨意义上的天气之天,但“天”与春夏秋冬四时的关联,即四时意义上的天似乎没有出现。
四、“上天”、“下土”与“天地”观念之形成
《诗经》于大小《雅》中三次用到“上天”一词,如《大雅·文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小雅·信南山》“上天同云,雨雪雰雰”、《小雅·小明》“明明上天,照临下土”。不少学者认为,《大雅·文王》作于周初,然而两周金文并无“上天”一词(38)西周时期最高神的称呼有“天”、“皇天”、“皇天王”、“帝”、“上帝”、“皇帝”、“皇上帝”,这些称呼也基本见于《尚书》。。《尚书·商书》之《仲虺之诰》“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汤诰》“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贲若草木,兆民允殖”,《周书》之《泰誓上》“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这三篇全部见于晚出的古文《尚书》(这三处大体上皆以“上天”与“下民”相对),也就是说,今文《尚书》没有“上天”一词。西周时期可能没有“上天”一词,其出现大概在春秋时期。《礼记·中庸》、《韩诗外传》都引述到《大雅·文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表示一种很高的境界。其中,“载”是“事”、运行的意思,郑玄说“天之道,难知也。耳不闻声音,鼻不闻香臭”(39)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十六,第965页。。在宋代,张载、二程、朱熹等很多大儒在其理学思想建构中多引用“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宋儒非常乐于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来诠释天道本体。《诗经》原文“上天之载”应当还是有宗教性的,但是宋儒接着《中庸》对其做了高度哲学化、本体化的解读。
与“上天之载”不同,“上天同云”、“明明上天”显然皆是指自然现象之天。“上天同云”为气象之天,意思是天上阴云满布。“明明上天,照临下土”是就日月之天而言。“下土”一词于《诗经》风雅颂凡八见,但是《尚书》只有《舜贡》说到“厥土惟壤,下土坟垆”,此与《诗经》中的“下土”意义也不一致,而且近人又多认为《舜贡》作于战国时期,两周金文铭文里似只有《哀成叔鼎》(年代约在公元前372年到公元前367年间)说到“哀成叔之鼎永用禋祀,(朽) 于下土,台(以)事康公”(40)参见赵振华:《哀成叔鼎的铭文与年代》,《文物》,1981年第7期,第69页。。《逸周书·祭公解》中说“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孙大开封方于下土”(41)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40页。,但是清华简《祭公之顾命》作“天子、三公,我亦上下譬于文武之受命,皇[甚冘]方邦”(42)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第174页。,没有“下土”一词。《墨子》引先王之书说到,“明哲维天,临君下土”(《天志中》)(43)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97页。,又引《商书》曰:“若能共允,隹天下之合,下土之葆”(44)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38页。(《明鬼下》)。《左传》没有“下土”一词,《国语·吴语》中载周王答夫差的话中有“不唯下土之不康靖”一语。那么,综合这些来看,“下土”一词很有可能是春秋时期才出现。
《诗经》中“下土”大概有水土、土地、国土、天下、下民、天地之地等方面的含义。《商颂·长发》中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楚辞·天问》云:“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下土方”即“下土四方”的意思,这里是讲大禹平治水土。《大雅·云汉》中的“耗斁下土,宁丁我躬”,是说宣王时天下大旱,长时间不下雨,大地都枯焦了,这里的“下土”指土地、大地。《鲁颂·宫》说“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其中“下土”是政权、国土意义上的天下。《大雅·下武》中说“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这里的“下土”也是指天下,但重点是说诸侯和民众要以成王为榜样。《小雅·小旻》说:“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此处的“下土”其实相当于《诗经》中常用的“下民”。《诗经》风雅颂中“下民”凡八见,今古文《尚书》中16见,春秋末期的“鱼鼎匕”中也有“下民”一词(45)参见吴镇烽:《“鱼鼎匕”新释》,《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2期。,可见该词应该比较古老。(上)天、(上)帝与(下)民相对在《诗》、《书》中是一种普遍性话语模式。然而这种“上”、“下”话语,后来更多是指上天、下地(下土)。《大雅·云汉》中说“上下尊瘗,靡神不宗”,这里的“上下”一般也理解为天神(上)、地祇(下)。
《邶风·日月》中说“日居月诸,照临下土”、“日居月诸,下土是冒”,这与《小雅·小明》中的“明明上天,照临下土”意思相同,明明之上天是指经验层面的日月之光。《清华简·耆夜》载周公赋诗《明明上帝》曰:“明明上帝,临下之光”(46)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第150页。,这句诗非常接近《大雅·皇矣》所说的“皇矣上帝,临下有赫”,这里的“明”与“皇”所形容之上帝之光超越了日月之光。西周金文里常有“皇上帝”一词,“皇矣上帝”当是对“皇上帝”的诗化处理(47)日本学者家井真也指出,“‘皇上帝’与《小雅·节南山之什·正月》‘有皇上帝’、《大雅·文王之什·皇矣》‘皇矣上帝’相近”。参见〔日〕家井真:《诗经原意研究》,第一章,陆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页。。《说苑·权谋》载孔子引《诗》曰:“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孔子家语·六本》引作 “皇皇上天,其命不忒”。“明明上天”有可能是由“皇皇上帝”演变而来的,并由绝对的神性之光过渡到经验的日月之光,进而“上天”开始与“下土”并提,形成了初步的天地观念。与此同时,“天”与“土”相对时,“天”的人格神、意志性、主宰义开始隐退,更多的是一种自然空间之天空义(当然,在神格义之外,“天”的内涵也非常丰富,衍化出很多哲理义和德性义,并非只有简单的感官空间天空义),同时,“天下”观念也自然形成(48)西周金文里唯“遂公盨”有“天下”二字,而遂公盨是2002年由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专家在海外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的,但是也有学者怀疑其为伪造。。《小雅·北山》中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里的“天下”、“土”、“臣民”关联出现,凸显的是王者的绝对权威性。
“上天”、“下土”可以被视为天地观念的雏形阶段,然而真正成熟的天地观念应该还是比较晚的。今文《尚书》中,“地”字三见:《商书·盘庚下》(49)《盘庚》的创作时代有盘庚时代说、小辛时代说、殷商时代说、殷周之际说、西周初年说、春秋时代改定说(顾颉刚主此观点)等看法。参见李民:《〈尚书·盘庚篇〉的制作时代》,《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第36页。“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周书·金滕》(50)顾颉刚认为《金滕》是东周间的作品,赵俪生认为“顾先生在此颇有见地”。参见赵俪生:《说〈鸱鸮〉兼及〈金滕〉》,《齐鲁学刊》,1992年第1期,第34页。“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周书·吕刑》(51)传统观点认为《吕刑》作于西周穆王时代,近现代“疑古派”则否认《吕刑》作于“穆王说”,他们认为《吕刑》是晚出之书,或作于春秋,或作于春秋以后。参见马小红:《试论〈吕刑〉的制定年代》,《晋阳学刊》,1989年第6期,第84页。“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三处用到“地”字。综合前人相关研究,笔者倾向于认为,这三篇文献写定应当在西周晚期或东周早期。《诗经》中“土”字很多,但“地”字仅两见:一是《小雅·斯干》“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这是歌颂周天王(可能是宣王)宫室落成的诗,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生了女孩,就让她睡在地铺上,给她包一副襁褓,让她玩瓦器纺轮;二是《小雅·正月》(52)该诗为东周平王初年,二王并立的产物。参见晁福林:《霸权迭兴:春秋霸主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36-38页。赵逵夫主编的《先秦文学编年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27页)系此诗于公元前770年。对《小雅·正月》文本也有学者予以质疑,翟相君认为《正月》后五章存在错简。参见翟相君:《〈诗经·正月〉的历法及错简》,《汉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意思是:都说天很高,走路不敢直起身;都说地很厚,不敢大步走。在乱世,要处处小心。“地”字出现及“天”、“地”对举的观念可能在西周晚期或东周早期。《墨子·尚贤》中说,“《周颂》道之曰:‘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于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则此言圣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修久也。故圣人之德盖总乎天地者也。”《墨子》这里所引“《周颂》”当形成于春秋时期,其“天高、地普”之说及“与天地同常”的观念显然要比《小雅·正月》“天高、地厚”说在内涵上更为丰富。
作为比照,同时也非常有意思的是,整个《易经》卦爻辞也仅出现一次“地”字,而且是天地对举,即明夷卦上六爻辞“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就思想实质而言,这里“登天、入地”之说与乾卦“跃渊、飞天”是一致的。我们知道,后来的《易传》大谈天地之道,思想也非常深刻,然而在卦爻辞中“天、地”仅一见,而且其意思浅显直白。《易传》当形成于战国中后期,这时期百家争鸣,诸子思想非常活跃,就传世著作来看,几乎无人不谈天地,天地思想成为战国中后期中国诸子思想的基本框架,诸子丰富多彩的天地思想,形成了中国思想的独特标识。《易经》、《诗经》各一次出现天地对举,而且都是非常素朴的天地观念,说明其成书时代应当比较早,大概在西周晚期到东周早期这个阶段。
余 论
如上所论,《诗经》中关于“天”有“皇天”、“旻天”、“昊天”、“苍天”、“上天”五种称谓,从文献历史与思想逻辑的统一来讲,“皇天”、“旻天”出现的比较早,“昊天”、“苍天”、“上天”较晚。这五种天有什么区别呢?这在《诗经》中可能是自然或偶然呈现出来的。然而后人试图对其区别作统一解释,秦汉时期的毛亨在解释《王风·黍离》“悠悠苍天”时说,“悠悠,远意。苍天,以体言之。尊而君之,则称皇天;元气广大,则称昊天;仁覆闵下,则称旻天;自上降鉴,则称上天;据远视之苍苍然,则称苍天”(53)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四,第253、255页。,这种解释的特点可以概况为空间德性义。与毛传空间德性义五天说不同,《尔雅》(54)《尔雅》据说是“秦汉之间学诗者纂集说诗博士解诂之言”,刘毓庆认为“《尔雅》是诠释《诗》《书》语汇的先秦古籍,其中释《诗》犹多,实堪称《诗经》学史上的第一部诠释著作”。参见刘毓庆:《〈尔雅〉的出现与〈诗经〉诠释学的产生》一文提要,《铜仁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从四时德性义的角度解释《诗经》诸天,其《释天》中说“春为苍天(万物苍苍然生),夏为昊天(言气晧旰),秋为旻天(旻犹愍也,愍万物雕落),冬为上天(言时无事在上临下而已)”(55)括号中文字为东晋郭璞注。参见王闿运:《尔雅集解》,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178页。,“天”与四时关联,实际上也自然化了。在经学史上,很多学者对这两种说法作了不同的解释。也有一些学者试图会通此二说,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东汉末年著名经学家郑玄,他认为:“春气博施,故以广大言之。夏气高明,故以远大言之。秋气或杀或生,故以闵下言之。冬气闭藏而清察,故以监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号也。六艺之中,诸称天者,以情所求言之耳,非必于其时称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苍天苍天’,求天之高明(56)郑玄这里实际上是以春为昊天、夏为苍天,与今传本《尔雅》有异。清代陈寿祺认为“《尔雅》旧本有作春昊夏苍者,许君《异义》及郑驳所据《尔雅》皆然”(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5页)。。‘旻天不吊’,求天之生杀当得其宜。‘上天同云’,求天之所为当顺其时也。此之求天,犹人之说事,各从其主耳。”(57)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四,第253、255页。在此,郑玄大体上综合了毛传和《尔雅》的观点。
实际上,汉儒的这些看法并不见得有多少道理,顾颉刚就批评说,“汉儒最喜排列,偶得异名即妄生分别,遂至愈整理而愈乱,天号其一端也”(58)顾颉刚:《浪口村随笔》,卷三,《旻天、昊天》,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5、84-85页。。在顾颉刚看来,“旻天者,天降不祥时之称谓也”,而“‘昊天、皇天’等名,所以形容天之伟大,而上帝为最大之神,其状与同,故连骈称之则曰‘昊天上帝’或‘皇天上帝’。《云汉》之诗,周民困于大旱,将无孑遗,怨悱甚矣。然而言及上帝则只能曰‘昊天上帝则不我遗’、‘昊天上帝宁俾我遯’,必不得易之曰‘旻天上帝’也,此可以识其故矣”(59)顾颉刚:《浪口村随笔》,卷三,《旻天、昊天》,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5、84-85页。。顾先生对皇天、昊天、旻天的理解有一定道理,也就是说这些名号的产生有偶然性,不同的名号可能也就是换一种说法,没必要“妄生分别”,像汉儒那样试图把它们纳入到一个统一系统里来解释可能确实没必要,也显得有些牵强。在古籍中,“旻天不吊”、“昊天不吊”出现的频次几乎相等,与“不吊”相连,到底宜作“旻天”还是“昊天”,也确实很难下结论。类似的情况还有,关于“皇天上帝”与“昊天上帝”,两者是相似可以互换,还是略有不同,不宜混同,也让人困惑。总之,在一些语境下,昊天与旻天、皇天都有可能混同,或替换之后似乎并不觉得突兀,而“旻天”与“皇天”好像泾渭分明。
“皇天”、“旻天”、“苍天”在《诗经》中都是神格义,而“昊天”既有神格义也有自然义。“旻天”、“苍天”、“昊天”在《诗经》中多有怨刺之情,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也反映了西周晚期或春秋时期人的主体性与理性精神的高涨。与“上帝”强烈的神格义相比,“上天”一方面有哲学化的倾向,同时也自然空间化;上帝神格之天,多与“下民”相对,而空间化自然之“上天”开始与“下土”相对,逐步形成了一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天地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