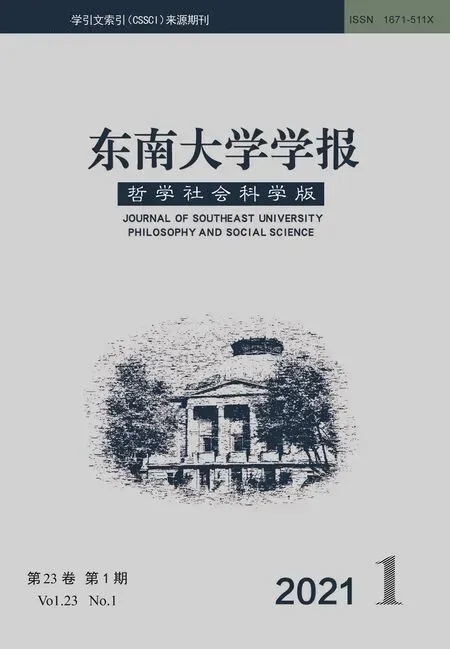韩柳孟子观之分歧及其思想史意义
——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张 勇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在中国文化史上,孟子无疑是最受争议的先秦大儒之一。先秦时期,孟子作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员,所受到的除少量来自本学派的褒扬外,更多的则是来自各方面的批评(1)如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批评道:“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闻见杂博”。见《荀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3页。。两汉时期,随着儒学的繁荣,孟子地位大幅提升,《孟子》一书也曾列于官学,但同时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2)如司马迁赞同梁惠王以“迂远而阔于事情”来评价孟子。见《史记》(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43页。。魏晋至盛唐,儒学飘零,孟子随之归于寂寞。中唐以降,韩愈以高蹈八荒、抗心千秋的情怀强烈主张提升孟子地位,而他的诤友柳宗元则激烈反对这一主张,两人孟子观形成尖锐的对立,这一对立是当时儒佛道三教互相激荡的结果,在当时及后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意义。
一、韩柳孟子观的诸方分歧
在韩愈、柳宗元文集中有大量关于孟子的材料,这些材料大都比较分散,若把它们集中起来,放在当时儒佛道三教相摩相荡的文化背景下来审视,会清晰地发现二人孟子观上的分歧。分歧是多方面的,从三教关系视角来看,最重要者当数以下四个方面:
(一)关于孟子夷夏观的分歧
为了捍卫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孟子一方面大力提倡“距杨墨,放淫辞”(3)朱熹:《孟子·滕文公下》,《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72页。,另一方面强调夷夏之大防,主张“用夏变夷”,反对“用夷变夏”(4)朱熹:《孟子·滕文公上》,《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0页。。对于这种排斥异端的激进思想,韩柳有完全不同的评价。
与韩愈不同,柳宗元反对孟子的“夷夏论”,明确提出“夷夏若均”思想,主张以“道”而不是“夷夏”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10)柳宗元:《送贾山人南游序》,《柳宗元集》(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65页。。他对韩愈的排佛思想深为不满,批评其“不信道而斥焉以夷”(11)柳宗元:《送僧浩初序》,《柳宗元集》(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73页。,这一批评实际上也是对孟子“夷夏论”的间接批评。关于如何对待异己思想,柳宗元说:杨墨及释氏之说,尽管在思想上与孔子有“抵捂而不合”之处,但由于“皆有以佐世”,因而应该“通而同之”(12)柳宗元:《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62至663页。。这种观点与孟子及韩愈是截然不同的。
(二)关于孟子义利观的分歧
“义利之辨”是孟子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此问题上,他有明确的重义轻利立场。在《孟子·告子下》中,他反对为人臣、人子、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君、其父、其兄,而主张“怀仁义”以事之,其核心观点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1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1页。
韩愈十分赞成孟子的义利观。在《上张仆射书》中,他说:
孟子有云:今之诸侯无大相过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时,与孟子之时又加远矣,皆好其闻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闻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义者也:未有好利而爱其君者,未有好义而忘其君者(14)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1页。。
韩愈继承孟子义利观,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表现出鲜明的重义轻利立场。
与韩愈不同,柳宗元反对孟子的义利观。如《吏商》:
或曰:“君子谋道不谋富,子见孟子之对宋牼乎?何以利为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诚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诚者,利进而害退焉。吾为是言,为利而为之者设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孟子好道而无情,其功缓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15)柳宗元:《柳宗元集》(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64页。
基于以上特点,本文提出一种适合于红外条件下的基于椭圆拟合的快速瞳孔定位改进算法,瞳孔定位过程如图3所示。
“孟子对宋硁”指的是上引《孟子·告子下》中的那番话。有人引用这段话来证明“谋道不谋富”,柳宗元表示反对。他认为,对普通百姓来说,空言“仁义”是没有意义的,对他们只能采用“以利退害”的办法,即以利来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接着,他又以《中庸》所载孔子之言“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来反驳孟子,从而证明“以利退害”的可行性。总之,在柳宗元看来,“义”与“利”并不必然对立,孟子只言“义”不言“利”,这种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观点是不切合实际的,也是不符合“孔子之道”的(16)参见张勇《论柳宗元的孟子观》,《哲学与文化》2011年第6期。。
(三)关于孟子心性论的分歧
孟子继承孔子的仁学思想,并从心性论高度论证其先天合理性。他说: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17)朱熹:《孟子·公孙丑上》,《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8页。。
人先天具有的“四心”分别是仁、义、礼、智的萌芽,故称“四端”,这“四端”经过后天的学习、修养就可以扩充为仁义礼智“四德”。在孟子的思想体系中,作为人经验观察和理性思考对象的“天”,被赋予“善”的内涵,并作为一切存在秩序和善的形而上根据和源泉。因此,他说:“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18)朱熹:《孟子·告子上》,《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36页。仁义忠信是上天赋予人的道德命令,因此称为“天爵”。
韩愈在《原性》中集中论述了对孟子“性善论”的看法。他提出“性三品”说,虽然从表面上看不同意孟子观点,其实与之并无实质性区别。他说:
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19)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0页。。
这段话中,“性”有两个层次:一是“所以为性者”,即抽象的、本体意义上的“性”;二是具体的、现实意义上的“性”,即个体天生所秉受之“性”。前者表现为仁义礼智信“五德”,是无所谓品第之分的;后者则可根据秉承“五德”多寡而分为上中下三品。前者近于宋明理学家所谓的“天命之性”,后者则近于“气质之性”(20)朱熹说:“如退之说三品等,皆是论气质之性。”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5页。。由此看来,韩愈心性论在本质上仍属“性善论”,其仁义礼智信“五德”之源也是高高在上的道德之“天”(21)如韩愈在《通解》一文中说:“且五常之教,与天地皆生。”见《韩昌黎文集校注》,第677页。。
与韩愈不同,柳宗元对孟子心性论直接提出了批评。他在《天爵论》中说:“仁义忠信,先儒名以为天爵,未之尽也。”(22)柳宗元:《柳宗元集》(一),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9页。这里没有直接点名的“先儒”指的正是孟子。柳宗元认为,孟子把仁义忠信看作“天爵”的观点是有问题的。他反对把“天”作为人的价值和意义系统的承载者,抽空“天”的道德内涵,还原其“自然”属性。“天”既然是无生命、无意识、无目的“自然”,那么它就不可能赋予人道德理性,它所赋予人的只是气,这气又分为“刚健之气”与“纯粹之气”,人禀“刚健之气”而形成“志”,禀“纯粹之气”而形成“明”,因此他说:“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与志而已矣。”(23)柳宗元:《柳宗元集》(一),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0页。在柳宗元看来,“明”与“志”只是人心性中一种“向善”的内驱力,其本身并不具有道德属性。这样,柳宗元就否定了孟子的“性善论”及其“天命论”依据。
(四)“道统”观上的分歧
韩愈十分推崇孟子,认为他是“孔子之道”最正宗的传承者。在《送王秀才序》中,韩愈说:孔子之道“大而能博”,弟子们只能以其“性之所近”而学,再“各以所能授弟子”,如此下去,孔子之道便“原远而末益分”了,而在众多传承者中,“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24)韩愈:《送王秀才序》,《韩昌黎文集校注》,第261页。。因此,强烈主张把孟子列入儒家“道统”之中:“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25)韩愈:《原道》,《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页。孟子之后,儒道失传,后世“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26)韩愈:《送王秀才序》,《韩昌黎文集校注》,第262页。。这就把孟子置于儒家“道统”的枢纽地位。有研究者说:“韩愈的‘道统’谱系上,真正居于中心位置的是孟子,其余的列祖列宗不过是配享从祀而已。”(27)(日)市川勘:《韩愈研究新论——思想与文章创作》,台北:文津出版社,2004年,第17页。诚哉是言!
与韩愈相反,柳宗元认为孟子并不是“孔子之道”的正宗继承者。立足于“性善论”,孟子孜孜不倦地论证以“仁心”行“仁政”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柳宗元认为这一想法过于浪漫,难以参与现实政治的建构:“孟子好道而无情,其功缓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28)柳宗元:《吏商》,《柳宗元集》(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64页。孟子空言仁义道德,而孔子则关心生民于实处,两人思想是有实质性差异的,因此孟子不是“孔子之道”的正宗继承人。
与韩愈一样,柳宗元也多次申述自己心目中的儒家“道统”,所不同的是,他没有一次把孟子列入其中。如他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说:“其道自尧、舜、禹、汤、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29)柳宗元:《柳宗元集》(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52页。在这个“道统”中,柳宗元最推崇的是孔子,把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与儒家“道统”的核心(30)张勇:《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91页。,而孟子在这个“道统”中是没有任何位置的。
从以上四个方面来看,韩柳二人的孟子观是对立的,一个推尊,一个贬抑。当然,韩愈推尊孟子并不是全盘肯定,如他在总体上肯定孟子“性善论”,但又提出自己的“性三品”说。同样,柳宗元贬抑孟子,也不是全盘否定,他也曾多次表达对孟子观点的认同(31)如《非国语·无射》:“孟子曰:‘今之乐犹古之乐也’‘与人同乐,则王矣’。吾独以孟子为知乐。”。韩愈在总体倾向上赞成孟子而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保持不同意见,柳宗元则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赞成孟子,但在总体倾向上持贬抑态度。同样是复兴儒学的旗手,韩柳两人对孟子这位儒学巨擘的态度怎么差距这么大呢?
二、韩柳孟子观分歧的原因
韩柳孟子观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歧,归根结底就是两点,一是对儒佛道三教关系的不同理解,二是对儒“道”内涵的不同理解。这两个方面,既是韩柳孟子观分歧的实质,也是造成分歧的根本原因。
(一)对儒佛道三教关系的不同理解
初唐以来,尽管每位帝王对待儒佛道三教的具体态度有所不同,但大都采取三教并行的文化政策,他们一方面提倡以儒学为治国之本,另一方面又提倡以道教、佛教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君主的三教并举政策及“三教论衡”活动,促进了三教鼎立文化格局的形成。以此为契机,佛道二教迅猛发展起来,不但信徒数量猛增,寺院、宫观遍布名山都邑,而且理论体系也发展成熟,在体系的完备及哲学思辨上都遥遥领先于儒家。
此时的儒学,虽然在统治者的扶持下恢复了正统地位,但随着其官学化的加深及科举考试的发展,越来越陷入章句之学中难以自拔,耀眼的政治光环下隐藏着其在“义理”与“经世”两方面的危机。韩愈描述当时儒学的困境说:“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32)韩愈:《与孟尚书书》,《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15页。柳宗元也说:“后之学者,穷老尽气,左视右顾,莫得而本。……甚矣圣人之难知也。”(33)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柳宗元集》(一),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08页。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很多儒家学者“外服儒风,内宗梵行”(34)白居易:《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序》,《全唐诗》(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83页。,阳奉阴违的学术态度令韩愈不禁发出“翱且逃也”之叹。
面对佛道二教的迅猛发展及儒学的理论危机,韩柳二人积极探寻儒学危机的根源。韩愈说:“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35)韩愈:《原道》,《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4页。韩愈认为儒学的危机源于佛道二教的冲击。与韩愈不同,柳宗元则认为儒学危机的根源在于其自身在社会实践上的不作为:“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覈,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36)柳宗元:《与吕道州论非国语书》,《柳宗元集》(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22页。沉溺于章句之学中的儒学,或漫无边际的发挥,或细碎烦琐的考证,根本不知道儒学的真精神是什么,已经完全失却了其“经世济民”之初心。韩柳对儒学危机根源的不同理解,间接决定了二人孟子观的分歧。
面对儒学危机,韩柳二人不约而同地提出全面复兴儒学主张,但由于二人对危机根源的不同理解,在复兴道路的选择上产生了分歧。韩愈由于把儒学危机归咎于佛道的冲击,因此认为,要全面复兴儒学就要打击佛老。柳宗元则认为,儒学的危机源于其自身“经世济民”功能的丧失,因此要全面复兴儒学就要充分吸收佛道二教中有补世教的资源,实现以儒学为中心的三教融合。这样,他们在儒佛道三教关系的处理上便产生了分歧,这一分歧直接导致了他们孟子观的对立。
为了打击佛老,韩愈抬高以“拒杨墨”而著称的孟子,借诠释孟子而凸显儒学的“仁义”内涵,从而把儒与佛、道严格区别开来。为了融合佛老,柳宗元则贬低孟子,借批判孟子而把儒学引向“经世济民”,从而在“佐世”上实现儒佛道三教的融合。
(二)对儒“道”内涵的不同理解
韩柳孟子观分歧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二人对儒“道”内涵的不同理解。韩愈认为,儒“道”的真精神在“仁义”:“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37)韩愈:《原道》,《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页。柳宗元则认为,儒“道”的真精神在于“经世济民”:“得位而以《诗》《礼》《春秋》之道施于事,及于物,思不负孔子之笔舌。能如是,然后可以为儒。儒可以说读为哉!”(38)柳宗元:《送徐从事北游序》,《柳宗元集》(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60页。在孔子以来的儒家思想体系中,既有偏重道德性命的“内圣”一面,也有偏重经世济民的“外王”一面,韩愈强调前者,柳宗元强调后者。韩强调儒“道”的主体性与超越性,柳则强调儒“道”的社会性与政治性。
以上差异,决定了韩柳孟子观上的对立。立足于儒道的“仁义”内涵,韩愈高度赞扬孟子:“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39)韩愈:《与孟尚书书》,《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14页。把孟子视为儒学“仁义”火种的孤独播撒者。立足于儒道的“经世济民”内涵,柳宗元批评孟子偏离孔子“急民”之初心而空言“仁义”道德。这一对立,正是源于二人对儒“道”内涵的不同理解。
钱穆论汉唐儒与理学家的区别云:“汉唐儒志在求善治,即初期宋儒亦如此。而理学家兴,则志在为真儒。志善治,必自孔子上溯之周公,为真儒,乃自孔子下究之孟轲。”(40)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五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15-216页。汉唐儒“求善治”,理学家“为真儒”,柳宗元为汉唐儒之余绪,韩愈则为理学家之先导。汉唐儒与理学家之别正是韩柳孟子观之别。韩愈孟子观志在“求真儒”,因此抬高孟子,把他置于儒家“道统”的核心,凸显其“拒杨墨”的战斗精神及“仁义”思想,以此打击佛老,从而保持儒学的纯粹性;柳宗元孟子观志在“求善治”,因此通过批评孟子来凸显儒道的“经世济民”思想,同时在“佐世”上实现儒佛道三教的融合。
三、韩柳孟子观分歧的思想史意义
(一)时代之问:儒学是什么
对于韩柳生活的中唐来说,“儒学是什么”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大问题。当时的局面是政治上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经济上国库耗竭、民不聊生,文化上三教鼎立、儒学孱弱。为了扭转这一颓废局面,韩柳都主张复兴儒学,主张以儒家之“道”作为振兴国家的旗帜。那么,儒学是什么?抑或说应该标举儒学的什么精神来挽救国家危机?这在当时是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正如韩愈在《送王秀才序》及《原道》中所说,孔子之道“大而能博”,其后学分为众多支派,究竟哪派所传才是正宗,这本身就是个棘手的问题,再加上佛道二教气势咄咄逼人,都以“孔子师”自居,而儒学则自称其“小”、甘拜下风,在这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的形势下,儒学的理性光辉已经完全被遮蔽了。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也说,儒家学者整日埋头于故纸堆,虽“穷老尽气”,却“莫得而本”。儒家之“本”到底是什么?这正是韩柳孟子观所争论的核心问题。
在纷纭复杂的儒家学派中,韩愈独标孟子,而在孟子复杂思想体系中独标其“仁义”,并由此回溯至孔子,从而把儒“道”定格在“仁义”上。对此思路,柳宗元表示反对,他要通过贬抑孟子而把儒“道”引向“经世济民”。《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载,有人写了一部贬低孟子的书,名曰《孟子评》,柳宗元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部书的宗旨在于通过贬低孟子而“明道”,并称赞其做到了“求诸中而表乎世”(41)柳宗元:《柳宗元集》(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23页。,即发掘出了儒学“经世济民”之真精神。韩愈通过抬高孟子而把儒“道”定位于“仁义”,柳宗元则通过贬抑孟子而把儒“道”定位于“经世济民”,韩柳孟子观的分歧代表了二人对儒“道”内涵的不同理解,是二人对“儒学是什么”这个时代之问所给出的答案。这一答案,也决定了他们对儒佛道三教关系的态度:是力排佛老还是三教融合。
黄俊杰把儒家诠释学分为三个“面相”,即“解经者”面相、“政治学”面相与“护教学”面相。关于后面两个“面相”,他解释说:“第二个面相与诠释者对社会、政治世界的展望有关。诠释者企图透过重新解释经典的途径,对他所面对的社会、政治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是一种‘返本以开新’的思考模式。第三个面相则是诠释者处于各种思潮强烈激荡的情境中,为了彰显他所认同的思想系统之正统性,常通过重新诠释经典的方式,排击‘非正统’思想。这是一种‘激浊以扬清’的思考模式。”(42)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14页。依此说法,韩愈抬高孟子,凸显儒“道”的“仁义”内涵,以此区别佛道,进而借助政治力量打击二教,其孟子观当属“护教学”面相(43)韩愈这一致思理路也招致佛教徒的猛烈反击,北宋云门契嵩出于“护教”目的,认为韩愈把儒“道”归为“仁义”,并不真正理解儒“道”。参见张勇《契嵩非韩的文学意义》,《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柳宗元贬抑孟子,凸显儒“道”的“经世济民”内涵,把儒学由书斋中的寻章摘句引向社会现实中的国计民生,其孟子观当属“政治学”面相。韩柳孟子观的不同面相,直接影响了宋代儒学对孟子的接受。
(二)韩柳孟子观分歧的宋代回响
北宋以降,国家恢复了中央集权,经济恢复了元气,儒学也蓬勃发展起来。宋代儒学大致是沿两条线发展的,一条是以道德性命为主题的理学,一条是以经世致用为主题的事功儒学。这两大学派都是在中唐儒学复兴运动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理学一脉受韩愈影响较深,而事功儒学一脉则受柳宗元影响较深。”(44)张勇:《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306页。因此,韩柳孟子观的分歧在宋代理学与事功儒学之间仍是余音袅袅。
沿着韩愈“护教学”的思路,理学家意在“求真儒”,因此大力推尊孟子,把他列入儒家“道统”,努力凸显孟子思想的“仁义”内涵,以此排斥佛教。朱熹说:
祖道曰:“只为佛老从心上起工夫,其学虽不是,然却有本。儒者只从言语文字上做,有知此事是合理会者,亦只做一场话说过了,所以输与他。”曰:“彼所谓心上工夫本不是,然却胜似儒者多。公此说却是。”(4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74页。
理学家们认为,儒学之所以落后于佛教是因为缺少系统的心性论,因此要想战胜佛教,就必须从传统儒家经典中挖掘心性资源,于是他们选择了孟子、选择了韩愈。程子说:“韩子论孟子甚善。非见得孟子意,亦道不到。”(46)朱熹:《孟子序说》,《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8页。朱子也说:“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此非深知所传者何事,则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传者何哉?曰仁义而已矣。”(47)余允文:《尊孟辨》卷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他们十分赞成韩愈的观点,把孟子视为儒家“道统”的核心,把“仁义”视为儒“道”的真精神。
沿着柳宗元“政治学”的诠释理路,宋代事功派儒学大都贬低孟子,反对把他列入儒家“道统”,并通过批评孟子而把儒“道”引向“经世济民”。李觏立足于现实事功批评孟子的性善论、义利观。如他说:“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48)李觏:《李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26页。南宋事功派儒学集大成者叶适,也对孟子思想大加鞭挞。他在《习学记言序目》中专列《孟子》一章,对孟子心性论、义利观及仁政思想进行全面而集中地批判,认为孟子思想有四大弊端:“开德广”“语治骤”“处己过”“涉世疏”(49)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739页。。概言之,即为:侈谈心性、空言仁政、背离“孔子本统”、不合现实之用,因此不应列入儒家“道统”。这些事功派儒家学者的孟子批评是与其对柳宗元的赞美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李觏在《上宋舍人书》等文中礼赞柳宗元对儒学的贡献,叶适也在《与戴少望书》等文中称赞柳宗元的“辅时及物”“救世俗之失”等思想。在他们的孟子观上柳宗元的影子是清晰可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