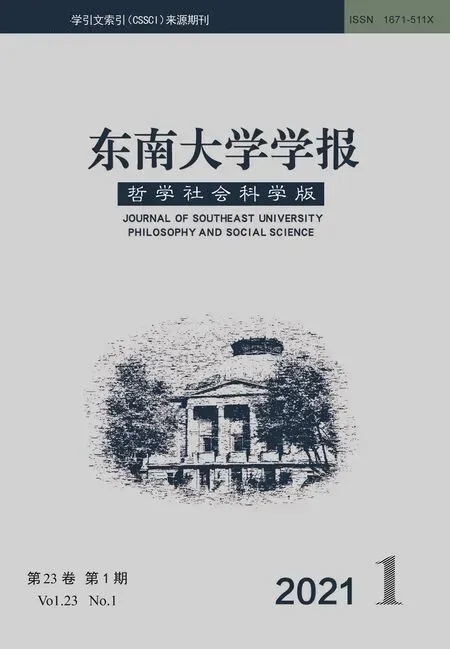中国家训文化源流论略
江雪莲
(华南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家训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文化遗产。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曾言:“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作为中国家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家训文化,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华民族繁衍生息、文明进步的精神“血脉”。当下中国要实现传统家训文化的创造性转型和创新性发展,亟须加强家训文化的学术研究。针对迄今国内相关学术研究总体上重视程度不够、系统性和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不多等不足,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建立“中国家训学”以加强家训文化的研究。笔者赞同多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家训学”,乐见更多有多学科视野和方法的家训文化研究成果。其中,从多学科视角探析中国家训文化源流,有助于系统、深入领悟和发掘家训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意义。
一、中国家训文化的萌发和起源
在中国家训文化的萌发和起源问题上,学界见仁见智。有学者认为,中国家训文化来源于古代中国人生产生活的实践经验,其最初形式是文字出现之前的原始歌舞(1)欧阳祯人:《中国古代家训的起源、思想及现代价值》,《理论月刊》2012年第4期。。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家训文化发源于远古神话时代。也有学者明确指出,在五帝禅让的神话故事中中国家训文化已见端倪(2)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2页。。更多的学者坚持以历史文献记载为准,认为中国家训文化发生的时间为夏朝之后到先秦时期。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家训文化是世族大家教育子孙后代的产物,严格意义上中国家训文化应发端于两汉并正式形成于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上述观点的分歧主要在于两个方面:1.对中国家训文化的来源和形式存在不同认识;2.对中国家训文化起源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根据存在不同看法。因此,研究中国家训文化的起源问题需弄清楚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中国家训文化以何种形式源自何时?中国家训文化产生的社会条件或历史根据是什么?问题一涉及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类型和文化载体及其源起、传承路径问题;问题二关涉孕育中国家训文化之古代社会的组织结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在年代久远、历史材料阙如兼残缺不全的情况下,从多学科视角,根据现有传世文献、地下考古发现和前人的历史研究等进行综合探究和合理推论是必要的。针对问题一,本文尝试引入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文化分层及大小文化传统论,结合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探究和合理推论,提出笔者的看法。针对问题二,本文将借助历史学、政治学的方法和成果,结合对古代社会的社会组织结构分析和文本文献分析进行综合探究和合理推论,提出笔者的观点。
首先,借鉴文化人类学的大小传统论,结合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等研究成果推论,中国家训文化存在着两个不同层次的传统:先于汉字、外于文字记录的大传统和由汉字记录的小传统。家训文化肇始的非文字家训,最初表现为事关宗族大事的口头规训(如诵)或以物(如钟)代言、以行(如歌舞)代言的仪式。
大小传统论是20世纪中叶西方人类学在研究从简单的“原始或部落社会”向有文字的复杂的文明社会过渡时提出的一种分析框架和解释模式,由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 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1956年出版的《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一书中首次提出。雷德菲尔德认为在复杂社会中存在两个不同文化层次的传统,并提出 “大传统”与“小传统”二元分析的框架模型用以说明。他以“大传统”指城市中由城镇的知识阶层所掌控书写的文化传统,以“小传统”指称乡村中由乡民通过非文字如口传、实物、仪式等方式传承的文化传统,认为二者对于文化而言缺一不可(3)罗伯特· 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王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90-116页。。这一文化分层理论后被欧洲学者改造为精英(上层)文化和大众(下层)文化或正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二元文化框架,广泛运用于人类学之外的许多学科的研究。中国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曾把这一理论运用于中国传统文化(4)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78页。,对应中国雅文化与俗文化的二元框架。事实上,虽然这一理论由西方人类学在20世纪中叶提出,但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古人不但早已自觉到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自始即致力于加强这两个传统之间的联系。”(5)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396页。循此思路,接着余先生的观点讲,由于不同文化间的密切关联互动,使得中国古代文化之分层具有相对性和颇为复杂的关系样态,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独特之处,因此不可简单照搬雷德菲尔德的理论,有必要加以中国本土化理解和创造性运用。要知道,在雷德菲尔德生活的美洲,考古学被视为人类学,而中国一般把考古学视为历史学,其任务是重构历史尤其是史前史。当年王国维先生提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于今便是强调史籍史学的文献研究与考古学的地下文物研究之间相互取长补短的必要性。古代中国文化具有西方文化无法比拟的复杂性,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因地域差别、种族差异和频繁的政权更迭等多种因素所致的文化多源性、多样性和多元性。朝代更迭导致的文化变更绝不是线性和单向进行。以三代文化为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先生指出:“业已从考古学角度明确分辨出夏商周分别是三种有联系却不相同的考古文化,各有自己的发祥地,彼此都有一定的并立共存期。三者的关系,并非‘父子’,却似‘兄弟’。”(6)赵辉:《考古学与中国历史的重构——为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五十周年而作》,《文物》2002年第7期。父子关系在遗传性能上为父→子的线性、单向的传递,兄弟关系则不是。如此复杂的情况,“传统二分法”显然无法全覆盖之,只能用于主要分层,须知各传统自身内部亦各有其多样性,并可再分层。另一更为重要的方面,古代中国文化演进中更常见的大小文化传统之间的互动以及各族群文化之间的多层叠加、融合变化,绝非西方人类学二元文化结构所能涵括。在此,笔者赞同中国文学人类学会会长、中国神话学会会长叶舒宪教授等人提出的颠覆性的本土化“再造”,“将由汉字记录的传统叫做小传统,把先于汉字和外于文字记录的传统视为大传统”(7)薛伟平:《以四重证据法重述“神话中国”》,《文汇读书周报》2017年5月22日。。
借用于阐释中国家训文化的起源,以文化人类学的大小文化传统论和相关多学科研究成果观之,中国家训文化存在着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先于汉字和外于文字记录的大传统和由汉字记录的小传统。那么,是否存在先于汉字、外于文字记录的非文字家训?诚如清华大学李学勤先生所言:“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以至夏商周三代这一大段,既不同于史前时代的纯依据考古,又有别于秦汉以下的文献完备,必须同时依靠文献和考古两者的研究。”(8)详见李学勤先生为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所撰“序言”。依照李学勤先生的“同时依靠文献和考古两者的研究”,先于汉字、外于文字记录的非文字家训的存在,已被近年来的一些考古研究所证实。2008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收到的一批竹简(简称“清华简”)中最早编排起来的一篇简书《保训》,上面有这样一句话:“昔前人传保(宝),必受之以詷,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终,汝以书受之。”尽管学界在某些字词的隶定、释读等方面仍存在分歧,多数学者还是接受《保训》记录的是周文王对太子发的传宝遗训。大意为:周文王在位第五十年,罹患重病,念及过去传承“宝训”,“必受之以詷”,担心自己等不及,遂以书面的方式传训于太子发。这句话的关键是“詷”作何解?学界对此意见不统一,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释为“诵”(9)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背诵或大声朗读)或“钟”(10)晁福林:《观念史研究的一个标本——清华简〈保训〉补释》,《文史哲》2015年第3期。。相较而言,释为“诵”更合理些。不过,无论“詷”作何解,都说明在文王传宝训之前,已有了以“口耳相传”的诵或以实物“钟”(作为礼器)为表征(代言)的非文字形式传承宝训的习俗。事实上,实物作为文化符号表征在古代很常见。有专家指出:“华夏文明有自己的一套早于文字数千年的符号系统——玉礼器符号。相关的神话知识少部分以文字记录形式保留在先秦礼书和典籍中,而大部分则被汉字书写遗漏掉了,久已淹没在三千多年以前的文化大传统之中,等待后人的再发现和再认识。”(11)薛伟平:《以四重证据法重述“神话中国”》,《文汇读书周报》2017-05-22。由此基本可以推定,家训产生伊始的非文字家训,其表现形式为诸如事关宗族大事如传承宝训的口头规训(如诵)或者以物(如钟)代言的仪式。除此之外,理应包括以行代言的形式,如原始歌舞(12)欧阳祯人在《中国古代家训的起源、思想及现代价值》中也有此类看法。参见《理论月刊》2012年第4期。。原始歌舞在关于远古时代的神话叙事中有大量记载。所有古文明国家的历史都始于神话叙事,历史神话实际上也是大小传统融合的产物。中国上古神话是一个汇合了关于上古传说、历史、宗教和仪式的集合体,通常通过口述、寓言、仪式、舞蹈或戏(歌)曲等方式在上古社会中流传。原始歌舞是其中之一,实际上是以行代言。
非文字家训文化传统的存在及其对家训文化的开创意义提示我们:假如我们只重视史籍家训文献小传统,而忽视非文字家训文化大传统,中华家训文化内部的多样性、丰富性、客观性,极有可能被汉字中心和中原文化中心的小传统所遮蔽。今天的中国家训文化研究,应突破以往过于依赖传世文献的局限,注重口传和非物质遗产等民间和民族活态文化、文物的搜集整理和挖掘,与图像、传世文献、新出土的文字材料(甲骨文金文和竹简石刻等)彼此之间相互参照、互证与检验、辨伪,建构多视角的立体性家训文化文本系统,找回因文字记载的疏漏而失落的家训文化信息。某种意义上这是在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基础上的新阐释和发展。事实上,即使在文字出现后,由于各种原因,许多民间家训未能用文字记录的形式保存和流传下来。时至今日,大量民间的非文字家训文化遗珠亟须发现和发掘。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民族歌舞民谣、谚语寓言、神话传说、民族史诗以及诸如祝酒、祭祀、婚嫁、丧葬等一些节庆和特殊仪式歌辞,这些民间家训文化资源具有重要价值,亟须搜集整理和(汉语)文字转存。
其次,借助历史学、政治学的方法和成果,探寻中国家训文化发生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根据以及起源时间。从分析古代社会的社会组织结构入手,结合相关传世和出土文献的文本分析可以推定,只有当原始家庭发展到以父系血缘结合形成宗族社会、原始父系家长制衍化为宗法制度的时候,才有家训产生的需要和可能。中国家训文化可能萌芽于已为宗族社会的尧舜时期,目前所知有关尧舜时期部落间的政治联姻、帝位传承等事关宗族大事的规训和教导以及“五教”,可视为家训的萌芽和早期形式。
一些研究者认为,有家庭就会有家训(13)曾凡贞:《中国传统家训起源探析》,《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这一观点并不全面和准确。家庭的出现当然是家训产生的第一历史前提和必要条件,但并非其充要条件。事实上,人类脱离动物后最初形成的原始家庭,基本上只是其功能在于某种程度上确定或规约两性关系及其婚姻生活的一种群居式家庭。严格说来,那时的生产生活单位是原始群落而不是家庭,因而家训产生的可能性不大。在此涉及古代社会的社会组织结构问题。19世纪英国著名法学家亨利·萨姆奈·梅因((H.S.Maine)在其历史法学名著《古代法》中提出,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在结构上的差异在于,近代社会是一个个人的集合体,而古代社会是“一个许多家庭的集合体”(14)[英]梅因:《古代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72页。,即宗族社会。宗族是人类出于生存和安全的目的,由几个核心家庭(总人数一般30~50人)松散地组成的集合体。本质上,宗族是一种基于男性世系而形成的家庭联合体、一个依托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而组建的有其独特功能的社会组织;功能上,宗族主要发挥着行政管理、教育教化、赈济救助、军事防卫等功能,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和天然的区域优势,深刻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二为一形成的宗族制度,也就是王族贵族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是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完全一致的制度。宗族制度由氏族社会的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父系家长(父亲或祖父)对于家庭财产、家庭成员以及家庭事务具有绝对支配权,当然也包括对家族成员的教诫规训(家训),家训出于维护宗族利益和宗法制度之需应运而生。换言之,当社会形成宗族和宗法制的时候,才有家训文化产生的需要和可能。
从中国古代史相关史料来看,随着氏族公社特别是父系氏族社会的出现,在尧舜生活的年代,作为生产和生活基本单元的实质意义上的个体家庭和家庭关系已经成为公社的主要结构,父权制和父系家长制已经相当发达,已然出现以父系血缘结合的宗族,具有产生家训的需要和可能。具体而言,笔者认为,中国家训文化可能萌芽于已为宗族社会的尧舜时期,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其一,部落间的政治联姻。历史学研究业已表明,利用婚姻方式团结各氏族部落是尧舜时期的立国之本。显然,这种政治联姻缘于家族之间的生存竞争,超出小家庭的需要而出自于宗族的利益需要,是关系到宗族兴废存亡的大事。或许因此之故,遵从此种政治联姻成为当时中国帝王家对子女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成为历代皇家家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点从历史上尧帝两个女儿遵旨嫁给舜的政治联姻故事中可见一斑。据文献记载,后世广为传颂的一些家庭美德被认为来源于尧舜时代。汉代刘向的《列女传·有虞二妃》称:“天下称二妃聪明贞仁。”二妃指尧帝长女娥皇和次女女英,姐妹俩“聪明贞仁”“德纯而行笃”,“甚有妇道”。舜即位后,娥皇女英被分封为后和妃。她俩用智慧和宽容,“谦谦恭俭,思尽妇道”,不但极大地成全了舜的美名,而且巧妙地化解了家庭危机。对此,《列女传》不仅将二位列入“母仪传”第一,而且搬出《诗经》里“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的诗句大大予以褒赞。其二,“五教”(五典之教)。司马迁认为,历史上的义、慈、友、恭、孝等作为“五教”的家训基本内容,是由舜提出来并付诸实施的。司马迁说:“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15)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5页。其三,传位“宝训”。2008年清华简《保训》篇有讲到“宝训”的流传历史,历经虞舜、唐尧、河伯、上甲微、有易、商汤,再到文王等数族数代,说明尧舜时期开始以“诵”传承宝训,这也可以作为家训起源于尧舜时期的佐证。
随着宗族势力的扩大、私有制的出现和捍卫宗族利益的需要,“家”天下王朝的出现成为必然。禹之后世袭制的确立,一举开创中国以“家”为模式组建“家”天下王朝的创建历史。而“家”天下王朝的基石和纽带正是血缘家庭关系,所谓家国同构、家国一体。在“家-国-天”三位一体的古代社会机制下,宗族成员的社会化、家族之间的生存竞争、家庭内部的家务分担、抚育晚辈的教化责任、维系家族的安和永续、协调内部人际关系等事关家族和国家存亡的需要,是中国家训这一特殊文化现象得以数千年绵延不绝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根据。
二、中国家训文化的确立和成文
随着父权制、父系家长制与私有财产制的紧密结合,宗法制度得以进一步巩固和确立,中国家训文化由此迎来一个大的发展契机,得以实现质的飞跃,即由汉字记录的家训问世。《尚书·多士》篇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古文字学研究亦表明,迄今为止,尚不能肯定殷商前文字的存在。迄今已知最早的由汉字记录的家训为商周皇家家训(多半由史官或后人记录),由其所肇始和确立的中国汉字家训文化传统一脉,贡献了中国家训文化的开篇之作,开启了中国家训文化的新篇章、新气象。
对于中国家训文化的开篇之作,众说不一。比较常见的是以周公的《诫伯禽书》为最早的家训,并称周公为“家训开创者”。流传较广的这一说法从何时何人开始,已无从考证。然而,如前所述,最新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成果证实,其父周文王以书面形式传承宝训的临终遗训《保训》早于《诫伯禽书》。另外,有不少人以《颜氏家训》为最早的家训。此说法主要依据宋代著名藏书家陈振孙的一句话:“古今家训,以此为祖。”(16)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674》,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但是,此处“家训始祖”的说法无非称赞《颜氏家训》对后世家训的深远影响,并非严格意义上言其为首篇家训。实际上,该书成书时间比较晚,约在公元6世纪末。就该书本身而言,不仅内容丰富,涵盖了从饮食起居、修身养性到为人处事、致学求仕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而且立意深远,凝聚了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对人生的深切体悟和饱含仁慈睿智的长者对子孙的舐犊之情,因而被树为古代士族大家教育的范本和后世家训效仿的样本。因此,准确地说,《颜氏家训》是第一本冠名“家训”的家训系统论著。它在中国家训文化史上具有的里程碑意义实至名归。可以说,唐代以后的家训莫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其影响。明朝袁衷在其家训专著《庭帏杂录》中赞道:“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清人王钺在《读书丛残》中说:“北齐黄门颜之推《家训》二十篇,篇章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当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
确定中国家训开篇之作,既需要对文本及其记录的事件进行时间排序,也需要考虑文本和事件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意义。近年来有学者提出《盘庚上》或《保训》为中国首篇家训,各有侧重。根据现有文献和新近考古成果,结合历史语境分析和文化意义辨析,由汉字记录的家训传统中迄今已知最早的是具有“家族相似性”(17)此处借用奥地利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哲学代表作《哲学研究》中提出的“家族相似性”概念。参见[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7-48页。的商周皇家家训群,表明文献家训之源头或肇始形态和非文字家训一样具有多样性。根据其内容和文体的差异,我们认为,商周皇家家训群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帝王政事(令)训、帝王传宝遗训和皇属(18)皇属即皇帝的宗族。出自《晋书·谯王承传》:“吾以闇短,託宗皇属。”子弟训(诫),分别以《盘庚上》、《保训》和《诫伯禽书》为代表,其集大成者为周公。
首先,《尚书·盘庚上》为中国最早的帝王政事训。
所谓帝王政事训,是帝王家首要的和最常见的家训。其内容主要是告诫以皇帝为首的全体皇属如何对待和处理国家事务的政事(令),其文体采用帝王专属的“训”体。已被历史学家确证为《商书》中史料价值较高和年代最早的文献《盘庚》三篇中,记录殷王盘庚就迁都一事发表规训的《盘庚上》在时间上为最早。其语词较为古朴艰涩,一般认为是商代史官所做的记录,时代所致。其内容为:史载当时对于商王盘庚迁都于殷的决定,下至平民百姓,上至王亲贵戚都有怨言,盘庚因此召集贵戚聚集一堂,向他们作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训诫。他先训斥贵族煽动百姓的做法是错误的,后指出自己的决断是建立在对当前形势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的(“予若观火”),劝诫贵戚们应该“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不要用自己的言论去欺骗那些老弱幼小的人,而造成“若火之燎原,不可向迩”的难以收拾的地步。最后指出自己搬迁的意志已决:“若射之有志。”就像射箭一定要射中一样。同时要求贵戚们必须各司其职,听从统一指挥:“各长于厥居,勉出乃力,听予一人之作猷。”
事实上,《盘庚》三篇皆为训词:“格汝众,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上篇告诫贵戚,中篇训诫臣民,均为迁都前之训词;下篇则是迁都后告诫贵戚之辞。但很显然,中篇不算家训。那么,《盘庚》(上篇)是否为家训?对此学界存有争议,主要在于对其训诫对象的身份“贵戚”有不同理解,即“贵戚”是否是盘庚的血缘近亲、同族之人?据考证,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盘庚》训辞中言及:“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青及逸勤”“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和“先王”一起同享盘庚之祭的贵戚,多半是盘庚的血缘近亲、盘庚的同族之人。身份显赫的贵戚与王者同族同姓这一点,在后世文献(比如《孟子·万章下》)中也可找到印证(19)详细考证和释义,参见傅元琼、史为栋《〈商书·盘庚上〉与家训的起源》,《安徽文学》2008年第1期。。
其次,《保训》为中国最早的帝王传宝遗训。
所谓帝王传宝遗训,是帝王家最重要和特殊的一类家训。其内容主要是在位皇帝对继位者的传位遗训,文体上同样采用帝王专属的“训”体。前文提及的中国考古和历史学界近年来的重大发现2008年“清华简”《保训》,被多数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记载的是周文王姬昌的临终传宝遗训。该遗训共约2500枚,其中《保训》简文有11支简,每支长度只有28.5厘米的竹简上有22至24个字,除去第2支简上半残失,其余篇文大体已经齐全。作为“清华简”中最早得以编排起来的一篇简书,现已收录于历经两年多时间研究发表的清华简首批研究成果《清华大学藏战国书简(壹)》(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1年出版)一书中(20)根据清华简研究团队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整理报告主编李学勤先生介绍,这批简的性质是书籍,且与历史相关,竹简中不仅有失传了2000多年的战国《尚书》,还澄清了一些学术史上长期争论的疑难,复原了楚国历史及历史地理。。事实上,《尚书》中有多篇记录文王父子三代代代相传的家训,可见文王本人对自身言传身教的重视。虽然《逸周书》载有文王诫武王的训辞《文儆解》、《文传解》,武王诫成王的训辞《武儆解》,周公诫成王的训辞《无逸》,成王诫康王的训辞《顾命》(21)马智全:《从清华简〈保训〉看“训”文体特征》,《鲁东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但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是这篇文王的临终遗训——《保训》。我们认为,《保训》在中国家训文化史上的意义深远,甚至超过《盘庚》,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因:
(1)《保训》所记录的文王宝训的规训对象和训告内容较之《盘庚》更具有家训之典型意义。《保训》记录了一个处于弥留之际的父王对即将继位的儿子传授宝训的缘起和宝训内容,表达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护育教导和殷切希望。相较于对关系稍显宽泛的皇属大臣进行训教的《盘庚上》,基于直系亲子关系的《保训》显然更具有典型性。
(2)《保训》所记录的规训内容比《盘庚上》更完整和典型。原文如下:“惟王五十年,不豫,王念日之多历,恐坠宝训,戊子,自靧水,己丑,昧[爽]……[王]若曰:‘发,朕疾壹甚,恐不汝及训。昔前人传宝,必受之以詷,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终,汝以书受之。钦哉,勿淫!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兹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呜呼!发,祗之哉!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迺归中于河。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唐,祗备不懈,用受大命。呜呼!发,敬哉!朕闻兹不旧,命未有所延。今汝祗备毋懈,其有所由矣。不及尔身受大命,敬哉,勿淫!日不足,惟宿不详。”(22)李学勤:《清华简〈保训〉释读补正》,《中国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保训》的内容从全篇结构看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交代文王传授宝训的缘起;二是记录文王所传宝训的内容记录内容的部分分为三层意思:交代传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通过舜、上甲微及成汤的故事传授治国经验;告诫武王遵循宝训,勿荒淫、珍惜时间、夜以继日、勤勉为政、膺受天命。整个宝训的过程和内容十分清晰和完整。
(3)《保训》的思想性和思想史意义大大强于《盘庚上》。文王所传宝训的政治意图明确而深刻,内含丰富的兴邦建国、治国理政、文治武功的政治思想。近来学界对清华简的大量研究表明,《保训》中的“中”“欲”“德”“绪”“命”“敬”等观念和“敬德保民”“明德慎罚”“无逸勤政”等思想理念,具有深远的思想史意义,与西周时期乃至后世儒家的相关观念和思想有着内在联系。《保训》中不仅蕴涵着儒家“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中庸之道等思想的端倪,成为后世儒家关于清明之君、清明之制等观念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同时,文王以史为鉴的宝训精神可以视为周公等人的“殷鉴”思想的来源,《保训》的发现使殷鉴思想的时间提前了。后世儒家把文王当成“内圣外王”的典型加以推崇,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更是为后世政治家追求的理想目标。
最后,《诫伯禽书》为中国最早的皇家子弟训。
不同于前述帝王政事训和帝王传宝遗训皆以帝王为教导主体或(和)教导对象,所谓皇家子弟训指以同辈或隔代皇族子弟为教导主体和教导对象的家训,采用的文体多为“诫”体。《诫伯禽书》作为最早的皇家子弟训的代表,其内容丰富完整,堪称古代皇家家庭教育之经典。这段中国著名的古训,记载的是周成王把鲁国的土地分封给周公的儿子伯禽,周公对儿子的一段告诫。原文为:“去矣!子其无以鲁国骄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尝一沐而三握发,一食而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吾闻之曰:‘德行广大而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守以愚者益;博闻强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不谦者失天下,亡其身,桀纣是也。可不慎乎!”(23)刘向:《说苑全译》,王瑛、王天海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15-416页。对将承袭其爵位到鲁国封地的伯禽,周公现身说法,以自己“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亲身经历,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子要选贤任能、礼贤下士、尽心竭力治国理政,并特地以六种“谦德”强调,谦虚谨慎是治理天下、成就大业的第一要素。伯禽后来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没过几年就把鲁国治理成民风纯朴、务本重农、崇教敬学的礼仪之邦,世人赞誉其家教居功至伟。
《诫伯禽书》思想上立意高远、影响非凡。在思想上与文王《保训》一脉相承,但文字更为生动感人,更具感染力、说服力,为千古难得的文采与思想俱佳的政论佳作,对后世的影响巨大而深刻。周公披肝沥胆、勤勉谦恭、求贤若渴的精神和品格,被后世人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加以讴歌;作为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弟、成王的叔叔,周公皆能以身作则、辅国安邦、创立典制、制礼作乐,被视为中国古代政治精英之士大夫精神的代表和理想人格,也是后世为政者的典范。后人尊孔子为“至圣”、周公为“元圣”。据说孔子对这位于其学说影响最深、贡献最大的周公极为尊崇,竟至于经常梦见他。及至晚年,竟会哀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
此外,周公虽不是商周皇家家训第一人,然而堪称商周皇家家训之集大成者。他传承并光大了其父文王的家训思想,其家训传世之作既有广为流传的子弟训《诫伯禽书》,也有劝诫侄子成王的帝王训,在多样性上无人能出其右。篇篇家训皆有针对性地教导训诫,情真意切,颇具思想性和感染力,对后世家训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产生了正面的深远影响。以据称其劝诫成王的《无逸》为例,通篇以史为鉴,以正反面历史人物为例,强调只有勤政恤民、不贪图安乐、不懈怠政务方能长久的道理。据说孟子从中获得启示,得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名言。
三、中国家训文化的衍化和传播
中国家训文化的衍化和传播,既有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之发展和变迁互动的一面,也有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特点。为此,本文不着墨于一般性的中国家训文化的历史分期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研究,而主要聚焦于中国家训文化从先秦到清末衍化与传播的逻辑、特征,借以窥探、领悟传统家训文化自身内涵、意义的变化与发展。
第一,中国家训产生伊始并没有“家训”之名,也没有统一的名称。从商周皇家家训之(帝王)“训”和(子弟)“诫”,及至汉代“家训”和“家诫”复合词的出现,标志着家训文化从皇家逐步推广至贵族官宦和士族家,明确奠定了中国家训的基本涵义:以家族为基元,对家族成员从饮食起居、修身养性到为人处事、致学求仕等方方面面的训导和劝诫。
最初,家训文献的名称和称谓里甚至既没有“家”也没有“训”的字样,如开篇之作《盘庚上》。从一开始就没有统一的名称,如《盘庚上》所代表的较为常见的皇家政事(令)训以教导者或教导内容命名;《保训》所代表的以“训”为名的家训唯帝王专属,有别于如《诫伯禽书》所代表的子弟训,似乎只是众多皇家家训中的一类。这一点从词源上得到证实。据考证,“训”,最早见于《尚书》,原本是上古《书》体之一,即“典、谟、训、诰、誓、命”六种文体中的一种。《书》也叫《书经》,汉代改叫《尚书》,即“上古之书”,意为“公之于众的古代皇室文献”,其内容主要是记载古代君王治国理政的言行和政令。“训”的意思,根据孔安国《尚书序》的解释:“教导之文曰训”。“训”作为一种文体,指中国古代教导君王治国理政的文辞(字)。也即是说,“训”作为一种教育形式,是指对君王进行的治国理政的教导。“训”专用于对君王的教导,与教导者是否为君王无关。如《伊训》的教导者不是君王,而是大臣伊尹,但教导对象是商王太甲;《保训》的教导者和对象均为君王。汉代以降,尤其是魏晋时期,“训”从皇家逐步推广至士族官宦人家,家和训合用以突出其平常家居的意义。据考证,复合词“家训”一词在蔡邕生活的东汉被使用。最早见于《后汉书· 文苑列传》:“议郎蔡邕深敬之,以为让宜处高任, 乃荐于何进曰:伏惟幕府初开,博选清英,华发旧德,并为元鬼。虽振鹭之集西雍,济济之在周庭,无以或加。窃见令史陈留边让,天授逸才,聪明贤智。龆龀夙孤,不尽家训。”南北朝颜之推为家训文化命名,其《颜氏家训》首次以“家训”为书名,作为后世家训的范本而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其带动下,涌现出大量以家训为名的佳作。如南宋陆游的《放翁家训》、朱熹的《紫阳朱子家训》、明代高攀龙的《高氏家训》、清代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家训》等。
当然,“家训”得以“名”符其“实”,不得不提到商周时期皇家家训的另一个文体——“诫”。从辞源考证,“诫”从“戒”衍化而来。“戒”作动词时,本意表防备、警惕,如《新书·大政》有云:“呜呼,戒之哉!戒之哉!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引申义为教令警省不犯错误。如《荀子·成相》:“不知戒,后必有”,“观往事,以自戒”,《毛诗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戒作名词时,本意为戒线,引申义为规矩和道理。据考证,在甲骨文和未经人工加工的原始商代铭文中已多次出现“戒”或“教戒”。如《甲骨文合集》第七册:“[丁]丑卜,勺·贞王乎万戒弓。九月。”《甲骨文编》卷三还出现“教”“戒” 连用的情形。《说文解字》:“诫,敕也。从言戒声。”《汉书》亦有:“前车覆后车诫。”诫的本意是警告,明确告知做事的规矩界限以免犯错误,适用于上对下、长辈对晚辈或平辈之间。其意和适用范围均与“训”有所不同。与《诫伯禽书》对皇家子弟的训诫有所不同的是,后世使用较多的适用于长辈对晚辈的平常“家诫”一词,突出了平常家居日用之告诫义。这一点在汉代变得非常普遍,自汉代开始大量出现“诫子书”、“家诫”。最早有汉代刘向的《诫子歆书》,之后有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诸葛亮的《诫子书》和《诫外甥书》、王艇的《家诫》、王肃的《家诫》、秘康的《家诫》以及李秉的《家诫》、徐勉的《诫子裕书》以及唐太宗李世民的《诫皇属》等。这些“(家)诫”文献通常是将往来书信集册成书,是有较为完整体系的教诫子孙的典型家训之作。
第二,中国家训文化的历史衍化和传播,存在着文字与非文字、民间与官方等不同的模式和路径。而不同文化模式和路径的交替、交错,催生出基于不同目的和功能的家训文化,其种类和称谓各异,造就了多姿多彩的中国家训文化,使其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多方面的作用。
中国家训名目繁多,令人叹为观止。除了人们熟悉的“家训”和“家诫”外,一般最为常见的称谓有:“家范”“家规”“家仪”“家礼”“家语” “家订”“家政”以及“家箴”“家约”“祖训”等,主要侧重于基本的亲缘关系之内的家族成员,规约性程度不等、形式上没有那么正式。除此之外,还有“族规”“族训”“族范”“宗规”“祠规”“行规”“乡约”等称谓,在基本亲缘关系基础上加入了有一定地缘关系的家庭乡党,可视为前者的扩大和强化,不仅适用范围广,规约性也更强、形式更为正式。笔者把这些基于不同目的和功能而具有不同名称的家训,大致分为以下三大类型:
(1)侧重典型示范和正面劝喻、鼓励的一般家训(祖训、族训),如“家范”(族范)、“家语”和“家教”。 “家范”(族范)即家教的范本,内容主要为齐家的规范、经典语录和优秀事例。据史志记载,狄仁杰曾著《家范》十卷失传,司马光沿用其名撰写的《家范》成为当时家训必备课本。南宋袁采的《袁氏世范》最富盛名,被冠以《颜氏家训》之亚,是著名的私塾训蒙课本。“家语”一般是长辈、尊者针对家庭成员的言行记录。颇负盛名的家语为父子宰相家清人张英的《聪训斋语》以及著名的晚清民国时期实业家周学熙的《周学熙家语》(《止庵家语》)。“家教”是针对家族成员的一般性教诫,侧重对家族成员的劝谕和鼓励。清代朱用纯的《朱柏庐治家格言》,因其通俗易懂、简明扼要、朗朗上口而广为人知。
(2)侧重订立规章制度、带有强制性的家训,如“家规”、“家仪”、“家礼”、“家订” (“家约”、“族规”、 “宗规”、“祠规”、“行规”、“乡约”等同理)。所谓“家规以惩恶,家训以劝善”,家规亦即家法,将家族成员所应共同遵守的事项以规条的形式列出,具有较强的强制性。在明代的法律中引入其不少内容的元人郑太和的《郑氏规范》,还有清人孙奇逢的《孝友堂家规》等为家规名作。“家仪”和“家礼”的主要内容是日常起居和冠、婚、丧、祭等礼节、仪式,侧重礼仪和行为方式,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代表性作品有司马光《涑水家仪》以及朱熹《家礼》等。司马光的《涑水家仪》是当时父母和女子必读。那时(至今依然可见)不少父母为其女孩取名“家仪”,或许是受其影响。“家订”,专为家族成员制订之意。如清代康熙年间名臣礼部尚书许汝霖的《德星堂家订》,从宴会、着装、嫁娶、凶丧、安葬、祭祀等日常生活方面,为后代子孙及族人立下严格家规,倡简戒奢,移风易俗。
(3)侧重事务管理、劳动技能等内容的家训,如“家政”。取其家庭事务管理之名,与“朝政”相对,突出居家理政、家国同理之意。内容包括劳作、经营、收支等事务性、务实性的家庭事务以及相应的家政精神。清人丁耀亢在《家政须知》自序中有言:“人皆知训子读书为光耀门户,而不知以家政教之也。往往有宦室富家,巨资厚蓄,其先人既往,不数年而子孙荡费至于饥寒无卓锥者。固其子孙之不肖,亦父兄未尝以家教习之,故蒙昧无知,财利归之他人,田土反为己害。”从个人成才、家业承续以及家族兴衰强调家政教育的重要性。
第三,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推进,中国传统家训文化历经萌发—成文、成型—成熟和繁盛—巅峰三个主要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其作为时代标志的一类家训。以商周皇家家训、魏晋官宦名仕家训、宋代治生家训和明清商贾家训为标志,家训文化逐步从政治生活向日常家居生活、行业生活渗透和拓展,在不同程度葆有皇家家训所肇始的政治文化基因及其价值底色的基础上,其平民化、社会化、职业化甚或超乎家族性的地域性的特征不断加强,最后发展成为涵括了政治生活、日常家居生活、行业(技能)生活及其角色分工、性别分工等的大教育和大文化。
中国家训文化的萌发—成文期,大致时间为尧舜至春秋战国。这一时期的家训以商周皇家家训群为代表,大多以兴邦治国、为官理政、避免亡族覆宗为主要内容,体现的是维护宗族和宗族国家利益的生存智慧和修齐治平之道,表现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虔诚惕惧心态。尽管其时家训的内容较为零散,多为因事训诫,常表现为一事一诫,且多为庙堂和生活经验的传授,没有形成体系,更缺少理论性,然而皇家家训所肇始的家训精神却伴随中国古代家训文化的发展始终,形成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皇家家训在历史上长期高度发达,其家国情怀、超义务的道德责任感等政治价值取向和人文关怀精神成为主流家训文化精神,并对其他阶层的家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国家训文化的成型-成熟时期,大致时间为秦汉至隋唐。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化以及文化下移和普及,越来越多的家居生活内容、性别角色分工和行业分工进入家训视野,家训文化日益生活化、平民化、社会化和系统化、理论化。先秦之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加入家庭(族)成员的日常起居以及冠(24)冠,指冠礼,亦称结发。加冠,是男子达20岁时举行的成年礼。行此礼后,表示男子已经成人,可以结婚成家了。、婚、丧、祭等礼节仪式的家仪、家教、家规。东汉出现了 “女训”。如蔡文姬的父亲蔡邕的《女训》、文学家和史学家班昭的《女诫》。秦汉至隋唐时期最具时代特点的家训,为两汉之后勃兴的世族大家教育子孙后代的名仕家训,以南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为经典之作。该书的宗旨为“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全书二十篇广泛涉及修身、治家、处世、为学等,其中不少见解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如:提倡学习,反对不学无术;主张“学贵能行”,反对空谈高论;强调学习应以读书为主,又要注意工农商贾等方面的知识等。《颜氏家训》对后世影响巨大,带动中国家训文化在随后的帝制时代以不同形式取得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唐宋年间借助全面推行的科举制走向平民之家。家训平民化的关键在于科举制带来社会阶层的半开放式流动,使入仕为官成为读书人尤其是寒门读书人的人生首选。
中国家训文化的繁盛-巅峰时期,大致时间为宋元明清时期。这一时期家训总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平民化和职业化。不仅产生了以司马光《家范》最具盛名的一批接近平民生活而被一般平民百姓所接受的佳作,而且增添了以往少有的“治生”的行业内容。北宋末年叶梦得的《石林治生家训要略》是较早以治生为主要内容的家训,明确将农、工、商、士四业囊括其中:“出作入息,农之治生也;居肆成事, 工之治生也;贸迁有无,商之治生也;膏油继晷,士之治生也。”而且商的排序不再是末位,实属难得。说明随着经济发展,商业和商人地位逐渐得到提高。当然,北宋人更为推崇的是入仕为官,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便出自北宋影响广泛的启蒙读物《神童诗》。到南宋,已提出士、农、工、商四业“皆为本业”,“同为齐民”。之后,商业和商人的社会地位在明清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明人有所谓“行行出状元”的说法,由冯惟敏在《玉抱肚·赠赵今燕》中首次提出:“琵琶轻扫动人怜,须信行行出状元。”其实,唐朝已有三十六行的说法,南宋周辉在《情波杂录》中有详细记载(25)南宋周辉在《情波杂录》中记载的“三十六行”是:肉肆行、鲜鱼行、海味行、米行、酱料行、花果行、宫粉行、酒行、茶行、汤店行、药肆行、柴行、棺木行、丝绸行、成衣行、顾绣行、针线行、皮革行、扎作行、故旧行、仵作行、网罟行、鼓乐行、杂耍行、彩舆行、珠宝行、玉石行、文房行、纸行、用具行、竹木行、铁器行、陶土行、花纱行、驿传行、巫行。。至宋代,已经增至七十二行,元人又把七十二行转记为一百二十行。如《元曲选·关汉卿》云:“想一百二十行,门门都好着衣吃饭。”明代的三百六十行之说,最早见于田汝成《游览志余》:“杭州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也。”清代徐珂在《清稗类钞·农商类》中言明:“三十六行者,种种职业也。就其分工而约计之,曰三十六行;倍之,则为七十二行。”明代大儒王阳明在《节庵方公墓表·乙酉》中更是提出振聋发聩的“四民(26)指士、农、工、商。异业而同道”,“士可以为商,商可以为士”,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贱商”观念,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肯定各个行业尤其是商贾的社会意义和价值,鼓励家族营生和个人治生的多样化,以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的内容教导子孙,成为明清家训中的重要内容。正如清朝汪辉祖的著名家训《双节堂庸训》所说:“如不能习儒, 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技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明清时期出现了专门的商业教育读本,如商业蒙训读本《营生集》,其广泛涉及重商立业、经商之道、致富感恩回馈等诸多内容,被后世商界誉为“营生宝典”。
明清商贾家训是在中国家训文化史上值得浓墨重彩记上一笔的丰厚遗产。与以往的商贾家训不同,明清商贾家训具有极其鲜明的多元职业价值取向和崇商重商的特点,同时具有地域性文化特征,以明清商帮家训最为典型。所谓商帮是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商人们自发组织形成的一种以血缘加地缘为纽带、由家族性亲缘组织如商号、商铺、作坊、工厂等扩展开来的新型地缘性商业组织。商人们利用其天然的乡邻关系+宗族关系,组织形成一个个各具特色的以地域为中心的商帮,开始以群体形象活跃于历史舞台,目的是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利用群体的力量更好地保护其家族营生或家族产业。以晋商、徽商为例,二者都凭借各自的家训文化,维系庞大家族的人丁兴旺和家业兴盛,前后数代人活跃在商业领域长达四五百年,商绩斐然,声名远播。徽商主张“贾而好儒”、“学而优则仕”和“学而优则商”并行不悖。并非教育后辈儿孙人人皆外出行贾,而是鼓励才华出众的子弟科举入仕,坚持以学促商,以商养学,大力兴办教育。徽商主要沿袭家族式经营和管理,其约束力量主要来自于宗族内部,通过具有鲜明宗族色彩的方式如族规、会规来对商人进行联合制裁。晋商则提倡“学而优则商”,更崇商重商,教导后辈子弟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鼓励家族中最优秀的学子经商。在从商理念上保持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关公为自己的商人信仰,在经营方式上主要采用联号制、伙计制和人身顶股制,实际上是经过改造的传统家族经营方式加上具有超越家族意义的现代企业经营方式的某些特点,如制定正式的规则、章程进行激励和约束,注重合同,强调契约精神,任人不唯亲、某些职位只可任用家族外人员等,在治理模式上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存在契合之处。可见,商帮实质上是一种扩大的家(宗)族亲缘组织。相应地,商帮家训可视为以往传统意义家训的拓展、强化和创新。总体上看,明清商帮家训中除了一般家训中必有的立人和治家内容以外,都特别重视信誉、提倡俭约、主张善待客户和雇员等经世济民的经商之道和商业伦理精神。后者不仅凝结于其家训之中,通过教导子孙后代世代传承下去,而且以不同的方式落实到家族企业的经营理念和治理模式中,成为中国家训文化中一份特殊的遗产。
最后,中国家训文化在汉字(或儒家)文化圈中的传播和发展,直接影响日本等国家训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这些国家特别是日本家训,在学习借鉴中国家训文化基础上的创新性发展,尤其是其近现代成功转型的经验值得深入研究和借鉴。
中国家训文化在海外儒家文化圈的传播型塑了日本、越南和韩国等国的家训文化。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家训文化与中国同本共源,深受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各国基于自身的社会实际情况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因而呈现出与中国不同的特点和历史遭遇。以日本为例。日本家训是在中国传统家训和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史载,《颜氏家训》在平安时代传入日本,很快当时的日本皇亲贵族中出现了以家训为形式的训诫条例。到奈良时代,约公元769年左右,日本第一部家训《私教类聚》问世。作者吉备真备曾作为遣唐留学生和遣唐副使先后两度赴唐朝为官生活了二十多年,其晚年回到日本所作的这部《私教类聚》参考了《颜氏家训》而著成,其中频繁引用《颜氏家训》、《论语》和《史记》等典籍的内容。虽然日本家训文化自产生伊始就已深深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与同期的中国唐宋时期家训相似,日本家训也具有鲜明的社会化和职业化特征,但由于日本“家”的特殊性(包括非血亲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多样化,其社会化和职业化甚于中国。而且,日本家训虽也起始于皇亲贵族,后遍及官宦、武士、商人、农民等各阶层,但以武士家训和商人家训最为常见。在日本明治维新后近代资本主义兴起背景下,出于完善企业治理和延续家业的需要,商人家训更是后来居上、异军突起,得到全面发展和繁荣兴盛。日本发达的商人家训文化,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商业人才的培养、推动了商业本身的繁荣,为日本近现代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组织基础,而且对日本近现代企业以“家宪”和“社是”、“社训”为主要形式的经营管理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家宪”、“社是”和“社训”是日本传统商业家训文化得以传承、延续、创新和现代转型的结果。或者说,日本近代以后的家训在形式上多以“家宪”相称,以突出家训作为家之法律的效力。换言之,日本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其传统家训文化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反而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且在日本近现代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动力作用。反观日本家训的源起国——中国,进入近代以后,传统家训文化逐渐衰落。不少人把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家训》视为“传统家范终结的标志”,认为其后传统家训被送进了历史博物馆。就连明清商帮家训,其命运也和日本商业家训截然不同。即便是最接近现代化边缘的晋商、广州十三行、潮商等,同样没能逃落衰变的命运。商帮大多不复存在,其所创立的百年老字号也所剩无几,至今仍活跃在企业界或商业界的更是稀少。相反,至今日本许多企业、商号历经百年沧桑依旧保持良好,受益于传统家训文化及其现代转型的日本社会,其整体良好的职业素质和职业伦理精神,包括“匠人精神”,令世人印象至深。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传统的传承和开新能否为我们带来某种启示?有哪些宝贵经验可资借鉴?中国传统家训文化该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深入研究。
四、结语
中国家训文化源远流长。历经漫长的历史发展,传统家训文化的内涵和意义已经变得极为丰富而且多元。中国历史上的家训文化之“家”早已不限于狭义的亲缘组织——家族、宗族,而是事实上已包括了“扩大的亲缘组织”。在此,笔者以“扩大的亲缘组织”指代那些以亲缘组织为基础而形成的形形色色的地缘性组织,如古代宗法社会或“家天下”国家,以及明清时期在宗族基础上组织形成的地缘性商贾群体组织——商帮。日本家训的“家”也是“扩大的亲缘组织”。相应地,中国历史上的家训之“训”亦早已不限于狭义的家庭教育,而已发展成为广泛涉及饮食起居、修身养性、为人处事、致学求仕、择业治生、治国理政等丰富内容以及从价值取向、精神追求和文化氛围到生活方式、生产经营管理方式等多层面的大教育和大文化。进言之,中国传统家训文化作为涵括政治生活、日常家居生活、行业生活及其角色、性别分工等广阔生活领域和职业领域的大教育和大文化,实际上已成为古人以家族为基元,又在相当程度上超越家族的一种社会化教育范式、社会文化类型和社会治理形式,具有现代社会单一家庭教育或学校教育、社会治理无可比拟的包容性和多维性。为此,亟须系统整理传统家训文化资源,重新审视、定位其当代意义,推陈出新,探索实现其创造性转型和创新性发展的形式和路径。一方面,应重视加强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系统梳理和学术研究,包括家训资源的全面收集、整理以及少数民族家训、非文字家训的文字和媒介转存,发掘出更多有益于当代中国的经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道德文化建设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在当下的家训文化研究和家风建设实践中,尚需着力思考“这一份独特的历史文化遗产如何才能真正有益于当下中国社会”?在辨析哪些应该传承及以何种方式传承,哪些不应该保留而须坚决抛弃,传统家训文化如何推陈出新,以何种方式实现其现代性转型和发展等诸多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学习借鉴。相较于拥有汉字与非文字或者官方与民间等多层次传统的中国家训文化,日本并没有自己原生的家训传统,只有来自中国的文献传统,原本种类和资源以及教育规约的理念和形式都远不如中国丰富、系统和多样的日本家训,却能成为日本实现现代社会转型的思想动力之一,其近现代成功转型的经验值得深入研究和借鉴,比较家训学研究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