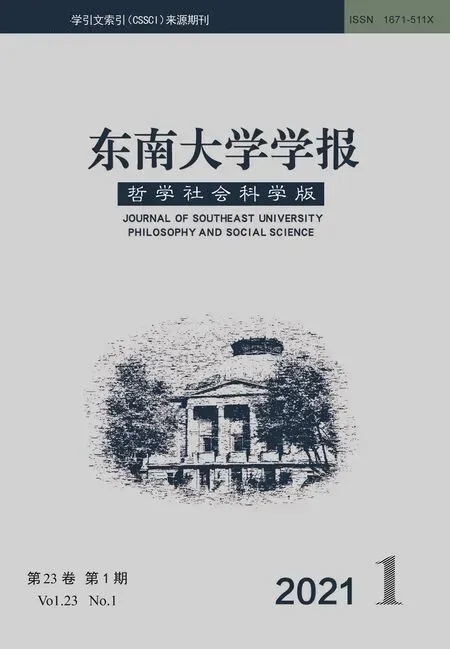社交网络时代影响力营销的广告法规制研究
马 辉
(扬州大学 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一、问题的提出
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不断迭代共同促成了社交网络的兴起,其不仅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交往模式,同时也催生了全新的经济业态,网红经济的异军突起成为社交网络时代最引人关注的经济现象。虽然网红或者网络红人现象的源起可追溯至20世纪末,不过网红经济则是在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网络普及后才开始走入大众视野。社交网络时代“网络化的社会生活方式、庞大的网民市场、日益旺盛的消费需求,使网络走红与经济社会收益变现之间的关联度日益紧密,中国网络社会发展因此出现了一个特有现象——网红经济”(1)杨江华:《从网络走红到网红经济:生成逻辑与演变过程》,《社会学评论》2018年第5期。。近些年来,社交网络营销、直播带货等网红经济模式已经成为我国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据统计,2019年我国社交电商消费者人数达5.12亿人,市场规模达20605.8亿元,同比增长63.2%(2)参见中国互联网协会微商工作组、创奇社交电商研究中心《2019中国社交电商行业发展报告》(2019-08-05)[2020-07-20],http://www.199it.com/archives/912420.html。,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期间,直播带货在拉动内需、复工复产、消费扶贫等多个方面发挥了立竿见影的积极作用。
网红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影响力经济,即在社群化的网络生活中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主体通过各种渠道将其影响力转化为经济收益的各种商业活动之总称(3)参见敖鹏《网红的缘起、发展逻辑及其隐忧》,《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1期;孙婧、王新新《网红与网红经济——基于名人理论的评析》,《外国经济与管理》2019年第4期。。依据在产业链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和收入来源差异,影响力变现可被划分为直接变现和间接变现两种类型。直接变现主要采取商品化模式,网络红人将影响力转化为有形或无形的商品进行销售以从终端用户处直接获取经济收益,其位于产业链中的供给侧一方,打赏、知识付费、网红品牌化运作等商业模式均可纳入影响力直接变现的范畴。间接变现主要采取影响力营销的方式,网络红人运用自身影响力宣传或推介第三方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进而从生产商或销售商处取得收入,其在产业链中充当了供给侧与需求侧的信息媒介,直播带货、隐蔽性广告等营销模式均可被纳入影响力间接变现的范畴。从法律规制的角度来说,直接变现的商品化模式中影响力转化为交易标的,网络红人与终端消费者之间的直接交易关系可通过赠与、买卖合同以及基础性的行为能力等相关法律制度加以调整,不会对既有法律体系带来太大冲击(4)如对于现实生活中引发广泛关注的未成年人网络打赏问题,最高院在《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中明确指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裁判规则实际上是对既有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具体化。。间接变现的影响力营销模式中网络红人开展的宣传推介活动无疑具有商业广告属性,但是其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广告在信息呈现方式、受众选择、说服策略、传播逻辑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由于我国现有的广告法体系制度建构围绕大众传媒商业广告模式展开,影响力营销模式中频繁出现的一些可能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如主体身份不确定、广告与内容混同、责任主体不清晰、劝诱活动引发的冲动购物等,难以在现有的广告法体系中获得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虽然新近发布的《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直播意见》)、《互联网直播营销信息内容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直播规定》)试图对直播带货中的违法广告问题进行规制,如《直播意见》第三条要求执法机关重点查处直播营销中的虚假广告、违法广告,《直播规定》第九条要求直播平台“防范和制止违法广告、价格欺诈等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第十六条、十八条禁止直播运营者和营销人员采取发布虚假信息、流量造假、删除或屏蔽不利评价等方式欺骗、误导消费者。不过,《直播规定》只是简单地将现有广告法禁止违法和虚假广告之规范目标和相关规则转接入直播带货领域,其并未留意到社交网络时代的直播带货广告与传统大众传媒广告在信息传播与劝诱模式上的差异,因此无法对包括直播带货在内的影响力营销广告提供有针对性的制度回应方案。可以说,社交网络时代与大众传媒时代的信息传播模式存在本质性差异,将肇始于大众传媒时代的广告法原理和制度直接套用至影响力营销领域必然会引发削足适履式的违和感。对此,应当首先查明社交网络时代影响力营销的广告信息传播模式,在此基础上审视既有广告法规范体系与影响力营销的不兼容之处,进而方可得出妥当的规制方案。
二、社交网络时代影响力营销的特征
严格来说,影响力营销并非网络时代的新生事物。早在20世纪初,随着广播、电影、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兴起,利用影视、体育明星等名人形象开展广告宣传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营销手段。名人作为获取注意力的载体,能够为所代言的商品带来更高的认知度和品牌信用度,从而影响消费者群体的选择(5)孙婧、王新新:《网红与网红经济——基于名人理论的评析》,《外国经济与管理》2019年第4期,第22页。,明星广告故而可被视作影响力营销的一种方式。随着社交网络时代的到来,去中心化、交互式的自媒体传播成为社群化网络生活的主要信息媒介,其一方面为大量网络红人的出现提供了沃土,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肇始于大众传媒时代的影响力营销模式。与大众传媒时代的广告营销活动相比,社交网络时代的影响力营销具有去中心化传播、圈层化受众、社群认同式劝诱三个特征。
1.去中心化传播
大众传媒时代的信息传播呈现为中心化的“点—面”结构,大众传媒机构作为信息的生产者、分发者和把关人,在信息传播中处于中心节点的位置。社交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则呈现为去中心化的网状结构,大量可以独立发布和接受信息的自媒体构成了网络上的信息节点,每个信息节点均可成为规模各异的信息传播网络中心(6)代玉梅:《自媒体的传播学解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5期,第5页。。需要说明的是,去中心化并不意味着没有中心,网络空间的海量信息远远超出普通网民的信息处理能力,面对四面八方涌来的巨量信息,网络用户惯常采取的信息筛选方案是从其信任的信息节点处获取信息,相应地受到大量用户信任或认可的网络红人、意见领袖等会成为信息传播的超级节点,从而产生“再中心化”的现象(7)李良荣、郑雯:《论新传播革命——“新传播革命”研究之二》,《现代传播》2012年第4期。。不过从媒介功能角度来说,超级节点和普通节点均拥有相同的信息生产、分发与传播功能,只是由于影响力的差异导致两类节点的传播范围和效果有所不同。
对于广告营销而言,去中心化传播意味着网状结构上的任何一个信息节点均可以成为广告媒介。一方面,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超级节点无疑会成为广告投放的绝佳渠道,近些年来网络红人广告报酬节节攀升即为明证(8)罗亦丹:《短视频网红如何炼成 MCN成“网红工厂”,头部播主月接300万广告》(2018-05-30)[2020-08-03],http://www.bjnews.com.cn/finance/2018/05/30/488935.html。;另一方面,普通节点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广告营销,如在商家折扣优惠的引诱下发布包含商业推广内容的社交网络信息,基于圈层认同感转发共享明星、网红的广告信息等现象屡见不鲜。可以说,去中心化传播模式为社交网络时代广告信息的爆炸式增长提供了技术支撑,网状结构下围绕超级节点展开的影响力营销可以通过与普通节点的互动产生更好的推广效果。
2.圈层化受众
社交网络时代自媒体传播的受众具有典型的圈层化特性。社交网络的群体聚集功能有助于那些在兴趣爱好、生活方式、行为等方面相同或相似的人建立起志趣相投的网络社群(9)孙国强等:《西方社交网络研究进展与未来展望》,《情报科学》2019年第2期,第173页。,前社交网络时代(BBS、论坛、社区)的网络群聚通常围绕特定的话题或事件展开,而社交网络时代则是通过身份建构和群体认同形成稳定化的网络社群(10)杨江华:《从网络走红到网红经济:生成逻辑与演变过程》,《社会学评论》2018年第5期,第20页。。虽然网络社群可以自由且几乎无成本地加入和退出(如点赞、关注、发起群聊等),不过由于网络社群的形成源于用户依照自身偏好和需求而进行的主动选择,作为身份认同与群体归属产物的网络社群因而具有较强的黏性,社群成员在构建集体认同的过程中拥有更强烈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愿望,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圈层化信息传播模式。相比于大众传媒时代受众的广泛性,圈层化传播模式下的受众通常为数量较少但却拥有更强群体认同感的社群成员。如果传播的信息符合圈层受众的偏好和需求,则圈层受众会对该信息表现出更强的参与性和回应性(11)刘燕南:《从“受众”到“后受众”:媒介演进与受众变迁》,《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3期,第8页。,成员间的互动、分享有助于信息在圈层内部不同节点间的迅速扩散。
圈层化受众之间的信息传播体现出明显的社交属性,即受众之间的信息传递与社交互动同步,因此广告营销必须嵌入圈层化受众之间的社交互动才能实现信息的有效传递。网络红人、意见领袖等“圈层名人”正是在与圈层受众的社交互动中获取了巨大的影响力,自然成为理想的圈层受众广告媒介。以直播带货为例,相比于“口红一哥”李佳琦、“淘宝一姐”薇娅等网络红人在直播带货领域的斐然业绩,大众传媒明星的直播带货却频频出现惨淡收场的结局(12)参见揭书宜《明星直播带货频现翻车背后:有些品牌不介意,为何拼不过网红》(2020-07-16)[2020-08-05],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sh/2020/07-16/9239551.shtml;张钟尹《明星直播带货频“翻车”如何戳破流量泡沫?》(2020-07-13)[2020-08-05],https://tech.sina.com.cn/roll/2020-07-13/doc-iivhvpwx5193104.shtml。。这种强烈的反差表明,知名度在面向圈层受众开展的直播带货中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通过与圈层受众的即时互动建构集体参与式的狂欢化场景才是直播带货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13)新冠疫情期间出于拉动内需、扶贫以及扩展销售渠道等多种目的,地方官员、企业高管、新闻主播等线下世界的名人纷纷试水直播带货,为了拉近与受众的距离,线下名人常通过卖萌的方式与受众互动,从而产生了较好的营销效果。参见闫玉刚、宫承波《狂欢化与去狂欢化——基于新冠疫情期间直播带货传播现象的冷思考》,《当代电视》2020年第6期,第95-96页。。总体上来说,由于圈层化受众不仅仅是信息的接收方,同时也是信息传播链条上必不可少的参与者,这也决定了大众传媒时代以信息单向传播为特征的明星代言广告模式自始不适用于社交网络上的影响力营销。
3.社群认同式劝诱
社交网络时代的到来为广告劝诱提供了新的契机。圈层化受众的形成客观上产生了对传统大众传媒受众的群组细分效果,(14)周大勇、王秀艳:《互联网 “圈层”传播与新受众的信息反应》,《图书馆情报学》2017年第21期,第36页。辅以算法推荐、数据挖掘等新兴网络技术,广告发布者可以更加精准地提供符合圈层受众偏好的信息。同时,圈层内部的信息传播与成员间的社交互动同步,圈层成员践行社群认同和确认身份归属的主要路径是围绕特定信息展开的讨论、分享乃至生成相关决策,高度的参与性使得圈层成员更乐意对包括广告信息在内的话题做出积极回应,从而极大提升了广告的传播效果和劝诱效果。相应地,网络红人、意见领袖等圈层名人可以隐性或显性地将广告信息嵌入圈层互动的主题,在建构和维系群体认同的互动交流中完成广告劝诱。
三、影响力营销的广告法规制困境
我国《广告法》在2015年修订时增加了互联网广告的相关规范,2016年原国家工商总局发布了《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以规范网络广告活动。不过现有的广告法制度框架和规制理念诞生于大众传媒时代,其规制的典型场景是以大众传媒机构为传播中心向不特定公众进行单向度的广告信息发送,对于互联网广告的规制更多是将传统的线下规制方案准用于线上活动(15)宋亚辉:《虚假广告的法律治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41-242页。。由于社交网络时代广告信息的去中心化、圈层化互动传播模式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广告迥然相异,这也导致既有的广告法规制框架面对社交网络影响力营销时不免捉襟见肘,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营销行为的法律性质认定难题
《广告法》将商业广告界定为“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传播活动,其构成要件包括商业推销之目的、广而告之的形式以及指向特定的商品或服务(16)宋亚辉:《虚假广告的法律治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5页。。一般认为,作为信息媒介活动的广告行为应当具有标出性,即在外观和内容上应当区别于非广告信息,产业链条上独立于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影响力营销过程中往往出现欠缺标出性的现象,从而引发了行为法律定性的困境。
首先在信息外观上,影响力营销过程中惯常采用的方式之一是将商业推广信息隐匿于社交互动信息之中,导致广告信息与非广告信息的混同。虽然早在大众传媒时代,软文广告、植入广告等隐藏广告信息标出性的现象就已经普遍存在,但是对于此类隐蔽型广告的抽象法律属性界定通常不存在争议,理论和实务界更为关注的问题是现实层面上的如何监管(17)如在软文广告规制的一篇代表性文献中,应飞虎、葛岩指出从经济活动的性质来看,软文广告具有商业广告的性质,规制难题在于软文广告的危害更为隐蔽,执法难度更大以及某些情形下执法机关的弱势。参见应飞虎、葛岩《软文广告的形式、危害和治理——对〈广告法〉第13条的研究》,《现代法学》2007年第3期;在植入广告规制的代表性文献中,李剑指出植入广告仍然是付费的信息传递方式,应被界定为商业广告,对于植入广告的规制应以可识别性为重心。参见李剑《植入式广告的法律规制研究》,《法学家》2011年第3期。。影响力营销中的隐蔽性广告当然同样面临相似的现实监管难题,不过需要考虑的一个先决性问题是借助社交网络平台发布的隐蔽性商业推广信息是否应当被认定为商业广告。即便影响力营销中存在MCN机构(Multitude Channel Network多渠道网络机构)、经纪公司等商业组织的参与,但信息发布仍然是以圈层名人的个人名义实施,其无疑具有私人言论的形式表征,内容也往往围绕生活记录、心得体验等有助于建构社群认同的主观感受信息加以展开。由于私人言论自由在法律体系中的较高价值位阶,传统上法律对于私人言论的干预力度远低于商业言论,尤其是当广告主提供的经济利益不高时,如赠送产品或服务、提供优惠券或折扣等,私人言论中融入具有商业推广目的的信息是否必然导致其转化为应受规制的广告信息无疑仍存商榷空间。
其次,影响力营销在产业链中可能与销售环节混同,引发行为定性困境。大众传媒时代发挥信息中介功能的广告行为在时间和空间上独立于生产和销售环节,但网络空间开展的直播带货实现了广告推广与销售行为在时空上的无缝对接融合,行为的共时性给法律属性界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究竟将直播带货界定为单一的广告行为或销售行为,还是将其视作同时实施的两种不同属性的行为,抑或创设一种有别于广告和销售的全新法律行为类型,理论与实务部门尚未形成统一意见。如《直播意见》仅仅指出“直播内容构成商业广告的”应承担《广告法》上的责任和义务,对于直播行为什么情形下构成商业广告,不构成商业广告的行为如何定性等问题则语焉不详。《直播规定》虽然对于直播中的信息发布设置了具体的行为规范,但是对于该行为属于独立的广告行为还是附属于销售行为则并不明确(18)《互联网直播营销信息内容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第十六条: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从事互联网直播营销信息内容服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社会公序良俗,真实、准确、全面地发布商品或服务信息,不得有以下行为:……该条文中并未明确指出应当遵守《广告法》之规定,表明立法者有意回避了对于直播营销中信息发布的行为定性问题。。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新增的互联网营销师职业工种则将广告推广与签订合同一并纳入直播营销行为的范畴(19)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关于对拟发布新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公告》(2020-05-11)[2020-08-20],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wgk/gggs/tg/202005/t20200511_368176.html。。直播带货中广告行为与销售行为的混同无疑会给广告法责任的施加带来障碍。
2.信息传播主体的身份界定困局
依据不同参与者在广告传播过程中的功能和地位,我国现行《广告法》将其类型化为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和广告代言人四类主体,并设定了相应的行为规范和责任机制。但是由于影响力营销与大众传媒广告在信息传播模式上的差异,圈层名人、MCN机构、经纪公司、网络平台等影响力营销的诸多参与方难以简单地被归入既有的类型化广告主体。
一方面,影响力营销中常出现广告制作、发布、证明推荐等多种媒介行为由同一主体实施的现象。如小红书、微博等社交平台上的美妆博主、时尚大V等圈层网红通常自行设计广告内容并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同时以自己的名义向圈层受众推介产品,同一主体发挥了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和广告代言人的三重功能。直播带货兴起后产业资本开始进入影响力营销领域,MCN机构、经纪公司等可以为其自行培养或签约的网红主播提供内容制作方面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广告经营者的功能,不过信息仍然通过网红主播的自媒体并以主播的名义发送,且直播带货过程中主播为了提升劝诱效果需要与受众保持实时互动,因而会对广告内容进行即时的增减,于此仍然会出现广告制作、发布、代言集于一身的情形。
另一方面,影响力营销中也出现了发挥部分传统广告主体功能的情形。如MCN机构通过素材筛选、创作指引、专业把关等方式参与广告内容制作(20)MCN机构本质上可被视作沟通内容生产者(网红)、平台、广告主的媒介,其可以通过将众多能力相对薄弱的内容生产者聚合起来建立频道,并帮助内容生产者更好地实现分发和商业价值变现。MCN机构会结合广告主需求、受众偏好、营销方案等参与内容策划、选题把控等内容生产环节。参见郭全中《MCN机构发展动因、现状、趋势与变现关键研究》,《新闻与写作》2020年第3期,第78-79页。,此种参与性活动可否被视作独立的“广告设计、制作”,进而将MCN机构等发挥辅助性功能的主体界定为广告经营者则不无疑问。《直播规定》虽然要求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遵守相同“禁止发布虚假信息”等行为规范,但是并未直接将此类规范的渊源诉诸于广告经营者或发布者义务(21)《直播规定》第十六至第十九条设定了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的行为规范,虽然条文表述中有“禁止发布虚假信息”(第十六条)、“不得以暗示等方式误导用户”(第十七条)等规定,但是《直播规定》并未明确此类行为规范的上位法渊源是什么,因此无法从条文表述中推定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的法律主体身份。。此外,网络平台为影响力营销提供了信息传播的虚拟场所,客观上发挥了信息发布的功能,但是其通常不负有与广告经营者或广告发布者相同的信息审核义务,将其界定为大众传媒时代充当信息“把关人”角色的广告发布者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嫌。可以佐证的是,《电子商务法》只是要求互联网平台负有制止违法广告的义务(22)《互联网广告暂行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未参与互联网广告经营活动,仅为互联网广告提供信息服务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对其明知或者应知利用其信息服务发布违法广告的,应当予以制止。该条文表明监管者并未对网络平台施加与广告发布者相同的信息审核义务,其规范结构与避风港规则较为类似。,《直播意见》仅规定电子商务平台对直播活动进行推广宣传构成商业广告的,须承担广告经营者或发布者责任,《直播规定》同样要求直播平台负有防范违法广告的义务,但是并未直接规定平台承担广告经营者或发布者责任。可以看出,现有立法只是基于MCN机构、网络平台在广告信息传播中的功能或作用要求其承担特定的行为义务,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行为义务设定与法律主体身份界定之间的关联性,表明立法者并不倾向于将MCN机构、网络平台直接纳入广告经营者或发布者的范围,其原因可能在于此类机构在信息传播链条上发挥的功能与传统大众传媒时代广告经营者、发布者不尽相同。
3.行政监管与民事追责的障碍
现有的《广告法》采取了公法责任与私法责任并行的实施机制,公法责任由行政监管加以落实,私法责任则通过私人主体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加以实现。前述主体身份与行为属性认定所面临的问题无疑会延续至法律责任施加的环节,如圈层名人究竟承担何种类型主体的法律责任,直播带货过程中主播的推广行为应承担广告法上的责任还是销售合同责任,如何对以个人观点出现的隐蔽性广告施加责任等。除却这些主体身份和行为性质认定困境延续到法律责任环节引发的问题外,社交网络时代影响力营销的信息传播模式也会给法律责任的落实带来新的挑战。
首先,影响力营销的去中心化传播模式造成了信息源的爆炸式增长,对所有自媒体信息节点进行全方位的监管问责显然远远超出了行政机关的能力范畴。传统上借助行业协会或传媒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实现自律监管在自媒体时代难以奏效,原因在于一方面自媒体数量众多且并非专门性的广告经营者,要求其加入并受到广告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另一方面在于自媒体并非专业传媒机构,且大量的自媒体甚至并不具有组织形式,因而欠缺传统大众传媒机构类似的内容编辑与广告部门之间的内部隔离机制,自媒体从业人员亦普遍缺乏隔离内容与广告的媒介伦理意识(23)庞云黠、李志军:《从混同到明示——自媒体内容与广告界限的伦理素描及探析》,《当代传播》2019年第1期,第104-107页。。因此,传统针对大众传媒机构展开的行政监管、行业自律监管以及组织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难以在去中心化的自媒体传播领域发挥效用。
其次,广告法的规制重心是虚假广告,而圈层名人发布的信息固然包含了部分可以进行真伪界定的事实信息,如产品或服务的功能、质量、规格等,但是由于影响力营销过程中的广告劝诱建立在社群认同的基础上,因而圈层网红往往更侧重于在和受众互动的过程中分享具有情感驱动性的生活理念、心得体会等主观信息(24)朱春阳、曾培伦:《圈层下的“新网红经济”:演化路径、价值逻辑与运行风险》,《编辑之友》2019年第12期,第7页。,以谋求与受众之间形成情感共鸣,并将这种情感认同与特定的消费实践相关联从而完成广告劝诱。在圈层化传播所建构的仪式性狂欢场景中,这种围绕情感认同展开的广告劝诱会产生更强的“符码操纵”效果(25)汪振军、乔小纳:《新兴媒体环境下的“符码操纵”——读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第102-103页。,引发消费者福利损失。但是由于涉及主观情感的信息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以真伪判断为基础的虚假和误导性广告法律责任自然难以施加(26)传统上,虚假广告的认定需要从客观层面检验信息的真伪,误导性广告的认定虽然需要诉诸于受众的主观认识,不过只有当受众的主观认识指向特定的“事实内核”时,方需要法律规制。参见程子薇《事实陈述、意见表达与我国误导性司法认定标准的构建》,《山东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四、广告法的回应路径:准用、改良与重建
上述分析表明,广告法既有的“主体—行为—责任”框架难以对影响力营销行为形成有效的制度约束,其原因在于广告法内置的大众传媒广告传播模式与社交网络时代的自媒体广告传播模式之间的差异。现有理论指出,对于互联网经济引发的交易结构变化,法律体系可通过准用、改良与重建三种模式予以回应(27)宋亚辉:《网络市场规制的三种模式及其适用原理》,《法学》2018年第10期。。就影响力营销而言,其发挥了与传统广告相同的信息媒介功能,这构成了准用既有广告法的基础,同时传播模式和劝诱方式的独特性也征引出改良既有制度与建构新制度的必要性。
1.广告法价值追求的准用
准用的基础在于新生事物与旧事物的同质性。虽然社交网络时代的影响力营销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广告营销在具体的行为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两者具有功能上的同质性,即都作为沟通供给侧与需求侧的信息媒介。这种新旧事物的功能同质性为法律规制的延续性提供了正当性基础,不过具体行为方式的差异意味着将广告法条文照搬到新的影响力营销领域并不具有可行性,准用当采取移转法律价值追求至新的社会环境之操作方案。
通说认为,广告规制的正当性在于解决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市场失灵问题(28)Robert Pitofsky, Beyond Nader: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the Regulation of Advertising”, Harvard Law Review, 1977,90(4), p.669.。具体言之,作为信息媒介的商业广告虽然有助于缓和经营者与消费者群体间的信息不对称,但是虚假性或误导性广告的频繁出现导致消费者的意思自治受到扭曲。其不仅造成微观层面的消费者利益损害,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由于消费者知情理性决策构成了市场机制有效运作的基础性条件,虚假或误导性广告对微观交易知情理性决策的破坏引致宏观层面的需求规律约束效用难以发挥,进而产生市场失灵的结果。
由此视之,广告法规制的终极价值追求是维持市场机制或需求规律的有效运作,其手段为通过禁止虚假或误导性广告确保消费者的知情理性决策得以实现。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广告相比,虽然影响力营销过程中也存在虚假或误导广告的现象,不过圈层化传播的特性意味着其在多数情况下主要采取主观认同式的广告劝诱方法。从个体层面来说,主观劝诱性信息无疑会影响消费者的决策,尽管这种影响是否可达到与虚假或误导性信息同等程度的意思自治侵害后果仍有待商榷。不过从市场秩序层面来说,社群认同式劝诱引发的圈层受众非理性决策显然存在扭曲需求规律的隐患。因此,广告法维持市场机制有效运作的价值追求仍应在影响力营销领域加以延续,法律规制的具体目标仍应为确保消费者的知情理性决策。只是其所面临的问题场域发生了转变,即从规制影响知情决策的虚假性或误导性信息转变为规制影响理性决策的主观劝诱性信息。
2.广告法规范体系的改良
由于信息传播模式的差异,产生于大众传媒时代的广告法规范体系自然不能照搬至社交网络时代的影响力营销领域,必须结合影响力营销的信息传播特质对既有的“主体—行为—责任”规制框架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良。
首先,对广告主体的类型进行功能导向的重新定位。现有的广告主体类型化区分源于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和广告代言人在大众传媒广告信息传播链条上的不同功能。广告主作为信息传播行为的发起者,广告经营者负责信息内容的制作,广告发布者提供了信息传播的媒介平台,广告代言人则以自身的知名度增强了广告信息的受关注度和可信赖度(29)广告法释义中广告监管部门指出广告代言是对代言人人格特征的商业利用,代言人以自己名义表达的推荐、证明意见对商品起了隐形担保的作用。参见国家工商总局广告监督管理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释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第11-12页。。影响力营销的去中心化自媒体传播模式中,广告信息的传播链条被压缩,广告主作为信息传播发起者的地位并无太大改变,不过在传播环节常出现多重功能集于一身的现象。信息内容的生产、发布以及对信息内容的增信往往是以圈层名人的个人名义完成。即便MCN机构、经纪公司等机构也可能直接或间接参与信息内容生产,但是一方面其通常隐匿于自媒体背后,难以识别此类机构在信息生产环节的具体参与程度,另一方面,自媒体交互式传播意味着在信息传播前台的圈层名人与受众互动时需要对信息内容进行即兴发挥,因此MCN机构、经纪公司在信息生产方面的功能与大众传媒模式下的广告经营者无法等量齐观。此外,网络平台虽然提供了信息发布场所,但是其与大众传媒模式下的广告发布者亦不能完全等同。大众传媒(包括门户网站)模式下信息发布渠道具有物理层面的资源稀缺性,广告发布者通过对信息发布渠道的控制实现收益,其构成了广告发布者的主要盈利渠道。自媒体传播模式下物理层面的信息发布节点不再具有资源稀缺性,社交网络平台也无需通过向使用信息节点的用户收费作为其主要的经济回报渠道(30)需要说明的是,淘宝、京东等电子商务平台仍然会向平台上的商家收取网络空间的虚拟店铺使用费,并为直播带货提供专门性的网络服务,但是这种费用的收取依附于销售行为,常采取交易额佣金的方式收取,并非单独针对营销信息的发布,电商平台往往会对经营者资质以及产品或服务类型进行审核,并不对广告信息发布进行过多干预。。因此互联网平台通常不对包括广告信息在内的信息发布行为进行大众传媒式的严格控制,自然不能将其直接视作与大众传媒发挥相同信息发布功能的广告发布者。可以说,自媒体传播模式下圈层名人在外观上具备了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广告代言人的三重功能,MCN机构、互联网平台仅仅是部分发挥了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的功能。因而,圈层名人应被视作兼具三重功能的广告运营者,而MCN机构、互联网平台则只有当能够证明其发挥了广告制作、发布功能时,方可将其视作在广告传播链条上发挥辅助功能的广告经营者或发布者。法律规制的重心应作出相应调整,即从大众传媒时代以广告经营者、发布者等大众传媒机构为中心的规制模式转变为自媒体时代以圈层名人为中心的规制模式。
其次,在行为规范方面,现有的广告法以打击虚假和误导性广告行为为中心。社交网络时代的影响力营销中,虚假广告和误导性广告的问题仍然存在,既有广告法的行为规范自然应当沿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影响力营销中广告行为往往在外观上与其他行为混同,如圈层名人在社交网络分享的呈现为个体主观感受的隐蔽性广告信息,其在外观上具有私人言论的性质,再如直播带货过程中广告劝诱行为与销售行为同步完成,行为在时空层面上同样难以分离。这种行为的混同性导致既有广告法的诸多行为规范和责任规范难以实施。圈层名人可能主张其行为属于个人言论,或者其作为经营者的销售代理人,不受广告法行为规范的限制。虽然我国《广告法》第十四条规定:“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能够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不过,该规则主要针对的是大众传媒将广告信息与新闻报道混同产生的存在误导效果的软文广告现象,其约束对象限于大众传播媒介。对此,应当变更该规则的适用对象,要求从事自媒体传播的圈层名人尽到广告标识义务。考虑到不同类型的广告信息混同现象,广告标识规范应有所差异。对于将广告信息隐匿于个人言论的现象,可以参照美国FTC的“社交网络影响者披露规则”,要求圈层名人对于社交网络上发布的包含荐证信息的言论,若其与信息涉及的品牌商或经营者存在实质性利益关系(包括支付金钱报酬或者非金钱性质的赠品、折扣等),那么应当使用清晰且简单的语言(如广告、赞助等标签)对信息进行标注(31)Ftc Disclosures 101 for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2019-11)[2020-11-10], https://www.ftc.gov/tips-advice/business-center/guidance/disclosures-101-social-media-influencers.,从而实现对广告信息和个人言论的有效区别。对于将广告劝诱与销售活动混同的现象,虽然受众通常可以识别出该行为的商业属性,不会产生隐蔽广告类似的误导效果,不过考虑到广告行为与销售行为的时空同步性,为了避免直播带货中圈层名人通过销售代理身份规避自身的独立责任,亦应要求其做出广告标识以明确行为属性,从而为事后的追责奠定基础。
再次,在责任规范方面,上述分析表明,影响力营销模式下广告规制的对象应以圈层名人为中心,行为规范方面需要凸显圈层名人的广告标识义务,责任规范自然应当依照主体和行为规范做出相应的调整。现有的《广告法》责任规范建构了三重责任体系,其中广告主对于绝大部分违法广告承担行政或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在明知或应知存在违法广告仍然从事广告制作、发布的,与广告主一并承担责任,广告代言人只在特定情形下承担责任。总体上来说,现有的责任规范重心在于发起广告活动的生产商或销售商和从事广告制作传播的大众传媒机构。影响力营销模式下的自媒体信息传播过程中,由于圈层名人发挥了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以及广告代言人的多重功能,仅从广告代言的角度界定圈层名人的责任显然并不合理,应结合圈层名人在信息传播中的功能重构责任规范的重心。原则上应当要求圈层名人承担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的责任,除非圈层名人可以证明MCN机构、互联网平台等在广告内容生产、广告信息发布中具有主导性作用,圈层名人仅仅发挥传声筒式的代言人角色,此种情形下圈层名人可以承担广告代言人责任,否则应承担更重的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责任。此外,现有广告法将违反标识义务的法律责任施加于从事广告发布的大众传媒机构(《广告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自媒体传播模式下圈层名人发挥了广告发布者的功能,承担标识义务的法律责任自无疑义,不过需要结合不同的信息传播模式设定差异化的法律责任,以激励责任主体主动履行标识义务。对于将广告行为与个人言论混同的情形,由于自媒体通常并不存在传统大众传媒的科层制组织机构及广告部门与非广告部门的内部隔离机制,广告行为的隐蔽性比传统的大众传媒软文广告更强,圈层名人广告标识义务的落实无疑会导致更高的执法成本从而造成法律责任的落空(32)传统大众传媒软文广告执法过程中,软文广告的不易识别构成了巨大的执法障碍。参见应飞虎、葛岩《软文广告的形式、危害和治理——对〈广告法〉第13条的研究》,《现代法学》2007年第3期。。对此,可以将广告主一并纳入标识义务的责任范围,即只要广告主与圈层名人之间存在实质性的利害关系,则要求广告主必须提醒并监督圈层名人在发布具有推广效果的社交网络信息时尽到标识义务,圈层名人可以通过证明广告主未要求其进行广告标识为由豁免责任。对于直播带货等将广告劝诱与销售行为混同的情形,考虑到既有法律体系中销售商承担更重的法律责任,对于直播带货这种外观上难以识别行为属性的现象,可通过要求圈层名人在未尽标识义务时承担销售商责任的方式激励其主动揭示行为性质。若圈层名人尽到标识义务,则其仅承担广告法上责任,反之则可以对其施加销售商责任,以此激励圈层名人主动履行标识义务。
3.广告法新型制度的建构
既有的《广告法》将虚假和误导性广告作为规制重心,行为规范和法律责任的设定均围绕该重心展开。社交网络时代的影响力营销中,圈层名人发布的广告信息中自然也会有虚假或误导性内容,其无疑应当受到《广告法》的严格规制。但是对于影响力营销引发的冲动购物、情绪化购物等非理性消费行为,旨在规制虚假和误导性广告的制度体系显然无能为力。对此,应建构全新的制度予以回应。
广告法对于虚假和误导性广告的规制旨在保障广告信息的真实性,不过现有的立法并未明确界定何谓“真实的商品信息”(33)邵海:《虚假广告治理中的侵权诉讼》,《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2期。。学界通说认为信息的真实性包含两个维度:其一,若特定信息可以从客观层面加以证伪,则该信息应被视作虚假信息(欺骗性广告)受到法律规制;其二,若特定信息足以使消费者产生主观层面的错误认识,则可以将其视作误导性信息(误导性广告)加以规制(34)宋亚辉:《虚假广告的法律治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3-54页。。不过无论是客观层面的虚假信息还是主观层面的误导性信息之认定,其共同之处在于均需要提炼出来一个客观存在的或者主观建构的事实,只有当信息与该事实不符时,方可视作虚假或者误导性信息(35)程子薇:《事实陈述、意见表达与我国误导性司法认定标准的构建》,《山东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反之,若广告信息不会使受众产生对事实的错误评价,则只能被视作无需规制的艺术性夸张(36)泛泛而谈的艺术性夸张不受广告法规制,其有四个特征:泛泛且模糊、所作陈述无法计算或不可证明、陈述具有主观性、消费者不会信赖。美国法院也多认为艺术性夸张性质的非事实言论不会产生舞蹈效果。参见黄武双《不正当比较广告的法律规制》,《中外法学》2017年第6期。。由此视之,影响力营销中圈层名人虽然也会传播部分与交易标的相关的事实信息,虚假和误导性制度因而仍有适用空间。但是对于圈层名人传播的旨在激发受众情绪反应的信息,尤其是直播带货中主播出于建构虚拟狂欢场景、强化社群认同、渲染消费情绪等目的而传播的情感驱动性信息,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其会诱发消费者的冲动消费、过度消费等非理性行为(37)相关的研究参见肖珺、郭苏南《算法情感:直播带货中的情绪传播》,《新闻与写作》2020年第9期;李晶、郑珊珊《网络主播对直播带货“仪式”的构建——基于尼克·库尔德里的批判性分析》,《当代电视》2020年第11期;刘洋等《网络直播购物特征对消费者购买行为影响研究》,《软科学》,2020年第6期。,然而由于此类信息并不直接或间接涉及交易标的事实层面之描述或评价,自然无法纳入虚假或误导性制度的约束范畴。
可以说,问题场域的差异决定了旨在保障知情决策的虚假和误导性广告规制天然地不适合解决影响力营销中理性决策受到侵蚀的问题。对此,消费者法中的撤回权制度可以对非理性决策发挥一定的事后救济功能,但是考虑到撤回权实施的高昂社会成本(38)徐伟:《重估网络购物中的消费者撤回权》,《法学》2016年第3期。,更妥当的做法是通过延缓交易的生效时间来对情绪化的非理性决策进行预防性控制。即对直播带货这种建立在即时互动基础上,通过虚拟狂欢场景诱导消费者非理性决策的广告劝诱活动设置交易生效的冷静期。如规定在直播带货期间订立的合同不能即时生效,要求消费者在直播带货结束一段时间后(如24小时之后48小时之内)必须通过积极确认的方式使合同生效,否则合同便不生效力,以此避免消费者冲动购物、情绪化购物等非理性决策的负面影响。这种对于意思自治的救济能够在不对行为人决策自由进行过度干预的基础上有效避免非理性决策的不良影响,可以对影响力营销所引发的不当劝诱进行有效规制。
五、结语
社会生活的不断变迁征引出法制变革的必要性。不过作为一个自创生系统,法律的演进总是需要从既往规范实践的知识积淀中获取规整新生事物的抽象指引,“任何的革新都必须从现存的、现知的和不变的开始”(39)[德]尼古拉斯·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赵春燕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第406页。。由此视之,社交网络时代的到来虽然引发了信息传播模式的颠覆性变革,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将诞生于大众传媒时代的广告法全盘抛弃。一方面,广告法保障消费者意思自治之价值追求仍应在影响力营销规制中得以延续;另一方面,结合影响力营销的信息传播模式和劝诱机制,广告法既有的“主体—行为—责任”制度亦可在进行有针对性地改良后予以沿用。此外,对于影响力营销诱发的消费者非理性决策,则需要建构全新的交易生效冷静期加以预防。当然,影响力营销引发的法律问题存在于多个领域,如个人信息保护、消费合同纠纷、不正当竞争等显然超出了广告法的功能范畴,更多的研究仍有待未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