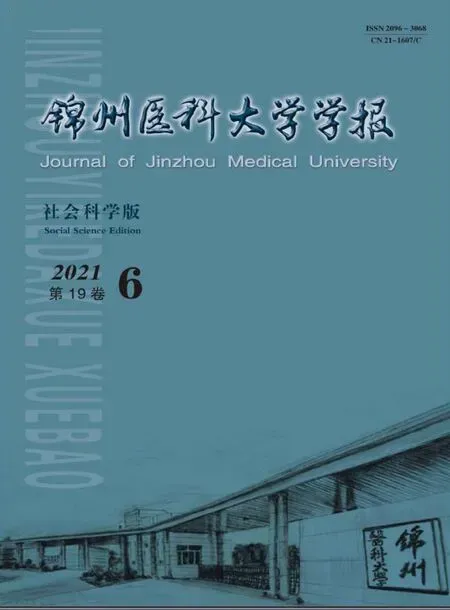“词汇化”论薮:英汉对比视角
程培莉
(太原工业学院 外语系,山西 太原 030008)
著名语言学家Givón(1971)提出了“今日之词法乃昨日之句法”的观点[1],从此揭开了词汇化研究的序幕。一般来说,“词汇化”被看作语言进化的一种类型,例如,语言中的某些句子或短语随着语言的使用被逐渐概念化为“词项”。换句话说,“词汇化”实际上就是语言演变的一种现象,具体来说,其通常指某种类型的语言形式(如短语或句子,即一般比“词”更长的语法单位)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凝固为一个词或词项。
一般而言,汉语被认为是分析型语言的代表,而英语则是综合型语言的代表,二者具有较大参数差异(Huang 2015)[2]。根据我们的观察,英、汉语所存在的参数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词汇化程度方面的差异,而这些差异的产生具有两大方面的动因,即语言本体结构和社会因素。学界普遍认为,从跨语言的角度来观察语言的词汇化程度,可以一定程度上揭示语言演变的发展规律,这对于进一步认知和识解语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拟以英、汉两种语言中的词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分析并对比这两种语言在“词汇化”方面的共性和差异,同时尝试给出“词汇化”差异所产生的原因。下面我们首先进行文献回顾,并指出既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盲区,而后重新来看两种语言中的词汇化情况,并尝试全面给出两种语言呈现出词汇化差异的原因。
一、既有研究回顾
从词汇化的相关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Anttila 1989[3];Hadumod 2000[4];Blank 2001[5];Brinton &Traugott 2005[6];沈家煊1994[7];胡壮麟2003[8];刘茁2005[9];毛海燕2007[10];李景华、崔艳嫣2011[11];朱永生2014;阳盼2016 等)都对这类语言现象进行了关注。这些研究颇有洞见,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我们对“词汇化”的认识和理解。根据我们的梳理,这些研究大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词汇化”的界定。针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出现在“词汇化”研究的初始阶段,学者们对“什么是词汇化”“如何界定词汇化”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并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界定。例如,Blank(2001)在研究中指出,“词汇化”实际上存在多种含义,但一般来说,“词汇化”主要指“超词”的句法单位逐渐丧失组构性,并进入词库,成为具有规约性特征和整体性特征的“词库词项”。Anttila(1989)则将“词汇化”定义为“某些句法结构失去句法规则的语法性原则或规律”。但需要指出的是,从这方面来界定的“词汇化”,往往会在具体的构词法或语法化研究中出现更为确切但内容呈现差异的界定。Brinton&Traugott(2005:90)则将词汇化界定为,“在某种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言者采用某种句法或新造短语进行表义,并随着时间推进,逐渐演变为独立词项的过程”。罗思明等(2007)则认为“词汇化”实际上就是指句子或短语的语义成分被编码成词的历程。但总的来说,“词汇化”定义的研究大体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从共时角度来说,“词汇化”往往被当作语言中将概念转换呈现为“词”的过程;从历时角度来说,“词汇化”一般被理解为“短语等非词单位逐渐凝固或变得紧凑而形成单词的过程。
2.“词汇化”现象研究。根据掌握的文献来看,新近很多学者(王连盛2018;吴汉江2018等)都对“词汇化”现象展开了研究,并得出了颇有洞见的研究结论。例如,阳盼(2016)从词汇化角度专题对“不无”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他指出“不无”作为一种“双重否定结构”,实际上经历了从跨层句法结构到凝固为双音词的“词汇化”过程。王连盛(2018)主要对动结式的词汇化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探究,他认为动结式可以根据词汇化程度分为短语、词法词以及词汇词三种类型,同时还提出了判定该类结构式词汇化程度的标准。另外,朱俊玄(2018)、吴汉江(2018)以及公丕盈(2021)等也分别对汉语中的某种词汇化现象进行了个案分析,深化了我们对词汇化现象的了解。尽管以上相关研究分析细致,所得结论也颇具说服力,但总归只是对“词汇化”现象的个案探讨,从中还不能概括出较为一般的语言规律或语言演变规则。
3.英汉(跨语言)对比视角的“词汇化”研究。从跨语言对比视角来探究“词汇化”现象,有利于更好地发现语言的演变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对此,刘茁(2005)、毛海燕(2007)、周国辉和郭欣(2010)、向琼(2011)以及李景华和崔艳嫣(2011)等都从这一研究视角进行了分析。例如,刘茁(2005)在研究中指出,英汉词汇化程度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种语言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以及“观念文化”。周国辉和郭欣(2010)则主要依据词汇化的相关理论,对比分析了英汉语中新词的词汇化程度,他们发现由于语言的本体结构特性,英语新词的词汇化程度明显高于汉语中新词的词汇化程度。
首先,从英汉对比视角进行的研究为“词汇化”提供了新的研究切入点,但从相关研究来看,从该角度进行的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目前对英汉对比视角的研究关注度仍有欠缺;其次,跨语言的“词汇化”研究过度关注差异,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共性的存在;最后,相关研究对产生“词汇化”差异的背后动因归纳还不够完善,除了相应的社会文化因素外,语言的本体结构特征也是“词汇化”程度各异的重要原因。由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弥补以往研究中的缺陷,并尝试填补研究空白,从而完善并推动“词汇化”现象的研究,进一步揭示语言演变的规律。
二、词汇化程度
根据Banczerowski 的相关论述,对于同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来说,如果可以采用一个“词项”来进行表述,那么这种表达方式就可以称之为“综合表达法”;反之,如果对于该复杂的概念需要某种句法结构或(较长的)短语来进行表征的话,那么这种表达方式就属于“分析表达法”。简而言之,“综合表达法”往往代表语言中的词汇化程度较高,而“分析表达法”则通常说明语言中的词汇化程度较低。以英语中的“stink”为例,尽管其在形式表征上只有一个词项,但在概念表达方面却语义蕴含丰富,表示“产生或散发出剧烈的臭气(give a strong bad smell)。
为了描述的便宜性,刘茁(2005)在研究中提出可以引入“lexeme(汉语中一般译为‘词位’)”用于阐释词汇化程度。根据Hadumod(2000)的说法,“词位”应该是语言中“词项”的最基本的、抽象的单位,其通常可以以不同的语法表征形式出现。例如,pay、paid 以及pays 都是词位“pay”的语法表达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词位还可以是其它词位的组构成分,例如,词位“pay”本身还可以是词位“payoff”的一个组构成分。概括来说,如果“词位”只有一个“词项”,那么该词位可以被看作“简单词位”,例如“act”。但如果“词位”具有多个组构“词项”(即包含两个以上的词项),例如,包含多个词项的同义词位,“a teacher for English teaching”,则将这类现象称作复杂词位(即complex lexeme)。
在对词位的相关概念有一定了解后,我们可以对词汇化程度的高低进行更为具体的描述。具体而言,词汇化程度最高的当属不可分解的简单词位,这种词位往往只有一个单词,且不具有任何可分解的词缀,例如,上文提到的“stink”。即使如此,需要强调的是,汉语中的单音节词都属于这种情况,其一般都不具有可分解性。紧随其后的应该是具有派生性质的简单词位,这类词位一般由根词和词缀共同组成,具有一定的可分解性。例如,英语中的“psychologist”就是由词根“psychology”和词缀“-ist”派生组构而成;汉语中也有类似的现象,例如派生词“椅子”,该词的词根为“椅”,而词缀则是汉语中较为普遍的名词性后缀“子”。再往后面,“合成词”的词汇化程度较低,这类词通常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由词素组构形成,例如,英语中的“policeman”“blackboard”“mobile-phone”等等,而汉语中也有“海轮”“旅馆”等合成词。词汇化程度最低的应该是短语结构,例如英语中的“writer for science fiction”,汉语中如“亲如姐弟”等。
刘茁(2005)指出,不同文化所代表的语言中,词汇化程度存在很大差异,例如,英语中用“snow”来统称“雪”,但对于爱斯基摩人来说,则根据雪状态的不同将其分为五种情况,并采用五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来命名表征,即wind-driven snow、snow packed hard like ice、snow on the ground、falling snow 以及slushy snow。实际上,尽管由于文化的差异,各种语言中的词汇化程度不尽相同,但在英汉语中既存在差异,同时也包含共性。下面我们来具体论述两种语言中词汇化现象中的共性和差异。
三、英、汉词汇化表现中的共性和差异
1.英、汉语中词汇化的共性表现。从相关研究来看,由于英、汉语两种语言具有较大的文化差异,学界大多关注英、汉语中词汇化程度的差异,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两种语言中共性的讨论。实际上,从认知体验的角度来说,人们在概念化世界的时候,主要根据具身体验形成概念,而人类又居住于同一个客观世界,具有诸多雷同的具身体验和概念化认知过程,这就为不同语言之间可能存在共同的概念提供了基础,而“词汇化”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对大脑中抽象、模糊概念的表征过程。因此,在词汇化方面,英、汉语必然存在共性。例如,汉语中说“摆桌子”,而英语中也有对应的概念表达“set the table”。可以说,从人们的概念认知出发,英、汉语之间在很多方面存在相同或相似的概念基础,相应的词汇化方式也具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下面是我们观察到的一些英、汉语中词汇化现象的一些实例:
(1)a.after service;economic zone;house call
b.售后服务;经济特区;上门服务
(2)a.pillow talk;equivalence test;call girl
b.枕头风;同等测试;应召女郎
在这些例子中,同时包含了英、汉语中经济、环境、科技以及文化生活方面所涉及的新概念或新表达。通过英、汉语的对比可以发现,这些表达不仅意义对等,而且形式表征相同,即拥有相同的概念基础和相同的词汇化方式。具体而言,英、汉语中这些表达的出现都以相同的客观世界作为体验基础,因而具有类似的概念化方式;而从形式表征来看,这些新词的表达方式大多为复合词,即一般由已有的自由词素组构而来。向琼(2011)认为,英、汉语中这些表达实际上都采用了“直接赋值法”的词汇化方式,这种方法通常是直接将表达事物特征的词位组合起来进行表达。例如,英语中的“bar code”和汉语中所对应的“条形码”,就用来表述一种“条形数码”,其可以用来超市中商品的计算机结账和商品类别识别。
2.英、汉语中词汇化的差异表现。根据既有研究的发现,英、汉语在词汇化方面差异更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二者在对某些概念进行表征的时候具有不同的细化程度;对同一概念具有不同的词汇化方式;二者在语言形态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词汇化差异。下面我们一一来看:
第一,细化程度的差异。尽管人类同处于同一个客观世界,大多数的认知体验较为相似,但由于具体环境的差异,对于很多概念的细化程度并不一样。正如上文提到的“雪”的概念,英语中可能只用“snow”这一类指性词汇来代称“雪”的概念,而在爱斯基摩语中则根据雪状态的不同,将其细分为五种情况,并用五种不同的语言表达来进行表征。同理,英、汉语中也涉及到类似情况,英国素以海洋文化著称,海洋特征深刻地反映在英语词汇之中,例如,在英语词汇中就包含大量关于“船”的表达,诸如catamaran(双体船)、barge(驳船)、skiff(轻舟)、brig(双桅横帆船)等简单词位的船类词汇;另外还有包含两个简单词位所组成的复合词,如store-ship(军需船)、steamboat(汽艇)以及ferryboat(渡船)等。相反,汉民族的发展主要以农耕文化延绵千载。因此,在中国古代畜牧业曾经繁盛一时,而对应于汉语中的词汇,以词汇“马”为例,汉民族根据“马”的雄雌、毛色、品相、体态等方面的不同,将“马”细分为100 多种类型,例如“驹”(在中国古代指两岁的马)、“骊”(黑色的马)、“驷”(同时驾车的四匹马)、“骏”(良马)、“骄”(身高六尺的马)、“骥”(千里马)等等。根据郭锦桴的研究,在《尔雅》 以及《说文》中,对“牛”的命名有18 个,对“猪”的命名有13 个,对“羊”的命名也有11 个等。这些对家畜名字的细化,都反映出畜牧业在汉民族文化中的影响和作用。
第二,词汇化概念方式的差异。词汇化方式的差异实际上跟英、汉语中词汇细化程度的差异密切相关。以上文中提到的英语中的“船”的概念为例,在英语的词汇中,很多船的概念只需要一个不可分解的简单词位就可以表达出来,而由于语义的复杂性,汉语中又没有这样的专名对应,这就往往需要汉语采用较长的短语结构来进行编码。例如,英语中的“brig”只需要不可分解的简单词位就能表达出来,而汉语则需要采用复合词来进行表述,即“双桅横帆船”。类似的,汉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主要以农耕文化为主,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和“体力负荷”相关的词汇相当丰富。例如,在汉语中用来表达用身体进行搬运物体的词就有十多种类型,诸如“拖、拽、挎、负、抗、拎、荷、顶、拉等”。在英语中遇到这些情况,一般可以用“carry”来进行约指。但在有些语用环境中进行确切描述,英语中往往需要采用一些短语结构来进行描述,以汉语中的“挑”为例,英语中则需要用“carry on the shoulder pole”来进行对应。另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汉民族的饮食文化也颇为繁盛,在烹饪过程中就有各种各样的烹饪手法或制作方式,例如“煎、熬、烩、蒸、炸、播、烙、烧、腌、薰、炙、酱、煮”等,这对于烹饪文化相对单薄的英国来说,往往没有对应的专门术语,在翻译传播的过程中往往需要采用短语结构来进行编码,才可能较为确切地将复杂的语义概念表述出来。
第三,基于语言特性的词汇化差异。在语言结构特征方面,一般认为英语属于综合型表达的语言,而汉语属于分析型表达的语言,这反映在语言的形态结构特征方面:黏着语的英语语法特征相对丰富,具有众多的形态表征方式,而汉语则以孤立语著称,属于分析型语言,一般认为汉语缺乏典型形态。这种语言特性的差异也造成了两种语言词汇化方式的差异。周国辉和郭欣(2010)认为,总体来说,英语的词汇化程度较高,因为英语具有较为丰富的形态(如词缀),在词汇化过程中借助不同的形态就可以产生众多的派生词,而汉语由于缺乏形态,则需要在词汇化过程中尽可能采用“自由词素”组构的办法来进行表达。从这点来看,汉语的词汇化造就的新词往往具有高透明度、高分析性,而英语反之。
四、英、汉词汇化差异的动因
根据我们对英、汉语中词汇化差异现象的描述和分析,我们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论述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即社会文化因素和语言本体特征。
1.社会文化因素。语言的演化跟社会发展密不可分,而“词汇化”的产生必然也是社会发展所促动。向琼(2011)就在研究中提出,“词汇化历程紧跟人类进步,伴随语言发展而存在”。从社会文化方面来说,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切入。
第一,地域环境所导致的词汇化差异。实际上,地域环境的差别并非直接导致词汇化的不同。具体而言,由于地域环境的差异,人们会有不同的发展模式,例如,英国由于濒临海洋,航海业异常发达,发展出了盛极一时的“海洋文化”。而汉民族由于大多地处内陆,沿河而生,多靠农耕、畜牧为生,诞生了富有特色的“农耕文明”。这种由于地域环境差异所导致的文化差异,就进一步导致在词汇化方面的差异。例如,在英语词汇中具有丰富的跟“航海”相关的专业术语,上文中提及的对“船”概念的分类就是很好的例证。相反,汉民族由于以“农耕文明”为主,我们对于和“农耕”相关的表达就相对较为丰富。对于这种情况下的词汇,如果进行英、汉语的互译,则一般需要用较为复杂的短语结构来进行描述。
第二,风俗、制度所导致的词汇化差异。中国历史悠久,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是具有高度等级化的社会(刘茁2005)。这种历史的传承和风俗文化就使得中国在礼仪、制度方面具有特殊性和等级性。例如,根据周朝礼制,人根据等级不同可以分为十类,即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高度等级化的特征还体现在当时的亲属称谓方面,例如,古代有“九族”之称,即以“本人”为界,纵向各延展四代,分别为高曾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本人、子、孙、曾孙、玄孙。延续至今,现代汉语中的亲属称谓更多达20 多种,而这在英语中很多都没有对应的词汇。
第三,各种人文、科学理念所导致的词汇化差异。各种人文、科学理念涉及人文、社科、宗教以及艺术等方面的理念。英、汉民族具有不同的历史发展进展,在发展过程中也各自发展出具有特色的文化理念,在词汇化方式上也有较大差异。在汉语中我们有“经济学”“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而英语中对应为“economics”“linguistics”“anthropology”以及“psychology”等,从这些对应的表达来看,英语中一般以派生词为主,而汉语中多为合成词。换句话说,以人文、科学观念方面的词汇化现象来说,英语的词汇化程度比汉语词汇化程度更高。刘茁(2005)认为,这可能跟汉文化的“官本位”观念有关,中国古代多强调“出仕为官”,强调权力的重要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相对缓慢,各种人文、科技理念普及性交叉,继而影射体现到词汇化的具体表达里。
2.语言本体特征。语言本体特征的不同也是造成英、汉语词汇化差异的重要因素。首先,英语一般被认为是综合型语言,这就使得英语的词汇化程度更高,词汇化多以派生的方式进行;而汉语属于分析型语言,在词汇化过程中以自由词素组构形成的复合词或合成词为主,词汇化程度较低。其次,英语作为综合型的黏着语言,形态较为丰富,在词汇化过程中可以借助丰富的形态来进行构词或派生;而汉语是分析型的孤立语,一般认为缺乏形态,在构词上只能用合成法来进行构词。最后,英语词汇主要以数量不同的字母组成,形态上或长或短,较为灵活;而汉语词汇一般具有不同的笔画,但在整体形态上都属于“方块字”,空间占据较为均衡,多为不可分解的简单词位。这也导致汉语在词汇化过程中多以复合词为主,而英语多以派生词为主。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重新对英、汉语中的词汇化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我们考察了英、汉语中的词汇化现象,发现英、汉语中的词汇化现象并非只存在差异。由于具身体验的相似性,在词汇化方面,英、汉语同样具有相同的词汇化方式。然而,英、汉语在词汇化方面的差异更为明显,主要包括细化程度的差异、词汇化概念方式的差异以及基于语言特性的词汇化差异。随后,我们针对英、汉语词汇化的差异,给出了产生差异的原因分析,主要包括两个大方面,即社会文化因素和语言本体特征。综合分析,英汉语词汇化的发展离不开各自语言形成的历史渊源和生态背景,在实践两种语言交流转换过程中,词汇的准确妥帖运用是词汇化研究的目标和动力所在,词汇化发展离不开赖以生存的语言本土环境,其复杂性、规律性的发展变化将是语言学者持续关注研究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