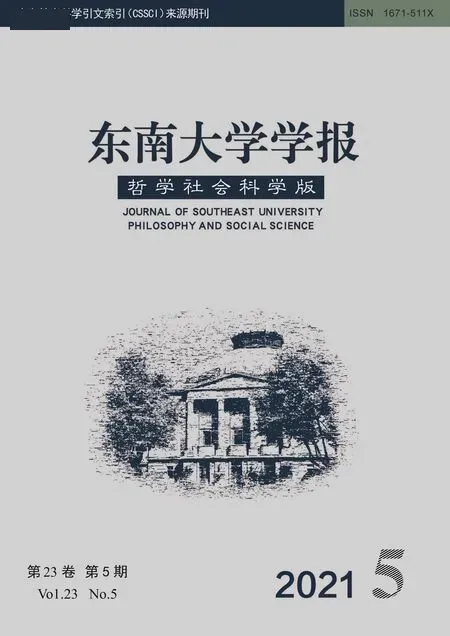还“德”于“史”:柳诒徵与二十世纪东南学派史学伦理化转向
胡 芮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20世纪初,维系中国社会伦理信仰的儒家思想传统摇摇欲坠。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下,士大夫想象中建构的“天下秩序”开始解体,“万国林立”的世界秩序逐渐浮现,一个让国人惊呼“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到来了。在文化变革的设想中,具有不同倾向的知识分子争鸣不已,形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文化论争。在传统的落日余晖中,如何在历史的陈迹里寻回再造民族道德信仰之基的砖瓦,虽然不同派别之间的论域并不完全重叠,但新文化派、国粹派、学衡派、欧化派们都绕不过一个共同的思想话题,那就是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传统。作为经验知识的总结,历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根据德罗伊森的观点,“人类的自我,借着历史知识为媒介,展开自己对自己的认识”(1)[德]耶尔恩·吕森:《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引论》,胡昌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页。。历史的方法,从本质上来说体现为解释的工作。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传统中,历史研究因研究目的的不同而被区分为“致用”和“求真”两种不同的路径,并逐步划分为“信古派”和“疑古派”两大不同阵营。受到西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影响,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坚持“史料本身会说话”的客观主义态度,强调历史学家的工作只是对过去经验进行客观研究和描述,不需要加入主观意见,在精神上内接乾嘉考证的史学传统。然而,清中期后史学传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章学诚有云:“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2)章学诚:《文史通义》第二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 年,第 66 页。直言史学不仅要做烦琐细密的考证,更要体现出“经世致用”的价值,强调作为一般经验知识的历史的社会价值。这种史学目的论为“信古派”所继承,其中又以“东南学派”(南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学人群体)为代表。“疑古”与“信古”之争表面上看只是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但对于中国而言,历史不仅是一般经验知识的陈列,更是民族精神血脉生长的机体,历史传统(史)和道德信仰(德)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是难以割裂的。柳诒徵(1880—1956)及其代表的“东南学派”致力于“还德于史”,其不激不随、幽微精深的研究在史学革命汹涌澎湃的浪潮下不啻为一种可贵的清醒。
一、观念转型中的史学“科学化”浪潮
“东南学派”是与“新史学”分庭抗礼的学术派别,对它的研究自然不能忽视其诞生的时代背景。自梁启超首倡新史学以来,“求真”便成为史学研究的核心思想。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剧变中,迫切的情势容不下审慎沉潜的学术态度,在变革传统史学的过程中,整体呈现出一片激进的姿态。20世纪初,对传统史学的猛烈批判,并非完全基于“科学”的立场,而更多的是体现出策略性。新学未立、传统已破,史学传统遽然中断,也导致社会伦理认同混乱、价值迷失等问题,史学家们不得不在批判史学传统的过程中着手重建科学的“新史学”。要准确理解观念转型中史学“科学化”的深层观念,应该首先厘清中西史学传统之差异,并探讨这种差异背后的哲学基础。
中国传统史学虽体例不一,但整体上都体现出伦理化倾向。在经学独尊的传统中,史学的主要作用是为经典承载的伦理纲常进行价值辩护,这也使得中国传统史学体现出浓厚的伦理化倾向。中国传统史学推重的“秉笔直书”虽然也关注“直”的真实性立场,但更多地侧重于道德评价,就此而言,传统史学的伦理本位以维护“三纲五常”正统道德评价体系为根本目的,历史叙事的主要功能是梳理伦理意义上的“典范”,是对圣王之道的具体还原。有论者指出:“对于中国传统史学而言,关于历史事件的个别记述,总是自身包含了意义和合法性的,而不需要构建整体化的解释框架或叙事框架,这导致中国传统史学长期拒斥理论、概念和解释框架。”(3)卓立、杨晶:《从“直书”到“求真”——清季民初“新史学”知识论转型的观念史考释》,《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第140页。传统史学伦理化的倾向在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中天然处于自洽的地位,伦理与史学相资为用的特点也使得中国传统史学呈现出一种繁荣的状态。梁启超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二百年前,可云如此)。”(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92页。史官建制客观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在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传统史学的繁荣。在肯定传统史学形式繁荣的同时,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成就却是质疑的。他说:“孔子所修《春秋》,体裁似依鲁史官之旧。……吾侪以今代的史眼读之……绝类村店所用之流水账簿。”(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93页。这实际上表达了中国数千年长期处于“有史料而无史”的状态,为其之后提倡史学革命奠定了批判前提。
而与此相对应的西方史学传统则呈现出另一种景象。西方文化传统中长期忽视史学纪实的作用,以至于在兰克学派之后,现代意义上的史学纪实才得到真正的重视。作为西方史学研究标签之一的“科学主义”实际上是启蒙之后才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英国史学家伯里曾言:“历史是一种科学:一点不少,一点也不多。”在强调史学是一种科学的同时,更明确表达要信守历史的学科边界(一点也不多)。在西方语境中,历史源自拉丁语historia,初意是“研究之结果”,到罗马时代,意义逐渐固定为“叙述”之意。西方历史观念中,叙述是历史的基础。叙述的目的通常在于传递信息或者态度,并不能提供系统的科学知识。这意味着在西方历史传统的早期,历史的科学性是较难得到保证的。傅斯年曾说:“欧洲史学有一特别现象,始自希腊即文史不能分离,史学独立,是晚年之事。”(6)傅斯年:《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3-154页。也就是说,在西方早期史学与文学长期关联,并没有独立之科学地位。而反观中国史学传统,“史”从词源学上讲,“史字从又持中,而尹氏之尹又从手持笔”(7)刘节:《中国史学史稿》,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4页。。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历史即是文字纪实,这与西方早期历史依赖于言说叙述有较大的区别。
整体来看,一方面,西方史学研究与文学叙事保持着密切关联,迟至启蒙运动之后,受到法国大革命等社会运动的影响,欧洲官方档案逐步开放,纪实文本逐步纳入到史学研究视域,西方史学才真正开始“科学化”浪潮。因此可说,现代西方史学的思想源头之一是纪实文本的发现和流行。另一方面,以追求普遍性为宗旨的西方哲学传统奉柏拉图主义为圭臬,对理性主义的执着又指引着其科学化、知识化、体系化。启蒙之后的西方史学在两种力量的影响下开启了追求普遍、确定、永恒的知识化进程。可以看出,现代西方史学的诞生动力是为了摆脱长期依赖于叙事的“非知识化”境地,但对纪实文本的偏重却又将其带上了实证主义的另一种困境,即,纪实文本的经验性、个别性史料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出普遍的、永恒的知识合法性?普遍性与个体性之间的张力非但没有在现代西方史学的语境中得以消除,而且在文明全球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中还得到某种程度地加强,这可能是兰克史学及其拥趸所没有料想到的。
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现代西方史学理论对中国传统史学形成了直接的影响。咸同兵燹后,西方史学实证主义更是携欧风美雨之威势迅速涤荡中华并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传统史学观念。严复等人传译西方著作,介绍西方思想,可谓中国近现代史学启蒙之先驱。严复译著范围较广,包含哲学、史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尤其是他对进化论的引入,引发中国思想界的剧烈震动,让严复迅速“暴得大名”,并由此奠定了其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先驱的地位(8)胡芮:《严复与近代儒家伦理话语体系的古今之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梁启超对严复译著的学术贡献作出了积极地评价:“我中国英文英语之见重,既数十年,学而通之者不下数千辈,而除严又陵外,曾无一人能以其学术思想输入于中国。”(9)梁启超:《东籍月旦》,《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25页。但严复的意译却因偏重于思想而偏离了原著,傅斯年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严几道先生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当时读英文、法文的很少,任他‘达旨’去罢,谁肯寻根追求。现在读外国文的人多了,随时可以发现毛病。”(10)傅斯年:《译书感言》,《傅斯年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90页。严复的翻译抽离了西学原著的思想语境,而代入了“绝对”的观念,对此,杨国荣认为这与传统哲学中对“道”“理”等固有的追求普遍永恒之理的思想有关(11)杨国荣:《实证主义与中国近代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4-15页。。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通过“格义”,以中国哲学传统概念为中介,向社会传播和普及西方观念是普遍的、策略性的做法。严复之后,梁启超对西学的引介进一步深入到价值层面。梁启超在吸收西方价值观念的同时,视野更为宽阔。相较于严复古奥的翻译,梁启超颇为实用主义地大量引用日本“和制汉语”。虽然严复认为不加斟酌地引用外来语会导致学术自主性的丧失,但依然无法改变清末中国思想界深受日本学界影响的事实,其中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对“科学”观念的引入。
与当代思想语境中“科学”意指“自然科学”所不同的是,在西方思想的源头,“科学”是希腊文再经拉丁化的概念,拉丁文scientia的本义是“有组织的知识体系”。兰克史学之前的西方史学依附于文学叙事,很难说具有独立的“组织”和“体系”,因此西方早期史学也不具备“科学”特征。“科学”概念初入中国时,采用的翻译概念是“格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迟至19世纪上半叶,science一词的含义已经固定于经验科学与实证主义。梁启超等人觉察出这种含义变化而开始用“科学”概念代替“格致”,这体现出中国思想界也意识到“科学”观念与理学格物致知传统的差别。“科学”观念的引入,对中国传统史学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开启了中国传统史学“由旧入新”的转变。张越认为,科学观念的引入和梁启超“新史学”可视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其主要原因在于他开始采用“民族”“国家”等现代观念,力图将伦理学意义上的史学发展为知识论意义上的史学(12)张越:《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与转变》,《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
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具有鲜明的目的论导向。概括起来,主要就是为了通过“史学革命”,形成科学的国家观念。“国与史”的关系问题也是梁启超新史学的核心关切。1901年至1902年,梁启超连续发表两篇文章阐述新史学观点,分别是《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在文章中梁启超严厉批判了传统史学不讲进化、不遵因果律,是僵死的陈迹,提倡历史研究要“以生人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为本位的历史”(1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73,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 29 页。,要从历史中阐发“人群进化之现象”,进而求得“公理公例”。进化论、以及对历史发展科学规律的追求,使得梁启超的新史学突破了两千年传统的“循环史观”,进而摆脱传统“一治一乱”的基本叙事架构,带领民族和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
“史学革命”的首要目的是改变传统史学有“朝廷的历史”而无“国家的历史”的现状。在《新史学》中,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史学虽然繁荣,但贻害甚巨,“推其病源有四端”,最首要的问题便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14)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9,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他将中国长达数千年的正史斥为帝王将相的家谱,有“私史”而无“国史”的结果便是造成民众国家意识淡漠,难以形成统一的国家伦理认同。近代学术史研究奠基人刘师培也认为,传统史学的主要缺点是“大约记一家一姓之事耳”,普通民众在传统历史中是被遮蔽的,历史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封建纲常秩序,“可以助愚民之用”(15)无畏 (刘师培):《新史篇 》,《警钟日报》,1904-08-02。。清季以来,传统伦理秩序体系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伦理化倾向明显的旧史学自然无法得到新式知识分子的认同。可以看出,“史学革命”的动因有强烈的“家国焦虑”。梁启超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16)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39页。史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唯一与西方学术相通之处,承载了彼时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希望。“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17)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36页。因此可以说,近代“史学革命”的产生与全新伦理秩序的重建是同步的。知识分子希望通过以“科学精神”重写“国史”,促进国家伦理认同,进而完成现代国家转型。然而,倡导新史学的学人们没有意识到,对传统史学采取激烈的批判立场,又直接导致了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生,“国”与“史”的关系不单单指向学术研究,同时也与民族国家的政治建构存在深刻地关联。
“史学革命”进一步地深刻变革了传统史学的哲学基础。从存在论基础来看,中国传统史学较少在时间的维度关注存在问题,而更多着意于空间问题。“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18)梁启超:《爱国论》,《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70页。在这种“中国中心观”中隐含着一种恒常不变的伦理信念,那就是中国及其礼乐文明位处天下的中心,是天下的意义之源。柳诒徵在《国史要义》中精要地阐释了这种传统历史哲学信念:“民俗之兴,发源天性,圣哲叙之,遂曰天叙。推之天子、诸侯、大夫、士庶,宜有秩次,亦出于天。而礼之等威差别,随以演进矣。从民俗而知天,原天理以定礼。故伦理者,礼之本也;仪节者,礼之文也。观秩叙之发明,而古史能述此要义。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者,盖莫大乎此。徒执书志以言礼,不惟隘于礼,抑亦隘于史矣。天人之际,所包者广。本天叙以定伦常,亦法天时以行政事。故古者太史之职,在顺时土,以帅阳官,守典奉法,以行月令。”(19)柳诒徵:《国史要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3页。自清末启蒙以来,时局巨变。西方文明的强势进入逐渐解构了国人长期以来的文化信念,大国优越感的丧失、文化中心地位的动摇,都体现出传统历史哲学基础已然发生嬗变。从静止的时空观到线性进化的发展观,“科学化”浪潮下的“史学革命”力图将中国拉上世界历史发展的轨道。对历史的研究,不再是“家谱学”意义上的伦理叙事,而是要形成普适性、知识性的“公理公例”。神化三代的儒学经典因此变得一文不名,“黄金古代”也从伦理信念中隐退,一个崭新的历史世界地平线开始浮现。
二、“进化论”视域中的“史德”问题
在史学“科学化”浪潮的裹挟下,道德、信仰等非知识性结构面临着被驱逐出历史的尴尬境地。虽然梁启超等标榜新史学的使命是为了寻求普遍意义上的“公理公例”,但事实上,建构新史学的诉求却是以追求或印证进化论式的历史规律和因果律为目标,历史作为“科学知识”的成色到底提高了多少似乎不是新史学建构者们真正关心的问题。有论者指出,“知识论的求真观,从归纳逻辑上说,如果可以分为先求真事实,再求真理的逻辑次序的话,那么对于中国新史学而言,这个次序则是颠倒的,是先建立求历史真理的观念,之后再过渡到求历史事实的新史学观”(20)卓立、杨晶:《从“直书”到“求真”——清季民初“新史学”知识论转型的观念史考释》,《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第140页。。这样的评论可谓切中肯綮。梁启超等对传统史学的伦理化倾向不满,并大力鞭笞传统纪实文本,并不是要废除传统史学的“写法”,而是主张用“民族国家”作为新的伦理价值取代传统纲常伦理评价体系,这种新的史学价值是建立在真理进化的哲学基础之上。
进化论及其历史学观点“线性史观”虽是个西方概念,但在中国传统史学思想中也能找到相似性表达。晚近以来,康有为阐发“公羊三世说”,认为历史发展是“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阶段发展,是最接近“线性史观”的表达。不过,康有为阐发“公羊三世说”主要是为了“托古改制”,因此在历史方面的影响较小。历史研究领域,在严复之后,薛福成(1838—1894)、王韬(1828—1897)、郑观应(1842—1922)、陈炽(1855—1900)等人都提出过某种分期观,架构出中国历史从过去到现在以及未来的理论体系。同时,晚清时日本史学家桑原隲藏(1870—1931)在其《东洋史要》中将中国的历史明确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个阶段,这一划分为中国思想界所接受,当时出版的教科书多以此为标准,进而形成了以“线性史观”为主流的史学观。
清末民初的史学研究版图中,隐然有“双峰对峙、南北分流”(21)关于近代中国学术的南北差别,参见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 49-55 页;蒋梦麟《文学·国学·旧学:民国时期的南方学术与学派建构——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中文系为中心》,《社会科学》2012 年第 3 期。的说法。近代以来,地域所造成的南北之学因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王汎森说:“东南文化是于北方新文化运动抗争的主力。晚清桐城文派主要势力是在东南,姚鼐(1732—1815)一生主要的学术活动在南京,流风余绪,影响深远。所以在民初新派人物眼中,南京是文化界旧势力的据点。”(22)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香港:三联书社,2008年,第216页。清末民初文化界逐步出现保守与激进的分野,亦即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呈现出的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学分南北”。然而,身处“线性史观”的叙事时空,中国史学界大体也保持着线性发展的同调。“中国科学社”内迁入东南大学也带来了科学精神以及现代学术思想(23)关于“中国科学社”与东南大学“科学名世”精神的讨论,参见孟杰《中国科学社早期发展与国立东南大学“科学名世”精神滥觞》,《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就连东南学派“领袖群伦”的史学大师柳诒徵,也在他的《中国文化史》中表达了进化论式的“公理公例”:“以进化之律论之,夏之社会,必以大进于唐、虞之时……”(24)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16页。当然,如果只关注到历史研究的主流趋势而忽略不同流派之间区别的话,那便会形成粗线条的历史叙事,不能全景展示这一时期真实的思想史景观。
以“五四”为时间节点,新文化运动逐渐发展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启蒙运动。方旭红认为:“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几乎同时产生,并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和反思。伦理精神是学衡派批判新文化派的核心。”(25)方旭红:《伦理精神——学衡派与新文化派伦理论争的核心》,《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25页。“学衡派”作为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学术共同体,其人员构成与“东南学派”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柳诒徵既是学衡派的代表人物,又是“东南学派”的精神领袖。近代思想史的通俗叙事中,“学衡派”或“东南学派”总是给人以“文化保守”的时代印象。但关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真实身份,本杰明·史华兹在总结西方学者论“五四”时引用了弗斯的经典概括:“五四时代著名的‘保守主义者’中,没有一个真正是全然生活于古老的中国里或准备用那些传统提供的武器来护卫过去传统的人。梁漱溟、梁启超、林纾、章炳麟、辜鸿铭和‘学衡’派,都是被西方思想范畴如此显著地影响的人,以致于无论我们称其为‘传统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都掩盖不了他们以全新的观点审视中国的过去这一事实。”(26)本杰明·史华兹:《五四运动的反省》导言,王跃、高力克:《五四: 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页。所谓的“保守主义者”并非全是抱残守缺的守旧派,实际上,他们批判新文化派将传统史学完全否定是缺乏内在精神的弊病。新文化运动初期,杜亚泉、梁簌溟等人主张辨别东西方文明之优劣,主张融合不同文明之优点。
一战过后,文化反思的工作开始在东西方同时展开,原本处于文化优越感中的西方人开始出现悲观和彷徨,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如警世钟一般给西方人的心灵造成极大的震撼。在困顿和反思中,他们也将眼光投向古老的东方,新人文主义开始在欧美国家出现。以美国学者白璧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者兼具传统和世界眼光,以谋求人类文明之会通为根本宗旨,积极推动这股浪潮并付诸实践。与此同时,中国的史学界也开始系统反思清末以来的“史学革命”之得失。实际上,从清末到民初,中国史学界对史学“科学化”浪潮表现出的热情一直呈现出衰减之势。尤其是一战过后,中国史学界对西学与进化论的信心严重受挫。曾豪言要“史学革命”的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处处流露出对绝对科学主义的怀疑,并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历史中人文主义的价值问题,新文化运动及后来的科玄论战都体现出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重视。
中国历史传统首重“人文”。与启蒙之后西方史学知识化追求所不同的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鲜明标识是“伦理”。如樊浩所言:“‘伦理’话语及其缔造的中国伦理传统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文明史意义。”(27)樊浩:《“伦理”话语的文明史意义》,《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5页。关于历史的道德问题,以及历史研究者的道德问题,也是中国近代史学观念变革中不能绕开的话题。乾嘉以来,章学诚在唐代刘知几“良史三才”(才、学、识)的基础上提出“史德”概念,认为“史德”为“著书者之心术”,并认为“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粹,大贤以下,所不能免也。”(28)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9页。史德既是史学家道德品质的展现,又是历史理论的基础。章学诚之后,梁启超也提出了“鉴空衡平”的历史研究方法。但在其“科学化”史学的谋划下,史学家主观道德问题并不是核心观念。对此柳诒徵批评梁启超“陈义甚高”,但却并没有深刻体察章学诚史德说之精义。在批判和借鉴章学诚、梁启超的“史德观”基础之上,柳诒徵表达了自己对史学研究道德问题的看法。
首先,柳诒徵认为历史与道德不可分离。他指出:“治史而不言德则已,言德则必究德之所由来,及其为用之普遍。”又说,“不当专求执德以驭史,而惟宜治史以蓄德矣。”(29)柳诒徵:《国史要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这与西方史学传统中的早期的叙事和知识主义倾向存在着巨大的不同。柳诒徵认为,中国史学传统中最为重要的特点是将“治史”视为道德完善的重要路径,其史学目的论有两个基本层次。其一,从个人道德修养的角度来看,他认为人类历史作为经验的总结和归纳,彰显着天赋灵明之“智慧”,历史的镜鉴作用能够使后人免于重蹈覆辙。柳诒徵认为,“以前人之经验, 启发后人之秉彝,惟史之功用最大”,“所谓耸善抑恶、昭明废幽、广德明志、疏秽镇浮、戒惧休劝者,皆以史为工具而求成其德也”(30)柳诒徵:《国史要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4页。。由此可以看出,柳诒徵把史学看作是个人德性养成的砥石。其二,治史不仅对个人道德修养具有重要作用,还能对社会伦理教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历史的重要作用就是让人产生道德信仰,进而结成道德团体。他说:“近人谓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士大夫庶民以成一道德团体。观于司徒十二教及各官之教,知此论非过信古人也。”(31)柳诒徵:《柳诒徵自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14页。柳诒徵秉持史学目的论的立场,阐发历史的道德属性。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也有类似的表达:“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32)王国维:《王国维手定观堂集林》,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59页。由此可见,一战前后的国内史学界开始对清末“史学革命”进行反思,原本将道德驱逐出历史领域的做法得到某种程度的纠偏。
其次,柳诒徵坚持“信古”的价值立场。中国史学传统本无“疑古”与“信古”之争,随着清末以降新史料和出土文献的出现,加之西方“科学”思潮的涌入,不同历史研究者对待传统史料的态度出现了价值差异。“东南学派”因地处南京,历史上深受桐城学派影响,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表现出对疑古派的强烈质疑。顾颉刚将禹解释为九鼎动物(虫)引发了“东南学派”的激烈反弹。用顾颉刚自己的话来讲,“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柳诒徵、刘掞藜师徒与其打了半年的笔墨官司(33)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第 17-18 页,收入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 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关于顾颉刚与柳诒徵、刘掞藜的论争文章收入该书。。柳诒徵认为,史官的职责虽然重信,但也不代表不能质疑。史家秉笔直书,虽不能做到完全忠实于事实,却是尽到了史德。因此不能因史有讳饰,就否定古有良史,更不能轻议古人。他说:“挟考据怀疑之术以治史,将史实因之而愈淆,而其为害于国族也亟矣。”(34)柳诒徵:《国史要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8页。在这里,柳诒徵敏锐地觉察出过度否定传统史学背后的非理性因素,“疑古”者大多慑于西方文明之强大而失去了客观中立的立场。胡适后来总结道:“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功夫。”(3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 4 册,1922 年 8 月 26 日,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4 年,第 731 页。直接给柳诒徵及其所代表的“东南学派”贴上了“信古”的标签,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南北二派的学术特点,对北派疑古而“简陋”的批评多少有些来自柳诒徵及其东南学派映衬的意味。胡适等人的疑古思想体现出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倾向,同时,晚近以来西方科学的传入,更是为“怀疑一切”“重估一切”奠定了思想基础。胡适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者戏侮的态度。那名词就是‘科学’。”(36)胡适:《〈科学人生观〉序》,载《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96页。胡适、顾颉刚等人可以视为梁启超之后将史学“科学化”浪潮推向第二阶段的代表,与后者简单地将“科学”概念引入史学领域所不同的是,胡适等人还将美国实证主义哲学方法与史学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了巨大影响。与之相对应的柳诒徵及其东南学派,只能从传统史德维度进行价值辩护,在传统价值日渐式微的近代,便难免应者寥寥了。
第三,对“礼”的价值坚守。柳诒徵认为,中国传统史学的精神是“礼”,并提出了“史出于礼”的观点,这与梁启超提倡“史学革命”将道德信仰驱逐出历史领域的做法完全不同。先秦时期,在政治机制的措置中史官与礼官职责不分,周代设五史以执掌礼法,他在《国史要义》开篇就表达了“礼由史章,而史出于礼”(37)柳诒徵:《国史要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页。的观点。史官在记载和撰写历史时必须以“礼”为评价标准,“所书与不书,皆有以示礼之得失”(38)柳诒徵:《国史要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页。。传统史学治史方法虽各不相同,但就其价值评判标准来看,都是出于“礼”,由此可说“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39)柳诒徵:《国史要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页。。与胡适、顾颉刚等人“怀疑一切”的态度所不同的是,柳诒徵对传统史学抱有强烈的价值信念。他认为,传统史学之要并不在于以“事实之真”而求得普遍性知识,而在于以“规律之真”印证传统礼制秩序的合法性,以现代西方科学观点来看,中国传统史学难免不完善甚至粗糙,但“礼”及其所承载的不变的“道”,才是维系世道人心最为重要的核心价值。由此可说,伦理是礼的根本,仪节只是历史的表现,“徒执书志以言礼,不仅隘于礼,而且隘于史”(40)范红霞:《柳诒徵文化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5页。。这里,柳诒徵显然是将“礼”作为区分中外史学的显著特征来看待。
总体来看,在“线性史观”的新史学浪潮下,柳诒徵在与“疑古派”的辩驳中基本阐述了其以“礼”为核心的道德史观。但在清末民初观念剧变的时空背景下,尤其是在传统儒家伦理因帝制覆灭失去依傍而成为“游魂”的思想条件下,柳诒徵对“礼”的维护很容易招致非议。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表达了对传统史学的不满:“他们脱不了儒书一尊的成见,故用全力治经学,而只用余力去治他书。”(41)胡适:《胡适文存》第2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4页。20世纪20年代文化领域的论争处处充满着火药味,胡适《题学衡》中揶揄道:“老胡没有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一本《学骂》!”(42)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第477页。但也客观体现出柳诒徵提出的“史德”问题确实打在了新史学的痛处,关于“史德”问题的探讨也在1930年代发展出新的思想轨迹。
三、《国风》时期的“经世致用”史学伦理
“东南学派”作为近代思想史领域中的重要学术共同体,其形成历史可以追溯到晚清新学改制。1902年三江师范学堂成立,1915年改设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启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乃至于浙江大学等近代新式高校,他们在人事师承、精神气质、思想倾向等方面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翁斌龢曾指出,南京高师值得纪念者,在于它的精神,他将这种精神或者学风概括为“笃实而有光辉”。柳诒徵从史学的角度对“南高精神”进行了梳理,他的《国朝太学考》《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大学》均有论述。黄佐《南雍篇》、王焕镳《首都志》等也从各个侧面展现了历史上以南京为地理范围的学术传承,清晰地刻画了近现代学术史上的“东南学派”。张其昀进一步将“东南学派”与“东南学术”贯通起来,在《源远流长之南京国学》一文中,张其昀明确地提出了“东南学派”。
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学术共同体多以刊物为平台相互唱和、竞相号召,形成学术思潮。30年代初期,《学衡》终刊之后,东南学派组织“国风社”,发行《国风》杂志。从学派传承来看,《国风》是《学衡》之延续。虽然《学衡》存世的时间有11年(1922—1933),但吴宓本人也承认,到了1927年底,《学衡》已事实上处于停办状态。胡先骕向吴宓提出“先将现有之《学衡》停办,完全另行改组。丝毫不用《学衡》旧名义”,建议改在南京出版,由柳诒徵、汤用彤等人主编。《学衡》80期以后改由南京钟山书局出版发行,编务由缪凤林担任,但实际上在南京的“学衡”旧人已经另起炉灶,创办了《国风》,开启了沈卫威所谓的“后学衡时代”。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学衡》杂志所奠定的思想基础之外,1921年,在南高师创办的《史地学报》也是奠基“后学衡时代”东南学派学术共同体的重要媒介。《史地学报》存续的时间是1921—1926年,大致与《学衡》活跃的时代相当,因其创办主体是南高师史地研究会,其主要的学术追求是普及国史认知和史地教育观念。《史地学报》继承了传统史学特色,作为学生自发组织的学术刊物,《史地学报》把教学与研究紧密结合,以期引起国内学人对史地教育的关注与探讨。但1925年底受东南大学“易长风波”影响,《史地学报》随之仓促结束,这也为1930年代“东南学派”重新在《国风》的旗帜下集结埋下了伏笔。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国风》超越《学衡》的意义在于,它是在继承传统道德价值的基础上,寻求一种伦理层面上的复兴,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其鲜明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上(43)胡芮:《〈国风〉(1932-1936)伦理思想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10月,第8页。。这一思想转向与“九一八事变”后空前加深的民族危机相关。作为钟山书局和《国风》的实际主持人,张其昀后来回忆创刊历史时说道:“九一八事变以后,作者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创办《国风》杂志,以提倡民族精神教育,唤起国魂为宗旨;执笔者多是南高、东大、中大师友们。”(44)张其昀:《六十年来之华学研究》,《张其昀先生文集》第19册,台北:文化大学出版部,1989年,第10252页。这除了点明刊物的宗旨之外,还有强调了杂志学术共同体的特征。抗战初期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史学观念的变迁已经基本完成。从中国传统思想预设天人感应式的实存主体化的生活世界观念转变为主客二分和实在论,虽然中国史学伦理本位的预设已经在科学主义、进化论的思潮下解体,但历史作为维系国家精神认同的重要传统,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的“科学的”学术观点却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传统历史维系的民族认同。在与刘掞藜、胡堇人的学术辩论中,顾颉刚提出了几条推翻信史的标准: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45)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9-101页。。虽然古史辨派提出的观点在学术层面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因“疑古”而产生的历史虚无、民族虚无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危害。针对这一问题,柳诒徵及其弟子坚持“经世致用”的史学目的论,力图对“史学革命”以来“为学问而学问”的历史中立论纠偏。
早在撰写《中国文化史》的20世纪20年代,柳诒徵就明确表达了史学具有道德属性。他说:史学与科学并非一事,“史非文学,非科学,自有其封域”(46)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弁言,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页。。与科学之求真所不同的是,史学应该在求真之上以求善。“古之大学明示正鹄,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于至善。……彝训炳然,百世奉习,官礼之兴以此,文教之昌以此。约之为史……”(47)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弁言,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页。史学作为人文科学,其使命不在于成为某种科学,而是追求“经世致用”。进入30年代,中国虽然已经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但是国家并无强烈的精神认同,加之外侮渐重,内外交困之下,若进一步以“科学”解构历史传统,就会导致民族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危机加剧。“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柳诒徵在《国风》发表文章《辽鹤巵言》表达了对国民不关心国情、社情的深深忧虑(48)柳诒徵:《辽鹤巵言》,《国风》,第1卷第5期,1932年10月10日。。有论者指出:“柳诒徵治史强调‘经世致用’,意在求善,自身、心、家、国、天下一以贯之者,正是儒家精神。”(49)郝志景:《“经世致用”与“为学问而学问”——柳诒徵“史学致用”论发微》,《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82页。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当代,有识之士主张“学术救国”,对于柳诒徵等淑世情怀深厚的知识分子而言,从史学中寻求治国之道便成为最佳选择。
辛亥革命之后,西方政体虽然在形式上得以确立,但国家的精神形态——伦理实体(民族)却没有真正的建立。西方列强轻视中国为“一盘散沙”:政治腐败、社会动乱、军阀割据。面对危机局势,柳诒徵提出要重视历史传统中“尚德主义”。1923年,柳诒徵曾在《学衡》上发表《中国乡治之尚德主义》一文,考察了中国乡治的起源及其流变过程,他着重强调了“尚德”在乡治中的重要作用。柳氏对乡治的关注与20年代中国“联省自治”的运动有一定的关系,但乡治“尚德主义”的提出却为当时迷信西方制度万能的社会提供了另一种社会建设路径。“尚德主义”实际上是从中国传统引导出民族重视道德因素的心理倾向,并将其与现代政治思想相结合,进而开出“德治”与“法治”有效结合的政治发展路径。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迅速沦陷。面对局势,柳诒徵发出了“只有私人崇尚富贵荣利之志,无建立国家增荣民族之志”的嗟叹,他大声疾呼,要求学界不分新旧、捐弃门户之见,“同谋国是,注重实际,不忽当前”“合力以谋人道正义”(50)柳诒徵:《说志》,《国风》第8卷第1期,1936年1月1日。,共同抵御外侮。《国风》时期柳氏行文充满激情,饱含着对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和忧患。“东南学派”对传统历史文化的保守和对“经世致用”的阐释,成为建构民族伦理认同的重要资源。柳诒徵等人提出传统史学孜孜以求的是如何恢复民族自尊,谋求民族的复兴。本着强烈的民族复兴意识,柳诒徵从文化史的角度深入阐释了“主权有转移,而国家从未灭亡”的原因,他的学术研究多围绕着“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这一时期,柳诒徵及“东南学派”编辑整理《江苏明代倭寇事辑》、宋代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明代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任应乾《山海漫谈》等都是“经世致用”史学观的时代体现。柳诒徵认为,史学传统中彰显的伦理型智慧赋予民族文化特有的弹性和韧性,使之能够在文明的变迁中克服危机,持续发展。
与《学衡》时代“唱和者”形象所不同的是,柳诒徵在《国风》时代更为积极主动。作为“国风社”的社长,《国风》刊物是其史学思想的直接体现者。从《国风》发表文章及其运行来看,柳诒徵不仅是精神领袖,而且切实主导了《国风》杂志的思想走向。柳诒徵的学术所长是中国文化史,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是显而易见的,与之前的“学衡派”诸学者相类似,他是道德理想主义与贤人政治主张的支持者。但进入1930年代,与“学衡派”时期的保守立场相比,他或许显得更为“激烈”,这种激烈就是他强烈的民族情感导致的史学救国倾向。柳诒徵门下三杰,龙(张其昀)、虎(胡焕庸)、狗(缪凤林),及相关学者组成的“东南学派”在这一时期通过将史学研究与民族意识结合起来,产生了广泛地影响。
作为“东南学派”的重要代表,张其昀1919年进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学习,以地理学为主修科目。张其昀回忆说,大学时代对其影响最深的老师有三位:刘伯明、柳诒徵、竺可桢。刘伯明曾留学美国西北大学,系统接受过西方哲学训练,重视思想的调适,倡导哲学思想史。张其昀说:“刘先生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主张哲学与史学应互为表里,人类文化史应以思想史为核心。”(51)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自序),《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0卷,台北:文化大学出版部,1989年,第10838页。柳诒徵则强调打通文史,宏观史论与朴学的精细考据相结合,尤其推崇顾炎武之史学、顾祖禹之地理学,他要求学生追踪“二顾之学”(52)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自序),《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0卷,台北:文化大学出版部,1989年,第10838页。。通过统计发现,张其昀在《国风》中发文最多,总计40篇。他不仅直接通过文章来表达学术观点,同时还具体操作杂志的发行以及钟山书局的经营事务。由此可见,张其昀是《国风》同人能够聚合的一个中心因素。以张其昀为核心,形成了不同层次的伦理关系——师友、同窗、同乡、同事。张其昀当年就读的南京高师名师云集,学术气象纵贯中西。刘伯明、梅光迪、吴宓、汤用彤主讲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另一位“东南学派”代表胡先骕后来回忆说:“……欧西文化之真实精神始为吾国士大夫所辨认,知忠信笃行不问华夷、不分古今,而宇宙间确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至理存在。”(53)胡先骕:《朴学之精神》,《国风》第8卷第1期,1936年1月。在《国风》运作的过程中,张其昀同窗好友群的作用也是巨大的。1919年张其昀入南高,同年的还有胡焕庸、陈训慈、缪凤林、景昌极、钱堃新、王庸、徐震堮、陆鸿图、向达等人,这些人也是《国风》的主要作者。
虽然文化论争的形势在1930年代“民族意识”的引导下出现了某种程度汇合,但“疑古派”与“信古派”的争论却并没有因此结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开始推销所谓的《大东亚民族史》,中国的史学家开始意识到中日之间的战争是一场“文化战争”,中国也应该有类似主题的“国史”“通史”。1932年,傅斯年原计划通过组织史语所专家学者一起撰写一部中国通史,但他很快意识到这项工作和史语所《旨趣》中宣称的历史研究原则——“史学只是史料学”相抵牾。然而,民族危机的迫切形势促使傅斯年在仓促间写成了一本简短的《东北史纲》,以便向“国联调查团”证明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但该书的出版很快招致“东南学派”郑鹤声、缪凤林等人的强烈批评。缪凤林在《大公报》副刊发表文章,批评顾颉刚在《东北史纲》的史料选取上存在重大失误,“不仅不知《两汉书》外与东北有关之金石已也,《两汉书》与《魏志》内有关东北史之记载,傅君亦未能尽读也。”(54)缪凤林:《评傅斯年君东北史纲卷首》,《国立中央大学文艺丛刊》第 1 卷第 2 期,1933 年 11 月,第 146 页。该文原在 1933年 6 月至 9 月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连载。缪凤林不仅指责傅斯年没有认真对待传统史料,而且连自己标榜的“动手动脚找资料”的治史原则都不顾了。缪文一出,史林哗然。虽缪凤林对傅斯年的批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同室操戈”的意气,但缪凤林却坚持认为,由于日本学者已经认真地考察过东北历史并获得了大量知识,中国史家有义务与日本学者出于同一水平上。王汎森认为,缪凤林对傅斯年的批评,是“民族主义情感促使他批评另一个爱国者的著作”(55)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70页。,颇有些“爱之深责之切”的意味。
《国风》时期,“东南学派”等文化保守主义学术共同体表达了一种共同的认识:新文化运动后兴盛的反传统造成了中国社会伦理秩序的瓦解,“一盘散沙”的局面势必招致外侮。与这些问题伴随的是对传统学术兴趣的复兴。许多知识分子认识到,自己声称的爱国立场和诋毁民族历史传统之间明显是矛盾的。1935年,十位大学教授发表了著名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了“我们是谁”的尖锐问题。同年,《国风》第6卷7—8期发表章太炎先生一系列演讲:《论读经有利而舞弊》《再释读书经之异议》《论经史实録不应无故怀疑》表达了明确的信史立场,驳斥胡适等新文化派对传统经典史料的轻视。很显然,“史学革命”“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浪高过一浪的反传统思潮在30年代有一次明显的转向,“东南学派”引领的史学伦理化的倾向开始逐渐抬头。《国风》第2卷第1期发表张荫麟文章《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系统总结了五种传统历史哲学家的研究方法与原则,分别是:(一)历史之计划与目的;(二)历史循环律;(三)历史“辩证法”;(四)历史演化律;(五)文化变迁之因果律(56)张荫麟:《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国风》第2卷第1号,1933年1月1日。。张荫麟反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他说:“进步、循环性、辩证法,皆可为人类史之部分的考察之导引观念、试探工具,而皆不可为范纳一切史象之模型。此吾对于史变形式之结论。”(57)张荫麟:《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国风》第2卷第1号,1933年1月1日。张荫麟以周代封建制度崩溃为例反驳历史发展理论,对演化论、理性主义的批判,实际上为历史阐释留下了伦理空间。
“东南学派”史学伦理化的倾向是一贯的。早在清末,柳诒徵就表现出重视伦理的思想倾向。1905年,柳诒徵担任江南高等学堂伦理课教师,采用的教材是自编《伦理口义》,1906年他又陆续编撰了《中国商业史》《中国商业道德》作为教材。1915年—1925年南高师时期,是柳诒徵成长为东南学派精神领袖的重要阶段,他在《国史要义》中精要地阐释了“道德”与“历史”的关系:“述一代全国之政事,而尤有一中心主干为史法史例,其所自出即礼是也。”又说“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58)柳诒徵:《史原第一》,《国史要义》,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9页。也就是说,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是道德观念与道德秩序的现实化。因此他认为史学研究与道德教化不能割裂,应该相互资用、互为阐发。在与“疑古派”十数年的辩论中,“东南学派”对伦理史学的信守虽然被时人视为“落后”“守旧”而青眼难逢,但却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留下独特的历史人文主义印记。
纵观柳诒徵一生的学术观点,中国文化中心史观是其核心思想,而史学伦理化思想又是这核心中的核心。《国风》“圣诞特刊”中,柳诒徵有两篇重要文章可以视为其史学伦理化观点的代表,分别是《孔学管见》和《明伦》。柳诒徵所坚持的“五伦”观念一直是近代“史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所激烈批判的对象。但柳诒徵坚持认为人伦、礼教乃是中国学术、道德、思想行为之根本依托。他主张传统“五伦”不能废弃,重新以“明五伦”作为改变世风和稳定人心的精神力量。柳诒徵阐释了“三纲五常”在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其“五伦”思想与民族意识有着深刻的联系。在《从历史上求民族复兴之路》中他指出“欲求民族复兴之路,必须认清吾民族何时为最兴盛,其时之兴盛由于何故,使一般人知今日之存亡危机之秋,非此不足以挽回溃势”(59)柳诒徵:《从历史上求民族复兴之路》,《国风》第5卷第1号,1934年7月1日。。这表明柳诒徵的史学伦理化倾向并不是要走向复古,而是要重新建构民族伦理认同,从民族历史发展规律中去寻找民族复兴之路,在民族优秀文化中汲取传统伦理智慧,以期能重建时代伦理精神。
四、结语
若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宏观视域下来看,在重大转折时期,关于历史哲学的争鸣似乎是不可避免的。19世纪,黑格尔与兰克之间也曾有过一场尖锐的思想交锋,并由此引发了德国史学界旷日持久的“史观派”与“史料派”之争。作为黑格尔学生,德罗伊森继承了其师“精神哲学”的思想精萃,同时又兼采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将历史研究的视线投射到“道德团体”之上,他说:“在历史的发展中,有时某个伦理道德团体显示出其重要性;有时另外一个道德团体领头发展,好像一切要靠它,一切以它为中心。这个起领导作用的团体,表现出的就是时代或者民族思想。”(60)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胡昌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7页。我们今天对柳诒徵及“东南学派”史学思想进行研究,并非单纯地品评人物、裁定优劣,而是希望通过对这一具有独特气质的“道德团体”发展历程的描画,揭橥民族伦理发展的历史逻辑,进而为文明发展的前路,擎起一支火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