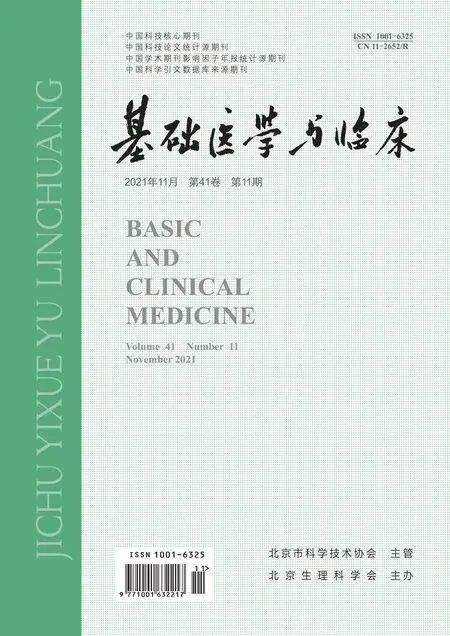COVID-19患者腹泻发生机制研究进展
张少罡,王 冬,宋 洁,张晓岚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消化内科, 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为一种新发病原体感染人体后导致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其病原体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 virus 2, SARS-CoV-2)。从2019年12月至今,COVID-19已成为全球性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造成巨大的社会和经济负担。感染SARS-CoV-2以后,大部分患者主要表现为发热、咳嗽等症状,一些患者迅速发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急性呼吸衰竭和其他严重并发症。但部分患者伴有腹泻、恶心呕吐等消化系统症状,甚至少数患者以腹泻等不典型症状为首发表现或唯一表现[1-2]。
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腹泻概况
COVID-19患者除了发热、干咳、乏力等典型的呼吸系统临床表现外,还会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不典型症状, 且出现腹泻等症状的患者更易发展成为重症肺炎,而在不典型症状中, 腹泻最为突出,COVID-19患者腹泻的发生率在2.0%~49.5%[2-7]。由此可见,腹泻是COVID-19患者常见的不典型症状之一。在各个研究中,患者出现腹泻的比例不同,可能是由于纳入的COVID-19患者的年龄、性别等基本情况不同、肺炎病情轻重不同以及纳入的病例数量不同、不同地域之间的人群差异、病毒毒力不同所导致,还可能与各研究中患者合并不同的基础疾病、基础健康状况不同有关。因此,COVID-19患者出现的消化系统症状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腹泻,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COVID-19患者除了有消化系统的临床表现外,近半数(48.1%)患者的粪便中可以检测到SARS-CoV-2,70.3%的患者在呼吸道标本转为阴性后,粪便标本中SARS-CoV-2检测仍为阳性[7],这表明SARS-CoV-2存在经粪口途径传播的可能性。但病毒是否能够绕过呼吸系统直接作用于肠道、粪便病毒载量是否达到感染标准、粪便病毒在体外留存时间、中间宿主是否存在等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定论,迄今尚不能确定SARS-CoV-2是否可通过粪口途径传播。但粪便和胃肠组织学样本中SARS-CoV-2的证据以及与鼻咽拭子相比SARS-CoV-2在粪便中存在的时间更久,强烈表明经粪口途径传播是可能的,也说明了对疑似患者行粪便标本SARS-CoV-2检测的合理性[7-8]。2020年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也明确表明虽然经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是主要传播途径,但不能除外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情况下存在经气溶胶传播的可能。由于在粪便、尿液中可分离到SARS-CoV-2,应注意其对环境污染造成接触传播或气溶胶传播。因此,尽管呼吸道飞沫传播和密切接触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但消化道很可能是潜在的传播途径,临床医生应警惕COVID-19患者的腹泻等消化道症状,尽早发现、识别以消化道症状为主的不典型病例,防止COVID-19患者的消化道分泌物造成接触传播或气溶胶传播,并及时对粪口途径传播进行预防和控制。
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腹泻的发病机制
2.1 病毒感染肠上皮细胞
SARS-CoV-2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 virus,SARS-CoV)有高度同源性,均为β属的冠状病毒,SARS-CoV-2的S蛋白与SARS-CoV的S蛋白相似,可以在细胞丝氨酸蛋白酶(TMPRSS2)作用下,通过S蛋白与宿主细胞表面的血管紧张素转化酶II(angiotensinconverting-enzyme Ⅱ, ACE2)蛋白结合,从而感染宿主上皮细胞[9-10]。ACE2不仅在Ⅱ型肺泡上皮细胞高表达,也可在消化道等其他系统的细胞中表达,通过数据分析确定了肺、心脏、食管、肾、膀胱和回肠为有感染风险的器官;明确了II型肺泡上皮细胞、心肌细胞、肾近端小管细胞、回肠和食管上皮细胞以及膀胱尿路上皮细胞为易受SARS-CoV-2感染的特定细胞类型[8,11]。在所有正常组织中,ACE2 mRNA表达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小肠、结肠、十二指肠、肾脏和胆囊;ACE2蛋白表达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十二指肠、小肠、胆囊、肾脏和睾丸[12]。此外,为COVID-19患者行胃肠镜检查时取食管、胃、十二指肠、直肠黏膜组织标本并进行免疫荧光染色后发现,ACE2蛋白在胃、十二指肠和直肠上皮的腺细胞中大量表达。在组织学表现上看,食管鳞状上皮中可见少量淋巴细胞浸润;胃、十二指肠和直肠固有层可见大量浆细胞和淋巴细胞浸润,间质水肿,说明病毒感染了胃肠道并引起了肠道的炎性反应。该研究还证实了几乎整个胃肠道都存在SARS-CoV-2的蛋白质外壳[8]。以上所述均为SARS-CoV-2感染胃肠道提供了可靠的证据。此外,根据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中提供的病理结果显示,食管、胃和肠管黏膜上皮有不同程度变性、坏死和脱落,进一步表明SARS-CoV-2可以感染胃肠道并引起胃肠道损伤。出现腹泻的COVID-19患者粪便常规和隐血试验结果提示其符合病毒性腹泻的特征[6]。由此可以推断由于胃肠道上皮的腺细胞中大量表达ACE2,SARS-CoV-2可以与胃肠道表达ACE2的细胞附着,再通过受体识别,蛋白酶裂解和膜融合等过程,进入胃肠道宿主细胞,导致胃肠道出现浆细胞、淋巴细胞浸润、间质水肿,被感染的肠道细胞受损导致吸收不良进而出现腹泻等症状。
2.2 肠道菌群失调
除了病毒感染直接破坏肠道上皮细胞导致腹泻,病毒感染还可导致肠道菌群失调、微生态紊乱进而导致腹泻。ACE2的氨基酸转运功能与肠道内的微生态有关,ACE2与中性氨基酸转运蛋白B0AT1相关联,在ACE2突变小鼠的小肠中不存在中性氨基酸转运蛋白B0AT1的表达,从而使得血清中中性氨基酸的水平显著降低。色氨酸为中性氨基酸当中的一种,其可以控制抗菌肽的表达,而抗菌肽的改变可以影响小肠和大肠的微生态[13],当SARS-CoV-2感染肠道细胞以后,部分肠道上皮细胞功能障碍甚至坏死、脱落,导致ACE2数量减少或使ACE2突变失去正常功能,中性氨基酸转运功能障碍,影响抗菌肽表达,肠道菌群失调,进而导致腹泻的发生。此研究还表明,当肠道氨基酸转运障碍时,可以直接导致机体营养不良,促进肠道炎性反应的发生导致腹泻。此外,肠道与呼吸道之间存在联系,即所谓的“肠-肺轴”,肠道与呼吸道的微生态改变会对免疫系统产生影响,肠道微生态改变后通过免疫系统介导炎性反应等过程导致呼吸道疾病的发生或进展,这说明当患者感染SARS-CoV-2以后,肠道微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肠道菌群失调从而使呼吸道疾病加重,机体免疫功能紊乱、促炎因子释放增多导致肠道炎性反应从而导致腹泻的发生。因此,对于出现腹泻的COVID-19患者,可以行粪便涂片检查了解细菌的数量是增多或减少,有无优势菌或真菌,观察革兰阳性杆菌、革兰阴性杆菌、革兰阳性球菌、革兰阴性球菌4类细菌的百分比、有无比例倒置等来评定受检者的菌群状态;还可以行粪便培养,观察有无可以导致腹泻的致病性细菌、真菌等;完善甲烷-氢呼气试验,根据试验结果判断有无小肠细菌过度增殖,综合判断患者有无肠道菌群失调,必要时可行粪便16S-rDNA高通量基因测序分析,确定粪便中菌群分布情况,从而更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
2.3 治疗药物相关性腹泻
使用抗病毒药物可能导致患者腹泻,一项COVID-19住院患者消化系统表现的描述性研究中发现,55.2%的患者出现腹泻与服用了奥司他韦(Oseltamivir)和(或)阿比多尔(Arbidol)等药物有关[6]。此外,使用抗生素治疗也是导致患者腹泻的原因之一,在纳入了1 099例COVID-19患者的研究中,57.5%的患者使用静脉注射抗生素,此研究中腹泻的发生率为3.8%[3];一项关于COVID-19的前瞻性研究表明,抗生素为患者最常用的药物,有64%的患者接受了抗生素治疗,该研究中腹泻的发生率为8.5%[14]。众所周知,常见抗菌药物(大环内酯类、头孢菌素类、β内酰胺类等)的不良反应引起的腹泻称抗生素性腹泻。COVID-19患者在应用抗生素治疗后,可能由于抗生素的不良反应引起抗生素性腹泻。因此,COVID-19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腹泻,需要注意可能与抗病毒药物和抗生素的使用有关。
2.4 精神心理因素
随着COVID-19疫情的加重,感染SARS-CoV-2的患者不可避免的产生焦虑、紧张等情绪,甚至严重者可发展成为抑郁。关于COVID-19患者心理健康、睡眠状况的调查研究发现,与对照组相比,COVID-19患者焦虑、抑郁、睡眠障碍的发生率明显升高,并且多表现为紧张、焦虑、烦躁、失眠等,此研究中出现腹泻的COVID-19患者比例为18.7%[5];还有一篇关于COVID-19患者紧张焦虑的研究表明,在感染SARS-CoV-2的患者中,焦虑和抑郁是突出的表现,大约2/3的患者有一种或两种焦虑、抑郁症状,此研究中有8.5%的患者出现了腹泻症状[14]。既往研究显示精神心理因素也可导致腹泻,推测COVID-19患者由于隔离等因素导致的高度紧张、焦虑抑郁状态等可能导致患者交感神经兴奋,胃肠动力加快,因此不排除合并有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的可能。
2.5 细胞因子风暴
感染SARS-CoV-2后可能会导致机体免疫系统紊乱,产生细胞因子风暴,被SARS-CoV-2感染的细胞释放大量的炎性介质和趋化因子,导致中性粒细胞聚集,其分泌物、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等也会促进免疫细胞的积累,促进炎性反应进一步加重[2]。在COVID-19患者的疾病进展过程中,细胞因子风暴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和肺外多器官功能衰竭的发生发展相关,患者全身情况较差,机体整体免疫力降低,病毒感染肠道的几率增加导致腹泻等胃肠道症状,还可以通过肠-肺轴等机制使得腹泻的发生率增加。
2.6 原发基础疾病加重
部分COVID-19患者合并有基础疾病[2-3],例如慢性阻塞性肺病、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血管病、乙型病毒性肝炎、癌等,这部分患者预后较差,且更可能发展为重症肺炎。还有部分COVID-19患者合并有原发性腹泻疾病,如炎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和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目前已经有关于IBD患者感染SARS-CoV-2的报道[15],IBD患者长期使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等治疗,机会性感染的风险增加,感染SARS-CoV-2的可能性会更大,且IBD患者更容易产生紧张、焦虑等情况,这些精神因素反而会加重疾病的活动、使原发疾病加重,使得腹泻的症状出现或加重。防止IBD病患者因急性发作而住院可能是避免患者群体感染SARS-CoV-2的最佳方法。
3 问题与展望
COVID-19患者出现腹泻的发病机制可能与SARS-CoV-2和消化道ACE2相互作用从而破坏上皮细胞导致肠道损伤、打破肠道菌群平衡及产生细胞因子风暴有关,此外COVID-19患者的精神心理因素、合并的基础疾病加重及治疗过程抗病毒药物和抗生素等药物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迄今还不能确定SARS-CoV-2能够经粪口途径传播,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因此,对于COVID-19患者出现腹泻等消化系统症状需要临床医生高度警惕,及时发现以免因漏诊造成病毒的传播。治疗上注意抗病毒及抗生素类药物的正确使用,对于肠道菌群失调的患者加用微生态制剂,同时兼顾合并的基础疾病的治疗,并及时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希冀医务工作者加深对COVID-19患者腹泻的认识,更好的了解疾病的发生机制,从而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提高患者的生存率的同时有效的减少病毒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