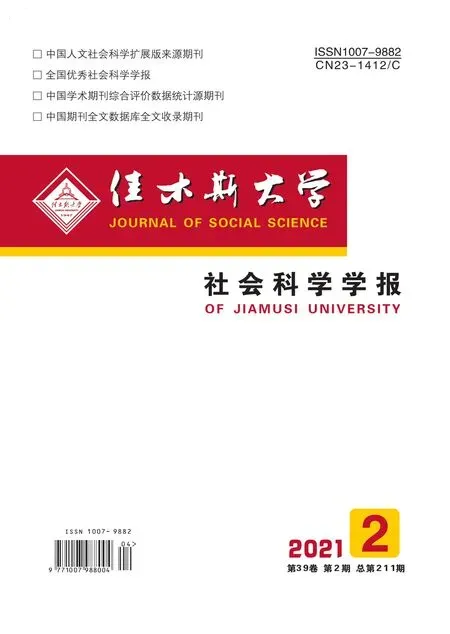解读拉赫娜·里茹托《影孩》中的“影”之意象*
周漪飒
(浙江大学 外语学院,浙江 杭州310058)
一、 引言
拉赫娜·玲子·里茹托(Rahna Reiko Rizzuto)为当代美国著名的日裔作家,以书写二战后普通的日裔美籍人的生活状况著名。她的笔锋尤其聚焦于其中的弱势群体——流民中的女性,以描写她们的生存境况,作品中充满了对女性力量的肯定及对未来的向往。这些流亡的女性不仅要经受战争带来的身与心的双重苦难,面临种族歧视,更甚至可能受到来自本族人内部的排斥及家庭的抛弃。《她为何离开我们》(Why She Left Us)在2000年取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后,《影孩》(Shadow Child)更使她一举成名,并成了她最负盛名的作品。故事叙述了自幼被美国养父母收养的弃婴莉莲,在冲动驱使的婚姻中被送入集中营,最后在遭受广岛之痛后回到美国,并独身在夏威夷岛生活的经历。以及她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性格迥异的花子和景子在遭受了青春期的决裂后,是如何收获和解、走向团聚的。
“影子”在文学中是一常用意象。一般认为,其多数情况下与消极情绪或“鬼怪”“幽灵”这种属于神秘领域的关键词联系起来。例如在福克纳的名作《喧嚣与骚动》中,影的意象使故事往寂静而沉默的方向发展,最终静止在悲剧中[2]34-35。但像《影孩》这类由影之意象贯穿全书的作品却并不多见,很少有作品能仅利用单一的意象将故事的内涵表达到如此极致。除了赋予了影之意象常用的消极内涵以外,里茹托也创新性地将影的内涵转换成绚丽而积极的“守护者”的形象。此外,里茹托擅长叙写内心深处的活动,她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散文般的抒情,这种笔触也使一种淡淡的哀伤像影子一般游动在全书之间。
二、“影”的三重隐喻
虽然小说全文处处渗透着影子的意象,但标题《影孩》却依旧存在理解空间。里茹托一般被认为是一位擅长描写女性的作家,本小说的情节故事也基本只涉及女性,那作者为何不将小说直接命名为“影之少女”(Shadow Girl)或“被阴影缠身的女性”(Shadow Woman)呢?本文倾向认为,《影孩》中提出的问题是人类的共性问题,并没有性别之分。
(一)“破坏之影”
影子首先象征着黑暗,与死亡、绝望及压倒性的力量紧密相连。小说中提到的最直接的破坏力无疑来自于战争。流落于战争中的莉莲时时遭受着死亡的威胁,可她本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广岛化作焦土,唯一的好朋友死在她面前时,莉莲才初次感受到深刻的痛苦和绝望,她才明白生活中的坎坷比起死亡根本不值一提。书中描写莉莲的部分基调阴郁。在她搭乘火车回到广岛时,所遇见的“亡灵队列”(实则为原子弹落下后逃离广岛的人们)成了她永远的噩梦:“有一团奇怪的炽芒燃烧在亡灵身后,这些亡灵好像完全笼罩在阴影之中……莉莲看见了他们的皮肤,那是漆黑的。有些皮肤被烧掉了,外露着森森的白骨。有些皮肤则好像挂在他们的身体上”[1]201。这些逃生者的背后是漆黑的、已变成人间地狱的广岛;笼罩着亡灵的“阴影”就是死神的黑袍。其次,自然力量对人类及环境的破坏也不容小觑。在景子初次跟随继父去观赏火山喷发时,她被自然力量的破坏力震慑,也领悟到某种力量是懂得厚积薄发的阴影才拥有的:“当他说到诞生这个词时,你又退缩了,但周围的空气里的确弥漫着新生的气息。有什么东西是真实存在着的,它正在转化成别的形态:这是一种永恒不变的、黑暗又质朴的力量”[1]124。最后,漆黑的影子又代表了一种野蛮的欺凌。在埃迪等人故意将患有幽闭恐惧症的花子引入岩洞时,他们还一边拿着手电筒在黑暗的岩壁中制造阴影取乐。这时那些不断浮动的阴影暗示了花子和景子即将遭受的伤害以及埃迪等人对这场探险的绝对控制权。
(二)“创伤之影”
过去的创伤化为一个人的影子或梦魇是本文中影之意象最明显的内涵。从其词源学来说,创伤(Trauma)本意是指外部力量给人的身体造成的物理性损伤。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创伤研究开始,基于社会历史及现实的需要,创伤理论就一直在不断丰富和发展。1995年,凯西·卡鲁斯给予了创伤最为权威的定义:“对于突如其来的、灾难性事件的一种无法回避的经历,其中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应往往是延宕的、无法控制的,并且通过幻觉或其它侵入的方式反复出现”[3]135。
由此可见,创伤带来的后遗症是无法逃避的,对于创伤受害者而言,创伤就像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影子。小说首先以姐姐花子为主视角开始了略显凌乱的叙述。花子性格单纯且有艺术天赋,但她的幽闭恐惧症被人利用而遭到霸凌,全身留下丑陋的疤痕。这对一个年轻的女孩来说是一段噩梦般的记忆。她无法摆脱这些伤疤,更无法从过去的创伤中走出来。为了逃避“黑影”,她离开家乡夏威夷,隐居在纽约一个洞穴似的出租房内,每天生活在昏暗的光线中,成了一个与社会脱节的人,并在时不时发作的梦魇中自暴自弃。布满阴影的地方充满了混沌与不可预料的危险,映射了花子一团糟的生活状态和心境。同时,花子无法控制自己不去嫉恨羡慕着阳光开朗的妹妹景子,一边觉得自己是“景的影子”[1]12,一边又坚持认为景子是伤害自己的元凶,殊不知自己片面的回忆、对创伤和寻求真相的逃避态度才是这种劣等感的根源。在花子的自述部分,大量意识流独白的涌入将时空及虚实界限模糊,为阅读带来了困难,也使读者徘徊在花子的心境迷宫内。
经历过广岛之痛的莉莲则一生都在与过去的创伤阴影做纠缠。少女时期时的冲动婚姻将她拉入了无法挽回的深渊,又在经历广岛之痛后费尽心思回到美国。双胞胎这样回忆她们的母亲:“她(莉莲),跪坐在……土沟边,看起来是那般渺小,将要沉没到无声的大地中去了,几乎都要与它融为一体,先是肩膀、再是头。……她只剩一点身体露在地上了,鬼鬼祟祟的黑暗蹑手蹑脚地抱住了她,在某个瞬间,她被带走了”[1]48-49。在这样的一副文字画面内,月下独耕的母亲自成了一副孤独的景色,而与之对应的是躲在窗边偷看母亲的双胞胎。这其中的距离暗示了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和隔阂,更象征了母亲心中始终有块不可揭露的伤痛领域是最亲的亲人也不能够触及的。
作者通过描写花子和莉莲的创伤之影,呈现了分别属于两代人的不同问题。这也是里茹托对人类遭遇及境况思考深邃的一种表现。莉莲颠沛于战争中,从未被当作一个人看待。前夫唐纳德将其视作所有物,在觉得她累赘后果断抛弃了她。她在日本时因为美籍背景而被日本人排斥,而回到美国后她的身份却是“日本来的流民”。因为两个国家都不认可她,她只得在两块大陆中间那个太平洋上的夏威夷岛生存下来。莉莲在战争期间更名为美夜,后者只是她所依附的美国大兵随口喊出的名字。在连一个生存问题都无法保障的环境中,尊严更显得微不足道。而在生存问题得到解决后,作为下一代的花子并不能摆脱母亲的创伤,就如畅销书作家汉娜·廷蒂(Hannah Tinti)说的,这本书显示了“创伤是如何遗传”②的。母亲的遭遇通过她在昏迷时的梦话传递给她的孩子们,使花子从小就无法树立对回忆的正确态度,她通常都将小时候的可怕涂鸦锁在箱子里。通过塑造两位人物的创伤之影,作者实则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类该如何处理创伤、正视回忆?接下来,本文将对该问题进行讨论。
(三)“守护之影”
除了如影随形的创伤以外,还有背后的守护。这一说法和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背后灵”有些类似。小说中的双胞胎妹妹景子个性外向勇敢,一直在暗中保护姐姐和母亲。因为不懂日语的两姐妹在小时候一次对名字的误读,景子接受了“为影”③的命运,并下定决心要变得像火山女神佩蕾一样坚毅勇敢,以保护自己的亲人:“……它(影子)瞬息万变,蕴藏无限可能。……绝不会受任何约束。它绝不总停驻于某处,更不会遭受堵塞。它永不孤独……”[1]151-152。上文已提到,母亲的创伤对孩子的“遗传”尤为明显,但在创伤被下一代继承的同时,景子也继承了母亲那些启发性的故事,并从中获得从不逃避的勇气和品质:“如果她能静静地站着,看着它的眼睛,一切就安然无恙”[1]122。为了替被歧视的母亲出气,景子想法设法反击那些嘲笑母亲的男孩,而不愿自己在学校做的事被母亲和姐姐发现。作者对景子的塑造也安排在人物的爱好中,景子因向往自然的力量,渴望自由,而爱好游泳。水和影子一样具有流动性。通过与水融为一体,她能够化柔为刚、化险为夷。
景子是小说中担负着“拯救职责”的人物,是身为“守护之影”的具体人物,但她也没能守护住被困在岩洞内遭受霸凌的花子。作者意在指出,治愈创伤除了背后守护的具体行动以外,还需要其他的方法。当在景子初到纽约时遭袭、花子与景子间原本“被守护者”和“守护者”的身份得到迫不得已的转换时,作者才开始铺成自己对治愈过去创伤的看法。里茹托安排花子——一个背负着不堪回首的过去、拥有人格缺陷的被动者,去担任主动的施救者角色,以表明生命中美好的过去及人际间的羁绊能带给人多么强大的力量,能化作自我守护及抵御伤痛的铠甲,而在日常生活中却如影子一般潜藏着令人难以发觉。“创伤不能独自面对,只有‘在关系中’才有康复的可能。创伤的复原首先应以恢复幸存者的权利和建立新关系为基础”[4]136。面对病床上的景子,花子开始去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她试图与医生交流,同时事无具细地回忆起她们纯真的童年,并向往着两人能回到儿时那种心灵相通、以及与母亲相亲的状态,由此开始重视起自己的妹妹及其他亲人。最后决定直面自己最不堪回首的过去,并搁置误会找出伤害景子的凶手。文中有一处细节是这样描写的:在母亲因核辐射影响而昏睡时,双胞胎就会尝试着把梦魇中的母亲所描述的鬼怪画下来以达到“镇邪”的目的,并用自己的方法将“被亡灵拽去另一个世界”[1]208的母亲拽回现实世界。透过此处描写,作者意在表明,当创伤和过去遗留的问题超出个人的解决能力时,也应该走出封闭的内心世界,去寻求外界的团结和帮助。
同时,里茹托并未着重将莉莲所遭受的创伤经历上升到二战时期的日裔美籍人的整体层面。虽然作者描写了曼扎纳集中营中日裔美籍人的生活状况、转运日本人的轮船等等,但她依旧将重心放在莉莲这个个体身上。从莉莲被唐纳德的家庭排斥与轻蔑开始,在美国长大的莉莲就从未在日本人身上寻找过认同;而在经历了广岛之痛以后,一直坚信自己是美国人的莉莲也不再去争取自身作为美国公民的权利。莉莲意识到,她的伤痛和悲剧并非是由立场或选择带来的。莉莲是创伤的隐忍者,同时也是反抗者。在毁灭性的打击面前,过于渺小的她只能接受既定事实并尽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于是,依靠着对夏威夷岛的向往以及对腹中一对双胞胎的爱和责任,莉莲用尽办法前往了夏威夷。作者似乎意在表明,人应给予自身价值足够的认可。在面对创伤时,自我的精神力量也非常重要。
三、结语
《影孩》的灵感来源于里茹托朋友遭受性侵害的亲身经历,这件事为她的创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里茹托说:“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女人,一个人类,我一直在思考写作如何能帮助我们治愈这个问题(创伤)。”④《影孩》显然是她为解决该问题而做出的尝试。综上所述,通过从“破坏力”“创伤”及“守护”这三个层面赋予“影子”意象不同的内涵,我们会发现里茹托在文本中所编织的对“过去”及“创伤”的思考。一方面,人们应当正视回忆;另一方面,应给予自身个人价值足够的重视,积极寻找生活的意义。在个体创伤无法得到解决时去积极寻求外界的联系与帮助。
[注释]
①该小说在国内已引进但尚未出版,所用引文皆为笔者自行翻译。
②汉娜·廷蒂(Hannah Tinti)为知名畅销书《好小偷》(The Good Theif)及《塞缪尔·霍利的十二种生活》(The Twelve Lives of Samuel Hawley)的作者。该评论见里茹托主页:https://rahnareikorizzuto.com/shadowchild/。
③“景”(Kei),在日语中本就是“影子”的意思。这是从未受过日语教育的两姐妹对“Kei”这个名字的误读,其实“Kei”读音下还能表示其他很多汉字。
④见拉赫娜·玲子·里祖托在2018年7月15日发表于其主页的博客文。https://rahnareikorizzuto.com/2018/07/fiction-and-the-chaos-of-trau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