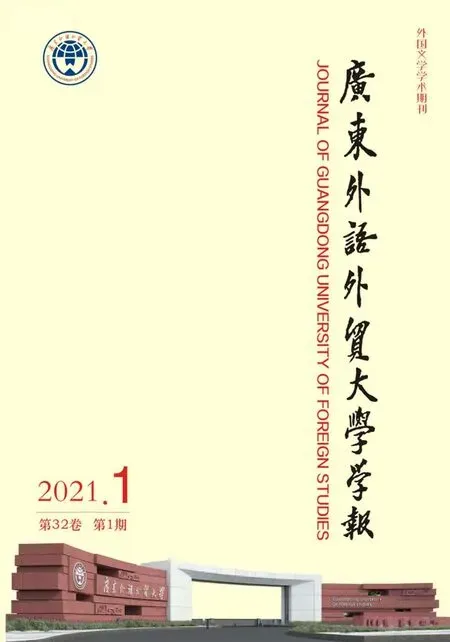《家》:族裔语境下的家园政治书写
张燕 林元富
引 言
《家》(Home, 2012)是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2019)的第10部长篇小说。故事以曾经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黑人退伍士兵弗兰克·莫尼(Frank Money)的创伤及疗伤经历为主线,探讨了20世纪50年代“热战”与“冷战”交互影响下美国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的生存困境。作品发表之后即引起评论界的高度关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独立报》等多家重要英美报刊纷纷载文评介此书,颂扬者居多。米凯科(Micaiko K.)(2012)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书评说,“该作品是理解莫氏所有作品的一把钥匙”。目前,学界对《家》的思想主题研究已颇为深入。研究者们从创伤、空间、身份建构、族裔离散、历史记忆、现代性反思、生命政治等角度探讨了该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及思想主题。蒋欣欣和舒建(2014)分析了小说主人公弗兰克的创伤经历,指出爱与亲情是美国黑人疗愈创伤的良药与走出创伤的根本;许克琪、马晶晶(2015)借用空间叙事理论从地志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三个方面分析小说主要人物的生命体验,探讨历史记忆与黑人身份主体性建构的关系;庞好农(2016)从精神病理学和社会伦理学的角度分析小说主要人物的心理创伤,指出莫氏笔下的战争创伤、亲情创伤及种族创伤折射了二战后美国黑人的生存窘境;艾瑞恩·彭纳(Erin Penner)(2016)通过分析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提醒读者不要忘记朝鲜战争及麦卡锡主义横行的年代美国普通民众所遭受的种种痛苦;胡俊(2017)从记忆与创伤的角度分析小说中的“对抗记忆”主题,认为非裔美国人关于家与个体成长的记忆都充满创伤;文森特(P. Vincent)(2017)认为,莫氏通过描写小说主要人物的辛酸经历,表达了在白人“殖民社会”里遭受凌辱的非裔美国人渴望自由与幸福的心声;刀喊英(2019)借用福柯的权力理论,从权力的空间管制、权力的规训效应和权力关系的流动性三个方面重释小说中的创伤书写,指出美国黑人只有回归社区,接纳过去,正视创伤,重建与他人的关系才有可能疗愈创伤,完成身心的“回家”之旅;张银霞(2018)借用西方现代性理论从时间、生产形态及文化传统三方面探讨了小说中的反现代性叙事,指出传统文化对当代黑人走出生存困境具有启迪意义;李晓丽(2020)分析了小说文本叙事中的生命政治表征与隐喻,认为莫氏打破了长久以来公共叙事中对生命政治在20世纪50年代任意宰制黑人生命的缄默。
《家》是一部思想内容十分丰富的作品。查尔斯(Charles R.)(2012)指出,小说触及了莫里森此前所有作品中探讨的那些令人惊悚的主题。关于《家》的思想主题,有一点读者不能忽视,即作家对于家(园)问题的深度思索。20世纪90年代,莫里森曾说,“种族和家园是她作品首要关注的主题”(Lubiano, 1997: 3-4)。她这一创作理念在新世纪的创作中未曾改变。在《家》发表之前,伊芙琳·施莱波(Evelyn J. Schreiber)(2010)曾就莫里森9部小说中的种族、创伤和家(园)主题做了整体性的考察。家(园)无疑是《家》的核心主题。该作品不光以家一词命名,而且以该词结束——“我们回家吧”(Let’s go home),其扉页上的题诗更是明确无误地点明了小说的家(园)主题:这是谁的屋子?/ 谁的夜晚没有一丝光亮?/ 哎呦,谁拥有这栋屋子?/ 它不是我的。/ 我向往另一栋甜美明亮的 / 看得见彩色的小船划过湖面,/ 广阔的田野向我张开双臂。/ 而这栋多么陌生。/ 暗影幢幢。/哎呦,告诉我,为什么我的钥匙能打开这把锁?①
对于《家》中的家(园)主题,在作品发表之初已有个别学者论及。赵宏维(2012:18)在评介该小说时指出,莫里森把家(园)想象置于种族历史的语境中,《家》中的人物命运表明“黑人社区或是黑人村落总是非裔种族最终的归宿和家园”。王守仁、吴新云(2013)从国家、社区和房子三个层面分析了小说中作家关于美国黑人生存空间的现实性和可能性的思考,并强调了爱在美国黑人家(园)建构中的重要作用。近些年,已有学者对小说中的家(园)主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何新敏(2016)从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三个方面对莫氏不同时期作品中的家(园)意象做了整体性的把握,指出莫氏笔下的家(园)意象经历了从具体到抽象,从物理空间到社会空间层层深化的嬗变,认为《家》为美国黑人描绘了一幅幸福快乐的家(园)蓝图;易朝辉(2016)分析小说中“家”意象与小说人物创伤经历之间的联系,认为主人公的归家和疗愈体现了莫氏在面对美国黑人个体及集体创伤时的乐观理想;马克·泰伯恩(Mark Tabone)(2018)认为小说中的家(园)意象折射了作家的乌托邦叙事冲动和当代非裔美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寻和期待。本文侧重从种族、性别和生态的维度审视《家》的家(园)主题,进一步探析莫里森在该作品中所表现的家园政治。
《家》与白人家园政治
按照雪莱·麦勒特(Shelley Mallet)(2004)的观点,传统意义上的家(园)常让人联想起房屋、家庭、避难所、自我、性别或旅行,是一个按功能、经济、审美和道德理念建构起来的狭小空间。现代意义上的家(园)不是一个局限于房屋和家庭关系的封闭空间,其边界较为开放,可延伸到社区、郊区、城镇或城市,它更强调一种宽广的社会关系。莫里森在其小说创作中对家(园)意义的探寻既强调物理空间的存在感,也注重个体对家庭、社区、性别或族群的认同感,是一种物质获得感与精神归属感的糅合。
《家》主人公弗兰克的继祖母丽诺尔(Lenore)是一位渴望融入白人家(园)的寻梦者。在原先的家被白人种族主义者毁坏之后,她所寻找的是那种把安全、舒适和独享作为首要考虑因素的传统白人式的家(园)空间。所以,当贫穷落魄的弗兰克一家人来投奔她时,她感到痛苦不堪,觉得自己的家(园)梦刹那间被击碎了,之后便将所有的怒气发泄在弗兰克尤其是他妹妹希(Cee)身上。虽然哥哥对妹妹保护有加,但由于父母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希在其继祖母的淫威之下养成了自轻自贱的个性。丽诺尔的前任丈夫被白人种族主义者所杀,之后她背井离乡,委身下嫁给身无分文的无业游民塞勒姆(Salem)。她虽然也曾像弗兰克一家人一样饱尝过无家可归的痛苦,但她始终无法容忍与他们分享自己的房子,对他们寄人篱下的悲戚没有丝毫的恻隐之心,即使他们“对她感激涕零,做了她希望他们做的一切并且毫无怨言”(Morrison, 2012: 88)②。丽诺尔以为,只要独享那所房子,她就能拥有一个舒适、安全的家。殊不知,房子只是一种物理空间结构或地理景观,而家(园)则是“一种情感空间”(Rubenstein, 2001: 1)。莫里森曾指出,家(园)是让人身心都感觉安全的社会空间,它的内涵绝不仅限于房屋(Lubiano, 1997: 10)。弗兰克一家搬走之后,虽然丽诺尔如愿以偿独享那幢房子,但她始终无法获得那种家的温暖和归属感:仗着自己有钱有房有车,她一直瞧不起自己的邻居,不屑与她们为伍;要不是帮她干活的小姑娘杰姬(Jackie),她与整个社区几乎是隔绝的。家本该是一个避风港,但丽诺尔的家最后却成了一个人人想要逃离的地方。弗兰克宁愿参加随时都可丢命的朝鲜战争也要逃离这个家,他的妹妹希即便被丈夫抛弃、父母双亡之后也不愿再回这个家,就连杰姬也与她的狗一样一去不复返。形单影只的丽诺尔最后因中风而长期被囚禁在那个牢笼似的房子里,口齿不清地说着连她丈夫都听不懂的话,几乎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她不惜代价得来的所谓家的隐私也被那些前来照看她而她曾经不屑一顾的女邻居所窥视。丽诺尔苦心经营的家(园)梦彻底破灭,莫里森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告诉读者:那种以个人主义为基点的白人家(园)理念未必适合其他美国族裔人群。
主人公弗兰克的女友莉莉(Lily)也是一位家(园)空间的寻梦者。小说故事没有交代莉莉属何族裔,但从她的生活状况来看,她应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有色人种。她不关心政治,也没有什么社交和朋友,她的生活目标是,努力工作攒够钱,把家安在城市高档的白人社区里。她天真地以为,“只要她穿戴整齐,头发纹丝不乱”(Morrison, 2012: 73),就能被白人社区所接纳。殊不知,对于白人而言,家(园)是“一种建立差异的方式”,它是“排异的”(George, 1996: 2)。买主与中介的一纸约定早就将如莉莉之类的“希伯来人、埃塞俄比亚人、马来人或其他亚裔等非我族类”(Morrison, 2012: 73)排斥在外。不过,莉莉对传统白人式的家(园)梦却是孜孜以求。与传统的白人女性一样,莉莉也认为家是居家女性个性的展现,女性所要做的就是“装饰和维护它,就像她装饰和维护她的思想、个性和身体一样”(George, 1996: 23)。她根本没意识到,家并非中立之所,“它是被他人构建,被他人设计的,[具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费小平,2010:10)。她寓所里随处放置的个人生活用品,诸如灌肠器、灌肠器附件、卷发器以及各色牌子的除毛液、脸霜、柔肤水和除臭剂等器物说明她认同的是城市白人男权社会的价值观;她遵循的是传统白人女性那种“女为悦己者容”的生活理念。弗兰克居住在她寓所期间,她不但没有抱怨他没有固定的工作,而且也能容忍“每一桩家务活——不管多小——一律是她的:他散落在地板上的衣物,水槽里盛有剩菜剩饭的盘子,瓶口大开的番茄酱瓶,排水管中他剃下的胡子,卫生间地板上扭成一堆的没绞干的毛巾”(Morrison, 2012: 78)。弗兰克离家出走之后,莉莉把她在雪地里捡到的那个钱包放在他曾睡过的地方。此一细节寓意深刻,它表明莉莉的心灵已无家可归,唯有通过金钱和物质来满足其扭曲的消费欲望,她此刻感受到的势必是霍米·巴巴所说的“非家幻觉”(the unhomeliness),即那种“家和世界位置对置时的陌生感”(Bhabha, 2004: 13)。
从空间和历史的角度看,美国理应是众多少数族裔人群的家园,但由于种族歧视的存在,他们很难有家(园)的归属感,“他们像是在异乡流亡者那样无所凭依”(王守仁、吴新云,2013:113)。美国主流社会对少数族裔的边缘化和疏离,使美国少数族裔没有明显的社会和文化归属感,使他们饱受身份焦虑的困扰(张莘梅, 2020: 29)。丽诺尔和莉莉的家(园)体验均以痛苦而告终,她们成了精神无所皈依之人。她们家(园)梦破碎的根本原因在于,她们盲目认同白人的家(园)政治,把自己的人生世界局限在一种或是个人主义或是父权思想为主导的狭小空间里;她们没有意识到传统的白人家(园)空间遵循男性霸权主义的逻辑,具有限制性和禁闭性的特点,它“不是圣殿而是牢笼”(Rubenstein, 2001: 2)。小说中,斯考特(Scott)医生的家显然是白人男性霸权主义统治下家(园)空间的写照③。弗兰克的妹妹希在斯考特医生家的遭遇说明,他家根本不是一个“具有养育意义和保护意义的空间”(George, 1996: 1)。不像莉莉狭小简陋的寓所,斯考特医生的家宽敞通透、装修精良,即使是希的佣人房也比莉莉的寓所强上许多倍,所以有一段时间希甚至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美好而安全的家。表面上看,斯考特的家是一个充满仁爱的半私人化、半公共化空间——斯考特医生把自己的诊所设在家中,免费帮穷家妇女或姑娘治病,而当这些女性因医治无效而亡时,他甚至还捐钱埋葬她们。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完全由父权理念所控制的家。女性在这个家里几乎是无声的,甚至是隐形的。斯考特医生的妻子犹如花瓶之类的摆设——尽管她身穿女王般丝质的宽袖曳地长裙,也从不用干家务活,但她极少离开这个家,整日沉溺于鸦片西汀和无聊的电视节目,对丈夫所做的事情她从不敢发表自己的看法。而斯考特医生所痴迷的女性子宫实验更是说明他的家是一个控制和阉割女性自我和属性的场所——他借用阴道窥探镜之类的医疗工具窥视女性的阴道和子宫,甚至还往她们的子宫里注射有毒的药物。希就差点因此而送命,尽管另一佣人萨拉(Sarah)和弗兰克对她的救助十分及时,但她却永久性地丧失了生育能力。斯考特医生的家是那个充斥着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白人社会的缩影,希的悲惨遭遇意味着,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试图在白人男权主义为主导的社会里寻找精神家园无异于缘木求鱼!
《家》与绿色家园空间的追寻
黑人是美国社会的“异乡人”(范小红,2016:156)。对他们而言,家(园)就是他们追求自由、平等、正义和机会的“美国梦”,它与种族、阶级、性别、身份、文化、历史等因素密不可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莫里森在其家(园)书写中十分强调个体(尤其是女性)日常伦理行为与社群生存环境的关联作用。在普林斯顿大学举办的种族问题研讨会(1994)上,莫里森曾做了一个题名为《家》的演讲。她用讲故事的方式描绘了她理想中的黑人家(园):
一个没有睡意的女人总是能从床上起身,披上披巾,坐在月光下的台阶上。如果她愿意还可以走出院子,沿着大路走走……方圆几里地没有任何东西会把她当作猎物。她可以慢慢悠悠地散步,想走多慢就走多慢,一边想着备餐或是家庭琐事;她也可以举头遥望星空,想想战争抑或什么都不想……如果途中她注意到有灯光从窗户上透出来,听到有婴儿因腹痛而哭闹,她会踱步到屋前,柔声叫唤屋里那个正在哄孩子的女人……然后,她可以决定回到自己的床上,疲劳劲一过就睡觉,或者也可以沿着她走的方向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路口,甚至更远……(Lubiano, 1997: 9-10)
按照莫里森的构想,一个有生命力的黑人家(园)绝不是一个封闭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隐私空间,它是一个特别关注黑人女性姐妹情谊、边界开放的社区化空间。西娅·多柏思(Cynthia Dobbs)指出,那是一种包括房屋及其周边人文环境、“涵盖其他女性的房子以及房子之间间隙”的“无边界的空间”,“它是否安全和自由取决于黑人女性是否同时感到自由、安全以及相互关联”(Dobss, 2011: 109-110)。
小说主人公弗兰克和他的妹妹希最后回到自己的家乡莲花镇(Lotus),他们住进了父母留下的闲置多年的老房子。莲花镇之所以成为这两兄妹最终选择的生活家园,正是因为它是一个边界开放的社区化空间。与具有排他性的白人家园不同,莲花镇是纳异的,它既能容纳有恋童倾向的K女士,也能容纳像丽诺尔那样生性自私刻薄的外乡人。镇上居民对邻居总是倾囊相助,对于那些来自异乡的陌生人(甚至是触犯法律的逃犯)也慷慨大方。在这个镇里女性之间关系和谐、融洽。给希治病疗伤的邻居爱索尔小姐(Miss Ethel)和其他女性尽管在长相、衣着、说话方式、饮食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她们能分享一切。对其居民而言,这个乡镇社区既安全又能让人充分享有隐私。从那些“院子烤架上的猪排发出的嗞嗞声”以及“屋子里土豆色拉、凉拌卷心菜丝以及早季的甜豆”和“凉在冰箱上的玛德拉糕”散发出的香味,弗兰克始终能感觉到一种“安全和善意”(Morrison, 2012: 118)。而身为女性的希同样也感到舒适自在,她甚至可以坐在爱索尔小姐的后门廊边裸露下半身,接受阳光对其下腹的照射治疗,而无须担心其他人的偷窥乃至伤害。她和莲花镇其他多位黑人女性如爱索尔小姐和梅林·斯通(Maylene Stone) 一样,都是在这个充满爱与关怀的社区里走出过去的阴影,抚平她曾遭受过的所有身心的创伤④。
更为重要的是,莲花镇已非莫氏早期小说《秀拉》(Sula, 1973)中的“底层”(Bottom)社区,它不再是一个束缚女性个性和自由的牢笼,不再是弱者的庇护所。相反,它成为女性展示人格和尊严的处所。在家所属的空间里,女性不再是需要保护的弱者,她们在经济和精神上都变成独立的个体。就连那个给社区男孩免费提供性启蒙且偶尔从中获取愉悦的K女士也不例外。她在自家的厨房里为别人做头发谋生,并且敢于忤逆那个前来劝她改“邪”归“正”的牧师。在父权社会里,厨房通常被认为是家(园)空间里女性伺候一家老小的场所。但在莲花镇,K女士却是在厨房里开展日常工作,为自己赢得经济上的独立,并最终拥有独立的人格。而希也是在厨房这一空间里开始独立思考自己的人生——她反思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并意识到作为一名女性,她应该独立自主,而非依赖自己的哥哥,更不能将自己捆绑于丈夫的身上,她甚至能从容接受自己永远不能做母亲的事实。此外,在爱索尔小姐的门廊里,希还与其他女性结下姐妹情谊,并在她们的指引下重新审视自我,开始新生活。门廊是传统家(园)空间里女性扮演她们角色(她们在那儿做女红)的地方,希也是在那里学会了缝制被子。笔者以为,希学会缝被子是其创造力的体现,是她谋求经济独立、赢得个人尊严、形成独立人格的象征。因此也可以说,莲花镇是一个以“女性在何处为标识的家园空间”(费小平,2010:25),希在那里的家(园)体验颠覆了男权社会对女性性别角色的界定。
莲花镇之所以能成为黑人女性却病疗伤、养护个性与人格的家园还有另一重要原因。文本显示,莲花镇是一个远离现代城市文明而与大自然共生共荣的绿色空间,是作家有意构建的一种生态意义的家园。与离莲花镇不远的“有商店、有自来水、有邮局、有银行、有学校”(Morrison, 2012: 46)的杰弗瑞(Jeffery)镇相比,莲花镇远离现代城市文明,它不通电,没有自来水,也没有车来车往的公路,更没有室内抽水马桶,居民们也不使用诸如冰箱之类的现代化电器,一切都呈现出前现代社会的特征。在那里,时间仿佛是不存在的,人们的生活完全按照自然的节奏,他们的日常安排遵循一种“超越时间的时间”(Morrison, 2012: 120)。弗兰克家里的那个“没有转柄,没有指针的手表”(Morrison, 2012: 120)表明,那里的居民不像生活在城市的人那样要时刻遭受“时间暴政”(吴国盛,2006:100)的约束和蹂躏。在莲花镇,人们普遍没有接受过太多的教育,他们很多人连《圣经》都读不懂。他们的生存更多是依靠那些感性的技能——“完美的记忆力,照相机般的头脑,灵敏的听觉和嗅觉”(Morrison, 2012: 128)。他们最重要的谋生工具不是现代化的机械而是他们自己的双手:他们用手缝被子、做食物罐头、用手采摘食物和宰杀动物(Morrison, 2012: 127)。希在生命垂危之际没有被送往现代化的城市医院,给她治疗疾病的药物不是各种抗生素而是阳光以及爱索尔小姐等人采摘的炉甘根之类的草药。
莲花镇有点像我国当代小说家阎连科小说中描写的“诗性地理空间”,如《日光流年》里的“三性村”、《受活》里的“受活庄”和《风雅颂》里的“诗经古城”,它们都位处深山老林,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生活自给自足,“自然而然”。莲花镇的居民也过着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活。他们在自己房子的前院以及后院种满了各种各样的鲜花——红的、紫的、粉的和中国蓝的金盏花、蔊金莲、天竺牡丹,它们能保护蔬菜免受疾病和食肉动物的糟蹋(Morrison, 2012: 117)。“社区母亲”(community mother)⑤爱索尔小姐家的花园无疑是莲花镇居民亲近大自然的隐喻:她的花园生机勃勃、欣欣向荣,“豇豆弯了又直,宣告着它们已经成熟待食。草莓须四处蔓延,它们高贵、红色的果实在晨雨中闪闪发亮。蜜蜂怀着敬意聚集在八角茴香的周围并吸食其花蜜”(Morrison, 2012: 130)。王守仁和吴新云(2013:116)将此花园意象解读为“一个人对各种威胁的应对和处理”, 他们的读解不无道理,因为爱索尔小姐是一个很有办法的园丁,她总能“阻断或摧毁花园的敌人”——“她围裙带子上系着一小包蒜瓣。她说,这是对付蚜虫的……胆大自信的浣熊那细嫩的脚掌一碰到碎报纸或围着植物的细铁丝网后就会哇哇大叫赶紧逃离。玉米棒安全地呆在纸袋子里,臭鼬没法糟蹋它们”(Morrison, 2012: 130)。不过,笔者以为,爱索尔小姐的花园更接近于米歇尔·克里夫(Michelle Cliff)在其《要求承认他们教我唾弃的身份》(ClaiminganIdentityTheyTaughtMetoDespise)一书中所描绘的那个花园:它是私人化领域和公共化领域的交界处,是一个“私人的开放空间”(George, 1996: 29),它能使家(园)免于成为一个“门户紧闭、边界封锁之所”(George, 1996: 18)。作为一种自然的隐喻,该花园意象在某种程度上蕴含了莫里森的“返魅自然观”⑥及其建构黑人生态家园的浪漫诗学动意。或许,在莫里森眼里,唯有自然才是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安全的身体栖居之地和心灵皈依之所。
《家》的家园想象与莫里森的家园政治隐喻
“家园是人类心灵深处永恒的依恋和风景”(刘保亮,2009:92)。建筑学家巴兰坦(A. Ballantyne)说,家(园)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础,“与我们生活中最为私密的部分密切相关”,它见证了“我们所受的羞辱和面临的困境,也看到了我们展现给外人的形象”(尤迪勇,2014:266)。需要强调的是,家(园)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客体,它是一个通过权力关系并以一系列表征符号为媒介建构起来的“主体想象物”,它涉及个体在不同空间中的身份与政治体验(费小平,2010:1-2)。纳斯塔就指出,它不一定指物理空间意义上的故土故园,其指涉意义是不断变换的,“它是这里也是那里,是过去也是现在,是本土也是全球的,是传统也是现代的”(Nasta,2002:244)。从后殖民批评的角度看,家(园)也可以指跨民族、跨文化语境中个体表述政治反抗、寻求文化身份认同的一种精神需要,它是一种建立在碎片记忆基础之上并经过再想象的“神话构思”(Nasta,2002:9)。罗斯玛丽·乔治(George, 1996: 6)一针见血地指出,“想象家园同想象国家一样都属于政治行为”。
莫里森在《家》中以精巧的笔法绘制了“一幅在精神困境中建构精神家园的黑人群像”(李美琴,2013:14)。小说中的家(园)想象无疑也是一种政治反抗叙事的隐喻,小说中的家(园)故事旨在颠覆那种充斥着男性霸权的私人化空间,即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被少数人建构为专属领地的充满欲望的地方”(George, 1996: 9)。也可以说,《家》中主人公的家乡莲花镇是一种寓言性的乡村生态空间——莲花是一种纯洁和完美的象征,其生长之地象征着“未开化的人类所处的混沌(状态)”(米特福德、威尔金森,2010:87)。莲花镇居民古朴的生活体验超出了他们现实世界的日常经验,他们所要对抗的是那个充满各种欲望和邪恶的、远离自然与生命本真状态的白人城市社会。
王守仁和吴新云(2013:119)在分析《家》的主题思想时指出,该小说在呈现黑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黑人家庭生活上有别于以往的作品,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基调”。何新敏(2016:35)也认为,《家》呈现了一幅黑人之“家”的蓝图,“它不再是冷漠的孤岛,而是一个快乐的家园”。笔者以为这一观点有点武断。小说中,弗兰克和他的妹妹希虽然最后在自己的故乡莲花镇找到了精神栖息之所,但那里的生活仍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抗争,它并非安全祥和的世外桃源。小说中有些细节特别值得读者注意,比如,第13章写道,蚜虫、蛞蝓、浣熊和臭鼬对爱索尔小姐的花园里的一切虎视眈眈,就连能孕育万物的太阳也“威胁着莲花镇,折磨着这里的山水草木”(Morrison, 2012: 117),并“尽其所能烧毁枝繁叶茂的大树下上帝所恩赐的宁静,糟蹋你与那些不会贬损或者摧毁你的人相处而得的快乐”(Morrison, 2012: 119)。贪婪的虫兽与火辣的太阳吞噬莲花镇绿色和宁静的生活。爱索尔小姐就说,“她的花园不是伊甸园”“整个掠夺性的世界”(Morrison, 2012: 130)时刻威胁着它的存在。莫里森似乎以一种隐喻性的方式告诉读者,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种族和性别歧视依然觊觎着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力图建设的家园。
家(园)是想象之物,“理想家园永远在建构中”(胡俊,2010:200)。从某种程度上讲,莫里森每一部小说的故事都与家(园)想象有关:《最蓝的眼睛》(1970)通过黑人小女孩佩科拉的悲剧命运告诉读者,在一个种族歧视肆虐的国度里,黑人的家(园)永远无法成为爱与温暖的空间;《秀拉》(1973)通过秀拉和奈尔不同的生活命运说明,以传统婚姻家庭观念为主导的黑人家(园)绝非黑人女性安身立命之处,它很有可能成为束缚女性自由和个性的牢笼;《所罗门之歌》(1977)中梅肯·戴德父亲建立的“林肯天堂”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黑人家园,梅肯永远是白人社会的寻梦者,他终其一生都未能回归那个理想的家园;《柏油孩子》(1981)中接受白人正统教育的黑人女性杰丹最终没有融入黑人的生活家园而宁愿成为白人世界里的文化孤儿;《宠儿》(1987)中的女主人公塞斯的生活家园笼罩着蓄奴制时期亲生女儿被自己惨杀的阴影;《爵士乐》(1992)中从南方乡村流落到北方城市的黑人夫妇乔和维奥利特因都市生活的种种压力而从未享受过爱的甜蜜和家的温暖……莫里森在《家》中的家(园)想象也是一种对非裔美国人历史与现实生活的再审视。
结 语
莫里森在《家》中探讨黑人建构家(园)的问题时仍然是“希望和警示参半”(胡俊,2010:210),该小说的基调与她前一部作品《一点慈悲》(AMercy, 2010)并无本质性的差别。如果说《一点慈悲》中作家通过描写白人种植园主雅各布(Jacob)那栋充满黑奴斑斑血迹的豪宅,鞭笞了白人种族主义家园空间奴役人性的邪恶和欲望,那么,《家》中那个边界开放、女性自由独立并相互关爱、各种生命形式皆被赋予主体性的绿色家(园)空间则是对以个人主义和父权思想为基点的白人家(园)空间的“反写”和颠覆。这种“反写”是作家试图从自己灵魂深处的怀疑和痛苦中挣扎出来的一种努力,是鲁迅式的“对绝望的反抗”。这种“努力”和“反抗”是作家本人在面对现实黑暗时有意装点一些光明而用的一种“曲笔”(钱理群,1999:144)。《家》的男女主人公弗兰克和他妹妹最后走出战争与暴力创伤的阴影,并找到他们的精神家园,此结局也可以视为莫里森有意设置的“曲笔”,其意蕴与莫氏以往的作品相近,也体现了作家“敢于面对历史与现实、努力为自己的同胞尤其是黑人女性寻找和探索生存之路的精神和勇气”(杜志卿,2006:94)。
注释:
该题诗的中译文为刘昱含所译,个别词句略有改动。见托妮·莫里森. 2014.家[M].刘昱含,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②作品中的引文出自Toni Morrison,Home(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2),引文为笔者自译。
③斯考特医生家里的书架上放的尽是那些充满种族主义思想的书籍,如《一个伟大种族的消逝》《遗传、种族与社会》等,读者不难判断他是个种族主义意识浓重的白人。
④莲花镇的女性身后似乎都有一段辛酸史:爱索尔小姐的一个儿子在底特律被杀;梅林·斯通只有一只眼睛,另外一只眼睛在锯木厂被一块木片戳瞎了。
⑤安德莉亚·奥瑞丽(Andrea O’Reilly)指出,爱索尔小姐与《宠儿》中的贝比· 萨格斯(Baby Suggs)以及《天堂》中的康索拉塔(Consolata)都是心有博爱的“社区母亲”(Dobbs, 2011: 114)。
⑥“返魅自然观”肯定自然的主体性,不以人类自身的利益为准则去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与“祛魅自然观”截然相反,后者强调工具理性,完全把自然看作是满足人类各种需要和欲望的存在。详见孔一蕾. 2013. 澳大利亚人的家园建构——大卫·马洛夫和他的小说[J]. 外国文学动态(2):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