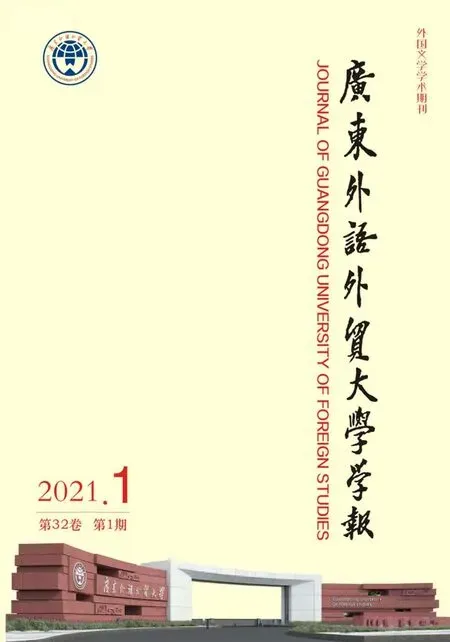论奥维德《变形记》中物的哲学与叙事
江澜
引 言
作为古罗马繁盛时期大诗人奥维德(P. Ovidius Naso,公元前43—公元17年)留给后世最光辉的遗产,采用六拍诗行扬抑抑格(hexameter dactyl)的神话叙事诗《变形记》(Metamorphōsēs)①自从问世以来吸引了无数的阅读者、翻译者、改编者、模仿者和研究者,相关的各种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即使在中国,也不乏支持者,既有译本,如杨周翰(1958)翻译的《变形记》,又有论著,如江澜(2019:443-447)的专著《古罗马诗歌史》第三编第四章第五节。此外,还有不少论文,如龙阳(2008:274-277)的《奥维德〈变形记〉爱的主题》、刘遥(2009:48-50)的《奥维德〈变形记〉的空间性》、吴琼(2012:128-142)的《观看与惩罚——奥维德〈变形记〉中的观看叙事》和赵蕾(2012:20-22)的《从〈变形记〉的政治意蕴看奥维德变形的真谛》。由于以人的认识论为哲学基础,迄今为止的研究都属于以人为中心的人叙事研究。
然而,在后人文主义和去人类中心的整体思潮下,叙事研究正在发生根本的转向,即从人叙事研究转向物叙事研究,其标志是2017年唐伟胜发表的理论性文章《思辨实在论与本体叙事学建构》(28-33)和实践性论文《爱伦·坡的“物”叙事:重读〈厄舍府的倒塌〉》(6-11)。物叙事研究的哲学基础是以物为本的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依据《思辨转向:大陆唯物论与实在论》(TheSpeculativeTurn:ContinentalMaterialismandRealism,2011),思辨实在论是由布雷西亚(R. Brassier)提出的,主要有四种变体,即梅亚苏(Q. Meillassoux)的思辨唯物论(speculative materialism)、布雷西亚的先验虚无论(transcendental nihilism)、格兰特(I. H. Grant)的先验唯物论(transcendental materialism)以及哈曼(G. Harman)与布莱恩特(L. Bryant)的面向物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尽管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侧重点,甚或有不同的立场,可他们的主旨是一致的,即抑人,扬物,重新定义物(郝苑,等,2017:102)。
在上述的语境下,拟用日益趋热的物叙事研究的全新视角,重新解读奥维德的《变形记》。
物的哲学
在《变形记》中,奥维德不仅讲述各种各样的变形故事,而且还阐述变形的哲学依据。在1984年为《变形记》中译本写的《译者序》中,译者杨周翰指出,变形背后的哲学基础是卢克莱修(T. Lucretius Carus)的一切都在变易的观点(奥维德,2008:4)。这是值得商榷的。与奥维德的《变形记》密切相关的不是卢克莱修在《物性论》(DeRerumNatura)中讲的伊壁鸠鲁(Epicurus)唯物主义自然哲学,而是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学说,即灵魂转移说。首先,在《变形记》中奥维德已经明确指出,毕达哥拉斯声称,他受神的感召说话,向世人表露至高的神意,像祭司(pontifex)——即“人与神之间的中介”——一样。第二,尽管伊壁鸠鲁学说与毕达哥拉斯学说都强调“变化”,而且都认为“有神”,可是两者存在本质的区别。譬如,伊壁鸠鲁认为,神不干预人的生活,而毕达哥拉斯学说则认为,神干预人的生活。又如,伊壁鸠鲁认为,灵魂是有死的(Lucretius,2006:6-15,220-253),而毕达哥拉斯则认为,灵魂“永不寂灭”。
奥维德之所以选择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移说作为变形的哲学依据,是因为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起初,奥维德轻视公共生活,重视私生活,回归人的内心世界,写非常私人的诉歌,尤其是爱情诉歌,如《恋歌》(Amores)和《爱经》(ArsAmatoria)。这已表明,奥维德属于消极反抗主流社会的墨萨拉(Mesalla)文学圈,而不属于为执政者效劳的迈克纳斯(Maecenas)文学圈。更重要的是,在《恋歌》中,奥维德痛斥把恺撒(Caesar)颂扬成为神的人,这肯定会让恺撒继承人奥古斯都(Augustus)耿耿于怀。而《爱经》又为伤风败俗推波助澜,与奥古斯都极力推行的整顿道德风纪的政策背道而驰。因此,尽管奥维德的第三任妻子与奥古斯都的妻子私交甚好,可他仍然引起奥古斯都强烈不满。公元前8年,奥古斯都抓住一个奥维德犯下的“错误”——或指奥维德见到奥古斯都的家丑,即奥古斯都的外孙女小尤利娅(Iulia)与人私通,流放奥维德。所以从创作时间(前8—前2年)来看,《变形记》是具有流放时期忏悔性质的作品。为了结束流放生活,中年的奥维德思想大转变。譬如,他强烈谴责刺杀恺撒的共和派,认为“忤逆之手疯狂地用恺撒的血抹污罗马的伟名”,把罗马人民对奥古斯都的忠心与众神对主神朱庇特的忠诚类比,甚至认为奥古斯都比恺撒更伟大,“不是由凡俗降生,他应该是神”,天神让奥古斯都统治罗马人民是“赐福给人类”(江澜2019:249-251,430-433,443,445)。总之,奥维德从反主流社会到迎合主流社会的思想大转变与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移说十分契合。
(一)万物有灵
与柏拉图(1963:119)把物体分为有灵魂的自动物体与无灵魂的他动物体不同,毕达哥拉斯主张万物有灵。
毕达哥拉斯认为,一切事物都由躯体与灵魂(anima)构成。首先,顾名思义,“一切事物”既包括一切事,又包括一切物。与此一致的是思辨实在论者格兰特与哈曼。在《谢林之后的自然哲学》(PhilosophiesofNatureAfterSchelling)里,先验唯物论者格兰特沿袭柏拉图的思辨物理学(speculative physics),主张万事万物物理学(physics of the all)。在《工具的存在——海德格尔与客体的形而上学》(Tool-Being:HeideggerandtheMetaphysicsofObjects,1999)里,哈曼反对暗中贬抑(undermine)或过度张扬(overmine)客体的两种极端策略,主张没有唯物论的实在论(Bryant,et al,2011:40,82)。依据哈曼的“面向物的本体论”,万事皆客体,无论是邮箱、电磁辐射、弯曲的时空、英联邦国家,还是命题态度;万物,无论是物理的还是虚构的,只要在实践中对其他事物的存在产生作用,都是平等的客体(郝苑,等,2017:103)。据此,奥维德的《变形记》中“一切事物”可以细分为三种:物理的客体,如人、动物、植物和无生物;虚构的客体,如神、仙、妖和怪;非物理的事,如长出会泄密的芦苇的秘密。
依据毕达哥拉斯的说法,“一切事物”不仅具有作为物质的躯体,而且还具有作为精神的灵魂。其中,灵魂是不死的,或者说,没有死灭。有的只是变化,即灵魂从一个躯体转移到另一个躯体中:“灵魂一旦离开躯体,又有新的躯体接纳它,它又在新的躯体中继续存在”(奥维德,2008:319)。
一切事物只有变化,没有死灭。灵魂是流动的,时而到东,时而到西,它遇到躯体——不论是什么东西的躯体——只要它高兴,就进去寄居。它可以从牲畜的躯体,移到人的躯体里去,又从我们人的躯体移进牲畜的躯体,但是永不寂灭。灵魂就像在蜡上打印,第二次的形状和第一次的形状绝不相同,而且它也绝不长久保持同一形状,但是蜡本身还是那块蜡。(奥维德,2008:319)
依据毕达哥拉斯的教导,尽管灵魂“寄居的躯体老在变换”,可是它不仅不会死灭,而且还会保持同一性:“灵魂永远是同一个灵魂”。由于灵魂的同一性,转世的观念才存在。譬如,毕达哥拉斯自称他的前世是特洛亚战争时期潘托俄斯(Panthoüs)之子欧福耳玻斯(Euphorbus),与罗马人的先祖埃涅阿斯(Aeneas)同宗(奥维德,2008:319)。
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移说以万物有灵论(animism)为前提。万物有灵论与古罗马人信奉的原始多神论密切相关。古罗马人认为,每一件物体、每一种现象都有自己的神灵,所以任意的事或物都有自己特有的神灵,前者如庇护神和哭泣神,后者如门神和河神。起初是个别意义上的神,后来由于有了综合思维能力,才有普遍意义的神(王焕生,2006:7)。在文学研究中,与万物有灵论密切相关的是最重要的物叙事概念泛灵主义(pan-psychism)。思辨实在论哲学家哈曼支持泛灵主义,提出名叫思辨心理学(speculative psychology)的新哲学学科,致力于研究“宇宙的心理阶层(cosmic layers of psyche)”和“探寻蚯蚓、灰尘、军队、粉笔和石头的特殊心理实在性”(Harman,2005:213)。
无论是万物有灵论,还是泛灵主义,只要有灵,事物就有生命。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一切事物皆有生命。有生命的不只是人、神、仙、妖、怪、动物和植物,还有无生物。譬如,“大地就像生物一样,它有生命”(奥维德,2008:323)。对于物叙事而言,有重大意义的是深入研究生命本身,即生命本体论(the ontology of life)。依据萨克(E. Thacker)的书《生后》(AfterLife),生命本体论旨在把生命(life)与生物(the living)分开,使得“形而上学的置换”成为可能,在这种置换中,生命通过另一个形而上学术语——如时间、形式或心灵——来思考:“每一种生命本体论都根据生命之外的事物来思考生命……生命之外的事物最常见的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如时间和时间性、形式和因果关系或心灵和内在性”。萨克追溯这个主题,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经院哲学和神秘主义/否定神学,斯宾诺莎(B. Spinoza)和康德(I. Kant),直到今天,并且揭示了这种三重置换在当今哲学中是如何活跃的,即在过程哲学和德勒兹主义(Deleuzianism)中生命是时间,在生物政治学的思想中生命是形式,在后世俗的宗教哲学中生命是心灵。萨克考察了思辨实在论与生命本体论的关系,为“生机论关联(vitalist correlation)”提出理据:“生机论关联是未能保持思想与物体、自我与世界的分离性和不可分离性的关联主义双重必然性之一,并且并不基于‘生命’的某些本体化概念”。最后,萨克对“生命”持怀疑态度:“生命不仅是哲学以内的问题,而且还是哲学以外的问题”(Thacker,2010: x,254)。
有生就有死。在毕达哥拉斯看来,事物的生与死只是形体的变化,即“改变旧形,创造新形”。从生到死的变化也不例外。
万物的形状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大自然最爱翻新,最爱改变旧形,创造新形。请你们相信我,宇宙间一切都是不灭的,只有形状的改变,形状的翻新。所谓“生”就是和旧的状态不同的状态开始了;所谓“死”就是旧的状态停止了。虽然事物或许会由此处移往彼处,由彼处移到此处,但是万物的总和则始终不变。(奥维德,2008:321)
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叙事聚焦于变形,即形体的变化。形体的变化就是状况的变化,即叙述的事件,因为在叙事中“事件是状况的变化”(Schmid,2014:15)或者是“由行动者所引起或经历的从一种状况到另一种状况的转变”,即“过程”(巴尔,2003:219,249)。
由于变形是形体变化的过程,在阐释奥维德《变形记》的变形主题时“过程哲学”就显得比较重要,尤其是在涉及物叙事时。在《无标准:康德、怀特海、德勒兹和美学》(WithoutCriteria:Kant,Whitehead,Deleuze,andAesthetics)里,夏维洛(S. Shaviro)主张一种基于过程的方法,既包含泛灵主义,也包含生机论(vitalism)或万物有灵论。对于夏维洛来说,怀特海(A. N. Whitehead)关于理解(prehensions)与联结(nexus)的哲学提供了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的最佳结合。在《活力物质》(VibrantMatter,2010)里,本尼特(J. Bennett)主张从人际关系向诸物件(things)的转变,向一种“活力物质”的转变,活力物质跨越生物和无生物(non-living)、人体和非人体(159-183)。此外,在《皮尔斯与自然的宗教形而上学》(CharlesSandersPeirceandaReligiousMetaphysicsofNature)中,尼莫辛斯基(L. Niemoczynski)用所谓的“思辨自然主义(speculative naturalism)”加以论证,自然界有能力洞察其自身的具有无限生产力的“活力”地域,他将其视为创造自然的自然(natura naturans)。
(二)万物平等
与柏拉图(1963:119-120,125-126)的万物分等级的观念——即有灵魂的自动物体控制无灵魂的他动物体和尘世的俗物是上界的神物在下界的摹本——不同,毕达哥拉斯主张万物平等的理念。
依据毕达哥拉斯,万物就是“一切事物”,“不论是什么东西”。在这一众声狂欢的文本世界,文本不再有一个中心的发声源或意旨中心,所以,文本意义不再显现为一元统领格局(赵胜杰, 2020: 61)。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万物不仅包括经验现实中存在的生物(如人、动物和植物)和无生物(如大地、矿物和星辰),还包括非经验现实中存在的神、仙、妖和怪。因此,作为与万物有灵具有同等重要的物叙事观念,万物平等分为五种,即物与物的平等、物与人的平等、物同神、仙、妖和怪之间的平等、人与人的平等以及神、仙、妖、怪之间的平等。其中,前三种属于物叙事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
1.物与物的平等
毕达哥拉斯认为,一切事物都由躯体与灵魂构成。其中,灵魂是没有死灭,只有流动,即从一个躯体移到另一个躯体。因此,物与物的平等具有三层含义:第一,一切事物都有各自的躯体;第二,一切事物都有各自的灵魂;第三,一切事物都变形,即事物的灵魂从一个躯体转移到另一个躯体里去。可见,作为灵魂的居所,事物的躯体具有独立性,即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躯体,而作为躯体的主宰,灵魂则保持同一性,即灵魂永不寂灭,具有转移的神秘能力。
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物与物的平等体现于事物之间的变形,既包括不同种事物之间的变形,例如山猫的尿与对尤利乌斯(Ulysses,即奥德修斯)友好的阿尔喀诺俄斯(Alcinoüs)的船变成石头,也包括同一种事物的世代更替,例如老凤凰死后变成新凤凰。此外,事物之间的变形还存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两种事物相结合,变成一种新的事物。譬如,无金的河流与弥达斯(Midas)身上代表贪欲的金子相结合,变成含有金沙的河流。这个特例正好解释了哈曼的面向物的本体论的一个观点:物体——即河流与金子——结合时,它们就创造了新的物体:含有金沙的河流。哈曼以此支持先验形而上学,即实在性仅由物体构成,没有物体系列的“底(bottom)”。物体本身就是无限的幽深处(recess),任何他物都无法知道,不能接近(Harman,2005:201)。由于物体的无限内敛(withdrawal)或隐退(withdrawn),物与物的平等体现于一个物体独立于他物。
2.物与人的平等
尽管思辨实在论的哲学家有不同的侧重点或立场,可还是在三个方面达成共识:(1)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去除人类至上的观念,人和物处于同一本体地位;(2)物具有独立于人类的生命与活性;(3)在抵达物的过程中,人类要充分想象,超越理性,忘掉自我(唐伟胜,2017a:29)。可见,物与人的平等既是本体地位的同一,又是生命与活性的独立性。
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物与人的平等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其中,前两种形式与变形的主题有关。第一种形式是物变成人,即通过拟人的手法提升物的本体地位,即扬物。第二种形式是人变成物,即为了实现物与人的平等,通过拟物的手法,完全抹平人类的痕迹,属于梅亚苏和布雷西亚的消灭主义(eliminativism)(唐伟胜,2017a:31)。第三种形式是在生命方面物与人等值。譬如,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割头发就等于杀人头,即尼苏斯的头。又如,为了替两个兄弟报仇,忒斯提俄斯(Thestius)之女阿尔泰亚(Althaea)烧毁一段关系到她儿子的寿命的木头,就把墨勒阿革洛斯(Meleager)活活烧死。此外,还存在物与人合体的特殊情况,即存在“人兽杂糅的怪物”(柏拉图,1963:94),如半人半羊的怪物萨蒂尔(Satyr)和半人半马的怪物涅索斯(Nessus)。人与物融为一体的原因很多。或者是因为人与物的交配生育,例如半人半牛的怪物弥诺陶洛斯(Minotaurus)是国王弥诺斯的王后帕西淮(Pasiphae)与公牛交配生育的。或者是因为人与神的交配生育,例如北风神玻瑞阿斯(Boreas)强抢俄利提亚(Orithyia)为妻,生的两个儿子卡拉伊斯(Calaïs)与泽特斯(Zetes)在两颊开始长胡须的时候,两肩长出一对翅膀。或者是因为神的帮助,例如珀罗普斯(Pelops)被父亲肢解,后来天神复位四肢,并装上象牙肩。不难发现,物与人虽然融为一体,但是作为这个整体的部分,在本体地位方面仍然是同一的。
3.物同神、仙、妖和怪之间的平等
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物同神、仙、妖和怪之间的平等主要有四种体现:(1)神格化叙事,即物变成神、仙、妖和怪,例如船变成水上女仙;(2)物化叙事,即神、仙、妖和怪变成物,例如女水仙佩里墨勒(Perimele)变成岛屿;(3)神与物等同,例如朱诺把卡利斯托(Callisto)变成熊,朱庇特(Jupiter)把她和他们的儿子阿尔卡斯(Arcas)变成神,即大小熊星。
需要明确的是,上述的平等既有绝对的平等,又有相对的平等。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绝对平等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在命运——即毕达哥拉斯所说的神意——面前万物平等,即在不可更改的命运面前,万物都只能服从,即听天由命。即使是神也不例外,都受命运的主宰,像朱庇特说的一样。
绝对平等的第二层含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万事万物的躯体或形体都在变化;万事万物的灵魂都没有死灭,只有转移,而且保持同一。即使是抽象的时间也不例外。
宇宙间一切都无定形,一切都在交易,一切形象都是在变易中形成的。时间本身就像流水,不断流动;时间和流水都不能停止流动,而是像一浪推一浪,后浪推前浪,前浪又推前浪,时间也同样前催后拥,永远更新。过去存在过的,今天就不存在了;过去没有存在过的,今天即将到来。时间永远都在翻新。(奥维德,2008:319)
可见,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在本体地位方面,动物、植物和无生物(如石头和星辰)同人、神、仙、妖和怪完全一样。
不过,除了绝对平等,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还存在相对的平等。譬如,毕达哥拉斯认为,牲畜与人平等,所以他主张吃植物、动物的奶,但不主张杀动物,尤其是杀无害的动物,更不主张吃动物的血和肉。显然,在毕达哥拉斯眼里,植物没有动物的地位高。此外,神仙妖怪往往比人厉害,人又比动物厉害。即使属于同一类,也有等级之分和能力差异。
总之,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万事万物在宏观方面享有绝对的平等,在微观方面只享有相对的平等。对于物叙事研究而言,比较有意义的不是相对的平等,而是绝对的平等,更确切地说,主要是在本体地位方面的平等。
物的叙事
由于事物具有生命,事物本身不仅是被动——柏拉图称之为他动——的客体,而且还是能动——柏拉图(1963:119-120)称之为自动——的主体,结构主义叙事学称之为行动元(actant)(Herman,et al,2005:1)。与此一致的是拉图尔(B.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丰卫平,2019:48)。奥维德的《变形记》很好地演绎了这个理论。正是在人与非人(即事物)的行动者网络中,变形成为可能。其中,物叙事研究重点关注行动者是非人的情况。变形的施事能力或者源于物性,如震动的大地和喷发的火山,或者源于有生命的事物具有的神秘力量,如美狄亚(Medea)给伊阿宋(Iason)的魔草和埃涅阿斯从界树上折下的金枝,或者兼而有之,如水。毕达哥拉斯认为,水不仅自己会变形,而且还能改变其他东西的形状。譬如,在下弦末尾时阿达玛尼亚人(Athamanes)把水浇在木头上取火,齐科涅斯人(Cicones)居住区的河水能使人的五脏变成石头,甚至水碰到的东西都变成大理石,克拉提斯(Crathis)与苏巴里斯(Sybaris)的河可以将头发变成琥珀和黄金。有的水不仅能改变人的身体,还能改变人的头脑,譬如,萨尔玛喀斯(Salmacis)与埃塞俄比亚(Aethiopia)的湖水可以使人发疯,克里托里乌姆(Clitorium)的泉水可以使人戒酒,而林库斯(Lyncus)河水却像纯酒,斐纽斯(Pheneus)的水白天喝无害,晚上喝则有害。
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由于在变形过程中事物变化的性质不同,物叙事可分为灵化叙事和物化叙事。
(一)灵化叙事
其中,灵化叙事就是事物具有了灵魂的叙事。在灵化叙事中,事物成为行动元,不再是人叙事中的客体,而是行为的主体,即具有神秘的施事能力。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依据行为客体的差异,灵化叙事大致包含三种情况,即无生命的事物变成灵物、物变成人和物变成神。
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第一种灵化叙事指无生命的事物变成灵物的叙事。依据事物的性质,灵化叙事分为两类:(1)无生物变成生物,例如阿尔代阿(Ardea,意为“苍鹭”)城陷落于埃涅阿斯以后,变成有生命的鸟,又如罗穆路斯的枪变成有生命的树;(2)抽象的事变成有生命的物,例如家奴将主人弥达斯长驴耳朵的秘密埋进土里,长出会泄密的芦苇。
第二种灵化叙事就是人格化叙事,即关于物变成人的叙事。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总共有八个关于物变成人的故事,而且都与神有关。第一个故事与神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有关。与中国古代女娲抟土造人(袁珂,2016:23)和《创世纪》(2:7)里上帝造人相似(国际圣经协会,1999:8),普罗米修斯用土和“清冽的泉水”掺和起来,依照主宰一切的天神的形象,捏造人。第二个故事与正义女神忒弥斯(Themis)有关。在大洪水以后,只剩下普罗米修斯之子丢卡利翁(Deucalion)和他的妹妹、妻子皮拉(Pyrrha)。按照忒弥斯的意志,男人丢卡利翁扔出去的石头就变成男人,女人皮拉扔出去的石头就变成了女人。第三个故事与女神帕拉斯(Pallas)——即雅典娜(Athena)——有关。按照雅典娜的吩咐,卡德摩斯(Cadmus,闪语“东方”)将蛇牙种在地里,长出武士。第四个故事是第三个故事的延续。伊阿宋将卡德摩斯种剩的蛇牙种在地上,变出武士。第五个故事与神王朱庇特有关。依据埃阿科斯(Aeacus)讲述蚁人(Myrmidones)的故事,在克里特岛,由于大瘟疫人口锐减,埃阿科斯在梦中祈祷,在朱庇特的帮助下,蚂蚁(Myrmex)变人,即蚁人族。第六个故事与女神维纳斯有关。在维纳斯的帮助下,塞浦路斯人皮格马利翁(Pygmalion)的象牙姑娘雕像变成人,与他结为夫妻。第七个故事与酒神巴克科斯(Baccus)有关。从俄里翁(Orion)的两个女儿的骨灰中诞生两个青年,人称“科罗尼”(Coronas)。第八个故事与埃特鲁里亚的神塔格斯(Tages)有关。埃特鲁里亚的农夫在他的田里看见土块“很快就失去土形,变成了人形,张开新生的嘴宣告未来的命运”,“是第一个教埃特鲁里亚人预卜未来的人”。
第三种灵化叙事是神格化叙事,即关于物变成神、仙、妖或怪的叙事。譬如,神后朱诺(Juno)将埃涅阿斯的船变成痛恨希腊人、同情特洛亚人的水上女仙:
船体忽然变软,木头变成了肉体,弯弯的船头变成了头,船桨变成了手指和能游水的腿,原来是船舷,现在成了人腰,船底中心的龙骨变成了脊椎,缆绳变成了柔软的头发,帆杆变成了臂膀,颜色还是从前的蓝灰色。(奥维德,2008:304)
(二)物化叙事
除了前述的灵化叙事,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还存在物化叙事。物化叙事的哲学基础是符合梅亚苏和布雷西亚的消灭主义的概念物化。“物化”一词源于庄生梦蝶的故事。在中国哲学中存在一些对物化的误解,如西晋郭象的“人生幻化论”、东晋慧远的“精神不灭论”、唐代成玄英和宋代林希逸的“物理自然论”、宋代陈景元、褚伯秀和陈碧虚的“宇宙气化论”以及宋代刘辰翁和清代刘凤苞的“境界顿悟论”,又如近代崔大华、崔宜明的“逻辑实证论”、徐复观、陈鼓应的“艺术境界论”和张少康、刘绍谨的“艺术创作论”。最新研究表明,追溯本源才是理解物化的正确方法,即以庄解庄,还原历史。庄子的核心思想是“化”,即物化,源于《周易》的“易化”,其终极在“道”,其底蕴在“自然”。化“是非”于“无是非”,化“不平等”于“平等”,化“人为”于“自然”,化“彼我”于“齐一”(何光顺,2005:55-58)。
依据“化”前的主体不同,物化叙事分为三类:非人生物的物化叙事、人的物化叙事和神的物化叙事。其中,非人生物的物化叙事指有生命的动物或植物变成无生物的叙事。譬如,袭击珀琉斯(Peleus)羊群的狼被海神涅柔斯(Nereus)之女、海仙普萨玛忒(Psamathe)变成石头,又如蛇吞九只鸟,变成石头蛇。不过,就数量而言,第一种物化叙事并不多。因此,物化叙事主要指人的物化叙事与神的物化叙事。
人的物化叙事指人变成物(包括动物、植物和无生物)的叙事。譬如,风神之女阿尔库俄涅(Alcyone)为死于海上的丈夫刻宇克斯(Ceyx)殉情,恩爱夫妻变成翠鸟。与物变人提高物的本体地位正好相反,人变成物则贬低人的本体地位。从伦理的角度看,人变成物的原因各不相同。
第一个原因是罪有应得。罪有应得的第一种情况是人的罪过。譬如,由于皮格马利翁的孙女密耳拉(Myrrha)恋父喀倪剌斯(Cinyras),犯下不伦的罪行,变成从树干渗出来的树脂名叫木拉(Murra)的树。比布利斯(Byblis)因为爱上弟弟,变成清泉。普洛克涅(Procne)向强暴并残害其妹妹菲罗墨拉(Philomela)的丈夫忒柔斯(Tereus)复仇,杀死她与忒柔斯的儿子伊提斯(Itys)并让忒柔斯食其肉,两姐妹变成燕子和夜莺,而品性污秽的忒柔斯变成田凫。疯狂的女人们打死俄耳甫斯(Orpheus),变成橡树。罪有应得的第二种情况是人性的弱点。譬如,朱庇特之子墨丘利(Mercury)不仅将失信老人巴图斯(Battus)变成告密石,而且还将嫉妒的阿格劳洛斯(Aglauros)变成石像。阿波罗(Apollo)与狄安娜的母亲拉托娜(Latona)不仅将骄傲的尼俄柏(Niobe)变成白石,而且还将恶意的乡人变成青蛙。此外,众神将喜欢撒谎的刻尔科普斯人(Cercopian)变成猴子。
第二个原因是神的惩罚。受到神的惩罚,则是因为神的愤怒。有时,惹神怒是无心的,例如狄安娜将偷看她洗澡的阿克泰翁(Actaeon)变成麋鹿。又如,美少年库帕里素斯(Cyparissus)哀伤误杀的神鹿,变成柏树。再如,德律俄珀(Dryope)因为掐摘湖边罗陀树上的水仙罗提斯(Lotis)变的花而变成罗陀树。有时,得罪神却是存心的。譬如,弥倪阿斯(Minyas)的女儿们不信奉巴克科斯,变成黄昏飞翔的动物(Vespertiliones),即蝙蝠。吕底亚的织女阿拉克涅(Arachne)触怒弥涅尔瓦,受到惩罚,变蜘蛛。阿尔克墨涅(Alcmene)的侍女盖兰提斯(Galanthis)顶撞送子娘娘卢齐娜(Lucina),受到处罚,变成了黄鼠狼。皮厄鲁斯(Pierus)的九个女儿因为与九位文艺女神比赛失败,变成喜鹊。卡德摩斯夫妻招神的憎恶,变蛇。那尔喀索斯(Narcissus)拒绝女仙厄科(Eco,意为“回声”)的爱,变成水仙花。河神珀纽斯(Peneus)之女达佛涅(Daphne)拒绝日神阿波罗的初恋,变成月桂树:“虽然变成了木头,木头依然向后退缩不让他亲吻”(奥维德,2008:16)。水仙卡利克罗(Chariclo)之女俄库罗厄(Ocyrhoe,意为“急流”) 违背神的意志,擅自预言,变成母马。
第三个原因是神的恩典。譬如,海神忒提斯把殉情的埃萨科斯(Aesacus)变潜水鸟。海神涅普顿把阿基琉斯用皮绳勒死的儿子库克诺斯(Cycnus,希腊语“天鹅”)变成天鹅。赫卡柏(Hecuba)变成狗,那个地方名叫库诺塞玛(Cynossema,希腊语“犬墓”)。普里阿摩斯(Priamos)侄子、黎明女神奥罗拉(Aurora)之子门农(Memnon)变成鸟,名叫门农尼得斯(Memnonides)。最特别的是,基尔克(Circe)——她曾把尤利乌斯的伙伴们变成猪(荷马,2015:186)——用毒草汁和咒语,把格劳科斯(Glaucus)暗恋的斯库拉(Scylla)先变成狗,后变成岩石。
此外,与物变成神的灵化叙事正好相反,神的物化叙事指神变成物。一般来讲,神变成物都是主动的。譬如,为了得到腓尼基国王阿革诺尔(Agenor)之女欧罗巴(Europa),朱庇特把自己变成公牛。又如,朱庇特化作金雨,和达那厄(Dana⊇)生珀耳修斯(Perseus)。再如,为了躲避珀琉斯的求爱,女海神特提斯(Thetis)施展法术,把自己变成鸟、树和雌虎。不过,有时神变成物却是被动的。譬如,女水仙变成厄齐那德斯(Echinadas)岛屿是因为希腊西北部大河阿刻罗俄斯(Achelous)的河神。
总之,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物化叙事的本质就是将人或神“化”为“物”,用贬低人或神的本体地位的方式,实践万物平等的观念。
(三)混杂型物叙事
前述的灵化叙事和物化叙事都属于简单型变易的故事,即推动叙事进程的力量是一次变易。此外,还存在一些复杂的情况,推动叙事进程的力量不只是一次变易,甚或不只是单向的变易,姑且称之为混杂型物叙事。
混杂型物叙事之所以复杂,首先是因为在形体或躯体方面主体变化多端。譬如,海神普洛透斯(Proteus)经常变换形体:有时是青年的人形,有时是动物,如狮子、野猪、蛇和公牛,有时是无生物,如石头、树、流成河的水或火。形体的变化是双向的或可逆的,即变化成其他形体以后,又恢复原形。譬如,厄律西克同(Erysichthon)因为砍倒五谷女神克瑞斯(Ceres)的树木(女仙),受到饥饿女神的惩罚,吃自己的肉,靠卖女为生,他的女儿在海神的帮助下变成男渔夫、母马、鸟、母牛或者鹿,才得以脱身,最后恢复女身。有的是在物化叙事中掺杂性别变化的故事。譬如在海神涅普顿(Neptune)的帮助下,被海神强暴的女子开纽斯(Caenis)变成英勇的男人,死后变成长黄翅膀的鸟。
第二,变易的缘由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自身的本领,譬如,卡吕冬(Calydonian)的河神阿刻罗俄斯会变成蛇和牛,而且还由于同海格立斯(Hercules)角力,失去一只角。有的则是借助于神。譬如,女仙基尔克用毒酒把尤利乌斯的伙伴们——如叙事者玛卡瑞乌斯(Macareus)——变成猪,不过在墨丘利给的魔吕(Moly)的帮助下,尤利乌斯制服基尔克,逼基尔克将伙伴们变回人形。类似的是,由于朱诺的愤怒,朱庇特把伊娥(Io)变成白牛,在朱诺平息怒气以后,在朱庇特的帮助下伊娥又恢复人形。有的变化是由于事物的神秘力量。譬如,忒拜先知特瑞西阿斯(Tiresias)因为用手杖去打在绿树林里交配的两条大蛇而变成女人,之后第八年又因为用手杖打那两条蛇变回男人。
不过,最复杂的是,在同一个故事中,不同的主体变成不同的物体。譬如,由于只爱女仙卡南斯(Canens,意为“歌唱”),拒绝女仙基尔克的爱,萨图尔努斯之子皮库斯(Picus)被基尔克施法,变成啄木鸟,而卡南斯坐化成清风。
结 语
综上所述,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变形是叙事的主题。不过,变形的依据不是卢克莱修的《物性论》,而是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移说。在叙述一系列变形故事的框架叙事中,除了传统的人叙事,还存在物叙事。其中,物叙事分为灵化叙事——主要包括人格化叙事和神格化叙事——和物化叙事(或拟物叙事)。有时,还存复杂型叙事,如灵化叙事与物化叙事掺杂在一起。
注释:
①关于奥维德《变形记》中的专名,外文出自Ovidius(2004 & 2005),中译依据杨周翰译本,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