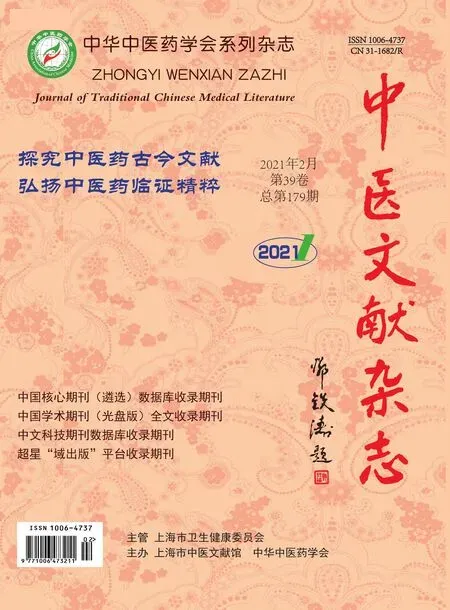古代中医药器具发展史述要*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100029) 林鹏妹 张弓也 薛含丽 段晓华
中医药器具的起源与人类的诞生相随,从原始社会简陋的石块到如今层出不穷的器械,中医药器具见证了社会生产力与中医药学的发展。中医药器具作为一种工具,不仅是中医药发展的产物,也是促进中医药发展的动力。对于中医药历史研究来说,中医药器具相比文献资料等其他形式的中医药信息载体更具直观性、可证性和可靠性。结合时代背景对中医药器具进行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影响中医药器具发展的因素,从而促进中医药器具的发展,实现中医药器具与中医药学互促互进的效果。
诊断类器具
中医四诊,即望、闻、问、切,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依赖自身感官发展起来的诊断方式。与西医相比,中医对外在的诊断类器具依赖较小,故而在近现代以前,中医诊断类器具发展较慢。出土文物及文献资料中诊断类器具亦较少,多为辅助诊断的器具。如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所藏隋唐时期的瓷质脉枕。此物枕面椭圆,两头微翘,表面施以青绿色釉[1]。到了近现代,为使诊断信息客观化,中医以自身理论为基础,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创制了具备定量、定性功能的诊断器具,如脉诊仪[2]、舌诊仪等。
治疗类器具
1.针灸科

2.外科
外科的发展起源同样较早。砭石即手术刀的前身。如1966年长沙接驾岭西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刀[9],1973年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第14号墓出土的石质的砭镰[4]。冶炼技术出现后,锋利的金属刀具逐渐取代了其他材质的刀具。1983年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的周代的青铜刀具,既可用于日常劳作,又可用于体表手术[4]。《周礼·天官》中将医生分为四类,即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其中疡医即广义上的外科医生,可见此时外科已成为独立的分科[10]。战乱年代大量的临床实践促进了外科技术的提高以及相应器具的产生,外科的发展尤为迅速。《五十二病方》中关于外科疾病的论述最多,记载了很多相关器具,包括治疗腹股沟斜疝的“壶卢”“疝气罩”“疝气带”,使用方法是以汤药置坛中,上盖带孔草席,对痔疮部位进行熏蒸[11],还有用于治疗疾病的“探针”,可知当时外科器具已取得一定发展。从《黄帝内经》对人体解剖结构有了详细描述可以看出,当时的外科学已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汉代华佗创制了麻沸散,为外科手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首都博物馆藏有汉代青铜镊一对,其柄端与传统药勺相似[1],制作精巧。晋末出现了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该书重点论述痈疽疮疖等外伤的诊断、治疗及预后。《诸病源候论》中关于开放性骨折的清创手术、分层缝合、异物清除、血管结扎等的记载,都体现了当时外科的发展水平。其中记载的“肠吻合术”“割治眼息肉术”“拔牙术”等复杂手术,没有精巧的外科器具是无法实现的。此外,危急重症方面的治疗亦有很大发展。相关记载有孙思邈以桑皮细线缝合阴囊撕裂,用竹筒吸取药汁进行灌肠治疗垂危之疳湿痢,用葱管导尿治疗尿闭。《世医得效方》《永类钤方》中都有关于外科器具的详细记载,如针、刀、剪、钳等。黑龙江流域博物馆藏有一组辽金时期的外科手术器具,包括刮刀、镊子、手术刀及起子等,从中可见当时的外科手术水平已相当成熟。明清时期,汪机、王肯堂、陈实功等医家进一步丰富了外科理论。《外科正宗》中记载了陈氏创用的多种外科手术方法和器具,其中的鼻息肉切除术,至今仍在临床袭用[10]。另外,随着“西医东渐”,外科器具不断细化。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藏有中医外科器械33件套,从中可窥见当时外科医药器具的发展[8]。
3.骨伤科
春秋战国时期,频繁的战乱促进了骨伤科的发展。《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脉死候》《阴阳十一脉灸经》中的记载反映了当时对开放性骨折、肩关节脱位等骨伤科疾病已有一定认识。《黄帝内经》中记载的用棉布浸药酒熨帖治疗寒痹的方法,是中医骨伤科治疗的雏形。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论述了开放性创口感染毒气的学说,强调了早期处理伤口的重要性。同时,该书推崇用小夹板的局部固定法和手法整复疗法,是最早记载用竹片固定治疗骨折的著作[12]。唐代蔺道人的《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是我国第一部骨伤科专著。该书系统总结了骨折的诊断治疗方法,为骨伤科的辨证论治奠定了基础。其中涉及大量的正骨器具,如整骨复位用的椅子、绢垫、细布以及复位后局部固定用的杉木片等。宋金元时期改医学为十三科,十三科中就有疮肿科与正骨金镟科,这标志着骨科与伤科的分离。元代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创用了悬吊复位法,该法利用软绳、大桑皮、杉树皮等器具辅助脊柱骨折的治疗。明清时期,骨伤科正式独立分科,医家们对骨伤科用具进行了改良和革新,许多用具至今仍在临床应用。吴谦的《医宗金鉴》总结了清代以前的正骨经验,并对医疗器具进行专节记述,涉及裹帘、振梃、披肩、攀索、叠砖等,并详细介绍了这些器具的使用方法及作用。书中还记载了运用攀索叠砖法、腰部垫枕法整复腰椎骨折脱位[12]。近现代,在总结中西医治疗骨伤疾病优缺点的基础上,骨伤科以缩短恢复时间和提高治疗效果为目的,不断改进骨伤科手术方法及器具。
4.五官科
中医眼科的理论基础早在《黄帝内经》时期就已奠定。从出土文物中可以窥见当时眼科疾病的治疗方法,如首都博物馆所藏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洗眼杯”[8],江苏江阴一明代墓中出土的与眼科玻璃洗壶相似的瓷淋洗壶[13]。眼科手术的历史同样相当悠久,早在《晋书》中就有医官为皇帝割去眼部瘤疾的记载。《外台秘要》中记载了白内障的手术治疗技术,即金针拨障术。《张氏医通》《目经大成》等著作对金针拨障术进行了详细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现代的针拨套出术,该技术相比国外的晶体摘除术更为优越[14]。《审视瑶函》中绘有眼科手术器械图31种,包括金针、毫针、烙铁、钩等。明清时期的眼科著作多附有眼科手术器械图,如《目科正宗》《眼科锦囊》《眼科要略》等。除手术器械外,还有搭头枕、遮风镜、滴水器、熏眼器等眼科医疗器械[15]。此外,我国在元代已用鱼脑骨作原料制成透明片,用黑色丝带将其系于眼睛之前,称为“鬼眼睛”,其结构及功效都与现代眼镜相似[14]。口腔科方面,随着口腔卫生意识逐渐提高,早在东汉就有用杨枝制成牙刷,以蘸药刷齿的记载[14]。“杨枝揩齿法”和“手指揩齿法”等口腔清洁法自此开始流行,口腔清洁用具也应运而生。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藏有唐代的“牙刷柄”[8],宋代著作《养生类纂》有植毛牙刷的记载[14]。关于口腔疾病的治疗,早在《金匮要略》中就记载了以雄黄治疗龋齿的“小儿疳虫蚀齿方”,远远早于1836年美国人斯普纳的砷剂失活牙髓技术[14]的记载。隋唐时期《新修本草》中关于汞合金牙齿填充术的记载,是世界上汞合金补牙的最早记载,较英国人Bell使用汞合金要早1200年[14]。《外台秘要》中载有以雄黄末塞牙孔口,再用烙铁烙之以治疗龋齿的方法。宋代《圣济总录》有治牙齿摇落,复安令著的坚齿散方,是我国已知最早的关于植牙处方及手术的记载,较国外最早记载的法国人福夏尔制作假牙和镶牙要早600年[14]。明代《本草纲目》记载有醋调砒霜,待干取粟粒大,以绵裹安齿缝内,第二天取出的医疗技术[14]。耳鼻喉科方面,关于耳聋的治疗,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首先记载了外用磁石,通过借助天然磁石的微弱磁场来治疗耳聋的办法,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代还有将磁石制成盆、枕类保健用品的记载。中医蒸熏术可以说是现代耳鼻喉科雾化吸入疗法的雏形。《太平圣惠方》中就记载了蒸熏蛇床子治疗喉痹肿痛的方法。江苏江阴明代墓出土的瓷质冰裂纹熏药罐,罐口直径约4 cm,周围有四个直径约1 cm的小孔,可能当作放置熏鼻醒脑开窍药的器具使用[13]。《儒门事亲》中记载了以筷子、针钩、纸卷等取咽中铜钱的案例。当然,相比之下,现代五官科给药器具已变得更为轻便、可控及易保存。
炮制类器具
在原始社会时期恶劣的居住环境下,人类容易感受风寒湿邪及外伤疾病。在长期的饮食生活中,人们发现了酒有驱寒除湿、舒筋活络的功效。《素问·汤液醪醴论》篇中记载“上古圣人作汤液醪醴”,《五十二病方》中药方亦多为药酒,这些记载可与出土文物中的大量酒器互相印证。早期人类已发现药材通过煎煮可获得更好疗效。青海柳湾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鸮面罐[8],与现今柳湾所用的煎药砂锅十分相似。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臼、玉杵,是早期的研药器具[4]。“方书鼻祖”《伤寒杂病论》的成书是药物学发展成熟的标志,炮制器具的发展与药物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在近代考古中,曾出土了一些战国及秦汉时期制药、称药及收藏药物的工具,如“药臼”“药杵”“药釜”等[8],是当时“治末吞服”制备药物的印证。1940年淮南出土了楚汉之间的合药罐[4]。1925年亳州出土了汉末的陶制药罐和陶勺。南京大学藏有汉代的铜制药桶[9]。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所藏的汉代的“丸”字双口药壶,壶颈外壁有一阴刻“丸”字,表明它是贮藏丸药的容器[8]。1953年长沙左公山战国墓葬中出土的称量药物的药衡,包括1个天平秤和大小9个砝码,这些砝码最重者不过4两,余者只有数钱或数分重。另外,山东省巨野县文化馆所藏的秦汉时期的“丹鼎”,出土时内有丹药250多粒,及朱砂、蚌壳等[8],是炼丹术发展的确证。首都博物馆藏有晋代药碾一件,槽中置有灰陶质的碾轮及碾钵。隋唐时期,陶瓷技术进一步发展,促进了器具的多样化及美观化。如陕西医史博物馆所藏的“白瓷药瓶”“黑釉瓷药瓶”[8]。北宋政府重视医学,本草学的发展最为瞩目,从出土的中医药炮制器具亦能得到印证。如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所藏的“采芝玉铲”“龙泉窖乳钵”“研钵”“‘内府’黑釉大药坛”“炼丹炉”等[8],首都博物馆所藏的宋代青铜药臼[1]。明清时期,中药炮制器具的用途不断丰富。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一系列“太医院用具”,包括“铁药碾”“药勺”“药筛”,还有大量存储药物的“药柜”等[8]。在现代,中医药炮制器具实现了飞跃发展,诞生了煎药机、制丸机、压片机等现代炮制器具,中医药炮制的自动化使得炮制效率大大提高。
教育类器具
教育类器具与医学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四川省绵阳市博物馆馆藏的西汉经络漆木人[8],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体经脉模型实物件。其体表镌有线条清晰并涂以红漆的经络循行径路共10条,与《足臂十一脉灸经》的“十一脉系统”以及《黄帝内经》的“十二脉系统”在数量、长度及循行等方面皆有不同,由此可窥见经络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9]。同时,我国早期的医学教育亦初见端倪。官办医学教育兴起于魏晋时期,在此之前,医学教育主要以家传和师承为主。中央医学教育一般设在太医院内,隋唐时期开始将医学教育推向地方。唐代设医学博士和助教,负责地方医学教育。宋金元时期,统治者重视医学并有不少创举,包括医学教育器具。宋天圣年间王惟一创铸的针灸铜人兼具了教育和考核的作用。《康熙大兴县志·卷一·舆地篇古迹考》载:“古铜人,太医院内,相传海中潮涌出者,虚中注水,关窍毕通,用以考验针灸,古色苍碧,其光莹然□目。”[16]该针灸铜人为青铜材质,相传是王惟一以禁军的身高体型为标准而设计的。为保持完整性,铜人体腔内装有木雕的五脏六腑。铜人被设计为前后两半,方便拆卸和组装。会试时,会试者事先将水银注入铜人体内,再在铜人体表涂上黄蜡以覆盖穴位。应试者如果扎中了穴位,水银就会从中流出,体现了“针入汞出”设计之法的巧妙[17]。其后该铜人经战乱颠簸、风吹日晒,已不能“会目案形”。明英宗下令仿天圣铜人重修一尊针灸铜人以供医用,即后世所称的“正统铜人”。《光绪顺天府志·卷七·京师志七衙署》载:“药王庙神像前铜人像,始作于宋天圣时,元至元间修之,明英宗时又修之,三皇庙内有针灸经石刻,明时重摹上石者。”[18]有学者考证,因八国联军战乱,“正统铜人”现流落于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中。正统铜人是《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文本的权威解释,对于针灸史和针灸教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9]。此外,1965年至1971年间,在北京拆除明代北京城墙的考古工作中,陆续发现了宋天圣《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石五方[6]。
其他类器具
医疗制度的发展从其附属产物亦可窥见。1966年在河北满城发掘了两座西汉墓(中山王刘胜及其妻子之墓),出土了一系列医药器具。其中有“医工”铜盆一件,其口沿及外壁共有三处刻有“医工”二字,该铜盆可能用于蒸药或制剂[8]。早期医药器具具有生活劳作和医疗救治的两用性。医药专用器具的诞生,标志着医者地位的提高和医学独立发展的开始。医疗制度的不断完善,使得医事活动得到了规范,临床疗效亦得到了保障。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汉太医丞印[8],可和《后汉书》所载的郭玉“和帝时为太医丞”互相印证。明前期政府重视地方医疗,统治者在全国设立“医学”,上至中央,下至州县,各地博物馆均藏有出土的“医学记”印[8]。医药卫生意识的提高,可从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藏有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唾壶”、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藏有的“青瓷骨灰罐”、南京博物院藏有的“香薰”等器具上得到印证[8]。战乱时期容易出现流行病,而香薰可用于防疫。首都博物馆藏有一晋代器物,其器身呈锥把形,口小腹大,腹上部有一桃形口,疑为兽用灌药器[1],此物亦可窥见当时兽医行业的发展。另外,以银制成的兼有试毒作用的医药器具,在清代宫廷中被大量使用。还有体现特殊功用的医药器具,如用象征封建权贵的象牙、玛瑙、檀香等制成的医药器具。
限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早期中医药器具与生活用具尚未有明确区分,且外形较为粗糙简单,用途亦较为单一。此外,早期医学虽已有一定发展,但疗效仍依托于神秘力量。如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的一件刻有雨师操龙形象的陶砭[13],医药器具上的鸟、龙等图腾就是原始崇拜的体现。另外,考古发掘中存在针具与龟甲一同出土的现象,这也是早期巫医不分的体现。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医学的发展,医药器具的外形及材质不断变化,治疗范围亦不断扩大。材质不同,疗效不同。《素问·病能论》载:“有颈痈者,或石治之,或针灸治之,而皆已,其真安在?岐伯曰:此同名异等者也,夫痈气之息者,宜以针开除去之。夫气盛血聚者,宜石而泻之。此所谓同病异治也。”外形不同,疗效不同。《灵枢·官针篇》载:“九针之宜,各有所为,长短大小,各有所施,不得其用,病弗能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自动化不断加强,医药器具在现代医疗中担当的责任也越来越大。中医药器具的发展应以服务于中医药为宗旨,以提高临床疗效为最终目的。如何在不丢失自身特色的同时,让现代科技为中医药服务,是当代中医药器具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