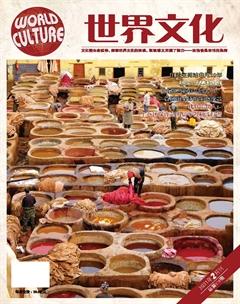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思考
门赐双 门薇薇
《最后的诗篇》是泰戈尔晚年68岁时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情节简单,没有像其前期创作的《戈拉》等小说那样为我们描绘一幅广阔的社会画面和曲折复杂的故事,而是洋溢着诗情画意和对自然的描绘。整部小说语言优雅且运用了大量的比喻、拟人等修辞,充满浪漫主义的诗意气息。这与泰戈尔诗人的气质是分不开的,同时也与当时的文学发展环境密切相关。
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受到英国及其所代表的西方社会的影响。20世纪初正是现代主义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印度文学的革新与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股潮流的影响。一批激进的文学改革者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采取全盘吸收的态度,完全抛弃了自身的文学传统。他们的小说及诗歌创作不再遵循传统小说和诗歌中注重情节、格律等的创作手法,大多语言艰涩,内容混乱,意义不明,并且充斥着对两性情欲的描写。泰戈尔作为印度传统文学的代表性人物,自然也受到了这批激进作家的攻击。
泰戈尔在此后与这批激进作家的交锋中,深化和完善了自己后期的诗学理论。他认为“所谓创新,是把能够启迪人们追求高尚的理想、具有远久价值的真实事物用最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创新与传统并不矛盾,不能割裂开来”。在肯定印度文学传统的同时,泰戈尔对西方文学的传入和影响并不完全排斥,但对西方现代派诗歌及其对孟加拉文学的影响持否定态度,对这种不再重视诗歌格律、语言晦涩的文学潮流是加以批判的,特别是孟加拉文学正处于近代化的发展阶段,这股潮流无异于一种畸形的引导,对文学发展毫无裨益。

在几次论战后,泰戈尔将自己的发言和观点整理成两篇文论——《文学的实质》和《文学的革新》,不料却引起进一步的论战,反对和赞成之声此起彼伏。正当双方的争论由文学领域渐渐转移到对泰戈尔本人的攻击,争辩的性质逐渐发生变化时,《最后的诗篇》发表了。这是泰戈尔晚年封笔数年后再次也是最后一次创作的长篇小说,却凭借其浪漫的风格、奔放热烈的情感表达以及新颖的形式,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
小说《最后的诗篇》是在全面接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激进派同其反对派的争论中诞生的,并且得到了双方的认可。连素有“印度劳伦斯”之称、对泰戈尔进行过猛烈攻击的诗人布塔戴瓦·巴苏也暗自承认:“《最后的诗篇》似乎是泰戈尔专门为向我们‘示范而写的,它的每一章节都是一首无与伦比的散文诗,这正是我们想写而又不知如何去写的。”印度的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浪漫主义风格在《最后的诗篇》中得到了完美結合,在人物形象刻画、小说中的诗歌形式和情感表达等方面,都体现出这位年近古稀的作家的不断进步和创新,为孟加拉文学的发展指引着方向,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人物刻画方面,小说虽然故事情节简单,涉及的主要人物也不多,但人物塑造并不单薄,主要运用强烈的对比来体现人物身上传统与现代相矛盾的一面。男主人公阿米德因为有过7年留学英国的经历,并且自身颇有才华,便对孟加拉文学大加讽刺,对泰戈尔更是直言:“一个诗人恬不知耻地活到六七十岁,那他只能降低身价,作践自己,最后只得处处模仿别人,毁了自己的创作风格……读者们有责任不让这些老朽的诗人活下去。”在这里泰戈尔也巧妙地将自己写入作品,成为阿米德大加议论和抨击的对象,并将这种处理延续到之后阿米德的恋爱过程中,成为故事发展的一条线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其实也是泰戈尔对当时以阿米德这种人为代表的激进派的回应与讽刺,表明自己反对这种全盘西化的立场。
接着,当阿米德与家庭女教师兰娃的恋情被曝光后,在传统门第阶级观念的束缚下,阿米德瞬间变得畏手畏脚起来,在收到电报得知妹妹们要来之后,阿米德不再像往日那样自信镇定,“面带忧色”,“东拉西扯地竭力想掩饰自己内心的阢陧不安”。而当妹妹们同兰娃一家起冲突时,“阿米德的舌头竟然不好使了,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泰戈尔通过对笔下这些自诩为追求西方先进事物、极力想摆脱属于自身的传统却窘态百出的形象的描绘,将现实中年轻激进派的模样呈现出来。泰戈尔认为“许多青年在文学中采取廉价的实践,因为这种实践简单。同时,他们以冒险主义进行层出不穷、别出心裁的创新,由此获得了一片喝彩声”。
在小说的诗歌形式方面,《最后的诗篇》和泰戈尔的其他小说一样,都有着一种共同的诗化风格,显示着作家浓厚的诗人气质。“浓郁的诗情几乎贯穿泰戈尔的每部作品。情景交融的描绘,以情托物的想象,诗情画意的渲染,形象比拟的手法,几乎见于他的每部作品。”在《最后的诗篇》中,与这股诗化小说气质相辅相成的是大量的诗歌创作和运用,几乎每一章节都有诗歌的插入,一些带有议论的性质,而更多则是抒情性的。
关于诗歌的形式,泰戈尔同样借主人公阿米德之口说明了激进派的观点:“诗坛霸主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末日已经来临……我们希望新的‘诗会主席的作品线条能挺拔笔直,像箭矢一样,像矛头一样,像尖刺一样——不要像花朵一样软绵绵,而要像电流一样,像神经痛一样……从今起,抛掉那令人伤脑筋的毫无意义的韵律吧!把你们的心从韵律中劫走。”可见,年轻的激进派们主张完全抛弃诗歌的格律,追求极端的情感体验,对传统中自然、草木、和谐的因素也不再注重,完全偏向西方现代主义中的异化。
泰戈尔对西方现代诗歌的态度在其文论《现代诗歌》中也有所体现。在与以李白为例的中国文学的比较中,泰戈尔是如此评价英国现代诗歌的:“英国诗人的诗歌显得不够淳朴自然,而且沾有污泥。他们似乎用自己的胳膊推撞着读者。这样的诗人看到的和表达的那个世界,犹如断壁残垣,满是尘埃。他们的心今天是不健康的,摇摆不定的。”显然现代诗歌中经常出现的怪异、艰涩、变态等元素,与泰戈尔所崇尚的传统意义的自然纯朴之美是相左的,所以招致泰戈尔的反感和否定。不过,泰戈尔并不是顽固坚守传统格律的作家,虽然对现代诗歌所表达的精神内涵加以批判,但在诗歌形式和格律上有着自己的观点。在他创作生涯的后期,也尝试过散文诗和带有现代色彩的自由体诗的创作。最为世人所知晓,同时也是让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殊荣的《吉檀迦利》,是诗人用英语且以散文形式所译,因为经过语言的转换,在押韵、格律等方面都有所舍弃。泰戈尔认为无论形式如何——散文也好,诗歌也好,散文诗也好,都是为了以其独有的形式特点去传达“美”的感受,“迄今为止,诗的形式是一成不变的,缺少美的享受;自由体诗不仅改变了诗的形式,而且也改变了我们对诗的概念,甚至改变了其内容”。
在《最后的诗篇》中,泰戈尔的诗歌创作就是采用自由体诗歌的形式。这种新的形式对于泰戈尔以后的诗歌创作以及对于青年诗人克服他们的“现代主义”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以看出,泰戈爾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在对待诗歌发展的态度上是非常宽容和灵活的,不拘泥于一格,而是始终跟随和把握诗歌的本质,将目光聚焦在美的表达上。
最后,在情感表达上,极具泰戈尔对“一”与“多”以及“和谐”理念的见解。印度传统文学历来注重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梨俱吠陀》《沙恭达罗》等文学经典中都有将自然作为审美对象,对草、木、水、云等丰富的自然景象的描绘。泰戈尔也不例外,在他看来,“自然是美的”这一说法没有丝毫问题,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因为我们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它。在《最后的诗篇》中,泰戈尔将主人公的相遇、相恋以及分离的场所安排在了希朗山,因此就有了大量对自然景色的描写,并且随着主人公恋爱中的情感变化而展现出不同的景色面貌。一开始,阿米德刚刚抵达希朗山,独自游玩几天后感觉这里和在城中一样无聊极了。而当他与兰娃邂逅并被其吸引后,“这一次不知怎么的,希朗山竟然把阿米德给深深地吸引住了”。在二人的热恋中,情与景完美合一:“树林茂密,浓荫翳日……半道上,一股涓涓细泉不愿顺着小路流去,它独辟蹊径,铺下了一颗颗鹅卵石。……恰好那儿有一个较深的小潭,潴留下一些水。那水宛如站在绿色帷幕下的一位罩着面纱的少女,羞羞答答,不肯出来。”这段即描写二人在山林中散步时,密林将他们包围,在一片宁静中衬托出兰娃的娇羞,两人彼此的情意都在不言中借山水得以倾诉,融为一体。
另一方面,泰戈尔在这部小说中没有了之前通常所展现的广阔社会环境,而是集中笔墨对阿米德和兰娃的恋情进行描写,不再牵扯过多的社会因素,如殖民统治、种姓制度、封建陋习等。小说回归到纯粹的爱情主题,多以对话的形式,将阿米德与兰娃在恋爱过程中彼此的细腻心理表达出来。
在小说结局的处理上,则又体现出泰戈尔独特的思想。阿米德与兰娃的恋情可谓一波三折,虽然两人相互爱慕,但敏锐的兰娃逐渐察觉到阿米德在恋爱中情感的异样,“你是个不热衷于成家立业的人,你只是在为满足爱的渴望而四处漫游,因而你往往以文学自娱。也正是这个原因才促使你来到我的身边……”直到最后,阿米德妹妹们赶到,直接的干预使二人的恋情走向了终点。可以说这是两个还不太成熟的青年人进行的一场恋爱的尝试,充满了年轻人的热情和活力,简单到只有两个人的世界。最后二人各自结婚,但泰戈尔借阿米德之口,将这种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从另一种角度进行解释:“爱情在空间里广泛存在着,它给予人们心灵的慰藉。当它与日常的一切相连时,便能给予人们以结合即同居的机会。慰藉与同居这两者我都需要。”阿米德与兰娃彼此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之前不愉快的分离而走向破裂和敌对,甚至最后互赠诗篇,表达了对过往的珍视和付出真情的肯定。
对于结尾的这种处理,体现出泰戈尔思想中的“一”与“多”及其相互关系。 “难道爱情可以按照故事书中的固定模式浇铸出来?不,绝对不行!我要亲手铸造自己的爱情故事。”在“一”与“多”的辩证统一关系中,阿米德并没有失去任何一个方面,他自身的激情、理想状态下的爱,作为“多”依旧广泛存在着;而他自己的选择、他自己的“创造”,又使他获得了属于自己的那个“一”。自身所得到的“一”受惠于“多”,“多”通过个人的“一”而得到具体的展现,由此达到“和谐”的状态。对于这种爱、这种状态,阿米德也在最后感叹道:“多好哇,我的兰娃!多好哇,我的凯蒂(阿米德妻子)!我阿米德真是太幸福了!”在泰戈尔笔下,这三人的关系超脱了一般世俗所关注的两性之间的情爱,在和谐中共存,也带上了属于泰戈尔自身独特的思想色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激进派青年人热衷于感官刺激的情欲描写的一种回应。
古稀之年的泰戈尔并没有停止自身的创新步伐。在西方文艺思潮的冲击与影响下,本身就有着深厚传统文学素养的他也在不断地自我突破,以其亲身实践,在东西碰撞的潮流中,做出自己对文学发展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