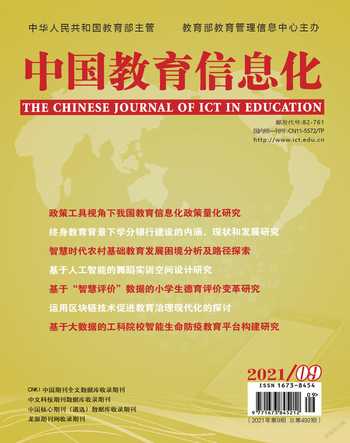教育大数据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
杨勇 段超 李凯琦 易雪玲
摘 要:文章立足于教育大数据这一基本前提,认为教育大数据的发展能够在教育研究层面上推动教育学的科学化从“思辨”走向“实证”,在社会层面上营造一种数字化生存与数字公民教育的文化新景象,在教育均衡方面为政府部门的决策与管理提供科学支撑,在教育经济方面推动教育精准扶贫业务的流程再造。
关键词:教育大数据;决策与管理;数字化;教育公平
中图分类号:G40-0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21)09-0040-04
一、引言
教育大数据研究与应用已经成为一项重大教育议题。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出“探索发挥大数据对变革教育方式、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支撑作用”。[1]基于教育大数据的教育科学发展、数字公民培养、管理决策制定、精准扶贫开展,极大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不仅在提升教育质量、更新文化理念、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社会公平等方面产生巨大价值,还对实现21世纪人类文明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可以预见,随着教育信息化从“信息技术教学应用”走向“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教育大数据的研究与实践将在这一过程中迎来大爆发。[2]
二、教育大数据:信息时代助力教育科学化的新基点
“从结绳记事、口耳相传,到之后的印刷媒体,再到如今的计算机网络与多媒体互动,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便利,也带来了各种可能。”[3] 生动多姿的人类发展历史展示出了技术革命所引发的生产力跃迁,不仅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还推动社会历史进程迈向新的发展阶段。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其变革与发展也相应遵循着这一基本的历史规律与逻辑线索,即教育生产中每一个新工具的出现都会带动原有教育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改变,从而推动教育结构的整体变革与转型发展。[4]因而当人类文明演进到21世纪之后,伴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以数据挖掘与学习分析为核心的教育大数据在信息时代先声夺人,在将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纪元的同时,还为教育学的科学发展与实践创新带来了新机遇。
在理论层面上,教育大数据的应用与推广,能够推动教育学的科学化发展进程从“思辨”走向“实证”,使其在成为一门“硬”科学道路上向前迈进一大步。具体而言,将以实验、量化为标识的大数据理念引入教育领域,以教育大数据的挖掘与分析为基点开展教育研究的实际工作,除了能够使教育科研人员更为清晰地理解教育研究的对象之外,还可以有效为整个研究过程提供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从而为教育学自身的理论构建奠定坚实的科学基础,使教育学摆脱過去学科发展中哲学思辨与经验总结两头强而科学理论构建中间弱的状态,并在广袤的科学之林中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理论气质与学科形象,最终彻底摆脱艾伦·拉格曼在《一门琢磨不定的科学:困扰不断的教育研究的历史》中描述的“后娘养的孩子”之角色定位。[5]
在实践运用中,教育大数据的蓬勃与兴起,可以促使教育的展开成为一种基于“循证”的科学实践。一般来说,教育大数据的教学支持服务不仅能够为学习实践赋予完整、深入的意义体验,还可以为教育方式的转变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在谈及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课堂师生互动的研究过程时,约瑟夫·艾伦等指出:“借助信息技术提供的智能分析技术,相关教育科研人员不仅可以使课堂话语的研究内容更加详实与充分,而且还能让整个研究过程更加客观与精确,从而提高整个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6] 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借助教育大数据的相关技术支持,教育的实践就是一项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事项,与此相应的教育人员也就不再是让·皮亚杰当年所描述的教育部的公务员,[7]他们的教育与实践不是仅仅依循教育部长的要求与指令,同时教育大数据分析的科学工具也为其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
三、数字化生存的文化新景象:大数据时代催生数字公民教育
进入20世纪中叶以来,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显著特征的信息技术快速兴起,在人类生活的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里产生一场影响深远的数据革命,由此将人类社会发展推向了信息文明的大数据时代。[8]正如迈尔·舍恩伯格所言:“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就像望远镜让我们能够感受宇宙、显微镜让我们能够观测微生物一样,大数据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成为新发明和新服务的源泉,而更多的改变正蓄势待发。”[9]在谈及这一以大数据为表征的时空场景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借由现代通信事业的飞速发展,信息网络技术已经营造了一个能够将全球数据信息自由传达的数字平台,通过这个由应用软件与光纤网络交织而成的智能平台,以数字化为标识的地球村已经变成了‘一望平川’的人类交流与沟通的网络场所”。[10]
信息技术衍生的大数据理念在教育领域中的长驱直入不仅重构了教与学的交往模式,而且还重构了人类经验建构的学习方式,进而由此孵育了被称为“数字公民”(Digital Citizen)的新型现代群体。[11]具体来说,大数据在教育实践中广泛应用构筑的“技术×人”彼此交互的数字化理念并形成一种独特的学习方式,对后信息时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它在信息化教育过程中营造了一个与现实社会并行不悖的虚拟世界的同时,还在这种数字化网络空间中创生了“数字土著”(Digital Natives)的新一代学习者;那些数字土著一边辗转沉浸于各类数字媒体技术搭建的电子幻象世界,一边能够在虚拟空间中自如地运用数字技术从事学习、工作与生活;因此他们在身份认知上除了拥有传统田园社区中的地域公民成分之外,还增加了一重现代网络社区的数字公民身份。[12]
站在人类文明演进的立场来看,数字公民概念的提出表明大数据发展已经在后信息社会里营造了一种数字化生存的文化新景象。正如信息时代的思想先知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所言:“未来大数据与数字信息不再只和信息技术和计算有关,它将直接决定我们的生存。”[13] 尤其是进入数字化生存时代以来,伴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规模化普及与物联网技术面向对象的实体化拓展,以“互联网+”为凸显特征的大数据技术在不断增加先前信息技术之于人类社会生产、交流、沟通等方面工具价值的同时,自身还逐渐扩容为人类寄居的现实生活世界,大数据由此成为一项重要的文化理念。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基于大数据的时代理念,我们有必要在传统教育方式基础上开展以数字公民为核心的教育新方式,以此培养能够在数字化生存时代进行各类创造性活动的数字公民。
四、公平与优化:教育大数据为政府部门的决策与管理提供科学支撑
从管理与决策的视野出发,信息技术支持的信息教育对促进均衡发展与社会公平方面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教育公平是促成社会公平的前提基础,在维系社会稳定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其基本要求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关键是机会公平,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14]时至今日,本着促成教育公平和填补数字鸿沟的初衷,我国现阶段正大力推广“三通两平台”,即实现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建设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目前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变革效果。[15]这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举措都体现出信息技术在管理决策方面的重要价值,彰显了政府管理的信息化与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事实上,就目前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实践来看,信息技术的推广和投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在信息资源上的差距,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发展之间的融合程度不断走向纵深,先前粗犷型的信息化投入方式在缓解教育公平上的弊端也随之显露出来,“无显著差异现象”[16]、“买得多用得少”[17]等问题成为信息技术变革教育挥之不去的阴影。面对这一现象,乔治·西门子等指出,教育大数据为我们推进信息化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就教育大数据的教学支持服务来说,基于对包括学习者基本情况、学习目标、动机水平、认知风格、学习需要等在内的数据的收集与分析,我们可以为其主动推送个性化的学习资源与有针对性的支持服务,而不再笼统地把所有学习内容进行打包通过教科书的形式提供给学习者。[18]
因此,从公平与优化的意义上来说,教育大数据为政府部门的决策与管理提供了工具支撑。在利用教育大数据技术促进教育公平的道路上,我们既要加大资源的投入和覆盖,以弥补信息技术不均衡发展在信息化准入层面引发的数字鸿沟;同时还需要在公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深挖各类优质的教育现象与资源,发挥大数据兼具的智能化与精准化性能;力争在促进教育公平的基础上,还能更为高效地帮助管理者做出科学决策,对各种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配置。站在教育资源的优化立场上来说,基于对各种基础数据的深度挖掘,我们可以把信息教育的管理与决策推进到一个更加科学化的层面上,从而极大提高各种教育资源配置的精准程度,提升资源应用的实际效能,最终尽可能地将均衡发展和社会公平问题落到实处。[19]
五、“互联网+教育”:大数据分析视野下精准扶贫业务的流程再造
时至今日,信息技术的崛起为社会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也为整个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调整。在整个演变过程中,不仅实现了麦克卢汉“地球村”的预言,进入了以网络社区为特征的数字时代;而且出现了弗朗西斯·福山所描述的社会秩序的“大分裂”,导致了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大重建。[20]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彻底将信息化与全球化的概念推向了极致。而作为人类认识与生产活动重要载体的教育,其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体系必将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首当其冲。实际上,自2001年麻省理工学院提出开放课件运动(OCW)以来,以互联网web2.0为技术支撑的教育全球化呈现出不可阻挡的趋势,最近掀起高等教育研究热潮的大规模开放网络课程(MOOC)更是这一势头的升级,传统教育的时空界限必将在互联网的推动下变得不那么泾渭分明。[21]
从社会实践的立场来看,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引发的信息化浪潮虽为人类文化的繁荣带来了空前的机遇,但这也为人类生活的发展,尤其是均衡发展的经济问题带来了极大的挑战;[22]实际上,伴随着人类信息文明的持续发展,贫富差距的扩大现象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显露出来,成为一项制约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而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要想破除文化井喷、社会发展与扶贫工作间的壁垒与鸿沟,关键在于教育。如何在有限的教育周期内实现文化创新与扶贫工作的协调平衡又为教育发展带来了新一轮的挑战;教育大计,效率为本,要想实现信息时代教育效能的最优化,关键还在于能在数字时代精确变革教育的大数据分析技术。借助教育大数据的智能分析,教育扶智工作在原来扶贫知其然的基础上,还能进一步知其所以然,从而真正实现精准扶贫业务的流程再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着力强化教育脱贫在民生脱贫致富中的关键性作用,大幅提升貧困地区教育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施教育扶贫结对帮扶行动计划。[23]而大数据技术在教育领域内的扩散则为这种精准性帮扶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杠杆,标志着我国扶贫工作开始从粗放型向精准型发生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要求我们把教育大数据视为一种“颠覆性技术”,把它作为推动教育精准扶贫业务流程再造的一种具有破坏性创新特征的革命性力量。[24]同时通过对大数据支持教育的机理和方法论进行探索,有助于我们明确时代变迁背景下现行教育扶贫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揭示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机理,确立利用教育大数据对经济发展变革的新方法论,进而为扑面而来的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发展做好准备。
六、结语
纵览上述大数据变革社会进程中信息化教育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教育大数据的研究与应用有着广袤的疆域与前景。从教育学自身的科学化演进,到文化建设中的数字化生存与数字公民教育场景,再到政治领域的管理决策之公平与优化,最终到经济发展中的精准扶贫,教育大数据的创新发展展现了大数据与教育融合的演化趋势,推动了信息技术与教育发展之间的深度融合,见证了不同背景下教育变革以及时代变迁二者之间的激荡与融合。因而从这一立场来看,教育大数据的研究与应用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成为教育创新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力。
参考文献:
[1]国发[2015]50号.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Z].
[2]杨宗凯,吴砥,郑旭东.教育信息化2.0:新时代信息技术变革教育的关键历史跃迁[J].教育研究,2018,39(4):16-22.
[3](美)柯林斯,哈尔弗森著;陈家刚,程佳铭译.技术时代重新思考教育:数字革命与美国的学校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
[4]桑新民.呼唤新世纪的教育哲学——人类自身生产探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118-125.
[5]Lagemann E C.An elusive science: The troubling history of education research [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231-247.
[6]Allen J,Gregory A,Mikami A,et al.Observations of Effectiv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s in Secondary School Classrooms: Predicting Student Achievement With the Classroom Assessment Scoring System-Secondary[J].School Psychology Review, 2013,42(1):76.
[7]Piaget J.Cognitive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Piaget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J].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1964,2(3):176-186.
[8]李曉东.信息化与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4-5.
[9]Mayer S V.Big Data-Eine Revolution,die unser Leben verndern wird[J]. Bundesgesundheitsblatt-Gesundheitsforschung-Gesundheitsschutz,2015, 58(8):788-793.
[10]Friedman T L.The world is flat: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s,2005:5-10.
[11]Prensky M.Digital natives,digital immigrants[J].On the horizon,2001, 9(5):1-6.
[12]Ohler J B.Digital Community,Digital Citizen[M].Thousand Oaks,CA:Corwin Press,2010:165-169.
[13]Negroponte N.Being digital[M].New York:Vintage,1996:11-21.
[14]杨银付.《教育规划纲要》的理念与政策创新[J].教育研究,2010(8):3-12.
[15]杨浩,徐娟,郑旭东.信息时代的数字公民教育[J].中国电化教育,2016(1):9-16.
[16]Layton J R.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henomenon[J].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1999,2(3):142-143.
[17]Twining P.Oversold and underused: computers in the classroom [J].Technology Pedagogy & Education,2003,11(1):111-112.
[18]Siemens G,Long P.Penetrating the Fog:Analytics in Learning and Education[J].EDUCAUSE review,2011,46(5):30.
[19]朱莎,杨浩,冯琳.国际“数字鸿沟”研究的现状、热点及前沿分析——兼论对教育信息化及教育均衡发展的启示[J].远程教育杂志,2017,35(1):82-93.
[20](美)弗朗西斯·福山著;刘榜离等译.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3-67.
[21]孙立会.开放教育基本特征的变迁——兼议MOOC之本源性问题[J].远程教育杂志,2014(2):30-38.
[22]陆有铨.躁动的百年——20世纪的教育历程[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10:175-181.
[23]陈恩伦,陈亮.教育信息化观照下的贫困地区教育精准扶贫模式探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7(3):58-62.
[24]Christensen,C.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M].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2013:xv.
(编辑:王天鹏)
2209501705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