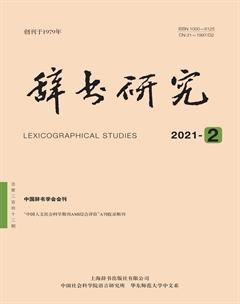阳历记日词“日、号”演变研究

摘 要 清末,随着西历在中国逐渐产生影响,西历记日词“日、号”应运而生,并用于汉语书面语。民国改历后,“号”使用范围扩大,进入共同语口语;1927年“国历运动”开始后,阳历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优势地位,“号”被淘汰出书面语,专用于口语。其演变动因有象似原则、经济原则、民族主义心理等。
关键词 号 日 变异和变化 语体对立及分工
“号”作为阳历记日词,与中国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也是外国人学习汉语时最早需要掌握的词之一,但其产生时间和来源尚未见专门讨论。明清时期,西历传入中国,催生的新记日词除了“号”,还有“日”。今天书面语用“日”,口语用“号”,这一语言变异是如何形成的似未得到关注。邱克威(2014),周琼(2017),车淑娅、周琼(2018)的研究均只涉及二者在清末民初新加坡华文报章中的使用及演变情况,语料的范围和类型有限,未能揭示二者语体对立及互补的形成过程。
本文将从变异理论视角出发,考察西(阳)历记日词“日、号”的来源和传播,揭示二者从并用于书面语到语体对立、形成分工的过程,并探讨影响这一演变的语言内外因素。
一、 “日、号”西历记日功能的形成
新记日词的产生和流传受到西历传入、晚清至民国时期历法体系变迁的直接影响。下面结合这一历史背景,讨论新词的来源和产生过程。
(一) “日”从表阴历到表西历、阳历
“日”本用于阴历记日,如:
(1) 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亡夫时户下髯奴便了,决贾万五千。(西汉王褒《僮约》)
明末,西历由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传入中国,影响仅限于天文学和宗教领域。真正在中国产生影响大约是19世纪中后期,中西方交往日渐增多,西历与时宪历并存,逐渐出现在外交、工商以及近代媒体传播领域。(吴岩,李帆2011)西历记日开始见于中外条约、传教士或外国人所办报刊,如《南京条约》《虎门条约》《遐迩贯珍》《六合丛谈》《申报》等。“日”开始表西历。《遐迩贯珍》中,西历记日与中历同,或用“日”,或省之,如1853年创刊号第一篇文章所附“一千八百五十三年日纪”,有西历每月一日与阴历日期的对照表,西历均用“日”,阴历只用序数词,如:
(2) 正月初一日,即壬子年十一月二十二;二月初一日,十二月二十四;……
外国人所编英汉词典中也是用“日”,如:
(3) April-fool,番四月初一日受舞弄者(罗存德《英华字典》)
用于西历记日,当前有“番、西、英”等时,可視为沿用汉语旧词;前无这些词帮助区分时,可视为旧词因为被用于新的语境——英语文化中的西历而扩大外延。清末,在西历传入中国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英语国家,《南京条约》《虎门条约》为中英两国之间签订,《遐迩贯珍》为英国传教士所办;英语表示月中某一日只用序数词,但因为汉语表示阴历月中日期用记日词“日”,中外人士遂沿用之。这种对译方式比起另造新词显然较为容易。
外国人在内地所办中文报刊,如《六合丛谈》《申报》《教会新报》《沪报》等,亦用“日”表西历,如:
(4) 大清同治壬申三月二十三日,英四月三十日,第一号(《申报》创刊号刊头,18720430)
也见于外使给中国总理衙门大臣的照会、中国出使或游外知识分子笔下,如郭嵩焘、刘锡鸿、张德彝、钱单士厘、梁启超等:
(5) 今岁,会堂期为西历二月初八日,即中国之十二月二十六日,呈递国书之次日也。(刘锡鸿《英轺私记 开会堂情形》)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财经、法律、教育、外交等诸多领域,使用西历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基于民族主义立场,改变清朝正朔,发布了《改用阳历令》。(湛晓白2013)103,107此后“日”亦表示阳历。同时兼表阴历记日,不够明晰,为西历专用记日词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二) “号”西(阳)历记日功能的来源
“号”指一个月里的日子,是其“表示次序”的一种特殊用法。后者近代汉语已见,如:
(6) 故事,殿试唱名,编排官以试卷列御座之西,对号以次拆封,转送中书侍郎,即与宰相对展进呈,以姓名呼之。(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转引自《汉语大词典》)
清代又新增跟西洋新事物有关的表报刊期数、纸币序号、轮船序号、门牌号等用法,如:
(7) 《遐迩贯珍》数号,每记花旗国与日本相立和约之事。至第十号,则载两国所议定约条之大意。[1854年罗森《日本日记》,转印自黄河清(2010)316]
表西历记日,应引申自表报刊期数,尤其是日报期数。日报本非中国自有,19世纪末才在中国本土出现,如外国人创办的《申报》《上海新报》等;此后有中国人创办的《述报》《大公报》等。日报每天一“号”,易使人将各期报纸与发行报纸的当天联系起来。某日报纸可以说某报第几号,也可以说几月几号的报纸,后者更便于查索且能体现报纸内容的时效性。近代报纸来自西洋,于是便以表报纸期数的“号”兼表同样来源的西历日期,下例(9)即是如此。
“号”19世纪初先见于东南亚,如马礼逊《神会论》,出版于马六甲英华书院;但传教士和外国人所办中文报刊直到19世纪80年代刊头还用“日”表西历,“号”也未见于19世纪外国人所编英汉词典,应非外国人所创,而是东南亚的中国人所创。19世纪80年代零星见于新加坡《叻报》和中国外交官张荫桓、崔国因等人的游记;19世纪90年代已普遍见于中国本土,如上海《新闻报》、武汉《汉报》、陕西《秦中书局汇报》《无锡白话报》,以及海外中文报刊,如澳门《知新报》、新加坡《星报》《天南新报》、日本横滨《清议报》等,也见于外交文书、国人翻译西人著作等,如:
(8) 据德基厘供,吉丁实因六月十八号所刊日报被拘,别无他罪。(张荫桓《三洲日记》18750715)
(9) 大清光绪十三年丁亥七月初一日 大英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八月十九号,第一千七百二十四号(《叻报》第1724号刊头)
(10) 西历七月念一号西报载有俄兵四十名前往高丽京城,……(《新闻报》18940805二版)
除《叻报》中可用于本地新闻外,均见于使用西历的西国事情或译自西报的外国新闻。原因在于:新加坡于19世纪初被英国占为殖民地,使用西历早于中国,西历在社会生活中使用范围较大;中国本土当时西历影响尚小,较少使用西历记日。
“号”的产生是语言接触引发的词义演变。汉语本没有专表西历记日的词位,只有表示月中某日的词位“日”,一般用于阴历;在英汉接触中,既用“日”兼表西历记日,又增加了这一词位,即“号”,以便与阴历记日词“日”相区别,前可加“(大)英、西(历)”等帮助区分。20世纪第一个十年以前,《叻报》记时日,阳历与农历即大体分别用“西(历)某年某月某号”与“华(历)某年某月某日”。(邱克威2014)这符合象似原则。因此,虽然“日”也可表西历,但因为兼表阴历记日,不符合这一原则,又创造了西历专用记日词“号”。
20世纪初,“号”的使用范围继续扩大,用于中国本土《申报》《大公报》《北洋官报》《伊犁白话报》,海外新加坡《日新报》《中兴日报》等及中国人颜惠庆所编英汉词典《英华大辞典》。民国成立后,沿用表示阳历。足以证明19、20世纪之交,“号”由于填补了西历记日的词位空缺,成为语言变项(variable)“西历一个月里的日子”的另一变式(variant),自产生后迅速在汉语书面语中流传开来,这很可能是受书面媒介——报刊助力所致;后借此进入口语。
二、 “日、号”语体对立及分工的形成
“日、号”清末产生,并用于书面语;民国初年,“号”进入口语,因语体差异与“日”形成变异。郭风岚(2006)指出语言变异有三种结果:断裂性变异、进行中的变化、完成了的变化。根据现今“日、号”分别用于书面语和口语、成为稳定变异的事实,可知变化已经完成。
(一) “日、号”语体差异的形成
“号”初期主要用于报刊、出使知识分子著作、外交照会、国人翻译西人著作等,多为文言。直至清政府灭亡,在白话作品中用例尚少。民初改历以后,才逐渐在口语中扩大使用,与“日”形成语体差异。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号”在南北白话报刊《无锡白话报》《京话日报》和南方白话小说《文明小史》《九尾狐》中有所使用,口语色彩初现端倪。如:
(11) 六月廿五号香港西报说道:法国人租赁广州灣,不免失算。(无锡白话报 五大洲邮电杂录,1898年11期)
(12) 倍立是总矿师,每月五百两,……小边、王八老爷当杂差,每人三十两,从下月一号起薪水,大家都欢欣鼓舞起来。(《文明小史》54回)
民初北京白话报刊《女子白话报》《爱国白话报》或其他报刊白话部分已用:
(13) 听说明日(三十一号)上午八九点钟,有保安警察队跟保卫队,在西便门外闷葫芦罐儿地方练习打靶。(《爱国白话报》,19130730四版)
大致同时,也见于域外官话教材,如日本、朝鲜北京话教材《汉语指南》《京华事略》《官话丛集》等:
(14) 伏,是从夏至起,就是阳历的六月二十二号算到二十七天是初伏,入伏。(金醒吾《京华事略 天时》)
说话人有师范学校的先生、举办讲习会的知识分子等。以上用例证明“号”至迟民国初年已南北通用,进入了共同语口语。至此,“号”因语体差异与“日”形成变异:“号”兼用于书面语和口语,“日”只用于书面语。二者所组成的语言变项属于标记项(marker),一般既反映说话人的社会层次,也反映其语体变化。(徐大明2007)153“日、号”这一阶段在本国使用者中主要反映语体变化,知识阶层在不同语体中分别使用。
19世纪20年代,“号”在白话和口语中继续扩大使用,开始见于小说人物语言,用例比较有限。如:
(15) 老太太又要往起撩围裙:“……秋天——十月七号。头一个中国人埋在这里,头一个!”(《二马》第二段)
出自看守墓地的英国老太太之口,属下层民众。也见于白话书信,如梁启超1926年以后写的《与儿女书》。
民初以降,“日”在白话报刊文章、书信、小说中续有使用,仍带有明显的书面语色彩,与“号”语体对立。如:
(16) 本月一日下午,友人出齐化门购买年物,遇见三档子特别新闻,如今说与诸君听听。(梅蓃《益世报 余谈》,19210205)
梁启超1922年开始写白话家书,直到1925年年底,落款和正文中均只用“日”。小说中多用于叙述,少用于人物语言,仅见于《留东外史》革命者和留日学生之口。
(二) “号”退出书面语
报纸是晚清民国时期使用西(阳)历记日词的典型语境之一,报章语言可视为书面语的代表,本节通过考察“日、号”在其中的使用情况及变化揭示二者在书面语中的演变。
1. “号”退出报头
19世纪末开始,“日、号”在书面语中并用,不符合经济原则,其一可能会退出书面语,但不能确定是哪一个。民国成立以后,报头日期词发生了变化,多数报头阳历记日纷纷改用“日”,以便与西历用“号”相区别。同时,阳历在公共生活中逐渐胜于阴历。以《新闻报》为例,1912年1月5日刊头仍是阴历用“日”和西历用“号”,次日未列旧历,阳历和西历均用“号”:
(17) 中华民国元年正月六号,西历一月六号
而1月10日阳历已改用“日”,与西历“号”相区别:
(18) 中华民国元年正月十日,西历一月十号
1913年西历也改用“日”,如:
(19) 中华民国二年五月念四日,即癸丑年四月十九日,西历五月念四日
持续到1927年1月28日,同年2月初开始不再列西历;1929年1月开始不再出现阴历,只列阳历日期。
《叻报》自1887年到1911年,刊头都是阴历用“日”,西历用“号”;民国以后阳历替代西历,刊头记日词几乎全用“日”。1930年以后取消阴历。(车淑娅,周琼2018)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将阳历定为“国历”,发起国历运动,强制推行,阳历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湛晓白2013)1930年前后,报头基本不再列阴历日期,体现了阳历在公共生活中的优势地位。下一小节的论述可知“号”退出书面语也是在同一时期。
2. “号”退出报纸主体部分
以《大公报》天津版(1902—1937)为例,自创刊起,报头已列西历“号”,但1902年6月17日至18日,主体部分只在涉外语境以西历记日,既用“日”,也用“号”,各仅1例,如:
(20) 外务部得有消息言六月十二日交还天津,已由津海关道唐绍仪与各国议定。又闻直隶官场传说天津交还之期至早必在西九月一号即华七月二十九日。二说未知孰是。(19020618二版)
1912年6月17日至18日,“号”用例增加,除了时事新闻,也用于启事、广告等,如:
(21) 启者:本号三月二号被兵匪抢失之交通股票,今将抬头号码注销。(19120617八版)
牵涉官方的文本虽也用“号”,但“日”用得更多。如:
(22) 十七日(初三日)本社特派员赴国务院调查如下:……(19120618二版)
1922年6月17日至18日,“号”仍沿用,但用例明显减少,仅见“十三号、十八号”。而1912年同期有“二号、三号、九号、十二号、十四号、十五号、十八号、二十三号、三十一号”等。“日”用例更多。有的新闻正文用“号”,落款用“日”;或正文用“日”,“号”用于其他功能,如火车车号。广告用“号”,亦用“日”。
1932年6月17日至18日,以“日”为主,“号”已鲜见,基本退出书面语。只见“九号、十号、十五号”,前二者见于同一篇白话文章,再次印证了“号”的语体色彩,预示了其此后去处。“号”或冠以“西历”,“日”或冠以“国历”,亦可反映时人心目中二者的用法、地位差异。正式语体倾向于用“日”。17日十版《天津地方法院公布栏》,落款均用“日”。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叻报》中。民国以前,其主体部分西历记日用“(西/大英)号”:民国成立后到1930年间,阳历记日兼用“日、号”,西历仍用“(大英)号”,亦偶见“(西)日”;1931年,以“日”为主,“号”仅偶见。(车淑娅,周琼2018)
(三) “日、号”从语体对立到语体分工
20世纪30年代,随着国历运动的开展,阳历的影响进一步深入,“号”在口语中的用例进一步增加,域外汉语教材不同版本的内容变化即可反映这种趋势。如:
(23) 今天几儿了?今儿初十。(《官话急就篇》1904)
今天几号了?今儿十号。(《急就篇》1933)
“号”退出书面语后,与“日”基本形成语体分工,在白话作品中共存,但小说中大致分别用于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互补分布。“号”开始见于本土文献中本国人物之口,如:
(24) 杨先生:我们俩是来请你们阖第光临,喝盅酒去!下月十二号——
洗老太太:阴历是几儿?这年月,又是阳历,又是阴历,还裹着星期,简直说不清哪天是哪天!(老舍《残雾》)
本文所调查民国时期白话作品中,“號”均用于人物语言,说话人多为受教育阶层,如例(24)“官小而衔多”的杨先生、《子夜》中的资本家等;下层使用者均为外国人,如《二马》中的英国老太太、《四世同堂》中的日本兵等。受教育程度低的本国人物可能因不用阳历而不用“号”,如例(24)局长之母洗老太太,社会地位不低,受教育程度不高。
用“号”还是用“日”,民国初期主要与语体有关,这一时期也与社会阶层、受教育程度有关。“日”为受教育阶层在书面语性强或较正式的场合使用,如小说叙述语言、书信、请帖等,个别用例见于人物语言,均系工作场合,如:
(25) 竹斋,现在我们两件事——益中收买的八个厂,本月三日抛出的一百万公债,都成了骑虎难下之势,我们只有硬着头皮干到哪里是哪里了!(《子夜》十)
使用者有土改工作队队长、资本家等。他们在口语性强或非正式的场合也用“号”。下层民众未见用“日”。正与徐大明(2006)6的论断一致,即与语体差异相对应的一般是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有关变式的出现一般受到语体和社会阶层的双重制约。
综上,民国以前,“日、号”主要为知识阶层在书面语中使用,口语中使用极其有限。因为当时西历主要在知识阶层中扩散,未被下层民众认知、认可。民国成立后,政府主导改历,知识分子积极进行历法科普,自上而下推行阳历,阳历影响范围不断扩张,“号”进入共同语口语,使用范围逐渐扩大。19世纪30年代退出书面语,只在口语中沿用,与“日”形成语体分工,对汉语语言系统产生影响,使得阳历记日这一义位拥有语体对立的两个词,系统达到对称平衡,变化完成。如表1所示:
变化原因除了经济原则,最重要的应是民族主义的排外心理。“号”自产生后一直是西历专用词,容易让人联想到西历的外来身份;民国以后,阳历实际是西历,成为国历,知识阶层出于民族主义心理,想要剥除其外来色彩,因此在代表正式语体的书面语中,“号”逐渐受到排斥。其他原因有:1. “日”作为记日词历史悠久,不具有外来色彩;向来主要用于书面语,阳历记日沿用,语体合宜。2. 阳历占优势后,口语中需要标记,以便与阴历多用序数词不用记日词区分,如:
(26) 他这个病得的也奇。上月中秋还跟着老太太,太太们顽了半夜,回家来好好的。到了二十后,一日比一日觉懒,也懒待吃东西,这将近有半个多月了。(《红楼梦》第11回)
使用记日词比用“西历、阳历”等说明更为经济。“号”民国初期已进入共同语口语,具有进一步扩散的基础,“日”主要用于书面语,不具备这一基础,因此,前者得以从书面语进入口语,从知识阶层到普通大众,自上而下传播。
三、 结语
汉语中表西历、阳历记日,书面语从用“日”到“日、号”并用;后来,“号”进入口语,二者出现语体差异,形成变异;最终,书面语淘汰“号”只用“日”,口语用“号”,两个记日词语体互补、分工明确,成为稳定的变异。
从语言内部看,演变动因主要是象似原则和经济原则。“日”兼表阴历记日和西历记日,不够明晰;“号”应运而生,专表西历,与阴历“日”明确区分。因此,得以与“日”在书面语中并用,因不符合经济原则,终被淘汰。后专用于口语,与其中阴历记日大多不用记日词相区分。从语言外部看,书面语选择“日”,与西历专用词“号”相区别,有民族主义心理的影响,与民国前期“星期”在书面语中替换“礼拜”的原因类似。“礼拜”的宗教色彩和异域来源,在其进入汉语共同语后,引起中国知识阶层的反感。(刘曼2019)
五四运动文白兴替,汉语新书面语的形成、书面语词和口语词语体对立的形成,对现代汉语词汇、共同语词汇的形成有直接影响。这一语言生活背景,对晚清民国时期受西方文化影响产生、在汉语近代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新词的演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结合本文个案和以往研究发现: 1. 有些新词来源不同,产生后先在不同人群中使用,进入共同语后形成语体对立,如时段时间词“点钟2、时2、小时2”。2. 有些口语词和书面语词产生时间有早晚,语体对立的形成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与“号”从书面语进入口语不同,“礼拜”和时点时间词“点钟1”等先产生于口语,后来进入书面语,与相应的书面语词“星期、时1”并存。3. 不同语体中,演变内容和演变进程存在差异。“日、号”的演变主要发生在书面语中,口语中自“号”进入后,一直沿用。“星期”替换“礼拜”,书面语中快于口语。钟点类时间词不同语体中发生更替的词不同,书面语中“点钟1→时1”“点钟2→小时”,口语中“点1”胜于“点钟1”“点钟2→钟头/小时→小时”,书面语中的替换亦早于口语。4. 五四运动前后二三十年是新词语体对立形成、书面语中新词更替的高发时期,适应了新兴白话正式语体形成的需要,是现代汉语书面语词汇形成的重要时期。(刘曼2019,2020)
参考文献
1. 车淑娅,周琼.语言接触视角下的清末民初新加坡华文报章时点时间词研究.中國语文,2018(4): 493-509,512.
2. 郭风岚.语言变异:本质、因素与结果.语言教学与研究,2006(5).
3. 黄河清.近现代辞源.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4. 刘曼.“礼拜”和“星期”流传、替换考.澳门理工学报,2019(3): 55-63.
5. 刘曼. 汉语钟点类时间词的更替及语体对立的形成.∥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编.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二十八辑),成都: 巴蜀书社,2020: 96-109.
6.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1993.
7. 邱克威.《叻报》的词语特点及其词汇学价值管窥.语言研究,2014(4): 102-107.
8. 吴岩,李帆.从“改正朔”到“改用西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5):71-75.
9. 徐大明主编.语言变异与变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10. 徐大明.社会语言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1. 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3: 104-108.
12. 周琼.新加坡《叻报》时间词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102-107.
(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陕西 710128)
(责任编辑 刘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