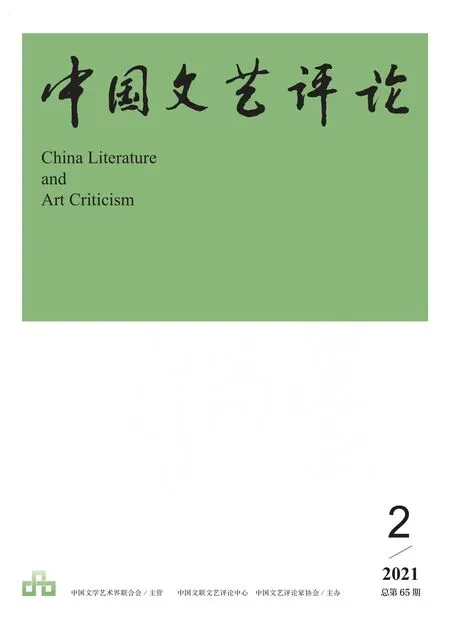台上台下的人生演绎
——评电视剧《装台》的叙事艺术
江腊生 江辰炀
随着时代生活的发展,电视剧作品不断向精致的中产趣味迈进,古装宫斗、仙侠玄幻、谍战悬疑不断上演,而真正具有平民视角、反映生活现实的电视剧作品越来越稀缺。改编自陈彦同名小说的电视剧《装台》热播后,引起了不少观众的叫好,原因是这部都市剧接地气、有温度。一反以往的都市剧中,场景都是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精致装修的别墅公寓,频频上演的都是律师、明星、商界大鳄等光鲜的人物故事,电视剧《装台》聚焦既有现代气息又历史韵味悠长的古城西安“装台人”这一特殊群体和“城中村”这一特殊空间,通过他们的装台人生,讲述了普通民众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温暖真切的日常故事,富有生活质感地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本质内涵。在喧嚣而又窘迫的生活中,剧中每一个装台人用他们的情怀、担当、韧性支撑起一个温暖的人性世界,表现了一种不慌不忙的坚强。其中充满日常生活烟火气的热度和温情,又潜在地与传统的民间伦理相契合。与此同时,作品通过大量引入地方传统文化的元素,将秦腔文化与现实世界构成互文,叙事张弛有度,既有感人的生活细节,又处处闪烁着生命与文化思考的亮光。电视剧《装台》打开都市世界的生活褶皱,以小见大、以情动人,为当下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提供了新的经验参考。

图1 电视剧《装台》海报
一、不慌不忙的生活坚强
剧中择取“装台人”这一生活在城中村的社会边缘群体,透过老百姓的琐碎日常,扒开了欲望都市下底层社会的真实境况。二代有房有车有钱,希望有一天能在舞台中间唱主角,为的是艺术。墩墩整天卖力装台,买彩票,却无钱娶媳妇,因的是现实。刁大军闯荡南方,赌博破产后贫病交加,只能由弟弟顺子带回家乡照顾。张大户有钱有势,在村子里搭台子请戏班,为的是已故父亲的三周年忌日。游走的医生在各个医院走穴,简陋医护室里也敢动痔疮手术。贫穷的大雀儿舍不得吃穿,为的是给女儿做植皮手术。孩子脸部烧伤后,只能待在家里自己习字,而无法去上学。刁菊花和巫英格无所事事,整天与贩卖假酒的老板厮混。秦腔团的事业日益下沉,瞿团长、靳导演为了振兴秦腔团,不惜低三下四求上司和赞助商,为的是能够将排练厅装上暖气。这些包罗万象的社会世态,通过以刁顺子为领头羊的装台人的生活加以折射,让我们感受到了当下社会毛细血管里的一系列阻滞,及其命运的苦楚。
然而,电视剧没有在二元对立的思维中,将这群装台人的生活写得愁云惨雾,而是书写他们身处底层却充满与生活一搏的生命韧劲。蜗居城中村的刁顺子,带着一帮外来打工的兄弟,为秦腔团表演、婚丧嫁娶等卖力装台。装台工是无人留意的冷门行业,作品聚焦为别人装台的群体,书写他们劳碌于舞台聚光灯外、生活在繁华都会的城市边缘的人生。舞台的光鲜亮丽完全遮盖住了他们的劳苦,他们耗尽全身的力气,获得的只是极其微薄的收入,甚至屡屡被骗。顺子为了大家不白干一回,忍着痔疮发作的疼痛,在交了手术费之后从医院逃走,坚持要回大家的工资。墩墩和手枪因为在张家祠堂里激情相遇,惹得张氏家族大怒,二人因害怕逃跑后,顺子为了挽回局面,替墩墩跪长夜,一直跪到双腿发麻。大雀儿在街头蹬着三轮拉货,为了争取时间而肩扛三轮车走过非机动车禁行的一段路,目的只为多赚点钱,为烫伤的女儿完成植皮手术。他劳累过度,两次心脏病猝发,最终因为没有及时医治而倒下。这些底层的装台工散发出原始的野性魅力,在让观众为他们的生活艰难而感叹与同情时,也让观众隔着屏幕仿佛感受到生命燃烧的味道。
底层人自有底层人的活法,忍受是这一群装台人求得生活的法宝。他们不属于英雄,无法在快意恩仇中表达自己的爱与恨,却总在生活的诸多细节中显得小心翼翼。刁顺子总讲“咱以后再也不干这装台的烂活儿”,但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即使因为女儿发飙一宿没睡,第二天还是早饭都来不及吃就赶去剧团;为了多揽活,在铁主任、瞿团长面前点头哈腰、极尽谄媚;为了讨工钱,厚着脸皮耍赖住进铁主任家;女儿因为后妈的到来,住进高消费的宾馆,给小狗美容,让顺子每天入不敷出。这一切都基于生活带来的忍受,正如剧中的画外音所说:“虽然顺子窝囊的性格好多人接受不了,但为了生活,很多时候他只能这样活着。”这个有血有肉、有真实痛感的小人物,身上有隐疾,心中有伤痛。他因为同病相怜“拾”回第三个妻子蔡素芬,结果使女儿刁菊花和他反目成仇;他的养女韩梅因为和“姐姐”刁菊花之间的“爱与利”的争夺导致关系不断恶化;他的以赌为生的哥哥刁大军也把他当作人生的靠山,动辄就要他拿出上万元还赌债等。他以自己佝偻的身躯默默承受了一切。剧中的顺子身患痔疮,这也成为了他生活状态的隐喻。痔疮对于顺子而言并非致命的病,但由于生活紧张他总是放弃治疗,这与日常生活当中的疼痛和隐忍直接相关。作品中,在蔡素芬离开他以后,他试图决绝地以读报、养鸟这样的农村退休干部的享乐方式来改变自己,但最终还是被他工友们的“三顾茅庐”所打动,又回到他的装台人生中去了,这也许就是他无法摆脱的宿命。说到底,是他无法摆脱对他人的生命责任。
同样,蔡素芬的忍受体现了妻性、母性的强大,也体现了她作为一个弱势女子的性格缺陷。刁菊花一次次地为难素芬、甚至无理取闹,素芬都忍受,为着自己的爱人顺子,也为着自己。为了防止刁菊花的骚扰,素芬让顺子把自己反锁在房间;她好心端了面条给躺在床上打游戏的刁菊花,却遭到对方的奚落。刁菊花在院子里砸花盆,她忍受了;刁菊花将自己好心买的便盆摔在身后,她忍受了;刁菊花将来访的剧团姚团长与蔡素芬锁于一室,她忍受了;甚至学生三皮的苦苦纠缠,她也忍受、微笑。剧中有一细节,顺子带到剧团的小黑乱跑,吓坏了靳导演,顺子把小黑放在地上,像西游记里孙悟空一样画了一个圈,让蔡素芬在边上看着。蔡素芬慢慢走进小圈子,蹲下来看着小黑。这个场景,充分展现了蔡素芬的忍受及其背后的性格弱点。一方面素芬“不嫌弃顺子家贫”,“容得下菊花胡闹”,人品、性情堪称一流。另一方面,素芬此前的生活,决定了她的性格弱点。如她向顺子所言,自己被前夫老板纠缠,前夫不堪其扰、愤而杀人,也因此被判处了死刑。街坊邻里和前夫家人,将其视作“红颜祸水”,她才背井离乡,来到了举目无亲的西安。三皮像影子一般跟随着素芬来到刁家村。明知素芬已经与顺子结合,他还坚持追求素芬,强吻素芬,可她并未严词斥责。即使她说要吹枕边风赶走三皮,话语也是绵软无力,甚至给人“欲拒还迎”之感。只有到后面,她毅然选择离开两个男人,去追求自己的独立,才活出了自己的根本。
这些装台人在忍受生活的艰难与苦楚中,没有对生活的世界耿耿于怀,却表现出一种不慌不忙的坚强。“不慌不忙的坚强”出自白落梅的《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林徽因传》,形容林徽因一生贵族式的静雅。这本与剧中装台人的生活无关,本文借用“不慌不忙的坚强”意指他们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他们身处城市的底层,却活出生命的高度;身在舞台的背后,却矜持地认为自己是搞艺术的;他们的日子过得异常窘迫,却始终不慌不忙、迎头笑对。他们给别人装台,也有别人给他们装台,在闭环的相互照应中透出的是普通人对温暖、对美好生活的渴望。顺子在拿不到工钱后,买上几个锅盔,看望独居的窦老师,两人就着啤酒,啃着锅盔,谈论着西安的美食。刁菊花故意弹电子琴而吵闹,素芬煮面的勺子竟然能够和着旋律轻轻地挥舞。为了能满足女儿看看游乐场的梦想,大雀儿在临死前坚持去游乐场拍了一组视频,最后在笑声中倒下。刁大军沉迷赌博,债务缠身,却又死要面子,在过年当天将家中的旧门换成新门。韩梅和满存励志向上,尽管生活艰难,却能凭着自己的能力在城市中打开一个小天地。即使是家里开煤矿的二代,也凭着自己的人脉和手艺,最终收获了与刁菊花的爱情。这些生活中的坚强,没有精神的高大上,没有大侠的快意恩仇,更多的是现实生活中的见招拆招,随物赋形。他们没有在生活的艰难面前败下阵来,而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保持一线生命的微光,趋向于人性的真善美。在今天享乐文化、佛系文化盛行的当下,不慌不忙的坚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质感,也感受到一种日常琐碎之外的诗意。人物有喜剧色彩,有淡淡的哀愁,还有含而不露的感伤,但角色的悲喜更多地是在展现笑对人生的生活态度,就像电视剧主题曲《不愁》中唱的那样:“生活虐我千遍万遍,我待它如同初恋。”
二、温情的浸润与伦理的后撤
电视剧《装台》在情感上没有赤裸裸的哗众取宠,也没有波涛汹涌的煽情,显得内敛而节制。剧中装台人的生活中除了体现不慌不忙的坚强,还有浸润其中的温情,包括日常的夫妻之情与朋友之情。这些情感的挖掘,看似流于日常生活,却极为深刻。剧中的“情”,世俗且带有烟火气,更贴近老百姓的现实生活。当观众看腻了悬浮的偶像剧、乌托邦式的爱情,《装台》中毫无粉饰、赤裸而自然的情感,似乎更能引发共鸣,勾起我们内心深处的感动。观众时不时地会为其中的一些情感细节颔首感动,而非大起大落的情绪宣泄。
电视剧对于人物之间男女关系的描写,可以说体现的是生活的情感热度而不是人性的欲望发泄。“情”,始终是这世上最耐人寻味的东西,七情六欲乃是人之本性,更是影视剧探讨的核心内容。这种情欲,无关乎低俗,就像刁顺子与蔡素芬之间的情感,质朴而浪漫,隐晦而撩人,让我们感受到了平凡人的甜蜜,以及人到中年最真实的七情六欲,烟火气十足。蔡素芬扭脚,顺子赶紧拿酒给她搓脚,表现出了足够的细心与体贴。顺子边给蔡素芬搓脚边深情凝望,一种百姓生活中的岁月静好直戳人心。尤其是当顺子在搓脚前倒酒让蔡素芬喝点,蔡素芬一句:“你回回都是搓二两喝八两,办的都是大事情”。这让人浮想联翩的“调情”,给寡淡的现实生活增加了无限趣味。还有顺子在饭桌上那句羞人的“今天晚上想跟你生活一下”,蔡素芬于是夺过酒瓶,应声坐在床头,满怀羞涩而又果断地看着正在吃饭的顺子,轻轻地拍着床单示意,日常生活的温暖中又不无欲望的逗引。看着刁顺子和蔡素芬之间温柔而又充盈着荷尔蒙的眼神,寡淡平常的日子被他们过出了令人艳羡的小幸福。电视剧反复出现的画面:每天早晨,刁顺子双手打开破旧的木门,蔡素芬拿起挡车的门槛,顺子把三轮车推出门外,二人一个蹬车,一个坐车,说说笑笑开始一天的营生。他们之间的爱情与婚姻,平平淡淡中掺杂着颗粒感的浪漫,生活充满了现实的质感。
离婚后的疤叔和八婶之间你来我往的言语相怼,却在疤叔看着八婶吃早点的奉承与调笑中,体现出一种夫妻之间的难以分舍。二代总是低三下四地取悦对方,而菊(“刁菊花”的简称)却一副趾高气昂的姿态,二人最终因为孩子的出生,成就一番被考验已久的爱情。靠赌博而发迹的刁大军,难以忘怀初恋桃花,临死之前将桃花的儿子托付给顺子。这些人世间平凡人的爱,虽不惊天动地,却是琐碎日常中的调味剂,带给喧嚣时代的人们真情的温暖与开心。
除了男女之情外,电视剧还在亲情和友情上大作文章。菊有了自己的孩子,梅(“韩梅”的简称)有了自己的男朋友,无论闹过多大的别扭,始终是一家人,没有什么能击垮亲情。从小缺失母爱的菊在妹妹梅要去陕南时,打电话让孩子的准父亲“过桥米线”亲自送梅走,还给了她一些零花钱,临行前拿出一副皮手套,让人感觉异样的温暖与柔情。顺子住院,菊不顾身孕大老远跑来看望,一进医院,父亲那辆又破又旧的三轮映入眼帘,到了医院二楼,整个医院又冷又脏,父亲孱弱地躺在病床上,菊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么多年,父亲就是靠那一辆破三轮把两个女儿养大成人,个中辛苦难以言说。当菊终于向蔡素芬说“对不起”时,两个都深深爱着顺子、却一直掐架的人终于和解了,这份亲情的力量来自生命的血液深处,又带有现实生活的劲道。

图2 电视剧《装台》剧照
如果说亲情和爱情还属于家庭伦理,那么弥散在电视剧中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则支撑起了一个现代社会弥足珍贵的人性空间。刁顺子和小学老师窦老师之间是师生之情,更是人伦之情。顺子辛辛苦苦带着大伙儿忙了一阵,为一个国际舞蹈节装台,不料经办人逃跑,众人领不到工资。他带着锅盔去看望窦老师,精神困境之中感受到的是真正的情感带来的温暖和亮色。这是作品中最打动人心的情节。正因为这种师生间的生命深情,老师才会将自己的身后之事托付给学生。二代出手大方,在装台的顺子他们没钱吃饭时,总是又给酒喝,又送面吃。他经常挂在嘴边的是,“没人脉啥都不顶”。刁顺子在装台队中,真情相待,无论谁有困难,都能出手相助。当墩墩和手枪在张家祠堂抱在一起被发现后,他顶替逃跑的墩墩跪长夜;他抱着铺盖来到铁主任家里,讨要装台队的工钱。当兄弟大雀儿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后,他收留孤儿寡母,并决心要帮大雀儿的女儿丽丽完成植皮手术。看着顺子带着病痛跪长夜,三皮不忍心,只身一人去找张大户赌酒。从来滴酒不沾的三皮端起一壶酒一口气喝完,瞬间倒地,顺子因此得以不跪。这便是三皮对顺子的友情,是顺子对大伙的友情激励了三皮,患难见真情,这样的友情让人感动不已。“人脉”、责任、担当、情怀构成了电视剧中人与人之间的热度。这种热度并非来自精神或灵魂层面的浸透,而是从日常生活的诸多细节中随意流淌出来。黑总将所有的房子出租,自己住在路边报废的车子里。当市容清理时,汽车被拖走,撒出来的却是一张张捐赠单。原来抠门的黑总把钱都捐给了最需要的人。在众人一片赞叹声中,黑总却满心欢喜地捡起一个车子上掉出来的指甲钳子。于是电视剧传达出一种人际之间既真切又自然的温情,观众在喧嚣而又孤独的日常世界中不时被击中敏感的神经,缓释了生存中因为利益而带来的紧张和冷漠。
同时,电视剧众多温情的生活细节中,通过社会底层普通劳动者的悲欢离合和喜怒哀乐,展现他们面对困难不屈服、不妥协的人生态度,传递了一种中国人骨子里向上的正能量。同时,这种正能量又潜在地与传统的民间伦理相契合,最终在日常生活的温情世界体现了电视剧一定的伦理取向。
首先,电视剧透过生活的“小角色”表现他们的困顿艰辛,体现了可贵的底层关怀,这是激发观众共情的核心。刁顺子是个下苦的装台队工头,也是个被生活捏搓的苦命人,但这些都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人生准则——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钱在这剧中显然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不过,钱再好也要取之有道,“不该有的连想都不应该想”。他并非不通世故人心,拿不到工钱,就抱着铺盖卷去铁主任家里堵他。在老姚那儿赚到了钱,他明白要给铁主任好处,因为他们相互依靠谁也离不开谁。面对一帮兄弟的时候,他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让兄弟吃亏,当然兄弟们也不会让他吃亏。他清楚自己的命运,也明白生活的真谛,人生好比一出戏,就得“我给你装台,你给我装台”。他活得拧巴也通透,即使生活总是虐他千百遍,他仍旧对未来生活抱有如初恋般的美好期待。因此,当素芬要告诉他前夫的事情的时候,他才会充满困惑地请求,“我能不能不知道你的过去?”他身边的那群人也没有一个人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他们心里,装台是艺术,装台人也是艺术人。这些小人物的精神弧光固然微弱却也坚定,凝结成了时代精神的大气象,为观众提供了温暖的心灵抚慰。
其次,电视剧通过底层生活空间的描绘,暗合了一种传统的民间伦理,自然契合了观众的伦理期待。在夫妻关系上,小人物之间相互信任,中间没有太多物质掺杂,而是传统的夫唱妇随。刁顺子将存放自己积蓄的铁盒子推到蔡素芬面前,放心让其管家。当三皮总是纠缠着蔡素芬,众人劝顺子当心时,他却觉得夫妻长久在一起就不必在乎。墩墩凭着一时的热度爱上了舞女手枪,而手枪却拿出自己的私房钱主动为其交上彩礼。即使在离婚后的疤叔和八婶之间,二人虽然天天斗嘴,当歹徒入室抢劫时,疤叔挺身而出打跑了歹徒,最终二人破镜重圆。大雀儿在外面没日没夜地干活,一心想着为家里多赚些钱,目的是让妻子和孩子过上好日子。这些夫妻关系并非建立在海誓山盟的基础上,而是在日常生活的一颦一蹙间流露出了日常的真情。这些夫妻之间的真爱流淌,直接与中国传统的伦理相关,而不是爱的精神张扬。
从电视剧的伦理结构上看,几乎每一组人物的命运走向都暗合了“好人有好报”的民间伦理。刁顺子和蔡素芬之间尽管有女儿的阻拦和三皮的纠缠,二人最终执手相看,戴上了结婚戒指。刁菊花和二代之间,一个低三下四,一个趾高气昂,最终在儿子出生后,成就美满婚姻,并得到父母的认同。八婶和疤叔离婚却不分散,最终由于城中村要拆迁而重新团聚。韩梅与满存这一对年轻的大学生,因为勤劳创业,在幸福婚姻的基础上也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尽管窦老师、刁大军、大雀儿三人留下一片人生的感慨和唏嘘,却还是让人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情。这些日常生活的温情流淌,通向的是一种传统的民间伦理取向。
河南老姚带来豫剧团演出,顺子和蔡素芬一起看着最喜欢的豫剧《清风亭》。剧中张继宝白发苍苍的母亲挣扎着爬起来将200文钱丢向儿子,万念俱灰地一头撞死在石台上。父亲看着老伴儿惨死在地,怒目圆睁拾起地上的棍棒发疯般向众人挥去,最终急火攻心被活活气死。张继保逼死母亲,气死父亲,这样毫无纲常伦理的人终于被天宫降下的雷电劈死。台上演员投入的演出,让顺子、素芬和台下的观众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剧中传达的传统“孝亲”伦理,让刁顺子接回病入膏肓的哥哥刁大军这一举动有了亲情的伦理依据。这种传统的家庭伦理与日常生活细节紧密结合,使得整个电视剧充满了烟火气与人情味。于是,电视剧在日常生活的温情中滑向民间传统的伦理,契合了观众内心对情感伦理的期待与对隐秘世界的渴求。
三、艺术与现实的精神同构
电视剧《装台》的妙处就在于选取“装台”这一独特生活世界,将艺术与人生自然紧密地融合起来。从电视剧的结构来看,《装台》包含着两个层面的互文结构,即台上的传统戏剧人生与台下的装台队伍的人生,一个是艺术文本,一个是现实文本,两个文本互相参照,艺术文本构成现实文本的隐喻符号。一群在舞台聚光灯背后的小人物,他们日常搭台、架灯、装箱的忙碌生活,构成电视剧的显性文本。贯穿《装台》整个剧作的秦腔《人面桃花》,构成了剧情推进的一个隐性文本。刁大军和初恋对象桃花之间曾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恋,后来桃花嫁人了。韩梅嫁去的小山村正好在桃花的家旁边,刁大军时隔多年之后再次和初恋见面时,二人都已是半百老人了。难怪刁大军第一次回来去看《人面桃花》这场戏时,会感动得落泪。大雀儿一生凄苦,因为女儿,挣的钱从来不敢乱花。女儿丽丽小时候被米汤烫伤了脸,孩子慢慢长大了,有了自尊心。脸是人的颜面,人面桃花的脸大家都爱,大雀儿正是为了给女儿追求一张完美的脸,而把自己生生累死,令人不禁唏嘘人生无常。刁顺子、蔡素芬二人之间的爱情“苦情戏”,正是《人面桃花》中“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写照。于是,我们不难捕捉到内潜于现实文本结构中的戏剧思维,在不断强化人物与现实的冲突中迫使人物做出一次次的隐忍,彰显装台人的性格和精神内涵。
同时,装台人把“装台”矜持地看成一种艺术。像秦腔团的角儿挑顺子来打追灯一样,顺子也摆着谱儿让导演来请他。因为无论他人怎么认为“装台”就是“搭台”,顺子他们始终认为这是一份和艺术有关的工作。搭台、架灯、布光、做桃花布景一丝不苟,甚至秦腔唱词也能随手拈来。即使第一次在舞台上推车,哑巴就表现出了天才的艺术才能。月色下的废弃剧场中,墩墩和手枪,一个忘情地跳着钢管舞,一个投入地打着红拳,艺术的世界和生活的世界相互交融。这些艺术与人生的精神同构,升华了生活本身所蕴蓄的复杂内涵,在隐喻人的生存状态的层面具有了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性。
在剧中,艺术的人生化通过原汁原味、带着生活毛边的百姓故事,传递出一种“心里富有,不跟生活认怂”的精神氛围。电视剧将时代舞台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寓于人情冷暖、世道人心的故事文本中,展示给我们一幅既有现代气息又不无人间烟火味的生活百态图。除了雁塔、钟鼓楼、古城墙等极富地域特色的标志性建筑外,该剧还向观众展现出古城西安乃至整个陕西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一面。剧中的刁家村作为现代都市中的城中村呈现在荧屏上,曲里拐弯的街巷、破旧但聚人气的院落,看起来有些拥挤,红红绿绿的灯箱和小店招牌以及热气腾腾的街边美食让人感到亲切。电视剧一开始,黑撒乐队的一首《陕西美食》中一段“报菜名”式的说唱,锅贴、凉粉、酸菜、炒米、春卷、醪糟、三原熏鸡、酸汤饺子,各种美食无不让人垂涎三尺。吃饭用盆、油泼面配蒜、蹲着吃,这既是正宗的陕西美食吃法,又体现了陕西人家的地道烟火气。因此,剧中没有城乡的二元对立,也不存在对现代城市的简单否定,这些烟火气的美食唤醒人们对精神故乡的记忆,通向了一个艺术的想象空间。于是电视剧超越了对城市底层人的同情,在“非现实性”的精神故乡建构中,具有丰富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反思。
从情节主线来看,一条线是刁顺子的家庭故事与秦腔团的社会故事相互糅杂,呈现出一种拨云见日的大开大合的气势。该剧并未因对苦难的深刻描写而落入苦情戏的俗套之中,而是通过对叙事节奏的巧妙把握,在一张一弛、跌宕起伏间让观众感受沉重现实中那些温情而美好的生活亮色,给人以克难奋进的精神动力。遭遇“家庭大战”后,顺子骑着三轮载着蔡素芬徜徉在田间街头,生活中的鸡飞狗跳被眼前的舒心与惬意所冲淡;秦腔团进京汇演,车队路遇碰瓷被人讹钱,但进城后又遇上好心的警察,一路护送他们到演出地点;哥哥刁大军风光一时却败光钱财因病去世,但他最后的时光有亲朋照顾陪伴,侄女刁菊花也与二代成婚,诞下了新的生命。生活的磨难与琐碎里蕴含着暖暖的人间诗意,葬礼伴随着婚礼,死亡迎来了新生。整个电视剧叙事节奏张弛有度,细微之处展现出一种新时代人间百态的社会大气象,在世情悲欢中尽显平凡生活的温暖亮色。
另一条线是刁顺子的家庭命运与秦腔团的社会命运相互参照。瞿团长用心张罗,铁主任四处寻找商业汇演的机会,用以解决秦腔团的经费问题。还有靳导演坚持自己的艺术标准,一次次向领导提出自己的意见和主张,申请经费,哪怕和领导闹翻也在所不惜。秦腔团刚上演《人面桃花》时没有观众,大伙束手无策,疤叔通过涨房租的压力实现了剧场观众满满的效果。最终,秦腔团在煤老板的赞助下,得以赴北京参加汇演,并一举获得成功。可以说,秦腔这个古老的文化艺术,通过现代企业的资助而得以发扬,这是传统文化传承的一种思路,也潜在地表达了对秦腔这门艺术难以为继的一种忧虑。然而刁顺子的手机铃声是秦腔,路边的黑总对秦腔也是随口就来,铁主任的妻子对秦腔痴迷有加,更有二代的梦想就是站在舞台中心当一个秦腔的角儿,这些都体现了以西安市民为代表的秦地文化之魂,也是复兴秦腔文化的未来希望。
于是,日常艰难中见希望,个体生命的追求与传统文化的走向互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波纹圈层的扩散结构。其实,刁顺子一群人赖以谋生的行业“装台”,本身就具有冷酷复杂的现实多义性。在人生的舞台上,刁顺子等人在给别人装置舞台时也完成了自己的生命表演,善良、忍让、责任,构成了他们台上台下的生活哲学。这些底层个体之间的温暖与情怀,给观众以生活的信心与希望,却没有将观众引向生命沉重的思考,而止步于表现他们的烟火世界。蔡素芬果断地离开两个男人的纠葛后,本可以表现她作为一个女性的主体追求,结尾却还是回到刁顺子的身边。剧中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细节都很接地气,观众在惊叹之余感受到更多的是生活的真与情怀的暖,而非个体生命价值的理解。世俗情怀的喜感氛围中,电视剧给观众以形而下的生活希望,一定程度上缺少了形而上的生命思考。
遭遇市场经济的冲刷后,秦腔等高雅艺术如何生存?这也是电视剧在表现装台人生之下的潜在反思。一方面电视剧除了选择刁家村这样的生活空间,表现秦腔艺术等传统文化的良好群众基础,还以舞台表演为辅线,串出《断桥》《杀狗》《赶坡》《斩单童》等一系列秦腔曲目,与装台人生的命运构成互文状态,将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现在观众面前。另一方面,电视剧又直面传统秦腔艺术的生存境遇,书写市场经济下传统艺术的尴尬及其悲壮。正如剧中舞台落幕,观众散场之后,靳导演久久注视舞台不忍离去。落寞的人、落寞的舞台成为落寞文化的隐喻。秦腔团缺经费、少观众,需要铁主任外包经营、搞活市场来获取剧团的开支,最终只能通过煤老板的经费支持实现进京演出。尽管这并非理想,但电视剧试图在秦腔艺术日渐衰微的尴尬状态中,通过装台人生的独特视角,寻找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可能路径。
可见,无论是装台人生命运的沉重与乐观,还是传统秦腔艺术氛围的营造与尴尬,最终都化为普通人的世俗生活与烟火情怀。这些问题弥散在剧中,于艺术与人生的互文状态下形成一种内在的张力,体现了导演对这些底层个体和传统文化命运的困惑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