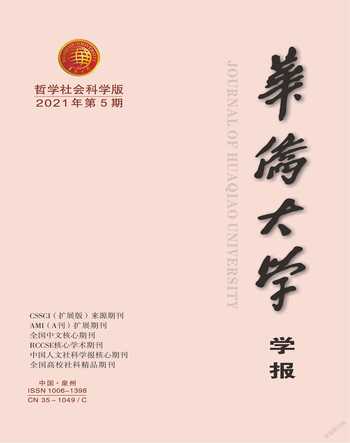剖析种族主义的思想利刃:霍克海默、阿多诺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吸收运用
许秩嘉 姜延军
摘 要:在对纳粹主义的批判中,霍克海默、阿多诺开创性地将精神分析吸收融入批判理论,建立了种族主义的分析图式,发现了种族主义的逻辑根基,构划了种族主义的瓦解路径,为法兰克福学派对精神分析理论持续几十年的深化整合奠定了思维框架、价值准则、实践旨趣,也为其持续不断冲击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逻辑埋下了祸根。霍克海默、阿多诺在整合精神分析中形成的种族主义批判视镜能帮助我们看清新冠疫情危机中部分西方国家种族主义肆虐现象的心理结构与经济本质,在反面镜鉴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汲取坚定的民族团结力量。
关键词:霍克海默;阿多诺;种族主义;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许秩嘉,哲学博士,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E-mail: jarvishsu@sina.com; 上海 201600)。姜延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1)05-0014-11
几千年来,“理性”始终是人类理解和解释历史前进动力的根本着眼点,从古希腊哲学对作为世界本源与人之本质的“理性逻各斯”之探索,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世俗化、人本化的思想解放中对理性精神之强调,再到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类控制自然、改变世界的理性能力之提升,“理性”越来越成为人类极致推崇与信赖的精神支点——人类相信可以凭借理性获得自由自律的生存,相信理性之发展即是人类价值之确证,相信理性是一切行为活动的最高评判标准。然而,进入20世纪以来,人类不仅没有因理性的高度发达而走入被许诺的幸福天国,反而在征服自然中遭到了报复,在发展科技中沦为了科技自律力量之奴仆,在种族屠戮中走向了自我毁灭的边缘。因此,生命哲学、唯意志论、精神分析等非理性主义思潮获得了快速发展。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开创者,霍克海默、阿多诺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对精神分析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出于对精神分析的兴趣,霍克海默早在大学时便选择心理学作为专业方向,并于1927年鼓励阿多诺撰写了一篇分析精神分析与超验现象学之关系的论文。随后,霍克海默选择弗洛伊德的学生卡尔·兰道尔(Karl Landauer)作为自己的精神医师,治愈了长期困扰自己的语言障碍症。1929年,霍克海默说服并帮助兰道尔建立了法兰克福精神分析研究所,吸纳弗洛姆等重要人物入会成为永久成员,极大地扩大了精神分析的影响力,也因此收到了弗洛伊德本人的两封致谢信。详见:[美]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1950)》,单世联译,广州:廣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4页。。1932年,在《社会研究杂志》的创刊号上,霍克海默发表了《历史与心理学》
一文,系统论述了心理视角对构建批判性的“社会哲学”的重要意义:“因此,人类理论与各种哲学人类学一起从静态本体论转变为生活在确定的历史时代中的人类心理学。”Max Horkheimer,Betwee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Selected Early Writings,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3,S113.在他看来,文化领域的相互独立性及其变化规律必须借助心理学才能得到掌握,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必须经由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的视角整合才能得到真正透析。因此,精神分析理论是“社会研究所和精神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但一直没有得到适当利用的工具”[德]贡尼、林古特:《霍克海默传》,任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3页。,弗洛伊德的思想“是我们的基石之一,没有它,我们的哲学就不会是这样。最近几星期我再次意识到他的伟大。”[美]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1950)》,第120页。阿多诺也就此在《社会研究杂志》创刊号上撰文。面对欧洲工人阶级对纳粹种族主义暴力行径的漠然态度,霍克海默、阿多诺试图借助精神分析来探索纳粹种族主义野蛮生长的群众心理根源,寻求阶级斗争隐而不发的心理因由:“于是,法西斯主义必须求助于情感需要,而不是理性意义上的民众利益——也就是说,它求助于原始的和非理性的愿望与恐惧。”[德]阿多诺,《权力主义人格》,李维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虽然霍克海默、阿多诺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吸收和利用要略晚于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展性—政治运动的赖希,但作为批判理论的创始人,他们在反犹主义批判中形成的精神分析整合逻辑塑造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非同一性”现实超越主题,为批判理论对精神分析持续几十年的吸收运用产生了奠基性影响。无论是弗洛姆的“社会性格”异化论,还是马尔库塞在批判“额外的压抑”中构建起的爱欲解放论,亦或是哈贝马斯在对精神分析的“深层解释学”定义中构建起的话语交往逻辑,都延续着霍克海默、阿多诺在整合精神分析中奠定的思维框架、价值准则、实践旨趣。然而,学界对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对话关系的研究普遍局限于赖希、弗洛姆、马尔库塞等典型意义上的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学界往往将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事实上,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并非指称某一特定学派,而是指综合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的理论思潮,其代表人物不仅有弗洛姆、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的骨干成员,还有奥地利的赖希、英国的奥兹本等非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代表人物,对霍克海默、阿多诺将精神分析引入法兰克福学派的开创性贡献缺乏充分关注。本文对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吸收运用精神分析理论中形成的种族(极权)主义批判逻辑作深入解读,以期获得对当前部分西方国家种族主义肆虐现象的肌理透视。
一 分析图式:经济系统←→人格系统←→文化上层建筑系统
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第二国际将文化上层建筑置于经济逻辑的绝对领导之下,使之沦为经济的僵化折射,失去了特殊的内在运行逻辑,似乎只需提及文化背后的经济属性就能够完成文化分析的全过程。但如果只关注文化的内在逻辑而不强调经济对文化的决定性主导,便看不清意识形态纷繁表象下的本质属性,从根本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轨迹。既然不能完全用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范畴来统一世界,将文化上层建筑视为对经济基础亦趋亦步的被动反映,也不能完全用黑格尔主义的“精神”范畴来统一世界,将客观世界视为主体精神的外化表现。那么,该如何调和客体必然性与精神能动性之关系,弥合经济与文化之间的断裂?精神分析理论很自然地成为了他们粘合这一“断裂”的最佳选择。1931年,在接任社会研究所所长的就职演讲中,霍克海默便提出社会哲学的核心关注应是“社会经济生活、个体心理发展与严格意义上的文化领域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德]霍克海默,《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王凤才译,《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123—129页。。通过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改造霍克海默、阿多诺虽然承认精神分析理论的巨大价值,但仍认为要对其作必要改造,强化其概念范畴的经济根基,剥离其个体主义外衣与唯心主义色彩,使其具备批判现实的超越维度,避免沦为服务资产阶级的、普世化的社会心理学。但在对精神分析理论之改造上,霍克海默、阿多诺与弗洛姆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只是在运用层面将精神分析推向经济社会领域,以此批判种族主义的心理机制,并不改变“性本能”的生物自然属性。而弗洛姆则试图从概念肌理层面上对“性本能”做广义的社会文化理解,其语境中的“本能”已脱离了纯粹的生物学色彩,更多指向文化学意义上的“存在两歧性”矛盾。弗洛姆的这一做法遭到了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会消抹本能与文明之间的天然冲突,压制个体与社会相对抗的驱力原则,削弱“性本能”的“非同一性”革命潜质。 ,霍克海默、阿多诺将人格系统引入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双向互动之中,逐步构建起“经济系统←→人格系统←→文化上层建筑系统”的分析图式:“一般的研究认为,人格是一种能动作用,社会对思想的影响是由它来中介的。如果弄清楚人格的作用,那么就有可能更好地了解哪些社会因素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以及它们以何种方式达到它们预期的结果。”[德]阿多诺,《权力主义人格》,李维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页。
首先,经济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心理形态,人在不同社会心理的驱动下选择了不同的文化上层建筑。霍克海默、阿多诺虽致力于运用精神分析对反犹主义心理结构开展深入解剖,但始终没有脱离孕育心理人格的经济土壤:“自由主义者将历史解释为孤立个体和他们不变的心理本质力量的交互作用。然而,如果根据人类社会生活过程发生的各种方式来划分历史,那么具有根本历史意义的是经济而非心理。”Max Horkheimer,Betwee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Selected Early Writings,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3,S118.在他们看来,德国民众之所以会对犹太人产生普遍的嫉妒与仇视情绪,根源于日耳曼人因一战战败及经济大萧条而生的脆弱民族自尊心。纳粹用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满足了日耳曼民族的自恋需要,用“优秀人种”的傲慢姿态迎合了其受挫的民族情绪。若想扭轉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基础,必须强化人格结构的社会经济属性,改变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如果德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不发生根本转变,法西斯主义人格就会持续生成,继而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提供社会心理温床:“由于(人格中的)潜在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是以一种伪民主的形式强加于人们头上的,因此不知内情的人们还满怀希望带着它走向未来。可以预测,如果现存的经济模式仍然得到维持的话,人们会继续受此模式的影响。”[德]阿多诺,《权力主义人格》,李维译,第1 264页。
其次,社会心理虽然受到经济的支配决定,但仍具有相对独立的感性运作规律,因而文化上层建筑具有不与经济亦趋亦步的多元解释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认为,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传统马克思主义并未细致阐明这一“决定”的具体生成方式,因而也无法阐清艺术、道德、宗教、习俗、价值观等社会文化成分在特定历史截片中的相对独立性及复杂变化规律,导致马克思主义陷入了经济决定论危机。霍克海默相信,引入心理中介环节可以丰富这一“决定”的多元生成路径,激活历史唯物主义的感性张力与微观解释力,有效解释文化上层建筑的自主能动性与相对独立性:“人类的需求与欲望,利益与热情都随着历史进程而变化。心理学和其他历史辅助科学必须合力交汇,共同解释任何特定历史阶段的价值观及其变化。”Max Horkheimer,Betwee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elected Early Writings,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3,S33.人格系统虽然受到经济结构的根源支配,但仍具有自己独特的非理性运行规律。正因如此,在分析纳粹的精神控制手段时,阿多诺强调要突破经济视角限定,聚焦种族仇视心理的感性煽动过程:“在德国,随着社会内部的经济冲突,甚至单凭这个原因就可以确定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迟早的事;但是,纳粹领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似乎并不这样认为;相反,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时刻关注民众的心理——激发他们的反民主潜能,屈从于这种潜能,消灭异己。”[德]阿多诺,《权力主义人格》,李维译,第13—14页。
最后,在人格系统的中介下,文化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得到了精细合理的解释。人类历史的形态更替必然会受到固有文化因素之阻碍,即便生产方式的变革已经完成,对旧文化形态的心理依赖仍会“粘附”于新社会结构之上,以“精神水泥”的方式抵触社会变革:“文化的粘附性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即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出于对其所处社会境遇的整体考虑,发展形成了一种心理构造,而某些特定的态度在这一动态化的心理塑造中发挥着重要的角色。换句话说,文化态度的粘附性源自于人们对其的热切执着。”Max Horkheimer,Critical Theory: Selected Essays,New York: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2002,S65.霍克海默以对中国社会的祖先信仰分析为例霍克海默表示,中国的农耕种植生产方式是尊崇长辈的文化得以生成的经济根基,因为只有经历长年累月的经验积累才能熟知天象、时节以及植物生长特性,这构筑了青年人的谦逊和老年人的威望。这种老年人对青年人的优越感在代际传承中获得了扩大甚至神话,祖先因而成为了具有至高权力和智慧的神明化身,个体对祖先崇拜与感激的心理机制在宗教形式中得以形成。对祖先的尊崇为人们提供了面临重大抉择时的逃避空间,也可以使身处困境的人在对远古声音的倾听中获得心理上的平静与安全。社会的伦理教化功能通过祖先崇拜的心理机制得以贯彻,进而塑造了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的社会价值结构与文化形态。当新的生产方式试图改变固有的文化形态时,粘附于新生产方式的祖先崇拜心理便会抵触社会变革,促使人们甘愿为落后于经济生产的文化上层建筑“忍辱负重”。可见,如果不引入社会心理系统而只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笼统方式来分析中国的祖先崇拜文化,很难说清农耕生产方式是如何塑造该文化形态的,更难解释农耕文明意识形态是如何阻碍现代化生产方式之推进的。,形象解析了经济、心理、文化三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交互关系,继而证明:特定生产方式塑造了人们对特定意识形态(文化系统)的心理认同,继而从中实现了对自身的感性维护。阿多诺则详细分析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之“粘附性”的具体表现方式——纳粹视现实的社会心理结构为固有的、民族的生物本性使然,以此维护法西斯主义人格的稳定性,继而维护军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人格结构的概念驳斥了下列观点,即把个体的一致性倾向归因于他内部‘天生的’或‘基本的’或‘民族的’东西。纳粹断言:自然的和生物的特征决定了一个人的存在。”[德]阿多诺,《权力主义人格》,李维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页。当然,在人格系统的中介下,文化因素既是维护固有秩序的“精神水泥”,但若利用得当也完全可以成为“毁灭这个社会的诸种力量的组成部分”[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92页。,发挥革命性的反向助推功能。
综上,通过对经济、心理与文化三者关系的精细阐释,霍克海默、阿多诺构建了种族主义的分析图式,为法兰克福学派融合精神分析奠定了一个关键思维框架。在这一图式的影响下,学派中很多学者都将心理因素视为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的中间环节,以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例如,弗洛姆以“力比多结构”“社会性格”为核心概念,塑造了以“社会经济状况对意识形态的群体的本能结构发生的影响”[美]弗洛姆:《弗洛姆著作精选——人性·社会·拯救》,黄颂杰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7页。为焦点的文化—心理模式,为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基础逻辑值得说明的是,较霍克海默、阿多诺而言,弗洛姆对经济、心理、文化三者之间关系的阐释更为系统、深入、集中,影响力也更为显著。但从时间上看,弗洛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最早见于1932年发表的《分析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和作用——关于精神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笔记》一文,较霍克海默1931年就职演讲中对经济、心理、文化之关系的关注略晚一年。霍克海默作为社会研究所的开创者,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对弗洛姆之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
二 逻辑根基:“理性文明”对“内在自然”的同一性整合
霍克海默、阿多諾对理性走向自我毁灭的批判受到了非理性主义思潮尤其是精神分析的深刻影响,在《理性之蚀》《批判理论》和《启蒙辩证法》中都能发掘出精神分析的思想痕迹。二者对反犹主义的批判方式存在细微差异,但对其内在本质的认知是一致的,这集中体现在二者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在精神分析的启发引导下,霍克海默、阿多诺发现了种族(极权)主义的逻辑根基——“理性文明”对“内在自然”(inner nature)的同一性压抑使人在寻求变相发泄释放中被轻易地捕获利用:“文化向来都对抑制革命的感情和野蛮的本能做出过贡献。工业化的文化也是这样。工业化的文化所描述的,是人们只能忍受残酷生活煎熬的条件。个人应该把他的冲天怨气作为推动力,为他所怨恨的集体权力服务。”[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43页。这是资本主义新型异化奴役的心理文化根源,也是现代人陷入感性狂热与理性坍塌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基础。
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将人的心理图式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层,并将超我对本我的压抑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源。本我遵循快乐原则,追求自然欲望的释放满足,但超我遵循现实原则,它通过自我来对本我的满足进行适当压抑,进而将被压抑的力比多能量升华转移至对社会发展有用的活动中:“我们已习惯于说,我们的文明是以性倾向为代价建立起来的。该倾向在社会抑制下,一部分的确被压抑了,另一部分则可以运用于其他目的。”[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论》,郭本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03页。在超我对本我的压抑过程中,自我往往将压抑的命令伪装为合理化的需要植入本我的潜意识中,使个体甘愿接受被压抑的命运,放弃享受真实快乐的权利。超我同时会提供一系列的幻想满足来补偿本我欲望,让本我在虚假满足中放弃抵抗。文明之演进必然以牺牲个体快乐之满足为代价,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超我力量对本我欲望的压抑史。
霍克海默、阿多诺继承了弗洛伊德的文明观,他们从中敏锐洞察到弗洛伊德语境中的超我对本我之压抑,实质上就是社会同一性对个体非同一性的统摄控制,也是代表文明的理性力量对“内在自然”的驯化奴役。文明意味着将每一个分散个体凝聚其中的社会秩序,意味着对自然本性的奴役与对个体特征的仇视。在文明力量的整合中,人获得了融入社会秩序的“同一性”入场券,却也牺牲了内在自然本性:“种类的同一性却限制了情况的同一性。文化事业恶毒地使人体现为类本质。每个人只是因为他可以代替别人,才能体现他的作用,表明他是一个人。”[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36—137页。因此,在霍克海默、阿多诺眼中,弗氏人格结构理论的贡献不仅在于发现了社会理性与自然本能间的分裂远离,更在于呈现出前者对后者开展同一性整合的欲望和方式。从这个角度上说,他们对理性与同一性逻辑的批判是对精神分析文明观的进一步深化阐释。
为具体解释理性对“内在自然”的压抑过程,霍克海默、阿多诺以精神分析的概念为基点,进一步提出了“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和“自我毁灭”(self-destruction)的概念,认为二者之间的趋同是文明社会中超我压抑本我的必然结果。“自我”作为自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碰撞交汇场域,始终挣扎在超我与本我的对抗间隙中,因而自我是虚弱无力的矛盾化角色,这种矛盾使得“自我保存”必然伴随着“自我毁灭”——自我为了获得社会的认同进而获取生存资源,必须遵循超我的要求来约束和监督本我,放弃本我之欲望满足,按社会的理性规则来塑造“同一性自我”;此时,自我的“自主”功能被“自保”功能所取代,同一性逻辑通过虚弱的自我被注入个体的人格基因里,自我放弃了个性化的欲望冲动,为文明的理性整合开辟道路;超我的理性规则在压抑本我的感性冲动中塑造了“同一性自我”,消解了自我的自主性,因而也掩盖了个体与社会的对立性,平息了主体的反抗欲望;在此,“自我保存”获得了实现,但其代价却是“自我毁灭”:“那种对人的惊讶反应,是古代维持自我生存的模式:生命是通过部分死亡而得到维持的。”[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71页。
人类为了自我保存而必然要走向自我毁灭,这一悖论在霍克海默、阿多诺对《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的解读中获得了形象清晰的阐释奥德修斯是史诗《奥德赛》中献木马计攻克特洛伊城的主角。战后,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泊异乡,经历千难万险,克服了各种诱惑。他拒吃海波利翁之牛,让水手们将自己牢牢捆在船桅上以抵制女妖的歌声诱惑,同时要求水手们用蜡堵住彼此的耳朵进而全力划桨。通过遏制自然本能的满足,奥德修斯和他的水手们活了下来,获得了胜利的荣誉,最终得以返回故乡。。奥德修斯“既反对自己死亡又反对自己幸福”[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29页。,这一神话中的矛盾境遇无疑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命运隐喻。人类为了拥有生命的延续而必须放弃生命的本能,为了获取“外在自然”的资源而必须牺牲“内在自然”的满足。在理性文明的发展推进中,同质化的社会秩序领域不断扩张、异质化的个体自主领域不断缩小,个体的幸福满足沦为了社会整体满足的牺牲品。然而,被压抑的自然本能欲望并未真正消逝,而是被挤压在潜意识之中,愈渐形成了对文明本身的怨恨。法西斯主义则充分利用了这一怨恨,使群众在种族主义狂热行径中获得了自然本能力量的报复性发泄释放:“一旦共和国的理想和原则与代表更强大势力的经济力量之利益发生冲突时,极权主义的鼓动挑拨便能轻而易举地实现。希特勒暗示他可以缔造一种力量,以此名义来解除对被压抑的自然本性的禁令,这迎合了其受众的潜意识。理性的说服永远不会如此有效,因为它与表面上文明之人的压抑原始冲动并不相称。”Max 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London·New York: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2004,S81.“自主性自我”被“同一性自我”控制、非同一性逻辑被同一性逻辑掩盖、内在自然被理性文明压抑,这是霍克海默、阿多诺眼中弗洛伊德文明观的精髓要义,也是其在精神分析的启发下发觉的种族主义逻辑根基。
霍克海默、阿多诺不仅从精神分析中找到了种族主义生成的心理学秘密,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在对精神分析的非同一性改造中为内在自然反抗理性文明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一方面,他们规避了弗洛伊德中后期理论中关于构建协调本我与超我之强大自我的同一性理论倾向,认为这种所谓的协调不过是自我在意识形态欺骗话语下构建起的对超我的新型顺从,致使精神分析沦为了消解解放意志的安慰剂。因此,他们吸收整合的主要是弗洛伊德早期的潜意识结构论、性本能动力论、成长与固着论、梦的解析论,从中找寻控诉同一性驯化的心理学支持,获取揭穿虚假意识的真实视镜,强化自我的自主性、保护个体的异质性、恢复世界的流变性:“弗洛伊德初期的理论表明,在给定的熟悉和普遍的社会条件下,社会禁忌适用于阻止人的本能发展,以使之回归至虐待狂层级。他的部分驱力理论、压抑理论、矛盾心理理论等等,对于从心理层面理解我们在此讨论的(仇恨与残暴的形成)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弗洛伊德本人并不在细节上追求其理论的运用。”Max Horkheimer,Betwee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Selected Early Writings,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3,S104.另一方面,如前所述,霍克海默、阿多诺坚决反对弗洛姆等人对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处理,要求在生物的原初意义上理解性本能,认为这是对抗理性整合的非同一性源泉所在。
综上,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对精神分析的启发借鉴和批判性整合中揭开了理性文明走向坍塌的心理面具,发现了纳粹种族主义的逻辑根基,形成了批判理论的重要价值准则:用内在自然的本能力量反抗理性文明的驯化奴役,反思压抑性文明的种族主义恶果,抵制资本主义社会的同一性逻辑。在这一价值准则的影响指引下,法兰克福学派很多哲学家都致力于运用精神分析开展相似的批判。例如,马尔库塞将人的自然本能理解为作为性欲升华之“爱欲”,并以此为基点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爱欲的“额外的压抑”,试图通过解放爱欲来构建非压抑性的文明;哈贝马斯则在对精神分析的“自我反思”化理解中提出了以兴趣为基础的认识论模型,并在对精神分析的“交往资质”化还原中打开了以主体间性为核心的交往行动理论端口,以此来批判工具理性所调节的“系统”(system)对交往理性所调节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之话语殖民。而无论是“额外的压抑”下的爱欲解放还是“话语殖民”下的交往行为合理化,本质上都遵循着反抗同一性压抑的价值结构,表达着对种族主义逻辑根基的强烈抵制。
三 瓦解路径:解蔽意识形态的虚幻满足
既然种族主义的逻辑根基是理性文明对内在自然的同一性压抑,那么该如何反抗压抑、瓦解根基?霍克海默、阿多诺表示,纳粹种族主义释放并利用了被理性文明压抑的内在自然力量,但也彻底摧毁了理性文明。真正应该反抗的是理性对自然本能的同一性奴役,而非理性自身。在野蛮的感性狂热中,内在自然获得的并非真实的满足,而是一种替代性的虚假满足,一种更为严密的同一性奴役。虽然资本主义文明对内在自然施与了极权高压,但种族主义狂热和文化工业享乐却为现代人提供了发泄欲望的替代性窗口,遮蔽了阶级剥削对现代人的残酷压抑,抹平了人的反抗欲望,在民众心理层面构筑起征服非同一性的虚假同一性:“一直寻求营销舒适与幻觉的文化工业,已从耗尽现代主义的欲望冲动中获益。”Theodor W. Adorno,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London·New York:Taylor and Francis e-Library, 2005,S24.因此,只有从心理层面揭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满足”内在自然的虚幻方式,才能真正反抗理性的同一性奴役、瓦解种族主义的逻辑根基,使內在自然获得真实的满足。鉴于此,精神分析作为一种识别虚假意识的“去伪存真”理论弗洛伊德对意识的真实性始终抱有怀疑,因而才开始挖掘被压入潜意识深处的真实欲望驱动,试图使人挣脱合理化思想体系的虚幻欺骗,在认清并接纳真实欲望后获得改造自我的勇气与力量。,无疑能够帮助识别这些“满足”内在自然的意识形态符码,解蔽虚假满足的心理运作机制。精神分析理论可以清晰展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掩盖利益失衡、提供虚假满足、消解反抗意识的心理路径,而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从经济层面解蔽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有力补充:“如果人类被剥夺了对被压抑的物质资源的补偿,那么在幻想中给人以尊重和成功的集体主义认同就变得极为重要。如果心理学可以证明这种心理满足的真实强烈性并不亚于物质满足,那我们对多种多样的世界历史现象的理解将极大增强。”Max Horkheimer,Betwee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Selected Early Writings,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3,S125.
具体而言,霍克海默、阿多诺以弗洛伊德关于“虚弱自我”“自恋情结”“俄狄浦斯情结”在希腊神化中,俄狄浦斯王子虽极力逃避神谕的诅咒,但却最终在不知情的前提下阴差阳错地杀父娶母,难逃命运的摆布.弗洛伊德用“俄狄浦斯情结”来说明男孩在童年“性器期”形成的恋母与憎父的潜意识。这种潜意识是儿童性欲发展的高潮也深刻影响着性心理与人格的形成。的心理学论述为切入点,剖析包括种族主义在内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欺骗手段。如前所述,在理性文明对内在自然的同一性压抑中,自我承受着超我和本我的双面夹击,因而其精神能量往往较为虚弱,自主功能低下。一个虚弱的自我在面对外在高压时十分渴望得到保护,因而极易受到心理暗示和动员操纵,使潜意识中对父亲的两难情感被纳粹种族主义捕获利用: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使家庭中传统的父亲权威日渐衰落,儿子对家庭权威的崇拜感降低,但并未因此形成强大自我,仍渴望一个强有力的外在权威来作为虚弱自我之精神庇佑,纳粹领袖则趁机化身为全能父亲的替代物,诱发个体对其产生父亲般的移情投射与情感依赖;另一方面,纳粹领袖利用反犹运动、反共运动将压抑在民众精神深处的父权憎恨从领袖转移至血腥暴力的破坏性活动中,促使民众在狂热的敌对情绪中宣泄了长期被文明压抑的自然本能,进一步加深了其对极权领袖的癫狂崇拜;更为严重的是,当虚弱的自我面对被压迫的奴役境遇时,往往会出于自尊考量而主动美化奴役行为,将剥削者神圣化进而使压迫行为合理化,以此缓解潜意识中的自卑感、无助感和屈辱感——剥削者的形象越是高大神圣,自己所受到的奴役和压迫越是容易得到释然,自尊保护与自恋满足方可获得实现;最后,文化工业无孔不入地渗透则使现代人进一步跌入了无底深渊——报纸、广播、电影、电视、流行音乐等通过塑造的成功人士、魅力明星进一步将民众的权威诉求从家中父亲转向社会“父亲”,通过对奢靡生活的广告宣传、明星轶事的猎奇刺激、幸福浪漫的影音造梦使民众被资本的谎言世界所催眠,沉迷于混淆幻想与现实的错觉系统之中,仿佛大众传媒呈现的世界即是真实世界,继而获得了对被压抑自然本能的幻觉化满足,“幸福地”享受着统治阶级对自己的实际压抑:“它(文化工业)通过一再忠实地重复迷惑视线的现象,不断地把现实的现象美化为理想,而轻巧灵活地克服重大的错误信息与公开的真实情况之间的矛盾。”[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38页。
总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拥有为被压抑的内在自然提供虚假满足的欺骗功能,个体在极权朝拜、种族敌视和虚幻享乐中保护了虚弱自我、转移了父权憎恨、维护了自恋情结,因而被轻而易举地整合到同一性的社会强制系统中:“理性现在通过将自然本能的反叛潜力纳入自己的系统来利用自然本能。纳粹操纵了德国人民被压制的欲望。”Max 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London·New York: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2004,S82.精神分析理论揭示了“虚假满足”的心理生成路径,继而能够唤醒内在自然对真实满足的渴望,为瓦解种族主义的逻辑根基提供革命性的反抗指引。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吸收精神分析中开拓的这一反抗路径对很多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革命实践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批判理论整合精神分析的实践旨趣。例如,弗洛姆将语言、逻辑、禁忌视为社会的“三重过滤器”,认为它们都受到意识形态的指令性编码,将与其意志不符的思想信念压抑至“社会无意识”中,先在地塑造着人的认知经验。唯有建立起思维层面的“理性怀疑”,开展深层的自我意识革命,才能挣脱意识形态的骗局,冲破幻想满足的迷雾,获得挣脱“锁链”的真实力量。
四 双重视镜:当代种族主义乱象的肌理透视
综上所述,在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开创性吸收运用中,霍克海默、阿多诺建立了种族主义的分析图式,发现了种族主义的逻辑根基,构划了种族主义的瓦解路径,对法兰克福学派与精神分析理论持续几十年的整合交织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霍克海默、阿多诺的精神指引下,弗洛姆、马尔库塞、本雅明、哈贝马斯等人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踏上了吸收运用精神分析的理论征程,并因精神分析自身的学派分裂及对其的理解分歧而形成了多样化的整合路线:弗洛姆从修正主义的精神分析出发,构建基于“社会性格”异化的心理—文化革命论;马尔库塞从泛性欲化的“爱欲”本能出发,构建破除“额外的压抑”的爱欲解放论;本雅明从精神分析的潜意识梦境结构出发,通过碎片化的隐喻意象来传递现代性救赎理想,构建起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隐秘链接;哈贝马斯则从对精神分析的解释学理解出发,构建基于“自我反思”的认识论模型及基于这一模型的交往理性反殖民论……
无疑,精神分析为法兰克福学派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思想利刃,赋予其洞悉社会历史深层结构的心理透视力和犀利穿透力,也确实在一定意义上从微观层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解释力。但霍克海默、阿多诺对精神分析的开创性引入也使批判理论在发展中始终穿梭着挣脱历史唯物主义轨道的游离因子,降低了对历史发展之客观必然性作科学分析的理论侧重。很显然,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引入精神分析之时就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始终强调心理因素的经济属性,试图将精神分析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框架之下。但无论其如何强调,精神分析对意识内在机理的侧重性关注都会在客观上弱化经济的宏观分析视角,在现实运行中将客观社会冲突转嫁至主观心理范围,使人远离政治经济维度,只关注意识与意识形态层面的升华解放,从而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效能。在这个意义上说,霍克海默、阿多诺引发了精神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空间场域中的“蝴蝶效应”,为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对精神分析持续几十年的深度吸纳整合打下了地基,也为其持续不断冲击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逻辑埋下了祸根。
即便如此,我们仍需看到霍克海默、阿多诺此种理论选择的时代背景支撑,看到其批判理论在跨学科整合中所获得的优越特質,这也是今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应重点关注的问题域。更为重要的是,霍克海默、阿多诺吸收运用精神分析理论而形成的“经济—心理”批判视镜对我们透视今天部分西方国家种族主义肆虐现象仍有极强的适用功能与借鉴意义。
在新冠疫情危机中,种族主义情绪在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异常高涨,种族主义活动愈演愈烈。这一方面表现为部分国家内部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政策歧视加剧、暴力冲突频发。例如,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公布的数据,截止2020年8月1日,美国18~49岁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群中,拉美裔、非裔和白人所占比例分别为38.5%、22%、28.6%https://covid.cdc.gov/covid-data-tracker/#demographics,而这三个人种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为16.9%、13.4%、62.1%外交部2020年4月数据,参见: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这说明,疫情对美国有色人种的影响要远高于白人。这一数据折射出当前美国有色人种在医疗卫生、居住与就业环境等方面较白人存在显著劣势的失衡现实,这也是全美范围爆发“黑人的命也是命”等黑人人权运动的社会现实根源。另一方面,当前种族主义肆虐还表现为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平崛起的零和博弈心态,试图用人种优势论、文明冲突论来遏制其他国家的发展复兴,用冷战思维来维护自己的霸权利益。
借助霍克海默、阿多诺的种族主义批判视镜,我们不难分析出当代种族主义现象背后的深层心理结构与经济现实——当前种族主义肆虐的根本原因在于,特定国家、阶层、团体在资源竞争中日渐难以维系不合理的特权经济秩序,因而产生了强烈的自我价值认同危机,以及不安、嫉妒、焦虑、愤恨的社会情绪与脆弱心境,进而对“非同一性”的包容度大幅下降,试图用种族主义话语来维护“自恋情结”,转移内在矛盾,维护霸权利益;代表资本特权利益的政客迎合了所谓“白种人”“美国人”“西方人”的自恋心理需求,用种族主义行径来投射压抑情绪,营造狂热崇拜,输出虚幻满足,从中快速积累政治威信克服眼前危机。
具体而言,一些西方国家内部的种族歧视现象根源于部分白种人维护特权利益,转移内部矛盾的霸权心理。近年来,有色人种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给其中下阶层中的白人群体(白人蓝领)带来了显著的就业竞争压力。而拉美裔与非裔移民的生育率要显著高于欧美白人的生育率,这进一步提升了中下阶层白人的资源焦虑。种族主义话语的高调抬头则是这一客观经济现实的意识形态反映,它用“白人至上”的傲慢来安抚特定群体在竞争中受挫的自尊心,用虚幻的话语满足填补其现实中的利益损失——似乎他们无法获得体面生存的原因不是自己能力不足或不够勤劳,不是白人资本家的剥削压榨,而是“劣等民族”“不择手段”地抢夺入侵。部分西方政客迎合了这一庞大群体的社会心态,用隐性的种族主义政策来收割狂热的政治支持,通过损害有色人种的利益来偏袒白人群体,恢复固有的白人特权秩序。
当前,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的种族歧视现象则根源于:一部分西方人为维护自身特权利益而转移国内矛盾的霸权心理。近年来,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腾飞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的特权经济秩序受到冲击。加上资本主义体制问题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部分西方国家经济形势下滑,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尖锐,自身的特权空间被快速压缩,制度与意识形态合法性遭受质疑。面对这样的现实,一些西方右翼政客利用了民众在劳动中积压的焦虑愤恨情绪,将之转移至“中国人”身上——似乎其不景气的生活状况不是资本主义的体制机制问题,不是大资本家长期霸权殖民的必然恶果,而是中国人搭了“顺风车”却“不择手段”地抢走了他们的饭碗。在这样的背景下,诸如“美国第一”“领导世界”“中国威胁”等傲慢论调自然非常容易赢得西方民众的非理性支持。种族主义情绪一方面安抚了部分西方人的自恋心理,满足了他们的“优越幻想”及脆弱自尊心;另一方面,这种意识形态话语反过来服务于特定人种的经济霸权利益,为一系列逆全球化的不公正经济规则造势。种族主义的此般心理与政治逻辑在新冠疫情中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境地——面对自身防疫失利的被动局面,部分西方政客借机进一步煽动种族主义情绪,通过病毒政治化的方式“甩锅”中国,激发其国内民众对华人的仇视偏见,试图以此来转移国内矛盾,减缓民众对其防疫失利事实的关注,并在狂热的情绪营造中为自己收割选票。
借助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反犹主义的双重批判视镜,我们不仅能够看清当代种族主义现象背后的心理与经济根源,还能够解码当代种族主义从外在殖民走向内在殖民的意识形态轨迹,即一种获得了合法化身份的“内化种族主义”如何得以生成。“内化种族主义”是种族主义不再停留在外在歧视与压迫范畴,而是潜入了被殖民压迫族群的深层人格系统之中,促使被压迫者心甘情愿地接受“低人一等”的被奴役命运,甚至主动地美化剥削行为,赞美骑在自己头上的特权人种,丑化自己的人种族群“内化种族主义”现象广泛存在于殖民历史之中,很多被殖民者会莫名产生对殖民者的强烈文化认同与情感链接,主动地贬低自身。这一现象在当代一些移民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中也并不罕见。今年美国黑人人权运动中桂格燕麦公司旗下品牌“杰米玛阿姨”和高露洁公司旗下品牌“黑人牙膏”的更标更名即是一种对内化种族主义的觉醒与反抗。。此时,种族主义获得了更为隐蔽的奴役空间和更为精美的合理化包装。运用“经济系统←→人格系统←→文化上层建筑系统”的分析图式不难知晓,这一现象显然诞生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对特权经济压迫的反向维护中。只是,这一“维护”不是直接发生的,而是经过了社会心理的中介——特权种族通过大众传媒等意识形态机器对被压迫种族进行思想文化控制,定向塑造不同种族的脸谱化形象,同时用所谓的“普世价值”“世界公民”来掩盖种族间的压迫事实;被压迫种族在长期的强权压制下往往为了维护自尊而欣然接受了对特权种族的意识形态美化,从中获取对自身被压迫命运的合理化安慰;在这一过程中,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将“奴性”潜移默化渗入了被压迫种族的心理结构中,使其意识不到被剥削奴役的现实,进一步维护特权种族的经济统治秩序。
种族主义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意识形态反映,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一天得不到根本扬弃,种族主义现象就一天不会消亡。新冠疫情仅是种族主义愈演愈烈的导火索,霸权主义与种族冲突并不会随着新冠疫情的结束而结束。并且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演变升级,种族主义现象将会随之升温,加剧全球的政治极化生态。2020年年底的美国大选纷争俨然演变成为了一场不同种族之间的内耗斗争,而法国中学教师塞缪尔·帕蒂遭伊斯兰移民斩首,东京奥运会种族歧视“槽点”频发等热点事件则进一步强化了种族主义问题的世界性扩散。习近平说:“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讲。运用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思想方法,基于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双重视镜,我们得以深入解剖西方种族主义肆虐现象的问题根源与生成机理,准确把握种族主义的发展动向与历史趋势,在反面镜鉴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汲取坚定的民族团结力量。
更具建设性的考量是,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历史唯物主义宏大叙事的微观“补充”和对种族主义“同一性”压抑本质的犀利洞察能够为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建设发展提供必要的警醒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凝聚着全世界华夏同胞的共同价值追求,彰显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创造着浩浩汤汤、一往无前的壮阔时代洪流。同时应清醒的是,宏大的历史必然性叙事总是容易造成对个体、边缘、差异、少数的掩盖忽视,降低社会系统的多元包容力。新冠疫情在我国刚爆发时暴露的“吹哨人”制度问题和部分患者在出院后受到的歧视现象便反映了值得我们警惕规避的“同一性”弊端,启迪我们在凝聚“共性”的基础上关注“个性”,追求同一与差异、宏观与微观、集体与个体的有机统一。
A Critical Weapon of Racism:
the Absorption of Psychoanalysis by Hockheimer and Adorno
XU Zhi-jia, JIANG Yan-jun
Abstract: Through criticizing of Nazism, Horkheimer and Adorno pioneered introducing psychoanalysis into critical theory, establishing the analysis scheme of racism, discovering the logical foundation of racism, constructing the path to disintegrate racism, which not only laid the ideological framework, value orientation and practical pursuit for Frankfurt School’s deepening integration of psychoanalysis for decades, but also buried a curse for its continuous impact on the essential logic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owever, their critical insight in absorbing psychoanalysis can still help us to see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essence of racism in some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current COVID-19 crisis, and to draw firm strength of national unity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opposite.
Keywords: Horkheimer; Adorno; racism; psychoanalysis; Marxism
【責任编辑 龚桂明】
3462501908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