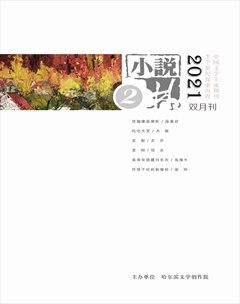狂怪不经的杨维桢
前后四十五年,动用百万大军,从中国北方的草原杀出,一路南下,最终在1279年灭掉了南宋,蒙古人取得了中国历史上元朝的统治权。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显然对中原汉人缺乏善意,把这部分南宋移民打成社会底层,大部分文人对命运的无常都选择了苟且行世,有民族气节的一类人,不是自杀就是被杀,或者成为山林中的隐者,还有如赵孟頫一样的做了降臣,并得到了当政者的优待,进入了元代统治机构,官至一品,还能掌握一定话语权,这并不容易。
在元代中前期,赵孟頫一统江湖,成为文坛带头大哥,赵孟頫的书法流畅雅致,代表了有元一代的文艺风尚。赵孟頫的艺术追求可以视作王羲之在元代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短暂的元代中前期,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书法家,几乎就是赵孟頫一人而已。
这种显现的表象一直持续到元代晚期,浙江绍兴一个年轻人在家乡的阁楼上经过五年的奋发苦读,终于从一座堆满典籍的藏书楼走了下来。为了建造这座读书楼,父亲卖掉了他心爱的良马,购置了古籍善本,只求他能在圣贤书中读出一条阳关大道,而后出人头地。这个年轻人极力配合父亲望子成龙的愿望,具备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发奋图强,废寝忘食,阁楼里旁人不得入内,父母想见他一面也十分困难,三天之内,只可见上一面,且不超过一炷香时间,饮食等生活必须品都是用一种传送带装置运送上去,这个小发明创造,主要是不想被人打扰他的读书,否则耽误考取功名,谁来负责?如此五年,自觉学有所成。
当这个年轻人走下阁楼,手里拿着他酷爱阅读的《春秋》,用旷世金石之音横扫了陈腐平庸的元代文坛,人之望而畏,成为新一代文坛盟主,此人便是杨维桢。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又号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梅花道人等,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狂放不羁、秉性高洁、孤傲倔强的杨维桢是元朝末年的江南文坛沙龙文化的重要人物,一些文学史的撰写者认为杨维桢代表了元诗之变的极致。
元代因为统治阶级主观上不重用南宋儒生为代表的遗老遗少,实行民族分化的等级政策,把民族作等级划分:蒙古为首,色目次之,契丹第三,“南人”在四种等级之中排名最末,又称南蛮,实为贬称。在民间社会的十类人的划分中,甚至有九儒十丐之说。“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这是宋遗民郑恩肖在《心史》中所记。而同是宋代遗民的谢枋得也说:“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如果真像谢枋得所言,元代的儒生士人介乎于妓女和乞丐之间,是何等卑微!“南人”之中的知识阶层成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群体。
但客观上元代的民族分化政策的客观影响,在文艺领域显现出另外一种意外的结果,不受政治干预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潮流在民间涌动,其中有追求的文艺人实现了自己的艺术价值。在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之下,嘉兴吴镇、无锡倪云林、常熟黄公望和会稽杨维桢,形成了元代晚期的文化图景。杨维桢在诗歌写作中以“情”为主,在书法中的狂狷怪诞既是这一时代的表征又是艺术的驱动力使然。
“人各有情性,则人各有诗也”,这是杨维桢的诗学主张,杨维桢是一个在思想和行动上能够高度保持一致的人,文如其人在铁崖公身上就是一种元代的现身说法,他能够通过诗歌阐述自己创作观念,达到理论高度和实践表达的统一,至于铁崖公的书法作品,也是这位身遭乱世为文为书为人都特立独行的元代文坛怪杰三位一体的精神体现。
考察杨维桢的艺术求索途径,可以看到他不惑之年以前就已经知道“当代人不可学”的道理,转而复古,这和赵孟頫倡导的理念情同所至。元朝文化人之所以復古,既有家国破灭的因素,也有个人名节的主观意愿,只不过到了元代晚期,南宋遗民的家国情怀和个人名节在杨维桢看来已经成为另一种表达,他已不为宋家山河的迭代而保持所谓的名节,对新社会的认同和维护的心理变得理所当然。在元代主持修订宋、辽、金三史之际,杨维桢便给元政府上书《正统辩》一文,以南宋为正统传至元朝,否定了辽金的正统地位,表达了他对元代统治合法性的认同。所以,杨维桢之所以苦读诗书,内心存在为帝王服务的忠君思想,晚年的事例可以证明,当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曾邀请杨维桢出仕为新时代的朝廷服务,被他拒绝,亦表达了对前朝的忠贞不二。
这种忠君爱国的思维,是通过杨维桢的父亲杨宏传递给儿子杨维桢,铁崖山下藏书楼苦读即可证实。所以,杨维桢从那让他记忆深刻的藏书楼出来,觉得自己已经获得一身本领,几乎可以所向无敌,这些学问如果不卖出去,在朝廷求得一官半职,要它何用?
元泰定四年,恰逢朝廷短暂的恢复科举,32岁的杨维桢便参加考试,获得了全国第二好成绩。在后来的书法作品中,杨维桢常自豪地把这次取得的进士名号书写于落款处。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约作于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的《竹西草堂志》在末尾署款中杨维桢写下:“第二甲进士会稽杨维桢也”,可见其一生对这次科举荣誉的重视程度,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名号,这又是一种什么心态呢,颇可玩味一番。
元朝统治者最怕汉族人动摇他们作为统治者的特权地位,为此,很多汉族人是进入不了政府的高级管理岗位任职的。他们甚至取消了定期的科举考试,人才的选拔大部分靠各级官员推荐,这里面难免会存在徇私舞弊的情况。只有在朝廷急需用人的关键时期,才进行科举选拔人才。杨维桢有幸获国考第二名的好成绩,加上此时他已完全认同元朝统治的合法性,自然引以为豪。
但是苦读书、学习好、考试成绩优异,并不一定代表能有好工作。可想杨维桢一身才华,即使考了全国第二,最后也只能在一个低等级的官位上一干就是好多年。考察杨维桢仕途发展的过程便可以充分理解这种心态。杨维桢32岁中进士,次年入官场,任天台县尹,再五年,38岁上任钱清盐司令,清廉为官,秉性耿直,直言敢谏,为民请命,不惜得罪权贵,罢免后回乡丁忧一年,绍兴授徒一年,杭州授徒三年。这一路匆匆走过,至正四年(1344)时年杨维桢已经49岁,到湖州东湖书院讲学,时已半百。从给杨维桢写《墓志铭》的明代大文豪宋濂的记载中,可以知道杨维桢在为官的岗位上干的还不错,但因性格刚直得罪高层,杨维桢政治报复的实现过程步履维艰,直到最后以文报国的政治理想惨遭破灭。元末乱世,义军频起,烽火连三月,虽然杨维桢尽显忠心,但效果适得其反,并未得到当政权贵的认可。可想而知,这位自认为才高八斗的文化人心里已经翻腾了不止一千只上古神兽草泥马了。天命之年,曾在官场混迹多年的杨维桢被贬且不得复出,其内心苦闷不言自明。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尤其是进士出身,彼时彼景非“落魄”两字可以形容。
元朝文化人有一种隐逸之风,这和元朝的政治环境有着直接关系,迭代之际,一些不愿意出仕的宋朝遗民作家,很愿意选择隐逸的生活方式,既能保持名节,又能安心搞创作。况且元朝对文化的相对漠视,让文人创作环境相对宽松,处于底层搞点文化建设还是相对比较安全,这种风气几乎贯穿了整个仅有百余年历史的元朝社会。元朝的文化明显特征之一就是精英文化和市井文化杂处的状态,元朝的文化开放源自向外扩张的全球化战略,因而既有底层的杂剧,如关汉卿、王实甫,也有如风花雪月的赵孟頫,更有一批外族的文化建设者也参与并且贡献了元文化的多样性。元代文化精彩纷呈是中国历史自有始皇封建以来,唯一可以和魏晋比肩的特殊时期。
这种文化杂处的交融状态也影响了杨维桢这类桀骜不驯的儒生,像很多官场的失意文人一样,杨维桢也有过隐逸文人的生活,《铁笛道人自传》云:“会稽有铁崖山,其高百丈,上有萼绿梅花数百植。层楼出梅花,积书数万卷,是道人所居也。”杨维桢这种行为并未贬损他在文坛的地位,反而让人觉得他有高尚之处。“铁崖狂怪不经,而步履自高”,明代人对他的评价,显然对其狂放的行为及其在文化上的大胆探索有所认同。
“五十狂夫心尚孩,不容俗物相填豗。兴来自控玉蹄马,醉后不辞金当杯。”1345年,杨维桢50岁之际所作诗歌自称“五十狂夫”,同年,杨维桢在洞庭得铁笛一把,从此自号“铁笛道人”。孔夫子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此时,杨维桢的个性养成已经到了不可更改的地步,只能顺着这条道路一路狂奔,至死方休。五十岁取“铁笛道人”的雅号,人生从此泾渭分明。号“铁笛道人”之前,杨维桢一心以文报国;有了“铁笛道人”这个称谓以后,一代“狂生”的形象越发生动而具体。
笛子这种乐器,很受古代一些散淡文人喜爱。传说中杨铁崖的笛子还是一件难得的宝贝,因为它的材质直接来自古代的一把叫做“莫邪”的宝剑。春秋晚期,越王勾践喜欢宝剑,命当时的造剑大师干将铸剑,干将夫妻不惜用生命和鲜血铸造了两把传世名器干将、莫邪。这个故事后来被鲁迅先生进行了故事新编,成为一个叫眉间尺的少年复仇的故事,在此不必多说。传说中这把著名的宝剑传到元末,被湖州一位名曰缑长弓的冶金大师熔之,卷铁造笛,开九孔,管长二尺九寸,赠与当时著名的音乐家、诗人、书法家兼文坛盟主杨维桢。杨维桢对铁笛甚是喜爱,《铁笛道人自传》中记载了这段佳话:“铁笛得洞庭湖中,冶人缑氏子尝掘地,得古莫邪,无所用,镕为铁叶,筒之,长二尺有九寸,窍其九,进于道人。道人吹之,窍皆应律,奇声绝人世。”
得了铁笛的杨维桢对此宝物爱不释手形影不离。于是赋诗一首云:“湖中冶师缑长弓,有如汉代陶安公。七月七日與天通,朱雀飞来化青童。且莫随仙踏飞鸿。道人铁笛已在手,铁冠八柱凌乔嵩。皇帝一统诛群凶,猛士干将无所庸。还徼上青子,天上裨重瞳。江心火电流赤虹,云凝雾结愁蟠龙。”
隐居休闲的时日,亦时常怀念得笛吹笛的所感,写下了很多和铁笛有关的诗句。“铁崖相见洞庭东,腰间笛佩苍精龙”“西洞庭,东洞庭,相逢铁笛铜龙精。从此吹春玉台上,丛霄不许谢玄卿。”偶得铁笛后,与笛同死生,铁笛之于杨氏,犹如身体的一部分,纳入到生命体认之中。
精通音律并有隐逸之名的杨维桢,虽然时常与黄公望、张雨等名士舟游海上,过一种仿佛超然物外的神仙生活。因其名望,很多人慕名去拜访他隐居的豪宅,但杨老先生很能摆谱,根本不想接见这些粉丝,“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这是他在自家门前写给粉丝们的一段真情告白。访客来了,他就坐在一个高台之上,身披有仙鹤刺绣的大氅,头上戴一铁冠,特别有明星范儿,粉丝们只能与他隔空对话,如果赶上杨老先生心情大好,粉丝们能看到他吹笛子表演,据说那感觉就像一个老神仙下凡,让人陶醉。也有人说流传后世的《梅花弄》就是沿用他的曲子。杨维桢虽未得道成仙,但在外人看来已是具有仙骨的世外高人了。
明代宋濂推其有晋人高风,并记载如下:“晚年益旷达,筑玄圃蓬台于松江之上,无日无宾,亦无日不沉醉,当酒酣耳热,呼侍儿出歌《白雪》之辞,君自倚凤琶和之,座客或翩跹起舞,顾盼生姿,俨然有晋人高风。”
晋人风度,不仅表现在对生命本体的纵乐认同,有时候也表现为对统治者的不合作的态度。1368年大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曾邀请过杨维桢入朝从政,但被杨维桢拒绝,杨维桢不仅拒绝朱元璋,此前还曾拒绝张士诚,那首“山中岁岁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的诗歌,就是为此事件所做。朱元璋第一次邀请不成功之后,又以修礼乐之名邀请,杨维桢遂前往。可见,忠于前朝之心,不能改,但为艺术可以屈尊,但不久后,晚年的杨维桢厌倦官宦的生活,毅然辞职归乡,宋濂作诗送行,有“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之誉。回乡后不久,75岁的杨维桢便结束了疏狂癫放的一生,留下被人评说的生前身后名。
总之,在同代人以及后世看来,无论神仙做派或诗歌中的怪诞和书法作品的狂放,杨维桢在人们眼中就是一个不与世事妥协的抗争者和逍遥派。如果说在他在文学艺术领域和为政领域都走上了离经叛道之路,那么在与朋友交往的生活细节之中,他则颇有江湖大哥的不讲道理。
与其齐名的元代擅长画山水的画家倪瓒,曾经与杨维桢要好,但因为倪瓒有洁癖,因一酒局,二人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酒局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南村辍耕录》有记载,元代文人在不怎么被政权关注的时候,往往自己抱团取暖,经常搞一些民间雅集之类的活动,有雅集就要有酒,有小姐姐,有歌舞,才玩得嗨。作为文坛盟主的杨维桢经常在这些文艺沙龙里面担当主持人的角色,宴会开始之后,也可能老杨玩得过于尽兴,整嗨了,把身边一个小姐姐的鞋子脱了下来,当作酒杯,不仅自斟自饮,还让在座诸兄弟用此“鞋杯”传递饮酒。这或许是杨维桢的另一癖好,当今心理学家不用分析即可判断他有一种心理疾病,名曰,恋足!
连上厕所都要用鹅毛铺于粪池之底的倪先生,喜欢那种鹅毛被■■激起飞扬的感官享受,哪里能忍受女人鞋里的臭脚丫子味道,何况还要拿它喝酒,这等不洁,在云林子看来,实在是可忍孰不可忍。想一想,这个元代最著名的画家,曾经找一个小姐姐回家,欲与之行鱼水之欢乐,可是到家之后,心里面就觉得小姐姐身体被那么多人占有过,肯定是不干净的,于是让小姐姐先洗澡,洗完之后还是觉得她没有洗干净,再让她洗,小姐姐感觉自己都要洗秃噜皮了,但大画家还是觉得她没有洗干净,如此反复,直至天明,大画家困倦,把小姐姐打发走了。你杨维桢用小姐姐的鞋子让这位有洁癖的大画家喝酒,开什么玩笑,不翻船才怪。于是,倪瓒大怒,拍案而去,结束了两人之间的友谊。自此,杨维桢再也没有和倪云林说过话。这事情我认为不能怪云林子,杨老大强人所难,多有冒犯之意,都是有个性的人,怎能不掀桌子。绝交就绝交吧,志同而道不合,也尿不到一壶。多年以后,云林在画作上写下“铁崖健笔老纵横,万卷当胸随所取”,不知是何所感!
或许杨维桢古怪的行事风格,亦或许杨维桢特别注意自己的感官体验,写了一些少儿不宜的诗篇,这让同代的评论家赐了他一个“文妖”的称谓,“余故曰会稽杨维桢之文狐也、文妖也。噫,狐之妖至于杀人之神,而文之妖往往使后生小子群趋而竞习焉。”(《王徵士集》卷三《文妖》)但后世学人并不太认可杨老先生是“文妖”的说法,尤其是四库全书的编辑者,甚至还反对这种称谓。
实际上把杨维桢的古怪行为理解成因为艺高人胆大而作出的怪诞行为于情于理也说得通,就像他自我表白一样:性情使然。唐伯虎的一句诗可以作为这种怪诞文风和书风的注脚,“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杨维桢是飘逸与坚硬的复杂混合体,他坚硬的时候,根本不畏强权,前文所讲,为官刚正,仗义执言,与张士诚、朱元璋政权的不合作态度,都体现了杨维桢为人的坚硬。这种坚硬和飘逸的品质也带到了他的书法创作之中。
说了这么多杨维桢人生的轶事,以及最开始提到的元代文化发展的大背景,还没有说杨氏书法是何等面目,但可以肯定地说,杨维桢的特立独行严重影响了他的书法艺术观,并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进行了书法的创作实践。在有元一代文坛霸主赵孟頫的倡导之下,书法家们也追求晋人风尚,杨维桢也被这股子洪流夹裹,但杨维桢比赵孟頫走得更远,也更彻底,恰恰是杨维桢的出现,才让元代的书法有了一种新的面目,可惜在当时很多人都看不懂,时至今日,很多人也不一定能欣赏得了这个700多年前的书法界的疯狂革新者。
这也难怪,看惯了二王的行云流水,以及赵孟頫的秀润流畅,再看杨维桢奇崛的书作,那些粗细变化的线条,歪歪斜斜笔画,大小错落排列的章法,无论认同与否,都能感觉到一股粗头乱服的狂乱的气息扑面袭来。但具体说明这些书法作品好在何处,还需要一番解释,才能体味这种书法的魅力所在。
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不仅因为他书法本身的艺术成就,还因为他对后世的影响力,经过唐代李世民牵头众多书法家跟进的集体努力,一直到清代初期,二王书法被一代一代人反复学习,无论如何推陈出新,几乎都是在二王的书法基础上实现的。清代碑学盛行,绕过了王羲之,开辟了另外一条学习书法的路径。即使这样,王羲之开创的帖学传统仍然占据大半江山,而且普通人学习的更多,直至今日王羲之都是学书人不可不学的典范。元朝时代,当然也在王羲之书风的影响之下,有资料表明,杨维桢对王羲之也十分喜爱,他写下了一首诗,表达了对王羲之的高度认同,“羲之在东床,风操夙所称。”也可以说对王羲之的认同就是对魏晋狂放不羁的风度的认同。
杨维桢现存的书法作品大部分都是他50岁以后书写的,50岁对于杨维桢来说无论是生活还是艺术都可以看作一个分水岭,人生态度的转变,对艺术审美的追求也会发生变化,但整体上从书法作品来看,杨维桢在书法上也追求复古,尤其是和赵孟頫一路书风相比,杨维桢书风则更古朴雄强,也更锋芒外露。可以看出,第一,杨维楨在元代复古的文化潮流中,书法艺术吸收了大量章草元素,《张氏通波阡表》和《梦游海棠诗卷》可以视为杨维桢具有章草风格的代表作品。章草是中国书法发展历史上的一种过渡性草书字体,出现于秦汉之际,盛行在东汉魏晋,到隋唐宋三代已经衰落,被更流畅秀美的小草所取代。章草是草书的最早形态,有完整的法度,境界古意盎然,元代在赵孟頫的提倡下和实践下,章草被重新发现,赵孟頫,康里巎巎、鲜于枢、邓文原等元代书法家都有留存后世的章草作品。但杨维桢的章草显然更具有表现力。从文本来看,杨维桢将行书和章草进行了整合,吸收了章草明显的捺笔特征,起笔多直接入锋,下笔迅疾、捺画燕尾重按快挑,有狂放锐利的夸张姿态,虽然同样以行书参章草,但杨维桢和赵孟頫等人的章草风格相比,更加具有突破传统的艺术表现力。据考,杨维桢之所以能写出如此锐利的字,和他使用的一种定制的毛笔有很大关系,这种叫“铁心颖”的毛笔是湖州制笔大师陆颖贵制造,笔心坚硬如铁,杨维桢视其为宝,杨维桢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这种毛笔时说,“予用之,劲而有力,圆而善任”,杨维桢认为合适的工具更能有助于他书写表现锐利风格的作品。
从杨维桢充满创意性的书法创作,还可以看到他与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某些传承关系。唐朝晚期以及两宋时代,颜真卿的书法影响力十分巨大,很多宋版书的印刷都已使用颜体,苏东坡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能事毕矣!”宋人把颜真卿推到了极其崇高的地位,成为文人学习的典范,这和颜真卿取得的艺术成就以及他忠贞爱国的正直形象是分不开的,而元代取宋代之,文化人改朝换代之际的名节问题,也影响了他们在书法艺术领域中对颜真卿的继承,古代人将书法和人格同时评价,所以在元代文人中颜真卿的书法不太吃香,或许元代文人在心理不敢直视颜鲁公的忠义,才有了赵孟頫越过宋代和唐代,追求晋人王羲之的做法。在别人不学颜真卿的时候,杨维桢却取法颜真卿在艺术上的创新精神为我所用,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杨维桢晚年名作《真镜庵募缘疏卷》将楷书、行书、草书相杂,夹以章草笔意写成,从这件奇特的作品之中完全能感受到《真镜庵募缘疏卷》和颜真卿那件以“破体书法”名作《裴将军诗》的血缘关系。
《周上卿墓志铭》,纸本,纵25.9厘米,横86.2厘米。这是杨维桢留世的唯一一件楷书作品,藏于辽宁博物馆。从这件作品之中可以看到唐初书法大师欧阳询父子的影子,尤其受小欧的影响巨大,可谓得欧阳通《道因法师碑》的精髓。杨维桢作《周上卿墓志铭》之时已66岁,正值书法创作的最佳时期,呈现了他楷书创作的精湛功力。
书法艺术有在继承中发展的历史规律,在继承前人的古法的基础上杨维桢高歌猛进,以狂怪不经之姿态,走上了一条具有独创精神的书法艺术之路。杨大师的书法,创造性贡献更直接地表现在其作品的章法上。章法这个专业术语通俗一点儿说更像作品呈现出来的画面感,它是欣赏者的第一感觉,书法作品的章法,是通过线条、墨色以及对创作画面作出的空间分割形成的对比关系呈现出来。古人评杨维桢的字是粗头乱服,有乱世气就是针对作品章法的感受得出的结论。观《真镜庵募缘疏卷》,字与字之间的大小错落,互相牵制、线条粗细、楷书和行书参杂,字形奇特,行与行之间摇曳跌宕,所有的字在画面之中均有动势,更像在战场厮杀,形成了对传统平整方正的破坏,但也正因为如此,其画面构成的有了强烈的视觉冲击,遂有明代书法家吴宽所说的那种“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牖,例载而归”的气势呈现。
艺术史也是一种当代史,在艺术家肉体生命存在的时间中不为时代认同的原因很复杂,但时人风气不可忽视,它表现一个时代的审美风向,逆风行走的人自然会被视为异数。随着时间的流逝,幸运者会被重新发现,因为其独特的艺术观念对当代有参考意义,并意合了某些艺术理论观念,可以在古代找到合理性的解释。
杨维桢是元代最具创新精神的书法家,其为文为书为人三位一体,融会贯通,自成一派风格,虽然在元明清的时代对其书法创作并未有充分的关注,但不可否认,杨维桢的创造性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杨维桢的章草创新直接影响了元末明初的另一位以章草见长的书法家宋克。清代中期的在书画上同样充满创意的书法家金农评杨维桢说:“高妙砺俗,字有坚光。”其习古不泥古的创新精神,今天看来也特别有参考意义。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书法在发展创新的潮流之中,杨维桢的书法观念以及在字法、章法的创造性逐渐被重新挖掘并重估其价值,相信有一天,杨维桢的怪诞书风也会成为中国书法传统的一份宝贵遗产被后人继承并发展。
作者简介:梁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出版长篇小说《马迭尔旅馆的枪声》《补丁》、短篇小说集《马戏团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