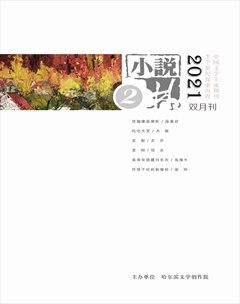抚摸童年的疼痛,是对精神的告慰
薛喜君
童年,小镇屋顶的烟囱里的袅袅炊烟令我痴迷,也让我忧伤。我痴迷于别人家的屋顶有好几个烟囱,这家一定人丁兴旺,即便吃着粗茶淡饭也会有笑语欢声;忧伤于我家的屋顶只有一个烟囱,烟囱还时不常地一杆一杆地往出蹿黑烟。我家灶台也往出呛烟,呛得母亲鼻涕眼泪常淌,还不住声地咳嗽。冷风从洞开的房门肆无忌惮地蹿进来——母亲说,灶台犯风,一刮西北风就倒烟。而北方的冬天,西北风又是常客。现在想来,呛烟多半是炕洞里结了霜的缘故。烟火也是势利眼的家伙,烟火不喜欢寂寞,烟火也不喜欢贫穷。父亲在另一座城市工作了许多年,母亲独自带着我们在小镇上生活了许多年。所以,女人撑着的日子,多少显得冷清和寂寥。
日子需要男人的光普照,日子里的女人才能散发出光辉。
我常常站在门楣下,看远远近近屋顶上烟囱里的炊烟。六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大多兄妹成群,老大带老二,老二带老三,捡柴拾煤也是那个年代孩子的日常。我是家中的长女,没有父亲在身边的孩子没有安全感,还比同龄的孩子过早地承载生活。虽然没有课业压力,却有生活上的愁苦。从我家走出二三百米,就是一条垫着煤灰渣滓的街道。一听见大门洞口卖豆腐老头的叫卖声,我就跑出去。手里要么捏着一毛钱,要么端着一碗黄豆,那个年代的豆腐可以用钱买也能用黄豆换。胡同对面的大院住着一群兵,屋后的高墙圈着铁刺网,大人们说那是看守所。我小得还不懂看守所意味着什么,就站在烟气行行的门洞口张望路对面,看红砖砌的大烟囱里的袅袅青烟,无以名状的忧伤像河水,在心头咕涌出一波又一波的白沫儿……夏天,我也会和玩伴们站在大门前看兵们打篮球。十七八岁的邻居姐姐告诫我,少搭理当兵的人,他们爱撩扯小姑娘。我不懂撩扯的深意,还照常站在大门外看兵们打篮球,听他们狼一样的喊叫声,看他们用一条白毛巾擦汗,听尖厉的哨音此起彼伏……可能是太小或者还不懂世间情愫的缘故,反正没有遭遇过兵们的“撩扯”。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不好生活的馈赠或失去究竟是一种遗憾,还是一种获得。
高墙里经常有车出入。但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从里面出来的车就有些壮观了。所谓的壮观是路上站了很多人,两辆或三五辆敞篷解放车从里面拉出犯人。犯人的脑袋露在车闸板外,车闸板挡住了人们的视线,看不见犯人们究竟是跪着还是蹲着。犯人的脖子上都挂着一块写着名字和所犯罪行的牌子,如“盗窃犯XX、流氓犯XXX”——不知道是牌子过于沉重,还是他们羞愧,抑或恐惧,大多犯人都垂着脑袋。也有犯人抻着戗毛戗刺的脑袋东张西望,大人说他们在寻找人群里的亲人。如果犯人身后站着两个持枪的兵,脖子上的牌子又打着大红叉,我们就知道他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犯人。车上还有其他陪绑游街的犯人,公审时,广播喇叭里浑厚的声音义正辞严地播报着毛主席语录和犯人的滔天罪行。在镇上游街示众一圈后,死刑犯就赴刑场了。因为近水楼台,我们总是能最先能看到拉犯人的车,一群孩子呜嗷喊叫地跟着敞篷车的后面跑,在五月阳光里跑得气喘吁吁,最终还是被汽车轮子甩掉了。死亡对于小孩子来说像一场打闹的游戏,孩子们也把对死亡的追逐当成一种游戏。童年除了见到棺材才会恐惧死亡,对于车上即将奔赴死亡者的心境,小孩子们才不理会——在一次追逐死亡犯人的车又被车轮甩下后,孩子们索然无味地觉得游戏结束得太快——灰暗的路上躺着一只丑陋无比的胶鞋,直射下来的光令胶鞋更加破烂不堪。胶鞋鞋尖的破洞像张着的嘴,前掌基本耍圈,只有后跟还连着。阳光下的胶鞋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什么,又仿佛在诅咒抛弃它的主人——我倏地站住了。确切地说是被这只丑陋的胶鞋刺疼了,眼前升起一片蒙蒙雾气……刚刚停止追逐的孩子们突然回过神儿,再次呜嗷喊叫冲向路中间这只丑陋的鞋,迅速把它当球踢起来——又寻找到新游戏的孩子们的笑声和打闹声如阳光一样炽烈。
我看见蹲在门口的高三,他咧着的嘴露出一口牙,熏黑的脸上牙白得扎眼。他身后破败的门半开半关地耷拉着,屋顶烟囱里的青烟缭绕得有气无力,他蜷缩着的身子更像一只被雨水淋透的鸡……高三家的大门冲看守所的高墙,我从没见过他妈,他爸把他当靶子打。哪怕他刚从马车轱辘下爬出来,也没躲过他爸的拳脚。没有女人的日子,屋里就没有光亮。高兴成还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底层劳动者,他不会理解好女人能让男人精神受孕的至高境界。精神需求对他来说,还不如一壶烧酒,一碗肉来得实在。但他一定需要女人的温暖,没有女人温暖的男人,活得不快意,眼睛里看到的也都是灰暗。儿子成了他发泄的出口,只有对儿子挥舞起拳脚,才能挥发他内心深处的卑微和扭曲。只有对儿子抡起巴掌,才能展示出雄性的力量。
因此,高三活得像一只过街的老鼠,一副噤若寒蝉的样子。
我很少和高三玩,但他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除了那只丑陋的胶鞋,一張瘦脸也从没洗透亮过,鼻翼两侧还有两撇黑胡子。他黑一条白一道的脸是灶膛里的煤灰作祟,鼻翼两侧的胡子是常年流淌的清鼻涕的杰作。一件褂子早已辨不出颜色,一条肥大的黑裤子留给了夏天,冬天干脆直接穿条精短的棉裤……每一个生命都会经历疼痛,但高三童年的疼痛令人唏嘘。他和他的父亲高兴成一样,都渴望爱,童年的高三渴望母爱,成年的高兴成渴望性爱。于是,他们都选择了寻找,只是他们寻找的方式不同。
但有一点却出奇的一致,他们都毫不留情地舍弃了对方。
我曾经写过成年后的高三,成年高三也尽显灰突,好在他对爱情还有期许。但他依然活得卑微,依然活得没有色彩,依然是人群中那个微不足道的人……一个经历疼痛的孩子,成年以后又能怎样呢。尽管童年的疼痛会被岁月漂洗得了无痕迹,但有些痛彻心扉的疼痛,岁月也无能为力。童年的遭遇也是一个人秉性和性格形成的重要因素。当然,我也不否认童年的疼痛有时候会是滋养生命的沃土,但这要有怎样的命和运啊。尽管高三最终还是选择了抗争,但他的抗争究竟会给生命带来什么?赢得什么?我不得而知。我笃定地知道,他一定是皮开肉绽。至于疼痛是否给他性格带来扭曲?我也不敢确定,高三还没长大就不知所终,他究竟是活着还是死去,米果都不知道,我更不知道。创作成年的高三时,他的命运是我臆想出来的。
后来,我发现高三童年的疼痛没有成为往事,他心头的疤痕依然隐隐作痛。
我忽略了高三的童年,亦如我对自己的童年也表达不够。一个没有童年的生命,岂不是更加悲哀也不公平。高三的童年值得回味,单就那只躺在路中间的胶鞋就一直活在我心头。胶鞋不仅刺疼我的心,还时时走进我的梦里暗送秋波。所以,我像悼念某种情感般地想象祭奠仪式,直到我以炊烟的形式把它展现出来,我才长吁一口气。我不仅抚摸了童年的疼痛,满足了对自己童年的祭奠,还虔诚地向精神作了告慰,也向那只遗落到路上的胶鞋解释了许久以来的冷落。很多时候,冷落只不过是一种表象,内心深处的火,早已把血液烧得沸腾……于是,我怕那双胶鞋孤单,把炊烟搬出来与它结伴。事实上,小镇屋顶上烟囱里的炊烟,也为我的忧伤加了砝码,因为它一边沉静地招摇,一边张扬地述说岁月。
2018年,我沉浸于童年的书写里不能自拔。《炊烟像面旗帜》就是那年的产物。
小说还是太轻了,它如何能承载起欢喜疼痛的生命呢。小说即便是走到读者面前,也只不过是作家书写上的一次完成。于生命,于生活,小说都轻飘得像一截草屑儿……但无论是炊烟还是胶鞋,童年的疼痛伴随了米果一生。作为写作者,我不用小说表述米果的疼痛和忧伤还能用什么?
毕竟,小说是表达命运和忧伤最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