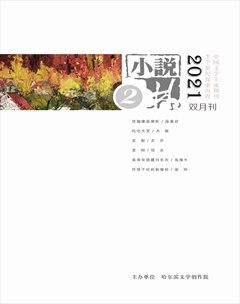村庄记
大解
我儿子小时候,是个爱动的孩子。大约四五岁时,经常自己在家里玩耍,一个人也能玩得热火朝天。那时候电视里经常播放武打片,他就有样学样,自己在家里耍,肢体动作加上嘴里不时发出哈哈的武打声,耍得非常热闹。有时候,他偶尔也会安静一会儿,一边玩一边自言自语。有一次他自言自语地说:“妈呀,你就是我的故乡。”我听到后一下子愣住了,我问他,刚才你说什么?他也愣住了,回答说,没说什么呀?很显然,他是不自觉地随口瞎说的,说完,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但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听到这句无意识的童言,我一下子蒙了。我突然觉得,孩子的嘴里也有箴言。从生命本体意义上说,母亲的身体,不正是每个人生命的故乡吗?
在人们的惯常意识中,故乡是一个人出生和长大的那个村庄,或者是一座城镇,这没错。我的故乡就是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山村,那里有我居住过的老房子,有我熟悉的人们,也有我的童年记忆。我常常想,那是我出生的故土,也是我出发的地方。若从身体上说,我也曾经在母亲的体内居住过,是母亲用自己的血肉在她的身体里重组了一个新的生命,给了我身体和灵魂。往深了说,母亲的身体才是一个人真正的故乡,出生即是离乡。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我却从来没有意识到,是儿子玩耍时信口说出的一句无意识的话,提醒了我,让我对故乡有了新的更深的认识。
故乡是一个人的胎记,永远也抹不掉。一个人不管走多远,不管他出生后经历了怎样的辗转和颠沛流离,甚至从未有过一个安稳的久留之地,他也有故乡,总有一个出生地属于他,总有一个母亲,是他生命的出发点。哪怕他的故乡破落了,拆毁了,搬迁了,被水库或风沙淹没了,或者说连废墟也不存在,彻底消失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他的精神故乡也依然在,没有人能够把故乡从一个人的心里完全抹去。
有人说,人们一生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离家更远。我认为这句话不全对,但也有一定道理。因为许多人确实如此,我就是其中之一。童年的时候,我特别向往远方,想走出去看看,我甚至曾经因为连绵的群山阻隔而感到深深的绝望。那时我想,我可能这辈子也走不出去了。长大了我才知道,群山是挡不住人的,一个人终究会走到他意想不到的地方,然后居住下来。一个人离家越远,故乡意识越浓。一个从未离开过故土的人,不可能有怀乡意识。我从未听说过哪个人把自己从生到死一直生活在其中的地方叫做故乡。故乡这个概念,是属于离乡人的。离开故乡的人不都是浪子,而离开母亲的身体而出生的人,因其独立存在而必将承受身体的孤独。关于身体和生命,这里不做深入讨论,我不想打岔。
话说回来,我的故乡是一个贫穷、封闭、落后的山村,我五六岁的时候,村庄里大多数都是茅草房,屋顶上的茅草每隔几年就会腐烂,需要更换新的茅草。那时候,村里很少的几家瓦房显得特别另类。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不仅生活着朴素而贫穷的人们,也生活着神和死者,同时也生活着多种动物和永生不能移动的荒草和树木。人们似乎活在一个神话世界里,缓慢的时间混淆了万物的界限,人们生生死死,仿佛都在一个漫长的梦境里。那时,村里的人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似乎也不想知道,仿佛一切本来如此,本该如此,没有人对生命和生活发出过任何疑问。
稳定的农耕社会把人们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有的人从生到死也没有走出过村庄,死后埋在村庄周边的土地里。人们死后按照姓氏和辈分安居在地下,过另一种漫长而寂静的生活,仿佛人生只是一个长剧的序幕,死后才是永居。在我眼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死者,每一个人在属于他自己的时代,他都是活的。一个人即使真的死了,从茅草屋搬到了坟墓里,也只是换一种居住方式而已。倘若有不安分的死者灵魂偷偷溜走,在夜色的掩护下回家看望在世的亲人,也必须在鸡叫以前返回到坟墓里,因为一旦天亮,就会有勤劳的人早早起来干活儿,而灵魂既空虚又胆小,不愿被人发现。
我的小说大多是记录我的故乡土地上那些生者和死者的平凡生活。当我在生死不明的混沌世界里穿行时,时间像空气一样透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文字所呈现出来的精神现实。我愿意建构一个丰富的多联通的文学空间,让那些超越时空的人和物自由穿行,无翅而飞。我认为,文学的任务不是去限定事物的边界,而是要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和外部,撕开所有的层面和间隔,让语言和世界相互敞开,展现出万物活跃的物理和精神的全景。
语言失去了边疆,精神的障碍也会随之消失,内视和远眺都会现出远景。而我出生和长大的小山村,恰好是人神共居的完全社会,给我提供了全部的能量和要素,任由我选择和发挥。另外,我痴迷于村庄故事也是因为它的古老和深邃,以及它的不可替代性。村庄是人类走出洞穴之后所建立的一个稳定的群落驿站,有别于封闭的城堡和喧闹的城镇,安静而祥和的村庄更加得到神的偏爱。村庄适合于胎儿和童年人居住,而这些,恰好我都经历过,并因此而得到过星空的覆盖和眷顾,有幸成为走在诗神右边的人。
除了安静和神秘,我对村庄的好感,有时也来源于它的梦一般的迷离。在我看来,在漫长的农耕时代里,村庄就像是人类留在大地上的一片片遗址,隐隐约约地分布在岁月深处,历经时光的摧毁而难以磨灭。我对那些模糊的不可名状的事物,经常陷入难以言表的古老的乡愁。村庄无论大小和胖瘦,都有强大的生存韧性,即使破败和衰老,却很难死去。在见过一片废墟,人走墙颓,石头和黄土都风化了,却又死而复生,在原址上长出新的房屋,再次成为人们的居所和归宿。当炊烟一次次升起,埋人的土地上隐现出四季衰荣,耕作的人们一代代老去,我和我的忧伤最终也会消失,弥漫在苍茫的风尘中。回望那些已经消逝的岁月,那些久远的依然在不断后退的先人们,我顿时感到自己生存背景的庞大和深远,甚至漫延至整个地域和族群。在漫过大地的生命潮水中,个人作为一股流动的血脉,是多么细弱而顽强,又是多么无奈。因此,乡愁可能不是自然感怀的一种思绪,而是来自于生命本体的深度忧伤,不会随时间和环境而改变。
我出生在一个村庄里,而且是一个闭塞贫寒的山村,这是我的命。命运所给予的,无论好坏,你都必须照单全收,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有时候,一个人只能听天由命,比如出生,你没有选择权;比如死亡,你没有拒绝权。有人说,人生的所有经历都是财富,但是有的经历,我不愿拥有;有的经历,我还想在重复无数次。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来生依然生于村庄,最好是山村,在山下,在水边,在一望无际的先人的背影后面,走完自己的一生。
在写作中,我愿意把故乡理解为原乡。我所认为的原乡不仅仅是人们居住的村庄、房屋、土地、山水、草木、生灵,也包括死者,以及穿越生死的血脉渊源,以及游走于人体内外的灵魂。而作为一个在场者,我很少出现在文字中,我不愿以一個现代人的身份,深入到古老的情境中,打破那种古老的秩序。毕竟从生命序列上说,我到来的时候,村庄里已经有了很多人,我是一个后来者,我还没有资格站在先人面前,当面说出他们的经历和隐藏的真相。另外,我愿意游走在开放的时空里,便于我随时抽身和穿越,去经历和接近那些虚无缥缈的事物,把不存在和不可能存在的幻境还原为现实,呈现出文学世界的多向性和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