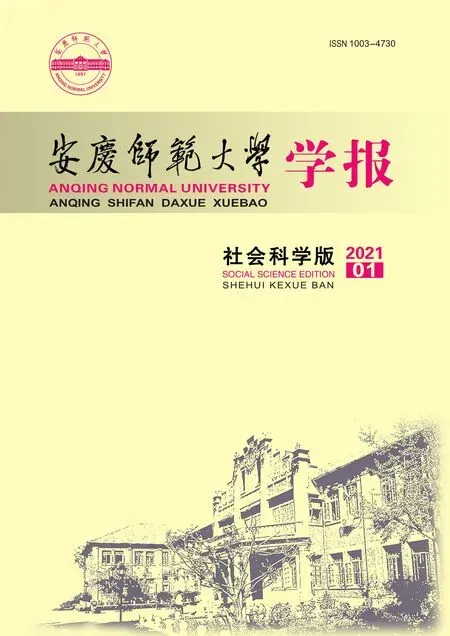“因文求意”:桐城古文家吴汝纶的治经之法
范丹凝
(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清代学术尚东林之绪,经学最盛。及至晚清,学界经历汉宋之学的对立与整合,诸家门户并立,相与轩轾。桐城派的古文家也参与了经学研究,却因偏重“辞章”而被汉学者讥为“空疏”,不得不标举宋儒义理之学以捍卫门庭。吴汝纶却主张将古文之学的重心复归到文章本身,强调“辞章”的独立价值。他认为“自古求道者必有赖于文”[1],“文之不存,周孔之教息矣”[2]353。是故文章不必附丽于义理和考据,而谈理、说经皆不得缺少文章的表述之功,不通经“文”,自然难解经书中蕴含的圣哲之“道”。他将“文”视作治经之一途,发掘古文之学在阐释经书中的作用,通过古文家独特的视角,分析经书文章中的结构规律和修辞特点,以文法诠释经文和经义。他的弟子贺涛将这种治经方法总结为“因文以求其意”[3]168。这种“因文求意”的治学方法继承了桐城前辈在治经方面的传统,从实用的角度扩大桐城派“辞章”之学的阃域,将古文之学上升成为古典学术研究方法之一,与汉学、宋学分庭抗礼。“因文求意”是吴汝纶作为桐城派古文家对于“辞章”之学在古文创作之外领域的探索和考量,丰富了清代经学研究的成果。古文之学也因此成为了经学研究之一途,从而在晚清学界占有了一席之地。
一、桐城派的经学传统
吴汝纶自幼熟悉故乡前辈家数,他以古文之学作为诠释经典之法的的观念,也并非一人一时之见。古文家向以文章之源出于六经,所以文章文本可作考据经义之用。在吴氏之前,许多桐城文家已有论及古文在阐经说理方面的作用。姚鼐素有“文不足而道不明”[4]5之论,即说经谈理必要有足够的文学素养。他所称“学问三端”之一便是考据,即古文要能兼考据之功。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中载录桐城文家《撰述考》四卷,其中除个人的文集、诗集、笔记、方志、评点、杂钞等外,还有连篇累牍的解说经义、考辨古籍的经学撰著,其数目总量超过了文学作品。可见桐城派文家参与经学研究的现象并不鲜见。
从著述实绩上看,桐城派古文家们说经大多以宋儒义理为依托,兼及考证名物、训诂音义。然而以宋儒成说为论者,不能自出新意;以考证训诂为文者,又不及汉学家研索之深。而其中有以古文文法阐释古书得失之处,却独具特色。以姚鼐为例,其《惜抱轩书札》本是为四库馆序录旧籍之作,平章诸书以程朱为轨,因不合当时之体,最终未被《四库全书总目》采纳。但其中颇多从文章的体势、语词等方面辨正伪体、考证文义的说经条目,别有新见。郭象升有言曰:“姚惜抱于伪古文,亦自谓于词气间可以别之,较考据者尤得真云”[5],此言殆是。其中有以文章结构判定真伪之例,云:
《元经十卷》其书虽依仿《中说》所谓诸条。然其记载,全无史法。……遂至不成文义。王通虽有僭经之失,然岂若是陋也?为伪作无疑[6]2。
《颜鲁公集》篇末乃有时议者举然云云。此《新唐书·陈京传》叙事之辞,非真卿本文益明[7]。
也从文章辞气方面的判别伪体的条目,如:
《孝经刊误》朱子疑为本曾子门人所记,后儒复取他书之语增益其间。是以精粗相杂,而文义亦有离析隔礙之病[8]。
《穆天子传六卷》要其文辞之古,必出周人,非后世所能伪也[6]10。
《难经本义》《难经》之书,《汉书艺文志》不载,始见于《隋书·经籍志》,托名扁鹊。虽未可信,然其辞甚古,殆汉人所为也[4]10。上文所列皆是从文法的层面判定文辞真伪的实例,具有鲜明的古文家特色。这种研究方法别开生面,为经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却也存在诸多弊端。首先,对作品词气的分析和考量皆依靠作者个人的文学修养,读者如对文事理解不深,将很难领会作者的观点;其次,单凭经文结构与辞气作为依据,这样的考证缺乏坚实而充足的证据,难以令人信服;再次,从说经著作的文体方面来看,古文家所作的说经著作大多依据古文之法写就,简明有余而论证不足,违背了考证经文的基本方法。姚鼐所作之《九经说》在当时就饱受汉学家批评,翁方纲责其:“不当自立议论,说经文字不可以作古文。”[9]15李慈铭亦訾姚氏:“以右文自命,所为经说,喜立异论,顿非家学之旧。群瞽和之,其弊遂肆。”[10]371在汉学家看来,姚氏以古文辞说经之法不合汉儒解经传统,即为“空疏谬妄”,“盖姚姬传虽讲求经术,然颇为异论。以后桐城、宛陵及江右新城空疏谬妄之学派,实自姬传开之,若方东树、陈用光、梅曾亮尤其著也。”[10]1052尽管桐城文家以古文辞说经的实验遭到了汉学家的诋斥,然而他们却并未因此而丧失治经的热情。盖在他们眼中,汉学家们的考据之文实不能尽发古书之义。张裕钊曾言:“夫古人之书,待说而明者,十之三四而已;因说之而晦者,盖十五六焉。”[11]12在古文家看来,汉学家的经解之作远不能令人满意,其“拘文牵义,鹜华炫博,好为枝词碎说”,正是重视文章法度的古文家所不能认可的。这也是他们不断探寻于汉学之外解释经书的方法的原因。
在汉学昌炽的背景下,桐城派古文家汲汲于经说学问,不仅是为了袒护门庭而在学术领域与汉学家们争驰,还是为了做好学术积累以备文章之用。因此他们主张将考据作为古文的学养准备,并声称应“以考证助文之境”[12]。对于桐城古文家而言,不废考据最好的方法就是以考据之学充当古文创作的学养,他们虽然极少在实际创作中引入考据,却都未肯轻言考据于文章无用,于考据之中发现于古有征的文辞和句式,亦对古文创作有所助力。曾国藩更是提出“一宗宋儒,不废汉学”的主张,认为历代古文名家,皆于训诂小学有所致力,“余观汉人词章,未有不精于小学训话者,如相如、子云、孟坚,于小学皆专著一书,《文选》于此三人之文著录最多。余于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马迁、韩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于小学训话,不妄下一字也。”[13]23熟习训诂可以在古文选字遣词方面更为得心应手,“国藩以为欲着字之古,宜研究《尔雅》《说文》、小学、训诂之书,故尝好观今人王氏、段氏之说;欲造句之古,宜熟读班、马、韩、欧之作,审其行气之短长,自然之节奏;欲谋篇之古,则群经诸子以至近世名家,莫不各有匠心,以成章法。”[14]在曾氏看来,训诂之学是和文章之法一样重要的创作条件,“训诂精确”方可得古人行文精髓。他评价韩愈之文:“其训诂亦甚精当。”[13]127故欲为古文,绝不可废训诂之力。他认为古文创作的最高境界是“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意欲“以戴、钱、段、王之训诂为扬、马、班、张之文章”,可惜“人事驰驱,有志未逮”。在他之后,曾门弟子们继承了其师以训诂助力古文创作的观点,如黎庶昌之言:“循曾氏之说,将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辨、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正桐城末流虚车之饰。”[15]可见湘乡一门所言之训诂,乃是作为文章写作的必要之功。古文只有融合了训诂、考证的功力,方能避免空谈,言之有物。
综合桐城派从姚鼐至曾国藩和曾门弟子对于考证、训诂的观点,可得出一个结论,即桐城文家有意愿将古文与经学考据联系起来。无论是为了反驳古文“空疏”之讥,还是为了创作本身。但他们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又使其所成之文在许多方面未能尽如人意。刘声木总结桐城文家的治学特点云:“桐城文学诸家,本经经纬史,涵泳百氏,不株株于一先生之言以自锢,其为文宗旨,撷经史之腴,简练肃穆,文从字顺,语必己出,一以义法为尚。”[16]桐城文家说经的特点,一方面体现在学术表达方面,他们的学术文章一般语辞畅达简练,重视法度。另一方面,他们以“义法”作为“经经纬史,涵泳百氏”之由,从经史之文的文法结构、语气辞章等角度理解经义、考证经文。吴汝纶“因文求意”的观点正是以桐城文家的说经实践为渊源,他综合了从姚鼐至曾国藩的桐城前辈关于古文与训诂考据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在古文家说经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对桐城古文之学新的理解。
二、“因文求意”观点的由来
吴汝纶论学“向于汉宋二途,皆所未安”[2]41。他平素不喜宋儒义理之书,又不满于汉学门户之见,曾评价阮元所编纂的经解诸书“未尽当人意,要为闳博巨观,资益学林不少。独其门户之见,使后来变本加厉,海内学者,专搜细碎,不复涵泳本经,究通文法,此其失也”[2]47。在他看来,汉学家的说经成就固然可观,但其固守门户之见,排击异己的“卫道”之举,则会导致说经的方法日趋狭隘。他认为,经学为天下公物,研究宜多途并举,“不可以一人浅见,悬定是非;亦不宜稍存瞻徇阿党,以留缺憾”[2]163。训诂考据,只是说经一道;“涵泳本经,究通文法”也是学者研究经典的必衍之义。而经书之“文法”,又与古文义法有莫大的干系。所以古文家以文章义法阐说经文经义,是名正言顺说经之途。“阎百诗、江慎修以来,诸说纷纷并起,误由弃传习之明据,奋不根之怪论,悬改千载上列国之世纪故也。如施彦士等,殆犹未足比数。以近世矜创获背前载,往往瞢不审是以非,贻误后生,故不可不辨。”[17]70在他看来,经书文法乃是研究经典的“明据”。汉儒考训字义,不重视义法修辞等事对经文的作用,对经书全文的理解并不全面,其说经必然存在漏洞。清代汉学家“古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18]的观点,过于偏重说经中训诂音义的一方面,忽视了经典文章中的辞气、结构、文法等另一方面,以最古之诂强合经文之体,往往混杂滞涩,其义难通,更遑论由训诂而知悉文章中蕴含的圣哲之理。
在吴汝纶看来,文本解析是经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认为“自古求道者有赖于文”,那么在研究圣哲经典时从文法辞章的角度阐释经典自然也是考证经文、经义的一种方式。而“文章与时升降”,故而经典之文的文法结构和语词特征具有十分明显的逻辑规律和时代特征,可以将其作为考订字义、判断文句真伪的标准。他在《与王晋卿》一文中详尽地论述了这一问题:
窃谓古经简奥,一由故训难通,一由文章难解,马、郑诸儒,通训诂不通文章,故往往迂僻可笑;若后之文士,不通训诂,则又望文生训,有似韩子所讥“郢书燕说”者,较是二者,其失维钧。若汉之相如、子云,文章极盛,小学尤精,盖于诸经无不淹贯,惜《凡将》《训纂》诸制,后人不得见耳。子长文字与六经同风,又亲问故于孔氏,盖不徒习传师说,兼有默讨冥会、独得于古人者,惜不得此才解说全经。其采摭《尚书》,但自成其一家之言,故不能多载。然则其偶有解释,其可宝贵,岂复寻常。自汉以来,经生家能通文章者,独毛公一人,其说经独多得言外之义,其释《采芑》云:“陈其盛美斯劣矣”,此文家之微言也,他说经者不解此义矣。文事之精者,不欲以经生自处,所谓“《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也。唐宋文人,于《六经》能抉摘隐奥矣,其所短则古训失也。朱子于理学家独为知文,其说得失参半,又其文事未深,故古人微妙深远之文,多以后世文字释之,往往不惬人意。我朝儒者鄙弃其说,一以汉人为归,可谓宏伟矣,唯意见用事,于汉则委曲弥缝,于宋则吹毛求疵,又其甚者,据贾、马、许、郑而上讥迁《史》,蒙窃未之敢信。凡鄙意于《尚书》,其说如此。又汉人最重家法,当时老师宿儒,各有承授,后生笃守,不迁于异说,今世后学,实无专师,古书具在,乃不能观其会通,而斤斤于汉儒家法,此非子骏所谓“专守残而妒道真”者耶?尊论“不知训诂不能得义理”,其说精矣,至“不欲离训诂与义理为二”,则本亭林之论,于鄙心尚有未安。乾嘉以来,训诂大明,至以之说经,则往往泥于最古之诂,而忘于此经文势不能合也;然则训诂虽通,于文章尚不能得,又况周情孔思邪!故鄙意于学,谓义理、文章、训诂,虽一源而分三端,兼之则为极至之诣,孔孟以后,不见其人,自余则各得偏长;如谓训诂与义理不可离,则汉之儒者,人人孔孟矣,恐未然也[2]615。
上文专就经学研究方法讨论训诂与文法的作用。其所言“文章”并非文体,而是专于文法修辞的辞章之学。吴汝纶认为,辞章之学与训诂考证在经学研究中同样重要。为此他列举了从汉代考据诸家到唐宋理学家再到清儒的著述得失,说明历代学者对文章之法的重视程度影响了其说经成就的高下。在他看来,历来说经各家,习考据者不通文辞,不能尽得经书言外之义;而习理学者于经籍大义有所了解,但不谙训诂,难免错漏之处,且又于文事未深,其阐经释理之言往往拗于文辞。“义理”与“考证”二家所失者,皆在于难通经书文辞,因此需要从辞章方面入手,“因文求意”,方能得《六经》隐奥之处。他认为,前代文家说经能抉摘《六经》“微妙深远”之处,但失于训诂,且大多无心专主说经一事,后世自然难见其说经之作。通过对比与分析,吴汝纶将“文章”于考据、义理三者并立为解经之法,三者皆备,方能于经“言外之义”“周情孔思”皆能有所引发。他不排斥考据和义理,但更强调辞章在阐释经义时的作用。“因文求意”正是以文章之法解说经书的方式,恰好可以填补训诂考据于说经的不足,能使解经之文在文法逻辑、修辞规律等方面合乎经文原作。文章既臻于圣人之文,其义遂可得圣人之宏旨。
吴汝纶“因文求意”观点的提出,与桐城派宗师姚鼐“学问三端”的古文理论密切相关。姚氏以“义理”“考据”“文章”为“古文之学”三端,“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19]“若古文之学,须兼三者之用,然后为之至”[20]。即古文要兼收义理、考据与文法修辞之事三者之用。“学问三端”原本专为古文立论,吴汝纶却将其应用在了经学研究领域。在上文所引的《与王晋卿》之中,他将古文之学的“学问三端”移之说经,认为“义理、文章、训诂”三者“虽一源而分三端,兼之则为极至之诣”。就说经方法而言,三者兼习方能全面地理解古圣昔贤之意。其中以“训诂”易“考据”,乃是针对王树枏来书中“不知训诂不能得义理”和“不欲离训诂与义理为二”的观点来说的。在他看来,经书也是记载圣哲之教的不刊之典,其中蕴含的“道”是介由文章的形式表现的,“凡吾圣贤之教,上者道胜而文至,其次道稍卑矣,而文犹足以久;独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17]148。“道”与“文”为一体两面,不可分离。经文即是古文,是以古文理论也可以引申为解说经文的方法。“义理”“考据”“辞章”既然是古文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学问,那么必然能够在阐经释义中发挥重要作用。义理与考据之学原本是宋、汉二家的释经成法,而以“辞章”释经者则未见其门。故而吴汝纶专就“三端”中的“辞章”一事,另立“辞章”解经之门,即“因文求意”,并将其与“义理”“考据”一道归为治经之途。这也是他对桐城派古文理论在说经领域的扩展和运用。
三、“因文求意”的实际运用方式与特点
“因文求意”的说经方法与吴汝纶对于桐城派古文之学的理解息息相关,类似于桐城文家对古文“精”与“粗”的分析。刘大櫆曾将文章之神气列位“文之最精处”,音节为“文之稍粗处”,字句为“文之最粗处也”。“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21]。神气与音节、字句之间的由“高妙”的文法相连。从古文创作的角度而言,为文欲得古文之神气就要在字句与音节中下功夫,掌握古文“高妙之法”;而从说经角度来说,古圣昔贤文字中的字句和音节也蕴含着“高妙之法”,把握了这种“高妙之法”,便可推求古人之“神气”。“因文求意”在说经中的具体施用方式即是出自于桐城派这种作文方法。它将文章体势、逻辑结构、辞气笔法有关的“文法”视为经文之表,而“经义”则为经文之里。研究者通过解读表层的“文法”探寻“经义”的所在。这一方法有别于汉宋任何一家的治学方法,是纯属于古文家的治经方式。通过分析文章的体势、结构、辞气等是否符合古圣昔贤的文法标准,从而推解经义、考辨经文,这便是“因文求意”在说经中的实际运行方式。尤其是对于经书中意蕴微妙幽深之文,只有通晓文章之体势脉络,辞气之轻重缓急,方能探知经书本义。吴汝纶在《记写本尚书后》一文中详论此法曰:
扬子云最四代之书,以为“浑浑尔”“噩噩”“灏灏尔”,彼有以通其故矣。由晋宋以来,士汨于晚出之伪篇,莫复知子云之所谓,独韩退之氏称虞夏《书》亦曰“浑浑”,于商于周,独取其“佶屈聱牙”者。诗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信哉!其徒李汉叙论六艺,又曰“《书》《礼》剔其伪书之伪”,盖自此发。且必退之与其徒常所讲说云尔,而汉诵述之,不然,汉之智殆不及此。圣人者,道与文故并至,下此则偏胜焉,少衰焉。要皆有孤诣独到,非可放效而袭似之者,知言者可望而决耳。吾犹惜近儒者考辨伪篇,论稍稍定矣,至问所谓“浑浑”者、“噩噩”者、“灏灏”者、“佶屈而聱牙”者,其瞢然二人莫辨犹若也[17]51-52。
由上文可见,文家“因文求意”考辨经书之举,汉代以降,不绝如缕。自扬雄至韩愈以及韩门弟子皆是文章解经之法的传人。自来经学家以义理、考据推解经文,各衷一是。习义理者疏于文字音义之训;习考据者遗乎圣哲之意。而对于古经中“浑浑尔”“噩噩”“灏灏尔”等难以训诂和厘清大义的部分,考据家和义疏家皆无法解释其意。要通晓这些似是而非的部分,就需要从经文的文法层面分析体势、结构、修辞方法和语言色彩等。介由这些文章文法层面的表象进行分析和解读,方能把握圣哲为文的主体思路和要领并因此领会经文真义。吴汝纶认为,圣人经典本是“文”“道”兼至,此后随时之降而文有稍衰,然皆有独到之处。而后世伪书的摹拟之文,或于“道”,或于“文”,皆不合古人之义,故而深知文事者“可望而决耳”。这便是他所谓“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的观点,即通过判定文章行文之法是否符合古人立言的规范,考察文章是否符合古圣昔贤之意。
吴汝纶在践行“因文求意”的过程中始终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所论纯然出于经书文本。而对于汉宋两家的经解成说“无所不采,而亦无所不扫”。施培毅将其解释为:“只要是对的便采收,错的便‘扫’。扫起来不仅去门户之见,也不在乎其人在经学界的地位。”[22]通观吴汝纶的经说实绩,“因文求意”在说经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考证与释义兼备。吴汝纶“因文求意”的观念重在强调“文”的作用,他将上古经书之文视作“古文”。在他看来,既是“古文”,必然遵循“有物”与“有序”两个规律。故而在分析经典文章时,他也会从“文法”与“文义”两个角度立论。从“文法”角度分析文章的结构和修辞,综合文势与词语的特质进行考证,有类似汉学考据的特点;“文义”则不规于宋儒对经义的理解,而是回归经书文本,从句义连贯的角度,通过考究上下文义和理解全书含义。这种阐释经典的方式不仅可以训诂经文字句,还能在整体方面把握经文内容,使其不会因为拘泥于一字一句之诂而忽略全文之意。如他在解释《尚书·顾命》“上宗奉同瑁”一句时,便不赞同段玉裁的说法,“段茂堂乃据《正义》,谓郑注云:王既对神,则一手受同,一手受瑁,定古文兼有同瑁二字”[2]285。吴汝纶则认为原本无“瑁”字,从文义看来,“同”“瑁”皆有酒杯之训,二字语义重复,而上古文章质简,绝不可能“同瑁”连文。因此他断定“瑁”字为“冃”之音训,是郑玄误从虞翻“古冃似同”之训,后世疏家“乃增‘瑁’于‘同’下”,疏家因之,故成“同瑁”之辞。“若孔疏所云‘一手受同,一手受瑁’,明是唐人义疏谫陋之语,不似汉人文义。况郑君注经,词皆简奥,岂有此等鄙俚文字哉!”可见“因文求意”能够同时考证原文和阐释经义,一方面根据古文用词之法考定文本,另一方面着眼文体风格确定文义。较之汉学家通过前人训诂来确定经书原文的方法更具说服力。可见“因文求意”能够从考证与释义两个角度解读经书,在可靠性方面有时能够超越汉学诸家。
第二,于古有征。历来的桐城文家以古文之法考论旧藉,往往招至“空疏”之讥,因为在汉学家看来,古文家以文法为考据方法,其说多异于汉儒。且于古书无征,近乎空谈。即便有些“异论”看上去合情合理,但缺少他书佐证,难以令人信服。如翁方纲曾论姚鼐说经“以丝衣说吴怃音近假借字为极当,但惜其无他佐证”[9]17。缺少有说服力的古书作为明证,是以文法释经的古文家们面临的一个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吴汝纶在论证上尽量选取汉人撰著作为例证。本着“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的观点,他以《史记》作为《尚书故》训诂经文、考据经义渊源,以扬雄《太玄》作为《易说》的渊源,“仆说《易》以《太玄》为主,说《书》以《史记》为主”[2]164“拙著《尚书故》,本旨专以《史记》为主,史公所无,乃考辨他家”[2]163。因为《太玄》与《史记》在行文方面近乎古圣昔贤之文,所以其说经亦必契合圣人之意。正如贺涛所言,“既庶几乎圣者之作,其于经必有默契于微二人独得其真者”[3]164,《太玄》和《史记》作为汉代经典,其中关于《周易》与《尚书》的论断,亦是不能被清代汉学家忽视的考证实据。吴汝纶以《史记》《太玄》等汉人著作作为因文求意的例证来源,是对“于古有征”考据原则的认同,客观上增加了“因文求意”的可信度。
第三,重视行文。吴汝纶不赞同乾嘉以来汉学过分强调字句训诂而忽视说经文辞的观念,尝言:“汉学以耳目为功,其行文尤可鄙笑。”[2]570他以汉、宋二家治《易》得失为例,说明说经文字的行文之法对于经解著作的影响,曰:“自太史公父子以‘昭明世,正《易传》’相付受,后无继述。两汉言《易》家大抵以小数异术附会《易》文,不能究知作《易》闳旨,各据所传习为说。近世儒流,乃舍本经而高信之。其为说支离僻晦,未有能逮《易本义》之洁约者,而后生末学,靡然共趋,群弃朱氏《易》若敝矫焉,不其惑与!”[17]203-204在他看来,太史公文法高隽,其说能传《易》之正解。两汉诸儒采小数异说,不重本经文法,导致其说混杂,经书本义反而不显,后世汉学家执迷此途,其说益失之偏僻支离。而理学家朱熹之所以能够在《易本义》中将经书大义明确地表达出来,并获得广泛地认可,便是因为其文理“洁约”。故而吴汝纶十分重视说经文字的文法表达,无论在自己的说经著作还是与他人讨论经解的信件中,都十分重视阐述文字的文法规律的逻辑,努力避免汉学著作中常见的由大量的列举例证和逐字分析导致主要阐述对象的混乱。他在提出观点时往往正反对比,突出观点的独立性;在例证分析时言简意赅,只列举最能够说明观点的证据,使说经文字不至于迷失在细碎庞杂的例证之中而忽略了阐述观点的作用。将这种审慎的态度应用在经说之中,非精研文字古文家而不能。故而“重视行文”也可谓“因文求意”独有的一个特点。
四、“因文求意”的评价与影响
吴汝纶对于自己的治学之法颇有自信,认为其说经之著“过于诗文”。然而代表其经学成就的《易说》和《尚书故》两部专著,却直到他过世之后方于家刻本中刊印。此二书问世之后,几乎没有得到当时学界的反馈。关于吴汝纶的经学观念和学术成果的评价也大部分来自其生前的亲友和门下弟子。
张裕钊作为吴汝纶多年的知交好友,对吴氏的说经观念了解最深。他也认同古文家独特的解经方式,曰:“好学深思之士,颛取古人之书,反复而熟读之,以意逆志,达于幽眇,其所得盖有远出寻常解说之上者矣。拘文牵义,骛华炫博,好为枝词碎说之徒,乌足以知此哉?”[11]12张裕钊肯定吴汝纶的经学功底,赞赏其博识广见,能发前人所不能:“阁下说经,闳识博通,自谓不于乾嘉诸儒门下乞生活,诚然。”[11]464又能细致入微,使人增长见识:“闻阁下论古抉摘杳微处,使人智识增倍,尤为得未曾有。”[11]472总体来看,张裕钊肯定吴汝纶经学成就,称赞吴氏“为自昔诸儒所未及,盖不独高出国朝为汉、宋二家之学者而已”[11]467,是间接承认并赞同吴氏说经所使用的不同于汉宋二家的方法。至于吴氏的门生弟子,大多对其师的说经著作给予了积极评价。“所著《书》《易》经说,于千古疑滞,条理咸晰,而文体犹崇绝。门人邯郸李景濂读之,叹曰:‘古今惟司马子长、韩退之吾不敢知,能此者无第三人矣’”[1]。在吴门弟子之中,贺涛对于“因文求意”的理解最为恰切。他曾应吴闿生之请为二书作序,序中言“因文求意”之旨颇得吴氏真谛。曰:“是故欲穷经者必求通其意,而欲通其意必先通其文。文从而后辞获所安,俯仰无所戾,义与事比,出入不离宗,求肖乎经而止。经之意之寄于文者,其法盖如是也。”[3]164贺涛肯定文章对于表情达意的作用,“文之用至广,经者群圣人所作,其至焉者。神志所措注,旨趣所流溢,既一寄之于文”,所以相较训诂、义理,由文法所得者更合圣贤之旨,“即文以求之,如亲与群圣人相接对,瞻容色,听声气,而唯诺于其前焉,更何有揣测之劳、扞格之患?”这种评价虽然不免将“因文求意”的成果描述得过于理想化,但却准确地表达了吴汝纶论学的要领。作为桐城派晚期重要的古文家,张裕钊与贺涛对吴汝纶经学理论的态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的理解并赞同“因文求意”的说经方法,认可他将古文家之“能事”拓展到学术领域的实践,而对于吴氏经学研究成果的讨论和反馈却不深刻。
在经学领域,比较重要的反响来自吴汝纶的另一位弟子尚秉和。尚氏作为近代易学耆宿,青年时期曾就读于保定莲池书院。他对“易”之本诂的见解,即本于其师《易说》中的观点:“吴先生曰:易者占卜之名。”[23]他在《周易尚氏学》的《说例》中引用了吴氏的观点,并且明言自己研究《易》受到了其师的影响:“吴挚父先生《易说》于《大畜》云:‘凡阳之行,遇阴则通,遇阴则阻。故初、二皆不进,而三利往。’于《节》云:‘《易》以阳在前为塞,阴在前为通。初之不出,以九二在前;二则可出而不出,故有失时之凶。’此实全《易》之精髓,为二千年所未发。愚于《易》理粗有所入,实以此数语为之阶。故特揭出,以尊师说。”[24]但他对于“因文求意”的说经方法和《易说》中其他有异于前人的见解,却未作评判。盖吴氏解经,其方法与结果都未免标新立异。从方法上而言,“因文求意”需要研究者在熟悉经书文本的同时全面掌握古文行文之法,对研究者自身的学养要求极高,“学不逮子贡者殆不足以定之”[17]39;而有的结论又过于新奇,“皆古人未言,亦无字书可证,悬空臆决,未必有当于人心”[2]164,令读者难以信服。要之,“因文解经”的方法既难施行,又难接受,且时逢国势日艰,传统学术光焰渐熸的晚清之世,其不被当时的学界认可也在情理之中。尽管在《易说》与《尚书故》问世之后,其子吴闿生又遵照二书的基本内容刊刻了《周易大义》和《尚书读本》,作为方便初学者阅读的文本,却依旧反响冷淡。
从经学研究的角度而言,吴汝纶“因文求意”的研究方法和相关学术成果没有被学界广泛了解并接受,然而从古文之学的立场看来,“因文求意”,代表着桐城派古文理论在学术领域的一次成功的实践。他从文法、修辞的角度判定真伪、解说经义,是古文家“能事”在经学研究方面的具体应用。通过实际研究将古文之体作为圣哲之道的表征,不仅反驳了历来汉学家对桐城派“空疏”的讥议,还论证了桐城派古文之学在阐释经典方面的作用,从实用的角度提高了古文的地位。如此看来,“因文求意”对古文的意义远大于经学。然而随着西方知识与学术思想的不断内骎,包括经学与古文之学在内的传统中学皆受到严重冲击。“因文求意”的观点尚未引起相当的关注就随着中学的衰落而泯于时代思潮之中。在吴汝纶身处晚清末世,学者们优游经史、谈艺论学之盛景已不复现,取而代之的是动荡的时代带给人们的危机意识和紧迫感。较之乾嘉时期,晚清治经学者锐减,纷乱的时局促使士人们更多关注与存亡有关的政事、西学等方面,不复关心经史辞章。连他自己也曾感叹道:“天下多事,吾辈沾沾于此,真乾坤腐儒也。”[2]101“方今欧美格致之学大行,国之兴衰强弱,必此之由。吾国周孔遗业,几成绝响,一二腐朽书生,龂龂抱残守缺,于身世何所裨益”[2]153。吴汝纶半生谋求以改革教育,力图以新学教化国民、挽救衰世,对于传统学术之存废抱有矛盾的心理。他生时坚决不许自己的著作刊行,或许正是出于这种考量。然而对于当今社会的研究者来说,吴汝纶在经学方面的观点和成就不可忽视。通过研究其不被重视的说经著作,才能够更全面地把握吴汝纶乃至晚清桐城派文家对古文的认识和改造,以及他们在思想变革之际为保存古典学术和文学所作的努力。
——论《江格尔》重要问题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