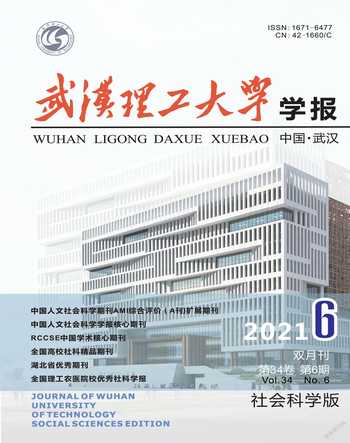库普兰德小说《X一代》中的逆托邦与异托邦解析
秦臻 陈世丹
摘 要: 加拿大作家道格拉斯·库普兰德的小说《X一代》涉及在乌托邦基础上诞生的逆托邦和异托邦。以怀旧为主旨的逆托邦是乌托邦在时间维度上的倒退,是继现代性返魅之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衍生出的另一幻象。小说中的棕榈泉逆托邦暂时缝补着过度现代性造成的主人公自我身份的断裂,为其提供虚假的意义感。异托邦是乌托邦在空间维度上的变体,在继承乌托邦的批判性和激励性的同时,透过自身特有的异质性表征、抗议和颠倒传统文本空间和常规社会空间的权威地位。通过建构社会异托邦和文本异托邦,主人公最终抛弃对逆托邦幻象的误认,直面残酷的真实。
关键词: 库普兰德;X一代;逆托邦;异托邦
中图分类号: I711.07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1.06.018
《X一代》(Generation X,1991)是加拿大作家道格拉斯·库普兰德(Douglas Coupland)的第一部小说,因其准确反映了当时北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特点,小说一经面世便引发了读者的共鸣,1960至1970年出生的世代也由此正式得名“X一代”。在数学中代表未知数的字母“X”精妙概括出X一代在外界眼中的形象——因摇摆不定和难以捉摸而无法被定义,也暗示着他们面对未来时的迷茫状态。媒体眼中的X一代明显缺少父辈(“婴儿潮”一代)的自信,“他们身上具有很深的悲剧性,而且是一种尚未被说明的悲剧……面对广泛的混乱,他们沉默,等待,使自己被遗忘”[1]。身为X一代中的一员,库普兰德拒绝上述标签式定义,认为X一代所谓的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中内隐着暗流汹涌的反抗和永不停息的自我颠覆。通过描写主人公从执迷于逆托邦到建构异托邦的历程,库普兰德揭示了X一代性格形成的根本原因,并以此为切入点深入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建构机制及运行规律。主人公的逆托邦思想诞生于世界去魅引发的未来失信,是乌托邦在时间维度上的倒退,蕴藏着回到部落、回到霍布斯、回到子宫的危险怀旧倾向。库普兰德透过异托邦之“镜”观照和反思常规空间,批判性地揭示了逆托邦的幻象本质,引导我们质疑传统意识形态的神话地位,打破现存秩序的结合力,穿越“对象a”替代物的重重遮蔽,不断接近真实。
一、 乌托邦基础上的逆托邦和异托邦
鲍曼(Zygmunt Bauman)在其遗著《怀旧的乌托邦》(Retrotopia)中提出了“逆托邦”(retrotopia)(又译“怀旧的乌托邦”)概念。逆托邦是以怀旧为主旨的乌托邦,它从乌托邦的“否定之否定”中出现,是乌托邦“被拒绝之后的复活”[2]13。由于逆托邦同时具有怀旧和乌托邦两者的特质,因此在探讨逆托邦的产生根源、特性及作用之前,有必要首先对鲍曼的乌托邦思想进行简要概括。鲍曼赞同布洛赫(Ernst Bloch)对乌托邦的广义界定方式,认为乌托邦是一种超验的、希望的、处在“可能性”范畴中的精神信念,而不是狭义层面上有特定蓝图的、必然会实现或已经实现了的、威尔斯(Herbert G.Wells)式的“理性王国”(the Kingdom of Reason)。鲍曼认为,理想家园式乌托邦是对莫尔“乌托邦”的失败模仿,前者在科学教条体系的监视和控制下,遵循历史知识和特定社会规划建成,失去了冲突和偶然性,因而失去了乌托邦精神中最重要的超越性。鲍曼的乌托邦是一个持续指向远方的起点,是不断“生成”(becoming)的选择和人类行为中的“活力在场”(activating presence),它批判世界现行状态的非自然、非必然性,激发个体改变当下的意志和潜能[3]16。
从鲍曼的论述中可归纳出乌托邦诞生的两个必要条件:一是由现存社会状态引发的人类“内在强制”(imperative),二是从“希望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hope)中产生的人类自信,两者缺一不可,从客观和主观层面合力促进乌托邦精神的生成。“内在强制”,即一种不可消除且无法餍足的离开此地而另寻别路的渴望。當人们意识到眼前的世界并非向来如此,而是人为设计和创造的可能世界之一时,便对“其他地方的事物”产生了情感,试图发挥人类行为的可选择性,“从他处寻找当下世界的替代物”[2]6。内在于人生存结构中的这种精神冲动引发人类对现存社会制度的反思,激励他们产生改变现状的意图。“希望的原则”关乎人类改变现状的信心,即相信在人类的运作下世界“可以被塑造成更适于满足人类需求的形态”[4]180。人类以工具理性为武器将自然降格为驯顺之物,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成功经验赋予人们征服社会的信心,相信可以把相同的能力运用在社会和思想领域中,获得类似的成就。总之,人类对另外社会的强制性欲望结合从征服自然的历史中获得的自信为乌托邦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在经济超速发展的后工业时代,希望的原则随着权威性和确定性的消解而逐渐失效,人类信心广泛缺失,在内在强制力的单独推动下,人类改变社会的意图经历了从未来到过去的转向,怀旧病由此接下进步狂的接力棒,势不可挡地在全球流行。鲍曼改写了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历史哲学论纲》(Thesi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关于“新天使”(Angelus Novus)的论述,用以隐喻这场灾难性的逆向风暴:“历史的天使现在又在拼命挣扎……他却改变了方向,脸从面向过去变成面向未来……而这次的风暴是从人们预期和忧惧的未来的‘地狱’刮向过去的‘天堂’”[2]1。正如鲍曼在《现代性和大屠杀》(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中描绘的那样,“进步”一词如今更多的与社会恶化而不是改善与提升相关联,往往引起与康德创造它时的原意相对立的情感——对迫近的灾难的恐惧。人们不再“去那尚未诞生、因此尚不存在的未来中寻找幸福”,而是“从那已失去、被盗走或被抛弃却未死的过去中寻找各式各样的乌托邦”[2]8。逆托邦是乌托邦在时间维度上的倒退,强调在时间性上不是向前看,而是逆转为向后看,往回看。
通过对比乌托邦和逆托邦的基本特性,可以进一步揭示逆托邦的本质。根据鲍曼的论述,可以概括出乌托邦的如下四个特性:第一,乌托邦是区分善恶的标准,具有批判性;第二,乌托邦是社会行动的向导,具有激励性;第三,乌托邦是无场所的“非在”,具有虚构性;第四,乌托邦发挥与众不同影响力的关键——超越性。乌托邦永远处于布洛赫所说的“尚未”态,人们透过乌托邦的未来视角回看当下,从而不断颠覆和超越现在。逆托邦摒弃了乌托邦的虚幻性,继承了乌托邦的批判性和激励性,却丧失了其最关键的超越性。在时间上,乌托邦立足当下、指涉未来,而逆托邦却固守过去、排斥现在、拒绝未来;在空间上,乌托邦兼具现实与非现实两种样态,逆托邦却在“故土”或“家园”中找到位置。乌托邦自身所固有的时空矛盾被詹姆逊称为“断裂”,和德里达的“延异”异曲同工。断裂造成认同与差异之间的张力,是乌托邦内在的转化势能。逆托邦却固守秩序的地方性,抛弃不断追求完美的思想和无休止变革的观念,排除未来的可能性,从而丧失了推动社会的根本动力。通过描写主人公的怀旧生活,库普兰德应和着鲍曼对逆托邦的批判,并进一步揭示出逆托邦的幻象本质。
尽管乌托邦精神受到鲍曼等哲学家的推崇,却无法避免其日渐式微。从“乌托邦已死”到如今的逆托邦趋势,乌托邦的衰落可在当今时空关系的新变化中找到原因。19世纪是迷恋时间的世纪。一方面,单向、连续、有始有终的线性时间表征着传统秩序的同一性,为宏大的历史书写提供叙述模式;另一方面,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导致了“迟缓的乡村时间”和“令人眼花缭乱的都市及工业化节奏”的共存[5]。进入20世纪,乡村被城市化进程收编,两者时间上的不同随之消失,时间彻底失去神圣性。乌托邦在时间的发展和历史的延续中蓄积张力,当人们不再信任时间,乌托邦也就丧失了其超越性和势能。福柯的“异托邦”是乌托邦在空间维度上的进化,它是“被实际实现了的乌托邦”,又在反映常规空间的逻辑上构成了乌托邦的反题。作为“真实的在场”,异托邦继承了乌托邦的批判性和激励性,又同时具有现实性;作为“反位所”,异托邦用空间异质性替代了乌托邦的时间超越性,发挥出后者所缺乏的实证性[6]16。
二、 逆托邦的幻象本质
作为逆托邦终极指向的“怀旧”(nostalgia)最初被用以描述远征士兵因思念故土产生的一系列病态生理症状。随着城市对乡村的同质化进程,空间维度的“乡”已无处可寻,指示“家”的路标被迫转向时间维度的“旧”,怀旧因此演变成一种“回望过去”的情怀,甚至从需要被治疗的生理性病症颠倒为心理学上用于应对焦虑的康复手段之一。究其本质,怀旧是一种“损失-替代情感”,是“身处生活与历史加速剧变时代的人们的一种防御机制”[7]33。X一代以“回家”的欲望替代真实阶级对抗,用“过去”的幻象治疗个体社会创伤,通过理想家园与当下现实的对立、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建构“回到部落”、“回到霍布斯”、“回到子宫”的逆托邦。
三位主人公从现代化都市搬到原始小鎮的怀旧行为发源于“回到部落”的渴望。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指出,怀旧的实质在于通过“承诺重建今天诸多有影响的意识形态一味主张的理想家园,引诱我们放弃批判思考,而代之以情感团结”[7]35。在《怀旧的乌托邦》中,鲍曼用最大限度维护本族利益的“部落”一词作为共同体的隐喻,表述个体对回归“理想家园”的渴望。在主人公所处的后工业社会,作为传统怀旧对象的乡村和信仰已不复存在,享有共同历史、遵守集体惯例的共同体成为处于具体和抽象之间的怀旧替代品。小说中的棕榈泉是一个典型社群性共同体:它位于美国西部科罗拉多沙漠的山谷之中,是一个“处处散发着中世纪味道”的小镇。这里人际关系简单,没有中产阶级,大多数居民是老人;人们的日常生活单调甚至贫乏,没有“固定文件的曲别针、浸泡衣物的柔顺剂或电视剧的重播”;成员们形成私密的、拥护特定文化的小群体,拒绝陌生人侵入[8]16。作为复杂、危险、动荡的社会现实的对立面,棕榈泉在主人公心中呈现出简单、安全、稳定等特质,具有安慰人心的力量。棕榈泉社群只是共同体在具象层面上的表现,主人公们的怀旧对象实则存在于更抽象的层面之上。三位主人公带着两只狗住在远离主街道的平房里,小平房像是“一个古怪、禁止生人入内的花园”,在这里他们“有足够的空间躲藏、迷失、伪装”[8]48。主人公所“思”之“乡”,是思想上的乡,是能够容纳他们理想身份建构的想象空间。博伊姆指出,“怀旧病的危险性在于它往往将想象的家园与实际的家园混为一谈”[7]34。从本质上说,“回到部落”的倾向是无家可归之人在“美好旧时光”(good old days)中寻找具体的或抽象的统一性家园的欲望,其要旨即在共同体及其感性气氛中寻找身份认同。棕榈泉共同体产生于“个体选择之后而非个体选择之前”[4]89,是主体回溯性想象的产物,作为抽象的、想象中的共同体的意义大于其实际意义。主人公心甘情愿地被共同体的同一性收编,以期在群体网络中定位自身,重获失落已久的意义感和归属感。
“回到部落”的逆托邦是X一代对同一性的欲求引发的回溯性建构,这种建构是在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基础上进行的。鲍曼指出,共同体的凝聚过程就是排斥他者、清除差异的过程。怀旧者常常将有损其自我连续性的“陌生人”排除在怀旧时空之外,通过分离他者完成自我身份的建构,这场“净化仪式”最终实现的无非是怀旧者“建立在排斥基础上的想象性自卫”[9]。同他者的对立引发了人类特有的攻击性和暴力倾向,使其重新释放出人性中被社会规则和现代礼节抑制却从未被驯服的“霍布斯式的兽性”[2]25。主人公戴戈对上代人和同龄人均显示出强烈的对抗心理,将他们视为实际的或潜在的敌人——世界是“被上一代弄脏的内裤”,前上司“挑走最好的那块蛋糕并在剩下的周围拦上带刺的篱笆”,同事们“专注于勾心斗角,为金钱身份地位努力拼抢”[8]56。对他者的敌意升级为愤怒的行动:因为路边一辆汽车上贴着“我们正一点点消耗着本属于我们孩子的一切”的标语,戴戈突然暴怒,打着“惩罚那些浪费我们资源的人”的旗号用石头在车上乱划;另一次,他用香烟在写着类似标语的敞篷车上烧洞,引发的大火将车完全烧毁[8]149。在“回到霍布斯”的逆向趋势中,社会“从共享改善的语篇转移到了个体生存的语篇”,人们“被重新命名为‘竞争性的个体’”,都在随时准备向对方发起责难[2]27。
为了重获“已失去的、与某种神秘力量相接触的机会”,三位主人公花费大量时间“体会孤独”:在沙漠中无目的地开车数小时,“大”字型躺在路边空地上直视太阳,在房顶平台长时间眺望圣安地列斯山脉,全身赤裸地浸泡在院子的水池中直到皮肤发白[8]69。他们醉心于回返不受外界打扰的安然平和的状态,这种回归母体、回归前语言阶段的欲望被鲍曼称为“回到子宫”。鲍曼的“回到子宫”类似于对拉康的回返“实在界”(the Real),即达到母子合二为一,没有任何“缺乏”(lack)的乌托邦状态[10]120。但拉康指出,人一旦经过父法的阉割,成为被言说的主体,回返实在界就已成为不可能。实在界只能出现于主体的回溯性想象中。主人公们所追求的逆托邦是拉康-齐泽克意义上的“幻象”。根据拉康的幻象公式,幻象就是分裂的主体对“对象a”(object a)的欲望。“对象a”是实在界被符号化之后的剩余物,它无法被语言描述,是一个纯粹的能指,“一个纯粹的短缺和虚空”[11]72。所有可以用语言表达的欲望对象——事业成功、财富自由、婚姻幸福、声名显赫——都是对象a之替代物。对象a在引起人们连绵不绝的欲望的同时,又使欲望之满足变得不可能,它是主体孜孜以求却不可复得之物和无法彻底摆脱之痛苦。对象a作为一种“不在场的在场”,通过不断引发主体的欲望,诱使主体建构意识形态幻象,用以掩盖实在界剩余所带来的“灼伤”。幻象发挥着“屏障”作用,这道屏障将大他者的不一致性掩盖起来,避免人们直面不堪忍受的实在界内核。齐泽克也指出,“幻象的功能就是填补他者中的空缺,隐藏其非一致性……透过它,我们把世界体验为一致性和有意义的”。只有“穿越幻象”,剥离出意识形态所隐含的快感内核,才能重新释放出主体的自由[11]75。《X一代》中,主人公们和主流社会彻底决裂,这似乎意味着他们成功穿越了幻象,认清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追求的一切不过都是对对象a的误认,但实际上,这种虚假的穿越反将他们引入了更深一层的误认:他们误以为棕榈泉的怀旧生活能够带来母子合一般的原初快感,并未意识到实在界从来就是无路可返的。逆托邦是“超越幻象的幻象”,它作为对象a的另一替代物,继续遮蔽着实在界快感的短缺,填补着引起欲望的空虚,却并不能真正弥合主体的整体性缺失[10]121。逆托邦幻象与梦境发挥着相类似的作用。梦的功能之一是延长睡眠,当做梦者感知到外界刺激,会立即建构一个包含这些刺激因素的梦,使自己不至于马上醒来。逆托邦幻象不过是使人继续睡眠、继续保持盲目性的梦境,在做梦者因丧失意义感而对当下的意识形态体系产生质疑的时刻被构建出来,转移着大众的注意力,维持着作为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可见,主人公并未真正穿越基本幻象,而逆托邦本身仍然在延续着幻象的结构。
就此,我们可以把X一代的逆托邦建构机制加以总结:面对历史连续性断裂的社会危机及个体归属感缺失的自我危机,主人公以隔离的方式拒绝主流社会的收编,在象征性的时间或空间中,运用“回到部落”和“回到霍布斯”的具体策略重建社会纽带,以期“回到子宫”,重获母子合一的快感。但由于实在界的不可回返,棕榈泉的自我边缘化生活只能作为对象a的替代物暂时缓解主人公们的创伤,并不能彻底治愈他们心灵的破败,弥合他们精神世界的殘缺。究其本质,主人公们追求的逆托邦同他们试图对抗的工具理性和消费文化一样,都是现代性返魅的产物。作为一种更不易识别的新神话,逆托邦以缝合的方式处理现代性带来的造成主体认同危机的一系列分裂,虚假地保证人们重获意义感。换句话说,以对抗伪装自身的逆托邦实则支撑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仍然是现代性的衍生品。
三、 异托邦的建构
面对“现在”的困境,人们在时间维度上寻求解答,构建出“指向未来”的乌托邦和“回到过去”的逆托邦。福柯却认为,当下普遍存在的焦虑与其说与时间有关,毋宁说与空间关系更密切。“世界正经历着像是由点线连接编织而成的网络版的生活,而非什么随着时间而发展的伟大生活”[6]15。线性时间主导的时代已经逐渐转变为空间并置的时代,运用时间逻辑进行的思考和建构已无法分析和解释“同时性的、并列的、远近的、共存的、散播的”空间状态[6]15。时间甚至变成了空间的一个维度,“也许只是显现为空间中绵延的诸要素间分布的诸多可能的游戏之一”[6]15。为了应对这一状况,福柯从空间维度重思乌托邦,提出一个“另类空间”概念——异托邦(heterotopia)。福柯曾给出两个关于异托邦的定义,分别涉及文本和社会两个空间。在文本空间中,异托邦是语言、语法本身的“异位”性质相遇的场所,是毁坏语言同时又建立语言的场所。在异质文本空间中,正常语法被反映和颠倒,语言的极限被挑战,从而引发人们对词与物内在连接、聚合方式的询问。异托邦也是表征权力、文化、知识的特殊社会空间,与常规社会空间构成表征、抗议和颠倒的关系。异质社会空间反映了常规空间运作逻辑及权力关系的非自然性,启发人们反思自身存在的状况。异托邦作为“镜子”一般真实存在的位所,呈现、反抗甚至颠倒其他场所[6]16。通过异托邦,我们得以跳出原有位置,从外在视角凝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常规空间,反思其机制、秩序和运作方式,从而抗议和颠倒传统文本空间和常规社会空间的权威地位。
小说中的棕榈泉就是一个起着镜子作用的社会异托邦,透过它,主人公得以重新审视之前视为真理的社会秩序和规律。首先,棕榈泉是有别于现代人生活空间的异空间。作为一个没有办公大楼、购物中心、电视转播的沙漠小镇,棕榈泉独立于现代都市的行列之外,是世人眼中的“其他地方”。其次,主人公也是常人眼中的异类、反叛者。他们打破了正常人求学、工作、结婚、生子的人生流程,在三十岁的关键年纪放弃了之前所积累的一切,过着在常人看来近乎自我毁灭的生活。安迪的邻居称他为“帕尔默家不正常的孩子”,父母为他“不停叹息”,弟弟泰勒评价他说,“你好像身怀重大秘密似的,总是无法进入‘俗人们’琐碎正常的生活”[8]123。偏离主流社会的棕榈泉和偏离生活常态的主人公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典型的“偏离异托邦”。福柯指出,偏离异托邦中表现出的他性是社会正常、普遍的连续链条“断裂”之处。通过观察和思考这种“断裂”,寻找连续性中不连续的原因,才能发现埋藏在常规空间中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标准[6]18。努力工作,贡献全部劳动价值;结婚生子,形成维系社会稳定的家庭单元……这些都是被世俗认可的、利于社会发展的活动。主人公们违背上述社会标准,因此成为被禁止和被排斥的对象,他们的“不正常”是当下文化标准建构出来的,而非一开始就存在的。棕榈泉既作为一个真实的小镇存在于社会中,又因他性独立于社会外,作为一个有着连接功能的关系场,它反映了正常社会空间的底层逻辑。更重要的是,它颠倒、反抗了正常空间的秩序和规律,使主人公意识到所谓“真理”只是被资本主义真理化的“真理”。
福柯指出,“在其历史过程中,一个社会可以造就出存在并将继续存在的异位,并以不同的方式来运作”[6]18。棕榈泉异托邦不仅在空间维度上呈现出偏离特质,还在时间维度上展现了不同文化的运作方式。在共时角度上,棕榈泉以“偏离”的角度存在于现代都市之外,反映和颠覆了社会规则的建构方式;在历时的角度上,棕榈泉虽作为固定的地理空间一直存在,其性质却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展现出不同的历史运作状态。棕榈泉位于加利福尼亚南部,地处沙漠中的谷地。20世纪50年代,一批房产开发商试图用“沙漠绿洲”的概念将这个美国西部的沙漠小镇打造为一个度假区和富人别墅区,棕榈泉也因遍布其中、体现“自然之美”的棕榈树和泉水而得名。这里一度聚满了对其前景充满希望的明星、富人和开发商,但最终开发以失败告终,喧闹的人群一夜间撤走,棕榈泉呈现出现在的状态——一種既非自然又非城市的面貌:小镇周围是大片的原始沙漠,从屋顶可以远眺圣安地列斯山天然的美景,但小镇上却遍布堆满碎石的马路、颜色褪尽的空房、废弃的加油站和死掉的棕榈树,成为“社会异类”的聚居地。从度假圣地到边缘小镇的棕榈泉在历史中既是同一场所又不是同一场所。作为现实空间,棕榈泉一直存在于美国版图之中,但其中反映出的社会文化关系却随着人类观念的发展产生了“变形”,这就是福柯所说的“同一位所的文化迁移”,是“空间的非空间性”,也是“文化的空间叠加问题”[6]18。当我们询问棕榈泉的空间场所在历史中是否依然同质”时,只有异托邦才能描述它既是同一场所又不是同一场所的叠加状态。
作为“文化叠加态”异托邦的棕榈泉暗含着作者对美国西部扩张史的隐喻。房产经纪人对棕榈泉的开发对应着西进运动中商人集团的土地投机行为。西进运动将远离喧嚣的田园变成文明现代的城市,塑造了以“天定使命观”为基础的美国国家身份意识,促成了通过自身奋斗实现美国梦的个人主义精神。棕榈泉的变化反映出美国何以成为今日之美国的一段重要历程,而棕榈泉从往日繁荣而复归平静荒芜,成为被主流社会排除在外的“异质空间”的变化过程,则暗示了都市建成的方式以及未来可能的命运:社会的形成源于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改造,而这种对自然的介入也会有被废弃和毁灭的一天。三位主人公在棕榈泉破败的街道上野餐,安迪看着满是空房和杂草的破败街景,眼前却浮现出了仿佛平行时空的故事,那是棕榈泉被成功开发后的模样:“同样是在这块空地上,矗立着……电影明星宽敞奢华的沙漠别墅”,安迪和朋友被邀请“享用屋内的泳池、加冰的朗姆酒、加州好莱坞式的落日和名流们的八卦新闻”[8]24。被成功建成别墅区的棕榈泉的幻影应和着它现实中的荒芜,两幅截然不同的图景形成强烈的对比,明确地展示出常规的偶然性和非常规的可能性,提醒着人们,现代都市并非从来如此,它们是自然被人类文明介入后的样子,这种改造不会永恒存在,而随时面临被废弃的命运。
主人公们还创造了一项“异质性”的活动——讲睡前故事。虽然名为睡前故事,但讲述的时间并不固定在睡前,也没有任何内容或方式的限制,唯一的规则就是听故事的人不能打断讲述者,且在故事讲完后不能发表任何评论。睡前故事虽然是口头形式的,却是由讲述人的言语、表情和肢体动作等构成的有机整体,占据了讲述者和聆听者的感知空间;同时,睡前故事在讲述方式、叙事手法、故事内容和最终目的等各个层面有异于主流文学,是传统文学空间之外的异质空间。因此,每个睡前故事都作为一个“文本异托邦”提醒着现代文学的最初起源。在书面文学诞生之前,“口头文学”(原始歌谣和神话故事)作为与人类记忆相伴共生的叙述模式,传递着集体经验与手工时代的价值观。通过唤起我们对文学原初形式的记忆,睡前故事质疑和反抗了现代文学的宏大叙事。此外,睡前故事的开始和结束是随机和任意的,不需要搭建情节和铺陈逻辑,讲述者可以无穷无尽地讲下去,也可以随时停止讲述。睡前故事的这个特点又将它和新闻故事区别开来。新闻通常需要包括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六要素,很难想象一则新闻是以“未完待续”结尾。睡前故事最大的特点在于意义的留白,而新闻需要即时获得反馈的模式已经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认知习惯,对结果的过分关注剥夺了故事自我阐释的空间。
睡前故事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对抗着以工作为中心、娱乐为填充的现代生活方式,同时它作为一种“口头文学”颠覆着现代文学和新闻故事的存在和表现形式。不仅如此,异托邦还存在于睡前故事的文本中,被主人公通过讲述的方式建构出来,是“文本异托邦”中的“社会异托邦”。戴戈的睡前故事多数是天启式的末日想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超市遭遇核爆炸”的故事。主人公和朋友目睹了世界灭亡的时刻:秩序在四散奔逃的人们眼中变得一文不值,他们用手推车互相冲撞,将商品丢得满地都是。在死亡来临的那一刻,没有人还在意文明和尊严。当“热浪从高处俯冲下来”的时候,主人公的同性朋友亲吻了他的嘴唇,这是他们生命最后一刻的记忆[8]90。福柯在讲述异托邦的六个特征时提到了这种具有“异时”性质的社会异托邦,它产生于人们“与其传统时间绝对的断裂时”,和时间的关联性表现在“其最徒劳、最短暂和最不确定的方面”[6]17。戴戈的故事将“个体失去生命”这个奇异的异时从线性排列的时间链条中提取出来,像观察空间一样对其加以窥视,在对日常秩序短暂的毁坏中,传统时间认知方式中被建构的规则——如秩序、文明、恋爱观等——变得荒谬和无意义,随时都可以被抛弃。主人公们在故事中共同创造的泰克斯拉欧玛星球也属于“异时”异托邦。他们将1974年(石油危机后一年)从地球的线性时间序列中摘取出来,放置在地球之外的小行星之上,保证了异时的累积和叠加。在这里,人类可以在永生状态下对传统生活意义进行反思和颠覆。
更为巧妙和复杂的是,有些故事中出现了同时具有“异时”和“异位”两方面因素的异托邦,例如“活在单词屋里的男人”。在用“单词”建成的魔力屋中生活了十年有余的爱德华再次踏出房门,他面对的是一个由“关系”构建的巨大城市,里面的建筑奇形怪状到让人无法理解,“有的像口红,有的像炮弹壳,有的像婚礼蛋糕和折叠的衬衫垫板”,城市里到处缠绕着“碳、冰柱和叶子花藤”,道路旁并列着巨型植物和黑洞,街角埋伏着投掷馅饼的小丑和拿着枪的儿童……虽然城市不售卖任何地图,人们却能在这一片混乱中毫无障碍地自由穿行[8]72。因为没有及时跟上城市的变化,错过了社会的统一收编,爱德华最终成为城市的漂流者。单词屋作为爱德华的个人空间独立于城市之外,具有空间上的异质性。爱德华“在与世隔绝的小屋里自得其乐地生活”,“他的同类们却在忙碌地建设”[8]72,相对于外界来说,单词屋的时间停止了流逝,又成为了“异时”。十年前的爱德华通晓很多单词,是同类中的佼佼者,从“异时”、“异位”中走出的爱德华却无法再用过去的思维模式解码由关系构建的新型城市,在他认知中毫无关联的事物——“巨型植物”、“黑洞”、“香水喷泉”和“咯咯叫的卡通鸡”[8]72——理所当然地并列出现,让他失去分类能力而迷失于无穷无尽的不确定性中。故事中城市人对爱德华的看法对应着现实社会中的普通人对精神病人的偏见。在熟悉社会空间秩序的城市人眼中,爱德华是个“精神错乱者”,城市人看到爱德华会“尖叫着,飞也似的跑开”[8]72,可对于爱德华来说,城市人又何尝不是疯子?透过单词屋异托邦,我们得以跳出常规位置,站在“精神病人”爱德华的角度观察和质疑早已习以为常的一切:我们熟悉的常规社会空间真的从来如此吗?我们看来井然有序的日常生活真的遵循着合理的秩序吗?我们坚信不疑的日常经验真的可靠吗?
总之,不正常的空间、时间和偏离的人都是异托邦的题中之意。不管文本还是社会空间的异托邦,具体空间还是隐喻空间的异托邦,在功能上都有根本的相似之处:它们都处在空间的特殊和极限位置,这样的位置使主人公意识到界限内的存在并非自然如此,而是被建构的并且正在被建构中,从而反思和颠覆这些建构和运作的逻辑。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曾说,“未知之物令人不安”,人类的“第一个冲动”便是寻找一个将未知转换为已知的解释来“消除这种令人痛苦的状态”[12]。但常识最大的危险性莫过于让我们停留在自我满足、自我中心和独断论中,“自以为对可能性了如指掌”[13]。异类的闯入总是给人们以惊恐感,因为它是使人焦虑的未知中的一种,但正是靠着这种未知性,异托邦冲破了长久以来秩序井然的关系建构,撕开了名为“常识”的面具,透过断裂的缝隙,我们得以探究深藏社会内部的运作逻辑和权利关系,反抗和颠覆那些之前从未想过可以被怀疑的“秩序”、“基础”和“真理”。
四、 结 语
鲍曼将人类发展比作一场接力赛,如今场上出现了极为危险的局势:逆托邦抢过乌托邦手中的接力棒,展开了对过去的追逐。“它可能改变跑道,但就是不会停下”[2]6。库普兰德认为异托邦的思辨力量可以阻止这种倒退。逆托邦试图将历史伪装成自然状态,异托邦则揭露所谓的自然的历史状态。处在空间并置的网状关系时代,以异托邦为镜观照现实,不断反思和颠覆现有认知,在批判中前进,是人们走向未来的最好方式。通过构建社会和文本异托邦,《X一代》的主人公们最终直面真实,彻底醒悟:他们身上的创伤是与生俱来、无药可医的。但他们并未就此坐以待毙,而是不断探寻出路。通过刻画主人公们打破常规、自我颠覆、追求真实的过程,库普兰德撕下了X一代身上“摇摆不定、离经叛道”的标签,为认清现实虚假本质却不放弃对抗,明知实在界不可回返仍不停奔跑的X一代正名,也表达出对这个世代的极大赞许和期望。
库普兰德始终坚信乌托邦精神的力量,虽然它在当今时代饱受质疑,甚至面临被逆托邦替代的危险,它却总是处在“尚未”到达的前方,激发着异托邦等更具适应性的新形式的诞生。正如鲍曼所说,“人们攀登一座又一座的山峰……永不满足的超越精神激励着人们去探索它们。人们每越过一座山都希望发现终途的宁静,然而他们真正得到的却是启程的兴奋”[3]141。在小说最后,三位主人公离开棕榈泉,再次启程前往墨西哥。与小说开始的那场怀旧之旅不同的是,墨西哥不再被认为是提供终极救赎的完美家园,而是他们决定不停建构的异托邦中的一个。像安迪故事中那个追逐闪电的人一样,他们将永不停止地在贫瘠的大地上逆风奔跑。
[参考文献]
[1] 杜布瓦.困惑的一代[J].蜀君,译.国外社会科学,1993(9):76.
[2] Zygmunt Bauman.Retrotopia[M].Malden: Polity Press,2017.
[3] Zygmunt Bauman.Socialism: The Active Utopia[M].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1976.
[4] Zygmunt Bauman.Liquid Time[M].Malden: Polity Press,2007.
[5] Fredric Jameson.The Aesthetics of Singularity[J].New Left Review,2015 (92):110.
[6] Michel Foucault.of Other Spaces [M]//Michiel Dehaene and Lieven De Cauter Ed.Heterotopia and the City: Public Space in a Postcivil Society.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8.
[7] Svetlana Boym.The Future of Nostalgia[M].New York: Basic,2001.
[8] Douglas Coupland.Generation X: Tales for An Accelerated Culture[M].New York: St.Martin’s Press,1991.
[9] Richard Sennett.The Myth of Purified Community[M]//The Use of Disorder: Personal Identity and City Style.London: Faber & Faber,1996:36.
[10]金浩.寻找香格里拉:从《日月》与《莲花》看西南边疆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书写[M]//陳思和,王德威.文学:2017秋冬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
[11]Slavoj Zizek.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M].London: Verso,1989.
[12]Friedrich Nietzsche.Twilight of the Idols: or How to Philosophize with a Hammer[M].Trans.Duncan Larg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187.
[13]Gaston Bachelard.The Poetics of Space[M].Boston: Beacon Press,1994:26.
(责任编辑 文 格)
3386500338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