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变革与文学变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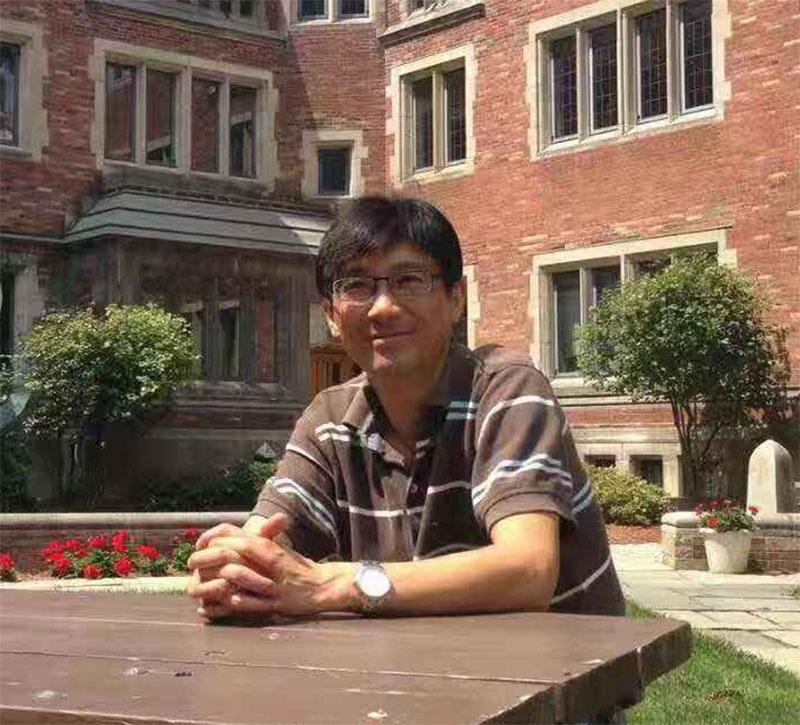
叶立文,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耶鲁大学访问学者。已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著有《史铁生评传》等多部专著。兼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曾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屈原文艺奖等多种奖励。
本期讨论“新经验与文学叙事的模式新变”问题。这当然是一个跨学科的宏大议题,因为单说经验之变,就涉及思想史、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多重领域。各领域学者不仅均有基于本学科的立场预设和价值期待,而且个人经验与研究方法也多有不同,因此要想从整体上把握新经验就变得十分困难。好在还有文学这个观察视角,当代作家对经验变革的细致书写,确实能够见出我们这个时代的认知模式的转变。
刘大先的文章,从讨论个体经验的有限性问题出发,以为本质化与真理性思维“可能化身为一种可欲的理想,但并非必然的实在”。既然“身处于历史进程之中的个体”,“很难窥破时代的真相与未来的趋势”,那么写作者不妨“要有某种企慕,一种源于经验又试图从中超拔出来的辩证”。唯有如此,文学写作方能“表达出要变化了的人和他的情感与精神,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重组”。
李浩的文章,具体分析了文学叙事模式的演进过程,以为这种变化“有一个或缓或急,或内或外的过程,一方面出自于文学创造性的自身诉求,而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与新经验的匹配。可以说,‘求新求变是文学永恒的内在趋动,它自然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文学的叙事模式”。由于“人类的认知和经验在不断的积累、变化与增殖,文学自然要与之做出同样的匹配才行”,因此“文学是人学”仍有其不断延展的新内容。
王晴飞的文章,则讨论了经验的新旧问题,指出“经验只有和主体融合,才会显出其意义,而同一经验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个体那里,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面目”。他主张“文学要切中更广大的人心,使我们更多地去理解、关心他人。当我们各自握着手中碎片化的观念、片面的知识而各执一词时,也只有文学的感受可以使我们放下偏执,想起‘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愿意倾听别人,习得感知他人苦痛与欢欣的能力。这是感受的力量,也是文学的力量”。
刘慈欣在《三体》中提到过一个“农场主假说”:农场里有一群火鸡,农场主每天中午11点来给它们喂食。火鸡中的一名科学家观察这个现象,一直观察了近一年都没有例外,于是它也发现了自己宇宙中的伟大定律:“每天上午11点,就有食物降临。”它在感恩节早晨向火鸡们公布了这个定律,但是这一天食物并没有如期降临,而是农场主进来把它们都捉去杀了。
这个故事来自于哲学家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对归纳主义的火鸡寓言,显然刘慈欣化用的时候指向于个体经验的有限性。也就是说,从近代以来的经验理性角度而言,个体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总是在某种方法与视角下进行的,这也注定了它不可能把握在其方法与视野之外的部分,理性的全知与对于世界本质式的理解已经被视作僭越与诞妄。对于个人的内部而言同样如此,心理学在精神分析话语与潜意识论说中,也失去了其绝大部分的领地,因为人们赫然发现许多时候对于人类精神与情感的探察只是流于浮表的层面,人性的复杂性与深度完全无法用巴甫洛夫式的生理反应一言以蔽之。
这给文学留下了巨大的生长空间,心理治疗大师维琴尼亚·萨提亚(Virginia Satir)的“冰山理论”,就直接被海明威化用了。人不仅仅是生理意义上的自然人,同时也是具有历史纵深意义的社会人,他也无法用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假设进行蜜蜂寓言式的推导,否则就无法解释伴随着人类经验的许多非功利乃至超功利的非理性献身与牺牲行为。经验的反映,不是是否能够把握世界准确性的问题,而是那种经由具体经验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带来本质与真理——充其量它们只是片面的洞察与局部的真相。
可以说,本质化与真理性思维在康德之后就成了一個可堪质疑的命题,它可能化身为一种可欲的理想,但并非必然的实在。因为这个世界变了,或者说我们的认知方式变了。面对着一个经历了并依然在进行着的现代性分化,专业化、区隔化乃至碎片化取代总体性、整全性,成为人们对待自身与世界的基本方式。这一点反映在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到现代主义的文学转型之中,也体现在史诗英雄那天人未分的集体性人格的宏阔生涯向小说主角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独自面对变幻莫测的个人生活的改变之中。所以,对于外部自然社会和个人内在心理精雕细凿的描摹与刻绘,让位于抽象隐喻般的寓言化表述,物理现实与心理现实的结合体现为现代派的各种技法所呈现出来的荒诞与变形。
这显示出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的认知模式转变——变化了的经验现实总会引发文学书写形态的变化。但这个问题并非自然而然出现的,事实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体现出一种不断演变的历史观,突破了循环论。这种文学史观念迟至中晚清焦循的《易余曲录》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才逐渐浮出水面。如今文学常识中关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观念,都是后来者后见之眼的归纳,如果回到文学现场,在宋朝甚至清朝的时候,诗还是文学写作的主流,只不过它们在后来接受者的视域中被边缘化了。近现代转型当中,中国人的时空观念、价值立场、知识视野都发生了天崩地坼般的变化,在文学史的书写中逐渐形成了影响到当下的历史观,对于既往文学历史的书写是在当代的视角和思维中进行的。强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导性文体,实际上是对过去的归纳、整编和经典化,为了凸显承传流变的脉络,为新型文学的产生提供合法性。就美学技巧而言,清诗较之乐府、唐诗无疑更为繁复精致,但变化了的现实使之丧失了接受者,影响力局限于文人阶层,无法与在彼时处于边缘位置的小说相抗衡。
对于身处于历史进程之中的个体而言,很难窥破时代的真相与未来的趋势,但是陷溺在经验的沼泽之中,则会让他泥足不前。因而一个写作者一定要有某种对于总体性与超越性的自觉追求,尽管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之任务,但他必须要有某种企慕,一种源于经验又试图从中超拔出來的辩证。换言之,写作者固然与他时代的经验现实要不可避免地发生关联,但它同时需要隔着一定的审美距离对经验现实进行凝视、审思与书写。我曾经在别的文章中分析过我们时代的多重现实,它是物理现实、心理现实与虚拟现实的叠合,甚至“增强现实”已经进入到日常生活当中,这一切带来“文化的融合”与“泛文学”的兴起,书面文字与印刷文化所形成的“纯文学”日益受到影音图文综合性媒介语境的影响,进而向“杂文学”或“大文学”返归与递进。
回到当下的经验的变革。2020年疫情影响下,似乎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思维,全球化的模式正在发生变化,但因为经济、技术与信息的交融,全球不同地方的人们都生活在彼此之间相互镶嵌而难以脱钩的共同体中。只是此前欧美中心所形成的“中心—边缘”的依附性世界体系面临着变革与重新改写的命运,这是世界格局大的语法的变革。从13世纪开始的大航海时代开始,伴随着印刷文明对知识的普及,工业化、商业化和殖民主义,欧洲兴起的地方性播撒为一种全球的普遍性。中国也在19世纪被迫卷入到世界史,以后发现代性的面目进入到欧美为中心的世界结构之中。在中国经过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加上冷战格局的瓦解,民族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复归,原先的世界结构显然也在逐渐发生变化。11月15日,RCEP协议的签订,中、日、韩、澳、新与东盟十国构建新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这也说明中国和亚洲试图在形成自己的世界关系平台。
从与文学关系更为紧密的媒介语境而言,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直接与间接经验极大丰富、纷至沓来,既有的经验可能会迅速失效,红极一时的现象也许昙花一现,其结果一方面是造成新兴经验在不同代际、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反哺与互动;另一方面纷至沓来的经验冲击则作用于受者的感知力,带来新感受力的产生。但同时,也不能不警惕信息茧房与“玻璃屋子”的现象,也就是说信息自身的增殖反倒可能带来对世界认知与理解的狭隘化。我们在当下可能要做的是摆脱真相思维或者本质思维,文学的总体性无法体现为全面搬演现实、总结规律、发现真相,而是在描述与想象中绽放出真理的一角。
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经验究竟是什么?我想不能完全沉浸在琐碎的感官刺激与碎片化的体验当中,当然它们是直观的基础——对我们冲击最大的是时空感受的改变,不仅由新的交通与媒体技术所形成的解放与自由,同时也有与之并生的情感与精神上的孤独、侘寂与疏离。可以说,我们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它使得时间感受变成一个永恒的瞬间感。为什么现在越来越难以把握世界的总体性?因为人口、资本、信息与技术在不断流动,城乡差别在变化,阶级区分在重构,性别差异在跨越,族群身份在迁移。固定、静止与本质化的世界、中国与个人都已经荡然无存。一方面是加速和流动所带来的时空压缩,比如飞机能迅速将人带往世界各地,网络上即时性的沟通;另一方面是时空的扩张,物理性的、社会性的时间和空间基础上,出现了虚拟的空间。这是新型的文化生态,一种融合了的文化,一切都弥散在一起,一个日用而不知的赛博格时代。我们既是一个自然意义上生物人,也成了一个赛博格人。人们通过基因改造、医疗技术、可穿戴式设备,不断地自我改造,同时也身处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智慧城市的实践与竞争之中。那么,人的精神状况、情感结构、感受方式,就同莎士比亚时代发生了差异,新的文学需要反思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的遗产及其在当下的缺陷。面对这样的变局,我认为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不仅仅是写出经验,更需要表达出要变化了的人和他的情感与精神,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重组。
写作往哪个方向走?从当下写作的实际看,我们可以观察到隐然成型的趋势。首先是讲故事,重叙述,轻描写,当信息泛滥、资讯漫衍的时候,以独创的“有意味的形式”化繁为简,举重若轻,讲一个经过时间检验的硬核故事,才能获得与读者的亲近性。其次进行思想实验,这是一种尝试把握总体性而采取的策略,这几年网络文学、武侠、科幻的兴起可以视作思想实验的操演。它们都有一种宏大叙事回归的迹象,指向于构想世界观的可能性,这一点同摹仿或变形式的现实反映或表现不同,它是如同盘古一样在混沌的、实然的多重经验中刀劈斧凿,开创一个应然的世界。
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困扰着写作者的问题。当现实与人本身都发生位移之时,模仿或者抽绎的方式固然依然不失为传统的文学技艺,但有时反其道而行之,在提炼、萃取时未尝不可以虚拟与再造。这也是文学作为创造性活动反作用于现实生活的意义所在。在复杂而丰富的经验中,意识到自身认知的局限性与创作的能动性,是一个写作者的起点与基础。我们只能了解部分的现实,认识片面的真相,洞察碎片的真理,那么就呈现与表述出这个就好了,它们会潜移默化地介入到世界的进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