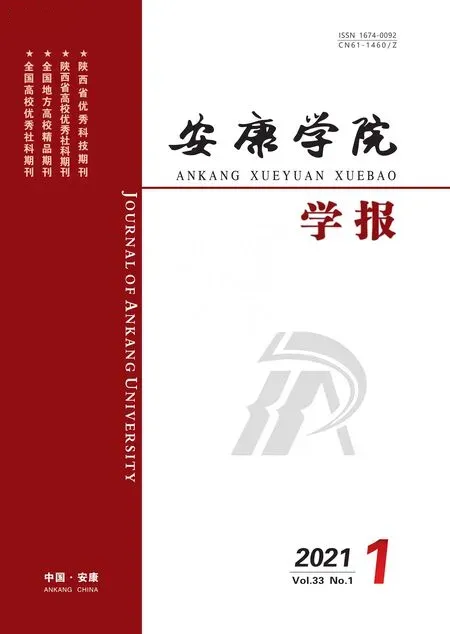影响杨译本《红楼梦》接受性因素的分析
李 烨,蒋 炜
(1.安徽新华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88;2.安徽新华学院 艺术学院,安徽 合肥 230088)
一、引言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无论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在世界文学史上都享有崇高地位。近年来,随着国家文化输出政策的重大转向,中国文化走出去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在此背景下,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红楼梦》的译介及其相关研究日益被关注。就《红楼梦》的英译本而言,英语《红楼梦》的节译本和全译本有十一种之多,时间跨度接近两百年[1]。其中,以英国汉学家霍克斯(David Hawkes)和他的学生闵福德(John Minford)合译的《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以及杨宪益和他的夫人戴乃迭(Gladys Yang)合译的《红楼梦》 (A Dream of Red Mansions)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大。
对《红楼梦》的译介研究也多集中在这两个全译本上,比较研究则成为通用的方法,选择的比较点集中在诗词曲赋、习语、宗教、饮食、服饰、灯谜、颜色、双关语、人物称谓、译者主体、翻译策略、翻译方法、意识形态、赞助人等方面[2]。
虽然研究者的教育背景和学养不尽相同,选择的章节内容各有差异,但文章的结论却大同小异,不外乎是杨、霍译本各有千秋,平分秋色。最流行的看法是,杨译注重对原作的忠实,反映出翻译策略上的异化和方法上的直译倾向;霍译则强调译文应符合译入语言的语文规范和文化习惯,反映出翻译策略上的归化和方法上的意译倾向[3]。这种评价基本上左右了二十余年来《红楼梦》译本比较研究的方向。有独立见解的文章不多。这种局面一方面反映了论文作者缺少独立思考的精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权威学者对普通研究者施加的看不见的影响。
这种认为杨、霍译本平分秋色的看法毕竟不利于对《红楼梦》译介的深入研究,因而,近年来少数学者也提出质疑。有学者指出采取例证研究的作者各取所需,研究结果不一定可靠,特别是译者的翻译策略如归化和异化问题[4];也有学者认为对两个译本的评价长期以来局限于学者和评论家之间,较少关注目的语读者的接受性[5]82,进而指出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的背景下,关注目的语读者的接受性,应该成为当前译介研究的重点问题。笔者肯定这一看法,拟从目的语读者接受视角出发,借助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资料,讨论杨、霍译本的差异所在,在此基础上分析造成差异的原因,以期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
二、目的语读者接受理论
读者接受理论源自文学批评,强调文学作品是文本和读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将这一理论引入翻译领域的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奈达认为,翻译的服务对象是读者或言语接受者,要评价译文质量的优劣,必须看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如何。他强调说:“不对信息接受者的作用进行全面的研究,对文本的任何分析都是不完整的。”[6]奈达理论的新颖之处在于将重点从比较文本转移到了比较读者,从而注意到以前一直被忽视,然而同样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因素——读者。“奈达的翻译理论是以目的语和目的语文本为归依,以译文和译文读者为中心的理论。”[7]如何检验译本在目的语读者中的接受效果呢?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是对目的语读者跟踪调查,通过问卷、读书心得与评价、图书借阅量、被引用的次数等数据作综合分析,这种方式对非目的语研究者存在着一定的困难,比如国内研究者要想了解《红楼梦》译本在欧美大学中的接受情况,就需要开展实地调查研究,从理论上讲只有获得足够多的样本时,获得的结论才可能真实可靠,但这都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这正是让很多研究者感到困难的地方。二是完形填空测试法,这种方法由奈达[8]提出。具体说来,就是在文本中每隔一定数量的词后空出一个单词让读者根据上下文去填空,“五十空就能较满意地看出文本的可接受性”。有研究者[5]82-87认为这种方法有效便捷,并将之应用于比较《红楼梦》不同英译本的接受情况。还有的研究者用这种方法测试了莫言文学作品《丰乳肥臀》英译本在美国读者中的接受情况[9]。由于两位研究者选取的样本偏少,均不超过18人,且覆盖面较窄,结论的可信度有待讨论,但不可否认两个测试的确反映出了目的语读者接受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
三、从目的语读者看《红楼梦》译本的可接受性
《红楼梦》的两个译本在英语国家的接受程度究竟如何?本文综合江帆[10]239、刘朝晖[5]82-87、王丽耘[11]、房芸菲[12]等人的研究成果做一整体上的归纳。如表1所示:

表1 《红楼梦》两个译本在英语国家的接受程度
以上调查研究可能因样本数量、调查对象和地域差别而存在某种缺陷,但整体上反映出的问题基本一致,即相比较而言,霍译本的可接受性强一些,杨译本的可接受性差一些。这也印证了国内一些著名学者的看法。“与英国翻译家霍克思与闵福德翻译的《红楼梦》译本相比,杨译《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却远不及霍译本”[13]5,“英语为母语的读者,更喜欢看霍克思的译本,在英美的图书馆内,借阅霍译本《红楼梦》的读者远远多于杨译本《红楼梦》的读者”[14]。笔者近期查阅中文购书网站“当当网”,发现霍译本《红楼梦》购书评价有428条,杨译本《红楼梦》购书评价只有3条,虽然评价者是中文读者,但似乎也值得参考。
在英语读者眼里,杨译本究竟存在哪些因素导致他们不喜欢?综合各种调查研究资料,总结如下:(1)语言不够自然流畅和地道,晦涩难懂;(2)人物众多,关系复杂难以分辨;(3)人物名称造成记忆困难和阅读无趣;(4)对书中节俗文化的陌生。这些问题,除了语言不够地道流畅之外,都是原著固有的问题,霍译本读者也有类似的评价,但由于霍译本处理这类问题的方法比较恰当,所以在阅读难度上大大低于杨译本。
四、影响杨译本可读性因素的分析
杨译本可读性不强的问题,其实译者本人很早前就意识到了。1980年,戴乃迭在为霍译本《红楼梦》撰写书评时,曾经赞许霍译本翻译方法的灵活性,她说:“在我看来,西方读者需要这样的帮助”,但是,“当我要采取同样的做法时,被我的中国同事否决了”,“霍克思的杰出贡献在于,他为西方读者提供了这一中国名著的优秀的英文译本。相比较之下,我恐怕我们的译本不过是一个逐字对照的文本”[10]243。这个看法也在戴乃迭后来接受的多次采访中被提及。比如,在接受澳洲记者的一次采访时,就《红楼梦》翻译的问题,她说道:“我们的灵活性太小了。有一位翻译家,我们非常钦佩,名叫大卫·霍克斯。他就比我们更有创造性。我们太死板,读者不爱看,因为我们偏于直译”。当记者问她翻译是否应具有创造性时,她回答道:“应该更富有创造性。翻译家应大致做到这样。然而,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受过去工作环境的限制,以致现在我们的翻译家比较拘泥于原文,译文平庸,还是深受过去老框框的影响”[15]4。
当国内文化界对杨氏夫妇推崇有加的时期,戴乃迭能够坦陈译本中的不足,其精神境界是令人钦佩的。戴乃迭认为译本缺少灵活性,偏于直译,逐字对照,造成了行文的死板,是英语读者不欢迎的主要原因。其实,缺少对目的语潜在读者的定位,译本没有目标读者,是造成偏于直译,或者逐字对照翻译的根本原因。戴乃迭在一次采访节目中曾说,“我们是为看不见的人民作翻译,英语翻译更是如此。我们不仅在为美国人或澳大利亚人作翻译,也在为亚非国家中懂英语的读者而工作,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读者究竟是谁”[15]11。为“看不见的人”做翻译,他们就失去了目标读者。有没有意向读者?似乎也很难说清楚,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只能忠实于作者和作品了。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杨宪益先生反复声明的忠实原文的翻译观念了。
如果仅仅是因为缺少目的语读者而采取逐字对照的翻译方法,显然这种认识过于肤浅了。忠实原文的翻译方法,表面上看只是一种翻译策略的问题,其深层原因则是翻译环境对译者主体的绑架。从杨宪益先生的个人自传和多次接受采访的资料中我们大致可以梳理出翻译《红楼梦》时的工作环境和时代环境,进而掌握一些造成接受性差的复杂原因。
(一)作为任务被动翻译,而非出于爱好主动翻译
《红楼梦》作为一部著名的中国古代小说,虽然在大众中知名度极高,但不意味着拥有广泛的读者,有些人对作品的了解来自道听途说,有些人读过只言片语,能读完全本的毕竟不多。书中众多的人物、复杂的关系、缓慢的情节发展、大量的风俗文化的描写,都需要一个人极有耐心才能读完。相比较而言,《红楼梦》 《三国演义》 《西游记》《水浒传》更受大众读者的欢迎,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有扣人心弦的事件,这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杨宪益先生多次说到他本人从小并不喜欢《红楼梦》,“其实,我不喜欢看《红楼梦》,小时候读《红楼梦》.我只读了一半都没读完”[15]65,“我小时候喜欢读的是宋代话本小说,还有《西游记》这一类,《红楼梦》大概十几岁才读的”[15]119,“我小时候对《西游记》 《三国演义》兴趣更大一些,对于《红楼梦》一直没有看全”,“《红楼梦》太像我们的老家,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很讨厌,我对《儒林外史》的兴趣比《红楼梦》大一些”[15]163。一生不喜欢《红楼梦》的人,由于上级领导的安排被迫接受了翻译工作。杨宪益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说:“周扬作文化部副部长,想起我会希腊和拉丁文,就把我调去译《荷马史诗》,后来又被出版社拉回来翻译《红楼梦》,反正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15]71又说:“不幸的是,我俩实际上只是受雇的翻译匠而已,该翻译什么不由我们作主,而负责选定的往往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几位年轻的中国编辑,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合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口味。我们翻译的很多这类作品并不值得我们为它浪费时间。”[15]221这两段话都表达了他在翻译问题上不能自主选择的无奈心情。这种情况下,译者不可能还有浓厚的兴趣去工作,一些富于才气的、创造性的火花也不可能闪现,最终造成译本平庸,对读者缺少吸引力。
(二)整个作品翻译时间短,速度快,较为仓促
翻译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堪比文学创作,为了一个贴切的表达,可能让人殚精竭虑,寝食难安。杜甫有诗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诗人贾岛也有名言:“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这类描写用来形容霍克思翻译《红楼梦》所付出的心血同样十分恰当。20世纪50年代,霍克思就倾心于《红楼梦》的翻译工作。1970年,为了能够全心投入这部中国文学巨著的翻译,不惜辞去牛津大学的教职。霍克斯用了10年时间,翻译了前80回,分别在1973、1977、1980年出版了英文版《红楼梦》的前三册,最后四十回,由霍克斯的女婿汉学家闵福德完成,分别于1982年和1986年出版。这其中的艰辛,在后来出版的霍克思本人的《红楼梦英译笔记》中有具体介绍。确是“十年辛苦不寻常”。反观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红楼梦》的过程,多少有些让人感到不可思议。首先,作品翻译的时间很短,据杨宪益先生讲,翻译前八十回只用了二年,出狱后翻译后四十回,大致用了4年。而霍克思仅前八十回就用去了十年。在杨宪益夫妇的这六年当中,还有很多杂事牵制着他们的精力。那么,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这部鸿篇巨制的翻译呢?提高翻译速度就成为必然。杨先生说:“所有的翻译都是我跟爱人合作,我拿着书直接口译,她打字,打得飞快,然后再修改。她做事比我用功。我们的翻译很快,那时是大跃进时期,什么都要快,最快的时候,翻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要求越快越好,结果我们一个礼拜就译完了。无所谓质量,就是要快。”[15]71杨宪益先生之妹杨敏如女士回忆说:“我哥哥就看着那个中文就打出来,没稿子。然后他们俩不说话,干事不说话,办公不说话。然后就往我嫂子那儿一递,我嫂子就拿着看,改,除非有些问题两个人说说话,但是没有问题,就听着安静极了。”[15]35为了尽快完成工作,不得不追求翻译的速度,尽管杨宪益夫妇极有才华,但由于缺少斟酌、推敲的过程,对译文最终质量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三)过于顺从的性格,抑制了翻译中的创造性
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文革”结束之前,国内政治运动频繁,杨宪益夫妇屡次受到牵连,还因此有过四年的牢狱生活。对这段历史,虽然后来在回忆录中讲的风轻云淡,实则表现了一个柔弱的知识分子内心的无奈和悲凉。当记者采访时,杨宪益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无所谓”,好像表现一个历经磨难的知识分子淡然处世的人生态度,其心灵深处,正像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文学荣誉博士时的感想一样,“多谢斑斓博士衣,无如心已似寒灰”[15]43。
长期的政治运动经历,造成了杨宪益过于顺从的性格,即使有一些不满和牢骚,也只是埋在心里,对于单位交付的工作,无法选择,只有接受。在工作中没有自我,在翻译实践中也很难表现出自我,翻译中丧失了创造性,只能亦步亦趋了。过于忠实于原作的翻译,非但难以译好原作,还会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戴乃迭在一次受访时说:“我觉得我们传统的翻译法是直译,过于死板的直译,以致使读者常常搞不懂我们说的是什么意思。政治性的社论尤其如此。”[15]11
(四)缺少评价译文质量的读者标准
杨宪益夫妇一生译著宏富,被称为“翻译整个中国”的翻译家。生前身后都享有盛誉,更是受到国内译界的高度推崇。正像谢天振在纪念杨宪益先生的一篇文章里所说:“这部《红楼梦》全译本自问世以来备受国内译界的推崇,被认为译得准确、生动、典雅。杨先生去世后,有人甚至不无哀伤地感叹说,杨宪益先生的病逝,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那就是《红楼梦》英语全本翻译的时代。在国内译界的大多数人看来,杨译本比霍译本更贴近原文,更能传递《红楼梦》原文的真谛和精髓。”[13]4可是在国内备受推崇的译著在国外却备受冷落的事实,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的评价标准是否存在问题?在专家评价标准之外,是否还需要一个读者评价标准?有人批评当代中国翻译是“自己制造,自己阅读,自我吹捧”[16],这种批评也许过于严苛,但冷静思考似乎不无道理。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长期以来我们的翻译批评系统里缺少读评价的标准。读者相对于译者和翻译评论家来讲,由于身份低微,话语权力弱小,他们的意见不会引起译者和评论家的重视,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读者的水平是造成他们阅读困难的原因,责任并不在译者身上。因此,译者和批评家总是高高在上,习惯于自以为是。这类现象在杨宪益先生的那个时代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杨宪益夫妇都是作为专家的身份被引进外文局的,他们的才华和政治地位在翻译界可以说无出其右了,赞美他们的译作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批评他们的作品既需要勇气,更需要真才实学,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又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最终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边倒的赞扬。当译者被淹没在一片好评之中时,只会增加译者的自信和乐观情绪,自然无暇考虑普通读者的感受,更何况处于目的语国家的读者。这种现象在译界目前还很普遍。
五、结语
以上分析了导致杨译本《红楼梦》接受性差的一些原因,但问题的主要责任并不能归结到杨宪益先生本人。因此,对于杨译本《红楼梦》中的一些瑕疵,读者应给予理解和包容。斗转星移,历史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随着我国进一步开放,对外文化交流日益活跃,翻译事业迎来了发展新机遇。和杨宪益先生相比,我们今天处在一个更好的时代。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让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每一位译者肩负的历史使命。作为文化传播重要途径的翻译工作,不能满足于译出和出版,以及国内一片赞美性的评价,我们要关注译作的最终效果——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反应。他们才是翻译产品的终端接受者、消费者和检验者。如果得不到目的语读者的认可,翻译注定是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