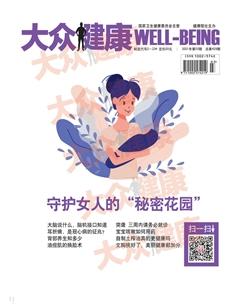大脑说什么,脑机接口知道
衣晓峰
2020年8月,特斯拉公司的创始人马斯克向媒体公布了自己麾下公司的一项重大成果——最新的脑机接口技术。
研究人员将一枚只有硬币大小的脑机接口设备植入猪脑中,建立了大脑与外界的联系。当这个猪的鼻子触碰到外界物体时,它脑内的神经活动有对应的反应,这表明这个植入装置采集了正确的神经信息。这个植入装置放进去两个月后,他们把这个小猪放在一个跑步机上,从它脑内的神经信号可以看出它走路的节律。马斯克说,这个设备已经申请到创新性医疗器械,下一步可以植入人脑了。
有专家借用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的话来评论这项技术:“这是个人迈出的一小步,但却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
科幻大片一步步走向现实
那么,“吃瓜”群众的问题来了:人们能够利用自己的大脑意念控制物体吗?电影《阿凡达》中所有生物的意识都能与机器连接的场景,会不会变成现实?给大脑安上电极或芯片,就能操纵想象中的一切事物,让万物互联、万物智能、人机互动了吗?
如果说,《阿凡达》所描述的场景离我们还有些遥远的话,那么这个摄制组拍的另一部科幻电影《阿丽塔:战斗天使》,所讲述的医生从垃圾堆捡到一个小女孩的脑袋,给她做了一个身体,实现了人脑组织和机械体共融的故事,则离我们越来越近。
临床上,瘫痪是神经系统常见的症状,表现为随意运动功能的减低或丧失,是神经、神经肌肉接头或肌肉疾病所致。
近年来,基于运动想象的脑机接口技术,其原理涉及脑电信号中包含与肢体运动相关的信息。当大脑开始执行运动想象任务时,通过深入挖掘相应的运动特征,可对人体运动意图进行识别,进而驱动机械臂等外部设备,真正做到靠意念来控制。
瘫痪病人因此有望凭借意念举起纸杯,翻阅报纸,实现意图表达。而如何采集尽可能少的脑电信号通道,同时确保较高的运动意图识别精度,是现今便携式可穿戴设备产品化、市场化的重要保证。
真正实现用大脑“说话”
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曹天傲指出,人脑的电信号蕴含了大量丰富的生理信息,如疲劳程度、专注度、情感、疼痛位置及强度、睡眠深度、麻醉深度和肢体运动意图等。通过深入挖掘脑电信号中的特征,可以客观、准确地反映人体当前的生理状态。故脑机接口技术不依赖外周神经和肌肉组织,就能直接构筑人脑与外部设备的通信渠道,即使对于因脑卒中等疾病而瘫痪的病人,也可以从其脑电信号中检测出运动意图,真正实现用大脑“说话”。

那么,脑电信号中具体包括运动意图的哪些特定信息?如何捕捉脑电信号来判断运动意图?怎样保证运动意图判断的准确性?针对这些问题,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孙金玮教授及其团队成员曹天傲、王启松等人自2018年到现在,已经在《物理学杂志》《测量科学与技术》等多个国际期刊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文章,从专业角度解决了上面一个个难题,为开启人类脑电信号未知的“大门”,铸造了一把“金钥匙”。
找捷径采集运动意图信号
许多肢体瘫痪病人的大脑损伤很小,仍具有良好的功能,只是中间传递运动信号的神经、神经肌肉接头或肌肉受伤,故可以通过脑机接口技术探寻脑电信号并探寻运动的意图所在。曹天傲解释,患者需要执行运动想象任务,即想象自己某一肢体的运动,但实际上该肢体保持不动,病人只是进入单纯的肢体运动想象场景。此时脑电波会呈现相应特征,研究人员将采集到的脑电信号进行噪声去除后,提取出运动相关特征,即可对病人运动意图做出预测识别。
传统思路是用尽可能多通道的脑电信号采集全面的信息,并利用算法提取运动意图特征,最后用专业的分类法提升意图预测的准确率。但这样的方法使实验操作更复杂,运算更耗时,设备更庞大,不利于实际产品的市场化。
孙金玮团队则是在控制运动意图识别准确率保持在一定范围内的基础上,通过对分析方法的改进,对脑电信号的采集通道展开权重分析,逐一判断每个通道的贡献大小,据此对通道权重展开排序,之后观察高权重通道的采集数量与最终运动意图识别准确率问的关系。结果发现,利用大约25%的通道已经能达到令人满意的识别率。而当增加采集通道数时,准确率无明显变化,甚至出现下降趋势。

孙金玮教授强调,这种“做减法”的脑区最佳通道选择策略,在保证大脑运动意图识别准确性的同时,借助尽可能少的采集通道,可以对头脑中的运动想象动作给出准确预测。瘫痪病人可以通过运动想象来控制外部设备,例如通过调控机械臂完成不同动作,抓取传递物体,喝水进食等,真正实现了“意念控制”的目的。
瘫痪病人也能“健步如飞”
脑机接口通过解码和揭示人类思维活动过程中的脑神经信号,构建起大脑与外部世界的直接“信息公路”,对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帕金森病、特发性震颤、高位截瘫等重度运动障碍疾病的治疗意义重大,可望取得全新的突破。
黑龙江省农垦总医院康复中心主任张俊教授认为,瘫痪病人完全可以利用其脑电信号,配合外部智能设备,如机械手、假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等,进行意图的表达与动作的执行。卧床不起的人,可以通过脑电信号,操控外部的智能机械手帮助自己移动物体,完成喝水吃饭。截肢患者往往生活不便,被笼罩在身体和心理的双重阴影下,而智能假肢的使用能够按照他们自己的大脑指令来完成动作,如借助脑控智能假腿站起来,甚至驱动假腿走路、上下楼梯,以及高速奔跑等,重返“陡步如飞”的状态。
脑卒中及脊髓损伤病人也完全可以凭借脑控智能机器人,开展康复训练,完成程序繁琐而又高难细致的指定动作。张俊认为,在康复进程中,患者大脑的电波活动反映了本人的强烈渴望和主动参与的意愿,这种主动参与性诱导了大脑神经通路的恢复,神经系统得到重塑和修复,有望让伤残者丧失已久的肢体运动功能“失而复得”。
展望未來,曹天傲博士指出,许多工种的劳动者经常要搬动沉重的货物,天长日久免不了腰肌劳损、腰弯背驼等问题。而一旦有了智能外骨骼的助力,搬运工人可通过自己的脑电活动,指挥外骨骼“大力士”协助搬运大件物体。毋庸置疑,外骨骼胜任的重量往往是人类本身最大力量的数倍。配备外骨骼的工人可代替叉车,将艰苦的劳动变得简单轻松。
这样的愿景,在中外科学家的努力下,不再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