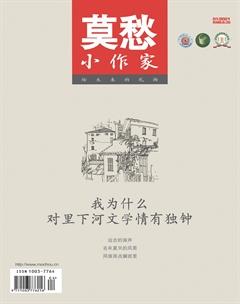住宿生
我上初三时,有过一段住宿经历,让我一生难忘。
按理说,来自农村的孩子,适应能力应该很强,可是我对住宿生活很不适应。
開学那天,我和父亲一人骑一辆自行车,车上满载着从家里带来的被褥、凉席,还有脸盆和饭缸等生活用品,一路“叮叮咣咣”来到学校。父亲把行李物品拎进宿舍,又塞给我几张大大小小的纸币,就急匆匆走了,好像我是邻居家的孩子,他只是顺道帮忙送一下。我知道他是去上班了,父亲是医院的临时工,负责烧锅炉。
初三的学习生活很枯燥,大部分时间都闷在教室里上课或者自习,下晚自习时往往都夜里十点了,住宿生们晃晃悠悠好像下夜班的苦工,陆续回到充斥着各种气味的宿舍。七八个人在狭窄的空间里各忙各的,准备洗漱的,吃零食的,还有学霸加班看书的,嘈杂的环境让人心情浮躁,难以入眠。
我想家了,想念家里那个安静的牛屋。牛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大人让我睡在牛屋,说是因为这里清净,可以安心学习,实际是家里住房紧张,让我住牛屋还能看牛,一举两得。不过,我觉得住牛屋挺好,我静静地看书,牛儿在旁边“咯吱咯吱”地吃草,我们相看两不厌。只是同学问我,你身上怎么一股牛屎味儿,让我有一点尴尬。后来,牛儿卖了,成了我上初三的学杂费。
住宿管理很严,两周才允许回家一次。有的学生娇气,想家时会偷偷地哭。也有家长不放心孩子,下晚自习后,拎着大包小包来看孩子。上铺的杜小华,他爸隔两三天就会来一趟,带着苹果、油条、鸡蛋糕,有一回还带了几个煮熟的咸鸭蛋,弄得宿舍里多了一股臭烘烘的味道。
父亲一趟也没有来看过我,我觉得自己被他遗忘了。每两周回家一次,也很少见到他,常常是拿了换洗衣物和母亲早已准备好的生活费,就返校了。至于在学校学习怎样、生活怎样,父亲从没有过问。
到了下学期,我的学习更加吃力。本来我读初二时的成绩就不理想,学业测试后,我的成绩又一次刷了新低。是的,那段时间我有点想放弃了,躲在教室角落里,偷偷读了半学期的小说。当班主任让我通知家长来学校时,我竟有点喜悦。
那天下午放学后,我没有上晚自习,而是请假去“请”家长。我把车子骑得哗哗响,去医院的锅炉房找父亲。远远的,我就看到了医院角落里那根乌黑的大烟囱。我把车子扎在锅炉房门口,走进操作间,轰隆隆的噪音让人的耳朵好像过火车一般。我问一个正在运煤的师傅,“师傅,请问老张在吗?”“谁?老张……他不上夜班。”
我有些失望,又疑惑不已,父亲整天不在家,又不上夜班,会去哪里呢?黑脸师傅看出了我的疑问,又吼道,“老张夜里在火车站扛活呢……”
我边走边问来到火车站,夜色已经很浓了,在昏黄的灯光下,我望见了父亲,他在一个高高的跳板上,一走一颤地往火车车厢里扛麻袋。原来父亲夜里就“住”在这里。
我没有“请”到父亲,偷偷回了学校。那天夜里,我躺在宿舍,一夜未眠。关于未来,我想了很多。忽然间,我觉得自己应该长大了。
没想到,一个多月后,父亲主动找到了我,那时我正在饭店后厨“哗啦哗啦”地刷盘子。后来听母亲说,为了找我,父亲几乎跑遍了全城的饭店。是杜小华“出卖”了我,如果不是他告诉父亲我“休学”去了饭店打工,父亲一定不会那么快找到我。
“走!”父亲从储物间把我的铺盖卷起来夹在自行车后座上,我跟着他走回了医院的锅炉房。
夜已深了。一张简陋的木板床上,我和父亲抵足而眠,在轰隆隆的噪声里,我第一次在家以外的地方,睡得那样香甜。
张海洋:在《微型小说选刊》《小说月刊》等报刊发表小说多篇。
编辑 沈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