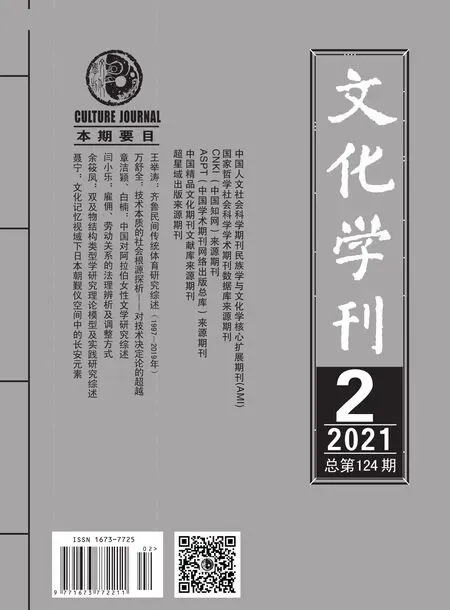渴望、逃离、自我救赎
——申京淑《单人房》的创作心理分析
吴友淼 苑英奕
一、研究背景
韩国作家申京淑出生于1963年,其小说《单人房》所描述的是一位十六岁少女在1979年至1981年三年间所经历的事。小说主人公少女的年龄与当时的申京淑相符,且作者在《单人房》一书的序中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大哥,我的表姐,1979年到1981年间就读于永登浦女高产业特别学级的她们,崔弘二国语老师,还有我,以及在此逗留期间,未能成为我的过去的希斋姐姐。”此段话提到的希斋姐姐正是小说中少女难以放下的症结,崔弘二老师、大哥、表姐皆在小说中出现,由此可以推断,《单人房》是作家申京淑的自传式小说。
《单人房》是以现在的“我”叙述过去的“我”所经历的事,主人公“我”与表姐来到城市,同哥哥一起住在单人房。主人公与表姐同时进入东南电气公司上班,后来主人公在单人房见证了希斋姐姐的死,心中难以释怀,最后以写作的方式将自己这段打工经历与希斋姐姐之死讲述出来。作家从一开始的难以释怀到完成写作,这一过程是一个从“本我”逃离到“自我”救赎的心理历程,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相符。因此,本文将基于人格结构理论视角,分析申京淑《单人房》的创作心理。
二、遵循本能,渴望“单人房”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形成有三大理论基础:潜意识理论、人格结构理论以及性欲说。弗洛伊德将人格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其中,本我是人类欲望的各种集合体,受到自我的检查和超我的监督。“本我是一种原始力量来源,是遗传下来的本能,‘本我’要求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是在快乐原则的支配下进行运作的。”[1]145“本我”追求快乐原则,获得满足便快乐,受到压抑则焦虑。
小说主人公没能升入高中,整日在家无事可做,想要离开家乡的欲望愈来愈强烈。主人公没离开农村之前始终焦躁不安,甚至将铁耙钉进了自己的脚掌。主人公总是在家门口的院子里等待邮差的到来,希望收到哥哥接她去城市的回信。小说开头两次描写了“我趴在院子里写信,哥哥,快来带我离开这个地方”,主人公所做的这些都表达了一个诉求:离开农村,去城市。
“本我”是人格结构中深层的基础,它的需求自由易变,流动不定。生存,是人类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主人公是为了名义上的“生存”来到了城市,主人公因不能继续上学,终日在家闲着,犹如一具没有灵魂的躯体。对主人公来说,去往城市,面对新鲜事物,开始新的生活,便是一种新的“生存形式”——存在感。为寻找存在感,主人公就产生了最初的“本我”——“离开农村”。如愿来到城市后,“本我”想要逃离农村的需求得到满足,需求发生转变,新的“本我”转变为“在城市生存下去”这一欲望。
主人公来到哥哥所在的城市后,发现想要在城市生存下来并不容易,没有钱,也没有住的地方,与哥哥、表姐挤在狭窄的单人房勉强生活。主人公在满足生存欲望时遇到了麻烦。由于年龄不够,无法进入工厂,于是主人公隐瞒真实年龄,借用他人的身份,留在工厂赚钱生存,满足了基本的需求。主人公“来到城市”的“本我”获得满足之后,则要为“留在城市生存下去”这一新的“本我”而奋斗,需求一直在不断发生变化。
三、从单人房出逃——逃离“本我”
“一个人要完成生存的使命,就必须去适应现实环境,从外界获得所需的一切,人在与现实环境的交往中产生的新的心理系统就是自我。”[1]145在社会现实之下,“本我”中的一部分分化出“自我”,“自我”依据“唯实原则”指挥“本我”,当“本我”欲望与现实相冲突,就需要“自我”跳出来进行调节,帮助“本我”趋利避害,最大限度满足“本我”。
主人公如愿来到城市,“离开农村”的“本我”此时获得了满足,接下来就是要在城市生存下来。在大哥的帮助下,主人公进入了东南电气公司上班,但由于工厂拖欠工资,恶意压榨工人,强制加班,辞职的人越来越多。因此,厂里有人开始呼吁成立工会,想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得属于自己的利益,主人公也加入了工会。但公司利用可以学习的机会来逼迫员工退出工会,主人公因想要继续学习,选择违背工会成员的信任,递交了退出工会书。“除了写作,别的事情都无所谓。现在,我也感觉不到羞愧。我不在乎!”[2]73此时的主人公已然在城市安顿下来,“在城市生存”的欲望继而转变为“留在工厂继续读书”,此时的“本我”即“想要继续读书”。但在满足此需求时,现实生活中却出现了阻碍,“自我”便作为中间调节者出现。此时的“自我”是现实中的“自我”,它调节主人公与工厂斗争的矛盾,让主人公认清现实,引导主人公做出了退出工会的选择,使主人公得以继续上学,重拾了继续写作的机会。这是“自我”对“本我”“想学习,想写作”欲望的最大满足。
“自我”也习惯于按照“本我”的欲望来行动,就像这种欲望是它所自有的一样。“自我”除了接受“本我”的本能要求,还力求满足“本我”趋乐避苦的愿望。“自从离开那里以后,我从来没去过附近。也许我在潜意识里希望自己尽量远离那段时间和那个空间。”[2]121这里的“那段时间”和“那个空间”就是指在单人房的三年。三年期间,主人公被工厂压榨,退出工会,遭受白眼,与主人公情同姐妹的希斋姐姐自杀,这些都是主人公的痛苦回忆,“本我”感受不到快乐,想要逃离这段回忆。“自我”本是作为调节者,但此时却成了“本我”的分身及辅助,帮“本我”选择回避,不去面对现实,这与前面让“本我”屈服于现实的“自我”不同。
小说中体现得很明显,只要有人提到单人房或跟过去那段时间有关的事,主人公都会找机会逃开,“为了躲避河桂淑的声音,我索性收拾提包,离家出走了”[2]43。一起上过产业体特别学级的同学河桂淑问主人公为什么不写写他们的故事,让主人公又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此时的主人公以旅行的方式回避这一问题。“他兴高采烈,而我战战兢兢,唯恐他会继续追问我是几班、国语老师是谁等等。我抓住机会,赶紧逃开了。”[2]46同是永登浦女子高中毕业的前辈与主人公谈及高中时代,主人公依然选择了回避,希望他终止对话。“本我”为避免承受过多的痛苦,要求逃避现实,驱使“自我”满足“本我”趋乐避苦的愿望,具体表现为与“单人房”隔离,只将它埋藏在心里,就如同将刺进脚心的铁耙扔进井里,不再浮现。此时“本我”的“逃离单人房”需求暂时得到了满足。
四、走出内心的“单人房”——超越“自我”
“‘超我’是一切道德限制的代表,是追求完美的冲动或者人类生活的较高尚行动的主体。”[3]“超我”的职责便是指导“自我”按其道德准则自居,遵循至善的原则。当“自我”没有按照“超我”所要求的准则行事,任由“本我”胡来时,“超我”便会惩罚“自我”,心生愧疚感;而当“自我”执行道德原则,引导“本我”回归“正途”,“超我”便会奖励“自我”,让人心生荣誉感。
主人公为了让自己逃避痛苦,选择用“自我”来保护“本我”,对往事避而不谈,这种避而不谈的方式并没有让主人公得到慰藉,反而让主人公内心备受煎熬。道德、良心的谴责让主人公开始正视那三年的回忆,开始了写作。当主人公每次想要停止叙述再次逃跑时,总是会被内心的声音按压住,“坐下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以及永远,坐下吧”[2]29。这时,“自我”有了清醒的认识,逃避不会让“本我”得到真正的释放,它需要做回调节者,战胜“本我”,压制住“本我”,让主人公坐下来写完这个故事,勇于面对那段往事。
主人公通过写作将压抑心中多年的事情讲给读者,将已经逃离单人房十多年的“我”重置于那段时空。对于主人公来说,决定要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在单人房的事对她来说反而变得客观了,主人公不再封闭内心,而是通过写作将内心的伤痛回忆讲给人们听。在写作中,主人公的伤口逐渐愈合,开始与希斋姐姐正面“对话”了,主人公和希斋姐姐达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和解。主人公夜深人静朝着吞没铁耙的水井里窥望时,希斋姐姐对主人公说:“想想那些敞开心灵活着的人们……把你遇见的人们的悲伤和喜悦散播给活着的人们吧,那些人的真实会改变你。”[2]323然后,“她扶起了隐藏在水井深处最偏僻峡谷里的铁耙……她离开了我的身体”[2]324。此刻主人公的心才真正得到解放,内心的“铁耙”已被拔除。与希斋姐姐的一番对话就如同“自我”在对“本我”进行疏导,过去的事就像那沉入井底的铁耙,不捞起来就永远会在,直接面对就会慢慢放下,想办法解决才会得到真正的救赎。
五、结语
《单人房》是一部回忆韩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产业化下的社会矛盾和打工者心酸生活的小说,也是作者青春岁月打工经历的真实写照。作者将亲身劳动经历映射在作品的主人公身上,借助主人公完成了自我成长。这不仅是一部个人自传,也是时代的真实写照。作者申京淑以亲身经历再现了韩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劳动现场,反映了当时离农进城的打工者的生活状况及底层人民在城市需面对的一系列生存问题和由此产生的矛盾心理。它既是一部通过细腻的笔触记录20世纪70年代打工妹的底层文学代表作,也是一部通过艰难的心路历程反映女性成长的代表作,在理解这部作品的时候,这两个角度都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