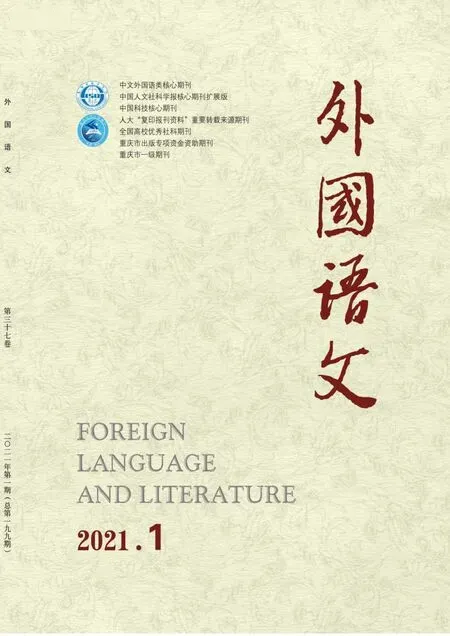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体系之动态性研究
——以理雅各译《诗经》为例
张广法 文军
(1. 南京邮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191)
0 引言
在文学翻译中,诗歌翻译历来受到重视,一直是翻译研究的焦点之一。近年来,汉语古诗,作为中国文学的精华,因其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特别受到译学界的青睐,研究主要涉及翻译史、译者风格、翻译过程和翻译策略等四个主要议题。汉语古诗英译史研究包括:(1)译者翻译活动史,具体译者包括庞德、华滋生、许渊冲、王红公等;(2)不同类型古诗英译史,如唐诗;(3)汉语古诗英译研究史,如楚辞。译者风格研究关注的是具体译本或者译者的翻译风格,如《红楼梦》诗词、《诗经》等。诗歌翻译过程研究是对汉语古诗翻译过程中的各类因素进行的理论探索,比如汉语古诗英译的中庸诗歌翻译观、古典诗歌翻译的“格式塔”解读、诗歌翻译中的框架操作等。最后一类是汉语古诗英译策略研究,有策略体系建构研究和具体技巧研究。近20年的汉语古诗英译研究呈现出理论研究的系统化和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两个明显趋势。理论研究的系统化体现在翻译史、译者风格、翻译过程和翻译策略等四个方面。在翻译学建立之前的前学科阶段,汉语古诗英译研究主要使用基于直接翻译经验的体悟法,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不足。随着翻译学的建立,人文社会科学中广泛使用的研究方法被引入到汉语古诗英译研究当中,研究的科学性和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得到了大幅提升。
在众多议题当中,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一直居于核心地位,不论是翻译史、译者风格还是翻译过程都或多或少地会与这个议题产生联系。有的研究与此相关,有的直接研究这个主题。文军、陈梅(2016)和文军(2019)在分析大量语料系统的基础上提出了包含“译诗语言易化策略”“译诗形式多样化策略”“译诗词语转换策略”和“附翻译扩展策略”四个核心部分的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体系。正如文军、陈梅(2016)所言,这些策略的选择并不是孤立的,往往会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会展现出动态变化的特征。为了研究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体系的动态变化性特征,我们以理雅各《诗经》的1871年和1876年译本为语料,通过对比分析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理雅各《诗经》1871年和1876年译本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有哪些差异?(2)这些差异体现了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体系的何种动态性特征?
本文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译本,通过把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体系的动态性概念转换为两个具体的研究问题,使用语料库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同一个译者在同一个时期翻译同一部诗作时所使用的不同策略,以及这些差异所反映出来的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体系的动态性特征。
1 研究框架: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体系
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体系是一个包含三个层次的有机整体。最高层是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体系,统领全局,下一层是四种分策略,包括“译诗语言易化策略”“译诗形式多样化策略”“译诗词语转换策略”和“附翻译扩展策略”,最下一层是具体的翻译技巧(文军 2019; 文军 等,2016)。这个策略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动态性,也就是这个策略体系的构成要素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同时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会受诗歌类型、译者、时代背景、目的语读者、出版社等语境的影响,进而展现出一定程度的变化。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张广法(2019a/2019b)、张文鹤、文军(2019)等的研究发现,在译诗形式上选择协韵型、借用型和自格律型的译者在译诗词语的翻译上受限较大,译诗词语的转换策略会影响到附翻译扩展策略。这些结论主要通过对若干首译诗的对比分析得出。一般原诗一首和译诗若干的案例代表性不足,因译诗数量有限,这难免会影响到研究结论的系统性和适用性。另外,所选译诗一般由不同译者在不同时期译出,译诗的读者对象也不尽相同,翻译策略的影响因素过多,难以完整解释策略体系的动态性特征。本研究针对以上问题设计研究方案,以期系统、完整地揭示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体系的动态性特征,得出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结论。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样本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理雅各1871年和1876年翻译出版的《诗经》英译本。1871年的译本共两卷,被收录在七卷本的《中国经典》中,书名为TheSheKingorTheBookofPoetry。该书的扉页提供了更为详尽的信息。英文书名为《中国经典:译介、训诂注释、序言和大量索引》(TheChineseClassics:withaTranslation,CriticalandExegeticalNotes,Prolegomena,andCopiousIndexes),明确了该书的体例安排。译者为詹姆士·理雅各(James Legge),当时的身份是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一名传教士。该书由伦敦的特鲁布纳出版社(Trübner & Co.)和香港的卡连佛出版社(Lane Crawford & Co.)联合出版。1876年的译本虽然也由理雅各翻译,但出版信息和译本体例发生了较大改变。书名仍为TheSheKingorTheBookofPoetry,但副标题被修改为“译为英语韵诗并附评论和注释”(TranslatedinEnglishVersewithEssaysandNotes)。理雅各当时的身份也发生改变,此时他是伦敦大学的汉学教授,扉页同时还注明其原为伦敦传教会成员。出版社由两家变为一家,为伦敦的特鲁布纳出版社。
这两个译本在原诗、译者、出版社、出版时间等变量上完全相同或相似,在译本体例和译诗形式上存在显著差异。本文以《诗经》的这两个译本为研究对象,使用语料库加文本分析的混合法来系统回答本文提出的两个问题,进而揭示出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体系的动态性特征。
2.2 研究方法
《诗经》译本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诗歌正文,二是译者在译诗正文之外添加的注释性文字,包括释义、赏析、研究与考据等内容。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体系包含四个分策略,即译诗语言易化策略、译诗形式多样化策略、译诗词语转换策略和附翻译扩展策略。诗歌正文的翻译主要使用前三种策略,我们将其称作“诗内策略”。诗歌正文之外注释性文字的处理使用的主要是附翻译扩展策略,我们称之为“诗外策略”。诗歌正文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词汇、句法、行数、每行音节数、韵律等方面,诗歌外解释性文字的差异则更多地体现在阐释视角、重点、详略等方面。因此,诗歌正文的差异可以使用语料库的方法予以解决,而诗歌外解释性文字的差异则可以使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来分析。语料库和文本细读两种方法相互结合,可以更加系统、全面地揭示两个译本在不同层次上的差异,进而为我们探索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体系的动态性特征提供完整、系统的实证数据。我们为本研究建立了一个《诗经》英译语料库,这个库包含三个子库(详见表1)。

表1 《诗经》英译语料库
第一个子库为汉英平行语料库,包含1871年和1876年的两个译本,这个库实现了汉英诗歌逐行对齐,方便翻译对比研究。第二和第三个子库分别是1871年和1876年《诗经》英译本单语语料库,从这两个库中可以提取体现译者风格的形符、类符、STTR、平均词长、诗歌行数、平均每行音节数等数据,方便对比两个译本的风格。1871年和1876年译本均收录译诗305首,包括风160首、雅105首、颂40首。本文从这些译本中随机抽取30首建立本库,涵盖风11首、雅11首、颂八首,所选译诗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3 研究结果
3.1诗内策略
诗歌正文的对比使用语料库的方法。对具体词语及其译文的检索使用平行语料库检索工具ParaConc,译诗的形符、类符、标准类符/形符比(STTR)、平均词长等基本参数使用Wordsmith 6.0提取。诗歌不同于其他文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往往具有比较严格的形式规则,一般体现在建行形式、节奏和韵律三个方面。我们需要提取能够反映以上特征的参数,共三个,分别为诗歌总行数、总音节数和平均每行音节数。这三个参数可以使用诗歌音节在线计数工具Syllable Counter(1)Syllable Counter是一款在线诗歌音节计数工具,网址为https:∥www.howmanysyllables.com/syllable_counter/,可以统计诗歌的每行音节数和总音节数。提取后计算得出。
表2的统计数据从宏观上反映了两个译本在不同参数上的异同。形符是指一个文本中出现的所有的词(包括重复的词),形符数也就是一个本文的总词数,类符是排除重复并忽略大小写后不同的词。类符/形符比是一个文本中所使用的不同的词汇的数量与总词汇量的比值,这个比值可以反映出一个文本中所使用的词汇的丰富程度,比值越大丰富性越高。但是,不同文本的长度一般有差异,不同文本的类符/形符比无法直接比较,通常是把这个数值标准化之后再加以比较。从标准类符/形符比的角度看,1871年译本是40.34,1876年译本是48.68,后者显著高于前者,说明1876年译本的词汇丰富程度比1871年译本高。虽然1876年译本的词汇更加丰富,但两个译本的平均词长相等。入选本语料库的30首汉语原诗总共732行,1871年译本与原诗一致,1876年的译本一共837行,比原诗多105行。这说明在译诗建行上,1871年的译本忠实于原诗,而1876年的译本改写较多(具体详见下文分析)。因为英语诗歌的节奏和韵律主要靠音节来实现,每行音节数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两个译本在节奏和韵律上的总体特点。1871年的译本平均每行音节数为9.65,1876年译本是8.37,后者显著低于前者。1876年译本比1871年的译本多出105行,所以两个译本的总音节数比较接近。

表2 《诗经》英译本基本参数
以上分析显示,1871年的译本词汇丰富程度较低,译诗行数与原诗一致,平均每行音节数较多,而1876年译本的词汇丰富程度较高,译诗比原诗多105行,但平均每行音节数较少。以上是两个译本总体的风格差异,下面从译诗语言的易化、译诗形式的多样化和译诗词语的转换策略三个诗内策略的角度详细分析二者的具体差异。
(1)译诗语言的易化
译诗语言的易化是指在翻译汉语古诗时,译者规避了原文的历史性,以读者容易接受的英语移译,这是一种化解古代语言与现代读者矛盾的有效策略(文军 等, 2016)。易化法包括当时化法和拟古法两种,当时化法是把古汉语翻译成当代英语的方法,拟古法是在当代英语中夹杂古旧词语的方法。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有些译者会使用拟古法,但也仅仅是在当代英语译文中偶尔夹杂一些拟古词,从整体上来说依然是一种语言的易化现象。理雅各并没有把《诗经》译为古英语以体现原诗语言上的时代性,而是全部译为当代英语。
除了当时化法之外,理雅各在两个译本中还使用了拟古法,在当代英语中掺杂进一些古旧词语,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原诗的时代性。语料库的数据分析显示,理雅各在1871年的译本中古旧词语的使用频率较低,仅包括代词的第二人称单数主格形式(thou)、动词的第二人称单数一般过去时(didst)、动词的第二人称单数一般现在时(makest)三种形式,而1876年译本中的古旧词语形式和数量均更加丰富,比如代词的第二人称单数主格形式(thou)、代词的第二人称单数宾格形式(thee)、代词第二人称所有格形式(thy)、动词的第二人称单数一般现在时(如makest、mak’st、dost、hast)、动词的第二人称单数一般过去时(如didst、did’st)、动词第三人称单数(如walketh、rideth、ruleth)等。
(2)译诗形式的多样化
译诗形式的多样化涉及英汉两种诗歌建行形式的差别。辜正坤(2010: 20)认为,印欧语言是符号化语言,一个单词的音节数不确定,而汉语一个字一个音节,在诗歌建行上比印欧语言灵活,故印欧语言难以模拟汉诗的建行形式。译诗形式的多样化指英语译诗如何表达汉语古诗的诗歌形式(文军 等,2016)。译诗形式的多样化包括五种形式:散体型、诗体无韵型、协韵型、借用型和自格律型。散体型是把汉诗译为散文的方法;采用诗体无韵型的译诗分行,但无韵律结构;使用协韵型的译诗既分行,同时又有一定的韵律形式,尤其是尾韵比较整齐;借用型是指借用目的语诗歌的诗体以替换原诗的格律;自格律型的译诗的格律并非借用目的语诗歌中现有的形式,而是译者专门设计的(文军,2019)。
两个译本在译诗形式多样化上有显著区别。首先,从诗歌分行看,1871年译本完全忠实原诗,都是732行,而1876年译本对原诗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写,有的译诗一行译为多行,有的多行合译为一行。综合来看,1876年译本在原诗的基础上增加了105行,总行数达837行。其次,从译诗分节看,1871年的译本全部未分节,1876年的译诗则全部进行了分节。最后,从韵律的角度看,理雅各在翻译1871年的译本时使用的是诗体无韵型的方法,即翻译成了无韵体自由诗的形式,而1876年的译本使用的主要是自格律的方法,一首诗歌每行音节数有固定规则,从6-12个音节不等,尾韵有双行韵和隔行韵,也有少数诗歌无尾韵。
下面以两首译诗为例,具体解释两个译本在译诗形式多样化上的差别。第一首译诗为《颂·有瞽》,本文仅摘录前六行(详见表3)。首先,从诗歌分行来看,汉语原诗一共13行,每行四字,结构整齐。1871年的译本同样为13行,1876年的译诗为26行,行数增加一倍。有的一行变两行,方法是原诗句译为英文,同时增译一行,增译的一行符合全诗的节奏和韵律规则。有的一行变六行,即原诗第六行,方法类似,原诗诗句译为英语,同时增加五行。其次,1871年的译诗未分节,1876年的译诗共26行,分为四节,第一节四行,第二节10行,第三节四行,第四节八行。最后,从韵律的角度看,1871年的译诗基本忠实地翻译出了原诗的意思,每行音节数不定,无尾韵,而1876年的译诗每行七个音节,诗尾双行押韵。

表3 《颂·有瞽》英译对比
有的译诗诗行增加,也有译诗诗行删减合并。《雅·十月之交》原诗有64行,绝大多数每行四字,个别行为五字或八字。1871年的译本同样为64行,1876年的译本为36行,比原诗少28行,处理方法是两行合并为一行。比如“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这两行,1871的译文同样为两行:“Then the moon became small, / And now the sun became small”,而1876年的译文则合并成一行“The moon eclipsed before, and now the sun!”译者在原诗的基础上进行了精简。除此之外,1871年的译诗并未分节,1876年的译诗被分成八节。最后,两个译本的韵律格式也有显著差异,1871年的译本无韵律,1876年的译本为抑扬格五音步,即每行10个音节,同时诗尾双行押韵。
(3)译诗词语的转换策略
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体系是一个整体,每种策略之间往往会相互影响,这种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译诗形式对译诗词语转换的影响上。译诗词语的转换策略一共包括11种方法:音译法、概括法、提译法、增添法、直译法、省略法、语气转换法、视角转换法、套译法、译写法和替换法(文军 2019; 文军 等,2016)。下面以《关雎》为例,同时结合语料库统计数据,具体阐释译诗词语的转换策略和其他策略之间的关系。
从总体上看,1871年的译诗在词语的转换方面更加忠实原诗,而1876年的译诗对原诗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写。1871年译诗的忠实性体现在对原诗词语的不增、不减、不改,词序的保留和诗行(2)诗行由词语构成,对诗行的任何操作都必须以词语为基础,或者说诗行的对应、增加或者减少均是对词语作相应处理的结果,故把诗行的分析归入译诗词语的转换这个部分。的对应三个方面。比如《关雎》前四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被译为:“Kwan-kwan go the ospreys, / On the islet the river./ 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 For our prince a good mate she.”这四句中的核心词语“关关”“雎鸠”“河”“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分别译为“Kwan-kwan”“ospreys”“river”“islet”“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lady”“prince”“good mate”,使用的主要是音译法和直译法。在词序方面,译诗除了根据英语的语法规则增添了一些介词、连词等形合手段之外,译诗词序和原诗基本对应。1871年译诗行数也与原诗完全一致,都是20行。1876年的译诗对原诗的改写幅度较大,体现在对原诗词语的增删改和对诗行的调整两个方面。比如原诗前两句中有四个核心词语“关关”“雎鸠”“河”“洲”,其中“关关”被省略,其他三个词分别被直译为“fish-hawk”“stream”“islet”。除此之外,译诗还增加了“hark”“voice”“their nest”“rejoice”等四个核心词语,对原诗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如果我们把这两句译诗回译成汉语,则变成“听那,河中小洲上的雎鸠/在窝里欢快地关关鸣叫”,对比原诗,词语的增、删、改更加明显。接下来两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每句分别被改译为两句,共四句,增加的两句为“Form them our thoughts to that young lay go”和“Where could be found, to share our prince’s state”。理雅各对1876年译诗的改写还体现在对同一诗行的处理上。本诗中“参差荇菜”和“窈窕淑女”两行反复出现,1871年的译诗与原诗相同,同样采用重复法,而1876年的译诗每次均使用新译法。
理雅各之所以对1876年的译本进行如此大的改写,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出于译诗形式的考虑(理雅各在译本前言中也有解释,详见下文分析)。1871年的译诗为无韵体自由诗,无韵律格式,而1876年的译诗有严格的韵律格式。1871年的译诗每行音节数多寡不定,最少为第一行,有六个音节,最多为第16行,有13个音节,同时也无尾韵。1876年的译诗为抑扬格五音步,每行10个音节,诗尾双行押韵。所以,我们在上文发现的理雅各对原诗词语的增、删、改和对诗行的调整均是为了满足这种韵律格式的要求,而1871年的译诗就没有这种限制,理雅各可以完全把注意力放在忠实地传译原诗词语意义上,不用削原诗意思之足而适译诗形式之履。
3.2 诗外策略
理雅各翻译的《诗经》的两个译本除译诗正文之外,还有大量的注释性文字,包括释义、赏析、研究与考据等内容,在本文中我们称之为“诗外策略”,和“诗内策略”相对。两个译本的诗外策略均包括前言和绪论两个主要部分,前言主要用来阐明翻译缘起、原则、策略等,绪论主要用来介绍《诗经》的成书历史、诗学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后世评注等,但两个译本的诗外策略在具体内容上存在显著差异。下面从翻译的缘起、翻译策略和原则和对《诗经》的介绍三个方面来对比两个译本的诗外策略。
1871年的译本分为上下两卷,上卷243页,下卷542页,共785页。前言和绪论置于上卷,共182页,占总篇幅的23.2%,内容的丰富程度可见一斑。在1871年译诗的前言中,理雅各详细阐明了他翻译《诗经》的原因。在理雅各之前,法国传教士孙璋(Alexandre de Lacharme)已经于1733年把《诗经》翻译成了拉丁文,但直到1830年才出版。理雅各(Legge, 1871: v)认为,这个版本的译文有很多明显的缺陷,如注释不让人满意,而且也不够详尽。为了译出“忠实于原诗的可靠的译本”,使自己的译本“尽善尽美”,理雅各决定把《诗经》翻译成英语(Legge, 1871: v)。他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研读原典,译出了《诗经》的全部诗篇,同时提供了详尽的注释。
理雅各还花了大量的篇幅来介绍自己的翻译策略和原则。上文分析显示,1871年的译诗为无韵体自由诗,词语的翻译更加忠实于原诗。理雅各给出了两个原因:(1)他认为英语诗歌的诗学价值和《诗经》不同,不应该用英诗韵律来替换汉诗韵律(Legge, 1871: 116)。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分析了本森(Bunsen)的GodinHistory第三卷第五章中收录的部分带韵律的英文版《诗经》。这些诗歌译自德语的韵诗,而德语的韵诗又译自拉丁语的韵诗。经过两次转译之后的结果是,如果只读译诗,即使是对非常熟悉《诗经》原文的读者来说,都难以分辨这些译诗的原诗是什么。(2)理雅各认为用英诗韵律替换《诗经》的韵律会破坏原诗的情感(sentiments)(Legge, 1871: 116)。因此,理雅各尽量忠实于原意,使用直译法,对原意力争做到不增、不减、不改。
理雅各还特别提到了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方法。《诗经》中有大量的动植物、鸟类、鱼类、昆虫等专有名词,这些词语的处理耗时耗力,不精确的译文还可能会让读者失望。为了译出准确的译文,理雅各请教了当时的专家,包括当时的中国作家和英国的植物学家。如此一来,之前拉丁文译本中靠译者猜测出来的大量译名均得到了确认(Legge, 1871: V-VI)。
在1871年的绪论中,理雅各还用五章的篇幅对《诗经》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第一章介绍了《诗经》版本的演变史,包括孔子之前的《诗经》、孔子对《诗经》的编辑、孔子时代的《诗经》和今本《诗经》(20世纪末)。第二章介绍《诗经》的来源以及后世对其的阐释和研究,包括《诗大序》《诗小序》、商周重要历史事件年代表等。第三章介绍《诗经》本身,包括韵律、汉字古音、诗学价值、文学创作手法等。第四章是西方学者对《诗经》的研究,理雅各在这里全文翻译了爱德华·比奥(Edouard Biot)发表在JournalofAsiatique杂志(1843)上的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通过《诗经》解读了周朝时的中国版图、政治制度、宗教、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内容。第五章介绍了译者翻译《诗经》时参考的文献,包括两类,一类是汉语文献,共55种,如《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钦定诗经传说汇纂》《春秋》《吕氏家塾读诗记》《毛诗集解》《毛诗集释》等,一类是西方学者研究《诗经》、中国文学和历史的文献,共10种。
1876年的译本为一卷,共431页,前言和绪论共57页,占总篇幅的13.2%,比1871年的占比低了10%。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两个译本的一个最显著区别是韵律。为什么理雅各在1871年的无韵体译诗出版五年之后,决定把其重译为韵诗?理雅各在1876年译本的前言中对此进行了解释。他说,尽管他1871年在翻译诗经时,就发现《诗经》中的很多诗歌都值得翻译成韵体诗,但是由于工作量太大,而且他还要忙于翻译其他中国典籍,所以重译之事一直被搁置了下来。1874年,理雅各的侄子约翰·理雅各(John Legge)建议他重译为韵诗,并表示愿意帮他完成这项工作,理雅各才最终决定重译。可见,1871年和1876年译本的翻译缘起完全不同。
理雅各1876年重译《诗经》的总体原则是“以韵诗译诗”(versifying),用理雅各的话说叫作“让中国诗歌穿上英语诗歌的长裙”(the Chinese poems in an English dress)(Legge, 1876: preface)。这个原则体现在对诗歌韵律和诗节的处理两个方面。理雅各对比了英汉诗在韵律上的差异,发现英语中的单尾韵和重音落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的双韵和三韵的总数有400多个,而《诗经》中的尾韵一共不到20个(Legge, 1876: 33)。如果照此译出,英语读者难免会感到重复、单调,故理雅各为重译本添加了新的韵律,以适应英语诗歌的韵律特点。理雅各还分析了《诗经》诗节的特点,发现每节四行较多,偶数行的诗节数量大于奇数行的诗节数量。理雅各对诗节的处理原则是,总体上忠实于原诗,诗节行数有增有减,增多减少。
在1876年的译本前言中,理雅各同样对《诗经》进行了介绍,介绍共分四章:第一章介绍孔子之前的《诗经》、孔子对《诗经》的编纂以及今本《诗经》;第二章介绍《诗经》的时代背景及涉及到的地点;第三章介绍《诗经》的韵律、音步、诗学价值等;第四章从古代中国的疆域、政治制度、宗教和社会环境等角度对《诗经》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从总体上看,1876年的介绍比1871年的介绍要简略得多。
4 讨论
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体系包含“译诗语言易化策略”“译诗形式多样化策略”“译诗词语转换策略”和“附翻译扩展策略”等四组分策略(文军, 2019; 文军 等,2016),并包含一系列具体的翻译技巧。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会对这些策略进行搭配使用,实现不同的翻译目的。以上案例分析显示,同一个译者(即理雅各),在同一时期(即19世纪末),翻译同一部诗歌时(即《诗经》),选择了不尽相同的策略组合。具体说来,在译诗语言的易化方面,1871年的译本主要使用现代英语,同时夹杂少许古旧词语,1876年的译本同样使用现代英语,但古旧词语使用较多。在译诗建行方面,1871年的译诗分行完全忠实于原诗,都是732行,未分诗节,而1876年的译本改写幅度较大,有的一行译为多行,有的多行合为一行,且全部划分诗节。在韵律的处理方面,1871年的译本使用的是诗体无韵型译法,译诗全部为无韵体自由诗,1876年的译本绝大部分为韵诗,一般每行音节数固定,从6-12个音节不等,尾韵有双行韵和隔行韵。在译诗词语的转换方面,1871年译诗更加忠实于原诗,受译诗形式的影响较小,词语不增、不减、不改,词序基本保留,而1876年的译诗改写较大,体现在对原诗词语的增、删、改几个方面。在诗外策略方面,在1871年的译本中,理雅各对《诗经》在欧洲的译介史、成书背景、演变历史、社会环境、诗学价值、翻译原则和策略等进行了极其详细的介绍,篇幅占比高达23.2%。在1876年译本的前言和绪论中,理雅各虽然也对以上内容进行了介绍,但因为这个译本主要针对英语读者,所以解释更加简洁(Legge, 1876: 31)。
汉语古诗英译策略的选择并不是孤立的,往往会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会展现出动态变化的特征(文军 等,2016)。理雅各在《诗经》的翻译上使用了不同的策略,这些策略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展现出了动态变化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条:
(1)译诗形式影响译诗词语的转换。译诗形式的多样化包括五种形式:散体型、诗体无韵型、协韵型、借用型和自格律型(文军,2019; 文军 等,2016)。从译诗形式和译诗词语转换之间的关系来看,译诗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不带韵律,包括散体型(即把诗歌译为散文)、诗体无韵型(即译为无韵体自由诗);另一类带有韵律,包括协韵型(尾韵较整齐)、借用型(借用英诗韵律)和自格律型(为译诗专门设计的韵律形式)。第一类译诗形式对译诗词语的转换影响较小,译者翻译原诗词语时的自由度较大,第二类译诗形式对译诗词语的转换影响较大,词语的转换必须置于固定的形式之内,增、删、改较多。以上实证分析显示,1871年的译诗在词语的转换上更加忠实于原诗,体现在对原诗词语的不增、不减、不改,词序的保留和诗行的对应三个方面,而1876年的译诗对原诗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写,体现在对原诗词语的增、删、改和对诗行的调整两个方面。张文鹤(2019)、张广法(2019b)和刘锦晖(2019)等学者对部分汉语古诗英译本的描写研究结果与本文的研究结果一致,发现译诗形式对译诗语言转换的影响。所以,译诗形式对译诗语言转换的影响很可能是汉语古诗英译策略动态性的一条普遍规律,当然有待更多的研究来对这一结果进行验证。
(2)译者的诗学观决定译诗形式。本研究发现,同一位译者在同一时期翻译同一部汉语古诗作品时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译诗形式。语料库数据显示,1871年的译诗行数与原诗一致,均为732行,无韵律格式,词语的转换也更加忠实,而1876年的译诗行数比原诗增加了105行,总数达837行,绝大部分译诗有韵律,每行音节数从6-12个不等,尾韵较整齐,对词语进行了较多的增、删、改等处理。两种译诗体现了理雅各两种迥然不同的诗学观。理雅各在1871年译本的前言中说,他“尽量使用直译法”来翻译《诗经》。英语诗歌的诗学特点和《诗经》不同,不应该用英诗的韵律来替换汉诗的韵律,否则译诗会变得面目全非,原诗的情感(sentiments)还会被破坏(Legge, 1871: 116)。五年之后,理雅各完全推翻了之前的观点,决定把《诗经》重译为英语韵诗。对于这种转变理雅各在1876年译本的绪论中进行了解释,他说“我不会再像1871年那样认为,《诗经》并不值得翻译成英语韵诗”,实际上,把《诗经》译为英语韵诗可以让英语读者认识到“汉语古诗作为一个整体所蕴含的巨大的诗学价值”,而且在重译的过程中,理雅各自己也感受到了之前从未体会到的汉诗之美(Legge, 1876: 33/35)。可见,1871年第一版《诗经》译本出版之后,理雅各的诗学观发生了彻底的转变,这种转变最终成为他重译《诗经》的一个重要因素。
(3)诗外策略阐释译诗正文和诗内策略。译者在译作正文之外增加的信息一般会介绍翻译的缘起、原作(包括原作的文学特色、文化传统、历史背景、文学价值等)、翻译策略与方法等。理雅各在两本版本的译文中均对《诗经》的文学特点和价值、翻译方法和策略、翻译时的参考资料等作了详细的介绍。但因为1876年的译本主要针对英语读者,对《诗经》原诗的介绍更加简单(Legge, 1876: 31)。
仔细对比以上三条动态性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译者的诗学观居于核心地位,它决定了译诗的形式和译诗词语的处理。两个版本的《诗经》译本体现了理雅各迥异的诗学观念,一种诗学观认为英诗韵律会损害原诗的意义和情感,译文应当尽量忠实,另一种认为英诗韵律有助于传递《诗经》的诗学价值和中国古典诗歌之美。这是造成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体系动态性的一个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还有社会文化因素等其他原因。1871年的译本出版之后,理雅各便忙于翻译其他中国典籍,无暇顾及重译之事。1874年春天,理雅各的侄子约翰·理雅各建议他把《诗经》重译为英语韵诗,并答应可以再找亚历山大·克兰(Alexander Cran)帮忙,理雅各这才与他人一起完成了重译工作(Legge, 1876: preface)。当然,以上是从较为宏观的层次上对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体系的动态性特征进行归纳总结,动态性特征的具体表现有很多,需要我们结合实际案例具体分析。
5 结语
本文综合使用语料库和文本分析的方法,揭示了同一个译者,在同一个时期,翻译同一部原作时在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所反映出来的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体系的动态性特征。对《诗经》1871年和1876年译本的语料库数据分析显示,1871年的译本词汇丰富程度较低,诗歌行数与原诗一致,平均每行音节数较多,译诗未分节,且无韵律格式,而1876年译本的词汇丰富程度较高,译诗行数比原诗多105行,每行音节数有固定规则,译诗均分节,绝大部分诗歌有比较整齐的尾韵形式。对语料库数据和相关副文本的研究显示,1871年的译本使用少许古旧词语,译诗为无韵体自由诗,词语的翻译忠实于原诗,副文本对《诗经》以及翻译原则和策略的介绍较为详细;1876年的译本中古旧词语的使用较多,译诗主要为韵诗,对词语和诗行的改译较大,副文本对《诗经》以及翻译原则和策略的介绍较为简略。汉语古诗英译策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以及特征的分析需要我们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