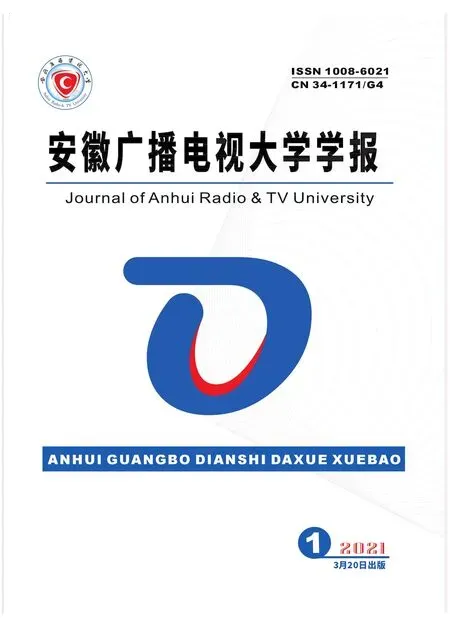论岳飞与杜充的关系
史泠歌
(铜仁学院 人文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
杜充,相州人,是岳飞的同乡,“喜功名,性残忍好杀,而短于谋略”,宋哲宗绍圣年间(公元1094-1098)登进士第,出任过光禄少卿、沧州知州。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东京留守宗泽去世,杜充接任东京留守,自此至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十一月马家渡之战,一直是岳飞的直接上级。但岳飞归属杜充直接领导,又是建炎三年初奉命率军回开封后的事。岳飞与杜充的关系如何?岳飞究竟是不是宋高宗所说的杜充“爱将”?是什么原因导致岳飞离开杜充,独自走上抗金战场?这些皆是研究岳飞的重要问题,也是研究南宋初年对金战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唯有岳飞独自成军后,方有克复建康之壮举,使南宋得以在东南立足。本文拟在前辈学者们的研究基础上,对岳飞与杜充的关系进行考察。
一、杜充的对金政策与作为
建炎元年(1127)至建炎三年(1129),杜充担当抗金重任的官职相继有北京留守、东京留守与江、淮宣抚使,了解杜充在三个职位上的对金政策与作为,是了解杜充与岳飞关系的重要前提。
(一)杜充任北京留守时“闭门不出”以避敌
《宋史》载:“旧制,天子巡守、亲征,则命亲王或大臣总留守事”。北宋东、西、南、北京留守各一人,职责重大,“管掌宫钥,及京城守卫、修葺、弹压之事,畿内钱榖、兵民之政,皆属焉”。南宋初创,并置东京留守、北京留守,建炎元年六月,宋廷以延康殿学士宗泽为开封尹、东京留守,显谟阁待制杜充为宝文阁直学士、大名尹、北京留守。大名府与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并号称“陪京”,“以大名当冲要”。志在“渡河恢复旧疆”的宗泽自然明白大名府为拱卫东京开封之屏障的重要性,因此移檄河北东路提点刑狱公事郭永,要他“与帅杜充、漕张益谦相掎角。永即朝夕谋战守具,因结东平权邦彦为援,不数日,声振河朔,已没州县皆复应官军,金人亦畏之,不敢动”。郭永联络了曾与宗泽一起出兵救开封的京东、西路安抚大使、兼知东平府权邦彦,准备共同配合宗泽的北伐大业。杜充空有虚名与大志,而没有治军管理之才,与张益谦同是误国败事之人。
建炎二年(1128)正月,北京留守、兼河北东路制置使杜充“奏磁、洺解围”。实际上,是濮王赵允让孙赵仲忽少子,皇叔、右监门卫大将军、贵州团练使赵士珸率领“义兵”收复的洺州。并非有学者所认为的:“危急时刻,杜充主动出击金军,收复了磁州、洺州,振奋了士气,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关于宗室赵士珸率领义兵收复洺州之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最为详细:
(建炎元年七月甲午)初士珸从上皇北狩,次洺州城东五里,与诸宗室议,欲遁还据城。谋未就,而敌围已合,同行皆散去。无一人留者。士珸得蹇驴,跨之西驰……迟明,抵武安县……得少壮者百余人,从至磁州,舍于州治。乃召集义军以解洺围。不旬日,得兵五千人,归附者至数万,以王江、李京将之。……及金人遣万户[余列]围洺州,(知洺州王)麟帅军民以城迎拜。军民怒,并其家杀之,独余统制官韩一在城中。士珸至邯郸,而统制官李琮亦以兵会。时金兵未退,士珸夜半薄城下,力战,破其寨。翌日入城,部分守御。金人力攻之,士珸励将士,以火砲中其攻具,以计生获其将领,乃解围而去。
赵士珸解洺州之围的主力是“归附者至数万”的“义兵”,并非是杜充下令出兵解围,属杜充管辖范围,其上奏理所当然。郭永曾画三策以给杜充,并问他看了没有。杜充回答:“未暇读也。”早就看透杜充“名称甚盛”却无能本质的郭永,当面责备杜充“人有志而无才,好名而遗实,骄蹇自用而有虚声”。正如郭永所说,杜充“当大任”只能误事。当年三月,杜充“与金人战于城下,败绩”,自是意料当中之事。此后,杜充在大名府“闭门以守”,再不敢出城与金军交战,因“败绩”降充显谟阁待制。七月,杜充任东京留守时,才复枢密直学士。宋人“南宗北杜”赞誉之语,是对宗泽守卫治理开封的肯定,并不清楚杜充的作为及其对金军的畏怯与无能,而是将赵士珸解洺州之围的战功归于杜充,才有此语。
(二)东京留守任上,擅弃开封
建炎元年七月,宗泽抵达开封后,组织军民部署开封城内外的立体城防,用抗金目标收编多股盗贼,组编留守司大军,谋划大举北伐。仅半年有余,东京留守司军就被宗泽锤炼成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在抗金战场上取得了不少战果。建炎二年七月,因宗泽去世,他编练的留守司大军,“数日间,将士去者十五”。
以宋高宗和黄潜善、汪伯彦为首的投降派,当然不会同意开封官民以宗泽子宗颖“继其父任”的请求,而是派遣杜充为东京留守,宗颖则为留守判官。南宋小朝廷要求杜充“遵禀朝廷,深戒妄作,以正前官之失。即便没有宋高宗与黄潜善、汪伯彦的叮咛和告诫,杜充也“无意于敌,尽反泽所为”。若杜充真正能做到“尽瘁国事,以继前官之美”,之前离开的将士还可以重新回归留守司。事实上,他只是“正前官之失”,上任伊始,立即终止宗泽的北伐部署,“河北诸屯豪杰皆散”。宗泽在世时,“既定先以薛广、张用、王善前驱统离城下”,薛广所部向相州挺进,因王善和张用两部未去会师,当年八月,薛广与金军“战于相州,败死”,“其众皆散”。相州城在经过近两年的苦守后,在建炎二年十一月被金军攻破,守城赵不试自杀。河东和河北的最后一批州县,包括北京大名府,全部被金军占领。
宗泽与北方义军约定建炎二年六月出师,配合北伐,杜充却断绝了对北方义军的联系与支持。“宗泽在,则盗可使为兵,杜充用,则兵皆为盗矣”。杜充“又务诛杀,故城下兵复为盗去,掠西南州县,数岁不能止”。面对金军的冬季攻势,杜充既没有积极谋划抗金对策,更没有派遣岳飞等留守司将官迎敌,“闻有金师,乃决黄河入清河,以沮兵”。杜充“决黄河”并不能阻挡金军骑兵,危害的只能是百姓,可见其既无与金军作战的勇气,也无作战的计谋。

从杜充当时的差遣来看,宋廷将关系到南宋政权生死存亡之重担交给他,他却擅弃开封,意味着金兵不费一兵一卒,就得到了长江以北的土地和人民,还可以渡江南下,直接威胁到南宋王朝的安危。宋朝丧失大约三分之一的土地,主要在杜充主持前沿军务之时。
(三)防守长江,“沿江皆无备”[3]978



总之,杜充不论是守北京,还是东京,以及长江防线抵御女真骑兵皆是外行,逃跑、内斗,以及在下属面前耍威风倒是内行,倒是“成就卓著”。
二、岳飞解救了杜充的个人危困[10]
杜充任东京留守后,除了“尽反泽所为”,将宗泽的北伐部署破坏殆尽,还充分展现了他“残忍好杀”的一面。杜充为树立自己在留守司的威名,便着手实施排除异己的错误行动,引发了自相残杀的内战,且在这场内战中使自己深处危困,而岳飞,作为杜充的下级,解救了杜充个人危困。
留守司统制官张用,与留守司将官曹成、李宏、马友皆拜为义兄弟,有数万兵力,杜充“以用军最盛,忌之”,企图消灭张用军,来增强自己的威望。当时张用军驻扎在开封城南的南御园,王善军驻扎开封城东的刘家寺,建炎三年正月十六日,杜充紧急命令屯驻在开封城西的岳飞、桑仲、李宝等军在南薰门集结,准备突袭张用军。《鄂国金佗续编》中有岳飞对幕僚黄纵谈论当时战况之语:“昔杜充留守京师,某有兵二千,来受充节制。始至,适城外有大寇数万,充即命某往战。充谓之,杜且斩。某不敢以兵寡不敌为辞,即往说贼约降,来禀充,充曰:‘我何尝令汝受降,须为我擒之!’某复往责贼,以约降而缓来,今不复受降矣!愿与汝挑战。贼魁出斗,某驰骑独往,奋大刀劈之,自顶至腰分为两,数万众不战而溃。”所谓的“大寇数万”,即驻扎在开封城南的张用军,以及驻扎城东的王善军,面对杜充的威胁,只能应战。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岳飞并不想参加杜充消灭异己的战事,始“以兵寡不敌为辞”,继以“说贼约降”,希望能避免自相残杀的内战,但是杜充却不同意,只能服从命令,被迫参加杜充引发的内战,且以寡击众,战败张用等军。
南薰门战败后,王善、张用军转攻陈州,杜充遣马皋军追击,被二者击败。二月,张用因久攻不克,引军离去。王善继续围攻陈州,杜充命都统制陈淬率领岳飞等“合击之”。岳飞“遣偏将岳亨,以游骑绝其行剽之路,获其饷卒、牛、驴。善兵不敢复出”。当月二十一日,岳飞率军在清河与王善军战,“大败之,擒其将孙胜、孙清以归,所降将卒甚众”。六月二十日,岳飞率军在开封府太康县崔桥镇西再次击败王善军,岳飞“单骑与岳亨深入,执馘以还”。张用离开陈州后,流窜至江西,在铁路步再次被岳飞击败。
南薰门之战前,攻击王善等军的东京留守司“官军大败”。此败关系到杜充的生死存亡,故他对岳飞说:“京师存亡,在此举也。”岳飞手下的将士,面对张用、王善等二十万大军,“众皆惧不敌”,岳飞却信心十足,鼓舞士气,“贼虽多,不整也,吾为诸君破之。”岳飞“左挟弓矢,右运铁矛,领数骑横冲其军。果乱。后骑皆死战,自午及申,贼众大败。”之后的数败王善,在铁路步再击败张用军,都是解救了杜充因处置不当造成的个人危困。杜充因此认为岳飞是可以信任和依赖的下属,亦不足为奇。
三、岳飞并非杜充“爱将”
(一)岳飞降于杜充与杜充用为统制之说辨析
熊克《中兴小纪》卷4建炎二年十一月条记载,河东招抚司都统制王彦“以效用人岳飞为军将”,“久之,飞见疑于彦,乃去,自为一军。至是,飞降于东京留守杜充”。李心传《三朝北盟会编》卷120载,“岳飞者,初隶张所营效用,飞随都统制王彦往太行山,遂自为一军,后归京城留守司,杜充用飞为统制”。同书卷203引《林泉野记》亦有相同记载。徐梦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载,“(建炎二年十一月)初,河北制置使王彦既渡河,其前军准备将岳飞无所属,遂以其众千人降于东京留守杜充。时种师道小校桑仲为溃卒所推,亦降于充。充皆以为将。”这四条所载“岳飞降于东京留守杜充”之说与“杜充用飞为统制”之说,皆有错谬。
建炎元年七月,宗泽任命八字军首领王彦“制置两河军事”。在太行山抗金的岳飞因与王彦抗金策略不同,深感与王彦难以共事,当年冬率领部众赴开封府接受宗泽的领导,成为东京留守司的一员将官。十二月,与金军在孟州汜水关的一战,岳飞一举打败金军后,被宗泽任命为统领。在宗泽的领导下,岳飞英勇奋战在抗金战场上,保持了“每出必捷”的作战记录,不久被提升为统制。
在建炎元年冬到建炎二年春战事中,岳飞的军功在东京留守司的将官中尚非是头等的。然而宗泽还是看上岳飞,在战后休整时找岳飞谈话,要其学习阵法。正是在讨论阵法之后,岳飞方才升迁统制。《宗忠简公事状》中所载宗泽让岳飞学习阵法的对话,《宋史》卷365《岳飞传》所述大致相同。岳飞后来组建岳家军,其基干正是原东京留守司军,且继承了宗泽治军用师的优良传统。故黄震评论说,宗泽“虽身不及用,尚能为我宋得一岳飞”。可知岳飞在建炎元年时,已经投奔东京留守宗泽,后升为统制。建炎二年七月,杜充接任东京留守时,岳飞依然是东京留守司的统制,只是在西京护陵寝,何来岳飞“降于杜充”,“杜充用为统制”之说?故熊克、李心传与徐梦莘的此段记载为误。
(二)岳飞为杜充“爱将”之说辨析
《中兴小纪》卷9建炎四年七月辛亥条、《鄂国金佗稡编》卷5《行实编年》、《鄂国金佗续编》卷17章颖编《鄂王传》、《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上卷2《范宗尹》皆载,建炎四年(1130)七月,右仆射范宗尹说:“‘张俊自浙西东称岳飞可用。’上曰:‘飞,杜充爱将。充于事君失节,而能用飞,亦有知人之明也。’” 岳飞真的如宋高宗所言,是“杜充爱将”吗?
所谓“爱将”,就是上司宠信的将领。如张宪是岳飞的“爱将”,自建炎末年至绍兴初年,已是岳飞的主要助手,战场上屡次立功,在军队管理方面,岳飞对张宪也是信任有加。绍兴六年(1136),岳飞眼疾发作,同提举一行事务张宪在鄂州主持军务;绍兴七年(1137),岳飞并统淮西军、大举北伐计划被宋廷取消,愤而辞职,是张宪与参谋官薛弼抚定军心;绍兴十年(1140)岳飞第四次北伐时,张宪负责收复开封以南地域。而岳飞虽然解救过杜充个人危困,为杜充所依赖和信任,却是数谏杜充抗金都无果,而且杜充也没有给岳飞提供其发挥军事指挥才能的机会,更没有为岳飞的未来发展进行过筹划,岳飞何谓其爱将?若杜充为人治军似宗泽,可能就没有了民族英雄岳飞与在抗金战场上威名赫赫的岳家军。从这一角度来看,是杜充成全了岳飞。
邓广铭先生在《岳飞传》中说,岳飞“因为有过去的战功和威名作保证,有他的正直坚定的态度作保证,便特别赢得了杜充的厚爱。”以杜充的残暴性格来看,岳飞数次进谏他都没有发怒,也算是“厚爱”吧。与岳飞与同一时期的王德,是刘光世“爱将”,赵密,是张俊“爱将”,杨政,是吴玠“爱将”,看看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和信任表现,再对比杜充与岳飞之间的关系,就会清楚杜充只是利用岳飞的善战和威名,解除自己的个人危机,进而保全自己的官位,实际上并没有把岳飞当作自己的“爱将”。
四、岳飞离开杜充的原因
岳飞之前因为抗金擅自脱离王彦已经受到了惩罚,为何又在建炎三年十一月建康之战后,在杜充未逃往对江真州前一天,离开杜充走上独自成军的道路?关键因素就是杜充的无能与残暴,以及岳飞渴望实现抗金理想。
(一)杜充的无能

岳飞有坚定的抗金理想,有“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军事思想,见识过张所的抗金志向,敬佩宗泽的治军有方与恢复故土的远谋,而杜充口口声声说:“方今艰难,帅臣不得坐运帷幄,当以冒矢石为事”,实际上却是“闭门不出”。杜充岂但是“短于谋略”,其实是只会说大话骗人,全无应战方略的庸人,自然遭到岳飞的鄙弃。对于杜充的无能,宋高宗后来也承认,“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闲猖獗。”
(二)杜充的残暴
杜充的残暴好杀,众所周知。他为沧州知州时,就滥杀无辜,留守东京时,“又务诛杀”,岳飞解救杜充个人危机的南薰门等战,也是因其残暴好杀引起。杜充在建康府“专以残杀为政,斩人无虚日”,引发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将领的不满与愤恨。建炎四年五月,刘光世上奏时再次控诉杜充的好杀:“杜充当权,求一节制,即能杀人,……况当路大权,生死在手,臣不容无惧。”《宋史·杜充传》也有“伺其败,众将甘心焉”之语,可知杜充对下属的苛刻与蛮横程度。
岳飞之前因为离开王彦付出了代价,故在杜充手下不敢再轻易做去留之计,只能忍耐。从他劝谏杜充的话语中可知是强忍怒火。但是,“亲眼看到过张所和宗泽的处事的规模,而志节方面又身为张所和宗泽所熏陶感染过的岳飞,能够安心听受杜充的节制吗?”多次目睹杜充的无策、无方、无能、无耻,岳飞的失望之情可想而知。杜充的残忍好杀,也是持“‘以仁为本’,珍视人命的军事观”的岳飞所不能忍受的。吕中《中兴大事记》曰:“此泽去,而东京之地不可守也。……充守东京,则虏至维扬。充守建康,则虏至明州。以充继泽,何异以渊代逖,以姜维而续孔明之事功!……宗泽死,而杜充守于外,天下事可知矣。”吕中说得透彻,岳飞也非常清楚,唯有离开杜充自成一军,才能实现“尽忠报国”的理想与抱负。
马家渡战败后,岳飞率部众退屯钟山,在杜充逃到江北真州之前,就做出决定离开杜充,寻找南宋朝廷。正因为杜充之叛,所以宋廷没有对擅自脱离杜充的岳飞进行责罚。总之,岳飞离开杜充,在宋金战争的时代背景下,是岳飞抗金的理想抱负使然,加之无法忍受杜充的无为与无能,最终独立成军走上抗金战场,亦是南宋初年抗金事业的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