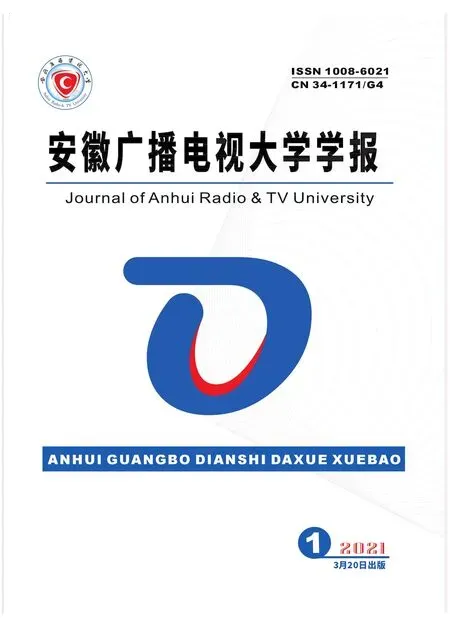诗歌《“我在重要的篱笆间生活”》作者形象阐释
段晓曼
(北京外国语大学 俄语学院,北京 100089)

而生与死的问题也是本文所要探讨诗歌的重要主题。“死”并不可怕,诗人在生活中也多次流露出对死的无所畏惧,对诗人来说,“死”中孕育着“生”,奔赴“死”是为了“重生”。这种对生死的哲理认知在诗歌艺术世界中得以自然流露。悖论而又不难理解的是,正是在艰难而充满禁令的沃罗涅日时期,诗人迎来了诗笔中断近一年后的灵感迸发期,正如A.阿赫玛托娃所说,“令人吃惊的是,广阔、宽度、深邃的呼吸恰出现在曼德尔施塔姆身处沃罗涅日时的诗歌中,而这期间他的处境是完全不自由的。”这里提到了现实生活、诗人个性与其诗歌艺术世界间密切的联系。无疑,诗人、小说家等文学创作者在作品中表达他本人对艺术、语言、人生的理解和取舍,并且这种理解和取舍与作家本人的生活和精神经历不可分割,很多作家甚至会以自己为原型构建人物形象,如《叶甫盖尼·奥涅金》《战争与和平》。但即便作家以真实姓名出现在作品中,也区别于真实的本人。作家不是直接作用于作品,而是借助于“面具”来呈现某种包罗万象的价值取向。这个“面具”就体现了作家在具体作品中呈现的“作者形象”。
一、“作者形象”与抒情之“我”
苏联著名学者В.维诺格拉多夫通过对大量有代表性的小说、诗歌作品的研究,结合语言学与文艺学的方法,从语文学的角度创建了文学修辞学这一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科学。“作者形象”理论便是他提出的文学修辞学的核心范畴,并且适用于文学以外的其他功能语体,具有普遍的价值。在维氏看来,“作者形象”是将文本组织、连接、统一起来的范畴,它将所有的修辞手段粘合成一个统一的系统,是文本的组织中心、结构轴心,是文学作品的核心,体现在文本的语层、修辞、风格、谋篇布局、视角、主题各个方面。我国学者也指出,“作者形象”包含了作者“对艺术现实的态度和对全民语的态度”,是“作品创作理念的唯一承载者”。А.戈尔什科夫认为,维氏这一学说是20世纪语文科学中空前的大事件,并清晰地指出:“‘作者形象’总是存在于文学作品中;它不是现实生活的作家,而是作家的‘演员’面具;任何的传记信息被果断摒弃;它可以以作品为基础被重构出来。”并且,这种重构可以借助一定的手段。
维氏从对文学文本的语言风格分析出发来阐释作者形象,因而认为文本主要是独白的。“独白”指的并不是作品中只存在一种声音,而是从“作者形象”一体独大的统摄作用而言的,正如А.戈尔什科夫所言,“‘作者形象’中融合了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语言手段,不同的风格等等”。巴赫金则从美学和哲学的角度发现了文本中的对话性,进而指出“作者”存在于任何艺术作品中。这个“作者”是以创作主体、创作个性被感知,而不是作品中刻画的某个具体形象,也非现实的作家其人。巴赫金并未用“形象”而是用“第二性的作者”来指称作品中出现的“作者”。他指出,“第一性作者”是真实的作家,他创造了“第二性的作者”,且后者区别于作品中的其他形象,具有创造性。可以发现,巴赫金的“第二性作者”与维氏的“作者形象”实为殊途同归。
维诺格拉多夫还专门研究了诗歌中的抒情之“我”,即抒情主人公的本质。维氏指出,抒情诗中的“我”不同于叙事作品中的讲述人“我”。抒情诗虽然很大程度上表达了诗人的直接感受,抒情之“我”同样不同于诗人其人,这一点不必再赘述。维氏认为,抒情之“我”是抒情诗研究的中心问题,并且与叙事作品中所提到的“作者形象”实为一体。“抒情之我译成维氏的语言,就是作者形象”,“抒情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正是或基本上就是叙事作品中的作者形象”。王加兴教授就曾探讨过普希金借助抒情之“我—作者形象”在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对换说修辞格的创新,展现了“作者形象”理论巨大的阐释力。
白春仁老师指出,“抒情短诗一般没有复杂的人物形象体系,视角不多,语层也较为单纯,基本上是抒情主人公驰骋情思的天地。考察作者形象……侧重点应当放到‘抒情之我’的语层上,放到交错变化的语型上,循着诗人思情波澜的开合起伏,寻求他表现情志的手法和辞彩,进而揭示诗中人物景物同主题思想的关系。”这为阐释诗歌提供了具体的策略。
二、《“我在重要的篱笆间生活”》作者形象的几个维度
В.阿格诺索夫曾指出,曼氏在创作的早期有时被称为“没有抒情主人公的诗人”。其原因在于,很多诗歌中抒情主人公虽然存在,但不以“我”显露,因此客观、哲理的意味凸显。阿格诺索夫教授认为,从1921至1925间的创作开始,曼氏诗歌中的抒情性得以巩固和确立。抒情性,也就是接近于诗人其人的作为创作主体的个性。作为曼氏后期创作的诗歌,《“我在重要的篱笆间生活”》也体现了诗人创作中抒情主人公特点的这一变化,诗人在创作中更加接近具体的现实生活,将居住环境写进诗歌,在艺术加工的同时使诗歌内涵更富层次感。
(一)谋篇布局
谋篇布局,或说结构,与作者形象密不可分。文学作品的布局用维诺格拉多夫的话说,就是“不同话语序列在复杂的文学艺术统一体中动态展开的系统”。不同的话语序列按照不同的方式排列组合,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布局。而话语序列可以是各种语型,不仅包括狭义上的词汇,也有按某种语音、句法、修辞手法等统合起来的某个序列。可以发现,在诗歌《“我在重要的篱笆间生活”》中,抒情之“我”的语层中糅合了多层特点鲜明的话语序列。从内容层来看,文学作品的内容是“主题的展开”。而展题又是在语言材料的组织,或说话语序列中进行的。这样,同样的主题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内容、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可见,话语序列、主题与内容、布局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对揭示作者形象尤为关键。
《“我在重要的篱笆间生活”》有三个诗节,每节四个诗行,从话语主体上讲,诗中只有抒情之“我”的语层。第一诗节抒情主人公揭示了自己生活场所的基本情况:众多的篱笆和工厂、风、沼泽、木柴小路。虽然篱笆、工厂不止一处,但在第一诗节中,除了让人联想到俄罗斯民歌人物“管家瓦尼卡”之外,“我”没有写到任何人物形象,甚至“管家瓦尼卡”的存在也只在“我”的揣测中。副词“白白地”“远”又暗示了某种孤独、失落的气氛。“泽间木柴小路”则渲染出环境的潮湿、凝重、窒息。“我”在这里生活,“在重要的篱笆间生活”,修饰语“重要的”与谓语“生活”中凸显了“我”区别于环境的某种积极主动性,“我”对生命的重视,这便是篱笆之所以“重要”的一个原因。为何是“篱笆间”,而非房屋?前者在空间感上突出“我”“生活”的乃是露天的室外,而非屋内,其中暗含着“我”的精神苦楚,“我”在这里居无定所/寄人篱下,这种“疏离”感在下面两节诗中得到强化。诗歌的视野从“我”近处的篱笆游离至木柴小路伸向的幽幽远方,空间得以延展:
Я живу на важных огородах.
我在重要的篱笆间生活。
Ванька-ключник мог бы здесь гулять.
管家瓦尼卡或许会在这里闲逛。
Ветер служит даром на заводах,
风白白在工厂当值,
И далеко убегает гать.
泽间木柴小路消失在远方。
第二诗节中,紧接第一诗节末尾的“远方”,“我”描写了篱笆住宅周遭寒冷夜幕下的开阔草原、黑耕地和房屋透出的“细粒的”灯火或说星星“细粒的”光;“冻透”一词的过去时态暗示“我”视角的转换,即由远处的“星火”切换至近处的室内,在“我”的笔下出现了真实活动的人——“气恼的主人”,“主人”直义指“我”住所的屋主。据说,创作本诗时,曼氏夫妇居住在农艺师Е.费多温的家里,曼氏在搬至新住所前与他发生了争吵。“主人”又与第一节中的“管家瓦尼卡”“篱笆/菜园”结合起来获得了另一层所指:处死瓦尼卡的大公。“我”仅用一个简单句便将季节、时辰、地点囊括进一幅风景图画中,并在其中使用了两个复合的临时性新词(окказионолизм):“黑耕地的”“细粒的”,暗示“我”在词语中的自由。看似无“我”的四行诗中,到处可发现“我”的踪迹。“冻透”的是“黑耕地的夜晚”,是“夜间的黑耕地”,也是“我”;“夜晚”在星火中“冻透”,也是“我”在室内“冻透”。而“主人”的气恼预示着“我”的命运变化:
Чернопахотная ночь степных закраин,
草原边沿那黑耕地的夜晚,
В мелкобисерных иззябла огоньках.
冻透在细粒的火光里。
За стеной обиженный хозяин,
墙那边气恼的主人,
Ходит-бродит в русских сапогах.
穿着俄罗斯皮靴不停来回走动。
第二节诗中,画面停留在穿俄罗斯皮靴的主人在屋内来回走动,第三诗节衔接上一节,写地板。从字面上看,“我”在描写“主人”因气恼踏坏了“豪华的木地板”,而地板的变形中暗示“主人”愤怒至极,预示着厄运或死亡的降临。细看二、三诗节交界处的动词时态也可以发现,“我”相对于所描写对象的时空视角发生了融合与交替。“动词现在时中存在作者的同步视角……动词过去时指明从同步视角向新的描写过渡”,即在第二节后两行中,“我”与“主人”——屋主或大公处于同一时空,第三节前两行则是“我”时空视角的过渡,既写“主人”的地板变形,又暗示“我”命运的困窘。由此,“我”自然而然从对愤怒主人的描写过渡到直露的自我抒情,最后两行诗可说是全诗的“诗眼”,情感也在高潮中交织、升华:
И богато искривилась половица,
豪华的木地板弯曲变形,
Этой палубы гробовая доска.
这甲板的丧殡之板。
У чужих людей мне плохо спится,
在别人那里我睡得不好,
Только смерть да лавочка близка.
只有死亡和阴谋很近。
可以发现,诗中出现了多个口语词,彼此可构成一个话语序列:(мог бы)гулять, даром, далеко, закраины, иззябла, ходит-бродит, плохо спится, да, лавочка.以及有沃罗涅日地方色彩的话语序列:важные, богато.与曼氏创作中抒情主人公多用中性词甚至崇高词汇不同的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诗中开始引入口语词、粗俗词汇乃至行话。这些词汇既在表达层更富表现力,也作用于诗歌的内容题旨层:一是与诗中出现的民歌形象“管家瓦尼卡”、“俄罗斯皮靴”意象共生相合,显然,“我”在瓦尼卡与大公的故事中找到了抒发自我情感、思索个人命运的寄托;二是暗示“我”与环境间的隔阂与疏离,这一点与诗中出现的对立词汇чужие-близка所隐含的“他人”与“我”、“主人”与“我”间的相斥之意不谋而合。而正如“他人”与“我”之间相斥与相吸矛盾共存,“我”将这些词汇引入描写显然也有融入生活之意。诗人曾在评论性散文《弗朗索瓦·维庸》(1910)中对维庸有如下论述,“就其本质是雌雄同体的存在,能够以内心对话的名义做无限的蜕变……多样地选择极好的二重奏:悲伤者与安慰者……”。诗人显然从这位艺术导师那里借鉴了这种在对话中实现蜕变的精神。
诗中也有与“死亡”相关的话语序列:стена, половица, гробовая доска, лавочка, смерть,除“стена”出现在第二节,其余四个均出现在第三节,准确地说,这一序列主要出现在诗歌的后六个诗行。由此也可看出死亡气息愈加集中。此外第一节“гать”、第三节指代房屋的“палуба”不仅呈现冰雪融化的四月周遭一片水迹,也隐喻“我”人生道路布满阴霾、住所无以依靠的状态。从一至三诗节,这一话语序列在空间上与“我”的距离不断逼近,“死亡”意义愈加直露、密集。正如В.斯维杰尔斯基在其有关曼氏沃罗涅日诗歌的专著中认为,空间的动态“建立在个性所能及的不同容积的空间的相互关系中——从与束缚和死亡相关的最窄小容积到无限的自由空旷”。
与“死亡”话语序列对应,诗中还存在“生”的话语序列:живу, степные закраины, чернозем, огоньки.可以发现这一序列出现在前六行诗中。此外,最后一行出现的“лавочка”除了有“阴谋”之意,也是“лавка”的指小形式,本诗的注解中指出,“лавочка”就在曼氏窗前,曼氏夫妇经常在上面小坐。可见该词中也折射出“我”与生活的契合之处,在“我”看来“лавочка”也是木质物体中唯一可靠的,这也体现在语气词“только”所传达的肯定之意。从上文分析可知,这首三节诗在内容上由两部分组成,前六个诗行主要描写居住的周遭大环境,后六个诗行则聚焦具体的、“他人的”室内。而“生”与“死”的话语序列分布也基本符合这一内涵结构。这样,“生”与“死”在对立中也存在交织融合。在两组话语序列的核心词汇,即诗末“смерть”的抽象性与开头“живу”的具体性、动作性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我”对“死”的清醒认知和对“生”的积极热爱。
“死亡对诗人来说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330首诗歌中,词汇死、死亡出现超过85次……但这不意味着曼氏不热爱生活。相反!……生命/生活一词超过40次。”正如曼氏遗孀Н.曼德尔施塔姆所回忆的:“他接受生活本来的样子,敏锐地感受着生活不同寻常的充实……他说,母亲死亡时他体会到在死亡中有特殊的隆重……似乎对他来说死亡不是终结,而是生活/生命的证明。”这更加论证了上文的分析。对曼氏来说,人格尊严被践踏才令他害怕。
(二)文本间联系
А.戈尔什科夫为“文本间联系”(межтекстовые связи)下了一个定义:存在于某个具体文本中的、借助一定的文学手段表达出来的、对另一个或另一些文本的参考。“文本间联系”是文本的一种可有可无的特征。与“文本间联系”概念相关的是“互文性”(интертекстуальность)。法国后结构主义代表克里斯蒂娃在1967的一篇有关巴赫金的论文中首次提出这一术语。在互文性范畴内,文本被理解成“由其他文本的元素构成,而不是与其他文本有关联”。法国学者罗兰·巴特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他将文本视为“去掉了引号的引文”,提出了“作者已死”的观点。“互文性”被理解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是任何文本的特征。考虑到这些区别以及互文性更典型的用于后结构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文论中,本文用“文本间联系”这一概念,在语文学视角下探讨《“我在重要的篱笆间生活”》中作者形象在其中的体现。
戈尔什科夫指出,文本间联系的实现手法主要有:引文、题词、用引文作为题目、用典及引起联想、重复已有的形象等。这里的引文包括狭义上逐字逐句引用,也包含广义上所有对其他文本进行参考的手法,本文采用狭义上的引文,以区别于其他几种手法。本诗中,抒情主人公主要使用了用典及引起联想的文本间联系手法。
用典,是说文本“与某个固定的文学、历史、神话概念或表达相关联”,或“通过提及众所周知的事实、历史事件、文学作品或某个文学场景等来暗示”。引起联想,是“一种有意识的手法——运用某个词、词组、句子,以激发对某个历史事实、神话、文学作品的记忆。”戈尔什科夫也指出了两者间区别之微小,这也是两个概念经常同时出现的原因。
“管家瓦尼卡”使人联想到俄罗斯民间创作中的形象,首先出现在基于史实而创的俄罗斯神话中,在口耳相传中形成了不同的故事版本和体裁,流行于18-19世纪的叙事诗《大公沃尔孔斯基和管家瓦尼亚》就是其中之一。关于他有不同的说法:如在《俄罗斯人文百科辞典》中,“管家瓦尼卡”被解释为流行于17-18世纪之交的民间叙事诗中的主人公,他是沃尔孔斯基大公的管家、农奴,成为大公夫人情夫的第三年被大公识破、刑讯;在《名言锦句辞典》中,“管家瓦尼卡”在В.克列斯托夫斯基(1839-1895)诗歌中是“可恶的拆散者”,诗歌被谱成曲并被视为俄罗斯民歌。不同的版本或突出大公愤怒至极,瓦尼卡被处死,或突显瓦尼卡被毒打的惨相,歌颂他的勇敢。
“管家瓦尼卡”在俄罗斯口头创作中主要以勇敢著称。上文提到,“主人”可指代大公,在他气恼地踱步中隐藏着不祥的命运变数,通过分析可见,这在第一节“管家瓦尼卡”一句中就已埋下伏笔。“瓦尼卡或许会在这里闲逛”,但是没有,这只是一种假设,因为“我”很清楚,他被捕了、将被处死。另一方面,在这里散步的是“我”。通过假定句中的文化联想,“我”与“瓦尼卡”之间形成多层的联系。“瓦尼卡”的勇敢就是“我”的勇敢:他曾被捕,“我”也因被捕而出现在“篱笆间”。他因“不合适的”爱情被捕,“我”因何便不得而知。他被处死,正符合“我”对自身处境的预感。可见,“我”从这个勇敢赴死、在大公面前坦坦荡荡的农奴身上找到了强烈的共鸣。而“我”截取的正是“瓦尼卡”被捕与被处死之间的一段。由此,“气恼的主人”在屋主、大公之外又映射出另一层含义:国家主人。这样,“我在别人那里睡得不好”中,“别人”的含义得以淡化,“睡得不好”有更深层的原因:对非自然死亡的预感。“我”要融入“黑土”世界的愿望在对“管家瓦尼卡”故事的联想中也得以突出。
值得一提的是,Н.涅克拉索夫写过一首仿民歌风格的叙事诗《菜农(Огородник)》(1846),诗中抒情之“我”是一个菜农,与贵族女儿相爱,被当作小偷抓捕、审问时,他始终三缄其口,最终被鞭打、判处苦役。涅克拉索夫显然化用了“管家瓦尼卡”的故事,在诗中以“我”之口流露出对有情人不得眷属的痛责。这显然同诗人与А.帕纳耶娃的爱情经历有关。相比之下,涅诗中“我”的叙述口吻更富民间故事色彩,“我”就是瓦尼卡,抒发的情感也大有不同。
沃罗涅日时期的诗歌“充满旨在传达心理状态的联想。”В.阿格诺索夫指出,在曼氏的诗中,“读者会看见为数众多的借自其他作者(……但丁、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或取自某个文化历史时期(古希腊、古罗马……)的形象和语句”。К.塔拉诺夫斯基指出,这首与道路情况、对已去生活之路及死亡的思考相关的诗与莱蒙托夫的《我独自一人走到大路上》(1841)有渊源。对比两首诗可发现其中的相通之处。
从韵律上看,两首诗均为五音步扬抑格,均使用交叉韵。诗歌开头一句在声音、句法结构上高度重合:Я живу на важных огородах.// Выхожу один я на дорогу.在结构上,均为自然环境描写与抒情两个部分。在内容主题层面,均有路、夜空、星星、睡梦、孤独、生命与死亡。相同的韵律使得两首诗都有一丝哀诗的愁绪。在对“死”的书写中都表达了对“生”的爱。但两首诗有着鲜明的不同。在空间上,曼氏诗中从开阔的草原转向拘束的室内,莱诗中只有辽阔之地。在结构上,曼诗中两部分在思想感情上是统一的,“管家瓦尼卡”的形象统摄全诗,莱诗中两部分则互相对立:自然的宁静和谐与“我”的不安思索。曼诗中的路是危险可怕的“泽间木柴小路”;黑夜里有“火光”,但寒冷至极;“我”生活着,但“死亡”让“我”觉得更近;“睡梦”与“死亡”对立。而莱蒙托夫诗中,路是发着亮光但艰难的“石子路”;“睡梦”与“死亡”等同,且“我”期望在“睡梦”或说“死亡”中,艺术生命长青。两首诗在抒情格调上也有很大不同,这从句法上可见端倪:曼诗均为陈述句,莱诗有多处感叹句、省略句、问句;曼诗中“我”的抒情更加冷静,莱诗中“我”的感情更加直露。可见,尽管曼氏与莱氏诗歌间存在联想关系,诗中抒情之“我”即作者形象的差别决定了两首诗在同中有着极多的异。
三、结语
“作者形象”作为(文学)文本中统筹全篇的核心,体现在内容层与表达层的方方面面,因而可以在主题、内容、谋篇布局、话语序列等要素的有机联系中探索它的踪迹。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在对各种文学、文化现象的引用或化用中体现其态度,在与源文本的对比中可凸显不同作品中“作者形象”的区别。曼德尔施塔姆被布罗茨基称为“文明的孩子”,他“对世界文化的眷念”体现在具体的诗歌创作实践中,集中体现在作品中“作者形象”往往通过不同国别、历史文化的棱镜进行哲思与抒情。《“我在重要的篱笆间生活”》中的抒情之“我”作为“作者形象”的集中体现,不同于诗人本人,但又与之不可分割,诗人本人的真实所见出现在作品中,在成为诗歌意象载体的同时作为辞象的基本意义而存在。“作者形象”就体现在将“第一性”现实升华为“第二性”现实中。在对命运和死亡的预感中,抒情之“我”表现出对“生”的坚持和热爱,对融入陌生环境、“黑土”生活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