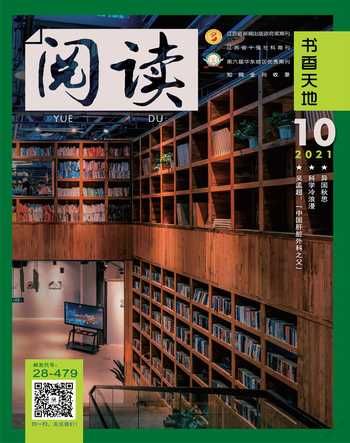王安忆:写作是我的宿命
茱茱


很难说王安忆是不是上海女人的脸相,宽额高鼻长手长脚,听人讲话常常伸长脖子,却把情绪藏得很深。不笑的时候简直肃穆,大概是常年以笔作犁在格子田里劳作的关系。
王安忆长年保持着旺盛的产量,也不断变换着写作题材和写作方式,德国汉学家顾彬说,王安忆写作是神经质的,根本不能停笔,自1979年以后,没有人能像她那样写出这么多值得严肃对待的作品。这种对待写作的方式,仿佛是她与自己,和读者达成的一个契约。之前去香港书展,她先讲了一个关于读者的故事。
监狱里的读者
有一年冬天,她在布鲁塞尔一个小书店里作讲演,来的听众不多,其中有一个中年的中国男人,早早来到,让她在一本《长恨歌》上签名。讲演完毕的提问环节,男人站起来讲了一个故事,他先给大家看那本《长恨歌》上的公章,印的是“布鲁塞尔非法移民拘禁所”,他是当年的非法移民,拘禁期间,监狱里放了两本中文书供人消遣,一本金庸的,一本王安忆《长恨歌》,在大家争着看金庸的时候,他无意地打开了《长恨歌》。曾经是上海人的他,顿时感到“我家临街的一扇窗打开了”,他在监狱里把这本书翻了两遍,后来想尽办法把书带了出来,而后还带着这本书进了法国的监狱。最后他说:今天是我51岁的生日,我带着这本书来到这里见到作者,当度过我的生日。
她讲述的语调是平淡的、迅速的,讲完故事就很快把情绪拉回来,她说自己和读者的关系是微妙的,读者喜欢的,也许是自己不喜欢的一部分。“所以我跟读者更多的是尴尬,读者还是隐性的存在比较好。”
作者与读者,彼此不相见的缘分是奇妙的。当年读《启蒙时代》读到数米的情节,在笔记本里恭敬地抄下来:“在那逼仄弯曲的街巷里,还有一对老年夫妇,你知道他们每天的功课是什么?数米。上午数出的米中午下锅,下午数出的米晚上下锅。这就是他们的内心生活。不是为生计劳苦,也不是纯精神活动,是在两者之间,附着于实物而衍生于内心。他们看上去是有些闷的,不大有风趣,其实是有着潜在的深刻的幽默。”新作《众声喧哗》里面又安排了欧伯伯数纽扣的桥段,带点禅味,像两段独幕剧,聚光灯定格在上海后街弄堂里、细水长流过日子的小市民背上,那是王安忆小说里的城市灵光。
恋恋俗世
昌平盛世里的俗世生活或许叫人倦乏,待经历了动荡苦难,或者犯错惹祸,日常生活就现出疗愈的功用,“它是那种煨药的细火,渐渐地药香满屋,沁人肺腑,疮痍渐平,元气恢复”。她把感官全部打开,反复写市井生活,不厌其烦。有人说,读王安忆的小说最痛苦和最享受的都在于細节,她下笔有如绣花,针脚绵密繁复,她写缝被子的线,“一针一针抽出来,理顺,洗净,晒干,再缝上。今年过了有明年,明年过了还有后年,一点不是得过且过。”日常生活是足以和虚无对峙的,“人生不能看远,看远了都虚无,要有一些近的东西来把你的眼睛挡一挡,就是市井。”所以老百姓是不大会虚无的,要挣钱、养家、追逐情爱,这些足以把虚无感填满。
在她看来,张爱玲和鲁迅都虚无,只是在这条路上,张爱玲和鲁迅迈出了不同的步伐。张爱玲的虚无简单而彻底,她相信人生是沉沦的、走下坡路的,所以她从虚无的入口抽身,转而坚守现世安稳。而鲁迅执意往虚无里走,“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
虚无本身没有欲望,也能让人从欲望中抽离出来,所以王安忆说,虚无本身就是升华。可以注意到的是,这种升华很多时候是由她笔下的女性来承担的,尖刻也好,厚道也好,大多是坚韧的,幸或不幸,都能扛下自己的选择。这种女性书写也寄托了她的审美。“在我的认识当中,男性留给审美的余地不太大,我总觉得他们是主流社会的中心,他们在生活舞台上已经被社会生活塑造过,不像女性带有一定的原始性,所以从美学上来说我是比较倾向于女性。她们更加接近自然本色,这是我的审美,也有点人生观吧。”
她写《我爱比尔》,那个叫阿三的姑娘,怎样因为执著于自己的西方幻想,由师范大学的美术学生,一步步成为专做外国人生意的“暗娼”。读的时候竟有些捏一把汗。王安忆写小说惯用叙事体,作为操控人物命运的作者,她的主体意识很强烈,人物对话不多,而以画外音般的叙述推动情节的前进,作者的立场和评判很是一目了然,也因如此,拿捏火候变得很重要。王安忆觉得这种写作方式能更方便明确地表达作者观念,“其实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还是比较喜欢写对话,你看《小鲍庄》里还是有很多对话,到后来慢慢我就比较迷恋叙述。叙述有一种客观性,它可以让我和我要写的故事拉开距离,然后客观地再写,可能写出来的面貌会很丰富。对话其实要作很多铺垫,小说毕竟不是戏剧,小说有个方便之处就是它可以叙述,小说的长处是叙述。”
她写的是人,也写的是塑造人的城市。每个作家都有一个施展想象力的舞台,这个舞台通常是与其休戚相关的山乡或城廓。沈从文有他的湘西边城,莫言有他的高密,上海似乎是王安忆别无选择的书写场域,她轻易不流露自己对上海的爱恨,哪怕是有讲述上海盛衰的煌煌长篇《长恨歌》与《天香》,繁华落尽唏嘘无尽,她还是要说这个城市其实是粗粝的、不浪漫的。
远去的理想国
1983年,她和母亲茹志鹃来到爱荷华参加聂华苓的国际作家写作计划,台湾作家陈映真去机场接她们母女,那段经历,成为她人生的转折点。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常带着些被时代亏欠的怨愤。那一年同去爱荷华的有很多来自“问题国家”,菲律宾、波兰、印度尼西亚。陈映真对她说,“你看看你周围,他们问题都很严重,不要以为就中国问题严重”。这是很重要的转折,视野打开,也从耿耿于怀中走出来。而陈映真,这个来自中国台湾的具有左翼色彩的理想主义者,无疑成了她极其重要的前辈。王安忆时常强调前面要有人:“我的焦虑是很想寻找前辈,因为前辈意味着传统。”
陈映真对王安忆和那一辈人的影响也许是深远和复杂的,罗岗说,“陈映真和鲁迅的契合点,更重要的在于,他们到晚年,都接受了社会主义”。时代变迁,以大家都看到的方式无可阻挡地前行,世界变得一样,她想要紧跟的前辈,未及赶上他,“他已经被时代甩在身后,成了落伍者”。陈映真对很多人和事失望,未竟的事业,未完成的理想国,让身后的王安忆也染上了他的失望。“我们要的东西似乎有了,却不是原先以为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要什么了,只知道不要什么,我们越知道不要什么,就越不知道要什么。”
也是同一年,聂华苓的丈夫保罗·安格尔生病,从纽约请来一个大师,顺便给这些中国作家看相,看到王安忆母女,“他说得很微妙,我很难表达清楚,他说你们俩都是艰辛,但你妈妈是苦的艰辛,你是乐的艰辛”。我欲要将这谶言同她的写作生涯拉上关系,她又很迅速地打断:“我跟你说,宗教的事情、哲学的事情都不能说得那么死,你们这个年龄不能这么快下判断。”
我无以得知她的失落或希冀,只知道写作是她的使命,大概也是宿命。我也宁愿缩回读者的距离,继续等待下一个虚构的理想国。
(摘编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无物之阵》一书)
3785501186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