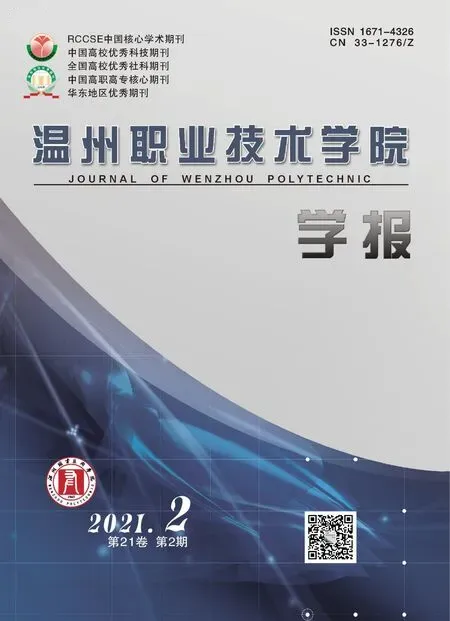“南怀瑾现象”综论
陶祝婉,沈 潜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自20世纪90年代起,南怀瑾的著作在大陆大量出版,一时成为最畅销的系列文化读物之一。如今,南怀瑾的著作几乎都有大陆版,其人也受到“许多人的高度的崇敬”[1]。这一著作热销、作者被热捧的现象堪称“南怀瑾热”。同时,在这波热潮中,学界也就南怀瑾的著述及为学问题展开了争鸣,热捧和争议并存,形成了“南怀瑾现象”。本文从这一现象的成因、围绕南怀瑾著述的争议、对南怀瑾其人的评价及定位三个方面,结合学界主要意见做简要述评。
一、“南怀瑾现象”的成因
“南怀瑾现象”形成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这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并非偶然,它既有深刻的社会时代背景,又基于南怀瑾为学及其著作的自身特点。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基于不同视角的解释,主要有四类观点。
1.适应道德人心疗救的需要
杨志刚认为,因为商品经济的繁荣、物质生活的繁盛、法制建设的滞后、道德领域的失范和无序,人们试图通过挖掘传统伦理道德资源以重建道德体系,因而形成“国学热”。“南先生谈文化,往往谈的就是人格修养,道德教育”,这是他的作品得到赞许的原因[2]。徐洪兴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五四”先辈们摧毁了旧道德、旧文化,但新道德、新文化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这使得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进退失据,致有“文革”,又有之后的功利至上、道德沦丧。南怀瑾的著作重在讲人格的培养,其目的在于启发我们“在进退失据的现实环境中”,如何避免“在纷纭混乱中忙得团团而转,失落本位而不知其所适从”[3]。汪涌豪则强调自19世纪西方物质文明对中国社会、文化形成冲击以来,人们面对物质膨胀和道德沦丧,失去了有效应对,南怀瑾先生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精研儒释道三家,发见民族精神和理想人格,为在现实环境中进退失据的人们及纷乱之世中的颓败人性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疗救[4]。由此可见,“南怀瑾热”与“国学热”同步,其成因与后来的“于丹热”有诸多类似之处。
2.成功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
徐洪兴认为,南怀瑾的著作让人趋之若鹜,原因在于南怀瑾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进行了必要的现代化、世俗化、大众化的调整、转换,适应了人们渴望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需求[5]。张红霞认为,一般学者对经典的研究往往注重于考据、训诂和疏释,而南怀瑾对经典所包含的思想精髓有着深切的体认,进行了极其睿智的发挥和阐释,讲述经史合参、旁征博引,语言表达通俗流畅、生动诙谐,使得读者在轻松、浪漫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传统文化的熏习,开启人生智慧,因此对之好评如潮[6]。邢东风也认为,南怀瑾的著作深入浅出、触类旁通、自成一家之言,而且文笔流畅,没有干涩古板的学究气,并不时闪现智慧的火花和独到的见地,因此能够吸引广大的读者[7]。陈士强、郭建庆认为,南怀瑾的著作之所以深受各阶层人士的喜爱,并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是因其能从古代的人和事中撷取经验教训,作为今日的参考和借鉴[8]。姜义华也认为,南怀瑾著作之所以畅销,重要的一条就是南怀瑾先生为学术大众化和大众学术化尽心竭力,他以博大精深的学术功底和在中国传统文化各方面的高深造诣,对人们所关切的现实问题所作的贴近人心与人情的解说,使读者不仅将其视为严师,而且视为知己[9]。也就是说,南怀瑾的思想精髓和表达方式符合大众口味,契合了传统思想文化普及化、大众化的时代需求。
3.一种面对新的文化情境和文化大众的释义
顾晓鸣认为,在现代文化格局中,人们阅读时更看重联系自身生活和工作需要,不将作者本意作为阅读追求的主要目标,且与文本相比,人们更看重作者的阐释方式和写作行为。如南怀瑾按照“自己的领悟和讲授对象的需要”对经文进行主动的“别裁”和“他说”,就颇为符合现代文化机理。南怀瑾的机锋和智慧、“身体力行”的修持以及“社会性事业”的成功,也符合“(后)现代思潮对以西方逻各斯为中心的理性及其推演方式的怀疑和颠覆”以及“世界范围对人的躯体体验与文化关系的兴趣和研究”的大环境[10]。由此看来,南怀瑾的传统文化叙事不仅体现了道、禅的体验式、悟道式特点,也正呼应了后现代以来阐释学的新思潮。
4.诸多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曹晓虎认为,南怀瑾广泛阅读传统文化元典,有自己的学术创见。他“用现代学理性方法传播传统文化”,修养扎实,境界高深。南怀瑾携在台湾等地奔波教化三十多年的经验和影响力进入大陆,适逢大陆民众热切渴求国学之时,其著述语言生动通俗平实,使用现代商业传播手段。总之,“南怀瑾现象”是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交融的产物、思想研究和修行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海峡两岸文化市场交流的成果[11]。
5.南怀瑾本人长期苦心经营的结果
姚彬彬认为,南怀瑾及其门人的作品经常写到南怀瑾与早已有定评的近现代儒释道诸领域的著名学人以及各界名流的“令人难以置信”甚至“骇人听闻”的传奇交往经历,有意识地利用了常人潜意识层面的偶像崇拜的心理,神化自己的形象;而南怀瑾鼓吹所谓的“实证”或“修正”,其实是给予儒释道等传统文化典籍以神秘主义角度的诠释,从而吸引了许多具有猎奇心理的读者。因此,“南怀瑾现象”的形成,或可导源于文化启蒙的不够成熟,中国社会多年来重视科学技术而忽视科学精神的误区,亟待弥补[12]。
二、关于南怀瑾著述的学术争议
大陆读者主要是通过南怀瑾的著作了解其对传统文化经典的解读,因而围绕其著述的学术争论也必然成为“南怀瑾现象”中的热点。这些争议大致分为肯定和否定两派。
1.肯定其解读视角的价值和文化普及之功
学界普遍认为,从学术视角考察,南怀瑾的著作确实存在“硬伤”,但从传统文化普及的效果上看,他的著作自有其不可否认的价值。
郭冰认为,南先生在学术研究上也不可避免有先入为主之念,陷入主观臆断,致时有为合题意而生硬解释之嫌,他的主观随意性决定了《论语别裁》不可能是一部学术性很强的《论语》研究著作,他并不重视考据训诂,而多杂取百家且切合他生活经历的“一家之言”,所以书中很多地方有明显错误。但“南先生解读《论语》时时体现着他自己的思想特色,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将《论语》讲得妙趣横生,这是他的《论语别裁》大受推崇的原因。虽然他的讲解并不一定是《论语》本义,但至少他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角度,为传统文化的普及做出了贡献”[13]。他既指出了《论语别裁》存在明显错误,不是学术性很强的研究著作,又分析了它受欢迎的原因,肯定了它的价值,这是中肯而客观的评价。
曹晓虎认为:“不可否认,南怀瑾也有一些言论的学术性不强,甚至有些说法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不能过于苛责。毕竟,南怀瑾普及传统文化的受众不是学术界,而是普通大众,传道、授业、解惑都只能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南怀瑾思想涉及面太宽,涵盖易学、儒学、佛学、道学,兼及医卜天文、拳术剑道、诗词曲赋,不可能在每一个领域都达到专家级的水平。即使是学术大家在专业领域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学术错误。”[11]10他认为南怀瑾著作面对的是普通大众,语言表述上不宜过于学术化;南怀瑾思想涉及面太广,不可能全部精通,偶然的错误在所难免。既分析了这些“硬伤”产生的原因,又指出了它合理的一面。
宋红宝也认为南怀瑾的《论语别裁》“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在学术史上的价值还是可圈可点的”[14]。刘建军认为南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典籍的新诠释,为人们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空间与人生天地[15]。刘燕菇认为南著在众多诠释经典的作品中别具一格,既讲究实用性,又兼具哲理性,是传统文化经典诠释作品中既通俗又不失水准的优秀作品,“他以传统文化经典蕴含的哲理思想照察人心,从文化的角度剖析当今社会,其诠释传统文化的方式方法及内容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16]。徐祝林、徐徐两位学者也认为,南怀瑾博古通今,尽管学术界褒贬不一,但他在普及中国传统文化、使深奥的古籍通俗化、使专门的学术大众化方面,确实做出了成功的探索[17]。
总之,对南怀瑾的著述,学界的声音还是肯定者占据优势。
2.指出南怀瑾著作中的“硬伤”
学者们指出南怀瑾著作的“硬伤”,主要在于解读方法和知识的错谬两个方面。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著名学者张中行先生就撰文指出南怀瑾著作的问题。张先生认为,南怀瑾的《论语别裁》意见却还是五四前后极少数人圣道天经地义、反对打倒孔家店那一路,讲《论语》不能不牵涉到古事,专说小范围的典籍,南怀瑾的看法,都是《古史辨》以前,流行的信而好古那一路。借用桐城派的术语,是只要义理、辞章而不要考据[18]。张荣华也认为,南怀瑾提出,秦汉后道家一直“隐伏于幕后”,充扮“幕后之学”和“历史文化的导演”,《论语》二十篇的编排都是首尾呼应等结论,论据的分量不足,有些地方以老解孔,有些地方近乎“戏说”,只能“姑妄听之”,他最终是站在佛教的基本立场上研习、咏味或阐论儒道两家学说、义理[19]。李健胜认为,《论语别裁》中,南怀瑾释读的前提是使孔子语录合理化,他以上下文相连贯的释读办法,试图消解孔子语录中存在的惊论或不合理的成分,这样的阐释目的与现代学术意义上的阐释目标显然不相吻合,有一定的随意性,且他有时是曲意引征古史的;他对孔子语录进行了道家化、佛学化的阐释,诠释方法存在着不合理、不严谨的缺陷与不足;他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和对东西文化之间差异性的看法也过于偏颇[20]。邵盈午列举了《历史的经验》和《论语别裁》中多个“确实存在”“有待商榷的地方”和“令人遗憾的‘硬伤’”,认为南怀瑾先生的古文今译,没有“以古人之心为心”,“错逞私智望文生义以至‘六经注我’之处,颇不乏见”[21]。
如果上述批评只是不同方法论之间的选择和争议,那么下面这些关涉的就是知识性问题。如张中行先生指出《论语别裁》存在的错误:一是历史知识错误,如把小戴《礼记》说成是孔子所编。二是对《论语》原文的有些解释“不管语文规律,自己高兴怎么讲就怎么讲”。如讲《学而》篇“无友不如己者”时,将“无”解释为“没有”;讲《学而》篇“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竟解“在”为“在面前”,“没”解“在背后”,“志”为“言行一致”;讲《八侑》篇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把通“无”的“亡”读为“亡国”的“亡”[18]83-85。朱瑞新也指出,《论语别裁》在讲解《雍也》篇时竟把吴起也当作荀子的学生[22]。
3.否定其著作的价值
由于南怀瑾著作的这些“硬伤”,有的学者对其持全盘否定态度。张中行先生说:“至于我,算作杞人忧天也罢,顽固守旧也罢,总不愿意在有生之年,听见下一代,由于读了这‘妙趣横生’的著作,竟至发出‘不如诸夏之亡(wáng)也’的书声。”[18]86牛泽群认为,南怀瑾的《论语别裁》,“迂阔、陈腐、谬误、悖理,一应具在”“毫无明辨、透见、新获不必多怪,但新添的唬人的玄说、夸诞,以及隐约的神秘,则呕人”“更像是以《论语》强为引子的蹩脚的海聊神侃大杂烩”。它的畅销,除“包装炒作的成功外,足见中国大众文化的落后、辨别力的低下,以及青年的易被欺惑”[23]。他不但全盘否定南怀瑾《论语别裁》的价值,且把它的畅销归因于包装炒作及受众文化层次问题。对此,北京大学李零教授表示赞同[24]。
方舟子列举了南怀瑾《论语别裁》《南怀谨谈历史与人生》《历史的经验》等著作中存在的一些“中国历史常识错误”后,评论道:“对这位喜欢信口开河的‘国学大师’的大部头著作,我也就没有阅读的兴趣。《论语别裁》据说是当代讲解《论语》的名著,但我只读了这一章,就知道这位‘国学大师’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什么意思也没搞明白。”[25]深圳大学文学院徐晋如认为,“南怀瑾的书,错谬荒悖满篇,真称得上是‘满纸荒唐言’”“毫无价值”,根本不值得一读;南怀瑾本人,“文言阅读能力连现在的初中生水平都不如”“尊南怀瑾为南师的必系文盲”[26]。
当然,这种全盘否定南怀瑾著作价值的观点,在学术界并不占主流。
三、对南怀瑾其人的评价定位
观其书,想其人。在对“南怀瑾现象”的成因分析及著述争论中,自然会涉及对南怀瑾其人的评价和历史定位问题。而这同样不乏不同意见。
对南怀瑾其人,无论学界还是民间对他毁誉皆有。史飞翔对之总结得较全:“他集教授、居士、护法,宗教家、哲学家、杂家于一身,被人赞之为‘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有人称他是佛学大师、禅宗大师、密宗大师、易学大师、国学大师;有人称他是当代道家、现代隐士、‘通天教主’;也有人称他是‘高明术士’‘江湖骗子’。”[27]
不过,总的说来,学界持高度赞扬、崇敬或全盘否定两极观点的学者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学者所持的观点都较为中正。学界通常称其为“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15]65,“当代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28],“国际知名的文化学者”[29],或直接称“南怀瑾先生”。
对他的学识,学术界基本还是肯定的,如前文所举,姜义华认为南怀瑾先生有“博大精深的学术功底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各方面的高深造诣”;曹晓虎认为南怀瑾“广泛阅读传统文化元典,有自己的学术创见”“修养扎实,境界高深”;徐祝林、徐徐两位学者认为“南老的学问博古通今”,等等。
学界肯定南怀瑾在传播传统文化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普遍认为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做学术研究的学者。正如复旦大学王雷泉教授说:“南怀瑾先生的学问规模和抱负,很难用通常的学术尺度来格量。”[30]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这样评价南怀瑾:“他似乎从来也不是一个学院中专门研究一个学科的学者,而是一个穿行于政商两界,深入到华人社会的多方面的重要的角色,也是媒体和公众所需要的焦点人物。……他最重要的贡献却是始终以儒释道三家的阐释者的形象赋予了中国传统的价值一种现世的生活意义。”[1]文化谭、薛仁明两位学者认为:“南怀瑾读书极多极广,却绝非一般所说的学者。他没有学问的包袱,也不受学问所累。”[31]既肯定南怀瑾的学识、贡献,又看到了他的不同之处,理性而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