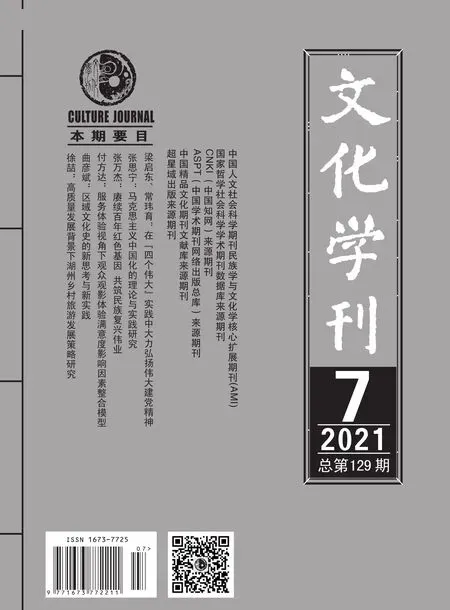试论王门“四句教”的实用价值
梁博瀚
王门“四句教”是明代思想家王守仁之“心学”的核心要义。这四句话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1]王守仁在天泉桥上将这四句话传于学生王畿和钱德洪,史称“天泉证道”。一种哲学思想,其根本作用便在于指导世人更好地生活,成为更完善的自己。王门“四句教”作为王门心学的核心,其根本价值也应该在实用层面。笔者认为既然是研究中国古代儒家的哲学思想,那么实用价值的探讨理应仍在儒家学说的范围之内。因此本文中的实用价值探讨主要围绕叔孙豹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而展开。下面,文章将首先对王门“四句教”的内容进行解析,然后按照“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总结其实用价值。
一、内容分析
王门“四句教”是在解释善、恶、心、意、良知和格物之间的关系的。我们首先来看“心”和善恶之间的关系。“无善无恶是心之体”强调的是“心”这个本体本身是超越善恶的。心在中国古代的哲学范畴中并不指心脏这一器官,而将之看作是“本体”。 “心只是万事万物的能照,如同镜子一般,以其能照,感通万物”[2]。这与禅宗所谓“心如明镜台”有相契合之处。王守仁强调“心即理”,把“心”当作万事万物的根本。而“心”是无善无恶的,这就说明了如果“心”没有被外物遮蔽,那么从“心”出发,便可以真切地感受和把握万事万物,所行之事就会合乎物理。而之所以人行事有善恶,不能准确地认识客观世界,就源于“意”。于是就引出了第二句话——“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意”是“心”具体化的表现形式。王守仁强调“意”是有善恶的,那么既然“意”源于“心”,“心”无善恶,“意”又怎么会有善恶呢?于是有很多人对这句话产生了质疑,其中就包括王守仁的嫡传弟子王畿。他认为“心”无善恶,“意”也无善恶;如果“意”有善恶,则“心”也有善恶。而同与他一道在天泉桥受教的钱德洪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心”和“意”之所以善恶不同,关键就在于“意”受到了“习心”的影响。“习心”是由宋代理学家们提出的概念,指的是经过耳目等感官而获取的意念或者说认识。简言之,“意”之所以有善,是因为人有“良知”,它引导人们向善;而“意”之所以有恶,是因为主观认识蒙蔽了“心”这个澄明的本体。于是从“意”又引出了下一句——“知善知恶是良知”。
吕思勉先生曾言:“良知之说,以一念之灵明为主。凡人种种皆可掩饰,惟此一念之灵明,绝难自欺。”[3]由此可见,“良知”其实就是一种主观上对物理的把握,而这种把握是发自于“心”的。它能应节目之变,随时随地引导人们向善[4]。这种“良知”源自先天,与生俱来。王守仁认为这个“良知”是具有能动性的,它可以分辨善恶而引导人向善。所以他才特别强调“致良知”。王守仁在《答顾东桥书》中言道:“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也。”[5]正因为“良知”能分辨善恶,引人向善,所以王守仁才教导我们要把握“良知”,以“良知”作为判断万事万物的标准,并且要做到“知行合一”。“良知”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如何“致良知”呢?这就引出了最后一句话——“为善去恶是格物”。
“格物”就是通过致良知的方式去掉对“心”这个本体的遮蔽。“为善”即是跟随“良知”而行事,“去恶”则是“格物”的主要工作。王之“格物”与朱子不同。朱子之“格物”是“即物穷理”的意思。而王守仁之“格物”,其“格”是“正”的意思,“正”的对象是恶的意念和行为,要求反求诸己,克服邪念,扫除“心”之遮蔽。
综上所述,王门“四句教”是对于传统儒家思想和心学思想的一种融合,其根本目的在于修身以成圣贤。《大学》中提出了“修身为本”的概念,并且强调想要“修身”需要“正心”“诚意”“致知”“格物”。而王门“四句教”正是解释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的。这四句话其实是一个循环。第一句话强调的“心”是本体,是澄明的,高于善恶的,所以要“正心”;第二句话强调“意”有善恶,根据“意”来行事,就必须“诚意”;第三句话强调“良知”是能识别善恶,引人向善,并具有能动性的意识,所以要“致良知”,即“致知”;最后,“致良知”的方式就是“为善去恶”,这种方法和过程就是“格物”。而“格物”是为了“正心”。于是从第一句话出发到最后一句为止,形成了“正心”——“诚意”——“致知”——“格物”——“正心”的循环。而这个循环的中心就是“身修”。
二、实用价值
接下来,将进一步探讨王门“四句教”的实用价值。正如我们前文所说,本章所采用的实用价值衡量标准,是按照传统儒家的“三不朽”的目标来划定的。下面我们将分别从“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对王门“四句教”的实用价值进行分析。
(一)立德
每个人都会有私欲,这是一种生物本能。在人类社会之中,一个人私欲的满足很有可能会对公众的利益造成损害。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在道德规范之内行事,我们的社会才能够按照其秩序平稳地运行。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呢?王门“四句教”给我们带来了启迪。
按照王门“四句教”的说法,人的良知能够分辨善恶,引人向善。之所以我们在生活中或多或少的做一些“恶事”,是因为我们的私欲遮蔽了我们的本心。要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就要遵循良知的指引,做到“知行合一”。私欲遮蔽了人们的良知,使人们“心安理得”地去做那些不道德的事情,而良知终究会在某一个时刻出来引人向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在时隔多年后对自己当初所做的“恶事”自责不已。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让良知始终保持在私欲之上,实时提醒自己要遵循良知的指引。然而私欲的力量是强大的,如果我们只是在心中了解何为善恶,而不去施行,那么私欲将会很快遮蔽良知。这个时候,就需要做到“知行合一”。所谓“知行合一”就是心中所想与实际所为合为一物。比如我们对父母的孝,在脑中有孝的意识,这便是“知”;而有孝的意识,在实际行动中有所施行,这便是“行”。“知行合一”就是心中知道对父母要孝顺,在行为上也要做孝顺之事。一事“知行合一”,事事皆“知行合一”,我们就可以战胜私欲,提升自身的道德水平,真正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
(二)立功
一个人若想要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展自己的事业,达成一定成就,必定要做到心无旁骛,一心为业。一位教师想要在杏坛取得成功,势必要真心为学生,认真备课、讲课;一位律师想要在法律界取得成功,必定要恪守道德与法律,诚心地帮助每一位委托人;一位商人想要在商界做得风生水起,必定要诚心敬意,童叟无欺……正心、诚意地对待自己的事业,这是立功之本。
王门“四句教”启示我们,要做到正心和诚意,就要进行格物。人们在自己的事业中奋斗,所遇困难何止千百,所经诱惑有如恒河沙数。这些外界的干扰会使得人们很难坚守良知,于是我们看见一个个的失败者心不正、意不诚,却在抱怨着命运的不公。王门格物的方法,与朱子的“即物穷理”不同,其核心在于内省。“静坐思虑”和“省察克治”就是内省的两种方法。所谓“静坐思虑”与佛家的禅坐和道家的吐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能帮助人静下心来,排除杂念,以把握内心深处的“理”。如果说“静坐思虑”尚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那么“省察克治”则是时时刻刻都可以做的功夫。“省察”就是要不断动用“元认知”系统进行自我监控;“克治”则是克服自己的“恶”的念头,改正身上的缺点。古今成大事者,虽不尽知王门心学,但其所作所为无不印证王门心学之说,无不践行着“格物”的功夫。想要达成自己在事业上的目标,取得一定成就,“格物”是基础。而“格物”的目的是能够正心、诚意地对待自己的事业。
(三)立言
按照王门心学的观点,“理”在心中,只要能够把握心中的“理”,则人人皆可以为圣贤。圣贤可以“立言”,普通人自然也可以。所谓“立言”,并不是一定要自成一派,万世不朽,也不是要普度众生,总结永恒的真理。“立言”于我们而言,就是将自己对“理”的把握,将自己格物以致良知的方式和经验记录下来,留与他人。以往儒家的士大夫们认为“立言”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在传统思想中总将其与著书立说相联系。此外,只有圣贤、大家或某一领域的代表人物才有资格“立言”,这是历朝历代知识分子的普遍思想。于是“立言”似乎成为了一小部分精英分子的专利。而王门心学告诉我们只要能“致良知”,只要能“知行合一”,善恶自明,本心自足,万物之理皆在心中,虽是凡夫俗子,亦可立言。事实上,在任何领域,有经验、有智慧的人都可以将自己的心得传与他人。立言并不是一种权利,而更多的像是一种责任。前人将经验留与后人,这是一种传承。
王门“四句教”为我们解释了“心”“意”“良知”“格物”与善恶之间的关系。它充分肯定了个体的地位,强调“知行合一”,有利于个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后世带来深远影响。它启示我们要跟随良知的指引,用“知行合一”的方式不断践行良好的道德规范,从而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它指引我们以内省的方式“格物”以“致良知”,达到正心、诚意地对待自己的事业,不断奋进,取得成就;它告诉我们普通人亦可将自己的智慧和经验以“立言”的方式传承下去,为个体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