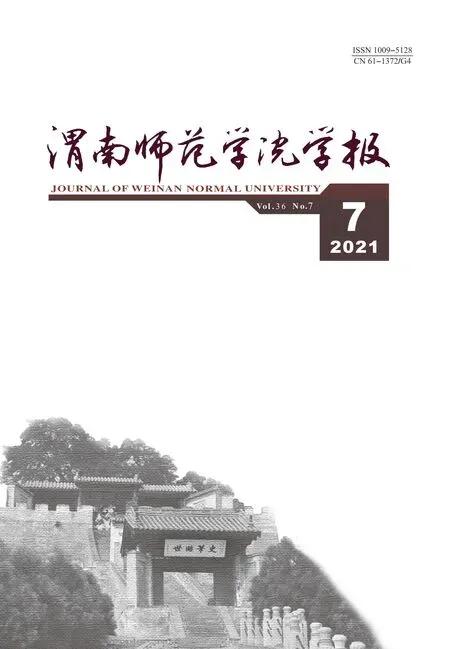带不走的家乡与青瓦
——彭家河乡土散文集《瓦下听风》的创作特色
张叹凤,曹雪萌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成都 610000)
《瓦下听风》是四川青年作家彭家河近年创作的散文作品结集,曾入选中国作家协会2013年度重点扶持项目,2017年9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品富有川北地域文化特色,乡土气息浓郁,行文清新自然,获得第九届四川文学奖散文奖项。作为“70后”作家,彭家河创作主要撷取家乡题材,书写生命中最深刻的体验与记忆。如《捕风者》《草木故园》《远去的乡村》《锈》《瓦下听风》等多篇散文,结集前后即入选国内多个省市中学语文阅读教辅范文,并作为试题附文分析(1)如《捕风者》被选作2016年镇江市中考语文试题;《草木故园》被选作2015年江西省语文中考模拟试题、2015福建高职单招语文试卷作文试题;《远去的乡村》被选作成都市金牛区2014—2015年度下学期高一期末调研试题;《锈》被选作上海市五校2015届高三第一学期联合教学质量调研语文试卷;《米》入选2019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模拟语文试题等。,由此可见受众较广,影响较大,文本的文化与文学内涵、张力不言而喻。
彭家河在四川北部农村、乡镇、县城工作多年,后调到省会成都,其丰富的生活工作经历为他的创作打下了坚实丰厚的基础。川北广袤乡村的青砖黑瓦与田野清风山峦矗立并活跃在他的记忆中,风声贯耳,经久不息。时代的飓风把现代化的气息吹向相对闭塞的大川北农村,令乡村青年走出家园,奋力拼搏,以融入城市发展空间,却又不免时时回望家园故土,拥抱亲情。砖瓦,在彭家河笔下是静默坚守的力量象征,亦是乡村最为具象的物质外貌与生态写照,如同川北乡村精神的图腾。彭家河在城市与乡村间奔走,青砖黑瓦似乎总是第一个或最后一个迎送游子亲人,也是第一道眏入眼帘的风景。连绵不绝的砖瓦连接着巴蜀、陕甘交界地,连接着人与自然、城乡关系,乡风穿越瓦脊,如同时代交响曲,既述说着过去,也述说着现在与未来。
作者将驻守并见证乡村变迁的风物作为主要描绘对象,于城乡之间探寻、思考社会发展进步的宏大主题,通过少年成长记忆、乡村民风民俗描绘以及对当下现代化的思考,对读城乡文明,从而正视“他者”与“自我”,着力调节两者之间原本比较对立冲突与异质的倾向,寻求城乡文明自然的融合交汇,发幽烛微,以“记得住乡愁”的创作动力,散文质地坚韧,格调高昂,意境幽远。由以下几个方面呈现创作特色风貌。
一、在乡土记忆中转动文学的世界
彭家河写道:“每一个写作者,其实都是在反复书写自己最熟悉的人和物。在我的印象中,川北风物为外界所知的还不够多、不够广,我愿意努力把川北大地上的故事写给人们看,让更多人知道。”[1]虽然是“反复书写”,但建立在真实的生命体验与不断提升自己认知的基础上的文学,总能“日新日日新”。五四新文学的乡土文学具有世界新知的大背景,是其有别于古代田园山水诗的根本区别。彭家河生于乡村,求学于城市,是具有城乡双重身份的知识分子,他将川北大地源源不断的生命气息,传导于行文中,并能推陈出新。
彭家河家乡处在四川盆地北部秦巴山区,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汇与移民群集的场域,故而民风古朴,勤劳崇文,因处于重山之中,世代因袭相对闭塞边缘化,民风持重的同时,观念不免亦趋于守旧固化。有学者曾经指出:“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个自然条件比较封闭与文化传统比较保守的特定区域,都容易形成特色非常鲜明的文学。”[3]36彭家河多以“苦寒”二字概括自己的童年生活,这是真实的写照,他从不掩饰过去的痛苦甚至于失望,在表现乡土生活方面,不肯蹈于浮泛抒情,更没有“风花雪月”的浅泛粉饰,他总是真切自然地描绘过往所经历或接受的一切,对乡人改变乡村落后面貌的坎坷历程,尤其着力,以至于形容毕现:
在碾滚和磨扇上,都有一个粗实的木架,牢牢固定在石碾滚和磨扇上,一端插入根木杆,用绳子拴在牛肩的木枷上。只要吆喝一声“走”,蒙着眼壳的牛便自觉地一圈一圈像钟一样,拖动着秒针一样的木棒和沉重的碾子或者磨盘转动,碾滚或磨盘下的谷子麦子转眼变得粉碎。现在想来,乡下的生命就是这样在岁月一轮一轮的重压下变成了尘埃。[2]138
深情中有热泪,温故中有立新,正如鲁迅当年论及乡土文学时所指出:“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也更能自慰的……”[4]125几十年来的城乡巨变,彭家河孩提时代的际遇景象多已不复存在,但他娓娓道来仍旧感味厚重,温暖动人。即如前人论述乡土文学:“人总是‘地之子’……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这不限于描写地方生活的‘乡土艺术’,一切的文艺都是如此。”[5]15-16
豌豆粒大的一点灯火,风一吹就灭了。把亮从这间屋拿到那间屋,还得一手拿亮,一手半围着那簇火苗背风慢行。乡村的节奏,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控制了下来。所以,从乡间油灯下熏出来的人,极少会性格火暴急功近利,总是那么恬淡镇静。[2]79
作者将大笔写意的渲染与细致入微的白描结合,形成诗意表现,表现出川北乡土记忆的独特艺术魅力。行文是写生,也是抒情,更是关系族群力量的生态怀旧。作者没有拾人牙慧,刻画往往来自生活积淀与文学领悟,他力图消解固有的浅泛的诗意模式,深深陶醉却又清醒地审视自己的心灵记忆。他给予读者的,不是浅泛的美化或者丑化,也不是夸大其词、耸人听闻的曲折惊险,而是在平实中传递的那一份温暖的乡情和挥之不去的乡愁。追寻川北独具的历史文化特色与现实路径发展,是作者这类散文的书写意图与基调。他把饱含悲欢离合的童年记忆与锲而不舍的多元文化地理、精神家园追寻相结合,互为表里,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中绘事传神,这是《瓦下听风》有别于其他区域乡土散文的一个突出特点。
评论家谢有顺曾说:“在中国,多数作家的童年都生活在乡村,这本来是一段绚丽的记忆,可以为作家提供无穷的素材,也可以为作家敞开观察中国的独特视角——毕竟,真正的中国,总是更接近乡村的,但是,现在的许多青年作家,几乎都背叛了自己的童年记忆、乡村经验,没有几个人再愿意诚实地面对自己所真正经验过的乡村中国。”[6]94坦然,回忆,讲述,其实都是需要勇气的。离开故乡的作家大多不愿去直面乡村过往或现实,或将故乡风土景物加以浅泛的溢美,往往对苦难记忆刻意遗忘或淡化,这无疑丧失了质朴的生活体验。而狭隘的视野、浅尝辄止的描写不免会给作品蒙上光晕雾罩,无法带领读者抵达作者真实的乡村生活经验深度。彭家河则坦言:“我的出生地与我的生活地把我的精神世界分成了两块,无论在哪里,出生地那一块总是厚实地铺在最底下。”[2]129在书写乡村美好时光的同时,不讳言曾经的艰苦生活际遇。如《旧石器》一文,描写“亲密”的小石磨:
我家灶屋就有一扇小幺磨,我们小时候,每天放学回来,都要一边烧锅煮饭一边使劲推动那扇沉重的磨扇,许多时候都是磨干玉米粒。小孩子想偷工减料,大把大把的玉米粒往磨孔里塞,只听得磨盘间啪啪直响,磨盘转眼就轻松了,可是落在磨槽里的全是囫囵的玉米瓣,母亲检验不合格,还得撮上来重新磨一遍,这下就重多了。[2]49
叙事,咏物,于真实的生活记忆表现文学描写与再现生活的力量。“石磨”,显然也是乡愁的具象与化身。彭家河散文多在朴实的“家”中探寻人间力量,驰骋想象,川北乡村生活风物,如红苕、大蒜、堰塘、油灯等,都是他对家乡生活的挂牵,也是城市生活压抑最为畅达的释放,如《方言》趣味十足,《染房头》记录历史变迁,《草木故园》讲述村民锯木的痛楚,《流转》描写农民收麦时的畅快,《米》记述男女老少的插秧“舞蹈”,《泥沙时代》承载筑房烧瓦的泥土气息……《染房头》组章中,作者并未铺排四合院的布局、摆设,而是着重介绍染房头“院子的脸”——楼的门等,如被川北人唤作“通子”的青石条,属于川北独特的建材,宽长的通道更有别“胡同儿”,是作为移民后代的川人的祖先崇拜与家乡符号。“燕儿窝,燕儿岩,燕儿的婆娘穿红鞋。会吃烟,会打牌,半夜半夜不回来”[2]136-137,类似民歌童谣,川北农村的生活情调跃然纸面,如同绘出。巴、蜀、秦三地交汇区人民泼辣、爽直、勇敢、诙谐、善良的特质显而易见。作者讲述捉“地牯牛”、吆牛磨面、寻鸡捣蛋等童年乐事,记录因石板松动而满身泥浆、因跟着牛屁股转圈而眩晕呕吐等儿时囧事,亦无不形象生动、妙趣横生。
“地方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系物桩,拴住的是这个地区的人与时间连续体之间的共有的经历。随着时间的堆积,空间成了地区,它们有着过去和将来,把人们捆在它的周围。”[7]138如同老舍之于北京,沈从文之于湘西,沙汀之于绵阳安县,彭家河于川北风土亦十分上心,这正是他创作心理学与美学追求的突出表现。能在精短的篇幅行文中将古老的文明与鲜活的现实生活相互交织,于朴拙的文化场景中寄寓深情,于“乡村哲学”中审视变与不变的心灵哲学。
“中外文学的历史证明,一切伟大作家的创作都是以他们生活的地域(乡土)作为‘支点’,转动着自己的文学世界。”[8]44地理环境、乡土记忆深刻影响了彭家河的创作风格与写作路径,充盈了作者的生活体验,川北地方经验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于闭塞的巴蜀场域限制中,扩展天地,将熟悉的乡村角落写得淋漓尽致、以小见大。文笔的野马,因为有了川北乡村的“系物桩”,从而“形散神聚”。
二、让乡村的美好升华于精神气质中
乡土的定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外延扩大,过去概指乡间农村,而现代以来则包括所在的城镇以及城市。乡土散文也不单指农村故事,彭家河的散文在描绘农村图景的同时,也着力表现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乡一体化社会转型这一时代变革,以求突围乡村的“他者”旧我,从而切身感受城乡巨变与一体融合。美国学者迈克·克朗曾在《文化地理学》作如下表述:空间对于定义“其他”群体起着关键性作用。在被称作“他者化”的过程中,“自我”和“他者”的特性以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建立了起来。“前者围绕一个共同特征把自己定义为‘其中之一’,接着,又把其他非成员定义为剩余者,即‘不在其中’。很显然,某一群体的选择性特性并不被另一群体所具备,而且存在着这样的倾向,即选择性特性总是指那些好的特征。所以,凡是被定义为其中之一的群体都在价值上得到了积极的肯定。”[7]78历史上的巴蜀乡土社会虽然多为移民与其后代构建,流动性相对来说比较强,但农业形态比较单一,主要还是靠自给自足、耕读传家,村民安土重迁、传宗接代的意识相对牢固,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即“瓦下听风”,变革的风气还是处于世间的后方。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当代社会的大发展,城市中的现代因素与创新活力使偏安一隅的乡村逐渐沦为“他者”,彭家河自述“村庄也随之半个或整个地搬进城,镶嵌在城市与郊区的夹缝里”[2]109。不仅“井”“牛”“麦”“瓦”逐渐在乡村中被边缘化,作家自己也不免被城市之风裹挟,在现代化浪潮中沉浮闯荡,以至陷入城乡间的罅隙中,成为“两栖动物”。《出生地》一文,作者从祖辈显赫一时又衰败的经验教训中,阐明出走乡村的必要性;在父亲对其进城的殷切期望中,看到了出走乡村的可能性;在乡民破茧成蝶、改变命运的渴望中,看到了出走乡村的迫切性。然而,当远离乡村、抛离故土之时,城市的压力竞争与蜗居的艰辛扑面而来,又使作者不免反思出走乡村的合法性与必要性。作者考取师范学校摆脱家乡局限,由乡村到县城教书,再于省城工作、写作,自身经历便是一个乡村成长——出离家乡——蜗居城市——立足打拼——回望、寻找家乡的心路历程,可以说这本散文集如同一部个人的“进城打工史”或者励志的自传体。基于亲身经历曲折坎坷,作者拥有作为“他者”的发言权。就乡村实地风物而言,离乡赴城的村民是乡村的他者,就城市生活而言,进城的村民仍处在边缘地带,仍是城市中的乡下人。这一现象在“五四”时代即出现,如沈从文、废名、艾芜等自称“乡下人”的写作。
作者彭家河清楚地看到,祖辈的乡土经验并不完全适用于当下发展语境,城市化的过程是世界化、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作者心中虽不免时有顾虑以及忧虑,却也能够坦然接纳这一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与结果。因此,不同于梭罗式散文家对神圣乡野的过度追寻,彭家河汇聚更多笔墨探讨出走乡村的“行者”处境,探求突围城乡困境的路径,他更愿将城市发展的隐忧、乡村隐退的阵痛、乡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与喜悦、身处城乡罅隙之间的内心冲突、压抑均掩映于行文之中,从而正视并劝慰作为“他者”的同人,历史辩证地看待这一现代进程,以亲密的边缘人角色反观城乡的双面镜像,追寻“他者”的生存突围,为现实变革进步做一名见证者、参与者。
彭家河将亲身经历的生活围城娓娓道来,如农民进驻城市时的游移与挣扎,于瓦下讲述,津津有味,却让人掩卷深思。在《流转》《麦子的流年》等文中记录了打工者进城与否的犹疑矛盾。因城市化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农村耕地,村民淳朴勤恳劳作,却无从摆脱贫瘠的生存困境。城市膨胀着任性的“风”,携来新鲜的事物、丰厚的报酬以及城市的身份、名望,无从耕种的剩余劳动力跟随打工者汇入城市洪流,将城市作为改善家庭困境的跳板,跻身充满汗水与委屈的“天堂”的尴尬。他们既葆有对乡村的依恋回顾,又无法割舍城市改革的巨大红利,从而农忙时下地、农闲时进城,成为乡村退进有据的谋略者、实施者:
这些怀揣丰富耕种经验的农民工,义无反顾地来到这个小城,却用最原始的方式挣钱养家。虽然同是汗流浃背,但是与在乡下相比,这汗水的价格的确有天壤之别。估计在城里守株待兔坐上几个月,就抵得上乡下起早摸黑一年半载,谁还愿意那样安贫乐道呢?即使是想在乡下过清净日子,可是男婚女嫁,生疮害病,那点微薄的收入又如何能够糊口,所以,进城也就迫不得已。[2]206-207
这是写实。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城市的发展使得乡土气息四布,但久之也未免消泯,作者在散文中提及乡村沦陷乃至被遗忘的隐痛,颇有所感:
村里的族规,村训,都没入荒草。村口的学堂早已成为空房,村外的肥田沃土,都成为杂草的天堂。乡村没有了人声,没有了烟火,丰收的喜悦和年关的喧闹都一片片地从往昔的岁月枝头落下,如今的乡村只剩光秃秃的两根枝丫,一根朝这,一根朝那,这一根叫荒芜,那一根也叫荒芜。[2]14
农具日渐锈蚀(《锈》),现钞取代“待嫁”的麦苗(《麦子的流年》),电灯让乡村再无“秘密”,石器独守着空房(《旧石器》),河沙被日夜掏空(《泥沙时代》),只有杂木草木蔓延不移……作者的笔下交织着复杂情结,虽无力阻止城市之风的强劲席卷,但面对乡村隐退及至消亡的阵痛,形诸笔端,时或不能自已。
彭家河是乡民中的一员,也是一名亲历者、观察者和沉思者,他在失望中更持有希望。他深知乡村赋予农民的个性特征和农事习俗无法消解殆尽,它们总会在方言、行为、人际关系乃至精神状态中自然表露,乡音、家谱、字辈、童年经历,均构成农村人的生命元素与符号,使他们无论到何处,都在心里带着家乡的印记而无法立即成为一名异化者,因为乡村不仅是摇篮也是图腾,是生命的印章。作者相信,乡村文化的根基沉淀在泥土深处,并非完全被抛除。工业化、城市化掳走的只是村民的“壳”,壳内包裹的乡村之魂留存于城乡社会乃至于季风中。作者为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感到欣喜与振奋,看到时代的惠利落实到各处,川北农村城市化的发展一再证明现代文明的普惠性、必要性。过去持久难消的贫穷,因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而逐渐改变,乡村孩童的笑靥、孤寡老人的归宿、安居工程的矗立(《锈》《泥沙时代》),机械化科学化农村生产的愉悦惊奇(《麦子的流年》),电气、信息通讯时代的迅猛发展(《亮》)等,作者于缅怀传统的同时,也诚实地书写着时代变革的鼓舞与希冀。
彭家河的散文是乡土抒情,也是我国改革开放探索之路的真实记录与见证。他相信由边缘的“他者”建构自我、大我之时,时代会给予奋斗者以新的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为积极的生活态度。作者在进入城市生活后,刊于《人民日报》的散文《走进成都》,即直书心声:“每居一地,我们都要改变寄居心态,积极融入参与,不做旁观者,而是做尽心尽力的建设者。”[9]
彭家河的散文是城乡结合的风景线,是新时代乡土探索与改革的写生与见证。
三、“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0]377自然包括各类生命形态与美好、平衡、合理的事物,彭家河的系列散文显然意识到现代化的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繁荣共生的重要性,这承有“顺应”与“保护”之道,珍视“我们”的生命,更应当珍视自然,珍视城乡各类美好生命形态。他散文中多选取乡村中稳定、和谐且坚定的风物形态作为咏物叙事抒写的对象,借助自然生命的流转记录人世变迁与感情寄托,在绿水青山的自然怀抱中抚摸生命轨迹,从而更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作者将草木、典故、轶闻趣事等川北乡村风物、文化一一解码,摄取隐秘而惟妙惟肖的细节情景,以诗意的文字传递给读者,大到家族谱系、族群融合迁徙,小到巷中石板小径、油灯灶台,皆以心刻录,彰显乡村的灵魂。“美”不再局限于作者的体验,更张弛于作者的想象中,即使渺小而鲜活的生命体也成为作者解码的对象,如铁具上不起眼的锈斑(《锈》)、被牛蹄踩软的泥膏(《泥沙时代》)、濒死前“波哦”的夜鸟声响(《隐秘的溃退》),均显于日常生活,他人易于忽略,而作者则特别用心记录,甚至用身心去拥抱,诗情画意从熟悉而陌生的乡村故事中清新流淌、婉转自然。
例如麦子,“她”摇身变作刚出阁的闺秀,以主角身份参与农人极为庄重的“婚礼”:
麦子,是乡下最顾家的媳妇。
农历十月,谷子都住进了仓,踏实的农民们便早早忙碌起麦子的婚礼了。农家计算好的那些碳铵、尿素是麦子最好的嫁妆。在麦子离开家的前夜,老农便会点起烟锅,叨念着哪块地肥,哪块地薄,分摊起麦子的陪嫁。
在丰盛的早餐过后,一家老小便扛上犁耙、炊具,连同耕地的牛、看家的狗、一路浩浩荡荡,送小麦出门。小麦要远嫁到村外的山上山下,新犁过的田垄散发着淳朴的芳香,一粒粒饱满的小麦就是那片整侍妥帖的土地上的新媳妇了。远离乡村,农户在田野垒起锅灶,露天生火做饭,袅娜的炊烟是麦子最后华丽的转身。这顿午餐,是为麦子摆设的婚宴。[2]107
川北农民也把米食视作最高崇敬的“天”:
到了米生儿育女的时候,谷便进入温室催芽或者喝饱水分直接到春寒料峭的冬水田里开始安营扎寨,这时,家家户户的男女老少都少不得挽起裤腿光着脚板下田,把赤裸的腿脚扎进冰冷的泥水,咬着牙躬着腰把嫩黄的秧苗一行一行小心安放在水田里划分出来的一条条泥箱上,腰不能弯得太久,还得不时的鞠躬,如同在一个庄严的仪式上不停地膜拜,这个生命的典礼,叫“安秧“或”按秧”。[2]55
庄稼、风物、生产无不是乡村的魂魄,对米麦的呵护与怜爱、崇敬,是村民情感最朴实的核心,作者描写自然生态如同描写自己的同胞骨肉,极具形状自然,倾尽感情。他以谦逊甚至谦卑的态度将自然生命物象置于生活高处,以“血浓于水”的亲切描述构成“同乡”关系,如同西方哲学家形容文学为“还乡的脚步”。在颇具人性的对话中,物我一体,乡风扑面,乡情暖心,从而透露出大千世界的伟大能量。由具象化为形而上的思索,无疑寄予着作者更多的生活哲学与生命思考。作者带不走的家乡,在他行文中无时不是零距离掇拾,甚至成为他的精神力量,不时“呼啸”与“低吟”。
“生态美学对人类生态系统的考察,是以人的生命存在为前提的,以各种生命系统的相互关联和运动为出发点。因此,人的生命观成为这一考察的理论基点。”[11]14彭家河衡量生态风物美好的标准依旧在人:麦稻有待嫁妇人的娇羞之美,石器有品格的坚不可摧,柏树有沉着质朴的本性,土地则有忠贞不渝的厚重单纯。这些风物均真实可感,是“人”的具象品格,甚至具备比凡人更美好的奉献精神。尤其是忠贞不移方面,作者似乎在续写着屈原讴歌楚巴大地的“橘颂”。显然,作者不再作为单调乡村的讲述者,而是立于生命征程与精神世界的“瓦下”,聆听生命的旋律,以表达自在的言说:
嫁过去了,小麦深入土地度起了蜜月。蜜月过后,她慢慢探出了头,害羞地出现在自己的院落,那望穿秋水的村庄便成了她的娘家。在新落户的土地上,小麦越长越滋润,腰身越来越苗条。微风过处,麦子们在田野里载歌载舞。娘家人不时过来走走,看到麦子生活幸福,也乐得吼几声山歌。
麦子守护着自己家园,默默担负着自己的责任。农夫的儿子打工去了,农夫的媳妇也打工走了,娘家的亲人基本上全到广东深圳了,只有麦子仍生活在村庄。麦子独自顶风挡雨,养家糊口,是乡下最后的村姑。在乡下,她们没有私奔,逃离这个贫困的地方;她们没有绯闻,败坏村庄的名声。纷杂尘世,麦子是乡下最忠诚的妻子,是土地最贤惠的媳妇。[2]107-108
另如《草木故园》《流转》《麦子的流年》《壳》《旧石器》《草》等作品,均“于细微处见精神”,歌咏乡土的精神与未来:
旧石器,映射着人间万相,卜筮着我们黯淡的未来……[2]53
麦子的流年,侵染着人世沧桑。[2]31
麦地的烟火,映照着千万个你我。[2]31
锈是铁唯一的癌。[2]10
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清晰可见,感情抑扬顿挫此起彼伏。作者不讳言悲剧的发生,凡生老病死、人生不测,皆有触及,但植根乡土的生命的内在韧性与能量,正是作者驱散虚无与悲观的正能量,从而也能警醒读者,珍重生命,保护乡村美好记忆,守住我们永恒的精神家园。
“天地万物已由‘宾语’变为‘主语’”[12]47,恰是驻守乡村的坚贞风物,刻录了川北大地生之坚强、新之必要。曾有学者坦言:“相对而言,散文与自然与生态的关系日渐疏离。我们越来越缺少与自然、与生态对话的散文,文字在面对自然时已经越来越缺少敏感,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不能抵达大自然的怀抱。我们的身体与语言文字长久没有阳光雨露的照射和滋润了。而所有的这些缺失,都表明人的思想、精神、胸襟、情怀、格调等都在从散文中退出,散文中已经没有了名士、绅士、隐士和叛徒。”[13]15彭家河的系列散文正好相反,他贵在乡村的力量书写,一如“瓦下听风”,他像一名麦田守望者,守卫着自己的心灵家园。
四、结语
作家彭家河不盲目追“风”,却能在“风”中坚守一名乡土作家的情怀,做一名城乡生活交融的“风语者”,让川北乡土成为他坚实的文学创作基地与创作动能,求新求变,乡土记忆与向往永远是他的精神港湾。他说:“不知道世事还会如何变幻,不知道我们还会走向何方,我相信,生养我们的那一块土地,永远会在那里等着我们。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在那里碰头!”[2]236城乡交融,根的意识,坚不可摧。如同黑格尔在18世纪形容中国为“田园共和国”,彭家河系列乡土散文的精神世界即有着无垠的长青的田园,是祖国的一方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