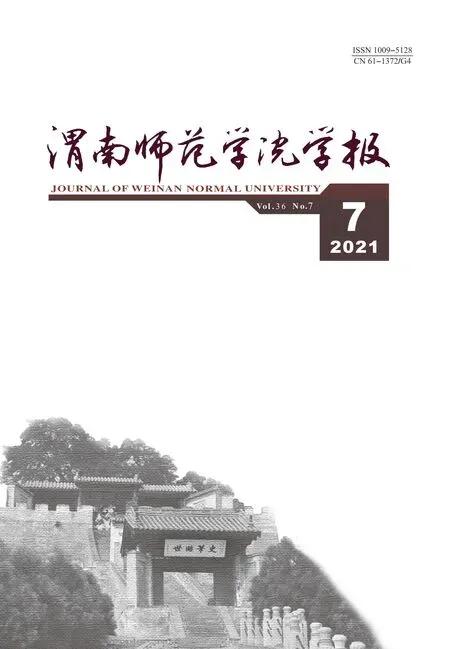《史记》校读拾遗
陈 豫 韬
(南京大学 文学院,南京 210023)
一
《史记·周本纪》:“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1]151
按:“盍往归之”之“盍”,作疑问代词“何”或疑问副词“何不”义皆不可训。《史记》中与此事相似之叙述还见于本书之《齐太公世家》与《伯夷列传》,也有“盍”字难训的问题。《齐太公世家》叙此事:“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1]1791《伯夷列传》写作:“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1]2583那么这两处文例,《伯夷列传》之“盍”不是处于人物对话中,同样不可训为“何”或“何不”。而《齐太公世家》之“盍”虽是在人物对话中,但结合上下文语境,此处是散宜生、闳夭来招揽吕尚。吕尚是意见的接受者,不能反而向提议的提出者提出相同的提议,故也不当作“何”或“何不”解。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对于此字的解释也存在很大的分歧。有衍文说,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引此段时皆去“盍”字径作“往归之”。梁玉绳《史记志疑》(以下称《志疑》)亦云:“盍字当衍。”[2]78有误字说,如日本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以下称《考证》)将“盍”改作“盖”云:“盖,各本作盍,后人依《孟子》改,今从《枫》《三》《南》本。”[3]237还有别义说,如王叔岷《史记斠证》(以下作《斠证》)云:“案盍非衍文;盍、盖古通,亦无烦改字……盍犹试也,‘盍往归之’犹云‘试往归之’,《庄子·让王篇》:‘昔周之兴,有士二人,处于孤竹,曰伯夷叔齐。二人相谓曰:吾闻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试往观焉。’”[4]119然而众说纷纭,皆非达解。如梁玉绳《志疑》以“盍”字为衍文,但岂能《本纪》《世家》《列传》三处都是衍文?泷川资言《考证》以“盍”为“盖”,以为后人所改,然“盖”“盍”本就通假。且如作“盖”,则作疑辞“大概”理解。而《周本纪》这里是陈述句,表肯定。其下文即为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武王”之记载,表明确有其事。则作“盖”与文意矛盾,亦不通。若依王叔岷先生解作“试”,其依据又仅是《庄子·让王篇》之改写。“盍”作“试”文献之中并无相关语例,故而似也缺乏说服力。
今考,前说皆误。《周本纪》《齐太公世家》《伯夷列传》三处“盍”字同义,皆应理解为“合”“一同”之义。“盍”字,古音匣纽叶部;“合”字,古音匣纽缉部。二字同属匣纽,“叶”“缉”旁转,音近通假。《尔雅·释诂上》云:“盍,合也。”又《易·豫》:“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王弼注:“盍,合也。”[5]32又《晏子春秋·外篇第八·第12章》:“公曰:‘合色寡人也?’”于省吾《双剑誃诸子新证》注曰:“合即盍之音假。”[6]96皆其例。体味此段大意,在言西伯侯姬昌之得人,士多归之。只有当“盍”通假作“合”,表示“一同”的意思时,才能同时疏通《周本纪》《齐太公世家》《伯夷列传》三处文意。
二
《史记·项羽本纪》:“少年欲立婴便为王,异军苍头特起。”[1]382
按:“少年欲立婴便为王”句,此句学者通常将“便”视为时间副词。然“便”作时间副词乃后起义,西汉司马迁时是否有此用法尚且存疑。今统计《史记》全书,用“便”字凡152例,疑似作时间副词之“便”,除此例外,唯3例:
(1)《史记·平准书》:“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鈇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便属在所县。”[1]1724(也许多学者认为,此“便”字当理解为“便利”[7]1468)
(2)《史记·东越列传》:“是时,楼船将军杨仆使使上书,愿便引兵击东越。”[1]3612
(3)《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冄、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1]3692
考以上4例(包括本例),虽作时间副词“便”可通,但将“便”字换为“使”字,亦皆得通。且4例中,《汉书》确有2例皆作“使”。如《汉书·食货志》:“使属在所县。”[8]1166《汉书·司马相如传》:“相如使略定西南夷。”[8]2581剩余2例,《汉书》亦不作“便”字,《汉书·项籍传》作“欲立婴为王”[8]1798;《汉书·闽粤传》作“愿请引兵击东粤”[8]3861,似乎过于凑巧。“使”“便”固形近易混。如《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苏代谓田轸曰:‘臣愿有谒于公,其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为福,不成亦为福。’”[1]2297而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陈轸章》作“便楚利公”[9]98。由于《史记》中“便”作时间副词的例证无一处不可作“使”字解者,故此处“便”为“使”之误字,或可聊备一说。
三
《史记·楚世家》:“张仪至秦,详醉坠车,称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仪以吾绝齐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遗北辱齐王。齐王大怒,折楚符而合于秦。”[1]2077
按:“乃使勇士宋遗北辱齐王”句。许多学者依照书面意思,将“宋遗”理解为人名。如梁玉绳《志疑》曰:“《秦策》言楚王‘使勇士往詈齐王’。《张仪传》言‘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骂齐王’。无宋遗姓名,史盖别有所据。《汉书》人表有宋遗,列第五等。”[2]1023张文虎云:“‘借宋之符’句,当有误。《史记·楚世家》作‘乃使勇士宋遗北辱齐王,折楚符而合于秦’,则是所使勇士姓宋名遗耳。”[10]522
考“宋遗”其人史无记载,《史记·张仪列传》作:“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骂齐王……”[1]2781当差近事实。然而楚之勇士北辱齐王何以要借宋之符节,楚国又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借宋国符节的呢?据记载,在楚怀王遣勇士“北辱齐王”之前,楚国实际已经做出过一系列与齐国断交的外交表示。《战国策》云:“楚王使人绝齐,使者未来,又重绝之。”[11]231《张仪列传》云:“于是遂闭关绝约于齐。”[1]2780可见,楚国出使齐国之所以要借用宋国的符节,是因楚国已经毁掉了齐国的符节。而在当时,使者行道是需要执符节为信物的。《周礼·地官·掌节》曰:“门关用符节……皆有期以反节,凡通达于天下者必有节。以传辅之。无节者,有几则不达。”[5]740所以,可知楚国向宋国所借符节,乃是宋国掌握的宋、齐之间相互通使的符节。故梁玉绳所谓:“此语可疑,骂齐何必用符。而楚自有符,亦何必借宋符乎?”[2]1251其说误。
张仪使楚,在秦惠文王十二年(前313)。这一时期宋国的君主是宋康王偃,宋国的国势很强盛,并不依赖于齐、楚两国。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君偃十一年(前318),自立为王。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1]1970那么宋国既然不是楚国的附属国,为何会把宋、齐之间交往的符节单独交给一个楚国的“勇士”,又由其独自手持宋节前往齐国“北骂齐王”呢?这显然有悖于当时的外交常理。故而,《张仪列传》中的“借宋之符”的这个“借”法,是很值得推敲的。
其实在《战国策》中,还记载了与张仪相关的另一件因为两国使节不通而借使他国的事例,可以窥见当时所谓“借符”的程序:“(张仪)乃使其舍人冯喜之楚,借使之齐。齐、楚之事已毕,因谓齐王……”[11]558在这一事例中,齐、魏交战不通使节,冯喜只有跟随楚国的使节团,等到了“齐、楚之事已毕”,才开始谈齐、魏之间的事。那么,《楚世家》中所记载楚、齐之间的使节不通,楚国借宋国的符节其情况自然也应是如此,而不会是直接把符节借给楚国的“勇士”。
那么如果“宋遗”不做人名理解,则此“遗”字作“送”义解。此句“乃使勇士宋遗北辱齐王”显然结构不完整。考牛运震《读史纠谬》云:“按楚无勇士宋遗,考之《战国策》乃云:‘遣勇士从宋遗齐王书。’则宋遗非人名也。太史公考据之学,往往疏略轻率如此。”又谓:“《史记》误撮为人名,《汉书》遂列其等于第五,真以讹传讹者也。”[12]21《史记疏证》云:“徐孚远曰:‘《战国策》曰:“遣勇士从宋遗齐王书,折券绝交。”则宋遗非人名也。’”[13]302又张照于武英殿本《史记·楚世家》所附《考证》亦云:“按《战国策》:‘遣勇士从宋遗齐王书,折券绝交。’……则宋遗非人名也。疑当作‘乃使勇士从宋遗书北辱齐王’,落‘从’字、‘书’字。”[14]考诸人所引《战国策》引文,不见于今本。今本《战国策》但作“乃使勇士往詈齐王”[11]231,然众口一词,似确有一《战国策》版本作此。若然,则《楚世家》此句当脱“从”“书”字。
四
《史记·留侯世家》:“留侯从上击代,出奇计马邑下,及立萧何相国,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1]2487
按:“出奇计马邑下”当作“出奇计下马邑”。《汉书·张良传》正作“出奇计下马邑”。裴骃《集解》引徐广说曰:“一云‘出奇计下马邑’。”[1]2487然后世学者亦有以“下马邑”为非者,如方回《续古今考》有“‘出奇计马邑下’《史记》是《汉书》非”条云:“《汉书·张良传》:‘良从上击代,出奇计下马邑。’《史记》世家作‘出奇计马邑下’。盖高帝击韩王信,张良亦在军中,出奇计于马邑之下,则不特陈平也。孟坚误会子长意,改书为下马邑,殊不然。”[15]468
今考方回《续古今考》之说颇多纰缪。所谓“盖高帝击韩王信,张良亦在军中,出奇计于马邑之下,则不特陈平也”云云,当是误记史书。高帝击韩王信于代在汉七年(前200),其事据《陈丞相世家》记载:“其明年(七年),以护军中尉从攻反者韩王信于代。卒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1]2500可见,陈平出奇计的地点是在平城白登山,其地在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而马邑则位于今山西省朔州市,二者在地理上尚有相当的距离,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据此,可知“出奇计马邑下”不可能指的是这一次事件,方回之说误甚。张良此次“出奇计下马邑”,其实应该发生在汉十一年(前196)。
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十年)八月,赵相国陈豨反代地。……九月,上自东往击之。……十一年,高祖在邯郸诛豨等未毕,豨将侯敞将万余人游行,王黄军曲逆,张春渡河击聊城。汉使将军郭蒙与齐将击,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马邑,马邑不下,即攻残之。”[1]487又《绛侯周勃世家》:“击陈豨,屠马邑。所将卒斩豨将军乘马絺。击韩信、陈豨、赵利军于楼烦,破之。”[1]2514又《韩信卢绾列传》:“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称病甚。九月,遂与王黄等反,自立为代王,劫略赵、代。……十一年冬,汉兵击斩陈豨将侯敞、王黄于曲逆下,破豨将张春于聊城,斩首万馀。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击东垣。”[1]3201-3202可见,当时陈豨自立为代王,周勃所率领的一路汉军久攻马邑不下。这是汉初征伐代地时,唯一能与张良“出奇计下马邑”相对应的历史记载。
从以上记载来看,汉十年征陈豨时,汉军应该是分为两路。一路由刘邦亲率,平定赵地。汉十一年冬时在邯郸、东垣等地平定叛乱。一路由太尉周勃率领,平定代地。汉十一年冬时在马邑一带。而张良乃是刘邦的谋臣,汉六年封功臣时刘邦称其:“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让其“自择齐三万户”。其地位尚高于周勃,不会随行在周勃军中。《留侯世家》也明白地记载的是“留侯从上击代”,则张良自是按惯例作为刘邦的重要谋士随在刘邦军中,而不是亲自领兵或跟随其他将领。所谓的“击代”,只不过是因为这次叛乱的中心人物陈豨当时自立为“代王”之故。那么既然汉十一年冬时张良在刘邦军中,就不可能是“出奇计马邑下”。况且从地理上看,邯郸位于今河北省南部,马邑位于今山西省北部。马邑至邯郸、东垣几乎上千里,张良时已多病,不必也不能亲身自往,最多只是谋划计策传示周勃而已,故当作“出奇计下马邑”。
综之,史文明载张良“从上”击代,此事细考史实,明白无误,当是“马邑”与“下”文为误倒。且据徐广之说,《史记》原有一版本作“下马邑”,则“马邑下”必是传写之误甚明。
五
《史记·淮阴侯列传》:“汉王遣张耳与韩信俱,引兵东,北击赵、代。后九月,破代兵,禽夏说阏与。”[1]3170
按:裴骃《集解》引李奇说云:“夏说,代相也。”[1]3171又《汉书·陈馀传》云:“馀为赵王弱,国初定,留傅赵王,而使夏说以相国守代。”颜师古注曰:“为代相国而居守。”[8]1839然考之《史记·曹丞相世家》则曰:“因从韩信击赵相国夏说军于邬东,大破之,斩夏说。”[1]2462夏说作“赵相国”。考之近世,则学者多以“夏说”为“代相国”为是者。王先谦《汉书补注·曹参传》引沈钦韩说云:“《陈馀传》馀为代王,留傅赵王,而使夏说以相国守代,此夏说自为代相也。《韩信传》注李奇曰:‘夏说,代相也。’其说是矣,此作‘赵盖’误。”[16]982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王叔岷《史记斠证》等,亦皆赞同《补注》的观点,认为《史记·曹丞相世家》误书。
今考,夏说正是以赵相国守代。据《韩信卢绾列传》记载:“高祖七年冬,韩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还,乃封豨为列侯,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兵,边兵皆属焉。”[1]3200又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十年)八月,赵相国陈豨反代地。上曰:‘豨尝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为列侯,以相国守代,今乃与王黄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1]487又《郦商传》:“汉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以将军从击荼……因攻代,受赵相国印。”[1]3226-3227这几段史料说明,汉初时代国的军事事务确实常由赵相国兼领。考《汉书·曹参传》载此事亦作“赵相国夏说”,可见文字本无误。故裴骃《集解》引李奇之说,误。
六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将军从击荼,战龙脱,先登陷阵,破荼军易下,却敌,迁为右丞相,赐爵列侯,与诸侯剖符,世世勿绝,食邑涿五千户,号曰涿侯。以右丞相别定上谷。因攻代,受赵相国印。以右丞相赵相国别与绛侯等定代、雁门,得代丞相程纵、守相郭同、将军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还,以将军为太上皇卫一岁七月。以右丞相击陈豨,残东垣。又以右丞相从高帝击黥布,攻其前拒,陷两陈,得以破布军,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户,除前所食。凡别破军三,降定郡六,县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将各一人,小将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1]3226-3227
按:“还,以将军为太上皇卫一岁七月。以右丞相击陈豨,残东垣。”学者素来颇多争议。王先谦《汉书补注》云:“《公卿表》,商为卫尉,即此事。”[16]1002杨树达《汉书窥管》云:“王说误也。据《表》,商为卫尉在六年,而得代丞相程纵,乃十年陈豨反时事,前后不合,不得言得纵还为卫尉也。”又云:“此传叙商战功,上下文皆无年月,此处不应独异。十月当属上读。”[17]329梁玉绳《志疑》云:“案《汉书》‘七月’作‘十月’,是。盖豨以十年九月反,不得言‘七月’矣。”[2]1341又王叔岷《斠证》引施之勉说云:“《公卿表》,商为卫尉,在高帝六年。此载于陈豨反前一年,则在九年。十年七月,太上皇崩。则商自九年正月至十年七月为太上皇卫一岁七月。十年九月,陈豨反。商又以右丞相击豨,残东垣也。王说非。‘七月’当属上读。”[4]2770
今考,诸说皆非,此段文字当有错简。现将本段所记载郦商的历史事件依次考证系年,以便于理解。
(1)“燕王臧荼反,商以将军从击荼,战龙脱,先登陷阵,破荼军易下,卻敌,迁为右丞相。”
此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五年……十(当作“七”)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1]480又《韩信卢绾列传》:“汉五年冬……七月还,从击燕王臧荼,臧荼降。”[1]3198则燕王臧荼反事在汉五年七月前后。
(2)“与诸侯剖符,世世勿绝,食邑涿五千户,号曰涿侯。”
郦商被封为涿侯,是在平定了臧荼叛乱之后的汉六年。这一年刘邦大封功臣,史书中很多佐证。如《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汉王立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夏侯)婴以太仆从击荼。明年,从至陈,取楚王信。更食汝阴,剖符世世勿绝。”[1]3231又《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亦记载云:“六年正月丙午,景侯(“景侯”乃商谥号)郦商元年。”[1]1065
(3)“以右丞相别定上谷。”
上谷一地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自战国以来便属燕国。汉初,此地亦属燕。《匈奴列传》云:“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1]3490则所谓“别定上谷”,当是针对燕国的作战。考汉初伐燕只有两次,一次是汉五年七月刘邦亲自将兵平定燕王臧荼;一次是汉十二年二月樊哙、周勃将兵平定燕王卢绾叛乱。史书不载郦商平定卢绾。据《绛侯周勃世家》云:“燕王卢绾反,勃以相国代樊哙将,……破绾军上兰,复击破绾军沮阳。追至长城,定上谷十二县,右北平十六县,辽西、辽东二十九县,渔阳二十二县。”[1]2515则卢绾反时定上谷者乃周勃。故郦商这里的记载应该承接上文,是针对臧荼残部的军事平叛行动。臧荼先于汉五年八月时被俘,故时间大概在汉六年。
(4)“因攻代,受赵相国印。以右丞相赵相国别与绛侯等定代、雁门,得代丞相程纵、守相郭同、将军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此事在陈豨反时。据《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定雁门郡十七县,云中郡十二县。因复击豨灵丘,破之,斩豨,得豨丞相程纵、将军陈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县。”[1]2514-2515即此事也。擒代丞相程纵、守相郭同,盖在斩陈豨之后。又据《韩信卢绾列传》:“高祖十二年冬,樊哙军卒追斩豨于灵丘。”[1]3202则获代丞相程纵、守相郭同当在汉十二年冬或稍后,而非杨树达先生认为的汉十年。
(5)“还,以将军为太上皇卫一岁七月。”
此事当在汉六年。周寿昌《汉书注校补》云:“沛公为汉王,商以将军为陇西都尉。及汉王即帝位,则商由梁相国迁右丞相,并无为卫尉之事。或因‘都尉’二字而误邪?《功臣表》亦不为卫尉。”[18]492其说误。据《史记·田儋列传》:“田横因谢曰:‘臣亨陛下之使郦生,今闻其弟郦商为汉将而贤,臣恐惧,不敢奉诏,请为庶人,守海岛中。’使还报,高皇帝乃诏卫尉郦商曰:‘齐王田横即至,人马从者敢动摇者致族夷!’”[1]3211-3212又《汉书·百官公卿表》亦载郦商汉六年以将军为卫尉[8]747,则郦商确实担任过卫尉一职。《汉书·百官公卿表》曰:“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8]728则与《史记》所谓“以将军为太上皇卫”职责相合。故而此事当系于汉六年。
(6)“以右丞相击陈豨,残东垣。”
此事当在汉十一年。据《史记·韩信卢绾列传》记载:“十一年冬,汉兵击斩陈豨将侯敞、王黄于曲逆下……十二月,上自击东垣,东垣不下,卒骂上;东垣降,卒骂者斩之,不骂者黥之。更命东垣为真定。”[1]3202又《高祖本纪》:“十一年……豨将赵利守东垣,高祖攻之,不下月余,卒骂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骂者斩之,不骂者原之。”[1]488则刘邦自汉十一年十二月攻东垣,而东垣月余不下,故下东垣当在汉十一年一月或者二月。
(7)“又以右丞相从高帝击黥布,攻其前拒,陷两陈,得以破布军。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户,除前所食。”
此事当在汉十二年初(十月)。黥布反事在汉十一年秋七月,汉军击破黥布的军队在汉十二年初。据《高祖本纪》:“(十一年)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十二年十月,高祖已击布军会甀,布走,令别将追之……十一月,高祖自布军至长安。”[1]489-491则此事当系之于汉十二年的十月左右。
(8)“凡别破军三,降定郡六,县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将各一人,小将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此系之于破黥布后,误。将此句与“因攻代,受赵相国印。以右丞相赵相国别与绛侯等定代、雁门,得代丞相程纵、守相郭同,将军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一句相比较,则所得丞相即程纵,守相即郭同。“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即“将军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则此当为平定代地之功,非破黥布之功也。否则何以两次作战,其立功俘获如此之同?当系于汉十二年冬或稍后。
可见,以上诸事皆逐次系年。唯“因攻代,受赵相国印。以右丞相赵相国别与绛侯等定代、雁门,得代丞相程纵、守相郭同、将军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一句汉十二年事,其上事在汉六年,其下事亦在汉六年,当是错简无疑。此句在汉十二年冬,时间上应置于击破黥布军之后。故此句应置于“除前所食”之下,“凡别破军三”上,其后又与“得丞相、守相、大将各一人,小将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一句彼此吻合。依此,则行文通畅无碍,当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