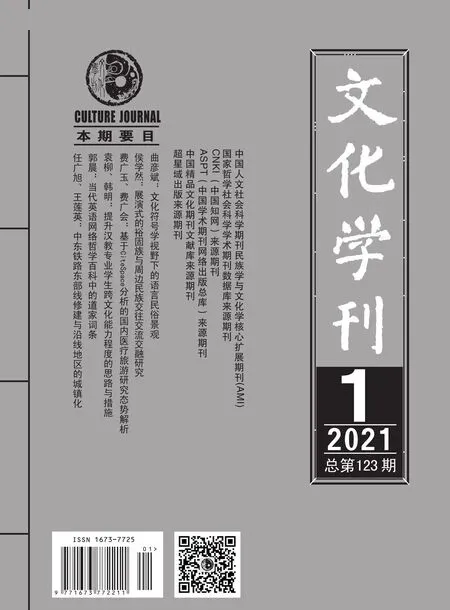从“新红颜写作”的命名说开去
蔡丹阳
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最值得关注的诗歌现象之一,它有别于前几代女性诗歌的书写态势,被诗歌评论家李少君、张德明命名为“新红颜写作”,在2010年5月7日二人博客中发表的文章《海边对话:关于“新红颜写作”》中正式提出。这一观点很快引发了诗歌界的论争,后来甚至超出了诗学范畴。可见,“新红颜写作”这一诗歌概念的提出引起的巨大轰动,21世纪诗歌中的女性写作由此推向理论批评平台,许多诗评家开始具体、系统地进行学术打量。这一概念的提出也是博客女性诗人群体得以命名的标志。
一、命名:缘起与延伸
“新红颜写作”的命名是在一次自由闲谈中得来的,诗歌评论家李少君和张德明在海南省海口市海口湾海边领事馆酒吧闲聊,谈及21世纪女性诗歌的话题。他们敏锐地发现一批女性诗人在个人博客上大量发表诗歌作品,有的还会附上相关图片,这样的形式吸引了不少读者,代表诗人有横行胭脂、施施然、李成恩、金铃子、冷盈袖等。很多人都发现了这个现象,但李、张二人率先提出用“新红颜写作”这个语词来概括这种女性诗歌创作的新样态。
在对谈中,张德明表示:“诗歌博客时代女性诗歌写作已经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个人博客给了女诗人一个新的展示平台,虽然网络世界鱼龙混杂,但是随着文学体裁自身的发展,会逐渐呈现合理的秩序。他们认为,本来处于文学弱势的女性可以在网络上展现自己的艺术才能,通过诗歌写作呈现女性的心灵世界。并且她们大多具备文学素养,有除诗人以外其他的职业体验和经验感受。在发表自己诗歌作品的同时,有的作者还会附上照片展示自己的形象,或是分享美术、摄影作品。诗歌一推出便能得到许多网友的阅读、评论甚至转载,网络对诗歌作品的接受、传播带来很大的便利,这对于写作者是极大的精神鼓舞。于是李少君和张德明给她们集体命名,期望得到诗歌批评界的关注,为她们争取更好的生长环境和空间平台,并且挖掘作品的美学潜质,丰富21世纪的诗坛。这个具有即时性质的命名确实能给当时正兴盛的女性博客诗歌带来不小的热点,不论是读者还是批评家,都会带着阅读期待和合法性质疑来关注这批诗歌。另外,给具有这种特性的女诗人集体命名,有利于带动诗人群体的阅读量和名声,至少比个人独唱要容易出彩,更具吸引力。
李少君将这批女诗人的写作倾向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展现现代女性的生活与思考;二是回顾传统文化,追溯古典诗意。这些主题容易与读者产生共鸣,带来较高阅读量。“新红颜”这一群体创作势头虽显旺盛,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如诗歌的雷同性与自我复制现象等。他们认为,“新红颜”现象的热度要看女性诗人自己的创作水平达到怎样的高度。这样的态度表现了批评家对这批女诗人的期待,他们为作者争取了被阅读、被评价的空间,而不是一味地夸耀来迎合自己命名的诗歌潮流。新鲜的诗歌的出现总会受到追捧和热议,但诗歌的美学价值和历史地位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
二、回溯:“新”与“红颜”
在“新红颜写作”提出的同时,众人也将这个语词进行拆解,从词源上讨论“新”和“红颜”的准确性与有效性,说明它在意义指涉上存在复杂多义的含混性,这也就显示了回溯并重审“新”和“红颜”内含外延的必要性。
根据李、张二人对博客时代女性诗歌的命名,读者朋友容易认定在这之前的女性作家都是“旧红颜”。从女性诗歌发展史来看,“新红颜”有别于20世纪的女性诗歌创作。20世纪20年代的冰心、林徽因在新文学环境下孕育,40年代的郑敏、陈敬容表现民族与个人命运的关系。新时期女性诗歌崛起,朦胧诗人舒婷、王小妮在诗歌中寄托了启蒙反思,第三代诗人翟永明、伊蕾尝试口语化写作,而90年代的安琪、蓝蓝则借鉴发展了西方现代主义……博客时代的“新红颜”显然呈现了与20世纪女性诗歌截然不同的审美倾向和诗歌格局。命名者运用“新”字或许并不是否定或淘汰此前的女性诗歌,而是对构建多样立体的女性诗歌框架和载体的记录,是对新型自由的诗歌创作环境与样式的展现和修饰,这也是对未来创作形式多样化的预示。“新”的最直接表现是在自由宽松的创作平台和环境之中呈现的生产性、发展性和可变性等潜质,这是区别于20世纪女性诗歌的创作范式。
而“红颜”一词更加深了各界的争议。古诗中“红颜”有少年的意思,如李白“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便指的是孟浩然少年时期。也指年轻人红润脸色,如龚自珍“此去东山又北山,镜中强半尚红颜”。最为人熟知的释义是表示女子的容貌,清代李渔的“青眼难逢,红颜易改”,南朝徐陵的“倡人歌吹罢,对镜览红颜”等,多是代表美女或姣好容貌。而在现代的一些辞典中,“红颜”的解释虽没有明显的贬义,但人们依然习惯将其与“红颜祸水”“红颜薄命”等词汇相联系,无法忽视其中带有的“胭脂气”。将它作为21世纪博客女性诗人的阐释,仿佛有过多关注女性诗人在网络平台中展现的容貌之嫌,无法突出这类女性诗歌的文本所显现的诗学价值,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新红颜”这样颇为醒目的命名无疑会使这批作家以及她们的作品更有吸引力,让读者带着阅读期待,考察这种诗歌样式的美学新质。他们显然是赋予了“红颜”以全新的意涵,以现代的视野将其诠释,它的“不可替代性”转化为文字就是“年轻的、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已经显示出创作才能并且还在不断成长和进步的女性诗人”[1]。
三、争鸣:群体心声与合法性质疑
在提出“新红颜写作”这个概念之后,许多人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诗人诉说“红颜”,学者阐释“红颜”。顺着讨论潮流,李、张二人又紧接着推出诗歌展,召开学术会,并与他人集结成了《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21世纪诗歌精选(第三辑):新红颜写作诗歌档案》《新红颜集》等几部书籍。很显然,这个命名带来的讨论效果符合命名者的预测,毕竟诗坛不平静是好事,有争鸣是学界活跃的表征。
“新红颜诗人”和当年“朦胧诗人”一样,不太参与正式论争,只是有过一些文章或访谈表达自己的诗歌观念及审美倾向。她们对诗歌带着一种虔诚的态度,表现在对诗的本质功能的理解,且更注重诗歌写作对自我抒发和人生感悟的传达。横行胭脂认为女性被称为“红颜”是美好的事情,有明显的色彩性,是自由而活跃的写作表征,且不认为女诗人会为这个命名而写作,她们的目的是要提供有意义的文本;金铃子将诗歌当作医治心灵的良药,对其有一份虔诚;李成恩享受网络带来的诗歌民主,且认为原创是写作的基本原则……这批“新红颜”诗人其实并不被命名所圈套,虽然被发现和讨论带来了名气同时也伴随着压力,但这个“私密却又公开”的特殊空间对诗歌创作的迎接和包容,确实给女性诗人以重要的意义,在21世纪诗坛中能呼唤新的诗歌力量。
对此,何平、霍俊明、陈卫、张立群等批评家都对“新红颜写作”展开过理论上的探讨。何平在剖析女性诗歌写作的过程中,质疑“新红颜写作”的命名并表达观点,他判断李、张二人不采用更“学理”的“个人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写作”,显然是因为“新红颜写作”更有利于这个话题在网络空间传播和扩散,而网络上的女性诗人乐于成为被窥视的对象,显然批评家发现了此命名的策略性和炒作意识;霍俊明认为博客上的女性诗歌呈现了一种悖论性特征,看似自由的空间其实反而是无形中的“限制”;陈卫愿意用“限定性喻体”来形容,“把它视作当下女性诗歌创作现象中的一种,这一命名才能体现出与它相符的时代价值和美学意义”[2]。显然,“新红颜”只是21世纪女性诗歌发展的一个方面,仍有不少诗人采用传统的纸质投稿,经过诗歌刊物审稿、评价、修改得以发表。批评家对“新红颜”这一命名的有效性以及这个诗歌群体的诗歌力量提出自己的意见,甚至是质疑。从命名“新鲜出炉”时的合理性讨论,到对具体诗歌的美学特征、语言技术经验的研究,以及探讨女性意识视域中这些作品表现的情感空间和经典化构建,批评家对“新红颜写作”的研究路径和角度,不仅表现了他们敏感的艺术感受力,也推动了诗歌创作与理论构建的发展,更是表达对包含“新红颜写作”在内的21世纪女性诗歌学术上的期待。
四、结语
距离“新红颜写作”概念的提出已十年,从这个语词的源头出发,探寻其命名缘由、群体队伍、诗学特征、局限问题等方面,有助于人们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再次观察和审视“新红颜写作”的诗歌生态。网络更新换代令人应接不暇,博客也早已被微博、公众号等新平台替代,“新红颜诗人”有的依然管理着自己的个人博客,有的出版了不少诗集,有的涉猎不同的艺术领域……她们是否依然热忱于用自由灵性的文字来表现个人情感世界,越来越喜欢快捷、简短信息的读者朋友是否还会喜欢?李少君和张德明的“新红颜期待”是否已经淡化?这,又会引发新的话题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