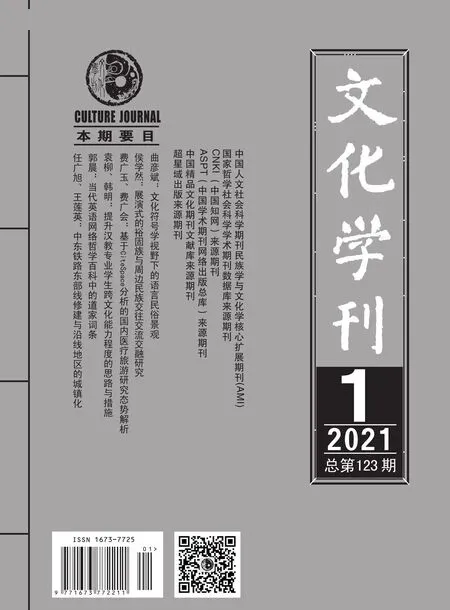论林纾译介小说对西方文化的改写与接受
——以《李迫大梦》为例
胡 珂
《李迫大梦》收于林纾1907年出版的译著《拊掌录》,原为华盛顿·欧文1820年作品《见闻札记》中的一个短篇——《瑞普·凡·温克尔》。故事讲述了美国殖民地时期一位农民为躲避妻子责骂外出打猎,偶然在山间碰见几位古人,偷喝了他们的酒后便昏昏睡去,不料醒来后世间已过数年,到家亲人已逝,村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因小说寓意颇似中国文学中“烂柯人”之典故,所以林纾特意为原题加入“大梦”,以表达物是人非、恍如隔世之感。值得注意的是,林纾译文并非对原作思想与形式的精准直译。作为晚清传统文人的代表,林纾对西方文化的入侵始终心存芥蒂,在“中体西用”原则的指导下,《李迫大梦》不可避免成为中西异质文化交流碰撞的产物,因此,对其进行文化层面的解读与分析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文化改写——介入、删削与强化
为适应清末文人的阅读习惯,林纾特意将《瑞普·凡·温克尔》译为古朴畅达的桐城古文,这种传统诗学审美的介入使《李迫大梦》读之犹如中国古典文言小说,彼时士人读起来亦无生涩之感。如原文中对主人公村庄的描写:
At the foot of these fairy mountains the voyager may have descried the light smoke curling up from a village,whose shingle roofs gleam among the trees, just where the blue tints of the upland melt away into the fresh green of the nearer landscape.[1]769
(笔者译:在这些仙境般的群山脚下,航行者会看到轻烟从一个村落里升起,树丛中闪现出农家的木屋顶,就在那里,山地的浅蓝转变为近处风光的一片新绿。)
可以看到,欧文继承了西方小说客观描写现实的传统,整句话的主语是voyager(航行者),其后几句的景物描写也都是以第三人称视角客观展开,不带有作者的感情色彩,后半部分定语从句的使用也让整个句子逻辑清晰,层次分明。相比之下,林纾译文则删去句中主语,以全知视角展开描写,并在其中加入传统文人特有的“移情”因素,将译文变得更富诗情与文气,读之仿佛步入桃花源,且看林译:
山趺之下,村人炊烟缕缕而上,树阴辄出楼角及瓦缝,隐隐若画。[2]5
很明显,林纾将原文light smoke、shingle roofs等名词转化为中国传统意象“炊烟”“楼角”,且有意弱化了动词在译文中的作用,仅通过各种意象的堆砌造景融情,以弥合原作中因句法繁复造成的主客割裂,这种物我浑融的境界与重理性、重再现的西方文化有着本质区别。
除了中国诗学传统的介入,《李迫大梦》中还存在儒家伦理道德的印记。关于主人公的性格,欧文认为“瑞普时刻准备去处理任何人的事,唯独少了他自己”(笔者译)[1]771;但到了林纾这里,则变为“李迫忠于为人,而惰于为己”[2]6。显然,欧文原话只是在概述李迫性情,不带任何价值判断,而林纾则在其中融入了儒家的道德标准,将李迫为人同“忠”相联系。宋儒朱熹有云:“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3]“忠”与“恕”乃事物辩证的两面,其中“忠”是内核,“恕”是“忠”的延伸与外化,“忠”不仅意味着尽己,还在于由内至外待人接物的坦荡,并将真诚与信任推己及人。小说里李迫总将他人与集体利益置于首位而不顾自身利益得失,这种行为在林纾看来便是“忠”的绝佳体现;另外,林纾亦形容李迫“忠能事妇人,礼重如长者”[2]5,这表明李迫虽惰于家事,但因他在为人处世方面做到了知礼明德,所以依然值得礼赞。如此一来,李迫的形象就有了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
为了让小说更符合传统文人口味,林纾也对原作中的宗教因素进行了删削。这首先体现在李迫宗族身份的改写上,原文中李迫的祖先是随总督彼得出征的基督教骑士,但林纾对此略去不表,仅以一句“先烈恒以武功著”[2]5草草带过,这让李迫一族与生俱来的宗教传统荡然无存;其次,欧文在原作开头附有一首颇具宗教意味的小诗,诗歌赞颂的是撒克逊人的神——渥登,作者将之比作永恒的真理,并鼓励人们至死不渝地坚持下去[1]769(注:笔者译)(1)原诗如下:“By Woden, God of Saxons From whence comes Wensday, that is Wodensday Truth is a thing that ever I will keep Unto thylke day in which I creep into My sepulcher.”。但林纾译文却将此诗直接删去,这极大削弱了整部小说的宗教意味;再次,原作表面在讲述李迫的神奇遭遇,实则是在宣扬一种宗教式的出世观念。李迫以醉酒躲过了世间政权更迭带来的苦难,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他的遭遇也让许多村民为之神往。林纾觉察到了这种宗教意味浓厚的超越倾向,并在译文末尾的跋中予以矫正,他强调:“裙腰之专制固非佳,然亦有乐此不疲,不愿趣仙乡,而但乐温柔乡者,惜汝未之见。”[2]59这等于奉劝读者专注现世生活,过好当下,不能麻痹自己,通过逃避而把希望寄托于来世。总之,原作里的宗教氛围在林纾译作中几乎被删削殆尽,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清末传统文人对西方宗教文化的不解乃至拒斥。
《李迫大梦》也存在对原作政治因素的强化。原作虽然充斥许多政治术语,但欧文对民主政治的基本态度是讽刺的。例如,李迫在旅馆所见的演说之人,欧文形容其为“一个瘦削且脾气暴躁的家伙,口袋里还塞满传单”[4],寥寥几笔就勾勒出政客的丑态。在原作结尾,欧文再次强调政治变革并未对主人公产生任何影响,以此弱化小说本身的政治性。但林纾却在其中看到了中国政治改良的希望,例如对那位旅馆演说者,林纾并无讽刺之意,而是将其描述为“但见一长瘦之人,方演说民权选举会议之议员与自由等事”[2]11。可以说,原作中对政治的讽刺态度在林译版本几无存留,取而代之的是对民主政治相对客观全面的展现。对于美国民主之父华盛顿,林纾也充满敬意,称其为“大将华盛顿”,并在译文结尾的跋中数次提及。由此可见,林纾身上依然具有传统士大夫胸怀天下的历史使命感,他对《瑞普·凡·温克尔》中政治因素的强化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中国谋求政治改良,以变法自强求富的历史呼应。这种强化虽是对原文的改写,但却切实反映了晚清知识分子求新求变的改革呼声。
二、文化接受——交汇与融合
林纾译文充满对原作的大量改写,但对西方文化的精髓与可取之处,林纾并未彻底否定,而是选择性地加以吸收融合,并力图以西方文化的新鲜血液重振中国传统,其中尤以政治接受为甚。《瑞普·凡·温克尔》虽然充斥对美国民主体制的不满与讽刺,但文中所言选举、权利、议院、国会等新奇词汇对林纾这样的晚清文人吸引颇大,这也是西方文化中值得借鉴之处。梁启超倡导文学界革命时就提出,小说的翻译及创作须“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其目的即在于利用西方的政治精神新民救国,改良群治。所谓“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晚清觉醒的知识分子普遍相信,政治上的改良是使中国摆脱积贫积弱状态的不二法门。这就要求译者优先翻译带有政治色彩的西方文化文本,同时强化文本的政治主题,以达到惊世救弊、改革图强的目的。译作中,面对民主演说时李迫“张目”“瞠目”“愕然”“浩叹”的态度何尝不是这些文人内心的真实写照。李迫所言“一夕之醉,而世局变幻如是”[2]12,正影射了传统士人面对西方政治突飞猛进时的感慨与无奈。所以,在《李迫大梦》中,林纾讽刺的重点不在于民主政治,而是专制之下国民的无知愚昧。他本人也接受了西方民主政治中设议院、开国会的主张,并希望以此改良中国政体,革新国家面貌,这种文化接受正是对晚清时代语境的无缝契合。
除了政治层面的接受,在《李迫大梦》所描述的两性关系中也能看出林纾对西方伦理的部分接纳。儒家一向重“礼”,而“礼”意味着等级的别异,因此夫妇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汉儒董仲舒更是以“夫为妻纲”将这种关系牢牢固定下来,让“三从四德”成为束缚女性的枷锁。在林纾早期译作里,对夫妻纲常的强调十分明显,但在《李迫大梦》中,林纾不再把女性视作男性的附庸,而是对婚姻生活中女性的地位进行提升,同时赋予女性更多权利与自主意识,这些做法体现出林纾女性观的进步。例如,针对李迫因惧内离家的举动,林纾评论道:“士大夫中有日受其夫人之夏楚,乃感恩踊跃,竭尽心力以图报,近世大有其人,而其人又为显者。”[2]59在林纾看来,婚姻生活里两性之间应是平等互惠的,妻子对丈夫的鞭策并不违背伦理纲纪,而是对丈夫的有益激励,丈夫甚至还要感恩妻子的责难。林纾在此十分强调女性的地位和作用,这与传统观念认为的男尊女卑大相径庭。另外,林纾也非常钦佩华盛顿为两性关系带来的改变,他指出:“顾不有华盛顿,而帷房谇诟之声,将日闻于人间。”[2]59华盛顿为民众带来了平等与自由,这种观念间接促进了夫妻关系的良性发展,所以在林纾看来是极其有益的。当然,林纾提升女性地位的做法并非为申女权,而是通过吸收西方两性理念反驳儒家伦理中的不合理因素,使其能够适应现世的发展。林纾本人对女权是持否定态度的[5],他也在跋中警告“女权亦昌,丈夫尤无伸眉之日”[2]59,可见林纾对西方两性关系的态度更多是一种批判式的接纳。
林纾对西方文化的接受还体现在叙事技法乃至文学观念的转变上。中国传统小说往往是全知全能叙事,且缺乏对人物内在心理的描写,《李迫大梦》则不然。林纾接受了原作叙事视角的转换,并在翻译中将其运用得炉火纯青。译作开头,林纾先以全知视角描写李迫村庄的自然地理环境,同时对李迫为人作了详细叙述。但从李迫出走深山开始,视角便转向了以他所见为主的内聚焦叙事,例如:
时天已垂暮,俯视沃壤云连,青绿弥望,远见黑逞河渐渐东逝,云光照水,风帆徐徐而没。内觑但见深谷,人迹弗至;谷底多堕石,以山峭蔽天,日力不及,状至阴沉;李迫凭高四望,垂暮将归。[2]8
林纾分别从“俯视”“远见”“内觑”“凭高”四个视角描绘了李迫所见,而不是像传统小说以全知视角写出,读者在此感受不到除李迫以外的叙述话语,这要归功于林纾对原作限知视角的模仿。另外,林纾也接受了原作心理刻画的技法,如李迫酒醒时懊悔不已,心中既感诧异,也觉恐怖,同时又担心妻子责骂,几重心思纠葛缠绕致其心理活动异常丰富。林纾翻译时并未忽略这些描写,而是使用三个“自念”将复杂的内心叙事加以串联展现,在叙事技巧上做到了中西结合。此外,不仅是《李迫大梦》,在整个林译作品中,小说的地位都被无限提升了,它不再被视作“小道”,而是作为表达作者观念的载体,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与政治功用,这与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三、文化心态——通变与保守
《李迫大梦》刊印于1907年,彼时文学界革命高潮虽已过去,但对文人的余温尚在。不过,相较于将西方思想直接注入旧形式的革命实践,林纾的这篇译作依旧显得有些保守。《李迫大梦》有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但更多的乃是对欧风美雨的警惕与拒斥。林纾甚至还专门在文末附跋,以矫正原作的部分观念,这和梁启超等人对待西方文化的开放态度有很大区别。可以说,作为传统文人的代表,儒家的思维观念与认知模式从未在林纾身上消散,但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林纾又必须通过学习西方来对儒家进行通变,以求得文化上的自强保种。因此,在林纾身上存在变革与保守的双重维度,这造就了其在文化选择上的复杂心态,并由此成为晚清士人群体的独特文化标识。
就以林纾为代表的传统文人而言,保守主义是其文化心态的主导[6],其中也蕴含着求新与求变。面对西洋文化的强势冲击,这些文人选择坚守传统,始终未有根本性的改变。他们对儒家文化抱有自信,认同“中体西用”,反对激进的政治文化革命,并希望通过温和的改良实现传统文化的增殖与再生。在文学上,他们依然坚持古文写作,反对淡而无味的白话,并在文章中以儒家伦理评判舶来的意识形态,拒斥其中的无用之物。与此同时,西方文化的强盛也使他们不得不着眼于异邦,通过寻求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互联互通来为传统增加新的生机与活力。但就这些人的“通变”而言,某种程度上依旧是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延续,并且这种“变”并非主动求变,而是被动且带有很强的功利性质的。对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译介源自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意识的觉醒,林纾的首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便出版于1899年,其后的《黑奴吁天录》更是警醒世人在压迫之下要奋起反击,护国保种。从本质上讲,林纾之“通变”乃是传统士大夫面对大道崩坏时内心责任感与使命感的迸发,其思想依然根植于儒家传统之中,目的是巩固儒家之正统。而在清朝覆灭后,以林纾为代表的文人往往又以文化遗老自居,言必称传统,这种恋旧守旧的保守心态自然使他们受到来自新文化阵营的猛烈攻击。
但是,如果将林纾所代表的文化心态置于更大的历史纵深中,我们也能发现其中的价值。在近代历史的不同阶段,中国文人对西方文化的接受程度也是不同的。鸦片战争后,虽有魏源等人著书立说译介欧美文化,但西方在传统文人眼中依旧是蛮夷之地,魏源等先行者也只是震惊于西方的军事文化,他们强调技术层面的学习,并没有深入西方文化的内核;中日甲午战争过后,传统文人对西方的态度发生转变,他们开始逐步接纳西方先进的政治文化与社会伦理,并乐意将其视作对传统的合理补充。这种学习触及西方文化的内核与精髓,但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文人依旧会对其中的异质因素进行删改,使之不超脱传统范畴,以在保守中求得变通,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便是如此,而林纾也是这一阶段中国文人心态的典型代表。随着西方文化在国内声势的日益浩大,新生代文人如胡适等也开始了对西方文化中更深的思想层面的学习,他们完全跳出儒教的束缚,直面传统文化的困境,力求将西方民主平等的内核融入其中,让中国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所以,在文化心态的演变中,林纾正处于近代文人由保守走向开放的中介点,他始终游走于变革与保守之间,既不像激进文化主义者那样极端,也不似守旧派固守祖宗之法不变。他坚持对西方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吸收,这种做法自有其合理性,只不过清朝灭亡后,向西方学习几乎已成共识,此时再谈中学为体自然会被视作异类,被攻讦也就在所难免。但不可否认,林纾对西方文化的复杂态度是近代知识分子文化心态演变的重要一环,并在其中起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从共时角度看,林纾文化心态中开放的一面客观上也为其他知识分子接触传播欧美文化创造了条件。在中西交流中,林纾一直扮演着文化媒介的角色,其翻译作为欧美文化的启蒙,既对一大批现代作家的文化倾向产生过直接影响,也间接促进了清末社会转型下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胡适、鲁迅、郭沫若等新文化运动主将都嗜读林译作品,并奉其为难得的珍馐。周作人曾直言:“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7]钱钟书亦承认:“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8]正是有了林纾的大力译介,西洋文化才能在儒家传统的夹缝中发芽生根,最终蔚为大观。因此,从同时代的接受情况看,林纾的文化心态亦有着极大的进步意义。
四、结语
《李迫大梦》中对西方文化的改写反映出林纾文化态度中保守的一面,但其中对西方政治与伦理的批判接受也体现出传统文人面对乱局时求新求变的务实精神。总体而言,通变与保守之间的摇摆构成了清末文人共有的文化心态,这种心态是晚清历史语境下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产物,它在近代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演变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在客观上督促传统士人殚智竭力,不断为晚清国人提供新的认知世界的途径,这背后透露出的复杂文化内涵值得我们一探再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