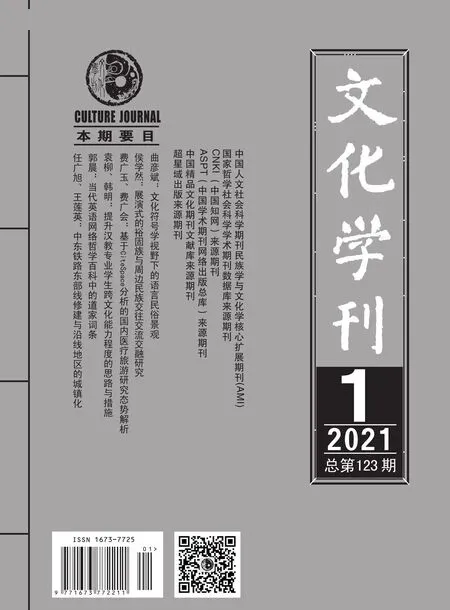从人物角色的表现形式探究萨特戏剧创作的演变过程
傅楚楚
法国哲学家萨特是西方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剧作家,他在戏剧创作和戏剧理论当中融合了他的存在主义思想。1947年,萨特在著作《境遇剧》(UnthéatredeSituations)中明确提出,他创作戏剧的目的是“充分发掘人性,向现代社会的人们描绘他们的面目,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希望与挣扎”[1]63。萨特认为,一个正在形成的性格是“最为动人的”,人物的性格并不是预先存在的,而是在行动中逐渐获得、逐渐发展的。这与萨特的存在主义不谋而合,即否认本质,承认使某一个体成为个体的因素。也就是说,萨特希望自己塑造的人物角色既不是脸谱化的性格类型,也不是被扭曲的抽象形象,而是人性本身。
从1941年动笔创作第一部完整的剧本到他作出以上论述的六年期间,萨特已经创作了四部戏剧作品,不包括未正式公演的《巴里奥纳》(Bariona)和两部残篇,这四部作品是:《苍蝇》(LesMouches,1941年)、《禁闭》(Huisclos,1944年)、《恭顺的妓女》(LaPutainRespectueuse,1946年)和《死无葬身之地》(MortsSansSépulture,1946年)。在这个时期,萨特的戏剧创作不仅在形式上经历了一个从非现实到现实形式的转变——《苍蝇》和《禁闭》都是以神话和想象形式表现的,《恭顺的妓女》和《死无葬身之地》的故事背景终于放在现实社会——其人物角色身上的存在主义绝对自由的特质也在逐渐减弱。早期我们能够很明显地看出作者隐藏在《苍蝇》的俄瑞斯忒斯和《禁闭》的加尔散身后表达自己的哲学观点,将他们当作自己的代言人,而在之后两部作品里,作者的阴影正慢慢撤退,开始将人物交给他们的希望和挣扎,令他们在极端境遇中展现人性。如果接着比对萨特1947年之后的戏剧作品就会发现,从1948年完成的《肮脏的手》(LesMainsSales)到1951年的《魔鬼与上帝》(LesDiableetleBonDieu),再到完成于1959年的《阿尔托纳的隐居者》(LesSéquestrésd’Altona),作者的创作理念一直是在不断变化的。
《苍蝇》的创作是向导演查理·杜兰(Charles Dullin)的致敬之举。杜兰曾说过:“不要表演字词,表演境遇。”萨特曾套用此语来定义自己的戏剧写作:“不要写字词,写境遇。”[1]272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戏剧命题,即“境遇剧”,力图表现人类普遍的处境以及在特定的境遇下人的自由选择。境遇在改变,萨特对人物的塑造也在演变。随着萨特的哲学思想逐步成熟和对介入文学的体会逐步加深,他的作品意识形态更为隐晦,观察视野也更为开阔,这种演变非常明显地以角色与外部三种不同的关系呈现出来:个人-他人、个人-集体和个人-历史。接下来笔者将通过上述三种呈现方式对萨特戏剧人物的演变进行探讨。
一、个人-他人
1941年,萨特开始《存在与虚无》的写作,这期间他同时在创作剧本《苍蝇》。1943年6月底,《存在与虚无》出版几个月后,他开始着手创作《禁闭》。无论是《苍蝇》还是《禁闭》,其人物角色实际扮演了身为哲学家的剧作者思想的传声筒,成为存在主义自由观具象的化身。萨特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谈到未完成的剧本《巴里奥纳》时,他说:“我后来之所以不再提《巴里奥纳》,是因为这个剧本很糟糕,它有太多的长篇大论了。”[1]266在萨特看来,《苍蝇》排演之后,他“看待戏剧的眼光已与之前不同”[1]272,但萨特似乎并没有说到做到,《苍蝇》里的长篇大论并没有减少,而且将代言作者存在主义思想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首先,俄瑞斯忒斯的形象是一个“摆脱了一切束缚,不被任何信仰所禁锢……没有家庭,没有祖国,没有宗教,没有职业,拥有参与世事之自由,同时又懂得不应投身其中”的人(第一幕,第二场),但他同时也承认了这种自由的空乏:“啊!我是多么的自由;而我的灵魂是多么绝妙的空乏。”(同上)所以,俄瑞斯忒斯所代表的其实是一种绝对而抽象的自由。其次,俄瑞斯忒斯的主要冲突对象朱庇特是一位天神,是万物的创作者,在两人正面对峙的时候,朱庇特的大段独白表明了他所象征的身份:“俄瑞斯忒斯!我创造了你,我创造了万物。”(第三幕,第二场)对此,萨特通过俄瑞斯忒斯之口说出了存在主义的宣言:“我是我的自由!一旦你创造出了我,我便不再属于你。”(同上)在此之前,萨特就让朱庇特说出了所谓天神的秘密:“人的心灵一旦爆发出自由,诸神就对他无能为力了。因为这就成了人间的事情,需要由其他的人——也仅仅只能靠其他的人——来决定,是放他生路,还是将他扼杀。”(第二幕,第五场)
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萨特的存在主义伦理观认为自由本身即行动的目的,这个自由是绝对的和抽象的,正如俄瑞斯忒斯在整部剧中发表了大量关于自由的言论之后,并没有真正为解放全城的举动负责到底,最终离开了阿尔戈斯。俄瑞斯忒斯的行为是一种贵族式的和英雄主义的介入,他“不愿与自己子民割裂开来”,他要成为“第一个踏上自由道路的人”[1]279,但他这种不与人民割裂的意愿与其将一切肩负于己身的行为是相背而驰的。俄瑞斯忒斯想成为人们之中的一个人,但他并不是真的想这样做,他只是在摆出一种姿态。剧终时,民众仍以民众的形式成群结队出现,俄瑞斯忒斯仍被排斥在外,尽管后者自说自话地宣布:“现在,我是你们中的一员了,鲜血将我们联结在一起……”(第三场,第六幕)但实际上,他只是陶醉于自己的自由之举:“所有一切都归咎于我,我将承担一切。不要再惧怕你们的死者,现在他们是我的死者。”(同上)俄瑞斯忒斯的自由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自由,他获得自身的自由之后将民众抛在身后,民众之中也许会有人效仿他选择自由,也许不会,但俄瑞斯忒斯——或者说作者本人——并不在意结果如何。因此,他最终实际上切断了与民众的联结,远离了他们,成为一个孤独的英雄。
同样,我们在《禁闭》中也发现了这种个人主义的观察视角。这部剧作创作于1943年,1944年首演。当时法国正处于德国占领时期,贝当政权偏居南部小城维希,摇摇欲坠,而巴黎的文化界小心翼翼地在德国审查机构的压迫下求生存。当时法国有很多学者勇敢地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对时局的不满,《禁闭》这部作品也被普遍认为是萨特对德军控制的不自由现状的控诉。萨特后来解释,他这部剧的目的正是要展现“荣誉与正直要求对德国人做出抵抗,无论结果为何”[1]280。有趣的是,虽然《禁闭》在战后戏剧界生命力长久,却并未作为一出抵抗剧而被铭记。在萨特全部作品的语境下,它首先是萨特实验主义哲学的一场广受欢迎的演出。《苍蝇》和《禁闭》这两部作品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自由,《苍蝇》取材自古典神话,《禁闭》使用了基督教地狱的概念,前者是获得个人自由,后者是失去个人自由,前者中的俄瑞斯忒斯将自己视为解放者,后者传达的信息却是屈从而非反叛,不过两部作品的立足点都是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观。
对《禁闭》来说,冲突来自加尔散-伊内丝-艾斯黛拉三人之间个人意愿的分歧,在“地狱”这种具有实验室性质的理论化空间里,社会影响无法渗透其中;对《苍蝇》来说,冲突发生在俄瑞斯忒斯的意志和朱庇特的意志之间,阿尔戈斯民众的意志无足轻重,而且阿尔戈斯人不过是俄瑞斯忒斯获得个人自由的工具,所以对其产生的影响相当有限。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萨特戏剧的人物角色遇到的利益冲突是由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矛盾引发的,矛盾始终围绕着不同个体之间展开,来自社会的影响还比较微弱。
二、个人-集体
1945年10月,《现代》(LeTempsModerne)杂志首期发行,标志了萨特介入文学的起点。1946年,萨特开始撰写《境遇》(Situations)第一卷和《境遇剧》;也是在这一年,萨特创作了《恭顺的妓女》和《死无葬身之地》。萨特对记者谈起《死无葬身之地》一剧的创作时提到时间背景的演变:“因为我认为现代戏剧应该是具有现代性的,所以我不会再写《苍蝇》那样的剧本了。”[1]272《恭顺的妓女》被作者本人评价为“失败之作”,《死无葬身之地》则很少被其提及,这两部作品可以看作过渡期的两次“试验”[2]。但我们从这两部作品可以看出,萨特开始更为关注社会对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产生的实质影响,比如《恭顺的妓女》探讨了白人社会的种族歧视和白人社会内部的社会等级歧视。
1948年,萨特加入革命民主同盟(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Révolutionnaire),这标志着他直接参与了政治运动,他的戏剧写作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一年他创作了政治戏剧《肮脏的手》。这部作品的故事发生在1943年到1945年之间一个叫伊瑞利(Illyrie)的国家(很明显是在指匈牙利,法语的匈牙利一词是“Hongrie”),取材于冷战时期现实题材,处理的是一个相当经典的党派内部斗争的问题:两个派系的政治路线产生了无法调解的矛盾,只能通过肉体消灭来摧毁反对派。为了达到夺取领导权的目的,党组织执行的唯一标准就是效率,无论是通过谎言,弄虚作假还是暗杀,只要达到目的即可,而这些都是与所谓的道德标准和人性背道而驰的,于是行动者必须“弄脏自己的双手”[3]101。在这一点上,关于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政治手段的思考已经代替了《苍蝇》中绝对自由的思考。
首先我们要承认的是,《肮脏的手》中的雨果和《苍蝇》中的俄瑞斯忒斯这两个人物有重叠也有拒斥。重叠是因为他们都是边缘化的革命者,都渴望通过一个暴力举动融入一个集体,俄瑞斯忒斯自觉“灵魂的空洞”,雨果追求存在的“重量”。可以说,雨果实际是“扎入现代社会”[4]34的俄瑞斯忒斯。两个角色同时也是相互拒斥的,因为俄瑞斯忒斯是一名“恐怖主义”英雄,他一旦决定杀人就毫不犹豫,杀人之后也毫无悔意,是一个真正的“冒险者”[5]。而雨果不同,尽管他一直渴望得到一个比报社编辑更危险、更光荣的任务,但他政治介入的态度并不鲜明。如果说俄瑞斯忒斯的介入是为了拥有与他人共同的回忆,雨果入党则是为了“忘记自我”。赫德雷一下子就发现了雨果话语中的关键之处:“你每一分钟都在想,要忘记自己。”(第三幕,第一场)他这样评价雨果:“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你晚出生了五十年,现在已经不兴恐怖主义那一套了。”(第二幕,第四场)
尽管雨果试图与过去决裂,却始终无法克服知识分子的缺点。付诸行动不同于纸上谈兵,雨果在完成暗杀行动时一直犹豫不决。在与妻子杰西卡嬉戏的场景中,他请求妻子相信自己,请求她认真一点:
雨果:看着我的眼睛,不要笑。听着:赫德雷的事,是真的。是组织派我来的。
雨果:杰西卡,我是认真的!
杰西卡:我也是。
雨果:你是装作认真罢了。你刚才这么跟我说的。
杰西卡:不对,是你在装认真。
雨果:你要相信我,求你了。(第三幕,第一场)
事实上,雨果并不是让他的妻子认真一点,他不断重复这个游戏的目的是让自己认真起来。行动之前,他犹豫不决,行动之后,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出于什么原因杀了赫德雷:“一个动作来得太快了,它一下子挣脱了你,而你却不知道是因为你想这么做,还是因为你无法控制它。”(第一幕,第四场)简而言之,从《苍蝇》到《肮脏的手》的演变,首先是从恐怖主义式的明确到知识分子式的暧昧的转变。
其次,我们可以看出《肮脏的手》观察视角的扩大,即人物关系不再局限于《禁闭》中的个人-他人,而是扩展到了个人-集体,雨果成为革命者的“同志”,他的介入行为受到了集体因素的影响,与集体利益发生了冲突。俄瑞斯忒斯在《苍蝇》中的起义则是贵族式的,他单枪匹马地行动,并没有和民众站在一起,民众只是他的子民而不是同志。这样的自由行动发生在古代神话故事的背景中似乎在情理之中,但俄瑞斯忒斯借尸还魂到现代社会成为雨果,贵族式的行为失效,个人的拯救不再具有意义,“人不再能够在孤独中解放自我并且接受其同类继续被奴役”[4]34。另外,阿尔戈斯人是一群很容易被蛊惑和操控的人,但雨果面对的是抵抗意识觉醒的人。不再是俄瑞斯忒斯为被奴役的人民忧虑,而是轮到革命者们嘲讽雨果。
但我们要认识到,雨果的介入其实与萨特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具有一样的性质,都抱有知识分子式的同情:萨特自称“持批判态度的伙伴”,他采取的是逻辑性的思考和哲学的思辨,同时置身于真正的革命事业之外[3]56。雨果这样喊道:“我从来都不饿。从不!从不!从不!你,也许你能告诉我,我到底要怎么做你们所有人才能不再指责我。”(第三幕,第三场)
我们似乎在雨果身上看到了离开阿尔戈斯城之后的俄瑞斯忒斯是什么下场:一个现代社会里的贵族,一个富有的、混在工人阶层的资产阶级,他永远不会被这个集体原谅和接纳,他永远不可能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
三、个人-历史
《存在与虚无》一书的结尾预告了续篇《存在主义伦理学》(Moraleexistentialiste),但续篇并没有写出来,只有几篇相关的笔记出版。这个1943年就宣布开始并于1947年动笔的写作计划于1948年就搁置了,因为萨特认为他在战后的哲学立场已经完全过时了。1948年无可争议地成为作者写作生涯的转折点,通过《肮脏的手》我们可以察觉其政治思考是如何转变的,也看得到其对之前作品的自我反思。
假如可以将俄瑞斯忒斯视为一名绝对的、恐怖主义的、毫无悔意的、乌托邦式介入的解放者,将雨果视为开始反思介入方式的俄瑞斯忒斯,那么我们就可以将《魔鬼与上帝》中的歌茨视为政治理念再次演变的雨果。在歌茨最后的大段独白中,他语气决绝,但相当被动:
歌茨:……我将让他们恐惧,因为我没有爱他们的其他方法,我将向他们下命令,因为我没有其他方法令他们服从,我将独自待在头顶这片空洞的天空之下,因为我没有别的办法与所有人共处。这场战争要打响,那我就去打。(第三幕,第六景,第二场)
其实在1952年6月2日出版的周刊《周六夜》(Samedi-Soir)与马塞尔·佩茹的访谈“魔鬼和上帝是一回事……我选择人类”中,萨特承认:
他(歌茨)与绝对的道德观决裂,采纳了历史的、人性的和特殊的道德观。他曾经珍视暴力,他先去挑衅上帝,然后又去取悦他。他现在懂得有时运用暴力,有时展现和平。于是他融入到他的弟兄中间,加入了农民起义。在魔鬼和上帝之间,他选择了人类。[1]34
…………
很显然,从《肮脏的手》开始,萨特已经开始修正之前创作中的绝对主义,直到《魔鬼与上帝》,他开始尝试采用历史观的立场。可以看出,比起《肮脏的手》中有关政治手段的思考,萨特在《魔鬼与上帝》中对于善与恶的思考更为沉稳、均衡。佩茹在同一篇访谈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是您第一次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自创作《自由之路》八年以来,您持有的‘伦理观’在这里终于有了一个结论是吗?”萨特回答说,雨果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资产阶级,他不明白正确行动的必要性。歌茨是一个思想转变了的雨果”[1]315
萨特戏剧对人物角色的塑造由此又迈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些角色在面对社会现实时,从绝对主义伦理观(追求绝对自由的俄瑞斯忒斯)转变为辩证思考(摇摆于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雨果),最终达到正确的介入行为(加入农民起义的歌茨)。在1951年6月7日刊载于《巴黎-新闻-不妥协者》(Paris-Presse-L’Intransigeant)的另一篇访谈中,萨特将《魔鬼与上帝》评价为《肮脏的手》的“补充”和“后续”[6]。在1951年5月31日刊载于《观察家》(L’Observateur)的访谈中,萨特说歌茨“以历史代替了绝对”[1]315。由此看出,作者对人物关系的视角再次扩大,萨特在《肮脏的手》中处理了个人-集体关系,在《魔鬼与上帝》中则是个人-历史关系。
1957年,萨特针对阿尔及利亚发生的战争和虐俘事件发声,1958年3月6日,他就亨利·阿莱格的《问题》(LaQuestion)一书针对阿尔及利亚虐俘问题撰写评论文章,发表于《快报》(L’Express)[7]。4月17日,他和绝交了六年之久的加缪重新站在一起,要求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虐俘行为采取法律制裁。最终,萨特笔下的戏剧人物也采用了与之前的作品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行动。
1959年,萨特创作了《阿尔托纳的隐居者》,这部涉及虐俘问题的作品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进行了思考:一个人在战时接受做一个刽子手,战后,他将如何与自己妥协,或如何不与自己妥协?这一次,萨特要“愚弄(军事)英雄主义”[1]348,展现同时代人的“暧昧感”,因为在他眼中,伦理和政治中“再也没有什么是简单明了的”[1]363。在这部作品中,我们通过弗朗茨这个人物可以看出,他不再是一个处于介入行为中的英雄,而是一个介入行为之后自我救赎的人,正如萨特所言,“要表现之后的人们”[1]354。
假如可以将雨果看作“扎入现代社会”的俄瑞斯忒斯,那么也可以将弗朗茨看作行动失败之后的俄瑞斯忒斯。时代与境遇的变化导致个人力量与个人解放较之于《肮脏的手》更加微弱,甚至消失不见。在父亲这个角色的眼中,良心不过是“王子的奢侈品”(第一幕,第二场)。当弗朗茨责备父亲不该与纳粹有生意往来时,父亲如同面对古希腊的俄瑞斯忒斯一般对弗朗茨说:“小王子啊!小王子!你想把整个世界都扛在肩上吗?世界很沉,而且你也不了解它……你是如此抽象。”(同上)
一个贵族的、抽象的俄瑞斯忒斯不再合时宜,但作为一个大工业家的儿子,一个接受意大利教育和艺术熏陶的、试图挽救清教主义的纯正性的“小王子”,他又能如何行事呢?弗朗茨——一个企图用隐居行为自我救赎的人物,他参与了虐俘,他意识到这是罪恶的,并因这种行为而感到恐惧,因此在战后试图逃避。战后的复兴让他充满罪恶感,因此他将自己关在阁楼,对外宣称自己已经死了,不去面对现实。弗朗茨坦陈:“我希望我的国家灭亡,我隐居起来就是为了不去见证它的复兴。”(第五幕,第一场)这个角色没有走上通往未来的自由道路,而是永远地幽居于过去。他的过去决定了现在的行动方式,因此“历史是由胜者书写的”(第一幕,第二场),弗朗茨的命运就取决于历史,他从来不选择,他说“我是被选择的”(第二幕,第五场),“我将如悔恨一样腐烂”(第二幕,第一场)。他像阿尔戈斯人一样永远地活在悔恨中,后者也从来无从选择,他们被摆布,遵命行事,他们全都有罪,并将被集体审判。
罗伯特·劳瑞斯指出,《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可以被视为萨特戏剧作品的“一个总结”[8]257,因为之前作品出现过的话题在这部作品几乎全部被重新探究:虐俘、道德败坏、他人的评判、责任感、自我审视,等等。这部作品也是其戏剧创作演变的一个回顾,这种演变无疑与萨特整个创作生涯中政治理念的演变息息相关。
四、结语
纵观上述代表了三种人物关系的表现形式可以看出,萨特想要实现两个趋势:其一,他希望境遇越来越具体,人物也越来越具体——在《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中他就借剧中角色之口批评俄瑞斯忒斯太过抽象;其二,他希望主角的地位逐渐淡化,也就是说从一个独立创造历史的个体过渡为一个具有依附性的由历史造就的产品。这三种人物关系分别可以由三部戏剧作品来代表(《苍蝇》《肮脏的手》《阿尔托纳的隐居者》),这些作品勾勒出了萨特由个人主义视角过渡到历史观视角的戏剧创作路程,也标志着作者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逐步成熟。
《苍蝇》中的朱庇特说:“一个人类要宣布我的黄昏。”劳瑞斯借用这句台词评价《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历史宣布了存在主义者的黄昏。”[8]257笔者认为,这句话同时也是对萨特的“境遇剧”创作演变过程一个很好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