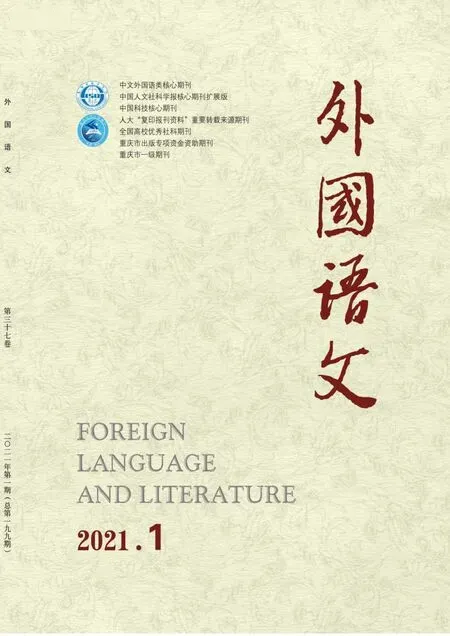《湖上夫人》:如画旅行中的多重凝视
龙瑞翠 王林海
(燕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0 引言
英国历史小说之父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因卓越的叙述能力被誉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在他充满瑰丽想象的历史小说中,既有对苏格兰传统满怀眷恋的记忆书写,也有对英格兰为中心的统一国家的渴望,从而在英苏关系问题上呈现出一种穆尔(Edwin Muir)称为“忠诚分裂症”(divided loyalty)、列文恩(George Levine)称为双重性(duality)的现象。皮托柯(Murray Pittock)在《苏格兰与爱尔兰的浪漫主义》(ScottishandIrishRomanticism)一书中进一步提出司各特关于英苏两邦同情性和解的观点。遗憾的是,正如司各特研究专家斯蒂芬在讨论司各特文学发展之路时仅一笔带过地说司各特早期诗歌创作“为他中年(历史小说创作)积累了大量蕴含着如画美景意象的故事”(Stephen,1909:136),皮托柯的关注点也在小说,虽然他承认司各特早期诗歌创作的价值,却并未深入讨论这些诗歌如何“对司各特最终成为伟大历史作家具有重要意义”(Pittock 188)。 虽然司各特小说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且研究者多认为他在处理英苏关系时坚持主和的立场,但司各特的诗歌却鲜有人关注。事实上,司各特历史小说创作几乎全部延续了早期诗歌创作的取材、主题和写作手法,诗歌也反映了他对英苏关系的立场。
笔者细读司各特最得意的叙事长诗《湖上夫人》(TheLadyoftheLake,1810)发现,故事以一位猎手因追猎牡鹿误入高地腹地、意外开启一场漫游苏格兰高地的如画旅行(Picturesque Tour)为开篇,从陌生人视角向读者呈现了一幅偏处北隅、古老高峻、忧郁孤寂的苏格兰高地景观。而后,诗人通过频繁切换外来者与本地人凝视视角的方式大手笔绘制一幅波澜壮阔的苏格兰史诗画卷,卷中水柔风清处自有美人抚琴轻歌,山高径曲处恰是英雄末路时,荒原阔野处,苏格兰高地儿郎策马挥刀斩情仇。司各特这一如画旅行式书写初见于《最后的行吟诗人》(TheLayoftheLastMinstrel,1805),成熟于《湖上夫人》,最终成为他抒写苏格兰高地的套路,一遍遍复现于他的历史小说创作之中。这一书写方式通过熟悉化、美化高地景色,从地理与文化两层面强化过去与现在的延续性,致力于唤起苏格兰人民的共同文化记忆,形塑苏格兰集体文化身份,成为苏格兰民族实现其民族身份认同的标志,广受世人喜爱(1)据皮托柯(Pittock,195)统计,《最后的行吟诗人》十年内发行了15版,《玛米恩》截止到1825年销售3.6万本,《湖上夫人》到1836年共卖出5万本。,并成为苏格兰文学叙述方式的典范和风景画作的重要取材对象。基于此,本文聚焦猎手的高地如画旅行,细读《湖上夫人》如何借助外部凝视、内部凝视、全知俯视等手段呈现16世纪苏格兰高地中心与边缘化关系的博弈,进而通过文本与时代语境的互文阅读探究诗人在处理英苏关系时表征出矛盾态度的原因与目的。
1 如画旅行者的凝视
正如司各特(1986:250)在1806年致赫伯尔(R. Heber)的信中所言,他创作《湖上夫人》的原则是:不能仅凭想象来叙述高地盖尔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而是要“栩栩如生地、形象逼真地描述那个不久前还确实存在的非凡民族”。为实现这一逼真效果,司各特从外部凝视故事发生的时空,向读者呈现一个具有强烈地理真实感的苏格兰高地世界:到处是山岩巉石的偏僻险峻,灯芯草、石楠荒草、羊齿蕨类等植被的恣意样态,让读者有种身临其境的即在感,再加上故事所涉地名莫兰河、贝维利山、乌蒙瓦高地、坎特林湖等都是真实存在且具有丰富历史典故的地理名称,这些细节鲜活地呈现出16世纪苏格兰高地原景,既满足了习惯城镇和英格兰平原生活的读者的猎奇心理,又使苏格兰读者有种空间熟悉感,同时也框定了全诗的叙事空间,即16世纪的苏格兰高地。
他这一写作策略即浪漫主义时期盛极一时的如画旅行书写。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受科技发展、农业改革、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影响,英国人旅行的目的与目的地已超越中世纪以来的宗教朝圣、地理大发现时期的探索式旅行,甚至不再局限于欧陆旅行(Grand Tour),而是致力对国内地理景观的重新发现,如画旅行应运而生。吉尔平(William Gilpin,1724—1804)的系列旅行指南,尤其是他的《散文三则:如画美、如画旅行与景观素描》(ThreeEssays:OnPicturesqueBeauty;onPicturesqueTravel;andonSketchingLandscape, 1792)则将这一新兴旅行方式推成时尚。“如画”(picturesque)作为一种关于地理景观的美学概念,推崇自然山水之美,与“优美”(beautiful)和“崇高”(sublime)并列为18—19世纪英国风景画家参悟自然的三大方式。它既不同于传统“优美”对安静祥和的强调和“崇高”对高大雄伟的追求,也与其时盛行的荷兰画派(2)荷兰画派出现于17世纪,盛行于19世纪,以细致入微观察生活所绘风俗画为典型,强调对风景、建筑物、服饰等进行静物细描,该画风被理查逊、奥斯丁等应用于小说创作之中,关注家庭内细节静物描写,呈现时代风俗画卷。对静物细节的关注迥异。如画美学理论的构建与践行者普莱斯(Uvedale Price,1747—1829)将如画的本质特征概括为粗犷、突变、不规则与复杂多样性(1796:60-62)。如画旅行者常借“克劳德之镜”(Claude Glass)——一种类似现代照相机镜头的小巧、有色凸透镜,固定凝视视角,在适当距离观赏自然景观。由于凸透镜的作用,如画风景超越日常风景,更富流动变化的色彩和引人入胜的细节,景观更旖旎曼妙,富有魅力。与此同时,由于旅行者在选择视角时具有强主观性,总是试图以最好视角在粗野自然与非规则性中寻求一种美的感官愉悦,凸透镜下的风景常常浸染着欣赏者的主观情感,充分满足浪漫主义者对自由、个性、自然等信条的追求,激发他们成为英国第一批本土旅行的践行者与书写者。司各特也是其中一员。他始终关注如画理论在文艺域的表现形式,并将如画美学基本理念揉到文学创作中(Allentuck,1973:189)。但与其他作家关注英格兰景观不同,他通过浪漫化、美化苏格兰高地,吸引英语读者关注苏格兰地理景观与文化,以提升苏格兰民族身份。
按照如画旅行的基本模式,《湖上夫人》中如画风景的主要观者是猎手詹姆斯。故事开篇,中年骑士詹姆斯策马溯河而上,在悬崖绝壁遍布的石楠荒野狩猎牡鹿,却意外迷路,误入恍如人间仙境的高地荒原。由于他是策马而行,凝视视角呈现出动态前驱之势,眼前风景由白昼日光下的青山苍穹,到夕阳西下的红霞余晖,再到夜色朦胧中的五彩旗幡……呈现出明显有别于低地平原风光的凯尔特边区(Celtic fringe)特色:幽溪静谷、巉岩峭壁、空山野洞和石楠荒野。虽说凯尔特边区“既被重构与侵占,又被排除在英国历史与政治生活之外”(Carruthers et al., 2003: 4),高地作为典型凯尔特地理景观,自然是萧瑟贫瘠的,但距离可使贫穷、荒废、衰败之地变成可赏玩的美景。如画旅行通过赋予旅行者一种间离身份(in-between)——身处地理景观但心态却超然于景观,拉大旅行者与景观的心理距离,从而避开“萧条贫困和文化差异的威胁”(Bohls, 2016: 247),使旅行者不自觉浪漫化、美化眼前景致,甚至产生异域家园的感觉,不自觉认同高地地理景观。司各特借詹姆斯如画旅行对高地的外部凝视,不仅陌生化了读者认知中贫瘠的高地景观,也使读者不自觉地接受这一美化了的自然景观。
司各特在陌生化高地自然景观的同时,又采用归化方式(domestication)书写高地人文景观。骑士策马而行不仅欣赏到了意想不到的高地曼妙自然风光,更认识了一群热情好客的高地人,了解到明显有别于低地社会的高地人文景观。野性十足的牡鹿引着低地来客进入迷人高地后便不知所踪,紧接着来客便看到淳朴善良、热情好客的高地人,诗歌呈现出一种“地理景观与原居民身份认同同行”(Pittock,2008:196)的效果。尽管延绵的大山、峡谷、悬崖、峭壁形成的贫瘠土地和稀缺生活资源迫使高地人不得不居住简陋的木屋,每天攀爬险峻山路,过着采集浆果、打鱼狩猎的原始农业生活,但他们却是最淳朴的人群,虽“不知客人的姓氏门第,/却献上待客的万般殷勤。/对陌生的客人毫无戒心”(30),使客人获得了家的安宁与熟悉,“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安宁和谐,/就像那山上缥缈的薄雾”(164)。正是通过这一近似于文化翻译的归化,旅行者詹姆斯向读者呈现了一幅既遥远又亲切的高地人文景观。他凝视视域下的被旅行者(travellees),即高地居民仿佛是生活在一个与他完全不同的、封闭的过去时空中,而他通过这场如画旅行既克服了地方与时间的辖制,也穿越人类文明之河,获得了彻底的自由。
陌生化高地自然景观带来的愉悦感和归化处理高地人文景观带来的熟悉感彻底颠覆了詹姆斯对高地人的认知。从诗歌后文可知,低地人坚信自己生活的世界充满的是骑士贵族、贵妇佳人及广大守法良民,信仰的是象征着自由、幸福和神圣的基督;而高地则是被低地流放的罪犯、叛军和不法强盗土匪聚集之所,与神的交流全部仰赖那位“倒像墓地里溜出来的德鲁伊僧侣”(87)。詹姆斯自小在这样的语境中长大,自然无法逃离对高地的偏见。然而“如画最终指向的是一种教养”(彭锋,2013:73),这趟如画旅行给詹姆斯一个真实的地方来体验和经历身体、情感和精神的自我检视与超越,使他产生再次认同自我身份的冲动,似乎高地才是他的家园。而高地人的热忱善良则使他意识到高地远不是他想象中的蛮荒之地,尤其是他在绝境处遇到那位向他施予援手的陌生高地人(他后来发现这是高地头人罗德里克)更纠正了他对高地的刻板偏见,让他了解到以往认知中野蛮、残忍、好斗的高地人其实具有极强族群归属感与荣誉感。
但为了部落,为了族人,
我不做违背荣誉的事情!
进攻一位弱者本是耻辱,
况且陌生人乃是神圣的名称;
领路、休息、食物、篝火,
陌生人的需要应该有求必应。(159)
尽管詹姆斯在言语上多番羞辱阿宾部落人,罗德里克依然如约把他安全送出高地,使詹姆斯在不自觉中赞赏、认同这个他曾认为野蛮落后的族群。当两位同样勇敢的敌手并肩卧在格子花衣襟上,“像亲兄弟一般睡得甜蜜安稳”(160),詹姆斯已放下偏见,接纳并试图像亲兄弟一样对待高地人。作为高低地相争强势一方的他主动向罗德里克求和:
你正派豁达的信义,
和我对你慷慨的感恩之情,
完全值得一种更好的报应;
非得用鲜血调节我们的不和?
别无他法?(176)
詹姆斯作为苏格兰王已经彻底改变了之前将高地人视为仇敌的态度,真正认可高地人的公民身份。从这个意义上说,詹姆斯的如画旅行不仅以如画风景打动旅行者的心灵,更对旅行者进行了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教育,正是在“漫游中我目睹法律被践踏,/漫游中我知晓要纠正冤情”(242)。因此他的如画旅行不只是一场身体的旅行,更是一场精神探索之旅。而读者随着旅行者詹姆斯的脚步似乎也获得了与他等同的社会精英身份,实现了一场身心提升的探索之旅。当然他对高地人公民身份的认可是以低地王权正统肯定为前提的,他对罗德里克的承诺已清楚表明其立场:
我用荣誉和誓言向你担保,
你将在你家乡修复你的城堡,
你将享有你现在所有的利益,
安安心心守护你的领地。(177)
由此,詹姆斯被浪漫化和美化为既有统一国土的雄心,又体恤臣下诸侯的开明君主,期望能通过给予高地人合理的公民权利,消解高地人被边缘化的他者身份,使其真正成为被认可的苏格兰公民,实现高低地的最终和解。詹姆斯在此表现出来的雄心与豁达品质一遍遍复现于司各特之后的历史小说中,成为他笔下理想君王的典范,和狮心王查理(《艾凡赫》)一样,“象征着一种强大的凝聚力,能够使国土上各个冲突的民族与阶级摒弃前嫌,紧紧地团结一起”(陈言旭,2016: 74)。
当然,尽管猎手詹姆斯随着漫游的不断深入对高地的凝视呈现出偏见→欣赏→认同→寻求和解的动态发展过程,但作为高地的意外闯入者,却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游客式的表层间离感,他看到的风景其实是他从高地贫瘠荒凉的土地中选择出来的一部分,而且是被他浪漫化与美化过的产物。与此相比,寄居罗德里克家的低地贵族少女艾伦对高地人的凝视似乎更深入内里。艾伦和父亲道格拉斯受低地王庭迫害,被迫流亡高地,幸得罗德里克收留才不至流离失所。艾伦恍若湖中仙子的出场方式让詹姆斯、也让读者误认她乃是高地少女,而且她在重返低地后,纵使身处豪华绣房,锦衣玉食,依然各种不适,总是“回想起那碧波环绕的小岛,/回想起鹿皮做成的华盖篷帐”(235),这一切无不说明她对高地地理景观与生活习惯的高度认同。但她从根本上说和詹姆斯一样,始终无法克服观光客的间离感,在评判高地人行为时表现出高人一等的文明人姿态。她眼中的罗德里克及其身后的阿宾族人虽然勇敢无畏,慷慨豁达,忠诚友善,但“当他野蛮的兽性发作,/他完全丧失了感情和人性”(54)。因此尽管高地人宣称为了自由宁可流尽部族最后一滴血,但其行为本身追根究底乃是为了复仇,而且是以血腥地洗劫低地村庄的方式实现的复仇,这样并不能真正实现族群自由,也缺乏人性的温情关怀。而且高地人只认头人不认低地国王,意味着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和低地其实是一体的,因此高地纵然在这场战争中赢了,也不过是一场高地掠夺低地财富的过程,不会实现高低地间的真正和平。艾伦对高地人的刻板认知暗示了她根深蒂固的族群偏见,而她带着国王的“承诺之戒”去低地为父亲和情人求情则表明她坚信低地政府会给自己申辩的机会,意味着她对低地国王法律效力和政府权威的认可。
正如夫勒尔所言,“旅行叙事是谁写的?这个问题至关重要”(Fowler,2016: 62)。司各特在书写詹姆斯近似于从文明闯入蛮荒的时间回溯之旅和艾伦对高地生活的深度体验时,与其他如画旅行书写一样,从发达地区返归非发达地区。虽然司各特笔下的詹姆斯浪漫化和美化了高地的自然和人文地理景观,虽然司各特没有明确评价艾伦对高地的认知,但诗人在呈现高低地普通人因战争被迫承受的凄苦,以及故事结尾处道格拉斯和艾伦的低地之行时,已明确其态度:他认同二者关于人性关怀与低地王权正统的立场,表现出以本地区文化/权力为中心的文化帝国主情怀。
2 来自如画旅行者之外的凝视
如前所述,通过呈现如画旅行者詹姆斯对苏格兰高地的外部凝视,司各特致力于向读者证明苏格兰王詹姆斯是一个“充满冒险精神、主动自发、目的纯粹、积极主动、极富好奇心的人,致力于在他地或他文化中寻找真实、确凿经历”(Kinsley,2016: 237)的旅行者,一个拥有间离身份,对世界充满包容的、“尊重差异的旅行者”(Youngs,2013: 60)。然而司各特在呈现高地人对他的反向凝视中,又向读者呈现了旅行伦理的另一端——那些被旅行者对詹姆斯的凝视判断,从而使他的身份变得扑朔迷离。
一开篇,高地人仅听到犬吠、马蹄、号角声便仿如惊弓之鸟,“快准备战斗!敌人已逼近山谷”(3),他们看到低地来客时自然对其身份产生各种惊疑揣测,误以为仇敌来袭。当低地来客面露愁容时,高地人忍不住揣测:他是“无冒险精神与好奇心的被动出游者” (Kinsley,2016: 237),因为偏离已预设好的舒适、熟悉路线而陷入困顿之中?还是如老行吟诗人阿兰伯的最坏猜测,他是被某种目的驱动的探险者(explorer),比如朝廷奸细甚或是高地仇敌?在后文全知视角的补充下读者了解到,这位来客来头不小,乃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那么读者又忍不住随着高地人的凝视目光发问:作为权势滔天的国王,他有何不如意之处?为何要跑到高地狩猎?罗德里克的答案是,詹姆斯及其贵族以狩猎为借口妄图逐鹿荒原,是充满侵略性的探险者与潜在征服者:
从梅格特草原,从亚若山岭,
从特威德河岸传来他们的哭声;
那些英勇的部落曾纵马驰骋的山谷
正变成牧场、废墟,荒野无人。
那个苏格兰王位的专制暴君
如此背信弃义,这般残酷无情,
现在他来了,他末日也将到来,
林中追猎的托词将化为泡影。
苏格兰头人能得到什么恩赐,
你们可看看边境部落的命运。(71)
罗德里克这段迅速拉近读者情感的控诉不仅削弱了艾伦对高地人品性的犀利谴责,也为高地人之前洗劫低地找到了合理借口,更为后文高地起义打下伏笔:高地人眼睁睁看着低地人洗劫他们的美丽家园,还将他们祖祖辈辈狩猎耕种的山谷变成牧场和废墟,强迫他们改变生活与生产方式,使他们的生存空间迅速萎缩,生存方式日渐式微。为寻求经济平等权,更为消解生存危机引发的民族身份认同焦虑,他们常常以反劫掠方式报复低地。罗德里克言语中流露出来的身份认同焦虑不仅是高地人的问题,也是整个苏格兰民族的问题。该时期统一的苏格兰已经形成,但与高地依然保持传统部族式生活与生产方式不同,低地在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信仰等各个方面均明显表征出“苏格兰低地的撒克逊种族化追求”(Pittock,2008: 192),低地实力迅速提升。而且低地为更好发展自身,常以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征服、掠夺高地资源,并积极努力以英格兰商业文化取代传统盖尔文化,致力于统一高地与低地的统治势力,成为苏格兰的最高统治与立法者。然而强势英格兰文化的影响在迅速提升低地实力的同时,也使低地人逐渐认同甚至自我归化为撒克逊人。司各特通过描写高地人的文化流失挣扎与低地人积极拥抱他民族归属身份,表现了他对苏格兰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
为强化高地人对低地的反向外部凝视效果,司各特还向读者呈现了高地人的自我内凝视。在积极凝视自我的高地人中,阿兰伯的民族自我内凝视最为冷静。在他看来,高地人乃是骄傲英勇、忠诚友爱的族群。这时期,由于低地人对高地人的残酷压迫、驱逐与强权统治高地人丧失了独立的政治地位,并最终沦为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然而高地人作为曾经的苏格兰主导力量,自然不甘于成为被猎杀的牡鹿。越来越深的民族生存危机感引发他们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迷茫与焦虑:高地人在苏格兰民族中处于何种位置?高地文化该如何继续成为新文化的主导或至少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消解自我迷茫与焦虑的方式是执着于过去,沉浸在一种静止的、高低地界限森然的境况,成为恪守传统苏格兰民族文化的民粹主义者,盘踞在高地边境,听从头人号令:
阿宾部落的男儿都举起刀剑;
白发苍苍的老人踊跃入列,
尽管他们的双手已拉不开弓弦;
乳臭未干的少年也应声而出,
尽管乌鸦也不怕他们开弓放箭。(110)
哪怕耗尽整个部族的最后一滴血,他们也要奋起反抗,以获取民族身份平等权。血脉相连的部族归属感使散居在各个角落的居民都承认自己是同一部落成员,并立刻放下一切事务奔聚一地。而头人罗德里克作为部族首领乃是低地人汲汲想要射猎的牡鹿之王,虽然他不无鲁莽,但为捍卫部族权益,他身先士卒,勇往直前,战死沙场,纵是弥留之际依然心系部族命运,表现出极强的血缘感和部族忠诚感。而这,是来自英格兰的士兵约翰所无法理解的。
发达的英格兰商业文化使仆人获得了个体自由,却也使人与人之间少了血脉相连的关爱与呵护。道格拉斯父女被迫流浪于高地本身便是因为低地社会的道德沦丧。在描写道格拉斯和艾伦重归低地时,司各特更是以一种优雅的反讽方式,俯视低地人庸俗势利、忘恩负义的小丑形象:
可贵族们正襟危坐国王身边,
一个个恭恭敬敬,目不斜视,
谁也没想到那位流放的勇士;
他们不会想到,尽管追猎之时,
他们曾把在他身边视为荣誉,
虽然他们在战场曾将他簇拥,
在他的盾牌后面寻求过护庇;
但他现在已失去国王的恩宠,
谁还会有心思把他记起?(194)
司各特借如画旅行者詹姆斯的外部凝视视角呈现一个原始的、近乎异域的凯尔特边缘地带——高地人的生活,使读者得以抽离逼仄现实,尽享异域的如画风景;然而此刻,他又通过全知俯视的方式引导读者重归英格兰化的低地生活,使读者清楚看到高低地人对待族群/族人、社会及世界的迥然态度,则低地人商业化的、冷漠的人际关系加倍凸显,高地人坚持古苏格兰信仰忠诚、热情好客与家族荣誉感原则的精神尤为可贵。
当然,诗人在呈现高地人的高血缘归属感同时,也通过全知俯视角向读者呈现了这场全民起义的后果:不仅没有给高地带来预期的身份平等权,反而使各行各业、不同阶级阶层家庭的青壮年故去。
是凄凉的挽歌,是女人的哭喊!
一位勇敢的猎手结束了他的追猎,
一名彪悍的武士永远放下了刀剑。
在未来的战争和狩猎之中,
谁能替他站在罗德里克身边!(100)
整个部族的生命延续受到严重威胁,民族存亡岌岌可危。因此虽然司各特赞赏罗德里克的豁达信义,却仍为他设计了被捕身亡的命运——过分尚武使他失去了与低地艾伦联姻的可能性,对高地独立的过分执念使他成为高、低地和平联合的障碍。但诗人复现惨烈战争场景并非为了使读者陷入恐慌之境。虽然战争场景惨烈异常,但诗人把故事放到16世纪的苏格兰形成的时空差却使读者既可凝视人间仙境般的高地风土人情,又可以不危及自身安全的方式身临其境地感受战争的悲惨壮烈,更以独特的情感感染力实现其政治目的:虽然反对英苏联盟的1715年和1745年高地叛乱早已过去,但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和1797年爱尔兰起义引发的思想动荡却将英苏矛盾再次摆在苏格兰人面前,诗人期望能以史为鉴,“保持与英格兰联盟乃是我们的上上之选,纵有如诺森伯兰那般沦为附庸的危险,也应首思民族之大义,万不能等出现关系破裂之时再作补救”(Davison,2000:160)。
为更好地探讨高低地关系,司各特引出高低地关系的纽带人物——道格拉斯。道格拉斯在文中出现频率不高,却是情节发展的关键:低地王庭驱逐他,高地却为他提供庇护,因而直接引发高低地战争;他重返低地并与低地王庭和解,最终使高低地停战。高地人对他的庇护使他真正深入了解高地风土人情,深切理解和同情高地居民的艰辛生活,并将他们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所以他不愿高地人也不愿任何苏格兰同胞卷入战争。
为我,开始一场无益的争端;
为我,母亲哀悼死去的儿子;
为我,妻子失去心爱的丈夫;
为我,孩子为失去父亲哭泣;
爱国者将悲叹被损害的法律,
他们将为此事诅咒道格拉斯。(199)
道格拉斯只好和女儿离开罗德里克的庇护,隐栖于尤里斯金——爱好和平的古凯尔特人曾经居住过的山洞。与此同时,尽管他受尽低地王庭贵族的冷眼,甚至被迫流亡高地,但他的祖国心始终属于低地王庭,“道格拉斯绝不会背叛朝廷,/用刀枪去对付苏格兰君王”(76)。因此他战前规劝罗德里克归顺低地,战后直奔低地,恳求低地王庭赦免罗德里克及其族人,积极促成高低地和解。道格拉斯这一国家观念归因于其出身和经历:他自幼在阿兰伯的竖琴声中长大,深受盖尔文化熏陶,同时又是低地国王的导师,不自觉地扮演起盖尔文化在高低地之间传承的媒介角色。在他看来,尽管高低地人生活地理环境不同,性格差异泾渭分明,但都传承自盖尔文化,恪守忠诚守诺、呵护弱者、能征善战的精神,乃是同宗同源的兄弟,应超越彼此偏见,重归兄弟情谊,互相认可与尊重。
司各特借道格拉斯之口提出以低地为中心,高低地互相认可与尊重的处理方式其实已初具“差异公民”雏形。所谓差异公民(Differentiated Citizenship),究其实是“既承认公民身份中的公共价值取向,又拥有族群身份的差异性”(91)。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司各特认为高低地乃是苏格兰的两个部分,应该彼此包容和认可,共同履行苏格兰公民的责任。然而正如鲍曼(2007:136)所言,每一种现存的差异都只是作为一种差异而得到永存,但若将差异理解成无差别的多元主义,就可能带来文化间的隔离乃至保卫各自文化的“圣战”,从而导致局部、地方性绝对主义的产生。司各特认为妥当处理高低地关系意味着低地不再歧视、镇压高地,高地也不再过分强调自我独特性,滋生民粹主义思想。因此,如果说罗德里克被捕身亡意味着高低地敌对关系在军事上的终结,高地人臣服于低地明君意味着二者对抗关系在政治上的终结,那么道格拉斯对兄弟情谊的强调则致力于从认知上消解高低地之间的敌对关系。据此司各特赞同这样一种国家观:以低地为中心、高低地互相包容的统一苏格兰。
倘若互文阅读诗歌文本与写作时代语境,读者又可将高低地关系看成是1707年苏英联合后其关系的时代隐喻。高地象征着苏格兰传统盖尔文化,低地则象征着新兴的英格兰商业文化,高低两地一起构成的国度从表面上看指大苏格兰民族,事实上象征着正在形成的新不列颠民族。“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亨廷顿,2005: 30)如果每个族群都只认同本族群的文化,而否定其他族群文化,那么整个社会就没有了共同的价值信念、目标追求及统一的行动准则和评价标准,自然也就无法形成统一的新民族——大不列颠民族,实现共同繁荣发展。因此在司各特看来,“民族主义诉求与联盟话语并不冲突,而是处于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复杂和动态平衡关系之中”(张秀丽, 2017:138)。在这一新不列颠民族中,苏格兰与英格兰人之间只存在居住地域的不同,而不存在平等与否的问题,遵从着有别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差异性民族文化观,即高低地间以英格兰为中心、苏格兰为衬托的兄弟关系,两个兄弟民族互相融合,形成统一的文化和大民族。来自低地的艾伦与高地青年马尔科姆的联姻便是英苏民族融合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艾伦被迫流浪于高地本身便是低地英格兰化社会道德沦丧的隐喻,而高地勇士马尔科姆身上的善良、正直和英勇恰好提供了艾伦渴望的道德拯救,二者的联姻意味着苏格兰传统文化对低地商业社会的精神救赎。但他们的联姻乃是基于低地国王宽容的恩准,意味着联合王国必然是以低地或英格兰为中心的,因为“英格兰民族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加同情一个高尚的敌对民族的不幸”(1)。当然苏格兰人要想在新不列颠民族中获得身份认同也应通过保存独特地理景观与盖尔血缘文化等方式确保本民族身份的独立性。司各特这一映射英苏联合政治隐喻的联姻方式成为他后来历史小说的范本,一遍遍述说着他对大不列颠国家政治体制的认同。
在此基础上,诗人通过呈现高低地人对经济文化模式的不同认知,表达了他对国家统一经济文化模式的美好愿望。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使英国中产阶级人数剧增,再加上启蒙运动对知识与世界的孜孜追求使18—19世纪之交的英国涌现出一批充满冒险精神、好奇心并向往异域文化的旅行者。然而法国大革命及由此引发的欧洲大小战争截断了英国人传统的欧陆游学之路。与此同时,国内工业革命使交通运输业飞速发展,国内旅行更加便捷和安全。因此,到北英格兰湖区、威尔士、苏格兰高地等英格兰东南部之外的“异域”旅行成为一种风尚。通过这些旅行,旅行者既可获得视觉愉悦,又能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旅行地获得一种身份提升的超然感,从而反向认同自己熟悉的(工业化)经济文化生活。诗歌一开篇对高地地理景观的描写表明,虽然荒原高山的雄奇峻美能激起游客的视觉愉悦,但于本地人而言也意味着贫穷与艰辛,而这二者恰是滋生焦躁偏执心理和闭目塞听行为的温床。同时,虽说“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权要求该社会保证每个人都能获得恰当的肯认”(汤云,2017: 98),但作为苏格兰文化源头,高地盖尔文化已被苏格兰文化边缘化,高地人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出现空前危机,变得焦躁偏执,闭目塞听,最终形成极端民粹主义。与之相反,以詹姆斯为首的低地人居住在舒适的城堡,过着体面、文明、幸福的生活,更易于形成平和、包容、反战的心理,接受先进思想,包容高地的不足,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高低地矛盾,实现国家统一。正是通过对比苏格兰传统高地的荒凉贫瘠和动荡不安与英格兰低地的安稳有序和繁荣富庶,司各特认同了休谟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观点:1707年英苏联合前的苏格兰没有一个法治的自由政府,而是一个野蛮暴力民族的代表,而英格兰则代表了先进文明的方向。据此,司各特从经济文化角度进一步强化英苏国家共同体的价值,认同以英格兰为主导的新不列颠民族国家,间接证明工业革命终将推动社会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司各特不是保守主义者,而是和平的激进主义者。
简言之,司各特以一场如画旅行为开端,通过呈现低地来客对高地的间离式凝视、高地人对低地人的反向凝视及其自我民族内凝视以及全知俯视,向读者再现一幅巴赫金式16世纪苏格兰地理景观图,重述高低地间征战与和解的历史,阐释其对高低地人的认知:高地人作为苏格兰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固然淳朴爱国,却也狭隘偏激,而低地人虽然冷漠势利,却也是进步文明的代表。但与同时代作家休姆(David Hume,1711—1776)将苏格兰分成有远见、热爱和平、商业化、积极建立不列颠民族的日耳曼低地和满是落后、暴力、懒惰的造反派分子的凯尔特高地不同,司各特认为高低地人虽然看似差异巨大,其实都是同根同源的盖尔人后裔。因此,不同凝视者所观的图景其实是统一于王权之下的苏格兰(不列颠)锦绣河山的不同部分;詹姆斯与其说是高地的闯入者,不如说是自己国土的欣赏者。为共建一个更好的不列颠王国,高低地双方(英苏两王国)需要互相理解与尊重,并针对各自缺陷做出有效改变,达成互相包容的和解。
3 结语
如前所述,司各特通过呈现苏格兰王詹姆斯在高地如画旅行的所见所闻、流亡高地的低地贵族少女艾伦对高地生活的深入凝视、高地人对低地人的反向凝视和对民族命运的自我内凝视,流露出对苏格兰传统文化的深深依恋;通过全知俯视和高低地文化传承的纽带道格拉斯从大苏格兰角度凝视苏格兰民族命运,更呈现了他对高低地关系的思索。尽管高低地边界依然在,詹姆斯的意外高地旅行却打破了高低地文化间隔离,而艾伦与马尔科姆的联姻及道格拉斯明显的政治联合主义表征则提供了一种司各特式的高低地关系处理方式:以低地为中心,高低地实现互相包容的和解。
司各特这一民族观的时代意义在于,他建构的苏格兰文化记忆是在英格兰-苏格兰联盟话语框架之下的文化记忆,其目的并非寻求苏格兰的政治独立,而是在政治统一框架下寻求苏格兰文化的独特性。他所致力的是历史与现实的和解,并最终建构一个具有极强文化包容性的统一民族:不列颠民族。众所周知,“七天”在基督教文化中意义非凡。《湖上夫人》总共六章,每一章叙述一天的故事,是否意味着给苏格兰/不列颠民族的未来留白一个诗章?在诗歌沉默留白处,读者不仅可以看到诗人对和解后的世界的积极期待,更可依据前文描绘润色未来,补一而实现“七”这一象征永恒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