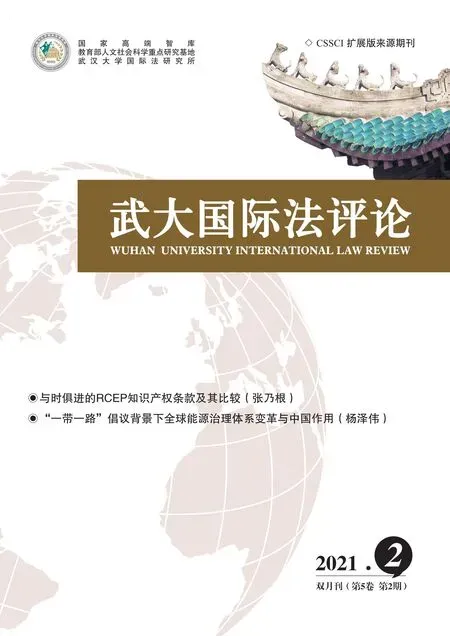“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作用
杨泽伟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①习近平:《顺应时代潮流 实现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7月26日,第2版。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在过去几十年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导致全球石油需求大幅震荡,未来全球能源格局充满不确定性。“一带一路”沿线有不少国家能源资源丰富,国际能源合作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研究“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问题,探讨中国在此变革进程中的作用,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主要特点
当今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主要有以下四大特点:
(一)全球能源版图正在重塑
1.美国能源政策大幅调整,成为了重要的能源出口国。2020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明确指出,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①See White House,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i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4,February 2020,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state-u nion-address-3/,visited on 20 November 2020.由于增产页岩油气,近年来美国油气产量不断攀升。特别是特朗普上台后,对美国的能源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例如,2017年1月美国政府发布了《美国优先能源计划》,提出将致力于降低管制、促进能源发展、实现能源独立。2017年4月《关于实施美国离岸能源战略的总统行政令》(Presidential Executive Order on Implementing An America-First Offshore Energy Strategy),扩大了美国离岸能源开采范围。2018年1月,美国内政部公布了《2019—2024年国家外大陆架油气开发租赁计划草案》(2019—2024 National Outer Continental Shelf Oil and Gas Leasing Draft Proposal Program),建议向油气开采业开放美国超过90%的外大陆架区域。②See Bureau of Ocean Energy Management,2019-2024 National Outer Continental Shelf Oil and Gas Leasing Draft Proposal Program,https://www.boem.gov/NP-Draft-Proposal-Program-2019-2024,visited on 20 November 2020.此外,2018年,美国能源部长里克·佩里提出“能源新现实主义”,阐释了要高效清洁地开采能源、简化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程序、推动能源大规模出口的长期愿景。③参见宋亦明:《重塑国际能源版图:急速扩张的美国能源出口》,《世界知识》2018年第12期,第54页。在上述种种政策措施的推动下,2018年底美国成为了石油净出口国。总之,美国借助能源政策成为了石油、天然气的重要出口国,从而使国际能源市场的供需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标志着国际油气市场进入了新时代。
2.发达国家石油消费显著下降、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能源贸易的主要参与者。据统计,197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称“经合组织”)石油消费总量为4130.3万桶/天,占全世界的74.25%;2018年为4870万桶/天,占比下降到49.12%。同期,非经合组织国家在世界石油消费中的比重由25.75%上升到51.8%,占了半壁江山。其中,中国和印度的石油消费增长最快,由1973年的153.2万桶/天上升到2018年的1789万桶/天,增长了11.68倍,所占比重从2.75%增长到18.04%。①参见王能全:《全球石油治理需要新思维》,《财经》2019年第5期,第103页。
3.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是近年来全球能源治理体系面临的最具深远意义的变化之一。②See Bo Kong,Governing China’s Energ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Governance,2 Global Policy 63(2011).近年来,中国石油、天然气消费对外依存度持续加大。2017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原油进口国。2018年中国天然气进口持续高速增长,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天然气进口国。根据中石油发布的《2018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2018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上升至69.8%,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则上升至45.3%;③参见中国石油新闻中心:《〈2018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发布》,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9/01/18/001717430.shtml,2020年11月20日访问。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能源前景2018—2050》报告,到2050年虽然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仍能控制在70%左右,但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却会上升至78.5%。④参见刘冬:《中阿能源合作趋于立体化》,《世界知识》2019年第17期,第16页。
(二)传统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纷纷转型
1.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正式启动了“联盟计划”(Activation of IEA Association)。众所周知,1974年成立的国际能源署是与经合组织相联系的石油消费国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其成员国仅限于经合组织的成员。国际能源署主要通过建立“应急机制”“国际石油市场的情报系统”“与石油公司的协商机制”以及实施“长期的能源合作计划”来保障成员国的石油供应安全。⑤参见杨泽伟:《中国能源安全法律保障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6-59页。2013年,国际能源署部长级会议发表了联合声明,提出将以联盟国参与国际能源署的各类常设小组会议及部长级会议的方式,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与联盟成员国提供共同的对话平台。2015年11月在巴黎部长级会议上,国际能源署与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宣布启动国际能源署“联盟计划”。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成为第一批联盟国。“联盟计划”赋予联盟国参与国际能源署的会议、培训与能力建设以及能源效益计划等方面的权利。“联盟计划”不但标志着国际能源署与联盟国在能源安全、能源数据与统计以及能源政策分析三个共享领域开启了进一步合作的新时代,而且是国际能源署转变为“一个真正的全球能源组织的第一步”①杨玉峰、[英]尼尔·赫斯特:《全球能源治理改革与中国的参与》,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
2.《能源宪章条约》(Energy Charter Treaty)开启了改革和现代化进程。《能源宪章条约》是唯一的、专门针对能源领域的多边条约。1998年4月,《能源宪章条约》正式生效。《能源宪章条约》旨在为国际能源安全提供普遍的规则,其规制内容涵盖了能源投资、能源贸易、能源过境、能源效率和能源争端解决等。②参见白中红:《〈能源宪章条约〉争端解决机制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1页。《能源宪章条约》还设立了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能源宪章会议”(Energy Charter Conference)。2004年《能源宪章条约》大会设立了工业咨询小组,以建立能源宪章会议及其不同工作组的咨询性平台,从而为能源投资、跨境运输和能源效率相关的问题提供建议。2009年《能源宪章条约》开始推进现代化改革进程,以应对新的挑战,并吸收更多的国家参与。2012年《能源宪章条约》采取巩固、扩大和推广的政策,以将《能源宪章条约》的原则向全球推广。
(三)全球能源治理的新平台不断涌现
近年来,出现了不少与全球能源治理相关的国际机构,如二十国集团(Group of Twenty,以下称G20)、国际能源论坛、清洁能源部长会议等。
1.G20。G20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机构,虽然主要关注经济和金融问题,但是早在2005年G20峰会就开展了“清洁能源、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对话。2009年,G20领导人共同承诺在中期消除化石能源补贴。特别是2014年11月通过的《G20能源合作原则》(G20 Principles on Energy Collaboration),呼吁国际能源机构承担更有代表性和包容性的角色,G20能源工作组的作用得到了增强,G20能源部长级会晤也成为常态。
2.国际能源论坛(International Energy Forum,IEF)。1991年成立的国际能源论坛,是目前综合性最强、成员国最多的国际能源机构。③国际能源论坛有70个成员国,涵盖了全球约90%的石油、天然气供应和消费。参见国际能源论坛网站,https://www.ief.org/about-ief/organisation/member-countries.aspx,2020年11月20日访问。其主要职能是以中立的身份促进成员国之间开展非正式、公开和可持续的全球能源对话,通过联合石油倡议协调能源数据的收集,增进成员国对共同能源利益的理解,提高能源市场的透明度和稳定性等。
3.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Clean Energy Ministerial,CEM)。2010年成立的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是一个高级别的全球论坛,旨在通过政策和项目的形式促进清洁能源技术的应用,其成员国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75%和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的90%,截至2020年2月有28个成员国。①参见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网站,https://www.cleanenergyministerial.org/initiatives,2020年11月20日访问。近年来,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推出了多项倡议,如电动汽车倡议、全球超级能源合作、生物质能源工作组、可持续水电发展倡议、女性清洁能源教育授权倡议和国际智能电网行动网络等。
此外,亚太经合组织②亚太经合组织专门设立了能源工作组,具有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能力。、上海合作组织③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被认为是“亚洲能源合作最具潜力的组织之一”。2005年,上海合作组织就提出了建立“能源俱乐部”的构想。2013年,中俄两国领导人再次呼吁成立“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金砖五国④金砖五国将能源确立为一个合作领域。因此,有学者认为金砖五国将在未来全球能源治理中发挥较大作用。See Navroz K.Dubash,From Norm Taker to Norm Maker?Indian Energy Governance in Global Context,2 Global Policy 7(2011).、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世界能源理事会、全球碳捕获与封存机构、国际能效合作伙伴关系、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机构,均为全球能源治理提供了方案或合作项目等方面的支持。⑤参见杨玉峰、[英]尼尔·赫斯特:《全球能源治理改革与中国的参与》,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四)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仍然面临多重挑战
当今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仍然面临多重的、复杂的和前所未有的挑战。⑥See Aleh Cherp,Jessica Jewell&Andreas Goldthau,Governing Global Energy:Systems,Transitions,Complexity,2 Global Policy 75(2011).
1.能源贫困问题仍然存在。虽然2015年第70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目标7专门强调:“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⑦UN,A/RES/70/1.,但是目前全球仍有13亿人用不上电,有26亿人炊事用能依然采用传统生物质能。⑧参见杨玉峰、[英]尼尔·赫斯特:《全球能源治理改革与中国的参与》,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页。有专家预测,即使到了2030年可能还有14亿人无法享受现代的能源服务。①See Ann Florini&Benjamin Sovacool,Bridging the Gaps in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17 Global Governance 68(2011);Aleh Cherp,Jessica Jewell&Andreas Goldthau,Governing Global Energy:Systems,Transitions,Complexity,2 Global Policy 75(2011);Navroz K.Dubash&Ann Florini,Mapping Global Governance,2 Global Policy 9(2011).
2.中东等能源生产地区恐怖主义的威胁并未消除。一方面,虽然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收复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控制的全部领土,但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并未彻底消灭,仍然对中东地区的油气生产构成威胁。另一方面,2019年9月沙特阿拉伯石油生产设施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无人机袭击,使沙特阿拉伯原油供应每日减少570万桶,这一数字约占沙特阿拉伯石油日产量的50%和全球石油日供应量的5%。可见,全球能源生产仍然面临多种多样的恐怖主义威胁。
3.能源供应与使用的方式亟待改变。诚如有学者所言,全球能源体系在21世纪发生的第一重大变革是非常规石油与天然气开采量的爆发式增长。②参见吴磊、曹峰毓:《论世界能源体系的双重变革与中国的能源转型》,《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3期,第37页。然而,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挑战。况且,世界各国要想共同完成2°C的气候目标,改变能源供应与使用的方式、发展低碳技术尤为重要。遗憾的是,虽然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国际公约,但是没有一个国际机构在切实推动能源低碳政策的发展与落实。③参见杨玉峰、[英]尼尔·赫斯特:《全球能源治理改革与中国的参与》,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3页。
综上可见,近些年全球能源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变革已经悄然开始。
二、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主要缺陷
(一)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滞后性比较突出
目前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缺乏包容性,滞后性较为明显。④See David G.Victor&Linda Yueh,The New Energy Order:Managing Insecuriti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89 Foreign Affairs 61-73(2010).
1.国际能源署等传统国际能源机构的法律制度较为陈旧。众所周知,目前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例如,成立于1960年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曾经是“最具影响力的石油生产国组织”①杨泽伟:《国际能源秩序的变革:国际法的作用与中国的角色定位》,《东方法学》2013年第4期,第88页。。然而,当今美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已成为国际石油出口市场的三大巨头。因此,随着卡塔尔于2019年1月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②参见石油输出国组织网站,https://www.opec.org/opec_web/en/about_us/25.htm,2020年11月20日访问。石油输出国组织已风光不再,仅靠其成员国的“配额政策和价格政策已经不足以解决当前能源市场的震荡”③杨玉峰、[英]尼尔·赫斯特:《全球能源治理改革与中国的参与》,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7页。。又如,国际能源署“作为石油消费国应对能源危机的集体机制”④William Martin&Evan Harrje,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n Jan Kallicki&David Goldwyn(eds.),Energy and Security:Toward a New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98(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然而,国际能源署的成员国政策一直都比较保守。国际能源署的基本法律文件——《国际能源纲领协议》(Agreement on an International Energy Program)第71条第1款明确规定:“此协议应对能够并愿意满足本纲领要求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任何成员国开放加入。”可见,国际能源署把成员国的范围严格限定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从而排除了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能源署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难断言:国际能源署“既不期望、也不认为有必要将其成员范围扩大到这些发达石油消费国以外”⑤肖兴利:《国际能源机构能源安全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
综上可见,无论是石油输出国组织还是国际能源署,这些传统的国际能源机构的法律制度的确存在不少与当今国际能源格局不相适应的地方。
2.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如上所述,当今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主要由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主导,既不包括,也无法代表新兴经济体。例如,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国,既不是国际能源署的成员国,也没有加入《能源宪章条约》。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的这种弱势地位,无疑降低了目前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有效性。
(二)全球能源治理机构之间的协调性明显不足
目前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缺乏一个权威性、专门性的全球能源协调机构。①See Aleh Cherp,Jessica Jewell&Andreas Goldthau,Governing Global Energy:Systems,Transitions,Complexity,2 Global Policy 75-87(2011);Navroz K.Dubash&Ann Florini,Mapping Global Governance,2 Global Policy 11(2011).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虽然国家间能源相互依存日益增强,但是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仍缺乏一个中心权威来协调能源政策。”②Leonardo Baccini et al.,Global Energy Governance:Trade,Infrastructure,and the Diffusion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https://core.ac.uk/reader/35435620,visited on 20 November 2020.当今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碎片化现象,③See Navroz K.Dubash&Ann Florini,Mapping Global Governance,2 Global Policy 6-18(2011).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代表的能源生产国与以国际能源署为代表的能源消费国之间的对立仍然存在,双方合作的障碍并未完全消除。虽然国际能源论坛的成员国囊括了能源生产国和能源消费国,但是国际能源论坛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和影响仍然有限。因此,兼顾能源生产国和能源消费国共同利益的全球性能源治理组织尚未建立。
第二,能源问题虽然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等国际机构的重要议题,但显然不是上述国际机构的工作重心和主要任务。
第三,传统的能源治理主要是各个主权国家按照煤炭、石油、天然气、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等能源治理的客体和类别来分别进行的。④See Navroz K.Dubash&Ann Florini,Mapping Global Governance,2 Global Policy 7(2011).况且,现存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不但职能相互重叠,而且治理的对象也主要局限于传统的化石能源。⑤See Navroz K.Dubash&Ann Florini,Mapping Global Governance,2 Global Policy 15(2011).
(三)全球能源治理规则的硬约束有待增强
一谈到“全球能源治理”,人们就会马上联想到“全球总督”(global governor)甚至“全球政府”(global government)——一个能够制定规则并能强制实施规则的机关。①See Ann Florini,The Peculiar Politics of Energy,26 Ethics&International Affairs 300(2012).然而,目前国际社会的现实是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不但缺乏普遍性的国际法规则,而且有关规则是以软约束为主。
1.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有关的多边条约较少、普遍性和影响力不足。如上所述,学者们一般认为:“《能源宪章条约》是目前能源领域唯一的多边条约。”②白中红:《〈能源宪章条约〉争端解决机制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然而,迄今包括欧盟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在内,只有53个缔约方批准了该条约。③参见《能源宪章条约》网站,https://www.energycharter.org/process/energy-charter-treaty-1994/energy-charter-treaty/,2020年11月20日访问。这说明该条约在国际社会近200个国家中缺乏足够的认同。况且,目前只有61个国际仲裁案是以《能源宪章条约》为主要依据的,这也说明该条约的影响力比较有限。④参见马妍:《全球能源治理变局:挑战与改革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1期,第60页。又如,在能源消费领域发挥一定作用的国际能源署,目前也只有30个成员国。⑤参见国际能源署网站,https://www.iea.org/countries,2020年11月20日访问。
2.全球能源治理新平台的相关决议仅具建议性质。例如,国际能源论坛主要是一个政府间的协调机构,其基本目标是“增进成员国对共同能源利益的理解和意识”⑥See International Energy Forum Charter,https://www.ief.org/about-ief/ief-charter.aspx,visited on 20 November 2020.,因而其职能主要是为各成员国提供交换意见、建立高层联系的平台,而不是制定政策,更没有权力给成员国施加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又如,2015年由《能源宪章条约》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国际能源宪章》(International Energy Charter)是对支持国际贸易和资源获取、增加能源领域国际投资的政治声明,也没有法律约束力。⑦参见《能源宪章条约》网站,https://www.energycharter.org/process/international-energy-charter-2015/overview/,2020年11月20日访问。
三、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变革
(一)加快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
如上所述,当今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没有准确反映世界能源形势的变化,因而应当加速推进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诚如国际能源署前署长诺波尔·塔纳卡(Nobuo Tanaka)所言,国际能源署要想继续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发挥关键作用,除了改革别无他途,因为研究表明从2006年到2030年,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87%来源于非经合组织国家,非经合组织国家在世界能源需求中的份额也将从51%增长到62%。①See Ann Florini,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n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2 Global Policy 48(2011).
因此,就国际能源署的现代化进程来说,首先,应该修改国际能源署的《国际能源纲领协议》,改变其成员国身份仅对经合组织国家开放的条约限制。其次,修改国际能源署特殊的表决程序,②参见肖兴利:《国际能源机构能源安全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2-105页。提高其决策机制的效率。最后,国际能源署还应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印度等主要石油消费大国的联系。③See Ann Florini,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n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2 Global Policy 40(2011),.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9月,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Fatih Birol)在访问中国时明确提出:“中国和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不仅要成为国际能源署的合作伙伴,更要参与到国际能源署的工作中来”,“推动国际能源署的现代化,使其发展为真正的国际能源机构”④杨玉峰、[英]尼尔·赫斯特:《全球能源治理改革与中国的参与》,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8页。。有学者也认为,中国国家能源局油气司副司长被任命为国际能源署高级顾问并在国际能源署工作,是国际能源署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标志性的重要一步”⑤杨玉峰、[英]尼尔·赫斯特:《全球能源治理改革与中国的参与》,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
(二)进一步加强国际能源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1.继续挖掘国际能源论坛的协调作用。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国际能源署就逐渐与石油输出国组织开展合作,双方不但签署了一项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而且成立了联合工作组进行共享数据等方面的工作。⑥See Ann Florini,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n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2 Global Policy 46(2011).有鉴于此,国际能源论坛作为政府间协调机构,自成立以来就已经促成了多项国际能源署与石油输出国组织间的合作项目,如建立联合石油倡议全球性数据库等。今后把这一数据库扩展到天然气、煤炭以及其他能源领域,应该是其发展的重要方向。因此,由国际能源论坛、国际能源署和石油输出国组织三个组织的秘书处开展联合行动,被认为是弥补当前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协调性不足的一项务实方案。①参见杨玉峰、[英]尼尔·赫斯特:《全球能源治理改革与中国的参与》,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6页。
2.充分发挥G20在能源领域的协调功能。一方面,G20自从关注“能源问题”议题以来,达成了诸多共识,特别是2014年布里斯班峰会通过的《G20能源合作原则》明确提出了“加强国际能源机构之间的协调,尽量最大程度减少各机构功能重复的现象”,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出席G20峰会的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影响力较大。特别是在G20机制中,存在被一些学者称之为“高权威性行为体”(high-status actors)②See Richard W.Mansbach&John A.Vasquez,In Search of Theory:A New Paradigm for Global Politics 96(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的国家,能够把有关全球能源治理议题纳入到G20议程中。此外,G20包括了世界主要石油消费国和生产国。2017年,G20国家占世界石油消费约80%和世界石油产量约60%;G20国家间石油互供,自给率为73.5%。③参见王能全:《全球石油治理需要新思维》,《财经》2019年第5期,第107页。事实上,近年来G20在提高能源效率和开发新能源技术等方面的能源治理作用较为突出。④参见刘宏松、项南月:《二十国集团与全球能源治理》,《国际展望》2015年第6期,第129页。因此,可以设立G20能源问题常设工作组,以更好地发挥G20在能源领域的协调功能。
(三)提高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国际法规则的普遍效力
1.增强《能源宪章条约》成员国的普遍性。其实,《能源宪章条约》一直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它源于1990年荷兰首相鲁德·吕贝尔斯(Ruud Lubbers)的一项政治动议(political initiative)和1991年《欧洲能源宪章》。《能源宪章条约》体系还包括1994年《能源效率和相关环境问题议定书》、1998年《能源宪章条约贸易条款修正案》、1999年《政府间跨国管道运输示范协议》、2003年《过境议定书(草案)》和2007《东道国政府与项目投资者之间的跨国管道运输示范协议》。2009年能源宪章开始推进现代化改革进程,并在2010年出炉了“能源宪章现代化政策的路线图”(Road Map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Energy Charter Process)。2012年还通过了“能源宪章关于巩固、扩大和推广的政策”(Energy Charter Policy on Consolidation,Expansion and Outreach)。①See Energy Charter Treaty,The Energy Charter Process,https://www.energycharter.org/process/overview/,visited on 20 November 2020.鉴于《能源宪章条约》目前已经得到欧亚大陆50多个国家的批准,成员国涵盖的地理范围广,因而进一步增强《能源宪章条约》成员国的普遍性、促进其向全世界参加国最多的国际能源多边条约发展,是其必然的趋势。
2.推动国际能源宪章由政治宣言向国际条约的转变。国际能源宪章的序言明确提出其“最终目标是扩大《能源宪章条约》和程序的地理范围”。因此,进一步推动国际能源宪章向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转变,既是《能源宪章条约》现代化的重要步骤,也是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完善的必然要求。
3.赋予全球能源治理新平台相关决议以约束力。尽管诸如国际能源论坛将自身定位为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其有关决议仅具建议性质。然而,鉴于国际能源论坛等全球能源治理新平台成员国较大的普遍性,赋予其相关决议具有法律约束力,无疑有助于进一步发挥此类平台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作用。
(四)充分发挥能源领域行业协会的作用
能源领域的行业协会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②See Navroz K.Dubash&Ann Florini,Mapping Global Governance,2 Global Policy 12(2011);Benjamin Sovacool et al.,Energy Governance,Transnational Rules,and the Resource Curse:Explo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83 World Development 179(2016).因为要实现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目标,能源领域行业协会之间的国际合作不可或缺。因此,重视诸如世界能源理事会、世界石油理事会、国际天然气联盟、世界能源协会、世界煤炭协会、国际水电协会、世界风能协会、世界核协会、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国际能源经济协会等能源行业协会的作用,是完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
四、“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中的作用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全球第一大天然气进口国”“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当进一步发挥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中的作用。
(一)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7年多来,取得了重要进展。在此基础上,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既有现实基础,也有法律保障,同时也是完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重要步骤。
1.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的现实基础
(1) “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能源资源丰富。据学者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油气剩余探明储量分别为1338亿吨、155万亿立方米,分别占世界剩余探明总储量的57%和78%,集中了俄罗斯、中亚及中东地区的重要油气资源国。①参见张翼:《“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呼之欲出》,《光明日报》2017年6月5日,第1版。
(2)能源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中,油气比重高、数额大。例如,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中缅油气管道、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②2019年12月2日,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它是全球能源领域最大的投资项目,合同金额为4000亿美元。该管道起自俄罗斯东西伯利亚,由布拉戈维申斯克进入中国黑龙江黑河。其中,俄境内管道全长约3000公里,中国国境内段新建管道3371公里,利用已建管道1740公里;每年输气380亿立方米。参见杨进:《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意义重大》,《世界知识》2019年第24期,第57页。等中国陆上跨国油气管道,已连接中亚国家、俄罗斯、缅甸等油气资源国与过境国。此外,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中沙延布炼化基地等重大项目,也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合作的典范。
(3)现有的多双边能源合作机制,为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提供了组织基础。一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联合国、G20、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国东盟、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亚洲合作对话、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国—阿盟、中国—海合会等多边框架下开展了广泛的能源合作。另一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在实施中国—东盟清洁能源能力建设计划,推动建设中国—阿盟清洁能源中心和中国—中东欧能源项目对话与合作中心等。③参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源合作愿景与行动》,https://www.yidaiyilu.gov.cn/zchj/qwfb/13745.htm,2020年11月20日访问。因此,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在上述多边双边能源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不言而喻,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将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向更深更广发展。
此外,截至2021年1月底,中国已累计同140个国家、31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5份政府间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①参见中国一带一路网:《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77298.htm,2021年3月31日访问。这不但说明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可,而且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2.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的法律保障
(1)中国政府出台的有关“一带一路”法律文件,为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提供了法律原则和行动指南。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年3月28日)、《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2017年5月10日)、《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源合作愿景与行动》(2017年5月16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2019年4月22日)等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文件。上述法律文件特别是《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源合作愿景与行动》,不但明确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的法律原则,如坚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而且指出了合作的重点领域,如加强能源产能合作、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
(2) “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设立,为呼之欲出的“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提供了“牙齿”。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了国际商事法庭,负责审理当事人之间的跨境商事纠纷案件。②参见2018年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既是中国建立符合现代国际法的“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有益尝试,也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提供了解决争端的法律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4月“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在北京正式成立,伙伴关系成员国共同对外发布了《“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合作原则与务实行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的重要一步。③截至2020年1月,“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成员国总数已经达到30个,包括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玻利维亚、柬埔寨、佛得角、乍得、中国、东帝汶、赤道几内亚、冈比亚、匈牙利、伊拉克、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马耳他、蒙古、缅甸、尼泊尔、尼日尔、巴基斯坦、刚果(布)、塞尔维亚、苏丹、苏里南、塔吉克斯坦、汤加、土耳其及委内瑞拉。
(二)积极为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毋庸讳言,中国是当今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新兴参与者和“跟跑者”。然而,早在2008年中国国家领导人就在国际能源会议上首次阐述了“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全球能源安全观”。2012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沟通与合作。”①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能源政策(2012)》白皮书,http://www.gov.cn/jrzg/2012-10/24/content_2250377.htm,2020年11月20日访问。2017年,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0页。因此,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为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提供平台,积极为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既是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需要,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重要体现。
1.充分发挥“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的作用。2016年3月,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Global Energy Interconnection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在中国北京正式成立。③详见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网站,https://www.geidco.org/overview/,2020年11月20日访问。它是为落实全球能源互联网倡议、由中国在能源领域成立的首个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已成为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和国际多边合作的重要平台。如今,全球能源互联网已成为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2018年以来,“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提出全球能源互联网“九横九纵”骨干网架和各大洲能源互联网构建思路,发布了《全球能源互联网骨干网架研究报告》《“一带一路”能源互联网研究报告》以及各大洲区域能源互联网规划,为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提供了顶层设计和行动路线图。④参见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网站,https://www.geidco.org/overview/,2020年11月20日访问。今后,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应在理念传播、战略规划、标准制定、资源支持和项目开发等领域继续发挥引领作用,为全球能源转型提供中国方案。
2.共同构建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一方面,中国应向世界展示在新能源开发和利用方面的成就,⑤目前全球大约60%的太阳能电池产自中国。分享在新能源开发和利用方面有关法律政策的成功举措。据统计,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已经连续第七年全球领先,2018年能源投资占全球能源总投资的32%,投资规模达到912亿美元。①See UN Environment Programme,Global Trends in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2019,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resources/report/global-trends-renewable-energy-investment-2019,visited on 20 November 2020.事实上,中国在新能源开发和利用方面的成就和经验,已经逐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例如,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表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和融资在全球领先,且已完成或超过了自身设定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帕特里夏·埃斯皮诺萨(Patricia Espinosa)也曾经明确指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正在努力减少排放,使其成为清洁技术的领导者,真正能够与世界不同国家分享他们的良好经验”②参见黄惠康:《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278页。。另一方面,中国还应进一步加强与有关新能源国际机构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促进新能源知识产权制度的合理应用,消除贸易壁垒,降低新能源技术的利用成本,以实现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11月由中国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所属上海电力与马耳他政府携手在黑山共建的新能源项目——黑山莫祖拉风电站正式投入运营。③黑山莫祖拉风电站总装机容量为46兆瓦,于2017年11月开始施工。该风电站每年可提供超过1.12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为黑山以清洁能源为基础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这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能源合作、推进能源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尝试和成果之一。此外,2019年12月由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建)投资开发的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牧牛山风电项目,举行首批风机并网发电仪式。④牧牛山风电项目位于塔斯马尼亚州中央高地,总投资约3.3亿澳元(约合15亿元人民币)。项目总装机容量148.4兆瓦,通过4公里220千伏输电线路与澳国家电网连接,投产后年均上网发电量约4.4亿度,可为超过6万个家庭提供优质清洁能源,并可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该项目说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新能源合作,大有可为。
3.“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下设“天然气国际论坛”。鉴于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未来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还将继续攀升,因而中国可倡导发起成立“天然气国际论坛”,作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的组成部分。成员可以包括重要的天然气生产国和天然气消费国以及相关的国际组织。“天然气国际论坛”可以就天然气数据收集与分享、市场预测、天然气管道运输安全以及争端解决等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
此外,2016年11月26日,中国国家级能源交易平台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正式投入运行。2018年3月26日,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原油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正式上市交易。上述举措,不仅将对英国布伦特原油期货和美国西得克萨斯中间基原油期货形成竞争之势,①参见《日本经济新闻》:《原油美元霸权被打开缺口》,转引自《参考消息》2018年3月28日,第14版。而且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迈出的重要步伐,有利于提升中国在油气价格领域的话语权。
五、结论
(一)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始终受到地缘政治的困扰
能源是关系到各国国计民生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始终受到地缘政治的困扰。②See Ann Florini&Benjamin Sovacool,Bridging the Gaps in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17 Global Governance 59(2011).一方面,从历史上看,作为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能源署,它的产生就是为了应对埃及和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第四次中东战争而引发的第一次全球性的石油危机。另一方面,就现实情况而言,能源资源的竞争、核不扩散制度的分歧、恐怖主义活动对能源基础设施的威胁等,③See Ann Florini&Benjamin Sovacool,Bridging the Gaps in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17 Global Governance 58(2011).无不体现全球复杂的能源地缘政治的影响。此外,俄罗斯与土耳其两国重点能源合作项目“土耳其流”天然气管道,既是乌克兰危机直接催生的结果,更折射了地缘政治的变化。而俄罗斯和欧洲国家合作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之所以一直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不但是因为美国希望欧洲国家购买本国的天然气,而且也有美国与俄罗斯进行战略竞争博弈的考量。
(二)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如上所述,能源问题与主权国家的战略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不但存在以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代表的石油生产国和以国际能源署为代表的石油消费国之间的对立,而且在国际能源机构内部各成员国之间围绕该机构的性质、合作领域、决策机制、权利义务以及争端解决等制度因素也产生分歧。这种对立与分歧,既是造成目前各个国际能源组织成员国的普遍性不如联合国体系的国际组织的原因,也是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变革比较缓慢的重要因素。因此,不难断言,无论是《能源宪章条约》的现代化进程,还是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三)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变革应秉持“能源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和努力方向。“能源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秉持“能源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实现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目标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的根本要求。一方面,能源安全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目标是保障安全、稳定和可持续的全球能源体系,协助各国政府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目标。①参见杨玉峰、[英]尼尔·赫斯特:《全球能源治理改革与中国的参与》,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4页。另一方面,“能源命运共同体”彰显了现代国际法的一种先进的价值追求,蕴含了民主、公平、正义等国际法价值,体现了全球能源共同安全观的核心思想。特别是“能源命运共同体”包含的重要原则——“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既是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新发展,②参见杨泽伟:《“一带一路”倡议与现代国际法的发展》,《武大国际法评论》2019年第6期,第5-6页。也是实现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