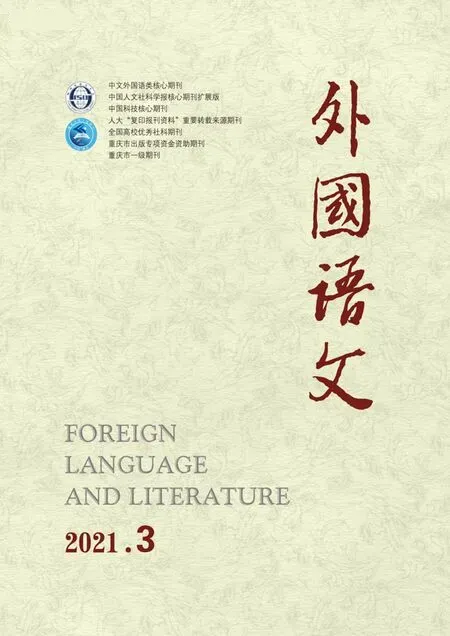韩南《无声戏》译本的译者行为批评分析
朱斌
(四川外国语大学 商务英语学院,重庆 400031)
0 引言
美国知名汉学家韩南(Patric Hanan)致力于汉学研究60载,对中西文明交流贡献突出,蜚声于国内外汉学界。同时,他也是一位翻译家(陈平原,2020)。他在晚年翻译《无声戏》等近十部明清小说,赋予这些在国内“被遮蔽”的作品以“新的生命”。《无声戏》是明末清初小说家李渔所作,代表了彼时白话小说的最高成就,但在以诗文为正统的传统文学观念里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位置。
1990年,韩南教授节译了其中的六回故事,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译本一经问世,数次再版,广受好评。知名学者李欧梵(Leo Ou-fan Lee)称,每每阅读译本让人“其乐无穷”,不禁“深夜里击节赞赏”(韩南,2010:236)。1994年,美国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 Mair)将译本的第三回《女陈平计生七处》收入《哥伦比亚中国古代文学选集》(TheColumbiaAnthologyofTraditionalChineseLiterature);1996年,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将译本的第六回《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收入《中国文学编年史: 从先秦到 1911》(AnAnthologyofChineseLiterature:Beginningsto1911)(何敏,2008)。《无声戏》甚至走进了美国的大学课堂,成了东亚文学课程的教材(肖娴,2019)。除专业读者外,译本也赢得了大众读者的高度评价。
在中国“尘封”数百年的《无声戏》,经过韩南独特的话语阐释,在新的文化语境里“柳暗花明”,重获“新生”,甚至有被经典化的趋势。无疑,这是中国文学走出国门,走进目标文化系统的成功范例,值得我们关注。但目前对韩南《无声戏》英译的相关研究比较匮乏,唯有黄玉枝(2018)从深度翻译的视角论述了该译本。鉴于此,本文借鉴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翻译内、外分野的理念,从翻译外和翻译内两个层面探索该译本呈现的译者行为特征,为中国文学对外译介提供有益借鉴。
1 译者行为特征的翻译外与翻译内层面
在翻译研究的历史长河中,翻译家长期处于隐身、被淹没的状态。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后,“译者的主体性逐渐得到重视”(周领顺 等,2018),许钧也多次呼吁“加强翻译家研究”(刘云虹 等,2020)。赵军峰(2006)指出,以往的翻译家研究似乎只是史料的钩沉或翻译思想的总结,缺乏一定的理论思想指导,其成果流于表面。可喜的是,近年来,周领顺首创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翻译家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是翻译研究的新趋势,值得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周领顺,2019)。周领顺(2014b:3-7)首次将“译者行为作为一个批判性研究的话题”。从狭义上讲,译者行为“指的是译者身份下译者所有的角色行为,译者是源语文本(原文)意义转换的执行者,彰显的是其语言性,也包括译者身份下译者的社会性角色行为,译者的目的语文本(译文)的调适者,彰显的是社会性”。他进而提出,译者的行为特征可以从翻译内和翻译外两个层面来考察,“翻译内指的是翻译内部因素及其研究,主要关涉的是语码转换上的问题……翻译外指的是翻译外部因素及其研究,主要关涉的是社会上的问题” (周领顺,2014a:12)。前者注重文本与文本间的转换过程,聚焦文本的语言、风格、意义等方面的求真或务实的考察,后者注重翻译行为之外的因素,如文本选择的缘由、翻译效果的考察和文本的考证等。翻译内层面和翻译外层面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周领顺,2014a:13),唯有将两个层面结合起来综合考察韩南《无声戏》的英译行为,才能确保对韩南英译的《无声戏》做出全面而又客观的翻译评价。
2 翻译外:文本选择与节译行为
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学史上是一种地位卑下的文体, 常被贬为文学中的“闲书”(谭帆,1996)。李欧梵就曾感叹,中国学者似乎对通俗文学存有成见,“认为不登‘新文学’大雅之堂”(韩南,2010:235)。据韩南回忆,他在20世纪80年代参加中国学术会议时,主办方得知自己的演讲题目不是鲁迅而是“非主流”的李渔时“不禁愕然”(凌筱峤,2014:102)。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相关著作中自然很难寻觅到李渔的踪影,鲁迅先生在1923年创作的《中国小说史略》对他只字未提便是明证。李渔创作的《无声戏》自然也难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在清代甚至沦为禁毁小说之列。这不禁让人好奇:韩南为何会对这部“不入流”的作品产生兴趣?译者为何仅选译其中的六回?
2.1 文本选择之源:研究兴趣为媒
“译者行为是社会性的、目的性的行为,其所从事的翻译活动也必然带有相应的特征。”(周领顺,2014b:30)通常,译者会在所处的时空背景下,能动地调动自己全部的学识,进而构建一种选择标准和判断体系(邹振环,2012:426)。韩南乃哈佛大学知名教授、享誉全球的汉学家。他在1990年翻译《无声戏》时已积累足够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因此,对于文本选择,他享有较大的话语权,较少受市场或经济因素的干扰。对于这样一位操文本选择权的译者,其个人的学术背景、趣味爱好、价值观念抑或个人对原文的偏好,都可能成为左右文本选择的主导因素。
韩南与中国文学的学术“因缘”始于偶然。1954年他在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最初的兴趣是英国中古历史传奇。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韦利(Arthur Waley)和庞德(Ezra Pound)所译的中国诗歌,这一“偶遇”竟影响了他未来学术发展的方向。中国诗歌中蕴藏的文化精髓深深打动了他,并促使他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转而到伦敦大学攻读中文学士学位,从而开启了汉学之路。2009年,他回忆初识中国文学时的感受时说:“我感觉好像闯入了一个充满无知的真空。周围的人对中国除了意识形态以外一无所知。这使得我意识到中国的文学、文化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领域竟然完全被忽视了。相比之下,英美文学研究则已日益细致化,即使是冷僻、艰深的课题也不乏研究者。”(凌筱峤,2014:99)不难看出,韩南的研究兴趣从英国文学转到中国文学,源于对英美学者长期忽视中国文学现状的纠偏,更源于对中国文学的价值认同,这成为推动他选择《无声戏》作为英译对象的原动力。
如果说李渔是“幸运儿”,那韩南定是那位“明眼人”。他摒弃了中国文人对通俗小说“抄袭前人,粗制滥造”(袁进,2009:12)之名的传统看法,在大堆“平庸作品”中爬梳剔抉,发掘李渔的独特价值,进而开始潜心研究。1981年,在《中国话本小说史》(TheChineseVernacularStory)中,他就专章论述李渔的戏剧理论、小说创作,并重点讨论《无声戏》和《十二楼》两部小说的特点和内容。1985年,韩南开启第三次中国之行,访学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以期完成他“偏爱”的作家李渔的专著,也就是后来(1988)在美国出版的《创造李渔》(TheInventionofLiYu)。在本书的前言中,韩南对李渔作了如下描述:
在中国所有的前现代小说家中,李渔给我们提供了将其思想和艺术放在一起加以研究的最佳机会:首先,因为他留下了大量的作品,涵盖各种体裁,这一点可说没有其他作家已做到;其次,因为他有着清晰连贯地向读者阐释自己观点的热情;第三,因为他的作品高度地成为一个整体,允许甚至要求一种全面的批评方法。(韩南,2010:1-2)
由此看来,李渔的价值经韩南的重估后得以“重见天日”:第一,李渔和西方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家一样多产,有各种作品留世:书信、戏剧、小说、笠翁一家言等。在韩南看来,这些作品“雅俗共赏”,可以带来文人或士大夫以外的“声音”,对整个社会的文学发展意义重大(骁马,1985)。第二,李渔敢于并善于表达自我,诚如韩南所言,“在故事以及小说中,李渔几乎将传统叙述者角色翻改成他自己的形象,因此,他个人的见解与评论就侵入乃至支配了故事”(韩南,2010:39)。这样的写作技巧使得他在同时代的作家中脱颖而出,这无疑也是引发韩南关注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三,在韩南心目中,李渔是一位了不起的喜剧作家。他善用倒置创作新奇小说,恰如爱尔兰的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和德国的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捷克学者布罗日克(1988:73)指出:“兴趣是对所偏爱的客体或活动的一种积极的态度。”韩南对李渔作品所独有的艺术和美学价值而产生浓厚的研究兴趣,而这种兴趣又催生他对李渔的一种积极态度,即通过翻译进一步挖掘李渔作品的价值。价值不是固有之物,也不是臆造之物,而是实践的产物(袁贵仁,1991:161)。韩南正是认识到这一点,便从1990年开始潜心翻译《肉蒲团》《无声戏》《十二楼》等李渔的小说,挖掘它们的潜藏价值,致力于将更多“非主流”作品译介到英语世界,以期“推动学术研究与教学”(凌筱峤,2014:105)。
2.2 节译行为之因:重构“经典”叙事
《无声戏》所存版本众多,有必要对其版本嬗变情况进行简单说明。据学者萧欣桥(1987)考证,大概在顺治十三年(1656)前后,李渔在杭州完成了第一部小说集《无声戏初集》,即现存的日本尊经阁(Sonkeikaku)藏本,其副本收录于德国汉学家马汉茂(Helmut Martin)编辑的《李渔全集》(1970)中(Hanan,1990:ix)。该集包括12回故事,出版精良,配有名家的图画。《无声戏初集》出版后不久,李渔迅速推出了《无声戏二集》。相较于前集,本集包含的六回故事较长,但现已失传,其内容散见于《连城璧》中。顺治末年,在好友杜濬的帮助下,李渔从《无声戏初集》和《无声戏二集》中分别截取七回和五回,合编为《无声戏合集》。该集改变了先前篇目的顺序,故事的标题也从单句变为双句,相邻故事的关联性也有所丧失。康熙初年,李渔将本集的书名改为《连城璧》,并把《无声戏合集》未收录的五回和新创作的一回作为外编编入,共收18回,其副本存于日本佐伯图书馆(Saeki Municipal Library),国内的大连市图书馆也藏有抄本,但有两回缺失(沈新林,1992:35)。1991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李渔全集》(第八卷)收录了《无声戏》《连城璧》两书。该版本基本保留了原刻本的内容和编排方式,是当前国内最权威的藏本。
基于上面论述可知,《无声戏》共包含了18回故事,但译者韩南仅选择了《丑郎君怕偏生艳》《美男子避惑反生疑》《女陈平计生七出》《男孟母教合三迁》《变女为儿菩萨巧》《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等六回故事进行翻译。
节译行为与译者遵循的“趣味性”原则息息相关。他在《中国白话小说史》中指出,“《无声戏》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等四篇是这个集子里最有趣的小说”(韩南,1989:172)。译本的前四回便取自这四篇故事。第一篇《丑郎君怕娇偏生艳》打破中国浪漫喜剧“郎才女貌”“才子佳人”的传统模式,讲述“美女该嫁丑夫”的故事;第二篇《美男子避惑反生疑》一反常态,“大胆地宣称最危险的一类官员就是清官”(Hanan,1990: viii),因为“贪官的毛病有药可医,清官的过失无人敢谏”;第五篇《女陈平计生七出》讲述了在险情面前,能够力挽狂澜的英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男性,竟是不识一字的女性,“可谓别开生面”(韩南,1989:171);第六篇《男孟母教合三迁》挑战儒家传统伦理纲常,续写秀士与美童的男同性恋故事,且将同性恋当作“义夫节妇”来赞扬。可见,在韩南心目中,那些颠覆传统叙事、打破人们思维定式的话题是最有趣的、最具娱乐性的故事。
而本集的第九篇《变女为儿菩萨巧》讲述主人公施达卿行善不忠,仅得一个“半雌半雄的石女”,后经点拨继续行善,石女终变男孩的故事,突出“施恶必有惩、行善终有报”的主题(骆兵,2004:230)。该篇入选的原因有二:第一,本篇虽没有前四篇那样具有明显的“倒置”特征,但“半男半女”的情节也同样赋予故事诙谐幽默的意趣,能给读者带来“新”与“奇”的心理感受;第二,本篇充分体现了李渔小说创作的思想性,即“劝善与惩恶并重”的典型特征(骆兵,2004:220-221)。
本集中的另外七篇未入选的原因则与译者秉持的“优中选优”原则相关(刘晓晖 等,2020)。第三篇《改八字苦尽甜来》和第四篇《失千金祸因福生》,前篇讲“命”,后篇讲“运”,设计巧妙,但在韩南看来,它们可能是“模仿凌濛初之作”,不够创新(韩南,1989:171);第七篇《人宿妓穷鬼诉镖冤》和第八篇《鬼偷钱活人还赌债》是关于嫖和赌的话题,属于西方文学中常谈的话题;第十篇《移妻换妾鬼神奇》讲述妒妇的故事,这在当时已是烂熟的主题(韩南,1989:171);第11篇《儿孙弃骸骨撞仆奔丧》和第12篇《妻妾艳琵琶梅香守节》讲父子之间或妻妾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两篇叙述上还算精彩,但与第一篇的故事主题多有重叠。可见,译者在译介李渔小说的初期,倾向于挑选那些最精彩的、能最大限度地吸引读者兴趣的内容,而舍弃一些相对“逊色”的故事。
《无声戏初集》的艺术价值最高,质量最为上乘,也最符合韩南对李渔“密针线师”的评价(Hanan,1988:138)。他对后来出版的《无声戏合集》就颇有微词,称它可能是作者为了商业目的的应急之作(韩南,2010:26)。译本的最后一回选取的是《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本文以下简称《谭》),这也是在《无声戏初集》之外选取的唯一一篇故事。这样的选择并不是译者随意而为之,实则是他缜密构思、布局的结果,其目的是重构“经典”:第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本是古时婚姻的应有之道,而本篇中的男女主人公毅然抵抗封建礼教,成为封建婚姻最坚决的叛逆者。显然,这是对经典叙事的颠覆性逆写,与前五回故事在创作手法上保持高度一致;第二,《谭》和译本第五回《变女为儿菩萨巧》在“劝善与惩恶”的主题上紧密关联,这样译本中每两回故事都相互对照,凸显了李渔的谋篇布局能力,也方便读者体会原文的文学性;第三,《谭》作为最后一篇入选有画龙点睛之妙。《谭》的核心叙事围绕戏展开,故事情节的发展也是由戏来推动。这样,整个译本以“戏”入题,再以“戏”收场,前后形成了两相呼应的效果,巧妙地再现了李渔的“结构意识”。
在翻译外层面,译者的文本选择行为和节译行为与译者所受的教育背景、学术兴趣和内化于心的价值判断息息相关。韩南对李渔的学术研究兴趣以及借译本推动“学术研究和教学”的愿望是文本选择的原动力,而译者内化于心的“趣味性”原则、“优中选优”原则和重构“经典”叙事的夙愿是节译行为的深层动机。
3 翻译内:“求真”的追求与“务实”的考量
翻译是一项社会文化活动。“同样是进行中国文化的译出实践,不同的译者态度可能会造成迥异的译者行为。”(周领顺,2020)换言之,译者的文化态度一定程度上支配了译者种种策略的选择(许钧,2002)。在某一具体翻译事件中,若译者较为认同源语文化价值,他便倾向于采取一种“抵抗式”策略,其行为是向原文和作者靠拢的“求真翻译”;若译者偏向本土文化立场,他易于采取“顺畅式”策略,其行为是向读者和社会靠拢的“务实翻译”(周领顺,2020)。
3.1 “求真”:彰显源语的“异质性话语”
3.1.1对话的翻译
李渔小说创作讲究自然本色,用语通俗,但不落于粗俗。他善于通过人物的行动、对话来刻画人物形象,就像刻画戏曲舞台上的生、旦、净、末、丑一样(骆兵,2004:235)。李渔的话本小说常具有雅化与趋俗相互交融的特点。译者是如何处理这些特有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呢?试看《谭》中男女主人公的一段对话。
例(1)
原文:“小姐小姐,你是个聪明绝顶之人,岂不知小生之来意乎?”藐姑也像念戏一般,答应他道:“人非木石,夫岂不知,但若有情难诉耳。”谭楚玉又道:“老夫人提防得紧,村学究拘管得严,不知等到何时,才能勾遂我三生之愿?”藐姑道:“只好良心相许,俟诸异日而已。此时十目相视,万无佳会可乘,幸无妄想。”……谭楚玉点点头道:“敬闻命矣。”(李渔,1991:257-258)
译文:“O Mistress, Mistress, most intelligent creature as thou art, how canst thou not be aware of my purpose in coming?”
Miaogu replied, also as if reciting: Man is not made of wood or stone, so how can he be unaware? It grieveth me that I cannot speak my love!”
Tan continued:“Madam watcheth closely, and the pedagogue is strict. How long must I wait ere I fulfill the desire of three lifetimes?”
“We can but give each other our hearts and await another day. Here, before the gaze of all, there is, i’faith, no chance of a tryst. Pray cease thy too, too sanguine hopes.”
…
“I shall respectfully dothy bidding”, said Tan, with a nod. (Li Yu, 1990:170-171)
本段是谭楚玉在排练间向刘藐姑传送求爱信息的对话。谭楚玉爱慕刘藐姑已久,但限于藐姑父母拘管得紧,窥伺半年都未获向对方表露心声的机会。幸亏一日,排练间师父临时外出,他们二人终获可诉衷肠的机会,但又惧同门角色察觉。于是,便想出一条妙计:将“之乎者也”这样晦涩的古文穿插在对话中,以对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角色造成理解上的障碍,从而方便他们的交流。面对原文俗语和古文混杂的语言风格,译者并未一味迁就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将它们归化处理成通俗的现代英语,而是站在源语文化的立场,做了如下“求真”的处理:一是用古英语来对应原文中的晦涩古文。译者既是原作的读者、阐释者,也是原作的再现者,他应该给译文读者创造机会,使其能像原文读者那样欣赏作品。显然,韩南是这方面的高手。他在译文中将thou、art 、grieveth、watcheth、ere、thy、thee、i’faith等古英语和现代英语并用,给目标读者带来阅读的障碍,竭力让英语读者在阅读译文时获得中文读者阅读原文时相似的印象和情感。二是选用同等程度的雅词翻译原文中雅词。原文在描述戏班的老师时用了“村学究”,描写约会时用了“佳会”,译者在翻译时同样使用了较高级词汇pedagogue和tryst去替换口语表达中较常用的teacher和date,“求真”于作者李渔的语言风格,也恰当地表征出两位主人公的文化水平,将他们的形象原汁原味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3.1.2诗词的翻译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自唐以降,古典小说家会有意无意间借助诗词以显露自己的才情,抑或借此“赢得听众的赏识并提高说话者的身份”(陈平原,2003:211)。 因此,“叙事中夹带大量诗词”便成了古典小说创作的一种风尚(陈平原,2003:223)。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无声戏》同样也不例外:小说每回的开头多是一诗或一词,或二者兼有,以点明全文的主旨;正文中也常常根据情节或情感的需要穿插了大量诗词。这些诗词是推动故事发展、烘托人物形象的有效手段,“为小说整体形式的意味表达贡献无穷的生机”(邱江宁,2005:62)。笔者发现,面对源语文化的这一叙事结构模式,译者翻译了所有的诗词,凸显了原文的异质性身份。如果我们再仔细分析译本中的诗歌翻译,更能看出译者“求真”的翻译行为。现以卷首语的一首诗歌翻译为例。
例(2)
原文:天公局法乱如麻,十对夫妻九配差。
常使娇莺栖老树,惯教顽石伴奇花。
合欢床上眠仇侣,交颈帷中带软枷。
只有鸳鸯无错配,不须梦里抱琵琶。(李渔,1991:5)
译文:Haphazard are the matches made in Heaven,
Nine couples in ten are wrongly chosen.
The oriole perches on the ancient stock,
The flower grows by the lifeless rock.
At dangers drawn from the day they are wed,
Their lovemaking turns to torture in bed.
Only the lovebird finds the right mate,
And need not dream of a kindlierfate. (Li Yu, 1990: 3)
原诗为中国传统诗歌中的七言律诗,共四联,对照工整,每行七字共56字;格律严谨,一二四六八句最后一个字均押尾韵,属于典型的“平起首句入韵式”。译者在确保译本准确达意的基础上巧妙地复现了原诗的形式美和音律美。第一,面对原诗在结构、字数、标点上完全相对的形式特征,译者同样以一句对应翻译原诗的一句,且在句子长短、标点符号上尽量保持一致,基本获得了一种空间上的动态平衡,重现了原诗的形式美;二是竭力再现原诗优美和谐的音律。原诗属于典型的中国格律诗,一二四六八句最后一个字均押尾韵[a]。译本虽不能像原诗那样均押同一个尾韵,但译者巧妙地采用aabbccdd这种典型的英诗格律诗的形式代之:第一二行分别以Heaven和chosen结尾,押音素[n] ;第三四行分别以stock和rock结尾,押音素[k];第五六行分别以wed和bed结尾,押音素[d];第七八行分别以mate和fate结尾,押音素[t]。这样的处理自然可以彰显原诗的“异质性话语”,方便了英语读者领略原诗的风貌和艺术魅力,从而“求真”于原诗的创作特色。
3.1.3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无声戏》中蕴含了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其中所负载的历史、人物、熟语等内容的翻译非常重要,但同时也是摆在译者面前的巨大鸿沟。要将这些民族文化特色有效传达给西方受众,并获得他们的认可,给译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汉学家韩南在翻译《无声戏》时已对原作进行了扎实的研究,所以他的处理方式多为保留原语“异质性”的直译法,或者是可以达到同样效果的直译加注释法。
例(3)
原文:明朝自流寇倡乱,闯贼乘机,以至沧桑鼎革,将近二十年。(李渔,1991:93)
译文:During the final two decades of Ming Dynasty, from the time the roving bandits fomented their rebellions and the Dashing Brigand seized his chance right up until the change of mandate.
Note: The rebel Li Zicheng who helped topple the Ming Dynasty, was known as “The Dashing Prince”, of which “Dashing Brigand” is a sardonic variation. The change of mandate refers to the founding of the Qing (Manchu) dynasty. (Li Yu, 1990:78)
文中的“闯贼”指的是明朝农民起义的领袖李自成。1644年,他推翻明王朝,建立大顺,号称“闯王”。历史上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有称他是“农民革命中的伟人”,也有称他为“凶狡的强盗”。在李渔笔下,他是一个“闯贼”的负面形象。对于这一文化负载信息,译者显然采取有意识的“求真”行为,采用的是直译加尾注的深度翻译方法。首先,将“闯”直译为“Dashing”,凸显李自成勇猛有胆略;将“贼”直译为“Brigand”,凸显其“盗贼”“强盗”形象。然后在尾注里对“闯贼”这一文化意象进行了阐释,从而将译文置于丰富的文化语言和文化背景中,有效地弥补了西方受众对这一历史人物的文化缺失。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对“潘安之貌,子建之才”“西子重生,太真复出”中典型的历史人物的翻译,均是直译加注的深度翻译方法。
例(4)
原文:说来教人腐心切齿。(李渔,1991:94)
译文:And even to mention them is enough to make us gnash our teeth. (Li Yu, 1990: 79)
“腐心切齿”出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它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表达,我们通过“切齿”这一动作,可以联想到某人的极端气愤或痛恨的心情,或是某人竭力抑制住自己情绪或感觉的表情。英语中对应的表达很多,例如make one burn with anger、hate with all one’s soul、detest to the extreme、indignant、 furious等。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在翻译《红楼梦》第97回中的“令人切齿”时将其意译为“What hateful creatures they are!”(冯庆华,2008:18-19)。这样的处理方式传达了原文的意思,但遗憾的是切齿的生动意象完全丧失。此处,韩南将其直译为“gnash our teeth”,既保留了原文“切齿”的意象,又完美地传达了原语的精神风貌,也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属于典型的“求真翻译”。
3.2“务实”:迎合目标文化的价值规范
3.2.1眉批的省略
评点为明清小说的一大特点,其形式多样,主要与古时候的阅读方式相关,包括回前总评、眉批、夹批、旁批、总评等(叶朗,1982:13),而眉批加总评的形式是评点最流行的方式。评点是当时小说创作的重要要素,可以“对作品情感主旨的强化或修正, 对作品艺术形式的增饰和加工, 对作品体制和文字的修订”(谭帆,1998)。
《无声戏》叙事模式就延续了当时盛行的方式,即眉批加总评的评点方式。韩南选译的六回故事包含123条眉批以及六条总评,但译本仅保留了总评,省略了全部的眉批。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很重要的形式在异国文学中可能就毫无意义。诚如英国学者托尼·本奈特(Tony Bennett)指出:“某一特定的、在某一历史情境中被认作是‘文学的’文本,也许在另一情境中却全然处于等式的另一边。”(张冰,2000:165)换言之,一个特殊形式是否具有“文学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观察者的立场或视角。显然,韩南此处是站在目标文化的立场。在他看来,“眉批并不能提供事实性信息,只是平添了一些喜剧或讽刺,以及偶尔对故事技艺的赞扬”(Hanan,1990:xi)。因此,省略眉批不译可以迎合目标文化的传统规范,也可满足现代读者对阅读流畅性的要求。
3.2.2年龄的翻译
在中国古代,虚数是常用的一种年龄计算方式。按照虚数的记法,人一出生就算一岁,以后每遇新年就增加一岁,因此,这样计算出来的岁数要比足岁大一到两岁。周岁指婴儿出世那日起整满一年,民间通常在孩子周岁或生日那一天举行庆祝活动,俗称“做周岁”。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年龄多以虚数计算。下面,我们看下译者是如何处理原文中的年龄。
例(5)
原文:只是女儿年纪尚小,还不曾到破瓜的时节。(李渔,1991:262)
译文:But my daughter is still very young, not yet fifteen. (Li Yu,1990: 177)
例(6)
原文:流落在三吴、两浙之间,年龄才十七岁。(李渔,1991:256)
译文:He had drifted from place to place in eastern Jiangsu and in Zhejiang, and was now sixteen years old. (Li Yu,1990: 168)
韩南是一位非常严谨的译者。他在翻译之前必做研究,对中国古代以虚岁计算年龄的这一文化信息相当熟知。中国的唐宋诗词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句子,如“正是破瓜年纪,含情惯得人饶”。其中的“破瓜”指的就是16岁。面对中国古代文化这一特质,译者并没有通过直译加注的方式凸显源文的异质性特质,而是将源文中的虚岁都换算成了西方通行的实岁,即在虚岁的基础上减去一岁后再直译为英文的“务实翻译”。因此,源文中“破瓜”被翻译为“fifteen”,“17岁”被翻译为“sixteen years old”。显然,译者此时是站在目的语文化的立场,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旨在迎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心理认知,实现翻译的社会功用。
“求真”和“务实”处于连续统的两端,但两者之间不是完全割裂和绝对化的,是“相互制约的”,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差异只是表现在倾向性及其程度的强弱上” (周领顺,2019)。因此,面对“异质性话语”,在大多数情况下,韩南进行了求真性处理,他在选词、风格、文体、结构等方面尽量紧贴原文,竭力“让读者走向作者”,但有时译者也进行了务实性处理,通过省略、归化原文文化元素等多样的方法,尽力迎合目标文化价值规范。
4 结语
诚然,《无声戏》译本也有美中不足之处。例如,译者误将“阳气”翻译为“yang forces”(Li Yu,1990: 80);未能充分理解作者所讲的“她惯会做无米之炊”的修辞含义,误将其直译为“she was accustomed to cooking without rice”(Li Yu,1990: 82)。但这些瑕疵并不能遮蔽译本本身的经典性。毋庸置疑,《无声戏》与韩南的“相遇”是美好的。译者凭借个人极高的“修养”,在中西两种文化间来回“协调”,在“求真”和“务实”之间保持了理想中的平衡,既再现了原文的意义,又实现了翻译的社会功能,将《无声戏》打造成了“一部真正的译作”。按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话说,它“不会遮蔽原作,不会遮挡原作的光辉,而是通过自身的媒介加强了原作,让纯语言光辉更充分地在原作中散发出来”(Munday,2010:170)。韩南是一位成功的翻译家,他的翻译行为值得我们继续深度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