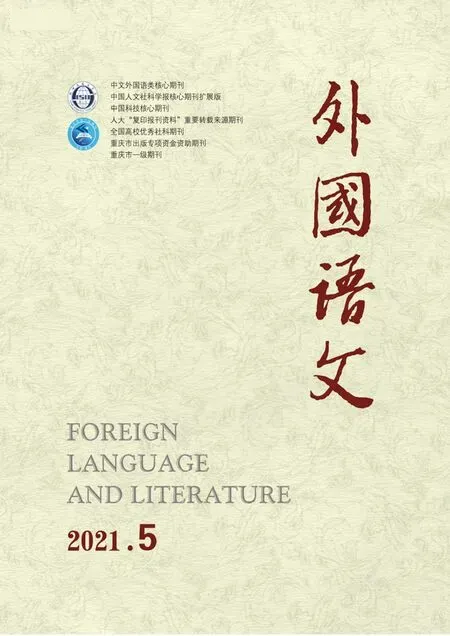“框子”和语言对柯尔律治“同一生命”的消解
王榕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重庆 400031 )
0 引言
萨缪尔·泰勒·柯尔律治的文学和哲学理论以对“同一生命”(one life)的追求为要义,也被称作“两极相遇”(Extremes Meeting)。在1817年版的《朋友》中,柯尔律治说:“自然与精神中的每种力量都必须生发出一个相对的力,作为其存在方式与表达形式:所有相对的力都有重新聚合的趋势,这是极性思想或二元论的普遍法则。”(Coleridge,1969:94)在这段简短的叙述中,至少可以看出极性思想的三个属性: 二元对立、 极性属性、重新聚合的动态性。柯尔律治对这三个属性深以为然,并以此作为自己哲学与文学思想的基础,由此生发出“两极调和有机论”。从字面上看,“两极调和有机论”至少可以拆解为两部分进行分析。首先,柯尔律治在头脑中预设了二元的概念,这种思想倾向表现为大多数浪漫主义者尽力弥合的自然与心灵的对立,其内涵可扩大至主观与客观的区别;就柯尔律治的思想来源而言,它体现为英国经验主义与德国理性主义的对立。其次,柯尔律治“两极调和有机论”的重点不在于强调两极的对立,而是试图弥合两极之间的鸿沟,即调和两极,调和后形成理想的有机论。总的来说,两极调和论是关于关系的科学,体现柯尔律治在继承西方二元对立哲学传统的框架之下试图达到二元调和的努力,表现在其宇宙生命观、自然观等诗学思想中。其中,“同一生命”是“两极调和有机论”在自然观中的体现,是自然与心灵融合的产物。目前对柯尔律治文学理论的研究集中探讨其理论建构的过程,少有评论家思考“两极调和”理论的效果究竟如何。本文通过追溯柯尔律治诗歌文本中的“框子”式意象,即处于生死边界的墓碑和“死中生”的状态,探讨柯尔律治诗歌文本与文学理论之间相互解构的关系,旨在为阐释柯尔律治的文学理论提供新的视角。
1 两极调和与“框子”逻辑
柯尔律治的两极调和理论深受二元论的影响。作为西方占重要地位的哲学思想,二元论思想划分形式与内容、内与外、表现与被表现等相互对立的概念,这形成文学与艺术领域传统的阐释结构。但德里达认为,这种状况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发生了变化,“因为第三批判试图解决精神与自然、内在现象与外在现象、内与外之间的对立”(Derrida, 1977: 35-36)。康德试图通过对“美”的探讨来沟通前两个批判中自然可感的领域与超自然的自由领域之间的鸿沟。他认为审美活动超越了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范畴,因为审美活动本身就是对主客关系的破坏:美的感觉不预设任何对象,很多时候也没有对应的对象,因此美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关系的关系”。但是德里达发现康德哲学中这一预先设想与实际操作之间的矛盾:“当康德坚持不能把逻辑判断的分析应用到美的判断中时,他却把一种逻辑判断的分析应用到美的判断中。康德不能证明这种装进框子的行为的合理性,或者人为强加的这种解除界限话语的合理性。”(Derrida, 1987:70)也就是说,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认识论是已有的框子(frame),他发现了审美这一外在于认识论框子的活动,因此他笃定审美活动是消除认识论框子界限的行为。但是,他对审美活动的分析并没有脱离认识论框架,对美的判断仍受逻辑判断的影响和引导,未能完全跳脱认识论框架。于是审美活动成为一种不断试图脱离框子又不断设置框子的行为,显示出康德理论预设与实际操作之间的矛盾。德里达以此为突破口解构康德试图以《判断力批判》弥合《纯粹理性批判》与《判断力批判》之间的鸿沟的努力。这种理论预设与实际操作之间的矛盾也存在于柯尔律治对“两极调和”理论的建构与阐释的矛盾中。
柯尔律治本人十分反对为了分隔(divide)而区分(distinguish),但同时他认为“在道德领域,我们就必须为了分隔而区分,即所有道德活动是从明晰善恶的区别开始的”(Coleridge,1993:14),因此,虽然柯尔律治提醒读者不要过分关注《古舟子咏》体现的生态伦理,以及《三个坟墓》中处于极端对立状态的天使般的女儿和恶魔般的母亲,但是从道德层面上看,以善恶区别的观点来分析这两首诗歌是完全可行的。同时,这两首诗歌试图阐释的问题绝不仅仅是简单的道德层面的是非题。也就是说,这两首诗歌蕴含二元对立的框子,同时也蕴含柯尔律治试图跳脱二元对立框子的努力,即柯氏试图为诗歌体现的二元对立关系寻找一个归宿——两极调和后的“同一生命”。但他始料未及的是,两极调和的基础,即处于两个极点的力之间的对立关系,会被一些处于边界的、模棱两可的、似是而非的存在所模糊。这些“框子”式的存在物会成为两极调和有机论内部的薄弱环节,成为解构的靶子。
从表面上看,《三个坟墓》呈现了典型的道德层面的是非题。《三个坟墓》的前两部分写作于1798年,后两个部分最早发表于1809年9月21日《朋友》第四卷,后收录于《神叶诗灵》1817、1828、1829和1834年的各个版本中。柯尔律治数十年对诗歌内容的修改体现其思想的转变。在诗歌的第一部分,柯尔律治对《奥赛罗》第三章第三句(“course of wooing”)的引用奠定了这首诗歌的情感基调:与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相似,《三个坟墓》也是一部由于主人公的性格缺陷而导致的爱情悲剧。玛丽和爱德华的爱情悲剧来源于母亲的病态性格以及女儿的软弱,母亲试图通过唆使爱德华与自己成婚来破坏女儿的婚姻,女儿因无法捍卫自己的爱情、得不到母亲的认可而意志消沉。诗歌前两部分通过刻画天使般的女儿和恶魔般的母亲这一对极端形象来营造尖锐的二元对立,体现柯尔律治对二元对立传统的继承。但在接触动态的极性思想后,他试图用幻想的观点来削弱作品体现的二元对立性,并且用一个更高的存在,即上帝来囊括整个故事的说教寓意,使母亲病态的行为合理化。于是,在《神叶诗灵》中,柯尔律治呼吁读者关注诗歌体现的心理问题:
我无意使这个故事偏向于悲剧色彩,更不想凸显它是个畸形的故事(即便是在二十多年前最初写作这个故事时我也反对这两种倾向),这个故事的重点在于说明想象的作用,是理念猛烈而突然地加诸想象的例子。我最近一直在阅读布莱恩·爱德华兹(Bryan Edwards)关于西印度群岛的黑人被施以巫术的描写,以及赫恩(Hearn)描写的与此相似的关于想象作用于印第安人的奇闻逸事(我提到的这些引文在富有想象力的读者们看来会得到很好的回报);在我的构想中,这样的例子不特殊存在于野蛮未开化的部落,目的是说明心灵在这些情况下是如何被影响的,以及被幻想影响的病态行动(morbid action)从一开始如何进展并体现出何种症状。(Coleridge,1912:267)。
于是一种设置框子与试图跳脱框子行为之间的矛盾得以凸显。柯尔律治在诗歌中塑造天使女儿和恶魔母亲的形象,试图形成鲜明的二元对立,但是通过刻画人物性格与人物关系间的矛盾,女儿和母亲形象所代表的善恶之间的界限被模糊。诗歌中充满悖论的意象:第一小节表面上描写人与自然的亲近关系,但蕴含矛盾的意义。叙述者年幼时经常在一片生长得“茂盛而甜美”的荆棘之下伸展自己。柯尔律治用甜美来描写满是尖刺的荆棘丛,荆棘丛形成的阴凉好似母亲的怀抱,在盛夏正午的炎热之下为“我”提供了一片阴凉。满是尖刺却让人如沐春风的荆棘丛恐怕是文中母亲的隐喻。在父亲去世后,玛丽的母亲独自将两个女儿抚养成人,从诗歌中可以看出女儿对母亲十分尊重,而女儿软弱的性格又反映出母亲的控制欲。让人如沐春风的母亲的怀抱却充满尖刺,并且那尖刺没有干枯,反而一直是茂盛的模样。在这些尖刺之下是三人的坟墓:其中显示母亲身份的墓穴中埋葬着母亲的尸身,另外两个坟墓只有墓碑,没有任何人的尸身。其中一个只写着日期与一句话,即“上帝的仁爱是无限的”,另一个则不带有任何信息。教堂司事的陈述表明,完整的坟墓、只有一句话的墓碑和没有任何信息的墓碑分别属于母亲、女儿、以及女儿的仆人。玛丽的母亲是无情的,在她的影响下玛丽即使结了婚也是个“贫瘠的”妻子。而结婚前的玛丽像杉木一样正直优雅,“她的尖顶直指天堂”。她心地单纯善良,却缺乏主见,面对爱情只会以母亲的想法为准。虽然玛丽的母亲最初同意二人的婚事,但是柯尔律治对《奥赛罗》第三章第三句的引用让读者觉得故事不会这么简单。诗歌一开始就引入荆棘丛这一暗指母亲的意象,暗喻母亲逐渐动摇的内心以及没有主见的女儿,矛盾开始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整个诗歌文本中没有女儿与母亲同时“在场”的场景,本应“伟大”的母亲其实是恶的化身,纯洁善良但是软弱怯懦的女儿反而助长了母亲的恶。矛盾的人物关系和失去所指的坟墓使玛丽与母亲的关系呈现出十分扭曲的态势。母亲的恶毒诅咒导致玛丽和爱德华两人没有后代,但“母亲仍然是母亲,世上最神圣的存在”(Coleridge,1912:277),母亲的形象充满反讽与悖论。婚后的玛丽好像生病一般无法开心,她避免与母亲见面,“不敢在外面转悠,以免在路上碰到母亲” (Coleridge,1912:277)。玛丽和爱德华共同的朋友艾伦在教堂内碰到玛丽的母亲时,也遭到了诅咒,而母亲从那以后再没出现在教堂。玛丽、爱德华和艾伦虽然被玛丽的母亲诅咒,但是三人对待后者的态度表现出矛盾:他们最终在物理距离上摆脱了玛丽的母亲,但在心理上无法摆脱她,甚至对她的影响有种依恋。在炎炎夏日,他们会去寻找那满是尖刺的荆棘丛所带来的阴凉感:在炎炎夏日,他们突然前来,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来的:而你在寻找一丝阴凉,但是树枝上几乎没有树叶(Coleridge,1912:283)。
这时我们不禁产生疑问,诗歌中女儿和母亲从未同时“在场”,第二部分两人对话也是隔着一扇门进行的,这唯一一次可能同时在场的机会也以女儿的昏倒而最终未能达成。母亲在恶毒地诅咒自己女儿之后,仍然被当作最为神圣的存在,这种表述与第一部分女儿天使的特质相符合。玛丽在母亲的诅咒下远离母亲,却变得如同母亲一样歇斯底里,让人觉得“天啊,你真像你母亲!” (Coleridge,1912:282)因此是否可以大胆猜测女儿和母亲其实是同一个能指,窥伺女儿女婿的母亲可能是女儿内心的另一种心理状态。也就是说女儿的心灵中存在至善与至恶两种极端对立的状态,在与爱德华结婚的问题上两种状态进行博弈。根据柯尔律治思想发展的特点,他试图为这种博弈找到一种结果,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因为玛丽和爱德华在与“玛丽母亲”得不到和解的状态之下最终结婚,但是婚后并不幸福,两个人每日都浑浑噩噩、心事重重。不论玛丽母亲是否当真具有物质实存,抑或只是玛丽心中的一种构想,都不能否认其与玛丽形成的尖锐的二元对立,而二者从未同时在场以及最终无法和解都说明两极调和的难度。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存在一些游荡于边界的、拥有两个极点的性质又不同于两个极点的东西,他们的存在会打破内与外的界限。在这个故事中就存在这样一种东西,表现为模棱两可的墓碑。
2 模糊生死界限的墓碑
墓碑的意义是碑上的字赋予的,要是碑上没有任何信息,那它只能是一块石头。墓碑的基本功用是标识墓地所在,更重要的是作为逝者的名片,显示此人的姓名、出生年月及死亡年月,作为一种能指本能性地指向一个所指,即墓中埋葬的人。但是这种所指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因为墓中具有物理实存的对象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物理实存,此时墓碑作为名片的指向作用开始消解,也就是说从墓碑具有指向性的那一刻开始,其指向的对象就开始失去在场性——指向过程开始的同时也意味着结束。这是墓碑的空间意义。柯尔律治这首诗歌的前言中表明:这个故事与其说是三个坟墓,不如说是三个“墓碑”,其中一个墓碑与正常无异,“包含名字和日期”,在这个墓碑之下埋葬着一个残忍的母亲,第二个墓碑上“只有日期、没有名字”,还有一行字“上帝的仁爱是无限的”(Coleridge,1912:269)。柯尔律治没有通过讲述人教堂司事提供任何关于第三个墓碑的线索和描述,在前言中提到后两个坟墓只有墓碑,即墓穴中没有任何人的尸身。因此从空间意义上看,该墓碑的指代作用模糊。从时间维度上看,其意义同样模糊。墓碑作为逝者的名片,出现的时间具有边界性,是具有物理实在的“人”与具有幽灵性质的“魂”的界限。墓碑的出现标志着人变成了魂,因此墓碑具有德里达式的“框子”性,是骑跨在生死界限上的存在,它的出现显示人到魂的过渡状态:既能证明这个人曾经生的状态,又代表这个人已经死去。《三个坟墓》中的墓碑由于信息的缺乏,其意义相较于普通的墓碑具有更强的模糊性。此时,墓碑已经不作为哀悼亡者的物质实存,作为能指,它不指代亡者尸身的埋葬地,也不包含生存者对亡者的悼念,而是成为漂浮的能指。我们无法断言其他两个坟墓之中究竟埋葬着谁的物质实存,甚至无法知晓其内部究竟是否存在任何物质实存。它的存在可以显示亡者对生者的影响,也可以指代生者对亡者无法割舍的依赖。墓碑反映人们留恋生命,恐惧死亡的原始本能,因此墓碑只为逝者而立。但是玛丽何以为自己立一座空坟?母亲的葬礼以及坟墓的选址、墓碑上篆刻的内容都由生者完成,因此“三个坟墓”其实是女儿玛丽的“杰作”。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个故事中不仅有反常的母亲,与之相联系的还有反常的女儿,甚至可以说母亲影响女儿,而女儿的默许助长母亲的病态行为。女儿将自己对母亲的依赖化作一个不完整的坟墓,代表她的一部分跟随母亲而去,又或者如上文所说,母亲指的是女儿的另一种心理状态。上文中我们反复强调“三个墓碑”中只有一个有姓名和时间的完整信息,第二个没有名字,只有一句话,而第三个墓碑上的信息完全缺失。有一种可能是柯尔律治在这里划分了物质的死亡和心灵的死亡。这个墓碑是玛丽为自己的心灵所立。玛丽、爱德华以及艾伦在被诅咒之后都经历了心灵之死,但只有玛丽在母亲的坟旁边为自己立了一座空坟,表明自己还是无法摆脱母亲的影响。对玛丽来说,墓碑正是消解了生与死的界限的存在。作为人,她的物理实存表面上仍然存在,但是她的心已死,因此这个没有姓名的墓碑中埋葬着仍然具有物质实存但是精神层面已经消失的玛丽的心。或者说,虽然玛丽的心还在跳动,维持着她的生命,但是它已经失去感觉的功能,失去快乐的能力。因此它虽具有物理性,但是除此之外再无他用。
在柯尔律治好友华兹华斯的诗歌中也出现过类似的坟墓意象,并且其所指更加模糊。在《我们一共七个人》(We are Seven)中,诗人碰到一个乡村小女孩,问她有几个兄弟姐妹。小女孩说加上她一共有兄弟姐妹七人,两个住在康威,两个去了海上,还有两个——姐姐简和弟弟约翰躺在坟地里。诗人告诉小女孩躺在坟地里的姐姐和弟弟现在已经不能算数,她现在只有五个兄弟姐妹。但是小女孩坚持认为“我们是七个”。坟墓作为能指的模糊指代关系在此又被确认:一个被放置于坟墓中的“人”究竟还能否被称为一个人?坟墓所指代的人的死亡状态在小女孩的心灵中并不成立,抑或在她的意识中并不存在生与死的概念,于是生与死在她看来并不是两种对立的状态,二者之间的界限变模糊:对她来说,坟墓指代被埋葬者的物质实存,那个人就在那儿。于是小女孩“经常到那儿(姐弟的坟边)织她的毛袜,给她的手绢缝边;常到那儿的地上去坐下,唱歌给他们消遣。到太阳落山了,将近黄昏,要是天气好,黑得晚,她常带点汤,上那儿吃她的晚饭”(Wordsworth,1984:84-85)。对她来说,姐姐简和弟弟约翰在她的意识中仍然活着,死亡就像睡觉一样,坟墓可能就是一张床,或是一个卧室,她在坟墓附近的系列活动都是在陪伴他们。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英语的惯常用法来看,简(Jane Doe)和约翰(John Doe)分别表示女性和男性的无名氏,即在真实姓名不详时对男性或女性的假设性称呼。小女孩的姐姐和弟弟被埋在树下,坟墓已经被青草覆盖,并且没有墓碑,也就是说两个死去的孩子没有自己的名片,这正好与二人作为“无名氏”的代号相吻合。同时,墓碑是一个人存在与死亡的证明,坟墓是存放尸身的场所,也是尸身开始腐化消失的场所。二人既没有墓碑也没有姓名,甚至连坟墓也被青草覆盖,因此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有理由怀疑其真实性:他们究竟是生是死?甚至是否真的存在过?小女孩口中那躺在坟墓中的姐姐和弟弟成为她头脑中两个漂浮的所指,没有能指能够证明其存在的状态。华兹华斯在叙事诗《兄弟》中借用牧师之口说:“对于生于山中、死于山中的人而言,想到死亡并不是一件痛苦沉重的事。”(Wordsworth,1984:160)对于山中的人来说,生与死的界限模糊,于是他们的墓园中“没有墓志铭,也没有纪念碑、墓碑或死者的姓名,只有我们每日踩踏的草地,和几个自然的坟墓” (Wordsworth,1984:156)。“没有墓碑,没有黄铜牌子,或者骷髅图案,没有我们尘世生活的记录,或者我们的希望,死者的家园,与放牧牛羊的草地几乎一模一样。” (Wordsworth,1984:160)
3 语言的牢笼与“死中生”的老水手
失去物理实指的墓碑和坟墓印证了德里达所说的文字的延宕状态,无法锚定意义,只是一串能指留下的踪迹。在《三个坟墓》中,恶毒的母亲为了得到女儿的爱人而中伤女儿,计划没有得逞又诅咒女儿、女婿和他们的朋友。这三个人被诅咒之后都魂不守舍,感觉永远失去了快乐,这彰显了声音与文字对人心灵的作用。文字作为咒语的作用同样体现在《理想国》的《美诺篇》,美诺说苏格拉底的话像“巫术”,像“符咒”,能控制人,使人麻痹,效果甚至强于蛇的毒液,因为这种侵蚀直接作用于人的灵魂。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克利斯贝尔》以及《古舟子咏》中。吉若丁(Geraldine)对克里斯德蓓的蛊惑表现在对其语言的禁锢上,使克里斯德蓓无法有效地与他人沟通,因此导致悖论式的人物关系。老水手的话像咒语一样施加在前去参加婚宴的年轻人身上,使其脚步动弹不得,只能安静倾听老水手的故事,并最终跟着他远去。值得注意的是,老水手是话语的施动者的同时也是话语的受动者,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即老水手最终是否被救赎。关于这个问题评论者持有不同的态度。将《古舟子咏》当作一则生态寓言的评论家多认为老水手最终被救赎(姚本标,2010:29)。老水手射杀带来南风的信天翁表示人试图控制自然的野心,但是结果造成除了老水手之外的全船人的死亡。而老水手在意识到自己的罪行后,看到水中美丽的水蛇,心中升腾起感激与祝福之情,于是不禁为它们祈福,这表明他终于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他最终被带回陆地,即获得救赎。于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同一生命”达成。但是这一观点可能忽略了一点,即上岸后的老水手仍然被禁锢在语言的无形镣铐中。
老水手回到陆地却不得不接受“死中生”的无穷无尽的折磨,因为他必须持续不断地重复这个故事:“像全身骨架被拆散,我这时痛苦万分;不得不如实讲述我的故事,讲完才觉得轻松。此后,说不准什么时刻,那痛苦又会来临,我只得把故事再讲一遍,免得烈火攻心。” (Coleridge,1912:208)从这个意义上看,TheRimeoftheAncientMariner并不是Mariner’s Rime,而是Rime’s Mariner,因为老水手将永远被困在语言的牢笼中,他见到婚礼的宾客后开始讲述的这个故事并不因为宾客的存在而讲,而是因为如若不讲,他便急火攻心。因此不是老水手在控制rime,而是rime将老水手变成rhymer,是rime在控制老水手,所以二者之间的从属关系其实应该被倒置。诗歌反映出老水手的自我其实是被语言建构与推进的(Reed,1984:173)。“死中生”将老水手从一个独立完整的人变成一个诗歌的讲述者。这些例证都证明柯尔律治隐隐约约感受到了文字的力量,但是囿于时代的限制,他无法把这个问题分析得如解构主义者一样透彻,而是最终将其归结为“巫术”,将其归置到想象的领域。其实巫术从本质上看也许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魔法性质,恰恰是通过语言影响人心,进而影响人的行为。
“死中生”不仅是女鬼的名字,更是老水手在海上的一种生存状态。老水手无故射杀带来好运的信天翁,使全船人遭受厄运,招引来名为“死”与“死中生”的两个女人。两人通过掷色子的游戏来决定老水手和船上其他人的命运。赌其他水手的命运时,“死”赌赢了,于是船上的两百个水手,没有一声哼叫,扑通扑通地连串倒下。赌老水手的命运时,“死中生”赢了,她凝结老水手的血液,使他有嘴却不能祷告,有眼却不敢睁开,实实在在成为死中生的状态。老水手非生非死,遇到他的人也不知其是人是鬼,于是在第四部分开端,前去参加婚礼却被老水手拦下的年轻人对他的印象是:“你叫我心惊受怕,老水手!你的手这样枯瘦!你又细又长,脸色焦黄,像海沙起棱起皱。我怕你,你眼神好似幽魂,你的手焦黄枯萎!” (Coleridge,1912:196)在第五部分,老水手迎来了那场雨时,他不觉得自己有四肢和躯体,全身轻得犹如一片羽毛,与第四部分年轻人认为他是幽魂的表述相呼应。听故事的宾客对他发自内心的恐惧,因为无法确定其是人是鬼。评论者认为,诗歌开头时用“it”指代老水手(It is an ancient Mariner)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与其说老水手是一个“他”,不如说是一个“它”,与其说他是一个人,不如说他就是雾本身(more rime than person)(Reed,1984:174)。船上其他船员在“死亡”之后也维持了一段时间虽死却生的状态,他们的“身躯不腐也不臭,瞪我的眼神依然恶狠狠,就像临终的时候” (Coleridge,1912:197);“死者们哼出声来。他们哼,他们动,他们站起来,不开口,不转眼珠,眼见一个个死人又活过来,即使在梦中,也玄乎”(V,330-334);“舵手开船向前,水手们又像往常一样,一个个拉绳牵缆,他们四肢僵直,像没有生命的器物,我们是幽灵船员” (Coleridge,1912:200)。其他船员虽然已经失去生命,但是他们的行动与处于死中生状态的老水手十分相似,老水手在叙述中也用“我们”将自己与其他船员归为一类,都是 “幽灵”(ghastly)般的存在。“死中生”诅咒老水手这一行为本身内含悖论,因为这一行为既使老水手承受无穷无尽的语言折磨,又拯救了他的生命。于是,柯尔律治制造出另一个同时包含生死内涵的符号,即游离于生死边缘的状态——死中生。
4 结语
《三个坟墓》与《古舟子咏》内含的自我解构性质不仅体现在诗歌的关键意象中,还与诗歌的叙事声音相关。《三个坟墓》由作为旁观者的教堂司事叙述,但是读者很难区分故事来自叙述者的视角还是故事人物的视角。也可说,叙述者尽量用人物的眼光取代自己的眼光,让读者通过人物的眼光来观察故事世界。《古舟子咏》的叙述声音虽然来自老水手,即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但是这种叙述本身很大程度上不来自于老水手的主动叙事行为,而是诅咒的衍生效果。讲述故事的老水手时而作为现在的“我”来追忆过往的事件,时而作为被追忆的“我”回到过去的事件中。二者是不同时期的“我”,现在的“我”知道整个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这是被追忆的“我”无法做到的。于是即便是亲身经过事件的老水手也无法重新在场于事件的发生过程,整个过程是由语言建构的。因此老水手代表的人类与自然最终的和解本质上是人与自己心灵的和解。两个故事都最终以文字形式流传下来,用德里达的话说,这是文字的“诡计”和“背信”。
以善与恶的对立,生与死的对立为表象的两极对立是两极相遇的基础,但这种对立的基础被一些边界性的、框子式的、模糊的、似是而非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存在,即处于生死边界的墓碑与“死中生”的状态所模糊,两极相遇的理论基础被架空。同时,语言和文字的咒语效果通过模糊的叙述声音最大限度地削弱“在场”的可信度,将读者引入由语言建构的眼花缭乱的想象世界。在这个以心灵为主导的世界中,一切皆有可能,包括“同一生命”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