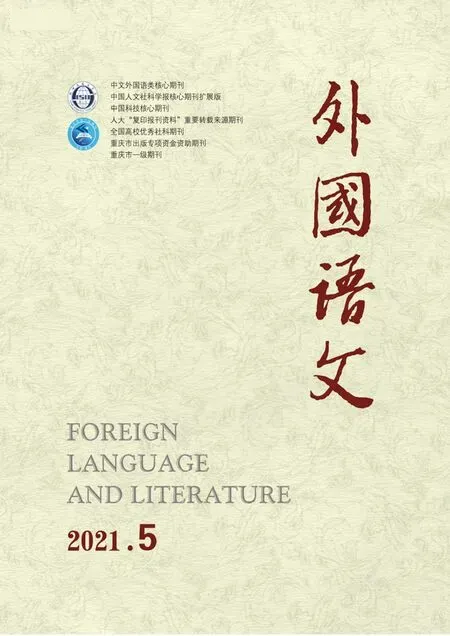弗兰克·奥哈拉诗歌创作的游戏特点
伍紫维 郑燕虹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0 引言
诗人、批评家T. S.艾略特在美国诗坛纵横半个世纪之久后遭遇以W. C.威廉斯为首的一批诗人的抵抗与反叛,他们践行的诗歌路线有别于艾略特的新批评派诗歌,被后人称为美国新诗人。他们对艾略特的态度从崇拜变为怀疑,继而到背叛,人员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强。在这支队伍中有一位出类拔萃的年轻骁将,他宛如一颗流星划过天空,璀璨而短暂,他名叫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
这位著名的纽约派诗人出生在美国马里兰,早年在新英格兰一带长大,从小受到很好的音乐、绘画等艺术教育与熏陶。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著述颇为丰富。1953年,他发表了第一首长诗《第二大道》(TheSecondAvenue),随后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紧急时刻的冥想》(MeditationsinImmediacy)。1960年,随着唐纳德·艾伦(Donald Allen)和沃伦·托尔曼(Warren Tallman)编辑的诗歌选集《美国新诗歌的诗学》(ThePoeticsoftheNewAmericanPoetry)的出版,奥哈拉才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奥哈拉曾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作,并任《艺术新闻》(ArtNews)杂志编辑。他在工作期间负责组织“美国新绘画”(The New American Painting)等多场画展、采访画家并评论他们的作品,由此结识了拉里·里弗斯(Larry Rivers)、格雷丝·哈提根(Grace Hartigan)、威廉·德·库宁(William de Kooning)、诺曼·布鲁姆(Norman Bluhm)等画家。奥哈拉与画家朋友之间紧密的联系为他们的游戏式合作奠定了基础。同时,随着纽约派画家对奥哈拉的诗歌创作影响日渐深远,他尝试将绘画与诗歌创作相结合并越来越重视诗歌的视觉效果。
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在《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HomoLudens:AStudyofthePlay-ElementinCulture)中写道:“游戏活动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有明显的秩序,遵循自愿接受的规则,远离生活必需的范围或者物质的功利。”(2007:145)他认为,“愉悦”是游戏的本质特点,追求愉悦则是游戏精神的核心所在。“游戏的心情或喜不自禁、或热情奔放,游戏的气氛或神圣、或欢庆,视天时地利而定。高扬的紧张情绪是游戏行为的伴侣,欢声笑语和心旷神怡随之而起。”(赫伊津哈,2007:145)奥哈拉与画家们愉悦的互动亦可谓是一种双人游戏,诗人与画家在此过程中享受游戏带来的快乐。他的许多诗歌宛如万花筒一般,充满了自由拼贴的诗歌意象。他设计的一些诗歌排版新颖独特,妙趣横生。罗素·弗格森(Russel Ferguson)在《纪念我的情感:奥哈拉与美国艺术》(InMemoryofMyFeelings:FrankO’HaraandAmericanArt)一书中曾评价:“奥哈拉等纽约派诗人的诗歌创作是一种‘游戏式的自发创作’。”(1999:20)在后现代主义批评家看来,这种“游戏式的自发创作”正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国内外少数学者亦曾注意到奥哈拉诗歌创作中的游戏特点,但极少有人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以奥哈拉的诗歌、诗学主张以及采访为依据,探讨奥哈拉诗歌创作的游戏特点。
1 愉悦的诗画游戏
约翰·赫伊津哈认为:“诗歌在远古具有创造文化的能力,诗歌诞生于游戏之中,它就是游戏,且无疑是神圣的游戏;与此同时,即使有这样的神圣性,它仍然接近于放任、欢快与嬉戏。”(2007:135)诗歌与游戏的渊源可追溯至古代。无论是西方古老的祭祀活动还是中国元宵节的猜灯谜、赛诗、对歌等游戏均与诗歌息息相关。诗歌与游戏最重要的契合点就是“欢快与嬉戏”。这种契合不仅仅是诗歌创作产生的一种外在效果,也是诗人们创作灵感的内在动力之一。奥哈拉与画家们的合作互动便极佳地体现了诗歌与游戏之间的契合,呈现出愉悦的游戏特点。美国当代著名批评家玛乔瑞·帕洛夫(Marjorie Perloff)指出:“诗人与画家的合作是20世纪常见的现象。看似不相关的诗歌与绘画的互动能给人们带来无尽的快乐。”(1997:96)奥哈拉与画家们在游戏互动中创作诗画结合的作品,同时享受着朋友之间互动以及诗歌与绘画的碰撞带来的乐趣。在笔者看来,这种诗歌与绘画互动的乐趣并不是简单的游戏之作,而是针对艾略特为代表的学院派诗歌的反动,奥哈拉在《个人主义:宣言》(Personism: A Manifesto)中宣称他并不是不知晓大家所说的崇高思想,但如何处置这些思想?他认为仅追求思想会适得其反,一旦这些所谓的崇高思想冒头,他必须停住,新灵感方能迸发。他认为许多美国诗人就像老妈子在哄孩子吃煮得过熟的食物,真不知道是否能吃(O’Hara,1983:110)。由此可见,新批评派诗歌主张逃离个性化,对诗歌精雕细刻,讲究结构与秩序,注重文本与细致阅读。这些思想当然既跟不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风起云涌的时代,又与奥哈拉等年轻诗人的诗学观背道而驰。
玛乔瑞·帕洛夫称奥哈拉为“纽约派抽象表现主义诗人”(New York School Abstract Expressionist Poet),其原因是奥哈拉与纽约派抽象表现主义画家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Perloff,1991: 174)。画家拉里·里弗斯以及美国诗人路易斯·麦克亚当斯(Lewis MacAdams)等人在采访、评论中均提及奥哈拉独特的社交魅力,他独特的个性吸引了许多画家与他交流合作并成为好友。奥哈拉在采访中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画家们是唯一对我们的诗歌感兴趣的一群人”,他认为“画家是我们唯一的听众”(O’Hara,1983:3)。奥哈拉与这些画家们心心相印,在艺术领域共同追求自由和创新。
1955年,画家诺曼·布鲁姆(Norman Bluhm)(1)诺曼·布鲁姆是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和行动派画家之一。从巴黎回到纽约,很快成为纽约艺术圈中的一员。奥哈拉经常拜访布鲁姆的工作室,两人时常一边听音乐一边欣赏画作。布鲁姆回忆道:“弗兰克和我都喜欢听音乐。我们经常在工作日上午相聚在工作室,听着音乐聊天、看看绘画作品。随后我们决定边听音乐边玩文字和绘画游戏。”布鲁姆认为他与奥哈拉的合作不是“严肃的艺术创作”,他们两人只想一边听音乐一边游戏(Bluhm,1997:10)。布鲁姆说:“每一幅诗画作品的创作题材均选自滑稽有趣的事。”(Perloff ,1997:107)布鲁姆和奥哈拉一旦聊到有趣好玩的事,两人便会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布鲁姆根据音乐的节奏在纸上画画,而奥哈拉则在纸张的空白处写诗。布鲁姆回忆起与奥哈拉的合作时说:“每一幅作品都不相同。奥哈拉在纸上写诗时,我就在工作室的另一侧,在纸上画些形状。这一切都是即时的,像朋友之间的对话,快速而有趣。”(Bluhm,1997:10)譬如他们一起创作《手掌》(hand)(2)See Bluhm, Norman & Frank O’Hara. Hand. 1960. Gouache and ink, New York University Art Collection.时,布鲁姆用黑色画笔在纸上勾勒出一只半握筷子的手,奥哈拉则在黑色粗大线条旁的空白处写诗——“you eat all the time/ you even know how to use/ chopsticks/ so why don’t you write me/ a letter/ forget it”。零散的诗行从上至下穿插在五个手指头与手指缝隙之间,从小拇指直至大拇指,调侃对方沉浸在美食世界中忘记了朋友。布鲁姆说:“我和奥哈拉都认为这次合作是一种消遣娱乐。我们一起创作纯粹是为了好玩,为了忘却烦恼和忧伤。”(Perloff,1997: 107)出于对快乐的追求,诗人和画家在轻松愉悦的动态互动中展开诗画游戏,两人在游戏中享受艺术创作带来的身心愉悦,忘却生活之烦恼。奥哈拉和布鲁姆共同创作了26幅诗画作品,这些作品趣味十足,呈现出轻松幽默的游戏风格。
弗兰克·奥哈拉与画家合作创作诗画作品的形式和风格是多种多样的。布鲁姆与奥哈拉的合作形式主要以两人共同在纸上绘画写诗为主,速度快。而奥哈拉与拉里·里弗斯(3)拉里·里弗斯是美国艺术家,“奥哈拉与里弗斯初次相遇时,俩人立马就相互吸引”(Perloff, 1997: 50),而后两人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展开了石版画合作。的合作形式主要以互动程度极高的石版画创作为主,耗时虽长但作品内涵丰富。法国文学理论家雅克·埃尔曼(Jacques Ehrmann)指出:“在游戏中,一切都是清晰明了的、动态的互动。”(1968:32-57)游戏者在游戏中不断地互动交流从而推动游戏的进程。这种动态互动在奥哈拉与里弗斯的合作中尤为突出。石版画创作对诗人与画家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诗人与画家需要一起商讨如何将诗歌与绘画反写在石板上。奥哈拉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一起在石头上绘画写诗。如果我不在那儿,里弗斯不会在石头上绘画。如果里弗斯不在一旁,我也不会在石头上写诗。”(O’Hara,1983:4)他们互相沟通交流,商讨应如何在画面中协调诗歌与绘画所处的位置以形成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布局。斯蒂芬·沃尔夫(Stephen Wolf)认为“石头”系列石版画是里弗斯和奥哈拉最成功的合作,其中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两人彼此熟知,他们能凭借直觉相互预测并相互补充;二是诗人和画家同时展开创作,就像双人表演(1998:94)。这种“双人表演”类似20年代中期在美国艺术界流行的偶发艺术(Happenings)(4)偶发艺术(Happenings)是由艺术家们,比如视觉艺术家、诗人、音乐家、作曲家等从各个学科领域出发,进行各种即时的实验性艺术表演。。在奥哈拉看来就是一种“即兴的游戏”,能给人带来“无尽的快乐”(O’Hara,1983:16-17)。在此系列作品中,奥哈拉诗歌中的意象不仅与里弗斯绘制的图像基本一致,而且诗行之间的情感与图像暗含的意义也相互照应。如《忧郁的早餐》(Melancholy Breakfast)(5)See Bluhm Norman & Frank O’Hara. Melancholy Breakfast. Plates 8 of Stones, 1957-60.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中,作品画面里包含了零星分布的厨具和食物,如桌子、煤气炉、烤面包机、排气扇和鸡蛋等。分散的诗行则与七零八落的图画相对应——“blue overhead/ blue underneath/ the silent egg thinks/ and the toaster’s electrical ear waits/ the stars are in that cloud is hid”。作品呈现出清晨厨房杂乱无章的情形,富有生活气息。沃尔夫认为奥哈拉和里弗斯合作的石版画中的诗歌和绘画几乎同时完成并且融为一体,只有两位彼此了解且熟悉彼此作品的人才能有这种形式的动态互动(Wolf,1998:112)。作品中的图画与诗歌相互交融,诗歌成为图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图画也成为诗歌不可分割的成分,诗人与画家在频繁的交流互动中享受艺术碰撞带来的乐趣。
奥哈拉热爱诗歌、绘画、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他为了寻求艺术创作带来的快乐与画家们展开有趣的游戏式合作。诗人和画家通过交流互动将他们所崇拜的艺术家、熟悉的亲朋好友以及自发的情感分别以诗歌与绘画的形式融入作品中。他们在轻松愉悦的游戏氛围中享受朋友之间的乐趣,创作诸多幽默诙谐的诗画作品,体现艺术家追求愉悦的游戏精神。
2 自由的意象拼贴游戏
康德曾多次强调游戏与艺术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认为艺术是自由的游戏(康德,2002:157)。艺术与游戏一样都是自由的、无功利的创作活动。康德认为自由是游戏的灵魂,游戏者在游戏中处于无拘无束的自由状态。席勒在康德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审美游戏说(6)席勒认为人类有两种自然冲动,一是“感性冲动”,二是“理性冲动”,而存在于两者之间并起调节作用的则为审美的“游戏冲动”。游戏冲动的对象是活的艺术形象,用以表明各种现象的审美属性,即最广义的美(17)。席勒认为人们只有凭借想象力在追求自由形式的尝试中,才能飞跃到审美的游戏(142)。,他认为审美游戏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形式”的活动,是真正、纯粹的游戏,而处于审美状态中的人摆脱了物质需求的束缚从而达到外在与内在自由的一种状态(席勒,1984:19)。奥哈拉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在诗歌创作中“渴望变得自由”,并在日记中写到:“我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因此我不追求精致的诗歌结构。我不喜欢诗歌节奏、谐音等技巧,我只管大胆地写诗。”(O’Hara,1983:13-110)奥哈拉内心对自由的渴望成为其诗歌创作的不竭动力,他自由地展开着游戏式的诗歌创作,尽情地书写关于纽约的城市诗歌。
20世纪中期的美国新批评派影响深远,艾略特等人提倡的“非个人化”诗学理念弱化了诗人的主观情感。奥哈拉对此感到非常不满,并多次表明学院派诗歌缺乏创作的乐趣,是一些关于“措辞的愚蠢想法”(O’Hara,1983:13)。奥哈拉在《我们》(US)(7)See Rivers, Larry & Frank O’Hara, US, 1957-1960, Plate 8 of Stones,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中写道:“诗歌在退步,绘画在发展。”他认为学院派诗歌对诗歌韵律和节奏的过度强调抑制了诗歌的多元化发展。相比之下,同时期画家形式新颖的实验性创作促进了绘画的发展。奥哈拉向画家朋友学习,研究绘画,并从绘画中汲取诗歌创作灵感,其诗歌中的拼贴便来源于绘画中的拼贴技巧。“拼贴是一种抽象艺术形式,主要将照片、碎纸片、新闻剪纸及细绳等多种事物并置并粘贴在平面上。”(Cran,2014:3)作为一种全新的创作技巧,拼贴在20世纪被广泛应用于绘画、诗歌、音乐等艺术创作之中。粘贴是拼贴的最大特征之一,艺术家们通过将多种元素粘贴并置,创作出新颖独特的艺术作品。纽约丰富多彩的艺术文化生活宛如一座巨大的拼贴艺术宝库,为奥哈拉提供了丰富的拼贴素材。奥哈拉在《今天》(Today)一诗中写道:“哦!袋鼠,金币,巧克力苏打!你们真美!珍珠,口琴,胶糖,阿司匹林!所有他们经常谈论的素材仍使一首诗成为奇迹。”(O’Hara,1971:15)他运用拼贴技巧将日常生活中的诸多事物、纽约的城市风貌、年轻的艺术家们及诸多诗歌创作经历写入诗歌之中,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歌。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奥哈拉在《第二大道》(Second Avenue)以及《复活节》(Easter)等诗中便运用了拼贴技巧,将日常生活中碎片化的经历拼贴在一起。随后,奥哈拉创作《我做这、我做那》(I do this, I do that)系列诗歌也运用拼贴技巧,记录其多姿多彩的日常生活。罗纳·克兰(Rona Cran)指出:“奥哈拉直接从他的日常生活中选取零星的经历和无关联的画面,并用一种充满生机的、变动的、即刻的拼贴形式剪切在一起。”(2014:160)克兰认为拼贴技巧对奥哈拉来说至关重要,虽然读者无法从字面上看到诗歌中所描述的每个细节,但是奥哈拉将最具代表性的部分拼贴起来吸引读者(Cran,2014:158)。奥哈拉诗歌中自由组合的意象就像万花筒中支离破碎的碎片,碎片之间虽然没有严密的逻辑关系,但是随时可以组合成美丽的图案。诗歌中自由拼贴的意象组合成为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呈现纽约各个角落的城市风貌。诗人用心地生活在城市之中并通过自由的游戏式创作将城市的风貌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诗歌之中,与读者分享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正如卡伦·韦尔(Karen Ware)所说的那样,奥哈拉诗歌中的“语言游戏以及诗歌意象游戏是献给抽象表现主义的赞歌”(2001:8)。
奥哈拉不仅用意象拼贴的方式凸显诗歌的视觉效果,他还将饱含声音的意象混杂在诗歌之中,以呈现诗歌美妙的声音效果,如他的诗作《音乐》(Music):“……阵阵的水柱喷射到水池里的叶片上/ 如同玻璃钢琴的音锤/……如同一个行进中的火车头/……我的门开着,通往仲冬的夜晚/ 雪轻轻地落到报纸上/……午后不久响起的/ 号角!雾气蒙蒙的天……/但是喷泉和雨都停止了……”(O’Hara,1971: 210)。该诗有很多饱含声音的意象:水柱在叶片上的撞击声、嘹亮的号角声、诗人脑海中急越如飞瀑的钢琴声、火车行进的隆隆声以及雪花簌簌飘落的声音等。诗人笔触下一个个饱含声音的意象宛如拟音师手中的道具,在大师的把玩下制造出神奇的效果。诗歌中美妙的声音与纽约街头的“骑士雕像”“五月花商店”“伯格多夫百货店”以及“公园大道”等意象完美融合,构成了一幅视觉效果与听觉效果完美结合的生动画面,呈现出一种无拘无束、心随景游的身心自由的状态。
克兰认为奥哈拉所处年代的正统文学压抑了诗人的创造力,但奥哈拉却一直在努力寻找个人的声音(Cran,2014:137)。奥哈拉在创作中采用拼贴技巧便是其寻求个人特色的尝试之一,表明他拒绝循规蹈矩,渴望摆脱传统诗歌的束缚,追求自由。
3 富有创造力的排版游戏
英国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认为游戏与创造力密不可分:“游戏是一种体验,通常是一种创造性的体验”(Winnicott,1971:67)。创造力是游戏极为重要的特征,“在游戏中,或许只有游戏中,孩子和成人才能充分发挥创造力”,“人们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发现自我”(Winnicott,1971:71-73)。无论游戏者是小孩还是成人,他们在游戏中不受规则的约束,可以尽情地发挥想象力进行创造,丰富的创造力也是愉悦和趣味的重要源泉。奥哈拉十分欣赏法国先锋派的创新精神,他提倡在创作中避免相似和无趣,他说:“如果你是一位画家,那么你应该创作出人们从未见过的作品。我认为避免无趣非常重要。”(O’Hara,1983:9)奥哈拉对创新的追求,在其诗歌排版的设计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他认为诗歌排版是诗歌的外在形式,是显而易见的。他说:“诗歌排版是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诗人以及诗歌身份的确立起重要作用。”(O’Hara,1983:33)奥哈拉在其诗学实践中,不断尝试突破传统的诗歌排版设计,设计了一系列新颖的图形诗(8)图形诗(Pattern Poetry)又称语相诗、视觉诗或者图像诗,是指通过书写、排字、版面设计、印刷等手段,使得诗歌在外形方面发生变异,形成某种图像的诗(刘文清 等,2014:11)。,表现出极强的创造力。
奥哈拉在采访中表示他的诗歌创作受法国诗人皮埃尔·勒韦迪(Pierre Reverdy)(9)皮埃尔·勒韦迪是法国超现实主义以及立体主义代表人,其诗歌短小且碎片化,具有较强的视觉表现力。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10)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是法国著名诗人、剧作家,其诗歌和戏剧在表达形式上多有创新,著有《图像集》(Calligrammes),被认为是超现实主义文艺运动的先驱之一。的影响很大(O’Hara,1971:3)。奥哈拉设计图形诗的灵感便来源于图形诗创始人之一阿波利奈尔。阿波利奈尔同样强调“诗歌必须要有创造力”(Bohn,2010:23)。奥哈拉对《图像集》评价颇高,认为该图形诗排版与诗歌主题相对应,比如“用飘落雨滴形状描写关于雨的诗歌”“用烟斗的形状描写关于吸烟的诗歌”以及“用埃菲尔铁塔的形状描写关于法国的诗歌”等(O’Hara,1983:33)。《图像集》呈现的视觉效果吸引奥哈拉,他也设计出具有同样视觉效果的诗歌排版(O’Hara,1971:33)。例如,他为纪念与画家弗莱希尔(11)简·弗莱希尔(Jane Freilicher)是20世纪中期美国的知名画家,也是纽约派画家中的一员。奥哈拉与弗莱希尔联系密切,彼此之间友谊深厚。的情谊,创作了一首名为“WHE EWHEE”的图形诗,该诗用零散分布的字母勾勒了弗莱希尔棱角分明的脸庞。“whee”是用于表达开心和喜悦之情的语气词。奥哈拉用四个大小写不一致且分行的“WHE/ EHWEE/ W/ hee whee” 绘制右侧的眉毛,传达弗莱希尔眉眼之间的喜悦之情。弗莱希尔的左侧眉毛和眼睛由“angry never /always perhaps/ never always/ like/ are blue velvet/ fluttering/ in one wind”组成,诗人用蓝色天鹅绒丝滑的质感暗示弗莱希尔温和的性格。奥哈拉用零散的字母“you, Jane Freilicher”组成鼻子,用“paint pots”组成下巴,表明弗莱希尔的画家身份以及她常用颜料作画的习惯(O’Hara,1971:25)。在这首诗中,弗兰克·奥哈拉将句子和单词拆分成零星的字母拼凑出一张脸的轮廓,用幽默的方式勾勒出一位乐观的女画家形象。该诗不仅展示出奥哈拉在诗行排版方面的独特创造力,也体现了其游戏于诗画间的创作意图和境界。
奥哈拉设计的诗歌排版不仅与诗歌主题相对应,而且具有丰富的情感内涵。例如,在诗歌《一束鲜花》(A Small Bouquet)中,奥哈拉用文字游戏呈现了世俗爱情之状态。该诗由零散的单词和短语组成一束花,花束由四部分构成,包括一个花瓶、两朵含苞欲放的花朵以及一朵绽放的鲜花。构成左侧花苞的“we do not know what violet”与构成枝干的“calls to us in the”以及充当绿叶的“wet”和“woods”组成了象征世俗的肉体之欲的花朵。中间盛开的花朵主要由“Or whether we really/ truly love the soft rose's effulgence”组成,诗文中“玫瑰的光辉”象征着爱之神圣。右侧花朵由构成花苞的“my whole life’s meaning! but I love you”、构成枝干的“more than”以及充当绿叶的“any flower”组成,揭示了爱情之于生命的重要。花瓶由“Believe me/ that all is not easy/ and I surely adore you/ winter and daytime, too”组成。爱情的维系并非易事,需要一心一意地经营和滋养(O’Hara,1977:9)。花瓶是用来盛放鲜花的容器,为鲜花提供营养液,持久的爱情需要养分的维持。奥哈拉用花瓶以及充满爱意的三朵花组成一束鲜花,呈现了爱情在养分的滋养下保持灵与肉的和谐一致的状态。沃尔特·艾尔(Walter Isle)认为游戏是用新的方式将事物组合在一起,并希望这种新的创造产生意义(1986:63)。奥哈拉通过文字游戏将零散的字母组成一束鲜花,诠释了世俗爱情应有的状态。诗人沉浸在创造性的幻想之中,无拘无束地设计诗歌的排版,并将其想要传达的意蕴镶嵌于新颖的诗歌排版之中,将诗歌的形式与诗人的内心感受结合在一起。
奥哈拉曾说:“纽约和欧洲的一些艺术家,尤其是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家给我一种感觉:一个人应该尝试做些事情而不是仅仅改进那些已被认可的事物,我们应该朝前看,要走得更远。”(O’Hara,1983:3)他用实际行动印证了这一点。诗人沉浸在天马行空的想象之中,发挥其非凡的创造力,不断尝试多种别具一格的图形诗。他的诗集中形态各异的诗歌排版设计,正是他不断创新的成果。
4 结语
玛乔瑞·帕洛夫(Marjorie G. Perloff)认为:“奥哈拉是一位让其诗歌像游戏的诗人。”(Perloff,1977:2)奥哈拉一生痴迷于艺术,享受诗歌、绘画以及音乐带来的乐趣,将艺术完美地融入生活之中。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倾其一身在诗歌领域进行创新实践。他自由地驰骋在游戏场中,将其对游戏精神的追求贯彻于诗歌创作实践,给美国现代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诗风。奥哈拉的游戏式创作摆脱了传统创作的束缚,开创个性化诗歌创作的尝试,影响了许多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