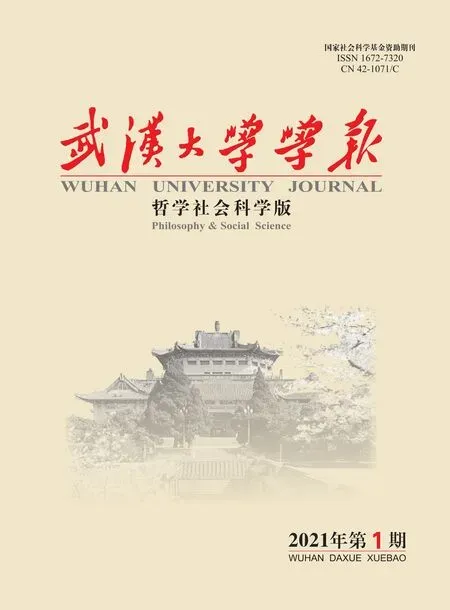托马斯·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主题之疑难的解决
王成军
阅读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读者,总会面对一个著名的与形而上学主题相关的疑难。在其《形而上学》中,亚氏一方面说,形而上学以最为普遍的“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beingquabeing)作为其研究主题并因此是一门不同于物理学、数学等特殊科学的普遍科学(universal science)①本文所用的亚里士多德的相关文本来自Jonathan Barnes主编的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Princeton,1984),相关引文由作者自己译出。按照惯例,本文在引用时,一律标注原著页边码。[1](1003a20-32),一方面又说,形而上学的主题是所谓的“脱离质料且不动”的“分离实体”(separate substances)并因此是“第一哲学”或“神学”[1](1026a10-22)。这意味着,如果《形而上学》呈现的确实是亚氏本人的思想且整部《形而上学》讨论的是同一门科学的话,那么,他将会面临一个显著的难题:一方面,形而上学将是一门以“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为主题的普遍科学,另一方面,它又将是一门以“分离实体”这一特殊类别的存在者为主题的特殊科学。然而,同一门科学如何可能既是普遍又是特殊的呢?作为一门应该具有自身统一性的科学,形而上学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后世的亚里士多德评注者和研究者[2](Pxvi-xxvii,P9-68),相关的争论也从中世纪一直延伸到当代[3](P385-392)。本文将就中世纪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在这一问题上的解决方案进行探讨。本文认为,阿奎那通过对形而上学之主题与目标的区分以及对“分离性”与“普遍性”的重新阐释,将“公共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视为形而上学的主题,将“分离实体”确立为形而上学研究的目标,较好地解决了亚氏的这一难题。并且,阿奎那的这一解决方案并非是对其前人(阿维森纳与阿威洛伊)所述方案的简单综合,而是一个更优的、更具哲学意义的方案,它不仅避免了前人方案的含混和困难,而且还令形而上学真正实现了从神学到存在论的转变。
一、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主题之疑难
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似乎为他所谓的“第一哲学”赋予了四个基本的特征:(1)补遗性,即在别的科学中尚未被涉及的事物应该在这门科学中得到讨论,包括特殊科学所要使用的那些最普遍的原则和术语(如矛盾律、“一”“多”“潜能”“现实”等)以及分离实体;(2)普遍性,即它应该能为其他的科学确立它们的研究主题以及所使用的推理原则;(3)第一性,即它自身的研究主题应该是第一性的、最高级的存在者并因此是最高贵的科学;(4)分离性,即作为物理学和数学之外的另一门思辨科学,它的研究主题不应该像那二者的主题一样或多或少地同质料有关联,而是应该完全“分离于”质料①在《形而上学》第 3卷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关于形而上学主题的 14个“难题”(Aporiai),我们这里所举出的这四个特征就来自对这 14个难题的概括[1](cf.995a24-996a17)。。
也许是为了令自己构想的这门科学能同时满足上述的四个特征,在论及其主题的时候,亚氏显得莫衷一是。在《形而上学》中,他关于形而上学主题的说法大致有:(1)“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以及必然属于存在者的诸属性”;(2)“实体”;(3)“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的所有的形式”,即所有的存在者;(4)“不动的且分离于质料的”“第一实体”[1](1003a20-25,1003b17-19,1003b19-22,1026a10-20)。这四种说法中,前三种的意思实际上是一致的,它们都可归于“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因为在亚氏看来,“实体”(ousia)就是“存在者”(to on/being)的核心意义[1](1003a33-b10),因而研究“实体”就相当于研究“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而(3)强调的则是这门科学的主题在外延上的普遍性,即它应该涉及从其作为存在者这一视角来考察的所有存在者。然而,(4)的主张却很不一样。在这里,亚氏提出了另外一类形而上学的专属对象——“分离实体”。按照他的看法,这些“分离实体”是“分离于质料且不动的”,优于物理学、数学的对象②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可感的存在者,即运动的自然实体,它们在存在上和定义上都依赖于质料;而数学的研究对象(数学实体)虽然在定义上并不依赖于质料,但其现实存在却要依赖于质料,即存在于质料之中[1](cf.1025b30-26a14)。,且是神圣的,故此,研究这类对象的科学是优于那两门科学的“第一哲学”并能被命名为“神学”[1](1026a17-22)。
如此看来,在亚氏那里,形而上学的研究主题似乎应该有两种:“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和“分离实体”。然而,这却令他陷入了一个看似不可避免的矛盾。因为,很明显,“分离实体”似乎应该同物理学研究的“可感且运动的存在者”以及数学所研究的“有量的存在者”一样,都是一类特殊的存在者,从属于“实体”这个范畴。若如此,那么,以这类特殊的存在者为主题的“第一哲学”或“神学”难道不是与物理学、数学一样也是特殊科学(particular sciences)吗?它如何可能是亚氏在《形而上学》第四卷试图建立的普遍科学呢?亚氏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提出了形而上学研究“分离实体”之后,他马上又补充道:
但是,有人会提出疑问,第一哲学是普遍的,抑或它探讨的是某类特别的,也即一类实在呢?……如果的确有某类不动的实体,则研究这类实体的这门科学将优于(物理学)并且是第一哲学,而且,就它是第一哲学而言,它又是普遍的。而探究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也属这门科学——既探究存在者是什么,也探究从属于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的那些属性。[1](1026a23-32)
这一补充表明他似乎想要调和上述的矛盾,但遗憾的是,他的这一核心论证是失败的:因为它是第一哲学,所以它是普遍的,因而也就是那门普遍科学。显然,我们无法从某个事物的“第一性”直接推导出其普遍性;而且,就算我们能推导出其普遍性,我们也无法保证这一具有普遍性的“第一哲学”就是他之前所构想的那门研究“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的普遍科学。当然,为了避免上述推论中的矛盾,我们也可以假定亚氏说的“分离实体”与“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是等同的。但这既不符合逻辑(两个术语的定义是完全不同的),也不符合亚氏的文本(在《形而上学》中,我们找不到任何能够表明二者是直接等同的论据)。最终,亚氏仍然面临着这一巨大挑战:形而上学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如果这门科学研究的既是“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又是“分离实体”,那么这二者是如何统一于同一门科学的?或言之,作为存在论的形而上学与作为“第一哲学”或“神学”的形而上学是同一门学科吗①要解决这个难题,一个最为简单且一劳永逸的方案就是消解这一难题在亚里士多德文本中的合法性,即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形而上学》的编撰历史,证明这本著作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文本,而是由亚氏不同时期思想、不同文体性质的文本乃至其学生的一些笔记“拼贴”在一起的。这样一来,关于形而上学之主题的问题就转化为了一个外在的关于文本历史的问题。比如,Werner Jaeger就认为,“关于形而上学之本性的这样两种阐释显然不是来自于同一个反思”,这一难题乃是因为亚氏不同时期的形而上学思想(前期受柏拉图的影响,以超感的分离实体为核心,后期则形成自己的特色,以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为核心)“熔接”(fuse)在一起造成的[4](P214-220)。此外,Paul Natorp、D.W.Ross等著名亚里士多德研究学者也持有类似的看法[2](P19-29)。但是,这一阐释近年来已基本被学者们否决。而且,这一阐释对本文论及的三位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家来说也并非是一个备选的方案,因为在评述《形而上学》的时候,他们不仅都不曾怀疑过这一文本的统一性,而且也都将其中的思想当作亚氏本人所持有的内在一致的、成体系的思想来对待的。?
二、阿奎那之前的两个主要解决方案
按照现代学者们的研究[5](P136-142)[6](P280-28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留下的这一难题并没有给古希腊的逍遥派评注者们造成太大的困扰,尽管个别评注者(比如 Alexander of Aphrodisias)对此问题有所意识,但他们基本上都将形而上学做了“神学化”(theologizing)的处理,认为形而上学基本是一门研究分离实体的神学。早期的阿拉伯评注者(比如 Al-Kindī)也继承了希腊评注者的这种做法。真正对这一难题有充分意识,给出了比较详细且具有代表性的阐释,并对后来的托马斯·阿奎那造成了影响的,乃是阿维森纳和阿威洛伊这两位最为杰出的阿拉伯哲学家。要理解阿奎那在这一议题上的独特贡献,我们有必要先行了解一下这两位阿拉伯哲学家分别提出的解决方案。
总体说来,在处理《形而上学》留下的这一难题时,两位阿拉伯哲学家恰好各自偏重于我们上述的亚氏为形而上学设定的两个可能主题的其中之一,即确立“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为形而上学主题(阿维森纳)或更倾心于“分离实体”(阿威洛伊)。而他们争论的核心,则特别地与亚氏所提出的一条关于科学的原则相关:任何一门科学都并不处理其自身主题的存在与本性,而是必须将其交给其他科学(一门更高级的科学)来证明并给定[1](1025b15-19,1064a6-10 )[7](71a1,76b5)。
我们先来看阿维森纳的方案。公正地说,阿维森纳大概是西方哲学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意识到亚氏留下的这一难题并进行了充分考察的哲学家[5](P146)。阿维森纳对形而上学主题的探求采取的是一种排除方法。通过排除时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流行意见”,他否定了以“分离实体”(“上帝”)或“所有存在者的终极原因”为形而上学之主题的做法并最终总结说:“这门科学的首要主题便是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the existent inasmuch as it is an existent)”[8](P9-10)[9](cf.P149-153)。
在这一点上,阿维森纳显得非常坚决。但问题是,他为何要排除“分离实体”(“上帝”)之作为形而上学主题的可能性呢?其理由正在于亚氏给出的那条关于科学之主题的规则。在阿维森纳看来,既然任何一门科学主题的存在与本性都需预先由其他科学来给定,那么,形而上学若以“上帝”(或“分离实体”)为主题,则这一主题的存在与本性也必定由其他科学来提供。事实上没有任何一门科学曾经做到这一点。相反,他认为,上帝的存在只能是在形而上学这门科学中被证实,否则将没有任何科学可以证明它[8](P3-4)。但一个紧随的问题是,如果上帝不能成为形而上学的主题,那么,“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又如何可能呢?于此,阿维森纳似乎诉诸一种理智直观的方法或者默认。在他看来,“存在者”(以及“事物”和“必然者”)就是人的理智所能把握的“第一个概念”或“首要的概念”,它(们)“是以一种原初的方式刻印在(impressed)灵魂上的,这一印象的产生并不需要什么被更好地认识的事物”[8](P22),也就是说,它是由我们的理智所直接把握的东西②关于此点,著名中世纪研究学者 John F.Wippel有清楚的论述[10](P39)。此外也有学者提出,阿维森纳在确立“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为形而上学主题时,借助的是所谓的“本体论分离”(ontological separation)这一理智活动[6](P288-299)。。由此,阿维森纳认为,这个“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无需由另一门科学来建立其存在与本性,“我们只需接纳它的存在与其所是就够了”[8](P9-10)。
阿维森纳认为,“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作为形而上学的主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能契合亚里士多德对这门科学的主题提出的“分离性”要求。在阿维森纳看来,就所有的存在者(实体、数字、尺度等等)的现实存在考虑,或者当它们在其他科学中被考虑的时候,的确是跟质料有关的。但是,当它们在形而上学中被考虑时,即就它们本身而言(比如,“作为实体的实体”)或者就它们作为存在者而言,它们却是“不与可感的东西(也即质料)相关联的”,也就是完全分离的[8](P8-9,12)。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对阿维森纳来说,对“上帝”(分离实体)的探究不再是形而上学的一部分了?不然。阿维森纳认为,在谈论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在其“主题”和“被寻求之事”(things sought after)之间做区分。他承认,尽管形而上学的主题是“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但它也涉及对所有其他学科都没有讨论过的事物的讨论,如“作为存在者的实体”“作为实体的物体”“数字”“尺度”“运动”“静止”“一和多”“潜能与现实”“普遍与特殊”等等,包括“非物质的实体”以及“上帝”。他认为,形而上学在对它们进行讨论的时候,也是就它们“作为存在者”而言的;形而上学之所以讨论它们,正因为它们是“无条件地伴随着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在形而上学当中“被寻求之事”[8](P10-11)。考虑到“上帝”就是“每一被造成的存在者(the caused existents)”的“第一因”,阿维森纳还进一步认为,对上帝的研究乃是形而上学的“终极目标”(the ultimate aim)[8](P14-15)。
如此一来,通过形而上学之“主题”以及在其之中“被寻求之事”的区分,阿维森纳似乎不仅回应了亚氏对科学之主题提出的要求,也能够借此将作为存在论的形而上学和作为神学的形而上学统一起来:
它是第一哲学,因为它是对于就存在而言的第一性的东西(第一因)以及就普遍性而言的第一性的事情(存在与一)的知识。它也是智慧,即对于我们所认识的那个最好的东西的最好的知识。……而且它也是对所有被造成之事物的终极原因的知识。此外,它也就是对于上帝的知识并因此被界定为神学,它由对于那些在定义以及存在上可分离于质料的事物的知识构成。[8](P11-12)
尽管在一些研究者看来,阿维森纳对亚里士多德那一难题“给予了最为详尽且最为清楚的阐释”,且“成功地”将《形而上学》中论及的多个主题“统一了起来”[5](P114,146),但另一位阿拉伯哲学家,被誉为“最杰出的亚里士多德评注家”的阿威洛伊却不会这么看。
必须承认,阿威洛伊本人并不反对将“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看作是形而上学的主题并称其为“普遍科学”[11](P60)[12](cf.P22-23)。但不同于阿维森纳的是,他明确指出“分离实体”也是形而上学的主题并进一步将这门科学划分为两个“必要的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作为存在者的可感存在者(sensible beings)以及“存在者”的必然伴随之事(essential concomitants),“第二部分”考虑“实体的原则”即分离实体①阿威洛伊认为形而上学还包括第三部分(“考虑特殊科学的主题并且经由为它们建立原则来消除它们的错误”),但在他看来,这一部分并非是形而上学之必要的部分[12](cf.P25)。。那么,如同阿维森纳可能会反对的,以分离实体作为形而上学的主题难道没有违反亚氏的那条关于科学之主题的规则吗?于此,阿威洛伊认为,他的这一看法不仅没有违背那条规则,而且恰恰就是坚持那条规则的结果。他认为,在这一点上阿维森纳“并没有以任何合宜的方式说出任何东西来”[12](P24),因为阿维森纳并没有看到分离实体的存在及其“非物质的”本性实际上已经由物理学(《物理学》第八卷)证明了[11](P75)[12](P22)。他的理由在于,尽管一门科学的主题通常要在“一门更高的科学”中被证明,但是,这种证明除了依靠从确定的原因或原则推导出结果的“绝对肯定的证明”(apodictical proof)方法外,还有“显示”(indications/dalā'il)的方法,即通过“从在后之事(things that are posterior)推导至在先之事(things that are prior)的方法”[11](P73-74),而《物理学》最后一卷对“不动的推动者”(“第一推动者”)的证明就是在以一种“显示”的方法来为形而上学提供可能的主题。他认为,若非如此,则分离实体的存在与本性根本不可能得到证明,既然对分离实体(尤其是上帝)的证明无论如何不可能通过“绝对肯定的证明”来实现[11](P74)。因而物理学对分离实体的这一证明对形而上学来说不仅绝不是“多余的”(super fl uous),而且还是形而上学研究所必须的一部分“前设”(presuppositions)①他甚至还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s,即“物理学之后”)之名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正是因为这门科学的研究需要预设由物理学证明的那些“非物质的能力”(immaterial potencies),故而《形而上学》的编者才为了“教育的目的”而把它放在《物理学》之后[12](cf.P26)。[12](P24)。这意味着,形而上学以“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和“分离实体”作为主题是完全可能的,既然它们“要么是自明的或几近于自明的东西,要么是在物理学中已经表明的事物”[12](P27)。
由此,阿威洛伊进一步认为,就“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与“分离实体”这二者看,后者才是形而上学真正的主题②绝大部分研究者都相信,对阿威洛伊来说,“分离实体”才是形而上学真正的主题[13](P13-14)[14](P197-199)。但也有个别研究者认为,尽管阿威洛伊坚持物理学已经证明了分离实体的存在并将之提供给了形而上学,但其眼中的形而上学主题仍是那些“普遍事物”,而分离实体作为终极原因“毋宁是这门科学所寻求的并且经由对普遍事物的研究而领会的东西”[15](P185)。。他甚至还说,“鉴于其主题的高贵性,有些人曾认为神圣科学仅仅考虑那些分离的东西”[12](P122)。其大致理由是:既然“(形而上学的)基本目标就是澄清关于可感事物之最为遥远的原因(the most remote causes)的知识”[12](P23),即将可感存在者视为“存在者”来考察并对其“从特殊的方面来考虑的动力因”(造成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而存在的动力因)进行把握,那么这一任务就只能是在讨论分离实体的神学之中得到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考察“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的第一部分形而上学不过是以“分离实体”为主题的第二部分形而上学所作的“准备”(preparation),后者才是这门科学的核心且是前者的“完成与完满”(completion and perfection)[12](P144)。
看起来,因为将其主题根本归结为分离实体,阿威洛伊理解的形而上学更像一门研究一类特殊存在者的特殊科学,或者说,根本上是“第一哲学”或“神学”。那他如何来保证这门科学作为普遍科学的性质呢?阿威洛伊说:既然“第一实体”是其他存在者的原因,因而对它的知识也便是对所有事物的知识,在这一意义上,“第一哲学”(“神学”)就是关于所有存在者的普遍科学[14](cf.P197)。他的基本论证是:在每一事物的属类中,居首位的东西都是该属类之中所有其他成员的原因或原则,也是最合适于该属类的名称来称述的东西,正如“热(heat)在最为专门的意义上称述的乃是那个凭其自身而是所有热的事物的原因的事物(也即火)”,因此,对这一首要的东西的研究就揭示了这一属类所有成员的“实质”(quiddity)。阿威洛伊认为,这一点也适用于“存在者”。既然只有实体才是真正的存在者,在所有的“实体”中,居于首位的正是分离实体(尤其是上帝),故分离实体就是“令(所有)具体事物的实质得以被知晓的东西”[12](P31)[11](cf.P78-79)。也即,一旦我们获得了关于分离实体的知识并且发现分离实体正是所有其他实体的终极原因,那我们也就获得了关于实体的最终知识,并进一步获得了关于“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或所有存在者的最为完备而确定的知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阿威洛伊声称“智慧(也即形而上学)就是对于第一原则的知识以及从第一原则的视角来看待的关于存在者的知识”[11](P207),这意味着以分离实体作为核心主题的形而上学仍不失为一门普遍科学。
至此我们看到,对亚氏留下的难题,阿维森纳和阿威洛伊根据各自的理解给出了殊为不同的答案。在前者看来,形而上学的严格主题应该是“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分离实体只能作为“被寻求之事”或“目标”出现在形而上学之中,这表明形而上学在本性上是作为普遍科学的存在论,但凭其最终对“上帝”这一第一因的揭示,它也成为“第一哲学”并部分地是神学。而对后者来说,形而上学的主题归根结底是“分离实体”,这门科学的性质因而也首先是神学和“第一哲学”,只是因为对分离实体的研究可以获致对所有存在者的知识,它才衍生出了“普遍科学”的意义。据 John F.Wippel的说法,阿维森纳和阿威洛伊在这个难题上的分歧在十三、十四世纪的经院学者中“非常闻名”[3](P386),故我们有理由认为,托马斯·阿奎那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或多或少受到二者的影响。但这并非如一些研究者所言,阿奎那只是“采取了阿维森纳的基本理论框架”,再根据阿威洛伊对之的批评做出“修正”[16](P87)。事实上,阿奎那在此问题上有完整、独特的思考,绝非对前述两个阿拉伯哲学家的简单综合。
三、阿奎那的解决方案
与前述的两位阿拉伯哲学家一样,阿奎那对形而上学主题的确定也是从各门科学的比较与划分开始的。在《〈形而上学〉评注》“导言”里,阿奎那提出,作为一切科学中最高级的一个门类,形而上学应该“在理智的程度上是最高的”,正如“在智力上优越的人自然就是其他人的统治者和主人”。既然如此,形而上学的主题应该满足的一个必要标准就是:它应该是“最可理解的对象”(the most intelligible objects)[17](Pxxix)。这个“最可理解的对象”,在他看来可以从三种意义上进行理解:(1)从“认知的次序”来讲,既然我们总是通过把握一个事物的原因才获得了关于它的确定知识,则一个原因越是能给我们提供确定的知识,它对我们的理智来说就越可理解。因而,“最可理解的对象”指的就是“第一原因”。(2)从“理智与感觉的比较”来看,如果说感觉是对个体的把握,那么理智应该是对“普遍之物”的领悟,因而对我们的理智来说,“最可理解的对象”就应该是“最为普遍的原则”,即“存在者”(ens/being)以及那些自然伴随存在者的东西(比如“一”与“多”、“潜能”与“现实”等),概言之,就是“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或者说“公共存在者”(ens commune/common being)。(3)从“理智自身的知识”来看,知识的对象越是分离于质料,相应的知识也便越高级,所以最高级的知识应该是对最为分离于质料的对象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最可理解的对象”即同时在定义和存在上分离于质料的事物,此即“上帝与灵智实体(God and the intelligences)”或“分离实体”[17](Pxxix-xxx)。
在列出上述的三类对象后,阿奎那立即将(1)和(3)进行了归并,因为在他看来,(1)说的“第一因”正是(3)说的“分离实体”。既然“分离实体”就是存在者的“普遍的且第一的原因”[17](Pxxx),作为形而上学主题的候选项就只剩下(2)说的“公共存在者”以及(3)指的“分离实体”,而这正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给出的两种。我们之前说过,如果同时坚持这二者都是形而上学的主题,就不可避免会带来阐释上的困难。阿奎那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紧接着又排除了(3)并且明确说:“尽管这门科学(形而上学或第一哲学)研究上述的三类事物,但是它并不将它们之中任意一个当作其主题来考察,而是仅仅将普遍的存在者(也即‘公共存在者’)当作主题考察”[17](Pxxx)。
为此,他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论证:作为一种理智活动,科学之“成全”就在于通过探求某类事物的原因来获得对该类事物的知识[18](P49)。所以任何一门科学都包含两个必要的要素,一是其特定的主题(其“形式对象”,formal object),另一则是其追求的目标(goal)(其主题的原因或原则),而且这二者之间有着明确区分:一个是研究的对象,一个是对那一对象进行研究的结果[17](cf.Pxxx)。正如物理学会同时涉及它们的主题“运动的事物”以及其运动的那些原则和原因,形而上学也同时涉及“公共存在者”与“分离实体”,但是只有前者才是形而上学所直接考察的专属对象或者主题,后者毋宁只是我们通过对前者的考察来间接把握的形而上学之“目标”①事实上,在《〈形而上学〉评注》中,阿奎那不止一次地强调了形而上学主题和目标的这一区分[17](cf.Pxxx,198,696)。。
如果形而上学以“公共存在者”为主题的话,那么它能否满足形而上学主题应该具有的“分离性”特征呢?阿奎那的回答是肯定的。在他看来,事实上,不仅仅是形而上学,即便是物理学和数学这两门理论科学,其主题对象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分离性的标准。这是因为,既然科学是理智的活动,而我们的理智本身是非物质性的,这便要求其对象也是非物质性的,而且还必须是“不动的”(immobile)东西而非处在变异中的偶然之物[18](P13-14)。换句话说,尽管思辨科学的对象在实在中未必分离于质料与运动(比如物理学所考察的自然实体),但是,当它们在我们的心灵中作为知识的对象被考察时,它们必定都抽离了个体化的物质性特征,以一种抽象化的、普遍化的形式呈现给我们的理智。这是否意味着,所有理论科学将无法区分呢?如果有区分,其标准会是什么呢?
于此,阿奎那进一步认为,尽管理论科学的对象就其作为理智的对象来讲都具有分离性的特征,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它们之间没有区分。它们的区分取决于我们以怎样的方式,或者说从何种视角来思考它们。这一视角在他看来,就是我们的理智所反思到的“它们分离于质料与运动的程度”[18](P14)。很显然,物理学和数学作为思辨科学的两个门类,其研究主题无疑就是这样区分的,即物理学的主题被我们的理智视作“同时在存在上和定义上依赖于质料的东西”(运动的或者说可感的存在者),数学的主题则被我们的理智视作“在存在上依赖于质料然而在定义上不依赖于质料的东西”(线或数等“数学实体”)。那么剩下的一门思辨科学的对象即形而上学的对象,就只能是“在存在上和定义上都分离于质料的东西”①注意,阿奎那根据与质料以及运动的关系而划分出的思辨科学的这三类研究对象已经穷尽了所有的可能,因为“在存在上不依赖质料然而在定义上却依赖质料的东西”是不可能的[13](cf.P9)。[18](P14)。问题是,若说“分离实体”满足“在存在上和定义上都分离于质料”这一标准倒很好理解,但说“公共存在者”或“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也满足这一标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以分离实体作为形而上学的主题不是正好满足这一标准吗?阿奎那对此的回答是,“在存在上和定义上都分离于质料的东西”有两种意义:一是指绝无可能在质料之中存在也不依赖于质料而被理解的事物,此即上帝、灵智实体等“分离实体”;一是指不依赖于质料就能被理解,然而却并不必然存在于质料之中的东西,即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存在于质料之中但却完全可以不存在于质料之中的事物。在他看来,“公共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即是如此,因为当“存在者”指涉自然实体或数学实体时,它无疑存在于质料之中,而当它指涉分离实体时,它并不存在于质料之中,这也就意味着,整体而言,它并不必然存在于质料之中[17](Pxxx,402)[18](cf.P14)。因而阿奎那认为,当我们说形而上学的主题是“公共存在者”或“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时,它也完全满足这门科学的主题所要求有的分离性,而且很显然,相比较于另外两门思辨科学的主题,它与“质料以及运动”的分离程度也是最为彻底的,因而也符合“最可理解的事物”这一标准从而确立其在诸门科学中的最高地位。
当然,与他的两位阿拉伯前辈一样,阿奎那也要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果说“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是形而上学的主题,那么,它是如何被给定的?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像阿威洛伊一样将形而上学主题的给定诉诸“另一门科学”(物理学),也没有像阿维森纳那样将之诉诸一种单纯的理智直观或者默认,而是将之诉诸我们理智的一种特殊运作——“分离”判断。
在阿奎那看来,我们的理智有两种运作,一是“对不可分者的理解”(understanding of indivisibles),即对于“一个东西之所是”的领悟;二是“判断”(judgement),即对我们在前一种运作中所领悟的事情进行肯定或否定陈述的过程。阿奎那认为,如果说第一种运作关系到一个事物的本性,那么第二种运作则关系到一个事物的存在(esse/Being)[18](P34-35),也即,鉴于命题与实在的一致性,当我们就某物 X形成“X是 Y”或“X不是 Y”这样的命题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在就X的某种性质进行陈述,我们还是在就其存在进行把握:X作为Y存在或者X不作为Y存在②新托马斯主义者将阿奎那的这一理论称为“存在判断”(Existential Judgement),其代表人物 Etienne Gilson对此有过出色的解释[19](P190-210)。。进而他指出,物理学和数学之主题的建立与第一种运作即单纯的领悟(apprehension)或理解有关。然而,形而上学对象的确立却只能依赖后一种理智的运作,特别是他称之为“分离”(separatio/separation)的否定判断[18](P35-41)。其原因大概在于,如果说形而上学的对象是“公共存在者”,则有一点很明确,它不是一个严格的种属概念(因为任何试图将之进行进一步划分的种差都属于“存在者”这一范畴),也不是事物的一种性质或形式(不像“可变动的”或“有量的”),因此它不能在单纯理解或者领悟的意义上被我们的理智从具体的存在者之中抽象出来,只能借助于判断[13](cf.P48)[19](cf.P190-210)。那么,我们理智的第二种运作(判断)如何能确立作为形而上学对象的“公共存在者”呢?阿奎那本人并没有对此进行详细说明,但按照一些新托马斯主义者在阿奎那形而上学框架内进行的解释[13](P36-40,44-49),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我们利用肯定的复合判断(composition)把握“有存在者存在”这一原始事实,即利用“X1是 Y1”“X2是Y2”……“Xn是Yn”等一系列判断来确立一些事物在我们心灵外的实在,并在这类判断基础上形成对“存在者”(that which is/being)的“模糊且普遍的”概念;第二步,我们再借助“分离”判断进一步确定“我们能就其作为存在者来考虑它”,即借助于“存在者本身不是可感的存在者”“存在者本身不是有量的存在者”或“存在者本身不是任何一类给定的特殊的存在者”之类的分离判断,我们就能将“存在者”从各类特殊存在者中“分离”出来并最终发现“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或“公共存在者”。由此,形而上学的主题得以给定,这门科学也由此而成为一门可能的科学。
那么,对阿奎那来说,剩下的问题是:形而上学的普遍性如何能得到说明。这看起来不是一个问题,既然他已将最为普遍的“公共存在者”确立为形而上学的主题,而在这门科学中涉及的一切存在者都可归于这一术语或属类。但是,既然这门科学以那些“分离实体”为研究目标且不可避免地涉及它们,那么,一旦它们不能像那些可感的存在者一样被归并为“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而在这门科学中被研究,这门科学的普遍性似乎就依然是不彻底的,或至少是可被质疑的。面对这个曾经困扰亚里士多德及其评注者的难题,阿奎那的解决办法是对“普遍性”(universality)一词做出新的界定。在阿奎那看来,“普遍性”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称谓的普遍性”(universality of predication),正如一个种相名词(“人”)能够称谓所有的在这个种之下的个体(“张三”“李四”等等),“存在者”这个词能称谓所有的存在者[17](P522,646),当我们说研究“公共存在者”的形而上学是普遍科学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在这种普遍性之外,还有另一种“因果的普遍性”(universality of causality),即如果一个事物是许多事物的原因(比如一条物理规则),则这个事物可以被我们视为“普遍且公共的原因”(universal and common cause)。如此说来,“分离实体”(特别指上帝)无疑是最为普遍且公共的原因,既然它是一切存在者作为存在者存在的原因[17](P402)[18](cf.P50)。因此,即便这门科学涉及对分离实体的讨论,也丝毫无损于它的普遍性;相反,这还加强了它作为普遍科学的地位,即不仅其主题(“公共存在者”)是最为普遍的,而且其考察所要达到的目标,也就是其主题的原因也是最为普遍的。正是出于这一考虑,在评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为了说明研究分离实体的“第一哲学”与“普遍科学”的统一性而给出的“因为它(分离实体)是第一的,因而也是普遍的”[1](1064b14)这一论证时,阿奎那特别说道:“因为它是第一的,它也必定是普遍的,因为,讨论首要存在者(primary beings)的科学与处理普遍的(存在者)的科学是同一门科学,既然首要存在者就是其他存在者的原则”[17](P731)。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借助对科学的“主题”与“目标”之间的区分以及对“分离性”“普遍性”的阐释,阿奎那有效地消解了亚里士多德的那一难题。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在肯定“分离实体”与“公共存在者”不同(正如原因与其后果不同)的前提下,通过把“分离实体”界定为研究目标,把“公共存在者”界定为形式对象或主题,把二者统一到形而上学这门科学之下,并且维持其作为普遍科学的本性:
因此,按照我们上述的三类令这门科学得其成全的对象(也即前述三类“最可理解的对象”),它有了三个名称。它被称作神圣科学或神学,因为它考虑上述实体(也即分离实体)。它被称作形而上学,因为它考虑存在者以及那些自然伴随存在者的属性。而它被称作第一哲学,乃因为它考虑事物的第一原因。[17](Pxxxi)
四、阿奎那方案的理论优势与哲学意义
至此我们看到,同前述的两位阿拉伯哲学家一样,阿奎那也试图在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框架内给予形而上学确定的主题并协调作为存在论的形而上学与作为“第一哲学”或“神学”的形而上学之间的张力。笔者认为,相较于两位阿拉伯哲学家提出的解决方案,阿奎那的方案有着其独特的理论优势和哲学贡献。
首先,阿奎那的方案成功地避开了两位阿拉伯哲学家方案中的歧义、模糊和不一致之处,维持了形而上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整全性与统一性,从而比前二者要更优。
如前所述,在阿奎那看来,一门科学的实质就在于以我们的理智去把握一类对象事物的原因,这一界定同时指涉一门科学的主题与目标。所谓一门科学的“主题”,乃是指这门科学的“形式对象”,即我们的理智从特定的视角(perspective)对事物进行的考量。拿阿奎那喜欢用的类比来说,这就好比,尽管一个“有颜色的物体”是我们看的对象,但只有“颜色”才是“视觉”的真正对象。所谓科学考察的“目标”,则是把握主题对象的原则和原因,也就是它为什么如我们所考虑的这样[20](cf.Pxv-xviii)[21](cf.P117-118)。无疑,这是一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理解,它同时也为前述的两位阿拉伯哲学家所接受。然而,如果仔细反思一下那两位阿拉伯哲学家的方案的话,我们会发现,它们似乎并没有彻底遵循这一“科学”界定,从而留下了种种混乱和歧义。
我们先检讨阿维森纳的方案。尽管一些研究者认为,阿维森纳的方案给予了亚里士多德的那一难题以“最为一致且系统的阐释”,因而是一个“成功的”方案[5](P115)。但是他们疏漏了阿维森纳方案中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尽管他借助“主题”和“被寻求之事”的区分否定了分离实体作为形而上学主题的可能,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于上帝与形而上学的主题(“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到底是什么关系,阿维森纳却并没有说清楚[10](P37-38)。看起来,当阿维森纳把“上帝”与“一和多”等“伴随着存在者的诸偶性”一起归为在形而上学中“被寻求之事”时,当他在其形而上学中把上帝称为“那个必然的存在者”(the necessary existent)[8](cf.P29-38)时,他似乎只不过是把“上帝”看作是“存在者”的一个范例,尽管这个范例是最高级且纯粹的。换句话说,“上帝”在这门科学中是被放在“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这个术语下讨论的①有许多研究者都已指出[3](P386)[6](P299)[13](P18),阿维森纳实际上是把“上帝”等分离实体理解为了“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的一部,在这个意义上,讨论“上帝”的神学成为讨论“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的存在论的一部分。因此,尽管阿维森纳承认分离实体(上帝)是形而上学知识的“终极目标”,但这一“目标”与形而上学作为一门科学所要达到的“目标”并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如果形而上学追求的“目标”是通过对其主题(“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之原因或原则的把握来获取对其主题的知识,即“对于(所有)存在者的终极阐释”的话,那么阿维森纳所谓的“目标”毋宁只是形而上学考察之路要达到的终点或顶峰,即“对于终极存在者的阐释”。这一点也在阿维森纳谈到这门科学所要把握的“原则”到底指什么时得到了清楚的印证:“存在者之整体没有任何的原则可言,仅仅对于被造成的存在者来说,一个原则才是原则。这一原则因此是存在者之一部分的原则。故此,这门科学并不以绝对的方式来调查存在者的原则,而是仅仅调查在其中的某些事物的原则,正如特殊科学所做的那样。”[8](P10-11)
更致命的是,阿维森纳把“上帝”等分离实体归并到“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的做法还不得不面临一个阿威洛伊式的诘难:如果如阿维森纳所说,“上帝”等分离实体的存在只能在形而上学中得到证明,而且,很清楚,它们也并不如可感存在者那样是我们可以凭“直觉”把握的事物,那么,在开始形而上学的研究之前,它们是如何可能被预先把握并被归入“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呢?很显然,他无法回应这一诘难。
那阿威洛伊的方案是不是就没问题呢?不然。的确,阿威洛伊说过,“形而上学寻求对(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的原因的陈述,而这些原因只有关于神性与神圣的事物(the divinity and the divine things)时才能得到陈述”[12](P23)。这听起来似乎很符合对“科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界定,即通过原因来阐释主题。但是,在阿威洛伊把“分离实体”也视作形而上学主题,并将对“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的讨论也归结为对“分离实体”的讨论时(这与阿维森纳的思路刚好相反)时,他不仅未能保有一门科学的主题和目标的清晰区分,而且还制造了新的困难。
如我们所见,在阿威洛伊那里,研究“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的存在论与研究“分离实体”的神学是形而上学中两个不同且存在递进关系的部分;而且,在主张形而上学有双重的主题之外,他似乎还为之设置了双重的目标。在对《形而上学》第十二卷进行评注的一开始,阿威洛伊就表明了这一点:“在有些卷中,他(指亚里士多德)讨论的是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的特征(characteristics),但在这一卷中,他讨论的是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的原则以及那个绝对实在的第一实体的原则。他乃是通过表明存在着一个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的实体以及这个实体是什么而做到这一点的。对于这个实体的阐释是这门科学的最终标靶( fi nal aim)。”[11](P59)这段话暗示,一方面如我们已指出的,在阿威洛伊看来,形而上学的主题是双重的,并且分离实体,更确切地说作为“第一实体”的上帝才是其真正的主题;另一方面,这也导致形而上学的目标也将是双重的,即揭示“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的原则”以及揭示“第一实体的原则”,而且后一工作才是其终极目标。这表明,尽管其致思路径和阿维森纳大为不同,但是,阿威洛伊所理解的形而上学的最终“目标”也仍然是“对终极存在者的阐释”,只不过在他的理论框架内,这一“对终极存在者的阐释”也是“对存在者的终极阐释”。
但阿威洛伊的方案会带来两个困难。一个明显的困难是,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框架内来理解,一门科学的统一性在于其“形式对象”即主题的统一性,然而很显然,阿威洛伊所设立的双重主题尽管都可以归为“在存在上和定义上都分离于质料的”,但它们的所指却是非常不同的:一个是我们从最普遍方面考虑的实在,另一个则是前者之首要的部分并且是其终极原因。因此,一旦将分离实体也视为形而上学的主题,他就始终摆脱不了亚氏的那个难题:形而上学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它究竟是两门科学还是一门科学?由此看,阿威洛伊把分离实体树立为形而上学主题的做法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更符合亚里士多德文本的原意,但根本无助于解决亚氏的难题,反而是沿袭了其混乱。另一个潜在的然而却更为严重的困难是,如果阿威洛伊严格坚持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科学界定,那么,当他将分离实体尤其是上帝作为形而上学的一个主题的时候,形而上学就必须要寻求这一主题的原因,即寻求“第一因”的原因。这无疑也是令人困惑的:既然他所谓的“第一实体”就是所有存在者的第一因,而且是“自因的”,那么说寻求“第一实体的原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按照一些研究者的解释,阿威洛伊的这一说法“很可能意谓某种类似于‘本质特性’(essential properties)的东西”[22](P12),但无论如何它并不是一门科学所要求的对其主题的最终理解——揭示主题事物为何如此的原因。换言之,如果形而上学真的以“第一实体”作为主题的话,那么它就不能满足于谈论“第一实体”的“本质特性”,正如物理学不能仅仅满足于讨论“运动的存在者”的特性。如此说来,当阿威洛伊为形而上学树立了双重的主题,并且试图通过将研究“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的存在论归并到研究“分离实体”的第一哲学或神学来维持形而上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统一性的时候,他终究也无法避免其阐释的模糊性并完全满足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科学界定。
相较之下,阿奎那的方案似乎要比他的两位前辈的方案更加严格地维护了形而上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统一性与整全性,而且,他的阐释也更为清楚且小心地避开了这二者方案中存在的问题。通过严格区分科学的“主题”和“目标”并坚持形而上学主题的单一性,阿奎那由此避免了阿威洛伊可能面临的困境;同时,鉴于阿奎那曾不止一次地明确指出,上帝是“存在之现实”(actus essendi/the act of being)或“存在自身”(ipsum esse/Existence itself),与一切存在者(ens/existent)有着根本的区分①对阿奎那来说,“存在者”(ens/being)意味着“拥有存在的东西”(esse habens/something having existence)[17](P770),而这暗示了存在与本质的区分。但是对于上帝来说,其本质也即其存在,因此,其作为“纯粹的存在”,超出了“存在者”这一范畴,否则,其不可能“不落入任何一个属类”且“不能增添任何东西”[23](P116-121,126-128)[24](P55-58)。,因此,不仅他眼中的这个“上帝”并不归属于“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这一主题,而且,在它是一切存在者现实性的根源这一意义上讲,“上帝”就是形而上学所要寻求的“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的终极原因,而非仅仅是如阿维森纳所说的那样是现存的存在者(即所谓的“被造成的存在者”或“(存在者中的)某些事物”)的终极原因②阿奎那曾明确表示过,“既然任何科学都寻求其主题之特有的原因”,那么形而上学要探求的“终极原因”就是其主题“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的原因[17](P198)。无疑,在他看来,形而上学所寻求的这个终极原因就是上帝,于此,他说得很明确:“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以上帝自身作为其原因。”[17](P418)由此可见,阿奎那对作为终极原因的上帝的理解跟阿维森纳的理解有着明显差异。。这样一来,尽管他与阿维森纳一样坚持分离实体(上帝)并不是形而上学的主题,但是他成功避开了阿维森纳的含混和论证负担,真正地将形而上学构建为一门整全的、同时包含着明确的主题和目标的科学。
其次,阿奎那的方案之所以是一个更优的方案,也是因为他的这一方案在解决亚氏留下的难题的同时,也为带有神学色彩的形而上学或者说“哲学神学”(philosophical theology)与宗教神学或者说“启示神学”(revealed theology)划定了清楚的界限,从而保全了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哲学知识的独立性并真正建立起了一种存在论,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
如我们前面所说,阿维森纳和阿威洛伊都试图在形而上学里把存在论与神学统一起来,尽管他们的思路迥异,但是他们至少在这一点上是不谋而合的:他们始终未曾摆脱先前的评注者对《形而上学》的“神学化”处理,认为神学才是形而上学的真正意义所在。在阿威洛伊那里,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他把分离实体视为形而上学的真正主题,把讨论“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的“第一部分”形而上学看作是讨论分离实体的“第二部分”形而上学的“准备”。就阿维森纳而言,尽管他始终强调形而上学的主题是“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但当他强调形而上学的“终极目标”就是“关于上帝之统治、精神性的天使及其等级的知识,以及关于天体的被安排完好的秩序的知识”[8](P14-15)时,他强调的仍然是这门科学的神学意义。故此我们看到,在这两位哲学家的形而上学当中,神学内容占了相当大的篇幅①在阿维森纳那里,他不仅试图讨论上帝的存在,而且还试图讨论上帝的属性(“爱”“纯粹的善”“和平”“一”等等)、上帝与世界的关系(“被造成的存在者”如何从上帝那里被造)、受造者的秩序、天使、天体以及天体与人的关系等等[8](cf.P21-22)。在这一点上,阿威洛伊也不遑多让,在其形而上学的“第二部分”,他同样以极大的热情讨论了分离实体的“存在的种类”“数量”“与可感实体的联系”“在存在上的相互关联”“位阶秩序”等等[12](cf.P133-134)。。很显然,在这两位哲学家心目中,无论形而上学的主题是什么,神学才是其核心的部分并且是其旨归。他们的区别或许只在于,对阿维森纳来说,形而上学虽是存在论,但神学是其核心的且最高的部分;对阿威洛伊来说,神学和存在论是形而上学两个相对独立的构成部分,但神学是存在论的归宿和完成。
当我们审视阿奎那的形而上学时,我们发现,他对形而上学所具有的神学色彩始终抱有一种谨慎的态度。与两位前人不同,阿奎那并没有在其形而上学中过多涉及神学的内容,除了论证“上帝的存在”。这是因为,他始终坚持分离实体(上帝)只能作为形而上学主题即“公共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的原因在这门科学中出现,它们如果要作为主题得到讨论,就只能是在真正的神学即启示神学之中。于此,阿奎那曾清楚地指出:“分离实体”可以在两种意义上来考虑,一种是“就其作为其他事物的原则”来考虑,一种是“就其自身的完全本性”来考虑。当它们出现在形而上学中时,它们是在第一种意义上来被考虑的,即作为“公共存在者”的原则来被考虑的;然而,如果要在第二种意义上来考虑它们,则只能是在一门“独立的科学”即“圣经所教导的神学”(theology taught in Sacred Scripture)中[18](P49-53)。阿奎那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对神学的区分,其深层的理由在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尽管“第一原则”在其自身是“最为显明的(evident)”,但当我们的理智去思考它们时,“莫若猫头鹰的眼睛去凝视太阳的光芒”,藉着自然理性之光,人只能通过那些原则的后果才能企及它们[18](P51)[25](P1-2)。这意味着,在阿奎那那里,形而上学对分离实体的讨论尽管的确是形而上学的完成而且是人类自然理性所能达到的极限,但它绝不是如两位阿拉伯哲学家所设想的那样是人类知识的终结或者“所有科学的完成”[12](P26),而是形而上学与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启示神学的临界点。
阿奎那对形而上学之神学色彩的这一限定有着特别的哲学意义。乍看起来,阿维森纳和阿威洛伊倾向于主张理性地处理神学议题的合法性②在这一点上,阿威洛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甚至认为宗教信仰应该以自然理性或者哲学为基础[26](cf.P41-42)。,这似乎是对人类理性的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也抬升了哲学的价值。但是换个角度来考虑,他们将神学作为形而上学核心内容的做法,无疑混淆了哲学与神学,也取消了或者至少是削弱了形而上学作为存在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哲学知识的本性。在中世纪哲学的大背景下,这很难说是对哲学的一种贡献而不是侵害,毕竟哲学与神学无论在对象上还是在方法上都颇有不同,本是两个有着清晰界限的知识领域。比较而言,阿奎那的方案对于保全形而上学作为哲学的独立性来说未尝不是一种更佳的处理。正是因为他始终坚持对形而上学所起到的神学功能的限定,从而真正地将形而上学从神学手里拯救了出来,保全了其作为存在论的本性①有人可能会疑惑,阿维森纳的方案难道就没有强调形而上学之作为存在论的本性吗?本文以为,阿维森纳对形而上学的界定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存在论,其理由至少有两点:首先如我们所分析的,即便他主张形而上学的主题是“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但他强调得更多的是神学;其次我们没有提及的是,因为把“存在”视为事物拥有的一种“偶性”或“属性”[8](cf.P23-24,37),阿维森纳所说的“存在者”实际上指的是一种“此时此地的实在”(here-and-now reality)而非“存在者”自身,而形而上学的工作也因此变成了考察任何一个事物的“此时此地的实在”而非“存在者”自身的本质结构和原因[14](cf.P211,222)。在这个意义上,他理解的形而上学并非真正的存在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21](P123,157),在阿奎那这里,形而上学的核心才真正从“超越的”(the transcendent,即上帝)转变为“超验的”(the transcendentals,即普遍意义上的存在者及其特性),形而上学也才在西方哲学的历史上真正地完成了从神学向存在论的转变,从而促成了“形而上学的第二次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