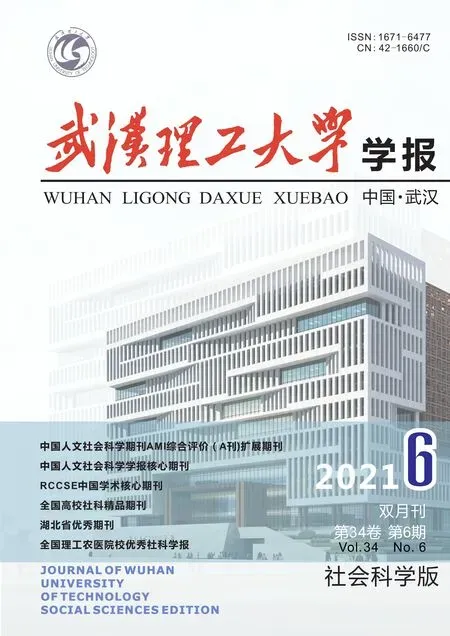文化“窄道”上的旅居者
——评拉比·阿拉梅丁的小说《历史的天使》
甘文平, 张 越
(武汉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武汉 430070)
一、 引 言
拉比·阿拉梅丁(Rabih Alameddine,1959—)是黎巴嫩裔美国作家。他出生在约旦阿曼的一个黎巴嫩家庭,在科威特和黎巴嫩长大,17岁去了英国,后来到了美国。他最初是一位工程师,后来转向文学创作和绘画,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和旧金山大学获得工程学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目前在旧金山和贝鲁特两地生活。到目前为止,阿拉梅丁先后创作了《酷爱》(Koolaids:TheArtofWar,1998)、《我,神性》(I:theDivine:ANovelinFirstChapters,2001)、《讲故事的人》(TheHakawati,2008)、《一个多余的女人》(AnUnnecessaryWoman,2013)、《历史的天使》(TheAngelofHistory:ANovel,2016)四部小说和一个短篇小说集《变态》(ThePerv:Stories,1999)。其中,《一个多余的女人》获得2014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历史的天使》获得2017年阿拉伯裔美国人图书奖和同性恋小说类的朗姆达文学奖。阿拉梅丁的小说大多采用写实与虚构相结合的写作手法表达了死亡与性爱、宗教与战争、(男)同性恋与艾滋病、创伤和记忆等“当时许多西方作家避而不谈的主题”[1],因此,阿拉梅丁的作品在当代世界文坛独树一帜。
《历史的天使》出版后立即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关注。除了上述提到的主题以外,西方学者认为该小说表达了“政治”[1]、“存在主义”[2]、“成长”[3]、“男同性恋共同体”[4]等主题①,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②、一部爱情书信小说③。但是,这些文章几乎都是简短的书评,国内尚无《历史的天使》的相关评述。
《历史的天使》的主人公名叫雅各布,是一个阿拉伯裔美国人,喜欢诗歌。他沉浸在失去同性恋朋友的悲痛之中,后因从电视里看到美军炸死他母亲家乡的无辜百姓而导致精神崩溃。于是他希望通过药物或者医生干预治愈自己的创伤。雅各布通过“日记”、“故事”、“在诊所”三种方式向他死去的同性恋男友多克“倾诉”自己的一生,该部分内容构成小说的主体。小说的另一部分内容由撒旦与死亡以及十四位圣人的“会话”构成,是对前面内容信息的补充。以上四种叙事形式交叉出现,共同叙写了主人公雅各布从童年到中年、从中东到美国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此外小说主要的人物还有雅各布的母亲和她的好友巴蒂亚。这些故事人物随着时序倒错的故事情节在虚实空间之间交替出现。本文拟分析雅各布人生三个阶段的旅居生活:童年时期以妓院为家的“妓院文化启蒙”、青年时期与同性相恋的“同性恋文化体验”、中年时期“与魔为伍”的“异教文化选择”。在西方文化霸权和美国白人文化霸权的统治下,主人公只能是文化“窄道”上的一个旅居者。主人公的经历见证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文化霸权和美国白人文化霸权的统治性以及少数族裔文化身份与命运之路的边缘性。
二、 以妓院为家——童年时期的“妓院文化启蒙”
雅各布和母亲离开家乡之后开始了流浪之旅,他们的第一站是埃及的妓院,他在那里亲历了“妓院文化启蒙”。西方文明掩盖下的欧美白人男性展现出的淫欲、欺骗、兽性行为及其给雅各布和其他女性带来的伤害,成为雅各布童年时期“妓院文化启蒙”道路上的特殊“风景”。
20世纪60—70年代,埃及社会动乱,平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整个埃及正处于不知所措和四分五裂的境地。贫穷……埃及是一贫如洗,每个埃及人都是一贫如洗。我们几乎是在乞求武器,甚至是在乞求糊口的面包”[5]。为了尽快发展经济,埃及新政府不得不向美国等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求助求救,于是美欧人成为埃及的救世主。妓院是美国人、英国人、联邦德国人、瑞典人等西方发达国家男性的享乐之地,却是少数族裔女性的地狱,也是雅各布的地狱。妓院汇集了众多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穷苦女性,而穷困潦倒的雅各布和他的母亲也成为了妓院里居住时间长达十年的“居民”。雅各布与她们一起深深地体会到了“妓院文化”的辛酸和丑陋。
首先,“妓院文化”剥夺了雅各布的正常童年生活,使他成为一个“负重”的旅居者。“作为个体生存在特定文化语境中,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他必须与所属社会文化以及周围他者形成联系”[6]。身处妓院这个特定的文化氛围中,由于年龄、身份、地位的特殊性,雅各布只能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他的第一份工作是为火盆生火’……必须来回跑着为每一个即将熄灭的水烟筒里添加炭火。如果他的动作慢了,一个男人就会盯住他。他的第二个身份是足疗师……他跑过去跪在客人面前,帮他脱掉鞋袜,为他按脚’”④[7]175-176。由于劳动强度大,雅各布的膝盖受伤出血,但他只能用绷带缠住后继续工作。美国著名的教育家杜威从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角度出发,提出了“教育即社会”和“从做中学”的教育原则,“主张儿童通过大量的社会活动,经过不断的尝试来获得社会经验、社会意识,把个人经验和社会经验结合起来”[8]。然而,雅各布的“社会活动”不是以快乐和身体健康成长为目的,而是被动性和强制性、以摧残身体为代价的。这种“透支性”的体力劳动对他弱小的身体是一个很大的重负,给他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伤害。雅各布从这种“教育”中获得的“个人经验”和“社会经验”充满了艰辛和苦涩。
其次,“妓院文化”扭曲了雅各布的性别身份,把他变成了白人男性“性侵”的对象。雅各布小时候从母亲那学会了涂指甲花,这本属于他童年生活的乐趣,却带给了他灾难。一个东德男人要求雅各布为他涂指甲彩,尽管“这很明显是一个奇怪的要求”[7]177,雅各布还是顺从了他的要求,跑过去跪在男子面前。突然,男人站起身,在所有男女的面前解开裤子,露出硕大的生殖器,它几乎碰到了雅各布的脸,并要求雅各布在它上面涂彩。雅各布此时全然不知所措,“即使想移动,也一动不动地跪在那儿”[7]177。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认为,“游戏是由快乐原则驱动的,是满足的源泉。游戏能帮助儿童发展自我的力量,克服本我和超我的冲突,是缓和心理紧张和使儿童掌握经验的净化反应”[9]。涂指甲花游戏几乎是童年雅各布的唯一乐趣,可东德男人与雅各布之间的“性游戏”完全是一种变态行为,它远远地超出了雅各布的生理和心理承受能力,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恐惧,严重地伤害了他的心理健康,给他造成持久性的不良心理影响。
与此同时,雅各布见证了欧美男人道德彻底沦丧的兽性本质。跟他玩“性游戏”的东德男人随即转向一个13岁的阿拉伯女孩。她被迫跪着,默默地在东德男人的生殖器上涂彩,直到对方满意为止。不仅如此,一个更有钱的西德男人夺走了小女孩的童贞。雅各布对此事的反应是“只记得她的两个小辫”[7]177——表达了极为复杂的心理与情感意义。首先,涂指甲花游戏不再给他带来愉悦和快乐,而是恐惧和创伤的象征;其次,表征童年的天真与快乐的“小辫”却遭到男性无情的践踏和蹂躏;最后,雅各布回避自己和小女孩遭“性侵”的行为,表明欧美男性的畸形“性文化”已经给他带来深深的伤害,且留下了噩梦般的记忆。此后在贝鲁特的寄宿学校读书期间,一帮白人男孩经常欺负雅各布,他们在雅各布的头上小便。成年男子和青少年男孩的“露阴”行为让雅各布对男性生殖器产生了既恐惧又好奇的近似病态的心理“情结”,成为了雅各布此后经历“同性恋文化体验”的潜在诱因之一。以上记忆一直伴随雅各布来到旧金山,不断加深他对欧美文明虚伪本质的认识。雅各布的愤怒“控诉”是对欧美白人男性非人性“妓院文化”的高度概括:“美国男人对她[巴蒂亚]的身体不感兴趣,只喜欢围着她,觉得她好玩……多克,你们美国人就是这样的混蛋,这样地把妓院搞乱。你不觉得你们是多么残忍,没有任何提示的残忍”[7]43。
综上所述,雅各布自出生之日就被西方文明扔进了文化的“暗道”,他在那里对自己和妓女们的边缘身份、欧美白人男性“性文化”以及强者文化和弱者文化之关系的本质有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认知,为他后来开启“同性恋文化体验”与“异教文化选择”之旅确定了一个重要基调。
三、 与同性相恋——青年时期的“同性恋文化体验”
主人公的第二段文化“窄道”之旅发生在美国。青年雅各布是在被美国白人社会遗弃的文化“角落”里体验到了同性恋文化,它包括美国主流社会对男同性恋的批评与否定态度、主人公与男同性恋者之间的不愉快交往经历、同性恋者患上艾滋病后的惨死,这种体验给雅各布后半段人生带来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雅各布孤身一人从中东来到美国旧金山后,突然被抛入到比“妓院文化”更加痛苦的生活与文化环境当中。首先,“美国主流社会对少数族裔的边缘化和疏离,使美国少数族裔没有明显的社会和文化归属感,使他们饱受身份焦虑的困扰”[10]。其次,小说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旧金山为中心的艾滋病大爆发、无数同性恋者死于艾滋病的历史。“1981年,艾滋病来到整个世界,没有人知道它会带走3000多万个生命……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艾滋病让许多婴儿潮男同性恋者和X一代人生活在惊愕之中”[11]。截至1985年,美国已经有1.2万人死于艾滋病。当时以里根总统的高级顾问帕特·布参南为代表的美国人普遍认为艾滋病主要来自同性恋,所以他们在经历了苦痛之后将一切罪魁祸首归之于同性恋,并把艾滋病与同性恋画上等号,把他们视为“魔鬼撒旦”。从此“同性恋作为亚文化群体长久以来始终漂移在社会制度的边缘,同性恋一直处于历史的遮蔽之下”[12],成为主流文化之外的“边道”式存在。雅各布就是这种特殊文化“景观”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雅各布初到美国,举目无亲,深感孤独。多克和他的朋友及时来到雅各布身边,关心与关爱他,把他引入通往同性恋文化体验的道路。他起初对同性恋朋友表达感激,因为他从他们那里找到了归属感:“当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家时,我被人们视而不见……你看到了我,格里格看到了我”[7]181。从个人经历上讲,他们之间的结识与交往是彼此心理和情感的共同需求。从社会环境来说,当时流行的同性恋文化成为他们彼此亲近的“温床”。对雅各布来说,他的“妓院文化启蒙”为他的同性恋文化体验提供了内驱力。所以,主客观因素共同决定了雅各布最终成为同性恋文化的实践者。
然而雅各布首先体会到同性恋者在美国社会的边缘处境。“我的六个朋友在六个月内都死了,他们都是我的密友——包括我的爱人。我们像婴儿,但是当我们一一死去时她在哪里……你怎么能不知道你的历史?我一遍又一遍地叫喊……你怎么能够允许世界忘记我们,删除我们的存在,完全省略掉同性恋历史呢?”[7]33。雅各布的“表白”包含三层意思。第一,他的朋友们先后都患上艾滋病离世了,他成为唯一的幸存者,他成为所有悲痛的承受者。第二,尽管他们都是成年人,但是他们如同被社会抛弃的婴儿,亟需得到母亲乳汁的滋养,但是“母亲(她)”没有出现并呵护他们。这个“她”既象征着他们自己的母亲,也象征着当时的美国社会。美国社会不仅漠视他们的存在,而且遗弃他们,使他们成为社会的孤儿。第三,雅各布希望他的伙伴像他一样,竭力呐喊和反抗,以期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可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美国社会已经把他们和他们的历史从美国历史中“删除”和“省略”了。以上三层含义构成递进关系,一步一步地将同性恋文化“挤压”到社会的“边道”上。
其次,雅各布的同性恋体验并没有给他带来生理上的快感,相反却加重了他精神上的重负与折磨。小说描写了雅各布和他六位朋友之间的“交流”和共同吸毒等场景,但雅各布并没有过多地流露出同性恋体验的愉悦感,而是更多地展示他在放纵之后的忏悔心理。例如,雅各布经历了在同性恋酒吧吸毒与性爱之后,深感良心上的羞愧和道德上的自责:“羞耻之心……自我诱惑,自我堕落,那就是我”[7]189。小说仅有一次描写了他们七人去旧金山的德洛丽丝公园踏青,当时他们之中已有人感染艾滋病:“因为一切正变得更糟,甚至比我们想象的更糟,所以我们不知道是否早该高兴”[7]228。那是他们最后一次“结伴同行”,是痛苦和绝望的相聚,也是即将走向死亡的诀别。
最后,雅各布深刻地体会到同性恋情结给他以及他的朋友的生理、心理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他多次回忆艾滋病夺走他六位朋友生命的往事。雅各布对多克说:“艾滋病是一条没有河床的河流……我在河里游着,漂浮着……它慢慢地汇流成小溪,抵达我生命的每一个遥远的角落”[7]154。雅各布彻底地意识到艾滋病不仅夺走了他所有朋友的生命,而且也即将吞噬他自己的全部世界。小说通过描写格里格之死将同性恋悲剧推向高潮,格里格患上艾滋病综合症的恐怖场面给读者留下最难忘的印象:
格里格知道他已经走到了路的尽头……他被诊断的当天宣告了世界末日的来临……出现了如此残酷而不同寻常的死刑结论:淋巴瘤、肺囊虫、卡里尼肺炎……还伴随着其他的并发症,其中包括巨细胞病毒的致命疾病……[7]224-225。
格里格的命运就是他们六个人命运的缩影,也是当时美国同性恋者命运的写照,他们都只是美国主流文化“大道”之外“小道”上的孤独生命过客。
四、 与“魔”为伍——中年时期的“异教文化选择”
雅各布经历了“同性恋文化体验”后成了一个“独行客”。此时的雅各布感到身心俱疲,万念俱灰,是撒旦和十四位圣人帮助他恢复了精神和意志,并最终促使中年时期的雅各布选择了“异教之道”——接受“魔鬼”撒旦和被视为“异己”的十四位圣人的指引,继续完成自己的生命之旅。
雅各布在接受撒旦和十四位圣人之前有过梦想——希望得到美国政府的“集体治疗”。“1973年美国男女同性恋者同时试图说服美国精神学会不再把同性恋列入精神病条目”[13],后来美国精神病学会建议美国社会对同性恋采取集体治疗,但是美国社会并未对此采取任何措施。因此雅各布的悲惨境遇没有得到任何改变,这正是他接受撒旦和十四位圣人的原因。
撒旦虽是魔鬼的象征,但他也是雅各布童年记忆中的英雄。撒旦在《圣经》和《古兰经》中都被称为魔鬼,《圣经》中的撒旦因为不听从上帝旨意并且反抗上帝而被逐出神山。伊斯兰教中的撒旦名叫“易卜劣斯”,意为“邪恶者”,有时也称撒旦。《古兰经》中他因拒绝服从安拉的命令,不向用泥人造就的人类祖先叩拜而被贬为魔鬼。尽管如此,雅各布对撒旦保留着美好记忆,因为在他的童年时期:“巴蒂亚阿姨给我讲述了好多遍……所有的天使同时向亚当跪拜,唯独易卜劣斯例外,拒绝跟他们一起向亚当鞠躬”[7]237-238。撒旦的故事和反抗形象伴随着雅各布的成长,慢慢地沉淀在他的记忆深处。
随着丧友之痛的持续加剧,雅各布对撒旦的认同感得到不断强化。雅各布坦言:“……我的撒旦是易卜劣斯,一个孤独的人……陪伴我的是易卜劣斯,没有别人。他是我的同伴。我相信他总是与我在一起……但是,当上帝要求易卜劣斯向亚当鞠躬时他拒绝了。易卜劣斯说,除了对你,我不会对其他任何人做这件事”[7]84。从受到“性文化”虐待的童年到受到白人同学歧视的青少年,再到经历同性恋文化创伤体验的青年——尽管荆棘满途,但是撒旦好像一只“无形之手”,一直指引并推动着雅各布在暗黑而崎岖的人生小路上艰难前行。对雅各布而言,美国社会没有他的安身之所,白人的上帝更不可能拯救他。他选择撒旦是因为撒旦成为他精神与力量的“领路人”。
经历了心理认同之后,雅各布最终在行动上选择了撒旦。雅各布在诊所并未得到应有的治疗,他甚至感到更加孤独。撒旦直接对雅各布说:“来吧,来吧。我是你的影子,振作起来……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上帝生病了,他带走了他的所有理智,但不包括你。你真的不需要这些药丸”[7]243。撒旦的一系列“警语”让雅各布放弃了治疗,放弃了对美国白人社会和白人上帝的幻想,选择与撒旦“同行”。
此后,雅各布同样接受了十四位圣人的帮助。他们对雅各布的关心与爱护同样伴随着雅各布的童年生活:“我告诉你,十四位圣人是我的圣人,他们陪伴着我的成长”[7]28。他们犹如雅各布人生中的精神导师,指引着雅各布的前进道路。雅各布在青少年时代再次加深了对十四位圣人的理解和认同:“……为什么罗马天主教不再相信她的存在……教堂删除了芭芭拉、玛格丽特、西里亚库和阿加修斯……教堂杀死了十四位圣人,再次处死了他们”[7]183。雅各布对十四位圣人故事的记忆与历史记载几乎完全相同,表明他们在雅各布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根据史料记载,天主教圣徒传统中有“十四救难圣人”的信仰。他们各司其职,负责治疗普通百姓的各种疾病,一千多年一直深受普通民众的欢迎与爱戴。然而1969年天皇保罗六世进行改革并颁布了新千年历,删除了圣芭芭拉和圣凯瑟琳等几位受欢迎的圣人。这一举动引起世俗媒体的极大关注和普通百姓的强烈不满。保罗六世给出的理由是那几位圣人的“真实历史证据相对不足”[14]。从此这几位圣人成为被主流宗教文化抹去的“异己”。尽管如此,他们的故事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以雅各布为代表的阿拉伯人民心底,成为他们宗教文化信仰的源泉。小说对教皇的霸权行为给予正面谴责:“保罗六世、约翰二十一世、洛奇四世,谁在乎?他们对我来说都一个样”[7]219。在雅各布心中,十四位救难圣人地位崇高,是百姓的救世主,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十四位圣人对雅各布的悉心照顾让雅各布投入他们的怀抱。在雅各布出现偏头痛和精神困扰之时,十四位圣人总是及时出现在他的身边关心他。在撒旦把雅各布从诊所领回家之后,十四位圣人立即来到雅各布家中。“我的母亲凯瑟琳来了……尤斯塔斯双手捧着我的心脏……撒旦接过我的心脏,怜爱地吻着它……”[7]245。雅各布视凯瑟琳为他的生命之母,视撒旦为自己的生命之父。雅各布彻底地接受了以撒旦和十四位圣人为代表的宗教文化,他们成为了贴着“异教”标签的“同路人”。雅各布最终决定将诗歌作为自己的武器,向世人揭露西方文明和美国白人社会的本质。
五、 结 语
《历史的天使》把主人公雅各布的半生经历置入中东历史和北非历史、美国社会以及世界宗教史的大背景中,展示了强者文化霸权下一个弱者的“狭窄”生命和精神文化生存空间。它没有阳光,充满了黑暗与不幸。生活在此空间的少数族裔群体都是主流文化与主流社会的边缘人和旅居者,他们的悲剧人生折射出作者的深沉悲悯情怀以及对霸权文化和西方文明虚伪本质的强烈批判意识。雅各布形象是《历史的天使》主题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作者阿拉梅丁本人社会身份的写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是作者其他作品中主要人物的缩影。因此,开展阿拉梅丁及其文学创作研究将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注释:
① Amnatta Forna认为《历史的天使》是一个政治故事。参见Amnatta Forna,“The Angel of History by Rabih Alameddine review—a gloriously political tale of survival,”TheGuardian,Oct.13,2016,p1,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6/oct/13/the-angel-of-history-by-rabih-ala-meddine-review.拉比·阿拉梅丁在2014年的访谈中表达了对美国政治的强烈不满:“我是一个黎巴嫩人,但不那么像;我是一个美国人,但不那么像。我唯一真正能确定的,我不足5英尺7英寸。”参见Roberta Silman,“Book Review:Rabih Alameddine’s ‘Angel of History’ — Knocked Askew,”TheArtsFuse,October5,2016,P4,https://artsfuse.org/150937/book-review-rabih-alameddines-angel-of-history-knocked-askew/.The Economist认为《历史的天使》展现了一个生命个体的存在主义戏剧事件。参见All Book Marks reviews forTheAngelofHistoryby Rabih Alameddine,TheEconomist,2019/07/22,p.5,https://bookmarks.reviews/reviews/all/the-angel-of-history/.Steven G.Kellman称《历史的天使》“在结构上是一部创造性的成长小说”。参见Steven G.Kellman,“Lost Allusions:Rabih Alameddine’sTheAngelofHistory”,BookforumMagazine,SEPT/OCT/NOV2016,p3,https://www.bookforum.com/print/2303/-16496.Erinn Beth Langille在解析《历史的天使》的写作特色时认为,它独特地平行处理了同性恋共同体和阿拉伯人共同体。参见Erinn Beth Langille,“A gay man’s night of reckoning in “The Angel of History,”CULTURE.Nov.5,2016,p1,https://www.macleans.ca/culture/a-gay-mans-night-of-reckoning-in-the-angel-of-history/.
② Farid Farid在分析《历史的天使》时说,小说的场景在“雅各布的故事”、“在诊所”、“雅各布的日记”以及“撒旦的访谈”之间转换,这种技巧使得魔幻现实主义的形象场景不断变化,叙述声音有时不和谐,故事人物之间模糊难辨。参见Farid “Rabih Alameddine’s The Angel of History melds sacred and profane,”THEAUSTRALIAN,March 31,2017,p.2,https://www.theaustralian.com.au/arts/review/rabih-alameddines-the-angel-of-history-melds-sacred-and-profane/news-story/8a54d7dbf.
③ Michael Schaub认为《历史的天使》是一封爱情书信,因为小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小说的主人公对他的男同性恋伙伴“多克”的内心表白。参见Michael Schaub,“‘Angel of History’Is A Heartfelt Cry,”NPR,October 8,2016,p3,https://www.npr.org/2016/10/08/496446525/angel-of-history-is-a-heartfelt-cry.
④ 作品中的引文出自Alameddine,Rabih.TheAngelofHistory.New York:Atlantic Monthly Press,2016.文中引文均为笔者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