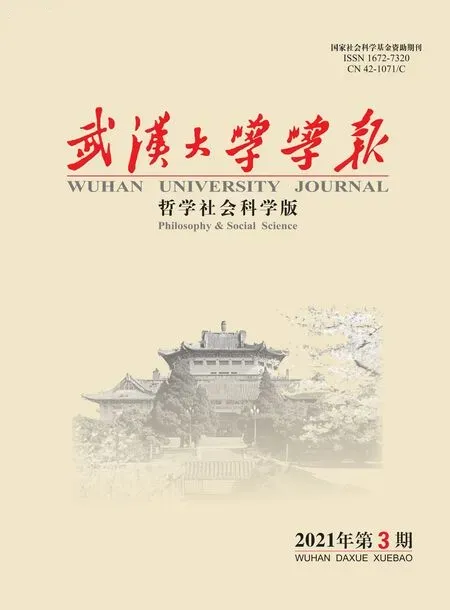“言可复也”究竟谓何
杨柳岸 杨逢彬
《论语·学而》第十三章的“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曹魏何晏《论语集解》,与宋代朱熹的《四书集注》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解读。何晏认为,“言可复也”为“出言反复”——说的话不必兑现;而朱熹释“复”为“践言”,“言可复也”就是“说的话可以兑现”。杨伯峻《论语译注》采纳朱熹的说法,孙晓春先生则认为何晏的解释是对的。而他们两位所依据的来自《左传》的两则材料完全相同。鉴于“信”与“义”是中国观念史、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先秦语言入手,对这一问题再作探讨。
一、“言可复也”的几种理解
《论语·学而》第十三章:“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言可复也”一句,杨伯峻先生说:“复,《左传·僖公九年》荀息说:‘吾与先君言矣,不可以贰,能欲复言而爱身乎?’又《哀公十六年》叶公说:‘吾闻胜也好复言……复言非信也。’这‘复言’都是‘实践诺言’之义。《论语》此义当同于此。朱熹《集注》云:‘复,践言也。’但未举论证,因之后代训诂家多有疑之者。童第德先生为我举出《左传》为证,足补古今字书所未及。”[1](P8)杨逢彬《论语新注新译》采用杨伯峻先生的说法,不过补充了《国语·楚语下》“复言而不谋身,展也”一例[2](P13)。孙晓春先生不同意上述解释,他说:
孔子的学生有若曾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如朱熹《集注》说:“信,约信也;义者,事之宜也;复,践言也……言约信而合其宜,则言必可践矣。”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也把这句话译为:“所守的约言符合义,说的话就能兑现。”其实,“复言”是春秋时期的习语,其意为出言反复。《左传·僖公九年》记载,晋国荀息说:“吾与先君言矣,不可以贰,能欲复言而爱身乎?”又据《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叶公说:“吾闻胜也好复言……复言,非信也。”便是这方面的例证。有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信接近于义,但并不是义,有些时候诺言是可以不履行的。[3](P26)
孙先生进一步解释道:
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中也引述了这两条材料,但可惜的是,杨先生却把这两条材料看错了,将其当成了“复言”是践守诺言的证据。[4](B02)
杨伯峻先生为什么“把这两条材料看错了”呢?孙先生的证据有两条:
一是汉魏注家对于“复言”早有确解,何晏《集解》对这句话解释说:“复犹覆也。义不必信,信非义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义。”何晏训“复”为“覆”,“复言”意即“出言反复”,照这一说法,“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的意思是:守信接近于义,诺言也是可以反覆或者不兑现的。这与朱熹说法恰好相反[4](B02)。
二是《左传·僖公九年》“吾与先君言矣,不可以贰,能欲复言而爱身乎”的孔颖达疏:“意能欲使前言可反复而行之,得爱惜身命不死乎?”(孙先生未举杜预注:“复言,言可复也。”)[5](P3908)《左传·哀公十六年》“吾闻胜也好复言……复言非信也”的杜预注:“言之所许,必欲复行之,不顾道理。”[5](P4730)孙先生说:“杜注的意思有些含糊,但从传文‘复言非信也’的文意来看,复言也是出言反复的意思。”[4](B02)
综上,对“言可复”的理解不同,实际上是何晏《集解》跟朱熹《集注》的分歧,他们的理解一为出言反复,一为兑现诺言,完全相反。何晏、朱熹未举证,而杨伯峻、孙晓春两位所举证据都是出自《左传》的相同的两条书证,只是孙先生引了《左传·僖公九年》的孔颖达疏以及他认为“意思有些含糊”的杜预注。
鉴于“言可复”的理解截然相反,而“信”与“义”又是中国观念史、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尽管在当代,这种截然相反的理解并非旗鼓相当,未分轩轾。一般注本皆从朱熹与杨伯峻先生的解释,且差别不大[6](P24)[7](P43)[8](P7)[9](P65)[10](P7-8),但由于何晏注、朱熹注都只是各执一说,并未驳倒另一说,这一问题的妥善解决尚“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因此,借由与孙晓春先生商讨的机会,我们对此问题试作一较为透彻的考察。
二、“复言”即践行其言
孙先生说:“有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信接近于义,但并不是义,有些时候诺言是可以不履行的。”这实际上是何晏《集解》“信非义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义”[5](P5338)的复述。“信近于义”果然是“信接近于义,但并不是义”吗?我们先看下列书证:
是以其事君近于罪,其交友近于患,其得上辟于辱,其为生偾于刑,故用于上则诛,行于下则弑,是故交通则辱,生患则危,此邪人之行也。(《晏子春秋·内篇问下》)
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礼记·乐记》)
贵有德,何为也?为其近于道也。贵贵,为其近于君也。贵老,为其近于亲也。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慈幼,为其近于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虽天子,
必有父,至弟近乎霸,虽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领天下国家也。(《礼记·祭义》)
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论语·学而》)
先看第一例。因为“近于罪”“近于患”,才“故用于上则诛,行于下则弑,是故交通则辱,生患则危”,且是“邪人之行”。第二、第三例与第一例类似,意思很显豁,不必多说。第四例即“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的下文,如果其上文为“信接近于义,但并不是义”,故而“诺言是可以不履行的”,那么,“恭近于礼”是否也应理解为“恭接近于礼,但并不是礼”?那“远耻辱也”该如何解释呢?总之,“近于罪”“近于患”也即和罪行差不多,和祸患差不多,没有“但并不是罪”“但并不是患”的言下之意。“信近于义”文例与之相同,也应作如是观。这类句子我们尚未找到反例。根据语言的社会性原则,在没有找到语言内部的确证证明“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确属例外之前,只能认为后者也没有“但并不是义”的言下之意。
孙先生又说《左传·哀公十六年》那条书证:“杜注的意思有些含糊,但从传文‘复言非信也’的文意来看,复言也是出言反复的意思。”如果“复言”果然是“出言反复”的话,那和“信”的意义就截然相反,那么,叶公有必要在这儿说类似“坏不是好”的赘疣之言吗?为了避免断章取义,我们不妨将《左传》这两例书证的上下文稍作展开:
初,献公使荀息傅奚齐,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对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公曰:“何谓忠贞?”对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无猜。贞也。”及里克将杀奚齐,先告荀息曰:“三怨将作,秦、晋辅之,子将何如?”荀息曰:“将死之。”里克曰:“无益也。”荀叔曰:“吾与先君言矣,不可以贰。能欲复言而爱身乎?虽无益也,将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谁不如我?我欲无贰而能谓人已乎?”(《僖公九年》)
子西欲召之(按,指白公胜),叶公曰:“吾闻胜也诈而乱,无乃害乎?”子西曰:“吾闻胜也信而勇,不为不利,舍诸边竟,使卫藩焉。”叶公曰:“周仁之谓信,率义之谓勇。吾闻胜也好复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复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从。召之使处吴竟,
为白公。(《哀公十六年》)
先看《僖公九年》一例。
第一,荀息先说“不可以贰”(沈玉成《左传译文》:“不能改变”),然后说:“能欲复言而爱身乎?”(沈译:“难道想要实践诺言又爱惜一身吗?”)也即,“不能改变”和“实践诺言”是一致的。我们之所以认同沈玉成的译文(也即杨伯峻先生的理解),是因为下文“且人之欲善,谁不如我?我欲无贰而能谓人已乎”(沈译:“而且人们要求上进,谁不像我一样?我不想改变诺言,难道能够对别人说不要这样吗?”)[11](P81)的“人之欲善”和“无贰”也是一致的。
第二,由第一点可知,“能欲……而……乎”这一句式中“而”的前后的词语所表达的意义是相反的,“而”之前的是善的、好的,“而”之后的是不好的、自私的。《左传·宣公二年》:“能欲诸侯而恶其难乎?”(沈译:“难道能够想得到诸侯的拥护而又厌恶困难吗?”)[11](P169)以及下文将要引用的《国语·晋语二》“岂能欲行吾言而又爱吾身乎”也可为证。因此,“能欲复言而爱身乎”的“复言”就不可能是“出言反复”。
第三,孔颖达疏:“意能欲使前言可反复而行之,得爱惜身命不死乎?”今译则为:“意思是说,为了能够使得以前许诺的话可以多次贯彻实行,能够爱惜生命不为此献身吗?”
“反复”一词在南北朝—隋唐之际的汉语中,除有“反复无常”的意义外,还有“多次”的意思。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作谓语、宾语,而后者作状语。如:“今车师已属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复,班将能保北虏不为边害乎?”(《后汉书·班超传》)“朝廷虑其反复也。”(《魏书·列传第九十一》)此其作谓语、宾语者。“二年九月甲申,岁星入太微,距右执法五寸,光明相及;十二月乙酉,逆行入太微,掩左执法;三年闰 月壬申,又顺行犯之,相去一寸。《保乾图》曰:‘臣擅命,岁星犯执法。’是时,高肇方为尚书令,故岁星反复由之,所以示人主也。天者若言曰:政刑之命乱矣,彼居重华之位者,盍将反复而观省焉。”(《魏书·志第四》)此其作状语者。孔疏重点是“行之”,“反复”作状语,状语、中心语由“而”字连接,与《魏书·志第四》最末一句“盍将反复而观省焉”一样,是“多次”的意思。“反复而行之”就是践行、实践。可见,孔疏恰可作为杨伯峻先生注的佐证,而非反证。
第四,请看《国语·晋语二》的一段文字:
二十六年,献公卒。里克将杀奚齐,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将杀孺子,子将如何?”荀息曰:“死吾君而杀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从之矣!”里克曰:“子死,孺子立,不亦可乎?子死,孺子废,焉用死?”荀息曰:“昔君问臣事君于我,我对以忠贞。君曰:‘何谓也?’我对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无不为,忠也。葬死者,养生者,死人复生不悔,生人不媿,贞也。’吾言既往矣,岂能欲行吾言而又爱吾身乎?虽死,焉避之?”
显然,这与《左传·僖公九年》那例说的是一件事情。其中,“岂能欲行吾言而又爱吾身乎”对应《左传》的“能欲复言而爱身乎”,这与孔疏所谓“能使前言可反复而行之,得爱惜身命不死乎”也是一致的。因此,“复言”就是“行吾言”,也即“践行我的诺言”。
再看《哀公十六年》一例。
首先,子西说:“吾闻胜也信而勇。”叶公则说:“复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沈译:“不管什么话都要实践,这不是信用;不管什么事情都不怕死,这不是勇敢。”)[11](P584)也即子西认为白公胜能实践诺言,是“信”;不怕死,是“勇”。叶公认为这还算不上“信”,算不上“勇”。
其次,如果“复言,非信也”是“说话反复无常,这不是信用”,不但是赘疣之语,而且下两句“期死,非勇也”也不好解释了。也就是说,“期死,非勇也”亦可证明“复言”是“实践诺言”的意思。
再次,孙先生说《哀公十六年》“吾闻胜也好复言……复言非信也”的杜预注“意思有些含糊”,我们则认为说得明明白白。当然,如果将“复言”理解为“反复其言”,杜预所说“言之所许,必欲复行之,不顾道理”确实“意思有些含糊”;但如果将其理解为“实践诺言”,意思则分外显豁:“诺言所许下的,非践行不可,却不顾是否合乎人情事理。”
三、“复言”即“言可复”
上文说过,杨逢彬《论语新注新译》采用杨伯峻先生的说法,但补充了《国语·楚语下》“复言而不谋身,展也”两句。如果我们将这例的前后文予以展开,意思就更为显豁了:
子高曰:“不可。其为人也,展而不信,爱而不仁,诈而不智,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复言而不谋身,展也;爱而不谋长,不仁也;以谋盖人,诈也;强忍犯义,毅也;直而不顾,不衷也;周言弃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华而不实者也,将焉用之。”
这一段仍然是讲白公胜的事情,子高即叶公。首先,“爱而不谋长”“直而不顾”可归纳为“美而恶”,“复言而不谋身”没有理由例外。“复言”之后的“爱”“谋”(“以谋”的“谋”)“强忍”“直”“周言”看上去都是好的德行,“复言”(实践诺言)也该如此,所以总结说:“皆有其华而不实者也。”如果“复言”是“反复其言”,那便是赤裸裸的小人行为,又如何能称为“华而不实”呢?其次,“复言而不谋身,展也”,韦昭注:“复言,言可复,不欺人也。不谋身,不计身害也。”这里值得注意的,一是“复言,言可复”,与《左传·僖公九年》“能欲复言而爱身乎”的杜预注“复言,言可复也”一样,将“复言”与《论语·学而》十三章的“言可复也”等同起来了。二是“复言”就是“不欺人”,其意义当然是实践诺言,而不可能是反复其言。
上古汉语的连词“而”,从上下文看,可用于“顺接”,也可用于“逆接”。“爱而不谋长”“直而不顾”等都是逆接,“复言而不谋身”似也不应例外。但《国语》韦昭注解“复言而不谋身,展也”之“展”为“诚也”[12](P528),这似乎与“爱而不谋长,不仁也”“直而不顾,不衷也”等句有所不同。而这样一来,“复言”解释为“反复其言”就更加说不通了,说话不算数,怎么能是“诚”呢?与上段引文紧接着的一段能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彼其父为戮于楚,其心又狷而不絜。若其狷也,不忘旧怨,而不以絜悛德,思报怨而已。则其爱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复之,其诈也足以谋之,其直也足以帅之,其周也足以盖之,其不絜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义,蔑不克矣。
“其展也足以复之”的“复”,韦昭注云:“复,复其前言”。依韦昭注“展”为“诚也”,此句理解为“其诚悫足以兑现其诺言”则文从字顺,而理解为“其诚悫足以出言反复”则极为不词。
以此例彼,“言可复也”的“复”,也是“践行、兑现”的意思。
四、何晏的“复言”释义
何晏解“言可复也”:“复犹覆也。义不必信,信非义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义。”他为什么会这样解释,我们以为原因有二:
第一,先秦典籍中,“复”常通“覆”。例如:《周易·乾·象传》“反复道也”,陆德明《经典释文》释“复,本亦作‘覆’。”《诗经·小雅·节南山》“恶怒是违”,郑玄笺“可反复也”,陆德明《释文》释“复,本又作‘覆’。”《大雅·緜》“陶复陶穴”,陆德明《释文》释“复,《说文》作‘覆’。”《大雅·公刘》“复降在原”,郑玄笺“言反覆之重居民也”,陆德明《释文》释“复,本亦‘覆’。”《大雅·抑》“斯言之玷”,郑玄笺“谁能反覆之”,陆德明《释文》释“复,本亦‘覆’。”《周颂·执竞》“威仪反反”,毛传“反,反复也”,孔颖达疏“复,定本作‘覆’。”《荀子·臣道》“以德复君而化之”,王先谦《集解》释“俞樾曰:‘《韩诗外传》“复”作“覆”。’”[13](P758)
因此,“复”多有训“反覆”者,如《诗经·小雅·蓼莪》“顾我复我”之郑玄笺、《后汉书·张奂传》“宜思大义顾复之报”李贤注等[13](P758)。
第二,先秦到魏晋南北朝的语言中有“反覆”一词,意思是反复无常。例如:
若飞鸟然,倾侧反覆无日,是亡国之兵也。(《荀子·议兵》)
谗夫多进,反覆言语生诈态。(《荀子·成相》)
平,反覆乱臣也,愿王察之。(《史记·陈丞相世家》)
人有毁苏秦者曰:“左右卖国反覆之臣也,将作乱。”(《史记·苏秦列传》)
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史记·淮阴侯列传》)
布自以杀卓为术报雠,欲以德之。术恶其反覆,拒而不受。(《三国志·魏书七》)
刘歆反覆莽世,傅毅党附权门。(《颜氏家训·文章》)
由此可知,何晏解“言可复”为“反覆其言”,是有一定的共时语言依据的。但是,这些依据是很不够的。 因为:
第一,与何晏同时代的“复言”是“再一次说”的意思。例如:
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汉书·董仲舒传》)
后桀党有谮光者,上辄怒曰:“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敢有毁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复言。(《汉书·霍光传》)
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三国志·蜀书五》)
降、少皆劝降。述曰:“废兴命也。岂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复言。(《后汉书·公孙述传》)
第二,从先秦到南北朝的“翻覆言语”是“总说”“翻来覆去地说”的意思。《荀子·成相》“反覆言语”已见上文。他例如:“计临贺故当不应翻覆言语,自生寒热也。”(《宋书·列传第五十九》)。按,“翻覆”今作“反复”。综上,何晏解“言可复也”为“复犹覆也。义不必信,信非义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义”,如第三部分所述,固然缺乏共时文例支撑;而通过以上几点的介绍,即使在何晏当时的语言中,亦未见“复言”表示“出言反复”之例。何晏之所据,只有“复”通“覆”与“反覆”常表示“反复无常”两点,而这显然是不够的。
五、考证结论有赖于同时代文例支撑
综上,“言可复”也即“复言”,到底是实践诺言,还是出言反复,支持前者的有《论语》朱熹注、《左传》杜预注及孔颖达疏、《国语》韦昭注,以及《左传》《国语》的各两条书证;支持后者的仅有《论语》何晏注。我们注意到,所有四条书证,也即文例,都是语言系统内部证据,都是支持“实践诺言”说的。而文例较之故训,更为关键,更有说服力。
鉴于孙先生采纳的何晏注不能提供文例支撑,我们认为,朱熹和杨伯峻先生对“言可复”的解释,是正确的。
本文所用的方法即杨树达先生所谓的“审句例”,他说:“前人于训诂之学有一大病焉,则不审句例是也。大言之,一国之文字,必有一国之句例;小言之,一书之文字,必有一书之句例。然古人于此绝不留意,但随本文加以训诂,其于通例相合与否,不之顾也。故往往郢书燕说,违失其真,至可惜也!王氏说经乃始注意及此,故往往据全书通例以说明一句之义,故往往泰山不移。”[14](P618)审句例,在现代语言学中即注重“语言的社会性”。何晏注找不到一例书证支持,正可以视作“古人于此绝不留意”的注脚。
对于先秦两汉典籍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疑难词句的解释,人们常常依据故训和文例(尤其是与被释词句同一时期的文例)。无疑,故训和文例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当几则故训解释不同时,我们以为应当引用文例来做判断;当故训、文例产生矛盾时,我们以为应当主要依从文例。
我们说,文例较之故训,更为关键,更有说服力,这是因为,文例实际反映的是分布。分布是词的意义的外在表现形式,它锁定了词的数个意义中的一种。也即词有几个意义,也就有几种分布(指分布总和)。属于句法的格式,也属于分布的范畴。这就决定了通过分布的考察,能较为准确地求得词和句的意义。这是我们考察疑难词句时以文例的考察为主的理由。
我们不妨举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高邮王氏释《诗经·邶风·终风》之“终风且暴”,其故训为汉代毛亨和韩婴所谓“终日风为终风”“终风,西风也”,高邮王氏却以同见于《诗经》的“终温且惠”“终窭且贫”“终和且平”“终善且有”证明了“此(本文作者按,指毛亨、韩婴的说法)皆缘词生训,非经文本义。‘终’犹‘既’也,言既风且暴也”[15](P191-193)。
“终风且暴”和“终温且惠”“终窭且贫”“终和且平”“终善且有”一样,都可归纳为“终~且~”的格式,它锁定了这一句里“终”的意义不能是“终止”或别的什么意义,只能是类似“既”的意义。
这一例中有两则故训,高邮王氏以文例推翻了这两则故训,而成为经典范例。下面,我们以《论语》的两处考证为例,来说明当几则故训解释不同时,或当故训、文例产生矛盾时,我们是如何抉择的。
其一,《论语·卫灵公》:“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这句话有歧义。何晏《集解》引马融说:“水火与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为甚。”王弼则说:“民之远于仁,甚于远水火也。”[5](P5471)我们倾向于王弼说。理由如下:
第一,《论语》时代,“甚”作为动词,是“过分”“严重”[16](P736)的意思;用作谓语时,通常用于描述一些不好的、恶劣的事物。例如:
甚矣吾衰也!(《论语·述而》)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论语·子张》)
高伯其为戮乎?复恶已甚矣。(《左传·桓公十七年》)
君子以齐人杀哀姜也为已甚矣。(《左传·僖公元年》)
晋不可启,寇不可翫,一之谓甚,其可再乎?(《左传·僖公五年》)
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子若不许,仇我必甚。(《左传·成公二年》)
若不能败,为辱已甚,不如还也。(《左传·成公六年》)
栾黡汰虐已甚。(《左传·襄公十四年》)
贪淫甚矣,独非罪乎?(《左传·昭公十六年》)
怠偷甚矣,非死逮之,必有大咎。(《国语·晋语八》)
在那一时期,当“甚”后接“于”字介宾结构,用于比较时,一般用于比较两个较为不好的事物中哪一个更为不好。例如:
楚师大败,王夷师熸,子反死之。郑叛吴兴,楚失诸侯……声子曰:“今又有甚于此。椒举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国语·周语上》)子常为政,而无礼不顾甚于成、灵。(《国语·楚语下》)
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孟子·公孙丑上》)
“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句式略同上举“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第二,《论语》时代的典籍中,“水火”通常代表可怕的、容易伤害人的事物。例如:
众怒如水火焉,不可为谋。(《左传·昭公十三年》)
水火之所犯,犹不可救,而况天乎?(《国语·周语下》)
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墨子·尚同》)
又与今人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墨子·兼爱》)
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它哉?避水火也。(《孟子·梁惠王下》)
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孟子·滕文公下》)
将“甚于水火”联系下文“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更能显现“水火”在此为威胁人身安全的事物[2](P308-309)。
这一例的马融说与王弼说是相反的,我们以文例来做判断,倾向于王弼说。
其二,《论语·学而》:“贤贤易色”。“贤贤易色”即尊贤轻色。第一个“贤”是形容词的意动用法,“尊敬”的意思,第二个“贤”指贤人。
何晏《集解》引孔安国说:“言以好色之心好贤则善。”皇侃《义疏》、朱熹《集注》略同,不引[17](P31)。孔说以“好贤”解“贤贤”,是对的;但解“易”为“交换”则误。因为《论语》时代,表达“用……交换……”,大多是“以……易……”的句式,偶尔也会是“易之以……”或“与……易……”;总之,必须与介宾结构共现。例如:
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左传·僖公三十年》)
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以小易大,彼恶知之……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孟子·梁惠王上》)
逢丑父与公易位。(《左传·成公二年》)
因此,果如孔安国所说“以好色之心好贤”,则当为“以贤贤易色”,所以,本章的“易”,是“轻视”的意思(“轻视”义可视为“轻易”义意动用法的固化)。“易”表“轻视”的句子还有:
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左传·襄公四年》)
秦、晋战于栎,晋师败绩,易秦故也。(《左传·襄公十一年》)
吴乘我丧,谓我不能师也,必易我而不戒。(《左传·襄公十三年》)
“贤贤易色”句式正同“贵货易土”,为两个谓宾结构组成的联合结构。这一意义的“易”也可用意义较为抽象的名词作宾语:“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孟子·离娄上》)所以,解“易色”为轻视色,是没有问题的。
“以……易……”“易之以……”以及“与……易……”与两个谓宾结构组成的联合结构都是格式,这些格式,分别锁定了“易”的“交换”的意义以及它的“轻视”的意义,这就是我们总结的“书证归纳格式,格式凸显意义”;“贤贤易色”属于两个谓宾结构组成的联合结构,这就排除了“交换”义,选择了“轻视”义[2](P7)。
这一例,当故训与文例有矛盾时,我们依从了文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