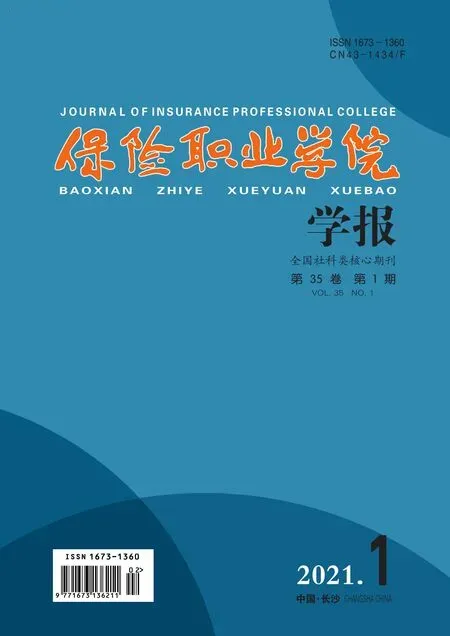监事会监督对保险公司风险承担影响实证研究
郝 臣,胡 港
(1.南开大学 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天津300071;2.南开大学 商学院,天津300071 3.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300071)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金融机构的风险问题受到理论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我国随着市场化、国际化不断深入,经济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金融体系面对的风险更为复杂,防范管理风险也变得更为重要。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防范金融风险是我国金融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是我国金融工作的根本任务”。李克强总理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金融运行总体平稳,但金融等领域风险有所积聚,明确提出实现重大金融风险的有效防控是我国今年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并强调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2019年12月,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在明确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明确了未来5年我国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发展目标;该意见将精准有效防范化解银行保险体系各类风险列为实现发展目标的六大方面举措之一。
一、引言
保险是金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的本质是承担风险,我国保险业自1980年恢复后持续扩张和快速发展,2019年行业全年原保费收入4.26万亿元,行业总资产20.56万亿元;截至2019年底,保险业资金运用余额18.5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2.91%。体量庞大的保险业一旦发生风险,对经济必然会造成深刻的影响。因此,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宏观背景下,保险业是重要一环,保险公司的风险承担问题亟待关注。
公司治理是一套从内部与外部两个维度影响保险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的制度安排。2006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完善保险公司治理,规范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同年,原中国保监会发布《关于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建立起市场行为、偿付能力和公司治理三大保险监管支柱,保险公司治理进入新阶段。监督机制、决策机制与激励机制共同构成了公司治理三大核心机制,我国1993年借鉴德日两国经验建立的监事会制度,与1997年导入的独立董事制度一起形成了并行的公司内部监督机制。我国保险公司治理的框架经过不断发展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治理合规性不断提高,从监事会角度探究公司治理中监督机制对保险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也是对公司治理有效性的深入研究。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手工整理了我国全部财产险和人身险公司共180家从2016年到2018年的系列数据,从监事会规模、监事平均教育水平、监事职业背景和职工监事比例四个方面实证研究了监事会监督这一公司治理内部监督机制对保险公司总体风险、杠杆风险、承保风险和投资风险的作用。已有研究多对监事会的作用从理论层面进行探讨,本文的研究能够在实证层面上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对监事会特征指标选取的多角度和样本选择的全面性是本文的具体创新所在。实践方面,本文的研究结论能为保险公司管控风险承担提供一些理论指导和建议,进而提高保险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二、文献综述
(一)保险公司风险承担的定义
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风险承担(Risk-taking)的内涵做出过讨论,Miller和Friesen(1978)将风险承担倾向定义为企业将资源投入到风险管理中的意愿[1];Lumpkin和Dess(1996)认为风险承担是企业追逐高利润并为此付出代价的倾向[2];朱南军和王文建(2017)将风险承担定义为企业获得利润的必要条件[3]。总的来说,学者的研究大多关注风险承担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认为风险承担在不同行业的表现也有所差别,而保险公司的风险承担具有高负债性导致高风险隐患、债权人分散和股东风险倾向增大等特殊性。
(二)保险公司内部治理对风险承担的影响
内部治理是管控保险公司风险承担的重要机制和手段,关于公司内部治理对保险公司风险承担影响的研究大多从股权治理、董事会治理、高管激励、组织形式四方面展开。股权治理上,Eling 和Marek(2013)认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的保险公司风险承担水平低[4];国内学者夏喆和靳龙(2013)的实证研究也证明第一大股东的高持股比例能降低保险公司风险承担水平[5];毛颖、孙蓉和甄浩(2019)从股权性质、股权集中度和持股结构等方面分析了股权治理对保险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6];Pagach 和Warr(2011),Cheng、Elyasiani 和Jia(2011)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保险公司风险承担的作用[7-8]。董事会治理上,Eling和Marek(2013),夏喆和靳龙(2013)的研究认为董事会的独立性能够降低保险公司风险承担水平[4-5];Ho、Lai和Lee(2013)发现董事会规模与保险公司的总体风险和杠杆风险承担水平正相关,与投资风险承担水平负相关[9]。高管激励上,Eling和Marek(2013)认为高管薪酬水平的提高能够降低风险承担水平[4]。组织形式上,国外学者较国内学者更关注其影响,多研究股份制和相互制保险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差异,如Ho、Lai 和 Lee(2013),Cole、He、Mccullough 和Sommer(2011)对不同样本的研究均认为相互制保险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较低[9-10]。此外,还有学者对再保险机制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认为再保险能够显著降低大型财产险公司的风险承担(牛雪舫,2019)[11]。
在公司内部治理中,监督机制是核心机制之一,而监事会是公司常设监督机构,也是“三会一层”公司治理组织架构中的重要一环,与独立董事构成并行的公司内部两大治理监督机制。监事会的系列特征是否对保险公司的风险承担产生影响,是否发挥了其对于提高保险公司治理有效性的作用,是亟待研究的一个问题。现有针对保险公司监事会与风险承担关系的研究较为匮乏,仅有少数文献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如夏喆和靳龙(2013)通过实证分析表明,监事会规模对于财险公司的绩效提高没有显著性影响,而对于寿险公司则有显著的负面影响[5]。
(三)保险公司外部治理对风险承担的影响
外部治理是存在于市场竞争之中,涉及社会责任、机构监管、利益相关者保护等众多主题的一种外在的制度安排(郝臣、付金薇和李维安,2018)[12]。在外部治理中,外部监管是非常重要的机制之一,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替代内部治理(徐华和李思荟,2013)[13],也是现有文献集中研究的视角。许多学者针对银行展开研究,如李晓庆和郝丽风(2013)认为资本监管能够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进而影响货币政策传导[14]。关于保险公司的相关研究也较为丰富,如赵桂芹和吴洪(2013)对财产险公司进行考察发现,偿付能力充足率与承保风险和投资风险承担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而资本比例与投资风险有显著双向负向影响的关系,但对承保风险无影响,提出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制度存在明显缺陷,仅有红线附近公司受到约束[15];雷鸣、苗吉宁和叶五一(2015)认为,监管压力不会使偿付能力不足的寿险公司显著降低自身的风险[16];赵桂芹和仲赛末(2019)认为,偿付能力弱的财险公司承保风险显著高于偿付能力充足的公司,总体风险和投资风险不显著低于偿付能力充足的公司[17];李艺华和郝臣(2019)的研究发现,外部监管与保险公司总体风险和杠杆风险承担水平负相关,产品市场竞争与保险公司总体风险和投资风险承担水平负相关[18]。
(四)文献综述小结
风险承担是公司进行投资决策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对提高企业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管理层激励、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等因素都会对公司风险承担水平产生影响(詹雷和郑琦,2015)[19]。回顾公司治理与风险承担的研究文献发现,由于保险行业以非上市公司为主,难以直接通过数据库获取公司治理数据,所以关于保险公司内外部治理对风险承担影响的研究文献总体并不丰富,实证研究相对匮乏。已有的相关研究在外部治理方面集中于探究外部监管机制的影响,少数学者考察了产品市场竞争的作用;在内部治理方面,多从股权结构、董事会、高管激励、组织形式四个层面展开研究,少有学者关注“三会一层”中的监事会,对监事会的研究多为规范性研究,研究角度也较为单一,主要从监事会规模和监事会会议次数两个维度进行研究。
监事会是公司治理组织架构中核心环节之一,承担监督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防止其违规经营使得公司承受过高风险的职责。保险公司作为管理风险的金融机构,其监事会理应具备更高的防范风险的素质与能力,应对公司风险承担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以监事会为切入点的研究能够弥补现有保险公司治理对风险承担研究的不足,在实践层面为监事会治理有效性的提升提供建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熊芳(2014)认为监事会规模需保持在适当范围才能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20]。过小的监事会容易受到董事会的影响和控制,不利于监事会职能的履行;监事会人数的增多能够提升监督力度,但是过于“臃肿”的监事会不利于监事内部的沟通与协调,会使得监督效率低下。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设:
H1:监事会规模与保险公司风险承担呈“U”型关系。
根据Hambrick 和Mason(1984)的高阶理论,高层管理者的个性特征会影响其行为,而高管层的行为决定着组织战略的形成和组织中其他成员的行为,组织是高层管理者的一种反映,高管层的整体特征能够预测组织产出[21]。高阶理论关注高管层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职业经历等因素的影响,本文认为保险公司监事会成员的教育水平能够影响其职能的行使,从而影响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设:
H2:监事平均教育水平与保险公司风险承担水平负相关。
基于高阶理论,监事会成员的特征会对保险公司风险承担造成影响。保险决策是极其专业化的决策,保险公司的监事应当具备更高的专业素养才能对这些决策进行监督,具体来讲,具有财务审计、保险精算、金融这些与行业密切关联职业背景的监事能在抑制保险公司的风险承担上发挥更好的作用。现有研究中,Altuntas、Berry-Stolzle 和Hoyt(2011)对保险公司的研究也证明了高管的职业生涯特点会影响公司的风险管理决策[22]。根据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第三个研究假设:
H3:密切关联职业背景的监事比例越高,保险公司风险承担水平越低。
职工监事是监事会中的一类特殊主体,代表全体职工利益,对公司活动进行监督。我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职工监事进行了规定,要求其占监事会总人数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职工监事制度在我国运行了20多年,在参与公司治理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李彦婷,2014)[23],借鉴于此,提出本文的第四个研究假设:
H4:职工监事比例与保险公司风险承担水平负相关。
四、实证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我国全部的财产险与人身险公司,总计180家,其中财产险公司89家,人身险公司91家。计算各保险公司风险承担所用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保险年鉴》中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整理所得,监事会治理的各维度数据根据各公司官方网站中公开信息披露栏目所披露的偿付能力报告手工整理所得,公司的基础信息来源于各公司网站的公开信息。鉴于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报告从2016年开始公开披露,因此本文选择的样本周期为2016-2018年,数据披露周期是2017-2019年。
(二)变量选取与模型设计
1.变量选取
对于被解释变量,徐华和李思芸(2013)的研究考虑了风险承担的多个方面。结合前人研究经验,本文选择从总体风险、杠杆风险、承保风险和投资风险四个维度来衡量保险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总体风险(stdroa)以保险公司过去三年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衡量,杠杆风险(zbj)以责任准备金与总资产的比例衡量,承保风险(pfl)以赔付支出与营业收入的比例衡量,投资风险(stdtz)为保险公司过去三年投资收益率的标准差,投资收益率为投资收益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之和与投资资产的比例。
解释变量主要反映监事会的一些整体特征。本文选取了监事会人数及其平方项衡量监事会规模(sup)特征;用硕博学历监事的比例测度监事会平均教育水平(edu);本文认为与监事监督密切关联的职业背景为财务审计、保险精算及金融背景,将这三类职业背景的监事占监事会总人数的比例(career)作为衡量监事职业背景的状况的指标;以职工监事的比例(staff)作为衡量职工监事状况的指标。
参考已有文献对控制变量的选择,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有:公司规模(lnsize),以总资产的对数计量;公司年龄(lnage),计算方法为ln(当年年份-成立年份+1);资本性质(zb),虚拟变量,1为中资,0为外资;险种类型(property),虚拟变量,1为财产险,0为人身险;组织形式(limit),虚拟变量,1为有限制,0为股份制。
2.模型设计
本文为考察监事会四方面特征对保险公司四类不同风险承担的影响,设计的实证模型如下:
模型(1)—(4)分别用于检验监事会对于总体风险承担水平、杠杆风险承担水平、承保风险承担水平和投资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其中,Xit为所有控制变量,εit为随机误差项。
五、描述性统计与实证结果
表1展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保险公司的承保风险和投资风险差异较大,其变异系数分别达到了10.93 和4.63,同时根据其标准差和极差情况,可以判断样本数据中存在极端值。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sup sup2 staff edu career lnsize lnage 474 474 432 432 432 484 484 3.4790 18.1625 0.2830 0.4930 0.4970 9.2480 2.0730 3.0000 9.0000 0.3330 0.5000 0.5000 8.8530 2.3030 2.4640 28.4694 0.2370 0.3430 0.3400 1.9230 0.7900 0.7080 1.5675 0.8390 0.6970 0.6850 0.2080 0.381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5.5620 0.0000 15.0000 225.0000 1.0000 1.0000 1.0000 15.0000 3.178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6.8260 0.0000 8.0000 64.0000 0.6670 1.0000 1.0000 12.8900 2.9440变量 N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最小值 最大值 P5 P95
为剔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pfl 和stdtz 这两个指标的数据进行缩尾处理,处理方法为在1%的水平上进行平滑化,即将1%之前和99%之后的值分别用这两个分位点上的值替代。处理后pfl 和stdtz的变异系数分别为1.4336和3.7192,标准差分别为0.5260和0.4449,极端值的影响消除。
考虑到监事会规模与其平方项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为了验证这一问题并消除其影响,本文计算了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结果显示变量sup的VIF值为11.78,sup2的VIF值为10.48,存在共线性问题,故对变量sup和sup2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后sup 和sup2的VIF值分别为3.81 和3.17,可以认为标准化处理基本解决了多重共线性问题。
将标准化处理后的变量记为sdsup 和sdsup2,本文后续回归均采用标准化处理及缩尾处理后的数据。在计量方法上,本文对四类风险分别采用OLS 稳健标准误回归、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进行LM 检验和Hausman 检验。检验结果认为,对于总体风险和杠杆风险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另外两类风险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各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如表2所示,监事职业背景的系数、职工监事比例的系数在投资风险的回归模型中表现为显著的负系数,显著性水平分别为1%和10%,监事会规模的平方项在杠杆风险的模型中表现为5%显著性水平下的负系数,其他解释变量的系数不显著。因此本文认为,具有财务审计、金融、保险精算等与行业密切关联的职业背景的监事比例越高,保险公司的投资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职工监事比例越高,保险公司的投资风险承担水平越低;监事会规模能够抑制保险公司的杠杆风险承担。
从表2回归结果来看,假设1和假设2不成立,监事会规模并未对保险公司风险承担产生U 型影响,而对杠杆风险可能存在抑制作用,监事平均教育水平对保险公司风险治理是无效的;假设3和假设4在投资风险层面得到验证,具有与保险行业密切关联的职业背景的监事越多,职工监事比例越高,保险公司投资风险承担水平越低。

表2 各模型实证回归结果
六、稳健性检验
根据数据和变量特点,本文调整了变量的分类标准进行稳健性检验。将监事平均教育水平分别定义为本科及以上监事占监事会总人数的比例、博士学历监事占监事会总人数的比例,分别记为edu1 和edu2;重新定义监事具有的与保险行业密切关联的职业背景,以财务审计和保险精算职业背景的监事占总监事人数的比例衡量该指标,记为career1。首先将上述指标分别单独替代原指标进行重新回归,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大部分变量系数不显著,监事的职业背景和职工监事比例在投资风险的回归模型中表现为显著的负系数,监事会规模的平方在杠杆风险模型中表现为显著负系数,在部分稳健性检验中监事会规模一项表现为显著正系数。限于篇幅原因,本文仅汇报以edu1单独替换edu的回归结果,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edu1替换edu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再将edu1 和career1 同时替代原模型变量,edu2和career1同时替代原模型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与基准实证结果基本一致,限于篇幅原因本文未汇报相关结果。上述所有回归结果证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七、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文从实证角度对监事会这一监督机制对于保险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展开了研究。首先回顾了相关研究文献,发现鲜有学者针对保险公司监事会这一主体进行实证研究,没有文献关注监事的个人特征、职工监事等对于风险承担的作用。基于上述研究现状和我国加强金融风险管控的背景,本文选取我国全部180家财产险和人身险公司为研究对象,手工整理了2016-2018年的相关数据,围绕监事会监督职能提出了四个研究假设,构建计量模型并实证考察了监事会监督对于保险公司各类风险的影响。
从本文的实证结果来看,具有财务审计、金融、保险精算等与保险行业密切关联职业背景的监事比例越高,保险公司的投资风险承担水平越低;同时,职工监事比例越高,保险公司的投资风险承担水平越低。但是,保险公司的监事教育水平并未对风险承担水平产生显著的影响,即未能有效抑制风险承担。监事会规模并未如预期般对保险公司风险承担存在U型影响,对于杠杆风险可能存在抑制作用,在一些检验中还表现出在一定范围内监事会规模可能会加剧保险公司杠杆风险承担水平的现象,这一影响需要进一步地探究。
总体来看,我国保险公司监事会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与设想存在一定的差距。李维安和郝臣(2006)对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的研究也发现了监事会存在虚置的现象,两位学者分析认为出现这一现象并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运行过程中存在股权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而影响监事会监督职能的发挥[24]。我国保险公司大多为非上市公司,监事会受重视程度不高,更容易出现上述问题而使得其监督职能的发挥受到影响。
本文认为,保险行业虽然在监管部门的强力监管下完成了公司治理架构的制度搭建,但是形式上的合规与完善并不能自然地导致公司治理作用的充分发挥,保险公司还需要主动地贯彻自主治理意识,积极提高改善自身的治理能力。同时,保险公司在提高监事会治理有效性的时候,需要关注职工监事的作用,注重监事会职业背景的合理搭配,更好地发挥监事会的监督职能。理论层面,未来的研究可以持续关注监事职业背景这一方向,探究细化其分类和考察的方法,同时本文的控制变量中未考虑独立董事、外部监管等其他治理机制的作用,之后研究可进一步关注监事会监督与其他治理机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