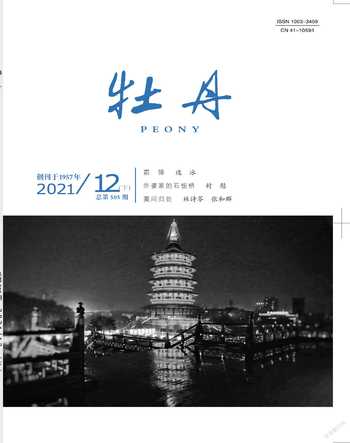外婆家的石板桥

封慰,生于1993年7月,江苏泰兴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硕士。曾于《中国考试》等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作品散见于各大文学网络。
金秋十月,十年没见的高中同桌石天邀请我参加他的婚礼。娘舅家后头四五米处,便是石天家的老宅,那里也将是婚礼的举办地。自外婆离开已四年多了,一直在外漂泊的我,许久不曾回来,甚是想念。临行前,我特地给舅去了电话,老人家似乎有些激动,我甚至能听见电话那头“窸窸窣窣”穿衣的声响。
九十年代双职工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小孩儿,童年的岁月,大多寄于国营厂兴办的托儿所,而我可能稍显得幸福一些,每年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可以枕在外婆的怀里看世界。
妻子对我的过往从来都是极感兴趣的,我向其描绘多少次,似乎都不如她亲眼瞧一瞧来得真切。那里也的的确确留存了很多我小时候的印记,此行,我们便夜宿于娘舅家,那里有一间承载着我梦想的小阁楼。
满足妻子要求的同时,借宿一宿似乎也成全了娘舅的心思,电话那头的老人家很高兴,那股子劲儿透过电流,似是在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耳垂。
从县城到镇上西大街,三十多公里,车开了近一小时,沿途的世界在秋雨中的模样让妻子的内心得到了满足,这大抵和她内心的江南水乡生活相当接近吧。
临近目的地的时候,妻子执意下来走走,看看我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呼吸这一方天地里诱人的气息。
我推开车门撑伞的当口,调皮的雨点儿挤开了车门与伞盖之间的缝隙,径直呼到了我的脸上,仅一瞬,我原本微皱的眼角舒缓开来。
是了,秋日里水乡的雨呀,看起来迅疾猛烈,可沾染到皮肤上的时候啊,那透亮的小水珠儿,便如同经年而成的琥珀,天色虽暗,却依旧能闪闪发光呢。
柔软而不失温润,远没有北方的雨那般冷冽。
也许,这就是家的感觉,一去经年,天上的云朵还认得我哩,给了我如此温柔的欢迎礼。
“传薪,街面上挺热闹的嘛,咱们脚下的柏油路多半也是新铺的吧?快看,那边几栋房子的样式也好看……”
没错,国家在发展,寻常百姓家同样是日新月异。
西大街对面的水带厂,曾是镇上顶顶有名的龙头企业,如今,厂区的围墙已被杂草掩映得斑斑驳驳。站在厂区的大门前,似乎还能回忆起和表兄弟们在里头穿梭的情景。
依附于住家户的小卖店、杂货铺消失得差不多了,街两头一溜儿的商铺,即便已近饭点,仍有不少人在与商户磋磨着价钱。
我们携手走在既熟悉又陌生的马路上,妻子时不时丢出一两个问题,得到我的解答后,她便欢快地小跳两步,全然不顾头顶落下的雨点以及脚下溅起的水花打湿了她的衣裤。
这是她第一次来到我的外婆家呢!而这一刻,我已迟到了四年。
“传薪,这就是外婆家的石板桥吗?”
是它,外婆家的石板桥!娘舅说过,这桥上还残留着他的童年嘞。
它有过名字,但石板上的字迹早就被岁月无情地湮没了。从我记事起,它始终被冠以“外婆家的石板桥”这样的称谓,也不知,是否埋没了它。
石板桥坑洼的外壳上爬满了青苔,湿湿的雨轻抚它的面庞,这青苔便显得油绿油绿的,三两道细小的车辙印,扒开了石板桥的衣裳,露出里头的生锈的钢筋和碎石子儿,这一切,无不彰显着它的老当益壮。
“对,就是它!过了这座桥,转过弯儿来便到家了!”
近乡情怯,我的话里隐隐透着一丝兴奋劲儿,夹杂着些许的慌乱,脑海中全是小时候从这无名的石板桥上经过的场景。
娘舅年轻的时候,肩上还担着到各村巡回放电影的活计,可别小看这活儿,责任大着哩,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嘛。
五六十年代,村里医疗水平有限,娘舅打针的时候伤了筋,右脚打小儿便落下了残疾。看似轻松悠闲的放映员工作,于娘舅而言,代表着无数个不为人知的日日夜夜。起早贪黑,早出晚归是常态。更遑论我们住在马路边上,时不时有大车压过路面的声响入梦,想睡个好觉,只有“习惯成自然”一条路。
“薪呐,是你吗?”
陷入回忆中的我,忽听得有人在唤我的名字,妻子也觉得是在叫我,搭在我右臂上的胳膊向下拽了一下。
我循声望去,石板桥的那头,隔着雨幕,闪出一个推着自行车、步履蹒跚、左右摇晃的身影。
“舅!”
自顾自地把伞塞到了妻子手中,全然没管她是否已经拿稳,我便奔向了石板桥的另一头。
“吱呀……吱呀……”
石板桥承载着发福的我,似乎有些吃力,时不时冒出几缕生命的低吟。
待到近前,我已顾不上这被标榜为“不堪用”的危桥了,我的注意力全在来人的身上。
那是母亲的三哥哥!那是我四年未见的亲娘舅!
“舅,这么大的雨,你腿脚不方便,怎么还一个人跑出來呀!”
“知道你要回来,下河网了一条大鱼,顺便给你买了点东西哩,你舅母不在,中午陪舅喝一杯!”
说话间,舅舅指了指车把手上头吊着的塑料袋,一红一黑,分外显眼。
“现在这路,比起从前的烂泥塘好走得没得命啦,那就是小玉吧,呵呵,好,好,好,舅给你们烧鱼吃!”
除了鬓角的白发多了一些,娘舅和从前比起来,似乎没什么变化:
雨天总要穿着套鞋,裹着部队里才会配发的雨衣,那还是二舅当年在部队的时候寄回来的呢,估计内里是一身不论颜色的工装吧。
我一把抢过娘舅手中的自行车,妻子也快步走上前来帮我们撑着伞。
三人行,微风细雨漫,家园近。
远远望去,娘舅家好似没什么变化,但走进去便知晓,里头早已别有洞天。
“几年前刚装修的,现在生活好啦。喏,那就是石天家的新房子,刚盖好没多久的水泥小楼房……”
娘舅接引我们上了阁楼,在后窗口指给我看石天的新家。高中时代的第二个春节,我和石天也曾在这里眺望远方,那时候,这里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希望。
“传薪,你看起来和小时候差不多呀?”
妻子在墙上的一堆照片里,准确地找到了我,瘦瘦小小,皮肤还有些黑。
娘舅一边侍弄着床上的被褥,一边大声地笑着,“可不是嘛,传薪打小儿就不好好吃饭,如今都这般大了,还是一样黑,一样瘦,小玉你以后可得好好管管他……”
墙上的老照片、橱窗里的日记本、杂物间里的废旧收音机,我确信在阁楼里重复我童年的生活,会给妻子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她哭了,但我却不知道她为何流泪。
娘舅从来都是先盛饭,再上桌的,这习惯很难改变。
坐上饭桌时,我发现了小时候我最爱吃的酱油煎炸水煮蛋!
它被娘舅放在泡沫箱子里保温,拿出来的时候,还冒着丝丝热气。屈指一算,一晃,我已有七八年没有品尝过舅舅的手艺了。
正式开动之前,娘舅神神秘秘地掏出来一个红色的塑料袋,我知道,那是刚刚挂在自行车车把儿上的另一袋东西。
“传薪,你从小就喜欢喝饮料,长大了这个习惯应该也没变吧?雪碧可乐什么的喝不得了,听说容易发胖,还容易蛀牙,你徐叔说,现在城里的孩子都爱喝这个什么姆奶茶,我就给你们买了两瓶。”
徐叔,街面儿上小卖部的老板。小時候跑到他那里去帮会儿忙,他总会给我们哥儿俩免费喝上一杯糖水。普通的茶杯上盖了一片方形的玻璃片,一杯一毛钱,放映电影的时候,徐叔的生意不要太好。
说话间,娘舅拎出了两瓶阿萨姆奶茶,顺手抽出一条白色的毛巾,反复擦拭了两遍瓶身,这才心满意足地将奶茶推到了我们的面前。
我的眼死死地盯着毛巾看,回不过神来。那条白毛巾,新得连贴标都还没有剪下来呢。阁楼上的被褥也是新的,纸篓里还留有剪下来的商品标签。但阁楼间是一直有人洒扫的,那里的味道,没变。
我猛地扒拉了几口饭,好似是被米粒儿给呛着了,眼角便溢出了些许东西。
舅舅赶紧帮我拧开了奶茶的瓶盖,我抄起瓶子一仰脖儿,甜甜的液体缓缓流进了我的心里,伴随着“咕嘟”的吞咽声,我凝视着娘舅,看他眉眼的神采,任由他给我和妻子夹菜、添饭。
舅,我长大了,您却老了。岁月磨白了您的黑发,可我还是曾经那个顽皮的孩子。
外婆走后,我和母亲每年奔赴的地方也少了一处,见到娘舅的次数更少了。远赴上千公里外求学七年的我,在家的时日颇少,似乎是瞬息之间,每次回家,总觉得您和母亲的两鬓多了些许白发,而外婆家门前那座爬满苔藓的石板桥,脊背上承接的印迹也越来越少了。
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走石板桥的人少了,它的使命也便终结了。但求亲人慢慢老,但求岁月慢慢行。青砖、红瓦、木大门,石板桥,娘舅,等我下次回家的时候,一切定还是记忆中的样子。
(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