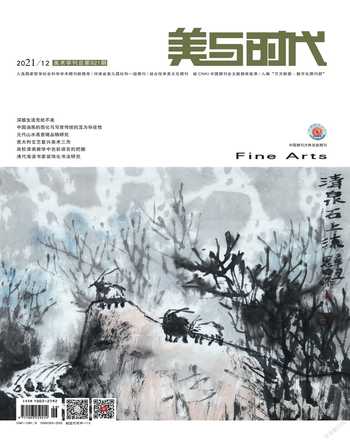中国画写生研究
宋寅帅
摘 要:“写生”一词,对于从事绘画专业的人而言,再熟悉不过。我们通常所谓的写生,是指在绘画中直接以实物为对象进行描绘的一种方式,基本上可以分为静物写生、肖像写生、风景写生,在国画领域,分别是对应花鸟、人物、山水。写生是画家创作灵感的来源,自古以来中国画家对写生的态度都是极为重视的。故而,从写生的概念及意义、写生与临摹的关系、不同画科的写生特点,以及近代中国画写生的改革进行简要分析,研究中国画的写生。
关键词:中国画;写生;临摹
一、写生的概念及意义
在刚开始接触和学习国画,或者其他画种时,往往都是从临摹前人画作开始,并且这种临摹伴随学习的全过程。临摹可以让我们在短期内高效率地了解国画的各种基本技法,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进行写生呢?学习国画如果只是一味地临摹,很容易被其完善的程式所束缚,缺乏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失去了个性的艺术是没有灵魂的,所以我们要进行写生。简而言之,临摹解决“怎么画”的问题,写生解决的是“画什么”的问题。正所谓“藝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写生可以让我们自觉地对景物进行细致的分析,发现生活中的美。那么我们该如何来进行写生呢?首先要注意的是,写生需要对构图、主次、景物取舍等几方面进行分析考量。写生与摄影不同,摄影是需要特定的季节、气候、光影,以及各种偶然事件,并需要对照片进行后期调色处理。而写生,就是画家对某一处景物的理解,它不是客观地对照着景物来描绘,不是看到什么画什么,而是要画家主观地对所看到的景物进行加工再创造。如果只是将所看到的景物如实地描绘出来,那就失去了写生的乐趣与魅力,写生也就没有了艺术性。比如:在风景写生中,画家可以突出强调前面松树的挺拔,弱化后面影响视觉效果的村庄;在人物写生中,为了表现人物的沧桑感,可以对人物面部特征进行夸张处理,但也不能完全脱离实际,不然就与写生的初衷相背离了。一般情况下,画家的写生作品并不直接作为成品展示,它更多是为了完成更宏伟的作品而收集的素材及灵感,因为写生环境一般是比较复杂的,这个环境有可能不适宜画家长时间停留创作,画家只能将此刻所看、所想、所感快速地记录下来。但这个也要因人而异,有些画家就需要这种特殊的创作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他能切实地感受自然,感受他所画之物,一旦脱离这种环境,就很难再进行创作。
二、写生与临摹的关系
中国画的写生考验的是传统的笔墨技巧和功力,因为笔墨是我国先人千余年来文化与智慧的积淀,是我国的艺术精华,所以在写生之前进行大量的临摹,可以摸索出古人对山石、树木的表现手法,以及对绘画气韵的呈现方法。我们写生所画的东西,大多都是临摹中积累起来的。有了临摹的功夫再进行对景写生,临摹时学到的各种技法也就自然而然地运用其中,我们再对实景稍加改变,便有了属于自己的创作。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面貌,每个画家都有自己的个性、修养和文化内涵。通过临摹认识古人,继承传统;通过写生了解当下,融合创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是唐代画家张璪所提出的艺术创作理论,其中的“造化”即自然实景,而“心源”便是画家内心的感受。由此可以看出,张璪强调了艺术与自然的关系,画家应当师法自然,但自然的美并不能直接成为艺术作品。要将自然美转变为艺术美,需要画家用心感受和构思,所以写生是画家与自然联系、与自然对话的方式。但“师造化”的要求要比写生高得多,既要求对物写生,又要求按照现实世界的规律创造艺术。
三、不同画科写生的特点
(一)花鸟画
自古以来中国画就有写生的传统,且有自己的一套表现手法。在花鸟画中,写生并非对物描写,而是“移生动质”,即描写生命,将人的性格气质移植到草木花鸟中,传达一种精神品质,这便是“传神”。谢赫的“六法论”首先便指出绘画中气韵为第一要义,气韵是高于技巧的,这需要画家除了捕捉绘画对象的形、色之外,还要表现出绘画对象的生动气息,关注造化自然,从中寻觅清新朴拙的气息。写生是使画面气韵生动的有效方式。
在花鸟画的写生中,五代时期有著名的黄筌和徐熙两位画家,有“黄家富贵”和“徐熙野逸”之说,以此来形容他们的才高技巧。黄筌善于取熔前人轻勾浓色的技法,独标高格。徐熙善于观察,描写物态极富野趣。黄筌的花鸟写生代表作品有《写生珍禽图》。在这幅作品中,黄筌用细密的线条和浓丽的色彩,描绘了大自然的众多生灵。图中画了鹡鸰、麻雀、鸠、龟等动物二十余只,且每一只动物都刻画得十分细微、精确,活灵活现,耐人寻味。鸟雀或静立,或展翅,或滑翔,动作各异,生动活泼;昆虫有大有小,小的仅似豆粒,却刻画得精确入微,须爪毕现,双翅呈透明状,鲜活如生;两只乌龟以侧上方俯视的角度进行描绘,前后的透视关系准确到位。黄筌经过长期不懈地细致观察并坚持写生,才能获得如此成功,成为一个画派的创始人。徐熙的作品给人以超逸清雅的感觉,其代表作真迹无存,现传为徐熙作品的《雪竹图》和《玉堂富贵图》皆非真迹,但也能从中领略其风格和画法。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花鸟画家有写生作品,比如北宋赵昌的《写生蝴蝶图》、南宋牧溪的《写生花鸟图》、明代周之冕的《百花图》都是写生花鸟画精品。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画家郑板桥的《竹》,其作品中的美源于现实中竹子的美,却不是现实的机械反映,而是他对现实审美认识的表现。他在一则画竹题记中写道:“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这里的“眼中之竹”和“胸中之竹”分别指的就是画家直接观察到的竹子和画家头脑改造而形成的审美意象。意象由于主体审美认识时的精神作用而使现实美得到强化、集中化、概括化或典型化,渗透进画家的思想情感和审美理想之中。
(二)山水画
与花鸟写生相比,山水画的写生更注重画面构图、气韵流动、笔墨技法等,并且有高远、深远、平远(“三远法”)的空间技法。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写生观中,画家会把对自然的深入观照和细微体会放在首位。正如石涛所言的“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达到与山川河流融会贯通、人景合一的境界。五代的荆浩、北宋的赵昌、元代的黄公望,他们都有独特的写生之法。但古人的写生作品都不能算是现代视觉意义上所谓的真实再现,他们更多是表现文人的心境、品格,山川河流虽在眼前,但通过笔墨的转化,便有了意境。不同出身、不同心情、不同性格的人在描绘同一处风景时,所产生的画面效果、所寄托的情感也大相径庭。比如同样是庐山,荆浩创作的《匡庐图》皴染兼备,笔墨之间表现了山的雄伟壮阔与烟岚的深远缥缈,营造了一幅雄伟刚劲与寂寞幽静相互交融的远离人间烟火的空灵世界。而沈周创作的《庐山高图》笔法稳健,气势雄浑,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和力量感,用笔苍润有力,颜色浓淡相间,突出一种谧静幽深的深远意境。
(三)人物画
在人物画方面,古人多数并没有直接对景实时写生,而是在细心观察之后,再结合自己的想象进行创作,并主张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紧紧抓住有利于传神的眼神、手势、身姿与重要细节,强调主次,详于传情的面部手势而略于衣冠,详于人物活动及其顾盼呼应而略于环境描写。人物活动与环境景物的关系上,抒情性的作品往往借创造意境氛围烘托人物情态,叙事性的作品在横幅或长卷构图中,往往以环境景物或室内陈设划分空间,如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便是如此。明代创立“波臣派”的画家曾鲸擅画肖像,极具特色。他十分注重观察,所画的人物特征鲜明,借鉴西画,强调以墨线和墨晕为骨,将光影相结合,既有中国画的意境又有西画的体积和质感。而对照人物进行实景写生的开创者,是蒋兆和,他在传统中国画的基础上融合西画之长,创造性地拓展了中国水墨人物画的技巧,画风质朴,充满人文关怀。
四、中国画写生的變革
近现代的中国风雨飘摇,西学东渐之风对我国的美术观念影响巨大。蔡元培主张对中国画进行改良,大力提倡写生,并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的演讲中提出:“此后对于习画,余有两种希望,即多作实物写生及持之以恒是也。”对于中国画写生而言,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到底是用中国的写生技巧,还是用西方的写生技巧。而从近现代画家的实践来看,出现了两种方法。一种是遵照西方观念的写生方法,比如徐悲鸿主张发展“传统中国画”的改良,立足中国现代写实主义美术,发表《中国画改良论》,参照南齐谢赫提出的“六法论”,根据西洋绘画的艺术法则提出了素描创作应遵循的“七法”,主张采用讲求透视的西法写生。另一种则是用民族传统的画法写生,最早由胡佩衡提出。他赞同写生,改造国画,但反对崇洋,认为此法最关键的条件是合乎中国画的理法,特别讲求笔法。李可染开创的以“写生方法形成实景美”的创作手法,是他用艺术实践对民族虚无主义的第一次回应。由此可见,近现代中国画的写生观念,乃引进西学之产物。中国画改良让中国画重获新生,走出一味效仿古人的传统,也使中国画的面貌焕然一新。
五、结语
中国是一个讲传统的国家,中国画更是讲传统的艺术。不同时代不同画科的不同画家,对写生都有独到的见解。在近现代,有许多仁人志士努力探索中国画的出路和未来,对中国画的写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写生考验的是眼和手的功夫。将山川河流尽收眼底,将笔墨技法赋予纸上,这需要画家既有丰富的审美经验,又有时代赋予的精神和个性,将三者合一,才能展现独特风格,才能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中,保持自我。
参考文献:
[1]李志国.中国画写生历史流变浅析[J].书画世界.2017(2):76.
[2]李萌.对中国画写生和创作关系的再认识[J].艺术评鉴.2017(6):14-15.
作者单位:
江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