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典识“玻璃”
——兼谈古代印度宝石学对中国的影响 ①
郑燕燕
内容提要:“玻璃”是古印度俗语“phaiha”或巴利语“phaika”的音译。该词大约在三国时期通过佛教传入中国,早期多写作“颇梨”“颇黎”“玻瓈”等,唐代开始出现“玻璃”的写法。它最初是指水精似的无色透明宝石,后来也指红宝石、蓝宝石、尖晶石等颜色艳丽且莹澈通透的彩色宝石,直到宋代才开始用来称呼硅酸盐类人造材料,也即今天所说的玻璃。今天的人造玻璃在古代通常被称为“琉璃”,只是宋元时期“琉璃”渐成釉陶制品专名,而人造玻璃与宝石“玻璃”通透的性状相似,因此其名称就由“琉璃”渐变为了“玻璃”。从“玻璃”和“琉璃”等词汇传播和使用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印度宝石学知识如何以佛教为载体渗透到古代中国的。
玻璃,在现代汉语中主要是指硅酸盐类人造材料,一般认为起源于四千多年前的两河流域,大约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在中国内地。关于中国古代的人造玻璃,不仅存有丰富的文献记载,还出土过大量考古实物,因此一直是个重要研究课题。学界利用上述材料考证玻璃的名称、起源、历史,分析玻璃的成分、产地、制作技术,探讨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和宗教文化意义等,可谓成果斐然。以人造玻璃的古代名称为例,章鸿钊、萧炳荣、张维用、罗学正、李志超、李清临、赵永、黄振发、齐东方与李雨生等学者都曾作过讨论。(1)章鸿钊:《石雅》,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6~20、37~38页;萧炳荣:《我国古代玻璃的名称问题》,《玻璃与搪瓷》1984年第5期,第56~59页;张维用:《琉璃名实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2期,第64~69、96页;罗学正:《琉璃称谓考辨》,《求索》1992年第1期,第113~115页;李志超:《汉语“玻璃”的起源》,收入《天人古义:中国科学史论纲》,大象出版社,2014年,第178~183页;李清临:《中国古代玻璃与琉璃名实问题刍议》,《武汉大学学报》2010 年第5 期,第626~639页;赵永:《琉璃名称考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5期,第63~72页;黄振发:《中国古代玻璃的名称》,干福熹等著:《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史》,上海科技出版社,2016年,第101~109页;齐东方,李雨生:《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玻璃器皿卷》,开明出版社,2018年,第3~13页。通过这些研究可知,人造玻璃在古代曾被称为“琉璃”“玻璃”“药玉”“硝子”“假水晶”“罐子玉”“料器”等。其中,讨论较多且争议较大的是“琉璃”一词,这是玻璃自汉代直至唐代的主要称呼。相较而言,关于“玻璃”一词的探讨则少得多,且一些论点仍有可商榷之处。
事实上,以“玻璃”称呼硅酸盐类人造材料是宋代以后才渐渐流行的,而在此之前这个词主要是指天然宝石。虽然上述诸位学者多已注意到这一点,却很少有人做出详细讨论,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宋代以前的世俗文献中,关于“玻璃”的记载非常有限,学者难以对该词追根溯源。不过,笔者注意到,“玻璃”曾是佛教的七宝之一,很早就出现在汉译佛典中,且很多记述颇有史料价值。因此,本文尝试结合世俗文献与佛教经典,讨论中国古人对“玻璃”的认识,并指出在这种认识的背后,隐藏着印度宝石学知识以佛教为载体传入中国的史实。
一 “玻璃”的词源及其本意
玻璃,早期又写作“颇黎”“颇梨”“玻梨”“玻瓈”等。大体自唐代开始,“玻璃”这种写法才出现,宋元以来渐渐流行,但并没有固定下来,其他写法仍旧继续使用。因此,在同一部佛经的不同汉译本中,或同一条史料的不同版本中,有时会使用不同的写法。如唐窥基撰《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赞》称:“其树生果,如玻璃色,一切众色,入颇梨色中。赞曰:第二广树,颇梨色者,谓红赤色,此为根本。一切宝色,为此所含,皆入此色。”(2)〔唐〕窥基:《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赞》卷二,《大正藏》第38册,第288页中。又,《旧唐书》卷一九八载,贞观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 “赤玻瓈”(3)《旧唐书》卷一九八《拂菻国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314页。,而《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四作“赤玻璃”(4)《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四“大秦国”条,中华书局,2007年,第3516页。。《新唐书》卷二二一记载,吐火罗国有“颇黎山”(5)《新唐书》卷二二一《吐火罗国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252页。,《文献通考》卷三三九作“玻璃山”(6)《文献通考》卷三三九“吐火罗国”条,中华书局,2011年,第9391页。。可见,“颇梨”“颇黎”“玻瓈”等同于“玻璃”。
“玻璃”等相关词汇最早出现在中国,是在汉译佛典中。其中,西晋之前的材料多有争议,如《大方便佛报恩经》曾提到“颇梨缕”(7)失译:《大方便报恩经》卷四,《大正藏》第3册,第144页下。,该经古代被列为东汉译经,但现代学者或怀疑其是伪经,(8)林显庭:《〈大方便佛报恩经〉纂者考及其唐代变文》,《中国文化月刊》1987年第91期,第65~91页。或认为其译于三国或两晋之后。(9)参看史光辉:《东汉佛经词汇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第132~144页;方一新,高列过:《从疑问句看〈大方便佛报恩经〉的翻译年代》,《语言研究》2005年第3期,第54~57页;史光辉:《从语言角度看〈大方便佛报恩经〉的翻译时代》,《古汉语研究》2009年第3期,第44~50页;方一新,高列过:《从佛教词语考辨〈大方便佛报恩经〉的时代》,《浙江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139~147页。三国曹魏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提到金、银、琉璃、颇梨等七宝树,但有学者怀疑其译于刘宋时期。(10)吕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齐鲁书社,1980年,第5页。东吴支谦译《菩萨本缘经》中也提到金、银、琉璃、颇梨等,(11)〔吴〕支谦译:《菩萨本缘经》卷一,《大正藏》第3册,第57页下。但该经同样被怀疑是西晋以后所译。(12)颜洽茂,熊娟:《〈菩萨本缘经〉撰集者和译者之考辨》,《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55~63页。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至迟在东晋十六国时,“颇梨”等已经频繁出现在译经中。
大概自南北朝开始,“颇梨”出现在佛典以外的汉语世俗文献中。《海内十洲记》曾提及“碧颇黎”(13)《太平御览》卷八〇八,中华书局,1960年,第3592页。,该书题为西汉东方朔撰,但实际可能是后世假托。(14)参看吴从祥:《〈海内十洲记〉成书新探》,《广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第93~97页。《梁四公记》提到萧梁时“扶南大舶从西天竺国来,卖碧玻黎镜”(15)〔唐〕张说:《梁四公记》,收入李剑国辑校:《唐五代传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2015年,第268页。,该书为唐人所撰小说,不能断言其所述为史实还是传说。比较早的明确记载见于南梁萧绎《金楼子》,其中提到“齐郁林王,尝取武帝衣箱开之,有金射雉、玻瓈、贯纳等”(16)〔梁〕萧绎撰;许逸民校笺:《金楼子校笺》卷一《箴戒篇》,中华书局,2011年,第343页。。另外,北齐魏收《魏书》提到,波斯国多颇梨。(17)《魏书》卷一〇二《波斯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27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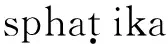
比较而言,当以印度语源说最为可信。究其原因有三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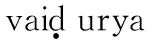



至于日下出火的说法,结合“白珠”“火珠”的译法,推测主要是因为“玻璃”雕琢成珠后,可以聚光生火。据《十诵律》记载,佛在世时,曾有一比丘以颇梨珠生火,为贼所见,误以为是珍宝而欲夺之,遂杀死比丘。佛陀知道此事后,规定比丘“从今不得畜月珠、日珠”(30)〔后秦〕弗若多罗译:《十诵律》卷三八,《大正藏》第23册,第278页中。。由此可知,印度古人很早就已经以“玻璃珠”作为生火器具了。
关于“玻璃”,印度古人的另一个奇妙看法是它生于山中,原为冰块。约生活于3世纪的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中就提到,颇梨珠出山窟中,是千岁冰化成。(31)〔天竺〕龙树菩萨造,〔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十,《大正藏》第25册,第134页上。又,鲍威尔所获梵语写卷中提到“雪山上的玻璃”,雪山即喜马拉雅山,古代印度人认为此山中出“玻璃”,很可能是因为喜马拉雅山终年冰雪覆盖。无独有偶,古罗马学者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也称,水晶是一种冰,出产于冬雪彻冻之地,因此不能用来盛装热饮。(32)D.E.Eichholz trans.,Pliny:Natural History,Vol.X,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p.181.考虑到古代罗马与印度存在密切的宝石贸易,老普林尼曾宣称,来自印度的水晶最受欢迎,所以两地之间“冰化为水晶”的说法,很可能是相互影响。
大概受《大智度论》等汉译佛典影响,中国古人也纷纷承袭水精为冰化之说。唐代崔珏《水晶枕》云:“千年积雪万年冰,掌上初擎力不胜。”(33)《全唐诗》卷五九一,第6860页。南宋杨万里《水精脍》云:“上饶灵山无他灵,空山满腹著水精。炯然非石亦非玉,乃是阴崖绝壑千秋万岁之坚冰。”(34)〔宋〕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第二册,中华书局,2007年,第616页。元人伊世珍《琅嬛记》引《志奇》载:“贞观中冬月祁寒,韦维家池水彻底俱冻。至季春,水无停流,而此池凝结如故。使人凿之,干坚如石。维往谛视,皆水晶也。”(35)〔元〕伊世珍辑:《琅嬛记》卷上,收入《丛书集成新编》第87册,新文丰出版公司,2008年,第421页。
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音译“玻璃”或意译“水精”,都不是严格的矿物学概念。古人辨识宝石多凭外观、产地而非质地,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1.虽质地不同但外观相似者,皆有可能被视为一物。因此,古代文献中的“玻璃”“水精”或“水晶”,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石英水晶(rock crystal),可能还包括其他种类的宝石,甚至是某些外观与天然宝石相似的人造物。关于这一点,后文还会进一步论述。2.虽质地相同但因外观、产地等有异,反被视为不同物。比如对那些熟悉印度语言和文化的佛经传译者而言,“玻璃”即“水精”,但对很多中国古人而言,“玻璃”带有明显的异国情调,与“水精”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在一些汉文文献中,“玻璃”和“水精”有时会并列出现,如唐代温庭筠有词云“水精帘里颇黎枕”(36)《全唐诗》卷八九一,第10064页。,显然词人将二者视为相似但不同的宝石。
二 从无色水精到五色宝石
从水精、水玉、白珠、千年冰等说法来看,“玻璃”最初应该是白色或无色透明的。这从佛典的一些描述中也可以看出端倪,比如佛陀眉间白毫如颇梨色,“皎然大白”(37)〔刘宋〕沮渠京声译:《治禅病秘要法》卷下,《大正藏》第15册,第339页下。;雨水落下,生成水泡,“似颇梨珠”(38)〔北魏〕菩提流支译:《入楞伽经》卷三,《大正藏》第16册,第532页上。;修持禅观时,观人骨“白如颇梨色”(39)〔后秦〕鸠摩罗什译:《禅法秘要经》卷上,《大正藏》第15册,第244页中。,皎然白净。正因颇梨珠无色透明,若与其他颜色的珠子放在一起,便会映射后者的颜色,而使自身颜色改变。(40)〔后秦〕筏提摩多译:《释摩诃衍论》卷三,《大正藏》第32册,第622页下。遇青色即变得像蓝宝石,遇红色像琥珀,遇绿色像祖母绿,遇黄色则像黄金。(41)〔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大正藏》第30册,第718页下~719页上。可以说,白色或无色透明曾是玻璃的最大特点。
但是,后来“玻璃”却出现了青黄赤白紫等多种颜色,如《杂阿含经》描述世尊入火三昧,“出种种火光,青黄赤白红颇梨色”(42)〔刘宋〕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卷八,《大正藏》第2册,第50页中。;《新华严经论》也称颇梨“此宝有青黄赤白”(43)〔唐〕李通玄:《新华严经论》卷十五,《大正藏》第36册,第816页下。。而且,因为颜色变得丰富,有人开始怀疑“玻璃”并非“水精”,如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称“颇胝迦,梵语宝名也,正梵音云飒破置迦。古译云是水精,此说非也。虽类水精,乃有紫白红碧四色差别。莹净通明,宝中最上。红碧最珍,紫白其次。如好光明砂,净无瑕点。云是千年冰化作者,谬说也”(44)〔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大正藏》第54册,第330页中。。
实际上,“玻璃”之所以会由无色变为五色,是因为在印度本土出现了一种不太寻常的理论,认为“玻璃”是一个包含数种宝石在内的属。关于这种理论,在印度宝石书《阿加斯蒂玛塔》(Agastimata)中,收集了两种不同的说法:1.“玻璃”包括nilagandhika(红宝石)、gomedaka(黄宝石)、vaidurya(蓝宝石)、marakata(绿宝石)四种;(45)nilagandhika是蓝红宝石(blue ruby),因nila意为蓝色,因此这种红宝石可能偏紫色;gomedaka是牛脂(一说牛胆),大概是指微黄色的宝石;vaidurya即琉璃,佛典中常指青色宝石,也即蓝色;marakata通常是指祖母绿或绿色宝石。2.除钻石、珍珠和珊瑚外,其他8种主要宝石如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等都包含在“玻璃”内。(46)Finot Louis,Les laidaires indiens,pp.130~131.
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证明,印度古人将红黄蓝绿色宝石视为“玻璃”的看法,同样影响到了中国。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中曾出土过一件银罐,罐中清理出蓝、黄、红、绿色宝石16块,其中蓝者7块,为蓝宝石;红者2块,为紫宝石或红宝石;黄者1块,为黄精、黄玉、或黄色刚玉;绿者6块,为绿玛瑙或绿玉髓。(47)关于宝石的种类,说法不一,参见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第32页;韩建武:《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宝石玉器》,《收藏家》2001年第3期,第7~9页;林梅村:《唐武德二年罽宾国贡品考:兼论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原为大明宫琼林库皇家宝藏》,《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6期,第100页。由于在银罐盖内有墨书题记,称罐内所盛物品有“颇黎等十六段”,可知上述宝石在唐代被称为“颇黎”。(48)有学者认为,银罐所处蓝宝石与红宝石数量最多、价值最高,且二者皆属刚玉家族,因此罐盖墨书所谓“颇黎”仅指刚玉类宝石(李国忠:《“火珠”的宝石学成分探讨》,《宝石和宝石学杂志》2009年第4期,第48页)。但笔者认为,将红、蓝宝石归为刚玉,从而与其他宝石区分开来,是今人根据矿物学知识做出的判断,并不能指望古人有这种能力。很显然,唐人的观点与印度宝石书提到的“玻璃包含红黄蓝绿四种宝石”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前者必然是受了后者的影响。
根据文献记载,唐代曾有五个国家来献“玻璃”,包括:武德二年劫国“遣使贡宝带、金锁、颇梨、水精杯各一,颇梨四百九十枚,大者如枣,小者如酸枣”;(49)《通典》卷一九三“劫国”条,中华书局,1988年,第5277~5278页。贞观十七年拂菻王“遣使献赤玻璃、绿玻璃、石绿、金精等物” ;(50)《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四“大秦国”条,第3516页。高宗上元二年拔汗那王“献碧颇黎”、龟兹国献“颇黎”(51)吴玉贵撰:《唐书辑校》卷四,中华书局,2008年,第1068~1069页。原文为“龟兹王白素稽献金颇黎”,“金”字下疑有夺文,故其所献玻瓈不知颜色。;开元二十六年吐火罗国“遣使献红玻璃、碧玻璃、生马脑、生金精及质汗等药”(52)《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六“吐火罗”条,第3571页。。其中劫国、吐火罗和拔汗那三国邻近,皆以颇梨为贡品,且吐火罗国“其城北有颇黎山”,由此可以推测三国所在地区是“玻璃”的一处重要产地。
唐代吐火罗国在今阿富汗东北部、塔吉克斯坦南部,都城为阿缓城(今阿富汗昆都士附近)。这里自古至今一直是重要的宝石产地,其中最出名的是巴达赫尚(Badakhshan)出产的青金石和巴拉斯红宝石(balas ruby)。13世纪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途经该地时就曾提到:“此地出产珍贵宝石,其中一种名巴拉斯(balasci),非常美丽且很珍贵,因其产地而得名……国王只恩准官方开采,其他人不得私自到山中开采……这些宝石全部属于国王,它们或者被当作贡品献给其他大国的君主,或者被当作礼物赠送给其他国家的国王……在此境内还有一座山,此山出产的群青色青金石(azur),是世界上最好的青金石。”(53)A.C.Moule & Paul Pelliot,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London:George Routledge & Sons Limited,1938,pp.136-137.青金石一般为蓝色,有时含黄铁矿,会呈现出金星密布的效果,在古代又被称为金精。(54)章鸿钊:《石雅》,第14页。前文提到,金精与红玻璃同时出现在了唐代吐火罗国的贡品名单中,推测红玻璃即巴拉斯红宝石。由此可见,青金石和巴拉斯红宝石自唐代直至元代一直是当地的重要外交礼物。(55)关于巴达赫尚的红宝石,可参看王一丹:《巴达赫尚的红宝石》,载荣新江,朱玉麒主编:《丝绸之路新探索——考古、文献与学术史》,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143~157页。该文征引了丰富的阿拉伯和波斯史料,但略感遗憾的是,未注意到这几条唐代的史料,因此误以为中国古人对巴达赫尚红宝石的认识始于元代。
现在通常所说的红宝石(ruby)是指红色刚玉,但巴拉斯红宝石实际却是尖晶石(spinel)。由于红宝石与红色尖晶石颜色和光泽非常相似,在古代经常被混为一谈。比如世界著名的“铁木尔红宝石”(Timur Ruby)以及“黑王子红宝石”(Black Prince’s Ruby),过去一直被视为红宝石,直到近代才鉴定出是尖晶石,(56)张蓓莉主编:《系统宝石学》,地质出版社,2006年,第281页。而它们的产地很可能就是巴达赫尚地区。在唐代,西安何家村窖藏的红宝石被认为是“玻璃”,那么吐火罗的巴拉斯尖晶石自然也可能被认为是“玻璃”。
劫国即劫比舍也国,唐代又称罽宾国或迦毕试国,在吐火罗西南,都城即今阿富汗喀布尔北面的贝格拉姆(Bgram)遗址,而喀布尔东南的吉格达列克(Jegdalek)河谷就出产红宝石、蓝宝石和尖晶石,其开采历史至少已经七百多年。(57)罗索夫斯基著;曹俊臣译:《阿富汗的宝石矿床》,《地质地球化学》1981年第1期,第10~12页。拔汗那国在吐火罗国以北,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交界的费尔干纳盆地。盆地三面环山,南面突厥斯坦山脉(Turkestan ridge)上勘探有蓝宝石,(58)http://www.geoportal-kg.org/index.php/geology/mineral-resources/raw-materials恰与该国所献“碧颇黎”颜色相符,因为石之青美者曰“碧”,碧颇黎当为蓝色。龟兹国以今新疆库车绿洲为中心,全盛时还包括拜城县等周边地区,而拜城县恰好就有红宝石矿。(59)罗益清:《中国红宝石矿床》,《矿床地质》1996年第15期,第27页。
既然“玻璃”所指实物由水精扩展到红黄蓝绿宝石,那么该词就不再仅用来翻译印度俗语phaiha、巴利语phaika或梵语偶尔也用来翻译其他外来词汇。唐代中天竺摩揭陀国的僧怛多蘖多、波罗瞿那弥舍沙合撰《唐梵两语双对集》,将汉语词汇所对应的梵语词汇的读音用汉字写出来,其中汉语“红颇梨”对应的梵语词汇为“钵纳么罗〔引〕誐”,(60)〔天竺〕僧怛多蘖多,波罗瞿那弥舍沙:《唐梵两语双对集》,《大正藏》第54册,第1242页上。笔者以为即梵语padmarag,该词词意即红宝石(ruby)。(61)Raj Roop Tank,Indian Gemmology,Jaipur:Dulichand Kirtichand Tank,1971,p.1.此外,“玻璃”有时还会用来翻译梵语(62)〔日〕平川彰编:《佛教汉梵大辞典》,第820页。词意为岩石,在汉译佛经中常音译为“试罗”“尸罗”,或意译为璧玉(63)〔日〕平川彰编:《佛教汉梵大辞典》,第828页。、碧玉(64)〔日〕平川彰编:《佛教汉梵大辞典》,第891页。。如《大方广佛华严经疏》提到,“尸罗幢者应云试罗,此云美玉”(65)〔唐〕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十一,《大正藏》第35册,第580页中。;《一切经音义》:“若云试罗,此翻为玉,谓以玉为幢,名尸罗幢也。”(66)〔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一,《大正藏》第54册,第437页上。从被译为“碧玉”的角度看,该词之所以与玻璃产生联系,大概是因为碧玉与碧玻璃颜色一致。(67)梵语有时也会被译为“碧绿”(平川彰编:《佛教汉梵大辞典》,第891页),应该也是由于碧玻璃的缘故。
三 佛典中人造玻璃的名称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直至唐代“玻璃”仍然主要是指天然宝石,而非现代所说的人造玻璃。特别是在汉译佛典中,“玻璃”作为七宝之一,基本都是指宝石。至于人造玻璃,在汉唐时期则另有名称,如“迦遮”“(假)琉璃”“瑠琉”“水精”等。

但当“琉璃”一词传入中国后,却经常被借用来称呼人造玻璃。这样,梵语或巴利语佛典中的人造玻璃“kca”,在汉译佛经中除被音译为“迦遮”,也会被意译为“琉璃”。(74)〔日〕平川彰编:《佛教汉梵大辞典》,第821、828页。这就造成了一种困局:汉译佛经中的“琉璃”有时指天然宝石,有时指人造玻璃。为了对它们作出区分,译经者往往会将天然宝石称为“真琉璃”或使用比较完整的音译“吠琉璃耶”“毘琉璃”等,而人造玻璃则称为“假琉璃”或使用简略音译“琉璃”。如慧琳《一切经音义》释“琉璃”时提到,琉璃“青色宝也。有假有真,真者难得,出外国。假者即此国炼石作之,染为五色也。”(75)〔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八,《大正藏》第54册,第418页下。其中所谓假琉璃,乃炼石染色所成,为人造玻璃无疑。唐代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卷三四提到,吐罗难陀尼有一“琉璃杯”,被人借去使用,结果“手脱便破”。(76)〔唐〕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卷十七,《大正藏》第24册,第374页下。此事在该经卷十七也曾提及,称琉璃杯为“假琉璃器”,“用时堕地便破” 。(77)〔唐〕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卷十七,《大正藏》第24册,第283页上。从“假琉璃”的称呼及其易碎的特点来看,这应该是一件人造玻璃杯。
这样,在一些佛典中提到的迦遮与无价宝、迦遮与吠琉璃的对比,在另外一些佛典中就翻译成了琉璃与吠琉璃、假琉璃与真琉璃的比较:“譬如世间有琉璃珠似毘琉璃,有人见之谓毘琉璃,愚痴凡夫亦复如是”(78)〔北魏〕瞿昙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卷四,《大正藏》第17册,第23页上。,“譬如有人弃舍无价吠瑠璃宝,乃取假伪瑠璃之珠”(79)〔唐〕般若,牟尼室利译:《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卷八,《大正藏》第19册,第560页中。,“如假琉璃宝大聚,不及一真琉璃宝”(80)〔宋〕法贤译:《佛说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卷三,《大正藏》第8册,第684页中。。从文意来看,引文中所谓琉璃、伪琉璃、假琉璃应与迦遮一样,是价值低廉的人造玻璃,而毘琉璃、吠琉璃、真琉璃则是指珍贵的天然宝石。

四 从天然宝石到人造玻璃
从文献的记载来看,人造玻璃的名称在古代中国经历了从“琉璃”到“玻璃”的变化。宋代以前人造玻璃常被称为“琉璃”,宋代以后则渐渐流行使用“玻璃”“硝子”“料器”之名。时至今日,“玻璃”成为人造玻璃的专名,与宝石再无瓜葛。之所出现这样的变化,恐怕要从人造玻璃自身的特点讲起。
人造玻璃大约诞生于四千多年前的两河流域,从一出现就经常模仿天然宝石,因而常与宝石同名。最初人造玻璃经常模仿青金石或绿松石,呈现不透明的蓝色或绿色,因此阿卡德人(Akkadian)中分别称它们为“产自窑炉的人造青金石”和“产自山中的天然青金石”,(86)戴维·怀特豪斯著;杨安琪译:《玻璃艺术简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6年,第19页。同样,在古希腊和古埃及,人造玻璃和青金石也曾使用同一名称。(87)E.Marianne Stern,“Ancient Glass in a Philological Context”,Mnemosyne,60.3,2007,p.388.后来,人造玻璃的透明度提高,颜色变淡乃至无色,便又模仿宝石水晶,使用水晶的名字。罗马老普林尼就曾提到,他生活的年代人造玻璃黑色如黑曜石、白色如萤石、蓝色如蓝宝石或青金石、无色透明如水晶,其中最珍贵的是模拟水晶的人造玻璃,当时人们多以人造玻璃仿造水晶器皿。(88)D.E.Eichholz trans.,Pliny:Natural History,Vol.X,pp.157,185.

虽然汉魏人造玻璃多青色,并因此与青色宝石“琉璃”共名。但是,随着中外交流活动的加深,人造玻璃器物沿着丝绸之路持续输入,中国本土制作玻璃技术不断发展,人们很快就发现琉璃不只有青色。如唐代颜师古曾批评孟康琉璃为青色的说法:“《魏略》云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盖自然之物,采泽光润,踰于众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销冶石汁,加以众药,灌而为之,尤虚脆不贞,实非真物。”(93)《汉书》卷九六《罽宾国传》,第3885页。又,《魏书》提到北魏时有大月氏人来华,“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瑠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94)《魏书》卷一〇二《大月氏传》,第2275页。一般认为此处人工铸造而成的五色琉璃即人造玻璃,以人造玻璃为门窗等建筑构件,很早就出现在西方罗马等地。
在各色人造玻璃中,从东晋南北朝开始,无色透明的人造玻璃日益增多,它们有时被称为“白琉璃”,有时则与“水精”相混淆。如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到,“外国作水精椀,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今以此语俗人,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类。”(95)〔东晋〕葛洪著;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卷二,1985年,中华书局,第22页。由五种灰铸造而成水精椀,为人造玻璃无疑,可是却被人误以为是天然水精。这种混淆一直持续到了唐宋时期。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的银罐中,曾清理出无色透明的宝石水晶杯及人造玻璃碗各1件,而罐盖上墨书题记却称之为“琉璃杯椀各一”,(96)陕西历史博物馆等:《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14页。显然宝石水晶杯被唐人误以为是人造玻璃,因而也使用了“琉璃”之名。南宋赵葵《行营杂录》记载,刘贡父一日朝会,与出身军伍的两帅相邻,两帅传玩一水精茶盂,问曰“不知何物所成,莹洁如此”,贡父答“此乃多年老冰耳”(97)〔宋〕赵葵录:《行营杂录》,收入《丛书集成初编》第2868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4页。。考虑到宋代人造玻璃器皿的使用情况,所谓“水精茶盂”应该是一件人造玻璃茶杯。
从上述人造玻璃在古代中国被称为“琉璃”或“水精”的情况,可以推知“玻璃”如何与人造玻璃产生联系:一方面,“玻璃”最初是指无色透明的宝石,意译为“水精”,这就很容易与无色透明的人造玻璃混淆。特别是《行营杂录》中视人造玻璃杯为多年老冰的说法,无疑与宝石“玻璃”为千年冰的说法有关。另一方面,唐代以来“玻璃”除了用来指无色透明的“水精”,也用来指青黄赤白紫等彩色宝石,即所谓“五色玻璃”,这难免使人联想到“五色琉璃”。尤其是考虑到“玻璃”与“琉璃”本就字形相近,且皆属西来宝物,经常一起出现在佛典中,如今又皆为五色,自然很容易被混为一谈。比如唐代李商隐有诗曰:“五色玻璃白昼寒,当年佛教印旃檀”,清代冯浩注释时就引《魏书》之“五色瑠璃”,认为李诗所谓“玻璃”即“琉璃”。(98)李商隐撰;刘学锴,余恕诚著:《李商隐诗歌集解》附编诗《咏三学山》,中华书局,2004年,第2244页。可以说正是“琉璃”“水精”和“玻璃”之间互相关联的复杂关系,为人造玻璃名称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而进一步促进了这种转变的,则是釉陶制品的流行。大约自东晋南北朝起,“琉璃”一词除用来称呼宝石和人造玻璃外,偶尔还用来称呼釉陶类建筑构件等。如《南齐书》记述北魏宫殿,“正殿西又有祠屋,琉璃为瓦”(99)《魏书》卷五七《魏虏传》,第986页。。事实上,很多早期人造玻璃透明度不高甚至完全不透明,从外观看与釉陶差别不大。更重要的是,东晋南北朝时佛教盛行,佛典中频频提及佛、菩萨、权贵等人物的居所为琉璃所造。受此影响,釉陶类建筑被称为“琉璃”,也就不难理解了。由于宝石琉璃较为少见,因此古代中国世俗生活中所谓琉璃,大多是指人造玻璃或釉陶。
但是至宋元时期,人造玻璃的透明度已经大为提高,与釉陶外观差异明显,而且釉陶日渐流行,与人造玻璃分庭抗礼,二者继续共用“琉璃”一名越来越不现实,必须加以区分。(100)安家瑶:《玻璃器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3页。于是,“琉璃”逐渐变为釉陶制品的专名,而“玻璃”则被用来称呼人造玻璃。这种情况可以从宋代蔡绦《铁围山丛谈》中的一段记载窥得一斑:北宋政和四年(1114),宋徽宗检察奉宸库,“时于奉宸中得龙涎香二琉璃缶、玻瓈母二大篚。玻瓈母者,若今之铁滓,然块大小犹儿拳,人莫知其方。又岁久无籍,且不知其所从来。或云柴世宗显德间大食所贡,真庙朝物也。玻瓈母,诸珰以意用火煅而模写之,但能作珂子状,青红黄白随其色,而不克自必也。”(101)蔡绦撰;惠民,沈锡麟点校:《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1983年,第97页。引文所谓玻瓈母即人造玻璃块,加热后可制成各类器皿,而用来盛放香料的琉璃缶应即釉陶制品。
事实上,“玻璃”所指实物,从最初无色水精,到后来红、蓝宝石等,皆为“莹净通明”之物,这是“玻璃”一词给人的重要印象。正因如此,诗文中常以“玻璃”来形容江河泉池。当宋代以后,“琉璃”一词越来越多地用来称呼透明度不高的釉陶制品时,以清澈通透著称的“玻璃”,无疑更契合透明度不断提高的人造玻璃。而且,相较于“水精”等名称,宝石“玻璃”在古代中国社会出现频率很低,将其名称挪作他用不容易引起歧义。于是,“玻璃”就取代“琉璃”,成为人造玻璃的新名称,并延续至今天。
五 结论
自汉代佛教沿着丝绸之路入华,不仅在精神文化方面潜移默化,而且在物质文化方面也影响深远。本文以现代汉语中经常使用的“玻璃”为例,指出它们实际是印度俗语phaiha或巴利语phaika的音译,大约是三国或稍晚时伴随佛经的传译而来到中国,音译为“玻璃”“颇梨”“玻瓈”,意译为“水精”“水玉”“火珠”等。在印度,“玻璃”本是天然宝石,一般是指无色透明的水晶或其他相似矿物,有时也指青黄赤白绿等有色宝石,如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等。印度人对“玻璃”有很多奇思妙想,并以佛典为载体传入中国,渗透到古代汉语诗歌小说中。及至丝路贸易和交流极为繁盛的唐代,宝石“玻璃”的实物也纷沓而来,在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中留下了印记。
但是,宋代以来,“玻璃”逐渐与宝石脱离关系,而用来指人造物,也即今天的人造玻璃。人造玻璃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北宋以前多称呼为“琉璃”,该词同样是印度词汇的音译,在汉代丝路开辟之初就因贸易而输入中国,又因与“玻璃”同为佛教七宝,而频繁出现在汉译佛典中,成为古代文人史家的笔下常客。在印度,“琉璃”同样是天然宝石,入华后渐渐成为人造玻璃和釉陶的名称,当宋代釉陶盛行且与人造玻璃差异日趋明显,“琉璃”就发展为釉陶的专名,而人造玻璃转而使用“玻璃”称呼。
将天然宝石“玻璃”之名用于人造玻璃,一方面是因为二者外观相似,皆莹澈通透,容易混为一谈;另一方面恐怕也与丝路变迁及佛教交流的衰落有关。佛典汉译是印度宝石学知识在中国传播的重要途径,当宋代时印度本土的佛教早已式微,北宋虽然偶有佛经汉译,但影响有限。缺少了佛教这条纽带,宋代以来的中国人对“玻璃”“琉璃”这些词汇的认识,就与印度本土渐行渐远,最终完全华化。与此同时,伴随着大食人的兴起以及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兴盛,阿拉伯宝石学东渐。受此影响,原被称为“玻璃”的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等,在宋代以后便改用阿拉伯或波斯语的“剌”“雅鹘”“助木剌”等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