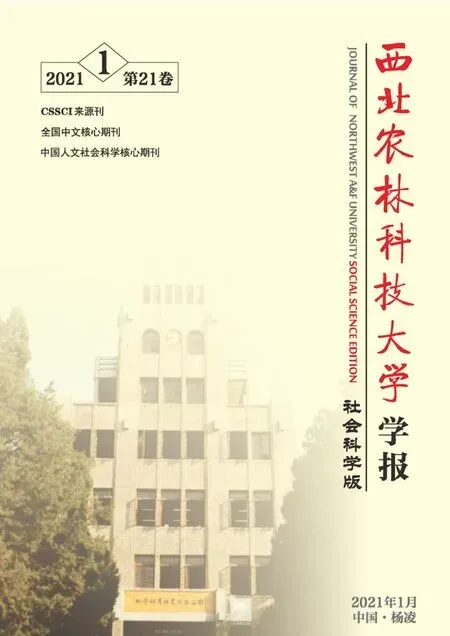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的激励效应
——兼论不同激励方式相对重要性
亓红帅 ,王 尧 ,王征兵*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2.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西安 710000)
引 言
村干部具有国家代理人与村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1],与政府、村民构成委托-代理关系,分别负责贯彻执行国家政策及行政任务,处理村庄公共事务,对政策执行力度、行政效能以及村民收入、公共品供给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具有重要作用[2-5]。目前,村干部实然角色并不能满足政府与村民期许,一些村干部消极应对、选择性执行、乱执行行政任务;还有一些村干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扮演着村政的撞钟者[6]、赢利型经纪人角色[7]。村干部实然角色反映了村干部激励明显不足。在基层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双重背景下,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健全激励村干部干事创业机制,村干部激励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村干部激励方式主要包括政府行政控制、村干部工资、村民自治制度三种形式[8]。作为村干部的委托人,政府通常通过限制性规则等行政程序与监督两种行政控制方式推动村干部执行行政命令。限制性规则规定村干部行政程序,约束村干部行政行为,对村干部的激励有限。政府监督试图通过各种上级检查、考核评比,即治理锦标赛的强监控-强激励模式,激励村干部承接行政任务[9]。然而过多过滥的政府检查使村干部疲于应付,削弱了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且行政成本较高,耗费大量资金与行政资源,只能保证重点任务的选择性执行[10-12]。村干部工资来源于县级财政与村集体收入,是政府与村民激励村干部的重要手段,裴志军利用CGSS数据发现薪酬决定主体与水平,决定村干部角色定位[13],王征兵、宁泽逵、郭斌等学者指出工资显著正向影响村干部工作积极性[14-16],而村集体收入匮乏使得村干部工资主要来源于县级财政,村干部工资水平低且为固定工资,低固定工资只能保证村干部低激励水平。作为村干部的另一委托人,村民主要借助村民自治制度激励村干部。村民自治制度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的正式制度安排,赋予村干部决策管理权力,满足村干部成就、权力、归属动机,具有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是激励村干部的主要方式。学者孙秀林利用6个省95个村庄微观调查数据,证明村庄民主促使村干部角色定位倾向于社区利益代言人[17],王征兵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规范化村治制度能明显提高村干部工作积极性[15]。然而目前村民自治主体虚置[18],村民自治制度实际运行水平较低[19],极大地制约了其激励效果。
村域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表征村庄社会基础优劣,决定着村民自治制度运行水平,因此提升村民自治制度激励效应的关键在于村域社会资本。村域社会资本具有价值生产能力,对人的激励、预期和行为产生显著影响[20],能有效发挥村庄声誉机制,进而提高村干部为村民服务的内在动机以及面子、声望等社会性收益。实地调查发现,低村域社会资本村庄,村干部留任意愿较低,甚至部分村庄无人愿意担任村干部。村域社会资本还可借助村庄紧密的社会网络有效识别村干部能力,传递村干部努力工作信息,规避村干部偷懒卸责行为,进而解决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田野观察发现,单姓小村往往具有紧密同质的社会网络,其村干部工作积极性往往高于其他村庄。由此可见,村域社会资本的激励规范、信息分享作用,能有效缓解村干部行政化、选择性执行等激励不足问题,是现有村干部激励方式的重要补充;相较于其他激励方式,村域社会资本具有稳固性、成本低、精准性的优势。
研究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的激励效应,对于解释村干部工作积极性与村域社会资本的关联现象,丰富集体社会资本理论与激励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已有研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为本文提供了研究基础与参考,但仍有以下不足:从研究内容上看,学者多关注政府控制、村干部工资、村民自治制度等正式制度的激励效应,关于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的激励效应研究也多从村域社会资本的某一维度进行剖析,村域社会资本激励村干部的作用机理研究有待深化,且不同激励方式的相对重要性有待拓展;从研究方法上看,村干部激励研究多以个案分析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相对较少;从研究数据上看,样本数据局限于某一县,代表性并不能得到充分保证,其研究结论在其他区域是否成立有待考察;从研究结论上看,村域社会资本可影响村民自治制度等变量,已有实证研究遗漏村域社会资本变量,将造成村民自治制度等变量的估计偏误,研究结论有待商榷。针对以上研究空白与局限,本文利用分层随机抽样调查,获取了陕西、河南、河北3省135个村383名村干部微观调查数据,剖析村域社会资本激励村干部的作用机理,使用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及各维度对村干部的激励效应,并考察不同村干部激励方式的相对重要性,为优化村干部激励机制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一、理论分析
(一)村域社会资本概念界定
学者将集体社会资本定义为群体社会联结、信任以及促成集体行动的群体结构方式[21]。该定义强调社会资本的集体性质,沿袭了普特南对社会资本信任、网络、规范的分析框架[22],并逐渐被广大学者认可。村域社会资本是一种特殊的集体社会资本。村民由于生活生产半径的重叠,具有共有治理的自治需求和共同的社会记忆,不得不重复互动博弈,在地缘、血缘以及亲缘的高度结合下,具有强烈的认同感、高度的信任和密集、同质、封闭的社会关联[23]。根据集体社会资本定义,借鉴已有村域社会资本相关文献[24-27],结合村庄社会的特征,学者将村域社会资本定义为促进村庄集体行动的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8]。村域认同指村民对村庄的认同程度,借鉴组织认同文献[28],主要包括村民归属感、村庄成员感以及志愿行为,是集体社会资本的群体结构方式,决定村庄价值生产能力水平[29]。村域信任指村民间的人际信任以及制度信任,人际信任指村民间的信任水平,制度信任指村民对自治制度、村干部的信任水平[30]。村域网络包括非正式村域网络与正式村域网络,描述村庄社会网络的结构属性,属于集体社会资本的群体社会联结。非正式村域网络指因血缘、地缘、亲缘等形成的村民社会网络;正式村域网络则指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村庄合作组织参与网络。
(二)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激励作用机理
村域社会资本通过内在动机驱动机制、村民合作机制、信息分享机制有效激励村干部(见图1)。内在动机驱动机制方面,村域社会资本可通过村庄共同愿景、社会记忆增强村干部成员感、归属感,形塑村干部利民偏好,建立村干部与村民的情感纽带,增强村干部的承诺,从而提高村干部为村民服务的内在动机[20];同时借助价值生产能力,增加村干部面子、声望等社会性收益[6],从而提高村干部受村民认可的内在动机;还可借助熟人社会的村域网络,有效识别村干部类型,提升村民选举机制的甄别能力,筛选出具有高内在动机的村干部。村干部内在动机则可有效提高村干部满意度,进而提高村干部留任意愿。

图1 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激励效应作用机理
村民合作机制方面,村域社会资本发挥价值生产功能,提高村民公共品自愿供给意愿,利用信息优势,限制村民搭便车等投机行为,提高村民信任预期,降低交易成本,增强村民集体行动能力,提高村民合作水平[30],吸纳政府支持,使得村干部更容易获得较高的工作成绩,满足村干部成就需要,进而增强村干部工作满意度与留任意愿。
信息分享机制方面,村域社会资本利用村域网络分享村干部工作的“闲言碎语”,村干部偷懒卸责等机会主义行为更容易被发现,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能够得到缓解,进而实现对村干部的问责和有效激励村干部[31]。
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村域社会资本及其各维度正向影响村干部留任意愿。
假设2:村域社会资本及其各维度正向影响村干部工作满意度。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为课题组2018年对陕西、河北、山东3个省份村干部的分层随机抽样调查,3个省跨越东中西3个区域,具有一定的区域代表性。根据县级经济发展水平,分别在3个省份各随机选取3个县,并在每个县随机抽取15个村,每个村抽取2~6名村干部(本文村干部仅限于村支部、村委会、监委会成员)。剔除无效样本后,最终获取3个省9个县135个村383份问卷,问卷有效率为95.75%。
(二)村域社会资本测度
根据上文对村域社会资本的界定,使用已有研究开发的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的村域社会资本量表[8],将村域社会资本分为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3个维度(见表1)。村域认同主要包括村庄归属感、村庄成员感以及志愿行为。村域信任主要包括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其中制度信任分为村民自治制度信任与村干部信任。村域网络主要包括正式村域网络与非正式村域网络。村域社会资本属于村级变量,其各题项数值由各村村干部原始调查数据加总平均获得。经检验得知,Cronbach’s α 系数为0.805,调研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KMO值为0.767,Bartlett球形检验和LR检验值达到0.05显著水平,调查数据适合因子分析;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获取3个公共因子,3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0.741,较好地解释了村域社会资本各指标信息。此外根据斜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将3个公共因子分别命名为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其与理论预设相符,村域社会资本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综上所述,村域社会资本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使用因子得分法分别得出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3个因子的具体水平,将因子方差贡献率占累积方差贡献率的百分比作为权重,综合3个因子求得因子总得分,得到村域社会资本总体水平。

表1 村域社会资本量表
(三)因变量与其他激励方式变量测度
本文因变量为村干部激励强度,借鉴已有学者研究[14-15],使用留任意愿、工作满意度进行表征,赋值方式见表2。工作满意度的测量主要有单一整体评估法以及综合评价法,学者指出两种方法同样有效,本文使用单一整体评估法[32]。调查数据显示,村干部留任意愿平均为3.258,村干部留任意愿一般,村干部工作满意度平均为3.543,村干部工作满意度相对较高,总体来看村干部激励强度有待提高。
村干部其他激励方式主要包括政府行政控制、村干部工资、村民自治制度。政府行政控制方面,政府检查次数反映了政府对村干部的监督水平,是政府行政控制的主要方式,因此选为政府行政控制的代理变量。选取村干部实际工资表征村干部工资,为便于回归结果的分析,将该变量单位转变为万元。随着国家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强制推行,村民代表会议作为村民自治的最高权力,其开展次数表征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行水平,因此借鉴孙秀林、Oi等的做法[17,33],使用村民代表会议次数表征村民自治制度运行水平。
(四)其他变量设置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村庄特征变量、个体特征变量以及省份虚拟变量,具体设置方式(见表2)。村庄特征变量方面,选取总户数、村干部人数、人均纯收入作为控制变量。村干部人数增加可能减少每个村干部工作量,进而可能正向影响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户数表征村庄规模,村庄规模增加可能导致工作量增加,工作满意度与留任意愿降低。人均纯收入代表村民收入,往往表征村干部任职的机会成本,因此人均纯收入减少可能负向影响村干部工作满意度、留任意愿。村干部个体特征方面,选取常见的人口特征学变量衡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年限。村主任、村支书、监委会主任作为一把手,具有更高的权力与成就感,因此可能正向影响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选取村干部职位作为控制变量。村干部任职时间越长,越愿意留任,越可能有更高的满意度,因此选为控制变量。此外,选取省份虚拟变量控制不可观测异质性。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模型与结果分析
(一)实证模型选取
1.Bioprobit模型。Bioprobit由Li和Tobias提出,类似于二元Probit模型,是有序Probit模型的扩展,模型使用最大似然法估计。当回归方程误差相关时,相对于分别估计,使用Bioprobit进行联立估计,具有更小的标准误,联立估计更加有效[34]。模型设置如下:

… …
2.相对重要性分析。相对重要性分析由Isareli[35]提出,利用不同解释变量对决定系数R2的贡献程度,旨在探究不同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相对重要性。Isareli考虑解释变量的相关性,以变量对R2的边际效用衡量解释变量的贡献。具体来言,解释变量Xk对R2的边际效用可以表示为:
其中,S是不包含变量Xk的其他解释变量。去掉某个解释变量后,回归系数通常会变化,估计系数以*表示。另外,变量Xk被剔除顺序不同,对R2的边际效用有所不同。为此,使用J!种剔除方式获得的估计结果的平均值,作为变量Xk的相对重要性指标RI。
(二)实证结果分析
1.回归结果分析。村干部激励回归结果见表3,模型1为基准模型,模型2加入控制变量考察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留任意愿以及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模型3考察村域社会资本3个维度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对村干部留任意愿以及工作满意度的影响。3个模型对数似然值显示模型拟合较好。分别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得知模型均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为防止异方差导致的估计失效,模型均使用稳健估计。3个模型athrho值显示留任意愿、工作满意度回归方程的随机扰动项非常相关,另外Wald检验非常显著,说明使用Bioprobit联合估计比单独估计更好。

表3 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激励回归模型结果
模型1回归结果与模型2回归结果均显示,在1%显著水平下,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留任意愿、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村域社会资本越高,村干部留任意愿越强,工作满意度越高,村干部工作积极性越高。实证结果与研究假说一致。模型3回归结果显示,在1%显著水平下,村域认同对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村域认同越高,村干部越愿意留任,工作满意度越高,村域认同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在5%显著水平下,村域信任对村干部留任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村域信任越高,村干部留任意愿越高;村域信任对村干部工作满意度影响为正,但不显著。根据模型3村域认同、村域信任回归系数,村域认同激励效应高于村域信任。村域网络对村干部留任意愿、工作满意度影响不显著,原因在于,较高的村域网络可能意味着村庄存在家族势力与派系斗争,阻碍村干部开展工作,进而负面影响其工作满意度与留任意愿。总体来言,村域社会资本正向影响村干部留任意愿以及工作满意度,是村干部激励的有效方式。
其他激励方式变量方面,政府检查对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原因在于政府检查次数越高,村干部需要承担的政务越多,村干部疲于应付检查,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降低,因此该激励方式应慎重使用。与王征兵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15],工资对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换言之,较高的工资能提高村干部工作积极性。村民代表会议次数对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原因在于村民代表会议次数越多,村民自治制度水平越高,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村干部偷懒卸责受到约束,村庄集体行动水平提高,村干部成就感、声誉与同事关系满意度越高,因此工作满意度与留任意愿越高。以上结论表明村民自治制度对村干部具有激励作用,与已有研究结论相符[14-15,17]。
控制变量方面,模型1和模型2控制变量结果大致相同,以模型1回归结果为准。村干部人数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原因在于村干部人数越多,每个村干部平均分担的任务减少,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越高。是否一把手对村干部留任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原因在于一把手具有更高的权力以及成就感,留任意愿更高。任职时间对村干部留任意愿、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任职时间越长,村干部越熟悉工作,工作满意度和留任意愿越高。省份虚拟变量回归结果表明,相对于河北,河南省留任意愿更低,与田野调查相符。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两种方法进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4。第一种方法,改变变量的测度方式,如模型1与模型2所示。上文村域社会资本及其各维度通过因子得分法获得,此处则通过计算各指标的均值获得村域社会资本以及各维度的具体数值。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具体而言,村域社会资本为量表所有指标的均值,村域认同为村庄归属感、村庄成员感、志愿主义题项的均值,村域信任为人际信任、村干部信任、自治制度信任题项的均值,村域网络为正式网络与非正式网络题项的均值。如模型1和模型2所示,村域社会资本、村域认同与村域信任对留任意愿、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村域网络对村干部留任意愿、工作满意度影响不显著,回归结论与上文一致。第二种方法,改变回归模型,使用Oprobit模型分别估计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模型,如模型3与模型4所示,模型结果与上文回归结果一致。通过两种稳健性检验方法发现,研究结论非常稳健。
(四)不同激励方式相对重要性分析
为便于分析,本文借鉴连玉君做法[36],不仅使用了相对重要性RI值以及指标排名,还使用了Krasikova等人标准化了的RI值[37]。具体来说,计算各变量的RI与RI总数之比,作为标准化贡献程度。这个标准的优点是使所有解释变量标准化程度贡献总和等于1,变量间相对重要性容易比较。相对重要性结果如表5所示,影响村干部留任意愿的各个变量相对重要性排序为村民自治制度>村域社会资本>工资>政府检查,RI值分别为0.051、0.036、0.034和0.003,变量对拟合优度R2的边际贡献为40.92%、29.19%、27.61%和2.28%。影响村干部工作满意度的各个变量相对重要性排序为村域社会资本>村民自治制度>工资>政府检查,RI值分别为0.034、0.030、0.016和0.003,变量对拟合优度R2的边际贡献为41.15%、35.42%、19.37%和4.05%。以上相对重要性分析表明,村域社会资本与村民自治制度是村干部激励最重要的两种方式,政府检查相对重要性最低。

表5 不同激励方式相对重要性分析结果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基于陕西、河南、河北3省135个村村干部调查数据,使用Bio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村域社会资本及其各维度对村干部留任意愿、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剖析了村域社会资本激励村干部的作用机理,比较了不同激励方式的相对重要性。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分别为3.258、3.543,村干部留任意愿、工作满意度水平较为一般,村干部激励强度有待提升。(2)村域社会资本通过内在动机驱动机制、村民合作机制、信息分享机制激励村干部。实证结果表明,村域社会资本正向影响村干部留任意愿、工作满意度,即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有显著的激励效应。(3)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正向影响村干部留任意愿和工作满意度,村域认同的激励效应高于村域信任;村域网络对村干部留任意愿和工作满意度影响不显著,即村域网络的激励效应不明显。(4)相对重要性分析结果表明,村域社会资本、村民自治制度、工资、政府检查对村干部留任意愿模型R2的边际贡献分别为29.19%、40.92%、27.61%和2.28%,对村干部工作满意度模型R2的边际贡献分别为41.15%、35.42%、19.37%和4.05%。村域社会资本与村民自治制度是村干部激励最重要的两种方式,工资激励贡献度次之,政府检查激励贡献度最低。
以上研究结论得出以下政策启示:(1)基层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双重背景下,目前政府过多检查、低固定工资制以及村民自治制度低效导致的村干部激励不足问题亟待解决,亟需提升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激励村干部干事创业。(2)政府控制成本较高、可持续性差,只能保证部分行政任务的强激励水平,政府检查负向激励村干部,因此,应谨慎使用该激励方式。(3)村干部工作目标的模糊性、多维任务关联性、工作效果的滞后性以及工作绩效的外生性使得固定工资制成为最优契约安排,不可随意将由固定工资制转变为绩效工资制,且应根据县级财政、村庄集体收入实际情况确定村干部工资水平,减少不必要的开支。(4)村民自治制度低效运行制约了村干部工作积极性,应着力提升村民自治制度运行水平,发挥其低成本、高效率优势。由于提升村民自治水平难度较大,因此,应着力提高村域社会资本。(5)村域社会资本作为德治的重要内容,借助激励规范、信息分享作用,能有效激励村干部;相较于其他激励方式,具有持久性、低成本、精准性优势,是现有村干部激励方式的有效补充。因此,有必要将村域社会资本视为一种有效的治理手段,积极培育和利用村域社会资本,增强村域认同和村域信任,正确引导村域网络,缓解其他激励方式的激励钝性,加快德治与自治的有机融合,协同激励村干部担当作为,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振兴。